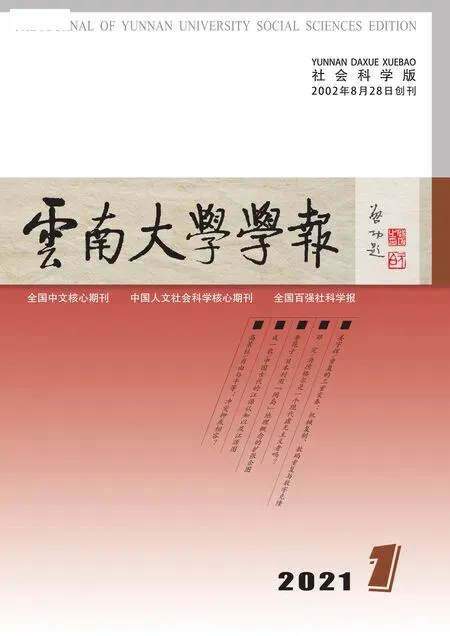中国古代的江源认知以及江源图
成一农,丰 瑾
[云南大学,昆明 650091]
与对黄河“河源”的认知不同,(1)关于中国古代的“河源”认知,参见成一农:《中国古代的河源图研究——基于知识史的一些解读》,《学术研究》2020年第6期,第109页。中国古代对于长江的源头,即“江源”的认知并不存在太大的争议,《禹贡》所记载的“岷山导江”说基本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近代以来,研究者认为直至明代后期,徐霞客才首次提出了金沙江应是“江源”的说法,由于这一观点接近于现代人对江源的认知,因此徐霞客的这一贡献受到了学界的一再褒扬。
本文首先对中国古代文献和地图中的“江源”认知进行了分析,并试图对徐霞客的这一贡献重新进行定位;然后将“江源”认知放置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进行分析,而不是像以往的研究那样将这一问题放置在现代“科学”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并由此希望对如何看待传统文化提出一些新的认知。
一、中国古代的江源认知
儒家经典《禹贡》中对于“长江”的流经有着简明的记载,即“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迆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由此,在中国古代,通常认为长江发源于“岷山”,如《水经注》“岷山,在蜀郡氐道县,大江所出”(2)〔北魏〕郦道元撰,〔清〕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段仲熙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卷三十三“江水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733页。等。不过,对于“岷山”的具体位置,则有着不同的认知,如齐召南《水道提纲》卷八“江上·自岷源至会金沙江于叙州府”中就提到:“大江源出岷山,山自边外地,绵数千里,《禹贡》‘导江之岷山’,亦曰汶山,今四川松潘卫西北也。又有北源岷山,在陕西岷州卫;南源又有二岷山,一在茂州,一在灌县,皆不如。”(3)〔清〕齐召南:《水道提纲》卷八“江上·自岷源至会金沙江于叙州府”,《故宫珍本丛刊》第234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40页。不过通常都认为“岷山导江”的岷山在四川松潘卫西北。(4)除了文献之外,后文引用的地图也能证明这一点。
到了近代,丁文江在《徐霞客先生宏祖年谱》中抄录了徐霞客的《溯江源考》,并提出徐霞客最早提出金沙江才是长江的源头,即“知金沙江为扬子江上游,自先生始,亦即先生地理上最重要之发见也。惜无继先生而起者,为之宣传……先生言江之发源,不详尽,仅言出犁牛石,经石门关,按石门关在丽江西五十里石鼓里之东,亦非由丽江入藏之大路,《江源考》亦不言及巴塘,似足为先生未尝入藏边之旁证”。(5)丁文江:《徐霞客先生宏祖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58页。
从徐霞客《溯江源考》的文字来看,确实徐霞客主张岷江并不是长江的源头,即“第见《禹贡》‘岷山导江’之文,遂以江源归之,而不知禹之导,乃其为害中国之始,非其滥觞发脉之始也。导河自积石,而河源不始于积石;导江自岷山,而江源亦不出于岷山。岷流入江而未始为江源,正如渭流入河,而未始为河源也”。(6)〔明〕徐弘祖:《江源考》,转引自丁文江《明徐霞客先生宏祖年谱》,第57页。而且确实明确提出金沙江为江源,即“岷流之南,又有大渡河,西自吐蕃,经黎雅与岷江合,在金沙江西北,其源亦长于岷,而不及金沙,故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7)同上。
但在1942年,谭其骧在其《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发现》一文中则对丁文江的这一认知提出了异议,大致而言,即认为实际上早在徐霞客之前,中国古人就已经知道金沙江源流的大致情况,如《水经注》以及《天下郡国利病书》所引前人《金沙江源流》《明史·地理志》等,因此金沙江的长度要超出岷江在当时应当是一种常识。不过,谭其骧并未彻底否定徐霞客的贡献,在文末最终的评价为“霞客所知前人无不知之,然而前人终无以金沙为江源者,以岷山导江为圣经之文,不敢轻言改易耳。霞客以真理驳圣经,敢言前人所不敢言,其正名之功,诚有足多,若云发见,则不知其可”。(8)谭其骧:《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发现》,《长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38页。谭其骧的这一评价比较中肯,但后来一些徐霞客的研究者对此依然存在一些异议,(9)如朱亚宗《徐霞客是长江正源的发现者——谭其骧对丁文江辨正之辨正》,《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2期,第182页。这与此处论述的问题无关,不再赘述。
丁文江提到的《徐霞客先生宏祖年谱》“知金沙江为扬子江上游,自先生始,亦即先生地理上最重要之发见也。惜无继先生而起者,为之宣传”是存在问题的。明代晚期和清代支持徐霞客这一认知的人还是存在的,如钱谦益在其所作《徐霞客传》中就提到:“客以《溯江纪源》一篇寓余,言《禹贡》‘岷山导江’,乃泛滥中国之始,非发源也。中国入河之水,为省五;入江之水,为省十一。计其吐纳,江倍于河。按其发源,河自昆仑之北,江亦自昆仑之南,非江源短而河源长也。又辨三龙大势,北龙夹河之北,南龙抱江之南,中龙中界之,特短;北龙只南向半支入中国,惟南龙磅礴半宇内,其脉亦发于昆仑,与金沙江相并南下,环滇池以达五岭。龙长则源脉亦长,江之所以大于河也。其书数万言,皆《桑经》《郦注》及汉、宋诸儒疏解《禹贡》所未及。”(10)引自胡渭:《禹贡锥指》卷十四下“附论江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69页。虽然没有对徐霞客的观点直接表明态度,但从“皆《桑经》《郦注》及汉、宋诸儒疏解《禹贡》所未及”一句来看,对其观点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不仅如此,《图书编》卷五十八“江源总论”实际上持以这样的认知,即:
水必有源,而源必有远近、小大不同,或远近各有源也,则必主夫远;或远近不甚相悬,而有大小之殊也,则必主夫大;纵使近大远微,而源远流长,犹必以远为主也,况近者微、远者大,乃主近而遗远,岂知源之论哉!……谓江水出岷山东南,至天彭山……又东过涪州、忠州、万州,言中国之江水,信得其源矣。然岷山在今茂州汶山县,发源不一而亦甚微,所谓发源滥觞者也。及阅《云南志》,则谓金沙江之源出于吐蕃异域,南流渐广,至于武定之金沙巡司,经丽鹤庆,又东过四州之会州建昌等卫,以达于马湖叙南,然后合于大江,趋于荆吴。又《缅甸宣慰司志》谓其地势广衍,有金沙江阔五里余,水势甚盛,缅人恃以为险。夫以缅甸较之茂州,其远近为何?如以汶山县之发源甚微者,较之缅甸阔五里余者,其大小又何如?况金沙江源出于吐蕃,则其远且大也明矣!何为言江源者止于蜀之岷山,而不及吐蕃之犁石?是舍夫远且大者,主夫近且微者。以是论江之源,吾不知也……或曰,水必发源于山,昆仑乃山之最高广者,岷山亦高山也,江源何为不祖岷山,而祖犁石?即曰,星宿海有泉百余窦,从平地泡出,非山也。何独疑犁石未必非高山乎?安知今之主江源于岷山者,无异昔之主河源于昆仑乎?唐刘元鼎所探河源,自以为过汉张骞矣。安知今之所谓江源出吐番犁石者,非唐之刘元鼎,而尚未得夫星宿海乎?姑即江水来自西番者,以俟真知江源之君子云。(11)《图书编》卷五十八“江源总论”,四库全书版。
《图书编》为章潢所编,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由其门人付梓成书,其时间应当早于徐霞客撰写《溯江源考》,且《图书编》所收大部分为前人著述,因此其中的“江源总论”有可能时间更早。由此,不仅正如谭其骧所说,金沙江的长度要超出岷江在中国古代应当是一种常识,而且在徐霞客之前就已经有人认为江源不在岷山,而是源自“西番”的金沙江,甚至具体指明了是在“犁石”。
无论这一认知最早的提出者是谁,这一认知在当时还是有着一定影响力的,甚至乾隆也对其进行了评价,如在《御制诗集》三集卷九十三中就提到:“按《禹贡》有岷山导江之文,厥后《桑经》《郦注》及汉宋诸儒并云江出岷山,其源不越益州之境,此皆囿于内地见闻所及,非探本之论。惟胡渭著《禹贡锥指》引明徐宏祖传,称其平生好远游,出玉门关至昆仑山,去中夏三万余里,尝作《溯江纪源》一篇,以岷山导江,特泛滥中国之始,按其发源则河自昆仑之北,江亦自昆仑之南,非江源短而河源长也。其说实得之目击,渭乃以其所经里数吹毛索瘢,殊为过当。夫昆仑即今所谓刚底斯,为群山祖脉,其水四方分流,然则大江之雄长四渎,不徒恃源于西蜀之眉州,义复何疑?但谓江源出天汉,则史家不无穿凿之说耳。”乾隆所持的观点也有着旁证,徐文靖《管城硕记》卷四:“按《溯江纪源》曰,《禹贡》岷山导江,特氾滥中国之始,按其发源,河自昆仑之北,江亦自昆仑之南。其龙脉与金沙江相并南下,环滇池以达五岭,江之所以大于河也。然亦志得其梗概,多略而不详。我圣祖谕阁部诸臣曰:‘岷江之源出黄河西巴颜喀拉岭察七尔哈纳,番名岷捏撮。《汉书》,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是也。《禹贡》导江之处在今四川黄胜关外乃楮山。古人谓江源与河源相近,《禹贡》岷山导江乃引其流,斯言实有可据,自黄胜关瀺灂而入至灌县,分数十道,至新津县复为一,东南行至叙州,金沙江自马湖来合之。金沙江之源自达拉喇嘛东北……迤逦诸土司界入蜀,合岷江出三峡,入楚’,天语煌煌,地理、河渠瞭然指掌……”(12)〔清〕徐文靖:《管城硕记》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71页。
不过,在明清时期,反对这样认知的依然不少,如全祖望的《江源辨》:“河源远而江源近,江源之不始于岷山,犹河源之不始于积石,昔人所同辞也。虽然谓不始于岷山则可,离岷山以求江源则不可。自明崇祯间,江阴徐霞客谓河源在昆仑之北,江源在昆仑之阳。常熟钱氏为作传,盛称其言。而吾乡万处士季野,已力辨以为妄……愚最取范石湖之说,以为大江自西戎来,自岷山出。举其大略,而不必确求所证于大荒之外。盖河山两戒,南纪以岷山嶓冢,负地络之阳为越门。北纪以三危积石,负地络之阴为胡门。而河源、江源,并在极西。以其九州之表,故《禹贡》略而不书。必指其地以实之,恐如宋孝宗之所以诮程泰之者矣。侍郎之学,淹贯古今,方今人物,愚所首推。而《江源考》失之好奇,故不敢不辨。”(13)〔清〕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第四十八卷“江源辨”,《清代诗文集汇编》30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41页。此外,胡渭在《禹贡锥指》中介绍了徐霞客的观点之后,也对其这一认知进行了反驳:“古书言昆仑者非一处……夫汉之昆仑在于阗,元之昆仑在吐蕃,相距可四五千里,而霞客乃浑而一之,其不学无识一至此乎?余谓霞客所言东西南北,茫然无辨,恐未必身历其地,徒恃其善走,大言以欺人耳,非但不学无识也。人皆以为能补《桑经》《郦注》,及汉宋诸儒疏解《禹贡》所未及,过矣。或曰:僧宗泐云,黄河出西番抹必力赤巴山,东北流为河源,西南流为牦牛河。牦牛河即丽水,一名金沙江者,自丽江府界,东北流,合若水为泸水,又东北至叙州府,而注于江。霞客言江源自昆仑之南,殆谓此耳。然抹必力赤巴非昆仑也。且岷山导江,经有明文,其可以丽水为正源乎?霞客不足道,牧斋一带巨公,文采炫耀,最易动人,故吾特为之辨。”(14)〔清〕胡渭:《禹贡锥指》卷十四下“附论江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69页。
大致而言,在清末之前,文本文献中对于江源大致有两种认知,一种遵循《禹贡》的记载,认为是发源于岷山的岷江;一种认为金沙江才是长江的正源,而其发源于“西番”。此外,也有一些调和之说,如认为长江虽然发源于岷山,但这只是长江流入“九州”之处,其源头应当在更西的“九州”之外,但难以确知其地。
二、中国古代地图中的江源
我们再看中国历代地图中对江源的描绘。与存在一些以“河源”为主题的地图不同,中国古代没有留存下来以“江源”为主题的地图,但在现存数量众多的“全国总图”中都标绘有江源。下面对此进行简要介绍。
宋代《禹迹图》中,在成都西北标绘了“岷山”,在“岷山”西北标绘了“大江源”,亦即大致将“岷山”作为江源,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图中还绘出了一条发源于大渡河以西经行云南以北最终注入“大江”的“若水”,其河道长度要长于发源于“大江源”的河道。
《华夷图》中虽然没有标注“江源”和“岷山”,但在位于成都、永康西北,威州以西处的长江一支河道的尽头上标注了“长江”,这应当代表地图绘制者认为长江的这一支应当就是“江源”所在。不过,该图同样还绘出了一条发源于恭州以西,流经云南以北最终注入“大江”的河道,其长度要远远长于标注有“大江”的河道。与《华夷图》存在源流关系的《历代地理指掌图》中《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15)参见成一农《浅析〈华夷图〉与〈历代地理指掌图〉中〈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之间的关系》,《文津学志》第六辑,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156页。也是如此,《历代地理指掌图》中的大部分地图也是如此。
《佛祖统纪》中的《东震旦地理图》,虽然没有标注“江源”,但图中长江被绘制为发源于“岷山”之下,且没有绘制更往西的其他的河道。
《六经图》中《禹贡随山浚川图》在“岷山”下标绘了“江源”,且没有绘制更往西的其他的河道。需要提及的是,这幅地图在一些清代的著作中依然被引用。
在为数不多的留存下来的元代地图中,胡一桂的《诗集传附录纂疏》中《十五国都地理之图》虽然没有标绘“江源”,但在岷山以东的长江河道的末端标注了“江”字,由此显示绘制者可能将“岷山”作为“江源”,此后的“十五国风”系列地图基本也是如此。(16)对于这一系列地图的研究,参见成一农《“十五国风”系列地图研究》,《安徽史学》2017年第5期,第18页。元代黄镇成的《尚书通考》中《禹贡九州水土之图》则直接在岷山以北标注了“长江源”。
明代《杨子器跋舆地图》中虽然没有绘制“岷山”,但在威州东北标绘了“大江源”,此外还在黎州安抚司以北标绘了“大渡河源”,在“星宿海”右侧标绘了“澜沧江源”,由于图中从这些“源头”发源的水流最终都流入了长江,因此,从图中的这种标绘方式来看,其所呈现的依然是传统的江源“岷山”说。
现存下来的明代中后期的“全国总图”基本是以《广舆图叙》的《大明一统图》、《大明一统志》的《大明一统之图》和《广舆图》的《舆地总图》为底图绘制的。其中《广舆图叙》的《大明一统图》谱系的“三大干龙”子类的地图,在“岷山”标绘了“江源”;在“二十八宿”子类的地图中,虽然没有标绘“岷山”,但将“江源”标绘在了成都西北不远处;“舆地总图”子类的地图中,则将“江源”标绘在了成都以北和岷州以东。《大明一统志》的《大明一统之图》谱系的地图,虽然没有明确标注“江源”,但图中长江发源于四川境内的一座山峰之下,显然其呈现的也是长江发源于岷山的观点。《广舆图》的《舆地总图》谱系中的地图,虽然没有标注“岷山”,但一些地图将“江源”标注在了成都西北,尤其是受到《广舆图》万历刻本影响的地图,由此显示这些地图所认知的“江源”,应当源自“岷山”。
此外,明末吴惟顺的《兵镜》的《二十八宿分野图》中所呈现的也是“岷山导江”说。(17)以上地图参见成一农:《中国古代舆地图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在清代中晚期流传甚广的《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谱系也是如此。如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嘉庆年间的《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以及嘉庆十六年的《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将“大江源”标绘在了“岷山”之下,虽然其还绘制出了发源于西藏的众多长江的支流,且在“乌斯藏”右上角“礼塘”标注“阿六江下流入金沙江”。甚至在清末民初出版的杨守敬的《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中也持这一观点。
总体而言,与文本文献不同,在中国传统舆图中基本呈现的就是“岷山导江”说,亦即将“江源”定在了岷山或者岷山附近,而几乎没有对江源的其他认知,且徐霞客的观点在明代后期的地图上也基本没有得到展现。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其中一些地图明确描绘了河道更为源远流长的金沙江。
三、结 论
通过上文的介绍可以看出,无论从传世的舆图还是文献来看,确实中国古人很早就知道在长江上游的诸多河道中,就长度而言,金沙江的河道是要远远长于岷江的,但就目前所见,大致到了明代才有人对江源“岷山”说提出疑义,且徐霞客并不是最早者。虽然这一认知在明清时期有着一定的支持者,但并没有动摇传统的长江源自岷山的观点。由此也就产生了一个现代人难以理解的问题,即中国古人很早就知道金沙江的河道要远远长于岷江,甚至那些支持传统的长江源自岷山的人也是如此,但为什么如此众多学者还坚持长江源自岷江呢?
在思考这一古代的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先考虑一下现代的问题。实际上截至现代时期,对于确定河流正源的标准依然存在争议,由此,也使得对于一些河流的正源存在争议,长江也是如此。孙仲明等人在《我国对长江江源认识的历史过程》一文中就谈到:“由于到目前为止,国际上还没有一种公认的划分河源的准则,所以在具体划分时,往往会出现不同的看法,这是很自然的。河源划分的依据颇为复杂,既要考虑到它的自然因素,又要顾及历史上的传统习惯。在自然因素中,除了长度、水量以外,还要考虑到流域面积、水系平面位置、方向、上下游的一致性、河谷地质年代、河流宽度和比降等。在社会因素方面,既要考虑到历史传统,又要注意到当地群众的习惯称呼等。以自然因素来说,当曲流量远比沱沱河为大(约大4—5倍), 其流域面积也大些,沱沱河的长度若不算姜根迪如冰川(长12.5公里),则要比当曲短11.5公里,如算上冰川也只比当曲长1公里(至于冰川能否算作河源的延伸,尚无统一规定)。根据这三点,当曲作为长江之源也未尝不可。楚玛尔河的长度、流域面积等均不如当曲和沱沱河,所以它被选择为长江正源的可能性已经排除。再从水系平面位置看,沱沱河位于楚玛尔河和当曲这两条大支流中间,河势方向比较顺直,而且源头位于所有长江支流的最西点,从该点至河口的直线距离最长,这是其他支流所不及的。另外,沱沱河的源头海拔比当曲要高,比降要大,在江塔曲汇流口以下,河道变宽,在沱沱河沿附近河谷宽约10公里,河床宽有500—600米,这也是当曲无与伦比的。而且当曲源头处还有一个向东的大弯曲,其行程远不如沱沱河顺当。综合上述这些条件, 沱沱河可以作为长江正源。”(18)孙仲明、赵苇航:《我国对长江江源认识的历史过程》,《扬州师院自然科学学报》1984年第1期,第78-79页。
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今天确定“江源”时虽然使用的是现代的一些数据,但实际上基于这些数据的标准依然是主观的,而不是纯粹客观的,且由此对于“江源”的确定依然存在争议。以此,我们可以反观中国古代确定“江源”的标准。
《图书编》卷五十八《江源总论》开篇即交代了其用以确定各类河源的标准:“水必有源,而源必有远近、小大不同,或远近各有源也,则必主夫远;或远近不甚相悬,而有大小之殊也,则必主夫大;纵使近大远微,而源远流长,犹必以远为主也,况近者微远者大,乃主近而遗远,岂知源之论哉!”亦即其标准是“远”和“大”,而两者中又以“远”为主,这也是该文将金沙江确定为“江源”的依据。而从徐霞客《溯江源考》来看,其所持的标准也是“远”。
而持长江发源“岷山”的学者所持的依据虽然不太一致,但大部分学者主要是坚持《禹贡》文本的经典地位,而不以河流的长度、远近作为标准,前文所举以《禹迹图》《华夷图》以及《杨子器跋舆地图》为代表的一些地图也是如此。虽然在这些地图中,显然发源于岷山的岷江长度并不是最长的,但在图中依然被标绘了“江源”。全祖望实际上也持这一观点,只是对“源”有着不同的认知,即长江确实源自岷山之外,但自岷山之后进入到“华夏”“九州”的范围后,才需要关注,而其在“华夏”之外的源头则难以确定,且不需要关注,即“愚最取范石湖之说,以为大江自西戎来,自岷山出。举其大略,而不必确求所证于大荒之外……而河源、江源,并在极西。以其九州之表,故《禹贡》略而不书。必指其地以实之,恐如宋孝宗之所以诮程泰之者矣”。胡渭的辩驳虽然以徐霞客和钱谦益论述中的内在矛盾为主,但在结论中强调的是“且岷山导江,《经》有明文,其可以丽水为正源乎”,依然强调《禹贡》记载的正当性。
总体而言,“江源”并不是一个针对事实的问题,而是一个主观认知的问题,没有绝对的对错,古代如此,今天也是如此,由此中国古代文化中基于《禹贡》将长江认定为发源于“岷山”,也是有其道理的,且不是错误的。因此,从古至今,对于“江源”的认知,并不是一个从错误走向正确的过程,而是一个标准变化的过程,我们不能将今人确定的标准强加给古人。
可以说,今天,绝大多数人都将中国近代作为一个转型时期来看待,不过通常研究者以及普通民众大多只关注于这一“转型时期”的社会、经济方面,而忽视了对其他方面的关注。虽然社会和经济的“转型”毋庸置疑是非常重要的,但还需要强调的是经历了这一“转型时期”的近代中国,在看待世界的方式上已经与传统时期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受到了科学、民主的洗礼的近代以及现代的中国人,在很多方面已经不太能理解古人看待和思考世界的方式。本文所讨论的“江源”问题即是一个例证,成长于一个“科学至上”时代的现代人,潜意识中已经认为所有问题的“可靠性”都应当来源于“眼见为实”的准确测量,试验、实地考察、测量数据是“可靠性”的来源。由此在“江源”问题中,更多考虑的是建立一种以经过实地测量或者其他方式测量获得的数据为代表的统一标准。而在中国古代,以及在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之前,“权威”以及“权威文本”就是可靠性的来源。这种差异,实际上来源于看待世界和思考世界的基本方式的差异,即现代人看待和思考世界的方式建基于以数字为其代表的“科学”之上,而古人则赋予了文本以更多的权威。本文并不想对这两者做出是否对错的判断,(19)需要说明的是,现代的科学哲学已经明确提出,科学并不能保证对于“真相”的揭示(参见A.F.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因此“科学”只是看待和研究问题的一种方法,且不是一种有着“至上”地位的方法。而是希望强调在今后关于古代的研究中我们应当意识到这种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尽量避免由此带来的我们对于古人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