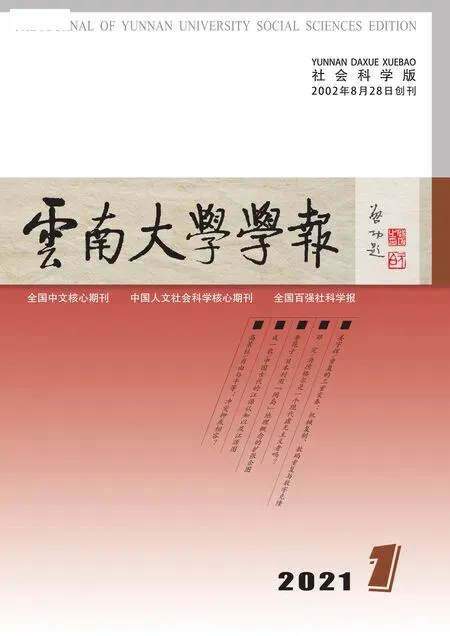黑格尔的第二自然
——一种解答还是一个问题
冯嘉荟
[巴黎第一大学,法国巴黎 75005]
一、导论:两种自然概念
黑格尔与自然主义的关系,是近年来黑格尔哲学对当代学界来说最吸引人的主题之一。(1)代表性的研究包括:Terry Pinkard, Hegel's Naturalism: Mind, Nature, and the Final Ends of Lif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Christoph Menke,Autonomie und Befreiung: Studien zu Hegel. Suhrkamp Verlag, 2018; Filippo Ranchio,Dimensionen der zweiten Natur: Hegels praktische Philosophie,Felix Meiner Verlag, 2016(作为对于第二自然概念的专题性研究,本书较为全面地概述了现有的相关文献)。人们试图通过重构其精神哲学与法哲学中关于自然与精神的关系的讨论,说明黑格尔提供了一种超越了二元论,同时不落入简单的还原论的哲学洞见。尽管人们会在“连续”“统一”“断裂”的不同说法之间保有争议,(2)争议的焦点在于,黑格尔的第二自然学说所提供的是对自然主义的辩护,拒绝还是改造?相关讨论可见:Alexis Papazoglou,“Hegel and Naturalism”, Hegel Bulletin, Vol.33, No.2(2012); Alison Stonen,“Hegel, Natural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Nature.”Hegel Bulletin, Vol.34, No.1(2013); Stefan Bird-Pollan, “Hegel’s Naturalism, the Negative and the First Person Standpoint”, Argumenta, Vol.4, No.2(2019); Julia Peters, “On Naturalism in Hegel's Philosophy of Spirit.”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24, No.1(2016).并且对于从哪一些文本出发来重构黑格尔关于自然与精神的关系而持开放的态度;不可争议的是,黑格尔哲学对于“自然”概念的阐发,是黑格尔作为哲学家而非历史人物的最富启发性的哲学焦点。
在黑格尔哲学中谈论“自然主义”,离不开麦克道尔在其《心灵与世界》中关于“第二自然”概念的阐发。根据麦克道尔,“自然的逻辑空间”与“理由的逻辑空间”的区分,带来了现代哲学的多种焦虑:自然作为规律的领域,与理性(对理由作出回应的能力)相对立,进而规范、意义以及自由问题无法得到哲学上(不论是方法论还是存在论层面)的说明。麦克道尔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启发下,重新激活了“第二自然”的概念。他提出,经过人类教化而习得的概念能力,是个体从其有机体的潜能中展开的,对理由和意义作出回应的能力。第二自然并不与第一自然相脱离,也不比第一自然更缺乏必然性。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实践智慧,它并不诉诸超自然的力量,与怪异神秘的玄思无关。以这一概念为支点,麦克道尔提出了他的“开明自然主义”,让自然主义的概念指向不局限于科学主义的意涵。(3)以上概述参考了韩林合:《麦克道尔的两种自然学说述评》,《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本文无意展开匹兹堡学派及其与黑格尔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背后的哲学问题。通过对当代问题意识的概述,至少清楚的是,当代语境中黑格尔哲学被建构为“自然主义”和“规范主义”之间的、某中第三方的、调和的观点,提供了一种哲学上有价值的“连续论”。(4)比如兰齐奥(Filippo Ranchio)表示:“黑格尔从有生命的自然界到精神不断发展的方法,并不意味着任何形式还原的自然主义。相反人的精神性恰恰在于,有限的主体实际上占有其自然基础和环境,并通过与自身作为自然存在物的分界来保证自己作为自主主体的精神本质。”(参见Filippo Ranchio,Dimensionen der zweiten Natur: Hegels praktische Philosophie,Felix Meiner Verlag, 2016, S.284)暂且不论最被支持的“连续论”的说法是否是有价值的哲学主张,我们暂时也不讨论黑格尔关于“自然”的讨论,是否能够——以非肢解的方式——合宜地放入当代有关自然主义和规范主义的讨论中。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在于,黑格尔所理解的自然,究竟是什么意思?
自然概念的一个基本意义是本性和本质。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表示:
本性(Natur)、独特的本质,还有那种在繁多而偶然的现象和转瞬即逝的外在表现里真正持久不变的实体性的东西,乃是事情的概念,或者说事情自身之内的普遍者。(5)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Wissenschaft der Logik I,Theorie-Werkausgabe, Bd.5,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6, S.26. 译文参考中译本黑格尔:《逻辑学(I)》,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4页。
自然概念的这一方面等同于“本性”、“概念”。它是事物自身所是的东西。此中文将其译为“本性”,以作出明确的界定。但是此处的自然不同于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讨论的自然概念。当Natur被翻译为“自然”时,它指向的是理念的外在性。黑格尔表示:
自然是作为异在(Anderessein)形式中的理念产生出来的。因为理念现在是对自身的否定,或者说,对它自身是外在的……外在性构成了自然的规定。
……自然在其定在中没有表现出任何自由,而是表现出必然性和偶然性。(6)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1830):Zweiter Teil Die Naturphilosophie,Theorie-Werkausgabe, Bd.9, §247,§248,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86, S.24,S.27. 中文译文参考了杨祖陶译本,见黑格尔:《精神哲学》,杨祖陶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在保持大部分译本不变的情况下,本文的引文对一些术语做了修改,比如Leiblichkeit不译为“形体性”,而是“身体性”;Selbstigkeit不译为“利己性”,而译为“自我性”;Mechanismus不译为“机制”,而译为“机械作用”。
可以说,严格意义上的自然,是祛魅了的对于本质和世界自身的理解。(7)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外在性的自然指向的仍然是本质与概念,而不是与作为本质的自然相平行的另一概念。换言之,不是自然概念有两个不同的意义,而是对于自然本身的理解演变,使得自然有了不同的意涵。这一演变是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紧密相连的。在现代机械论图景理解中的自然(也就是本质),不是目的论的统一秩序或者神秘不可把握力量,而是经历了自然科学透视的规律的领域。参考阿多:《伊西斯的面纱:自然的观念史随笔》,张卜天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不过为了避免讨论的歧义,我们还是区分了两种意义的自然概念。黑格尔把这一理解归结为理念自身运动的一个环节,是理念要实现自身所需要经历的他者、它的外在性。自然的领域意味着规定性的缺失,它表现为一系列矛盾,并且它从自身出发无法超越这些矛盾。赫拉克利特说,“自然善于隐藏”;而自然的不可捉摸的特性,不在于认识层面的遮蔽,而是存在层面的无规定性,或者说缺乏统一和内在的矛盾。(8)关于自然作为内在矛盾和缺乏规定性的意涵,参考Gilles Marmasse:Gilles Marmasse,Penser le réel: Hegel, la nature et l'esprit,Paris,Kimé, 2008,Chapitre 1,9.
那么,当代学者在讨论黑格尔“自然”问题时,他们指向的究竟是作为本质的自然,还是作为外在性的自然?以麦克道尔为例,当他谈论“自然主义”,尤其是批判“露骨的自然主义”(bald naturalism)时,他所理解的自然是物理主义的自然,这种观点以存在论的取消主义,方法论的科学主义为导向,所对应的是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的研究对象。但是当麦克道尔谈论“第二自然”概念时,他更接近亚里士多德的对于自然的理解,也就是事物的本性。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把两种意义的自然并列?当麦克道尔并列地谈论两种自然概念的时候,它们仅仅是在都具有必然性的意义上,可以被等而视之。而如果坚持自然的两种意义的区分,那么第二自然的自然主义并没有改变物理主义的自然主义的意涵。
伴随着“自然”概念的复杂性的,是对于“第二”的理解。在亚里士多德的语境中,“第二”的可以表示逻辑和时间在后的意思。在其他的语境中,“第二”可能表示在后或者否定意义,可能具有从中而来或者朝向的意义。事实上,现有的研究并未主题化地分析这些概念的具体意义。而如果没有对于它们的分析,就提出“第二自然”概念在哲学上的生产力,还为时尚早。
下文我们将指出:黑格尔“第二自然”学说中的“自然”,采取的是自然的第二种意义,也就是祛魅了的自然。即“人类凭借自身的理性活动所建构的规范世界,也是最终成就人类自由的地方。(9)王增福:《经验的概念化与第二自然:麦克道尔论心灵与世界关系的文本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99页。“第二”既有否定的意义,表示精神摆脱给定规定性的解放的方面,也有属己的意义,也就是把原本外在的规定性转化为主体的自身规定的方面。第二自然“属己的否定”的概念结构,打开了黑格尔客观精神学说的复杂面貌:它既是对于现代性种种困境的一种解答,也展开了更深的困惑。
二、第二自然作为习惯
黑格尔第一次主题性地讨论“第二自然”概念,是在主观精神部分。“精神”作为理念经历自然的外在性并重新返回自身的环节,一开始保持自然的规定。它进一步逐渐与直接的规定性相区别开,展开为感觉灵魂,即“作为个体的而与它的这个直接存在建立起关系,同时在直接存在的主规定性中是抽象自为的”。(10)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1830):Dritter Teil Die Philosophie des Geistes, Theorie-Werkausgabe,Bd.10, §390,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86, S.49.灵魂首先沉浸于这些自我感觉之中,与身体性的特殊规定不相区分。灵魂的运动在于它从这些特殊性中脱离出来,作为普遍和同一的自我展示自身。灵魂与身体性规定的断裂,被黑格尔规定为“第二自然”,也就是习惯。
“第二自然”在灵魂的身体性方面和灵魂作为自我关联的主体之间:它是灵魂逐渐摆脱身体规定,进而将自我的目的灌注于灵魂活动的中间环节。黑格尔描述了这一环节不同的实现机制:或者通过直接的否定,比如在身体锻炼中,克服直接感受到的疲惫和痛苦;或者经由长期的满足而钝化,常见的是欲望和冲动的满足,持久的重复之后灵魂的激情消散于无形;或者是通过多次重复带来的熟练,使得对身体而言外在的目的成为身体内在运行机理的一部分。可以看到,黑格尔所主要关心的,是灵魂自我规定的目的如何能够成为身体运作机制的一部分,也就是灵魂的精神性的规定如何能够身体化(verleiblichen)。一个习得了的习惯,经历了多次重复,成为主体无意识的活动的机制。(11)当代人可以合理地质疑,黑格尔对于“习惯”的理论描述,相较于今天心理学、生物学研究而言,缺乏实证的支撑且没有清晰的理论模型;或者至少从术语概念来说,“条件反射”“肌肉记忆”,都能提供更为清晰的对于习惯这一行为机制的刻画。的确,黑格尔在这里所探讨的内容,与今天心理学的相关研究共享同一个研究对象。不过黑格尔探讨人类行为中的习惯,并不意图将之纳入数理层面的解释模型;对黑格尔来说,重要的毋宁在于思考沉浸在身体的规定中的自我感觉,如何能够通过自我的自主规定,逐渐失去它的效力,进而让位于灵魂自身规定自身的自由的活动。精神是对于自然的外在性的扬弃,是理念从自然的领域中重新返回自身;因而习惯作为主观精神的环节。它运作于自然的规定与自由的活动之间:它是已经是,却还没有成为自身的主体;它是主体性自我实现的必然经历的机制。
具体来说,第二自然可分为两方面:将给定的规定转化为符合主体目标的工具;将主体自由的自我规定置于自然的外在秩序中。
首先,第二自然来自于对身体性规定的塑造和转化过程。在习惯中,自我以身体为中介展开它自身的目标。“灵魂必须……把肉体训练成它的活动的驯服而灵巧的工具”,(12)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1830):Dritter Teil Die Philosophie des Geistes, Theorie-Werkausgabe,Bd.10, §410, Z., S.190.这是对身体的否定性的塑造:通过多次重复中,从属于自然生理的领域的身体,转化而进入精神性的意图和目标的意义空间。精神性的教化和改造,让原本属于必然性的身体展开为自我的可能性,让身体的给定性转化为灵魂的工具。
另一方面,第二自然是精神性目标的自然的机械过程(Mechanismus)。在习惯中,灵魂是“放回到其纯粹观念性中的身体性”。(13)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1830):Dritter Teil Die Philosophie des Geistes, Theorie-Werkausgabe,Bd.10, §409, A., S.183.自我通过身体而展开它所有筹划的活动,它不得不制约于身体性的自然规定。这一制约首先体现于第二自然的实现方式:习惯的教化来自于重复和练习,它们是身体的机械过程,而非反思的自由的规定。其次在于第二自然的运作方式。习惯是无意识的,灵魂“无感受地和无意识地在它身上具有它们[感觉的种种特殊规定]并在它们中活动”。(14)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1830):Dritter Teil Die Philosophie des Geistes, Theorie-Werkausgabe,Bd.10, §410, S.183.种种特殊规定在习惯中被规定为“单纯存在着”。“存在着”表明,这是一种直接的联系,而不是设定的、否定的关系。再次,就第二自然运作的领域来说,它仍然从属于自然的外在性的领域。如果不经过这一中介,那么自我的自由的活动得不到实现。这也就是为何黑格尔以“精神性的机械过程”描述习惯。在大逻辑“机械论”中,黑格尔说:“精神的机械过程在于,精神的相关物的彼此之间相异、与精神相异……习惯,一种机械的行动方式都意味着,精神的所思所为都缺乏精神的渗透和在场。”(15)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Wissenschaft der Logik (II), Theorie-Werkausgabe, Bd.6,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86, S.410.“机械过程”的刻画意味着,第二自然运作着与自然物类似的机制,它以自然的方式否定了自然、仍然以自然的方式运作、停留于自然的领域。
可以看到,黑格尔这里对于“自然”的理解,采取的是上文分析的第二种自然概念。“自然”,就其存在而言,指的是外在性的领域,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结合(典型例子是时空物理世界的对象);就存在方式来说,“自然”表示给定性、外在性,或者是单纯存在着的阶段(与设定的存在相区分)。在这个意义上,“第二自然”显然不是“另一种自然”的意思,否则黑格尔谈论精神的塑造和教化,就没有意义。第二自然恰恰在于这样一种作用:让身体不仅仅服从自然必然性的秩序,同时也参与到自由的领域中。教化使得自然不再是自然,让自然剥去它的外在性。一个更直接的表达或许是将第二自然等同于“对自然的否定”,通过这一否定,自我能够逐步为自身建立符合它的意图的意义空间。精神在灵魂的阶段,以身体性为它的给定性和直接的规定。第二自然表明精神对它的异在的否定:在习惯中,欲望和偏好都变得无所谓了;身体所服从的不再是自然的欲求,而是有所意图的目的。
将第二自然的自然理解为外在性(而非本质)意义上的自然,这一点是比较明确的。然而伴随着这一理解,我们是否要把“第二”刻画为精神的否定性活动,还不那么清楚。显然,习惯运作着自然规定性的钝化:本来搅扰和纠缠自我的种种冲动和欲望,都变得无关紧要。可以说,第二自然超越了自然,是对自然的否定。
然而,把第二自然仅仅理解为对于自然的否定是不足够的,因为这会使得黑格尔无法与康德的二元主义立场相区分。事实上,“第二”作为否定的活动不是对于自然规定的简单脱离和超越,像康德对于自律和他律所做的区分那样。对于黑格尔来说同样重要的是,在对于自然规定性的否定中,自我重新占有了这些规定性,把这些规定把握为自身的规定。将外在性内在化,这一过程也叫做“属己(活动)”(Aneignen)。黑格尔表示:
精神的一切活动都无非是外在东西回复到内在性的各种不同的方式, 而这种内在性就是精神本身, 并且只有通过这种回复, 通过这种外在东西的观念化或同化, 精神才成为而且是精神。(16)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1830):Dritter Teil Die Philosophie des Geistes,Theorie-Werkausgabe, Bd.10, §381, Z.,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86, S.21.
自然的规定作为精神的异在,在精神的活动中脱离其外在性而进入精神自身的规定。自我将本来是他物的规定把握为自身的(eigen)规定。通过属己的活动主体扩大了它的规定性空间,也就是在与自身相关/与他者相关的运动中,(17)以“与自身关联”(relation to itself)和“与他者关联”(relation to other)的解读框架,主要根据鲍曼(BrandyBowman)的研究。参见Brady Bowman,Hegel and the Metaphysics of Absolute Negativ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1.4. “The logic of absolute negativi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monstrative ideal”.得到进一步展开。
皮特斯(Julia Peters)因而区分了第二自然作为从自然中的解放的两种意义:一种是否定性的,是对自然的克服;一种是属己的,是将外在性内在化的过程。(18)Julia Peters, “On Naturalism in Hegel’s Philosophy of Spirit.”,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Vol.24, No.1(2016), p.116.事实上,就第二自然运作的自然与精神的关系而言,它既是否定的也是属己的,或者说,它是属己的否定。属己与否定的统一,也是精神从与他者相关中回复到与自身相关,对否定性的否定。
三、第二自然作为制度
在主观精神的下一个阶段——客观精神中,黑格尔再一次引入了“第二自然”概念。(19)黑格尔认为,“习惯的形式包括精神活动的所有种类和阶段”,所以在哲学体系的不同阶段讨论第二自然,并不算顺序的错乱。核心的问题在于,在精神一切活动都运作着第二自然的机制,也就是精神属己的否定的活动。(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1830):Dritter Teil Die Philosophie des Geistes,Theorie-Werkausgabe, Bd.10, §410,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86, S.186.)不过,客观精神(法、现实的自由)中的“第二自然”所联系的不是习惯,而是客观精神自身;进一步说,是伦理的领域,这是“在伦理实体中熏陶渲染习惯而形成的……也是个体接受伦理共同体教育或者其同体对于个体教育的过。”(20)王增福:《经验的概念化与第二自然:麦克道尔论心灵与世界关系的文本学研究》,第200页。黑格尔分别在客观精神和伦理的导论中提到了“第二自然”的概念,并以“第二自然”作为法的基本规定:
法的体系是实现了的自由的王国,是从精神自身产生出来的、作为第二自然的精神的世界(21)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o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l im Grundrisse,Theorie-Werkausgabe, Bd.7, §4,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86, S.46. 中译本参考了邓安庆译本,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对伦理事物的习惯,成为取代最初纯粹自然意志的第二自然,它是渗透在习惯定在中的灵魂,是习惯定在的意义和现实。(22)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o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l im Grundrisse,Theorie-Werkausgabe, Bd.7, §151, S.301.
暂且不论为何黑格尔既以第二自然刻画法,也用之刻画法的一个环节(伦理);(23)直观地说,用同一个性质去描述一个事物和它的子集,是不准确的。但是在黑格尔这里,人们有理由支持这样一种界定,因为伦理是发展了的法,真正的客观精神。值得提问的问题在于,既然对黑格尔而言,第二自然是习惯(或者说,习惯是第二自然),并且第二自然也是法(或伦理)的领域,那么人们是否从黑格尔第二自然的学说推出:法(或者伦理)究其本质是一种习惯?
人们可以从思辨的规定方面支持这一主张。黑格尔在讨论“习惯”中已经指出,“第二自然”意味着精神对自然的外在性的属己的否定,是自由的、自我规定的主体通过否定性地吸纳其自然的方面,让主体的目的以自然的机制加以运作。就“第二自然”既是自由的(主体的活动)也是自然的(必然的)而言,法的确应当被理解为第二自然。因为黑格尔在客观精神学说中意图建立的法,作为自由的实现,既来自于自由意志的主体的反思活动,同时又带有必然性的外衣。可以认为,黑格尔第二自然学说是斯宾诺莎的回响:真正的自由不是超越自然必然性自由地建立新的因果链条,而是回到必然性。
然而思辨的规定在具体的法的环节中,会引向一系列具体的质疑:如果抽象法、道德、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它们本质上是一种习惯,那么黑格尔似乎与伯克等保守主义者一样,注重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传统,强调对现行秩序的非反思和非批判的接受。(24)事实上,这是对黑格尔法哲学最常见的批评:黑格尔是在为普鲁士政府的现行秩序辩护。最典型体现在Haym的《黑格尔和它的时代》之中。尤其是1820法哲学出版之际,由哈登堡所引导的一系列改革罢黜,开明学者人人自危。这社会背景让人们怀疑,是否黑格尔自身原本的启蒙倾向在一系列反改革的运动中被压制了,或者说扭曲,甚至不得不诉诸隐微写作?(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可见科维刚(Jean-François Kervégan)为《法哲学原理》法译本写作的导论。 Cf. Hegel Georg Friedrich Wilhelm,Principes de la philosophie du droit,tr. J.-F. Kervégan, Paris, PUF, 2013, pp.17-27.)以黑格尔在柏林期间的政治背景为理由,为黑格尔原本具有的启蒙倾向和自由主义的立场做辩解,这种做法恰恰背离了黑格尔自身的哲学观点。原因在于,黑格尔从来不认为自由的政治秩序的实现,仅仅是对客观秩序的批判和限制。在他看来,把政治制度当作外在的和单纯否定性的个体,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第二自然概念恰恰是一个切入点,说明黑格尔与通常的自由观(典型是柏林描述的消极自由)所不同的对于自由的理解。那么人们将难以理解,在什么意义上,黑格尔的法哲学是后大革命时代、启蒙思潮的产儿;在什么意义上,黑格尔是一个现代哲学家。让我们具体分析这一问题。
首先,在抽象法领域,习惯的确是法学家都需要面对的核心议题;至少在黑格尔时代,法学家关于法应当是习惯法还是实定法的讨论并未达成一致。历史法学派以萨维尼为代表,倾向于从民族文化传统的角度出发,强调法典化的负面作用。虽然黑格尔认为“习惯的形式包括精神活动的所有种类和阶段”,但与萨维尼对立,他认为,“法一般来说是实定的,它必须采取在某个国家有效的形式”。(25)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o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l im Grundrisse,Theorie-Werkausgabe, Bd.7, §3,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86, S.34.黑格尔所理解的习惯,并非历史法学派所坚持的属于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与传统规范,而是运作于任何精神的规定的非精神性机制。在这个意义上,习惯与实定法不但不构成冲突,反而就其思辨的层面是一致的:它们都表明了法作为自由的实现,依赖外在的条件。
其次,在道德领域,从黑格尔的界定来看,是很难谈论习惯的。意志的主观性要求它仅仅承认那些它所意识到的行动。行动的意图是衡量道德的标尺;道德以主体的内在性为其基本规定,一个仅仅出于长期习惯而作出的行动,不能被视为道德的行动;人们既无法从之挖掘出个别的意图,也难以进行责任的判定。不过,在道德的领域拒绝习惯,不意味着法不可以被理解为习惯,因为道德作为法的第二个环节,并不是实现了的法。
因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去考察,把伦理的领域(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理解为第二自然(也就是习惯),在何种意义上是成立的。相对而言,家庭能够被合理地理解为习惯。虽然家庭的基础是爱;但家庭作为一项伦理制度,其功能并不在于对激情的满足。对黑格尔来说,浪漫派的爱情观是天真的,对某一个体专一的爱其实只是个体的特殊癖好和偶然的心血来潮;在长期的共同居住中,新鲜感的刺激必定让位于理性化了的对共同生活的意愿。家庭似乎是伦理生活的习惯形态的典型事例。市民社会则不那么清楚,我们大概可以谈论这样两个环节:其自由的环节在于个体的特殊利益以及相伴随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自然的环节在于这一系列活动所沉淀的、为市民满足需要提供条件的生产和消费的交换空间。
在国家领域,“第二自然”表现于“政治意向”(politische Gesinnung),即个体对于客观秩序的态度。在理性化的现代国家中,个体对它所身处的世界带有直接的信任,也就是这样一种意识:
我的实体性的和特殊的利益被包含和保存在一个他者(在这里就是国家)的利益和目的中,被当作与作为单个人的我的关系,因此这个他物对我来说直接地就根本不是他物,我在这种意识中是自由的。(26)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o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l im Grundrisse,Theorie-Werkausgabe, Bd.7, §268, S.413.
这一信任感包含了精神展开的一系列环节(从主观精神的灵魂层面的规定到意识和自我意识,经历客观精神的人格、道德行动者、家庭成员和经济人)。因此,信任感作为一种与外在秩序的直接关联,不像灵魂学说中的习惯,纠缠于身体性自然的规定。具体来说,信任感首先与来自身体规定的种种感受(比如激情、愤怒、冲动)并无关系;因而它不同于与政治宣传和情绪鼓动燃起的爱国热情,也不是民粹主义的心理机制。其次,信任超越政治激情的机制,不同于习惯的习得,来自机械性的重复。在市民社会中,个体通过劳动实现个性的教化;而在国家中,特殊个体对普遍性的认识、在外在秩序中领会个体自由的能力,落实于一系列政治制度。最后,信任感不是无意识的,并非“近乎技”的熟练。信任感始终是一种意识,一种对于自身自由能够实现的条件的认识:在理性化的现代国家中,真正自由的个体能够把握到,它所身处并看起来是给定的甚至是强制性的客观秩序,其实是它自身自由实现的一部分。
可以认为,黑格尔对于信任的阐述,是对契约论的改造:在现代社会,政治体不能够来源于传统或神意,而需要从自由的个体及其意志的承认中,汲取合法性资源。黑格尔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反对从授权与代表(霍布斯)、普遍意志(卢梭)来建立现代国家的基础。(27)参见§258附释中黑格尔对卢梭的普遍意志的诊断:“卢梭所拥有的功劳,就是提出了一个原则, 此原则不仅就形式(诸如社会性冲动、神的权威),而且就内容而言 就是思想,虽然这是把思维本身,即把意志确立为国家的原则。……然而他所理解的意志,仅仅是特定形式的单个人的意志(后来费希特亦同)……这样一来,单个人 结合成为国家就变成了一种契约,而契约乃是以单个人的任性、意见和偏爱所表达的同意为其基础的。”(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o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l im Grundrisse,Theorie-Werkausgabe, Bd.7, S.400)黑格尔所不满意的在于,契约论以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体为原则,预设了一个独断的起点。古典自由主义赖以为理论基础个体,仅仅抽象了主体的部分侧面;它既是独断的,也是不充分的。这一对主体的理解是形式化的,除了自我保存的欲求,它无法给出具体的内容;此外,这里的个体还停留于主体性的方面,而没有达到实体性的方面,也就是说,它停留于意志和它所规定的外在世界的差异,没有超越这一差异而回复到个体的自我关联。
黑格尔通过阐发政治意向(信任),既批判也充实了契约论个体主义。在他看来,真正自由的个体面对它身处的世界保持着既反思又接纳的态度,这种信任感在现代国家中体现为爱国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下,爱国主义不是主动的奉献和献身,而是处于任何政治态度底层的基本意识。这一意识是具体的,任何在具体的历史和文化情境中的公民,都能够从它所身处的意义空间中表达自身的政治意向;这一意识也是实体性的,更准确地说,自在且自为的:个体投身于它的世界,并且在世界里找到自身。
信任所包含的直接性的规定还依赖进一步的外在条件,也就是政治制度。黑格尔说:
这些制度构成特殊领域的国家制度,即发展了和实现了的理性,因而是国家稳定的基础,同时也是个人对国家之信赖和信心的基础;它们是公共自由的支柱,因为在这些制度中特殊的自由是实现了的和合乎理性的, 所以在这些制度本身中自在地就存在着自由和必然的统一。(28)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o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l im Grundrisse,Theorie-Werkausgabe, Bd.7, §265, S.412.
制度进一步展开了个体自由所得以实现的外在的机制,它是精神的再次外化:个体首先摆脱了历史、权威、激情等外在的规定,成为独立的能够自身规定自身的意志;进一步,意志为了能够成为有所规定的意志,将其自由贯通于他所身处的客观秩序,进而这一秩序不再表现为现成的、陌生的东西。就这一秩序看起来是外在的、与主体的意图和筹划不相关而言,制度显现出必然性的外貌。
恰恰是在它以自然的方式运作的意义上,制度才是自由的实现。制度,作为第二自然,是精神性的机械作用。精神不是简单的主体的有所规定的否定,它在其显露(Offenbaren)中展开具体的规定性和内容。首先,精神“设定(Setzen)自然为它的世界”,(29)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1830):Dritter Teil Die Philosophie des Geistes,Theorie-Werkausgabe, Bd.10, §384,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86, S.29.自然作为精神的他者,在精神的设定中成为精神自己的世界,成为精神的产物。主体在这一精神化的世界中直接的与自身相关。另一方面,这一设定也是“预设(Voraussetzen)世界作为独立的自然”。(30)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1830):Dritter Teil Die Philosophie des Geistes,Theorie-Werkausgabe, Bd.10.S.29.“预设”意味着与他物相关。(31)“预设”概念立足于黑格尔在《逻辑学:本质论》中对于“外在的反思”的讨论。预设就是外在的反思。它表示反思发现某个已经存在的,对他来说是否定的东西。预设与这一规定性是外在的关系,也就是与他者相关的阶段。精神所设定的世界显露为自然的样态,独立于精神的规定;精神在其中找不到自身。设定与预设是精神自我展开所必然呈现的二重结构:自由的精神一方面是有所设定的否定性的活动;另一方面,设定的(gesetzt)同时也是存在着的(seiend),精神反思的活动在实在的领域展露为直接的规定。(32)门克对于第二自然的“设定”与“存在”的方面,给出了非常精彩的讨论,参见Christoph Menke,Autonomie und Befreiung: Studien zu Hegel.Suhrkamp Verlag, 2018, Kapitel 4,《Die Manifestation des Geistes.》.
既然精神的显露意味着,从设定的规定到存在着的规定,也就是说,自由的实现带有自然的方面,那么,法(自由)不可避免地是一种习惯(直接的规定)。黑格尔不是与启蒙潮流相悖逆的保守的、复辟的思想家。其哲学毋宁在于指出,启蒙运动(以及同一思想谱系的契约论思想)所依据的个体主义,如果充分考虑其实现的条件,不能停留于简单地从个体自我保存的意志出发而对于固有秩序的重新奠基。同样重要的是,重新奠基了的秩序仍然像传统秩序一样保持为外在的、给定的外观;只不过在更新过了的秩序中,个体不再与公共的世界相对立,而是在客观秩序中展开自身。
四、第二自然:精神的实现还是丧失?
就精神既设定自然为世界,又设定其世界为自然的双重形态而言,“第二自然”学说在哲学上具有正面的意义。这也是当代学者强调的,黑格尔弥合了自然与精神的对立,表达了超越自然与规范的二元论的一种统一论的观点。(33)如果放在黑格尔当代的语境中,这一问题毋宁在于如何超越康德的二元论,也就是去弥合第一批判和第二批判所导向的自然的与自由的王国的断裂。康德的第三批判以及谢林的自然哲学,都是某种意义上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从社会文化背景来看,在启蒙与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哲学家,他们的任务不仅仅是展开主体性的规定,还在于去思考,如何在一个以原子化的人性论和功利主义的自然观为潮流的时代中,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整全。(34)Cf. Charles Taylor,Hegel and modern socie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70.黑格尔在这个思考环境中,既不能满足于康德关于自然和自由王国的截然二分,也未停留在浪漫派对于大全的统一的理想之中。(35)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时期(以《基督教的精神和命运》为代表),短暂地表达了这一理想,希望通过爱的统一的力量缓解法则和生命的张力。但是这一浪漫派倾向的工作随后被耶拿的体系哲学的努力所取代。他一方面保留启蒙运动的基本主张:展开个体的自由以及自由得以发展的条件;另一方面,自由的解放不能够是对于个体身处的世界(那些现存的固有的规定)的单纯否定,解放和革命总是会进入秩序与常态,这是自由现实化的内在要求。
平卡德(Terry Pinkard)敏锐地指出,黑格尔的自然主义在于这样一个现代性问题:追求自由的个体如何能够居住于它的世界,如何能够“找回自身”(being at one with itself)。(36)Cf.Terry Pinkard,Hegel's Naturalism: Mind, Nature, and the Final Ends of Lif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Introduction”, “3.D Being at One as a self-sufficient final end”.黑格尔的方案显然不是古希腊城邦的生活形态,因为消融于伦理共同体的个体,缺乏现代人最为珍视的自由。黑格尔主张的毋宁是个体有所反思的对世界的信任——平卡德表述为“讽刺的亲密”(ironic intimacy)。(37)Cf.Terry Pinkard,Hegel's Naturalism: Mind, Nature, and the Final Ends of Lif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Introduction”, “7.A.1,Hegelian Amphibiens”.个体通过它的理性能力打破了实践日常的亲密性,而这一破碎同时也建立了新的亲密性:主体在世界中所感受到的异化被吸纳为主体安居于世界的一个要素。实现了的自由的个体,在现代社会不是融于城邦生活的公民,而是“两栖动物”:它活动于个体的自由与外在的必然性、内在的个体生活与理性的公共秩序之间。
如是解读的第二自然学说,是一种解答,甚至是哲学的慰藉和治疗:它安慰那些其个性自由在现代社会逐渐失落,在世界中找不到自我进而心生怨怼的个体,同时表明个体性的挣扎仅仅是世界所成为世界的一个方面。这一生存论的意义与存在论的(自然与精神)、政治哲学的(个体自由与公共制度)含义平行,并以思辨的规定为基础。正如前文所指出的,第二自然是设定与存在的统一,意味着精神一方面设定自然为它的世界,同时也设定世界为独立的自然。自我首先通过对于自然规定的否定,把自然的自在存在把握为为他存在;同时,自然的为他存在仍然是一种自在存在,也就是说,精神通过自然的中介所建立的与自身相关,包含了与他者关联的方面。黑格尔认为,“[精神的]显露是把自然创建为它的存在,精神在这种存在里给自己产生出其自由的肯定和真理”。(38)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1830):Dritter Teil Die Philosophie des Geistes,Theorie-Werkausgabe, Bd.10, §386,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86, S.29.
然而,承认自由的实现具有自然的方面,并不等于承认这就是真正的,所有人都欲求的自由。事实上,黑格尔自己的表述也是复杂的,在灵魂学说中黑格尔提到:“如果完全抽象地说的话, 对生活的习惯就是死亡本身。”(39)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1830):Dritter Teil Die Philosophie des Geistes,Theorie-Werkausgabe, Bd.10, §410, A., S.187.进一步谈论特定的习惯——记忆时,黑格尔表示,它是某种“丧失了精神的东西”(zu etwas Geistverlassenem)。(40)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1830):Dritter Teil Die Philosophie des Geistes,Theorie-Werkausgabe, Bd.10, §462, Z., S.280.黑格尔对于习惯的精神性规定的让步,表明了这一问题的复杂:一种以自然的机械方式运作的精神活动,究竟在什么意义上还能够是精神性的?
在《自主与解放》(Autonomie und Befreiung)一书以及随后的研究中,门克(Christoph Menke)发展了第二自然的这一侧面:第二自然指向的不是精神的实现,而是精神的丧失(Geistverlust)。这一机制表明:精神作为伦理,必然是机械的、外在的;精神的实现(Verwirklichung)总是伴随着它的物化(Verdinglichung)。在门克看来,第二自然是这样一个洞见:精神的自我解放免不了外在化的命运,自我本来寻求的是精神规定的实现,但它能达到的却是精神的缺失。因此,第二自然不是对于现代社会正面的肯定,(41)比如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批评了 “第二自然”学说。这一批评预设了第二自然是黑格尔关于社会理论的正面建构,是黑格尔对于现代性诸多问题的一个答案。卢卡奇以及随后的批判理论家对于“第二自然”的不满,在于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不能够通过第二自然式的机制而得到解答。(参考张双利:《第二自然与自由——论卢卡奇对黑格尔第二自然概念的转化》,《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而是一个批判的概念。
在门克看来,第二自然从属于黑格尔对于作为自主的自由的基本讨论。黑格尔和席勒一样,不能满足于康德式的,自身给出法则的自由。自己服从自己设定的法则(Selbstgesetzgebung),根据康德式的对自由的理解,自我与法则的关系是外在的,停留于应当(Sollen)。而真正的自我实现,在黑格尔看来,不是在应然的关系中臣服于法则的统治,而需要让法则对自我而言作为存在(Sein)而被纳入主体的自我规定的活动。而法则“存在的”方面是第二自然的哲学意义。它表明:法则包含有自然性的机制,这是精神的机械过程,也是在社会领域所显现的自由必然展现的形态。
在此意义上,门克认为黑格尔并非如麦克道尔所指示的,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回响,而是反过来说,通过第二自然概念批判了亚里士多德。门克引用《精神哲学》§463中“丧失了精神的东西”的表述,表示第二自然作为社会习惯,自身并不带有规范性的力量。自由为了获得实现,恰恰需要改造法则的自然样貌,通过有所规定的否定消解第二自然,进而让自我能够在自我规定的空间中获得解放。简言之,第二自然不是如古代伦理学所主张的那样,是伦理教化的成就(Gelingen),而是自我在社会习惯化的自我丢失(Selbstverlust)。
门克承认第二自然的不可避免,即精神的现实化必然以机械方式运作。但门克并不认为,这一命运就是主体能够接受且应该接受的最终目标。在基本哲学洞察上,门克强调精神和自然的差别;这一差别在他的否定—辩证解读中,体现为否定性与规定性的不可弥合的差异。有所规定的否定总是需要回溯到无规定的否定,这一更激进的否定性与既定的规定无关。激进否定性独立于一切规定性,也让一切规定独立于否定性的活动。
伴随他激进否定性观点的,是加剧的精神—自然的二元论。门克所刻画的第二自然停留于习惯的惰性,是不自由的。如果对应于导论一开始的区分,门克所理解的“自然”是彻底祛魅的现代意义上的自然。门克所理解的“第二”,是“另一种”的意思。而根据本文的解读,“第二”意味着否定和从中解放。这也就是为何在门克看来,精神的机械的机制等同于精神的丧失。而黑格尔从未表明,第二自然是某种不自由的形态,是自由的反面。恰恰相反,正如我们业已指出的,第二自然是法作为自由的实现的基本特征;换言之,现实的自由,必然是以第二自然的方式而存在。从黑格尔自身主张来看,物化并非对于精神的剥夺,因为如若没有直接性的外衣,那么精神的活动找不到它得以实现的现实性条件。精神的“再外化”恰恰是精神自我实现的一部分,否则,整个客观精神的领域,都将失去哲学上的效力。从他对自然的激进的理解来看,门克背离了黑格尔的基本立场。
然而,对门克的解读作出限制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走向他的反面,即把“自然”理解为事物的本质。这一理解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并且在当代有关“规范性”研究中得到大大发挥。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使第二自然概念包含了“教化”(Bildung)的意义,即使它的确意味着对外在秩序内在化,这一学说并非是对亚里士多德传统的简单回复。毕竟,在当代语境中讨论规范(价值、意义、习俗等等),始终面对相对主义、历史主义等不同维度的潜在批评。人们不能简单地诉诸传统、神意和其他独断的本体论预设,来声称作为第二自然的规范具有自然法则那样的必然性。传统的目的论的自然秩序,不再具有统摄性的哲学效力。而诉诸历史的沉淀、社会的习俗的做法,也仅仅是把哲学问题推向了非哲学的领域。这是一个现代性的悖论,人们不能满足于给定的、缺乏主体反思的现成秩序;但人们又需要生活在既定的社会秩序中,与所身处的世界保持亲密和熟悉。
黑格尔哲学的复杂恰恰在于,他既不接受彻底机械化的自然观(若是,那么他就无法完成他超越二元论的哲学任务),也不诉诸既定的对于本质和事物秩序的理解(因为哲学的任务在于“不仅把真相理解和表述为一个实体,而且同样也理解和表述为一个主体”);他既不认为精神的活动是对于自然规定的简单否定(一种直接的否定仍然落入二元论),也不相信实现了的自然仅仅是对于既有秩序的回复(经历了主体性透视的规定,是反思了的、返回自身的规定)。黑格尔的第二自然学说,运作着“属己的否定”的机制:(42)当代关于黑格尔“承认理论”,是对于“属己的否定”之展开机制的具体阐发,这一论题催生了丰富的研究。只不过,“承认”的主体间维度、理性的给予和回应理由,是否能穷尽主体在设定与预先设定、自我关联和与他者关联、精神性与自然性、外在性和内在领域之间的动态的规定,就是另一个问题了。第二自然作为实现了的自由,一方面在于精神否定其自然的规定,从直接的规定性中脱离出来;另一方在于精神把这些规定吸纳入自身规定之中,成为自身的本质。
这一对自然的重新占有——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自然的重新施魅——既可以理解为精神的自由的开展(在这个意义上,第二自然是肯定的概念),也可以被把握为精神的丢失(也就是说,第二自然是批判的概念)。第二自然概念,或许是黑格尔面对现代性一系列问题的回应,也可能仅仅是这些困惑在哲学上的表现。(43)当然,需要补充的是,第二自然处于有限精神的阶段。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因为精神落实于人类的精神,第二自然展开为某中精神的丧失。而如果把绝对精神也纳入讨论的范围,问题可能得到解决(也可能变得更为复杂)。
五、余 论
不论哪种方案,不论黑格尔是在批判还是肯定,不论第二自然所带来的是哲学的治疗还是哲学的困境,前文讨论至少达到了这样一个洞见:任何一种实在领域中展开的自由,总是带有外在性的外衣。外在性意味着重复、物化和机械化,这是不可避免的命运。
永远被新鲜感唤醒的现代人,最无法忍受平庸。但颇为悖谬的是,对平庸的接受是每一个现代人成为现代人的必经之路:“一个人不管和世界进行多少次的争吵, 在世界里多少次被扔到一边去,到头来他大半会找到他的姑娘和他的地位; 他会结婚,会变成和你我一样的庸俗市民。”(44)黑格尔:《美学》(二),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64页。
令人难以忍受,又不得不承受的习惯,究竟是解放还是死亡?这既是黑格尔提给读者的问题,也是读者面对自身会提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