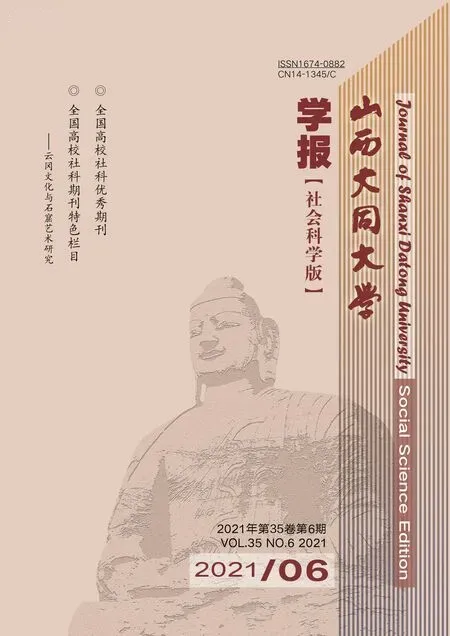也谈历史研究应厘清的几个基本问题
——基于东西方史学传统比较的视角
陈永华,陈浩然
(1.浙江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2;2.英国约克大学,英格兰 约克郡 YO10 5DD)
历史研究的任务在于弄清每一件具体史实的原貌,并揭示隐藏在历史现象背后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但是,一方面,由于史料本身也有“信度”问题,另一方面,历史研究也会天然反映研究者的兴趣和价值观,因而历史研究其实也是主观的。如何平衡和处理好主客观的关系成为历史研究绕不过去的话题。这其中,如何厘清和处理史学与文学的界限?客观性如何在在史书撰写中得到保证?如何在坚守马克思主义史观和借鉴年鉴学派等西方史观上找到平衡?这是比较重要的问题,本文试从东西方史学传统比较的视角提出一些思考。
一、史学与文学的分界
文学与历史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于“真实性”的要求有所不同,历史要求字字精确,而文学则允许想象和创造。则虽然说起来很简单,但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却很难贯彻到底。实际上,历史学本身的发展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求真”的贯彻过程。瞿林东认为,人类的历史活动是史学产生的客观基础,人类的历史记忆与历史意识的发展是史学产生的主观条件,人类创造出文字并由此出现了文字记载是史学产生的主观条件。[1](P7)“记忆-回忆”的人类本能,分节语的诞生等,都证明了无论东西方,史学从诞生之时就和文字紧密相连。同时,两者均将历史传说视作史学的源头。[2](P3)
早期的史学,实质上确是和文学混杂在一起的。西方史学中,古希腊史学是第一个高峰,希罗多德的《历史》是绕不开的一本著作。但这本书实质上是一本采用曲艺形式表达重大历史事件的史书。尽管希罗多德本人在作品中反复强调历史的本质是“客观的记录”,[3](P691)这一原则也成为了后世史学家纂史基本原则之一,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难以得到贯彻。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个提出了严格的史料批判原则,他也在作品中尽量保证自己立场的公正和记录的真实,但也免不了采用道听途说的史料和用小说笔法修饰自己记忆模糊之处。在往后的几千年历史中,每一个史家都将维护历史著作的“真实性”作为基本原则,但“真实性“在史学中的贯彻历程是曲折的,在中世纪,随意篡改甚至伪造历史司空见惯。蒙森的《罗马史》,以严谨的史学功底为基础,高超的小说笔法为辅助建构罗马的兴衰过程,让整部小说在真实性和艺术性上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中国史学对于将历史和文学区分开的觉醒相对来说晚一些。中国史学从一开始就和“官府”粘连在一起。中国的甲骨文、金文,以及春秋末年经过孔子整理编纂而成的《尚书》、《诗》的一部分代表了中国史学的萌芽阶段,这些文本虽然原本是为了记录历史事实而存在的,但是在实际的书写过程中由于主观和客观上的种种原因,却往往发生“修辞”盖过“纪实”的现象。比如为了寻求对仗的工整而加减词句,受限于记录载体(甲骨、青铜器、竹简等)而被迫省略历史细节,为了讨好统治阶级或者阐释作者的政治理想曲解自然现象,将神话不经考察当作历史事实进行记录。
孔子曾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4]虽然这句话的原意并不是来描述文学与史学的关系的,但它其实高度概括了中国古代文人内心对于两者关系的态度。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中国古代的文人多“取文而舍史”,更多在史学的题材,纂史的方法、史学人才的培养等方面做文章,而缺少带有哲学思辨的形而上的讨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发达的史官文化既是中国古代史学繁荣昌盛的基石,也是阻止史学向更高层次的境地发展的枷锁。
众所周知,《史记》是中国古代史学最为杰出的代表之一,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对于司马迁为了著作的文学性而牺牲了史学的真实性的批评其实一直没有停过。全书在记载历史事实时大量使用了人物的对话甚至心理描写,明显带有作者本人再创作的痕迹;再比如尽管作者本人对于三皇五帝的神话持保留态度,但这些神话传说对于阐释作者本人“华夏一统”的思想有帮助,便也在文中保留了下来;还有尽管作者创造了纪传体通史的体例,但在具体书写时又经常因为自己的主观意愿而“跳脱”出来,典型如给项羽、吕后立本纪。
如果说司马迁的《史记》问题在于再有“失之过详”,那孔子的《春秋》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体现。《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私人撰述的历史著作,也可以说它是后世众多私人修史的范例。《春秋》最大的特点便是“微言大义”,仅用约18000的篇幅便书写了春秋时期242年的历史,可见作者笔力之深厚。但是《春秋》这样做就丢失了很多历史细节,客观上给后世的读者造成了很多困难。《春秋》实质上发明了关于“礼”的语言,读者必须实现对于孔子的礼学理论有所了解才能正常阅读这本书,不然在阅读《春秋》时很容易陷入不知所云的境地,仿佛是在解读一个个字谜。[5](P102-105)
总的来说,历史与文学实在是难以分开的,如果没有文学的辅助,史学实质上是难以存在的,重点是如何把握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无限追求“真实”本身并不符合史学发展的要求。反过来讲,因为对史学“真实性”失去信心,转而形成“疑古”的唯心主义倾向也是不可取的。
二、史书撰写的“客观性”体现
“客观性”反映的是修史者的立场问题。修史的目的、选择的题材、修史时的态度、对一些关键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等均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反映出作者的立场选择。一般认为,修史者应该在修史的过程中尽量避免自己情感的代入,保持一种冷峻客观的风格对具体的历史事件进行如实记述。但实际上,从历史学的发展来看,对这一原则的贯彻是有反复的。尤其是近代史学研究兴起之后,跨学科研究的格局逐渐形成,受各方面影响,这一史学的“基本定律”变得更加动摇起来。
中国古代对于史学一些基本原则的探讨一直比较少,通常散见于各种历史著作中。中国古代第一部有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诞生于盛唐时期,刘知几的《史通》成书时间大概在公元710年左右,此时距离孔子修《春秋》已经过去了1000余年。《史通》的成书动机据刘知几自己说是因为自己不满朝中对于自己修史工作的横加干涉,故而“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6]这实际上也是大多数中国古代私人修史的者的动机。在书中,作者认为史书应该“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这实际上就在讨论史家主观意识和客观历史存在之间的关系。刘知几也提出了自己的史学批评标准——“记事之体,欲简而且详,疏而不漏”。[6]
客观的说,从中国史学诞生之日起,史家就在有意识地坚持自己修史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但中国史学的形成从一开始就和官府紧密粘连在一起,是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的。
首先,从史官的角度来说,史书在很多时候是他们政治生涯的附带品。中国古代修史者的修史初衷最为常见的就是政治仕途不顺,故而归隐田园修史,以此来阐发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所谓“仲尼厄而作春秋”就是如此,这就让他们在修史时很难保持一颗平常心,针对性地选择历史材料,在史书中添加自己的价值判断就是司空见惯了。尽管优秀的史官都会严肃对待自己的历史材料,但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也难以减少他们史书中的主观性。胡适等人曾评价《春秋》与其说是一部史书,不如说是一部经书,这一见解有其深刻的一面。中国史书“字带褒贬”的风格确实是和史学“客观性”的要求相悖的。
其次,中国古代经学的过度发展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客观性在史书中的贯彻。自董仲舒创立“天人感应”学说以来,一套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在一起的帝制神学体系便统治了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思想。[7](P15-19)在中国古代史书中随处可见“祥瑞”的影响,皇帝出身要么是“满屋红光”,要么是“龙凤盘绕”“凤鸣三日而不绝”。这种思想尽管也遭到过质疑,但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史。
西方史学对比于中国史学在客观性的觉醒上更为明确。早期的西方史学更多的带有“回忆录”的性质。纵观古希腊史学的名家,他们有很多都是早年位居高层,亲身经历了很多历史上的“大事件”,晚年他们功成身退,撰写回忆录来记录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这样的修史目的虽然很多时候不免让他们的文字有矫饰的嫌疑,但更多时候是让他们的文字相对平和,能够以一个较为公正的态度来进行记录。另一方面,“城邦政治”对整个西方社会影响至深,这就给了个人很多活动的空间。优越的生活再加上地中海温和的环境给了古希腊的思想者们充分的土壤。沿着地中海一圈,各种文明交相辉映,在彼此侵伐的过程中也在互相影响、融合。古代西方史学天生带有的哲学性和思辨性的原因或许就因此而来。也是在这个时期,史家们就已经明确提出了客观性的原则。修昔底德在创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他在书中让自己先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充当中立的法官,始终先让战争的当时双方均等陈述,然后再根据他个人的价值准绳对事实做评价。
实际上,无论中西方史学,真正彻底实践客观主义精神的史学只是极少数,大多数历史著作或多或少都带有很多作者的主观意图。近代以来,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一类学者主张跨学科研究,扩展历史研究范围,丰富历史研究的方法,历史研究也往往和社会研究、经济研究等混杂在一起。越是在这个时候,历史客观性的原则实际上就越应该得到贯彻。
三、新时代的历史研究方法
年鉴学派或许是新时代历史学众多学派中影响最广的一只。年鉴学派以社会史为中心,认为只有包括人类事实总和的历史才是完整的历史。年鉴学派以解释为目标,要求多学科综合性的研究,力求突破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史学的窠臼。
首先,在研究方法上使用了“大文科”的综合研究方法,社会学、民俗学、政治学、经济学、人口学、统计学甚至文学、法学等学科的方法都可以为自己所用,这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回到了历史学的本源上。应该说,新时代史学是具有中国传统儒学内核的,由“以史为鉴”“知行合一”的思想出发,进而形成了一套以试图解决人类生存问题而出发的理论。张载曾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亦可以成为新时代史学的宗旨之一。新时代史学不囿于学科间的桎梏,而强调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各种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即所谓“六经注我”。
其次,“官修史书”或许会成为未来史学的主要研究方式。“官修史书”具有两大特点,第一是与官方合作,充分享受组织丰富的人力物力;第二是多人合作模式。新时代史学走上“官修史书”的道路很多时候是一种被迫的结果,其实也就是受限于人力和财力的不足。首先,上文提到,在新时代史学中,统计学工具非常重要,那么这就势必需要大量的数据作为支撑。而新时代史学的目光聚焦于过去社会的中下层这些“被忽视的人群”,那么实际上有关的数据就要少得多。因此,我们在做研究时极为重视类似于“县志”、“鱼鳞册”等官方文书。官方文书的特点就是详细繁密,卷帙浩繁。要从这些材料里找到自己想要的材料无异于大海捞针。再加上那些易于得到结果往往已经被前人“掘走”了,想要得到新鲜的论点和数据,只能无限往深度进行挖掘,这样极为消耗精力和时间,而且有大量的时间被浪费在了甄别材料上。通过与官方合作,可以让这一过程大大缩短。其次,年鉴学派虽追求的“总体史”、“整体史”视角虽然被很多学者所批判,但是试图对过去社会进行全景式描写的尝试却几乎可以见于每一本相关著作。人类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混沌杂乱的系统,若想做全景叙述,就要求你对各领域都有相当深度的认识,成为一个“通才”。这在今天的社会更加不可能。因此,多人合作势在必行。想要像过去那样吸引“贵族”、“闲人”来进行研究很难再发生了。让官方托底,为研究者提供各方面的支持是很可能的一种研究途径。
最后,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史学的哲学底色。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两大特色,阶级划分和经济史研究方法,这两点已经被今天的历史学家们广泛接受,成为他们进行历史研究时最为基本和普遍的方法。[8](P151-158)德·圣克鲁瓦在《古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一书中对于阶级进行了定义:阶级是一种社会关系,一种客观存在实体,也是社会的一种集团,识别这个集团需要看它在整个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最重要的是根据它与生产条件(即生产资料与生产劳动)的关系来加以确认。[9](P348)经济史研究方法则是对于历史本质的一种研究方法。将社会的生产关系看作社会进步的推动力之一,以此来解释诸多社会现象。这样,通过阶级和经济两把钥匙,历史研究者找到了解释人类社会这个混沌系统的钥匙,从此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过去一切历史现象似乎都有了新的解释,原本似乎枯竭的历史之泉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总的来说,东西方史学在欧亚大陆的两端沿着自己的轨迹发展千年,交相辉映,彼此都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历史叙述逻辑。相比较西方史学对于客观性的反复强调,东方史学总体上更加注重历史的现实意义,把历史学当作政治的一种衍生。当然,对历史客观性的追求是两方史学一以贯之的,尤其是近代以后,这一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
新时代以来,历史学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一方面是自然科学武器大量被运用到历史学书写中,美国加州学派的量化经济史研究已经成为了今天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是历史学本身在叙述对象上的大大扩展,以往步入历史学家“法眼”的下层平民生活成为了今天历史学的主角。
近年来,社会史研究方兴未艾,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也变得异常迫切,但由于其呈现的历史现象并不久远,客观上更容易带上主观的烙印。因此在历史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更要注意厘清上述讨论的三个问题,从而为科学研究提供理论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