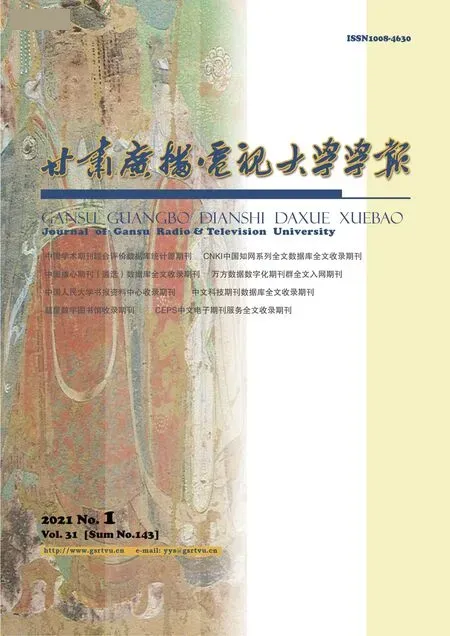庾信拟阮诗的继承与新变
——以阮籍《咏怀诗》与江淹、庾信拟阮诗的比较为基点
陈雅妮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自古以来便是公认的难解之作,刘勰《文心雕龙》的评价是“阮旨遥深”[1],钟嵘对其评价“厥旨渊放,归趣难求”[2],诗中使用了大量的意味不明的典故和模棱两可的意象,使诗歌的主旨也变得隐晦而曲折。另外,陈伯君还认为,后人在编辑这组诗并取名为《咏怀诗》时,其实也融入了不少自己的理解与想象[3],这些都是阮籍《咏怀诗》令人难以捉摸的原因。但在模拟文学盛行的六朝,阮籍《咏怀诗》却是许多文人乐于挑战的摹写对象,其中就包括了江淹和庾信。庾信是南北文化的集大成者,他的拟阮诗也体现了他对诗歌创作的思考,但学界对庾信《拟咏怀》的研究重点往往在乡关之思的情感价值上,鲜少结合阮籍原诗和前人拟阮诗来做体式对比,忽略了庾信拟阮诗在继承与新变上的诗学成就,为弥补这一遗憾,本文从诗歌体式的角度,来分析庾信拟阮诗对前人的因革,并总结其成就。
一、庾信拟阮诗概述
六朝是模拟风气渐盛的时代,六朝文人以前代经典为摹本,或学习文体,或力求相似,或展示文才,或借题发挥。在摹拟的过程中,他们促进了文体的成熟,推动着诗歌技巧的发展,其中江淹、庾信就是六朝拟诗的砥柱人物。江淹拟阮诗《效阮公诗十五首》是借古讽今,为进谏幕主刘景素而作的,而《杂体诗·阮步兵籍咏怀》(以下写作《阮步兵籍咏怀》)则是为了“学其文体”[4],但庾信《拟咏怀二十七首》的创作背景如何,暂时没有明确有力的材料来佐证。
(一)庾信拟阮诗的创作时间
林怡认为《拟咏怀二十七首》中展现了复杂多样的情感与思想,绝非一时一地所作,时间跨度至少长达二十多年[5]。而据牛贵琥考证,庾信《拟咏怀二十七首》应作于入北后的三年内,因第二十一首的内容与《枯树赋》相同,而《朝野佥载》的记载又可证《枯树赋》是作于入北后[6]36,那么《拟咏怀》也应作于此时。综合二家看法,笔者重新审视《拟咏怀》,该组诗无论在叙事内容还是情感表达上都复杂多样,可见庾信在创作期间的所见所感并非静止不变的,这也侧面印证了林怡所言,非一时一地之作,但从具体内容考察,描写江陵之战与梁元帝之悼的诗篇毕竟仍占大多数,说明大部分内容应如牛贵琥所言,作于入北初年。
(二)庾信拟阮诗的创作意图
至于《拟咏怀》是否有阮籍《咏怀诗》那样具有政治避祸与心情发泄的意义,学者们亦有不同说法,但认为二者具有相似创作背景的占多数。清代的倪璠认为庾信入北后作《拟咏怀》与阮籍在魏晋更替之时作《咏怀诗》,具有相似的政治处境,是“虑祸而发”的不得已之作[7]229。许逸民认为庾信出仕魏、周后因目睹多方战乱而作《拟咏怀》,有哀民生多艰之情[7]2。许东海《庾信生平及其赋之研究》认为诗中所写皆是“国破之伤恸,羁旅之愁苦”[8],牛贵琥亦是同样的看法[6]40。唯有赵红玲《六朝拟诗研究》摒弃了庾信“历四朝”而“奉十帝”生活经历的影响,仅从庾、阮二人两组咏怀诗的异同质素上入手,认为庾信拟阮并不追求相似[9]138-150,用词用意都体现了他个性化的诗歌追求。
综上所述,庾信取阮籍《咏怀诗》为模仿对象绝非率意而为,由南入北的人生经历也必然对他后期的创作有不小的影响,但不能因庾信一时一地的经历便给他后期所有作品烙上贰臣悲苦心态的印记,且《拟咏怀》展现出的思想感情也绝非一个简单的标签所能概括的,诗中展示的摹拟技巧、艺术风格、文学思想也不该被低估和忽略。
二、庾信拟阮诗的继承
在庾信的时代,阮籍以其独特的经历和个性成为了时人的精神榜样,同时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传播,也让诗人更加注重模拟创作时的体制规格。庾信《拟咏怀二十七首》的创作,不仅继承了阮籍原作《咏怀诗八十二首》,还有许多对江淹拟阮诗《阮步兵籍咏怀》《效阮公诗十五首》模仿的痕迹。庾信主要是对阮、江二人诗作中字词、句式、篇章等方面的一些沿用。
(一)字词的使用
字词包括了用字和用词,庾信在用字方面继承了阮籍用词的习惯,主要体现在数字、叠词和典故的运用上。
在阮籍《咏怀诗》中有大量具体的数字,除去像“二妃”“两仪”“八荒”这样具有特定历史、文化意义的数字词之外,阮籍最喜欢用的是“三”这个数字,如“三旬”“三山”“三荣”“三衢”等,可以看出阮籍在数字使用上的偏好。江淹拟阮诗几乎不见数字,庾信《拟咏怀》诗中却广泛运用数字,但庾信最喜欢用的数字是“一”。除去“一旦”“一朝”这样的具有状语意义的词汇之外,还有不少像“一郡”“一思”“一杯”这样的词,甚至为了使用“一”这个数字,不惜在句中犯重字和“八病”中的“小韵”,如“一顾重尺璧,千金轻一言”(《拟阮诗》其六)。庾信生活的时代已经是永明新声推广的时代,不可能明知故犯,可见庾信对阮籍数字使用的继承与偏好。
从叠词的使用方面,也能看出庾信对江淹拟阮诗的继承。庾信《拟咏怀》(其一)第三、四句的“索索无真气,昏昏有俗心”正好与江淹《效阮公诗》(其一)第三、四句的“戾戾曙风急,团团明月阴”有所对应,最显眼的就是叠词的继承关系,“索索”“昏昏”对应了“戾戾”“团团”。此外,庾信还将这种叠词广泛运用到了全诗中,如第十九首的“愦愦天公晓”“其觉乃于于,其忧惟悄悄”,第二十四首的“昏昏如坐雾,漫漫疑行海”,第二十五首的“怀抱独昏昏”。
从用典的角度考察,也能探知庾信在字词使用方面对原作的一些继承。阮籍《咏怀诗》之所以晦涩难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典故的大量使用,而庾信拟阮诗为拉近与原作的距离,一方面如阮籍一般频繁地用典,比如频繁地在诗中插入具有关塞历史意义的词汇,如“终为关外人”(其五),“榆关断音信”(其七),“遥看塞北云,悬想关山雪”(其十),“人多关塞衣”(其十七)等;另一方面则是大量地沿用原诗典故,如“湘水竹”(其十一)对应的是阮籍原作“二妃游江滨”(《咏怀诗》其二)中所用的娥皇、女英典故。“游子河梁上,应将苏武别”(其十)对应的是阮籍“李公悲东门,苏子狭三河”(《咏怀诗》其十三)中李陵、苏武赠别的典故。
(二)句式的模仿
对原作句式的模仿,可以说是拟诗作家常见的摹拟方法,并非庾信独创,但从直接引用和适当变式两种继承方式来考察庾信的拟阮诗,亦可窥得几分庾信的摹拟功力。
此外,江淹拟阮诗本身已经继承了不少阮籍诗的句式结构,庾信拟阮诗常常通过对江淹拟诗的参考与借鉴,来加强对阮诗的理解。如阮籍《咏怀诗》(其一)中的“翔鸟鸣北林”,“鸟北林”这一句式被江淹《效阮公诗》(其一)继承为“宿鸟惊东林”,而庾信捕捉到了江淹句式中“惊”的独特性,在《拟咏怀》(其一)中将其改造为“惊飞每失林”句式。还有“白马向清波,乘冰始渡河”(《拟咏怀》其八)这一句,阮籍原诗写作“驱马复来归,反顾望三河”(《咏怀诗》其五),江淹的《效阮公诗》“昔余登大梁,西南望洪河”(其八)只继承了原诗后半句的“望河”。庾信深知阮籍在句式组成上以“马”为意象的偏好,如“天马(汉武帝《天马歌》)出西北”(其四)、“良马骋轻舆”(其五十九)、“鞍马去行游”(其六十六),他在江淹拟阮诗的基础上对前半句进行补充。这种继承方式看上去似乎与阮籍原诗关系不大,但实际上却是多次摹拟加工后的精益求精。
当然,庾信也有跳过原作,直接继承前人拟作句式的地方,如江淹《阮步兵籍咏怀》的“精卫衔木石,谁能测幽微”其实是基于他自己的理解而新造的句子,庾信或是认为能紧扣阮诗主旨,或是觉得可以准确地表达自己的心境,将这个句子加以变式,融入进了自己的拟阮诗中,成为了《拟咏怀》(其七)中的“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断河”。类似的继承情况还出现在江淹《阮步兵籍咏怀》的“朝云乘变化”与庾信《拟咏怀》(其一)“风云能变色”之间,也是阮籍原诗没有,经过江淹的新创之后由庾信拟诗继承了这“云变”的句式结构。
(三)篇章的呼应
篇章包括诗歌篇幅和章节构成,阮籍的《咏怀诗》和江淹、庾信的拟咏怀诗均为组诗,每几首诗相当于一章,每几行诗相当于一节,彼此之间错落有序、互相对仗、遥相呼应,共同谱写出一组或起伏跌宕,或层层递进的奏鸣曲。
首先是诗歌篇幅,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奇数行偶数行的诗篇各半,三行至九行诗都有,还没有对诗行数量的明确偏好,鲍照《拟阮公夜中不能寐》仅一首,是四行诗,及至江淹《效阮公诗十五首》《阮步兵籍咏怀》的五行诗共10首,数量过半,江淹以“学其文体”的眼光去看待阮籍诗,认为以五行为代表的奇数行篇幅去展现阮籍《咏怀诗》最为合适,此后拟阮诗篇幅基本都是奇数行,五行诗的比例亦大大增加,如庾信《拟咏怀二十七首》五行诗15首,亦过半数,显然是受江淹影响。
此前阮籍一行之内鲜少用多个典故,如“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咏怀诗》其四),一般前句用典、后句抒情,一行一典才是阮诗主要的布局方式,而江淹“暂试武帝貌,一见李后灵”不仅一行用两典,用典的位置还极其对仗,间接促进了诗行间的对仗,庾信《拟咏怀》亦是如此,诗中有大量的像“吴起尝辞魏,韩非遂入秦”(其五)这样的对仗方式。除此之外,诗行间也多有对仗,如“横石三五片,长松一两株”(《拟咏怀》其十六),无论在名字、量词、数词的对应上都非常地完美,远超阮籍的“鉴兹二三者,愤懑从此舒”(《咏怀诗》其五十九)。不过这一点若放在六朝诗学演变的大背景下看,与其说是庾信继承了江淹的行文方式,倒不如说是六朝对仗意识对诗歌创作的普遍影响,此处仅做参考。
诗行之外,还有章节间的对应,如阮籍《咏怀诗》第十二首第二行有“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下面第十八首倒数第三行的“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却又遥相呼应上了。这样一头一尾相隔几首诗的章节回环方式在江淹拟阮诗中也有体现,江淹《效阮公诗》第四首首行“飘飘恍惚中,是非安所之”与第五首末行“变化未有极,恍惚谁能精”前后对应着。庾信也继承了阮、江二人这种章节回环的排布,《拟咏怀》第二首末行“既无六国印,翻思二顷田”与第十五首首行“六国始咆哮,纵横未定交”构成了回环对应,而“步兵未饮酒,中散未弹琴”(其一)、“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其十一)与“榖皮两书帙,壶卢一酒樽”(其二十五)章节之间隔了10首诗以上,甚至还形成了以“酒”为线索的三重对应,从不饮酒到一杯酒,再到一壶酒,逐渐展现了一个嗜酒之人借酒浇愁的心路历程,从总结构上看,这个布局也更为精细,可知庾信在继承的过程中亦有自己的思考和改良。
三、庾信拟阮诗的新变
通过上述同质分析,其实已经能窥探到庾信在对阮、江二人继承的过程中的一些细微变革,但这些变革还谈不上新变,只是基于传统摹拟手段的一些微调,庾信拟阮诗真正表现出新变的是在韵律、意境、主题等方面。
(一)韵律的完善
韵律包括诗歌节奏与押韵,五言诗的节奏一般分二一二型与二二一型,一般二二一型节奏要比二一二型更为舒缓,而押韵因不同朝代用韵习惯不同,本文不讨论韵脚的类型,只粗略地考察庾信拟阮诗中押韵的方式。
首先是节奏,阮籍原作《咏怀诗》中鲜少二二一节奏型,即便偶尔有一两句,下一句很快又重新调整为二一二型,如“昔日/繁华/子,安陵/与/龙阳”(其十二),“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其十五)。而庾信《拟咏怀》虽也以二一二型为主,但二二一节奏也不少,起码是有意识地在某些地方使用二二一节奏,如“自怜/才智/尽,空伤/年鬓/秋”(其三)、“惟彼/穷途/恸,知余/行路/难”(其四),一般用在诗篇的末尾,上下句节奏一致,舒缓节奏,以表落幕之意。此前江淹《效阮公诗》虽也有意识地运用二二一型,如“荣光/河雒/出,白云/苍梧/来”(其七),但使用的位置并不固定,因此这算是庾信在节奏型上有意而为之的新变了。
其次是押韵,阮籍《咏怀诗》、江淹《阮步兵籍咏怀》《效阮公诗》基本都能做到隔句押韵,且有不少诗歌是一韵到底。而至庾信《拟咏怀》时,几乎每一首诗都一韵到底,即使是没能一韵到底的第二十五首,押的也是“论”“源”这类近韵,并通过交韵的方式,让两种近韵交替出现在诗篇中,减少了异韵带来的生涩感,促进了诗歌韵律的和谐。庾信之前,与“四声八病”紧密联系的永明体已在文人圈里流行。如果说阮、江二人对于押韵的探索,还有一部分是在依赖天才性的直觉和习惯性的经验,那么到了庾信这里,完全就是理论和实践的自觉结合了。他的拟阮诗有多首押同韵的情况,并且还是相邻的几首,如第五首的“臣”韵与第六首的“恩”韵,第七首的“过”韵和第八首“河”韵,都可以体现出他在押韵方面的自主选择与自觉调整,这也是庾信拟阮诗对押韵的贡献与革新。
(二)意象的特色
诗歌意境主要依赖意象而建立起来,而意象是由客观物象与主观用意共同构建的,即客观的“象”与主观的“意”,通过诗人的融合而进入作品。
庾信拟阮诗中的意象与阮籍、江淹的咏怀诗有着很大差别。阮籍《咏怀诗》频繁使用的是《诗经》《庄子》《楚辞》《山海经》等典籍中具有仙道意义的文化意象,如“玄鹤”“凤凰”“青鸟”等飞鸟意象,还有“扶桑”“瀛洲”“吴洲”等地理意象,以及“飞泉”“兰房”“华树”等植物意象,共同构建的是阮籍心中的理想净土,这些意象表达的是对于求仙问道的渴望,亦是阮籍在现实中努力寻求避世的映射。江淹拟阮诗中的意象基本与阮籍《咏怀诗》中的无甚差别,只多了一些具有儒家政教意义的意象,如“松柏”“圣贤”“君子”“朱门”,也与他作诗以讽谏的目的不无关系。
庾信的拟阮诗中用得最多的是《左传》《史记》等典籍中具有时代厚度的历史意象,如“六国印”“燕客”“穷途”“尺璧”,与阮籍、江淹二人的“东门”“南岳”“西戎”“北山”这些历史意象也不同,庾信的落脚点在于以史明鉴,以历史成败经验来警醒自己和后人,而不是单纯地铺叙。此外他还格外偏好在天空、黑夜中能发出光亮的意象,如“残月”“直虹”“烽火”“落晖”“萤”“流星”“长星”,这样的意象往往具有不祥的暗示,使人联想到战争、分离、死亡,而这些卑不足道的微光与无尽黑夜、浩瀚星空放在一起映照对比,也让诗歌意境蒙上了一层浓厚的悲壮色彩,透露出诗人背后难以言说的失落、迷茫、悲愁。
(三)主题的深入
组诗一般都有一个大的核心主题,所有诗篇围绕这个核心主题各自阐发,但由于阮籍、江淹、庾信这几首诗都是比较大型的组诗,且也非一时一地所作,在具体行文中,自然也会根据具体的因缘际会而衍生出一个个小主题。
从大主题上看,阮籍《咏怀诗》主要围绕着坎壈咏怀①来阐述,各种意象、用典也是围绕着路途遥远、命运多舛来铺排的,如“方式从狭路”(其十)与“一身不自保”(其三);而江淹《效阮公诗》是基于政治教育的目的来展开,用词造句多精警、庄重,如“忠信主不合”(其三)与“富贵如浮云”(其二);庾信《拟咏怀》大方向上的确是围绕乡关之思来展开的,在环境上常常构建离别的场景,营造愁苦的氛围,如“燕客思辽水,秦人望陇头”(其三)、“雪泣悲去鲁”(其四)、“榆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其七)等。
而在核心主题之外,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除去坎壈之叹,还有对时光易逝的感慨,如“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其四);对世事无常的认识“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其三);对长生自由的向往,如“独有延年术,可以慰我心”(其十)。江淹《效阮公诗十五首》除去政教警示,还有对怀才不遇的哀愁,“志气多感失,泪下沾怀抱”(其三);对前贤的追思,如“高阳邈已远,伫立谁语哉”(其七);对朝堂乱象的批判,如“唯有驰骛士,风尘在一朝”(其十五)。至庾信《拟咏怀二十七首》,除了上述主题外,还多了对历史经验的思考,如“既无六国印,翻思二顷田”(其二);对当前时局的担忧,“倡家遭强聘,质子值仍留”(其三);对人生经历的反思,如“一朝人事尽,身名不足亲”(其五)。
四、庾信拟阮诗的成就
庾信拟阮诗的成就包括摹拟技巧、艺术风格、主旨思想等方面的成就。摹拟技巧方面,庾信在继承前人之作的过程中致力于创新;艺术风格方面,庾信在模拟的时候也融入自己的特色和思考,使拟诗成为己诗;诗歌主旨上,以古典写今事,融汇古今,以史明鉴。
(一)摹拟技巧:在继承中革新
虽然本文从诗歌体式的角度,将庾信拟阮诗中的继承与新变分而论之,但事实上,继承与新变是密不可分的,正如赵红玲在《六朝拟诗研究》中所说“庾信《拟咏怀诗二十七首》的摹拟,并不是摹拟习练式的,拟作与原作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且在语言、用典、对偶、声律各个方面与所拟原型存在很大距离。”[9]146结合上文亦可知,庾信在字词、句式、篇章上的继承并非单纯地沿袭,往往具有革新的意义,而在韵律、意境、主题发挥上的新变也非突兀地替换,而是建立在知己知彼基础上的发挥所长。
(二)艺术风格:化拟诗为己诗
(三)主旨思想:以我手融古今
庾信拟阮诗中展现出来的思想大多为古今成败之思,这些思考不仅是对历史事件单纯的复盘,更是庾信依据亲历事实而挑选的历史经验,一方面给自己情感宣泄的一个出路,借前贤的相似经历来抒发自己的凄楚郁闷之情,另一方面也是用历史典故来警示世人,通过吴起、韩非子等先秦诸子的成败经历,告诫世人曾经的政治建树与少年豪情终究会随着政权的更替而逝去,要学会在反思中接受现实、放下执念。另外,拟诗本身就具有一种和原作、前人拟作的天然联系,它既是一种传播媒介,也是一种沟通枢纽,勾连着古今相同的诗歌主题,抒发着人生代代无穷已的感慨,而庾信的拟阮诗,正是在这种历史厚度的加持下,有了融汇古今的深度。
注释:
①此处套用钟嵘对郭璞的评价,参看《诗品集注》“乃是坎壈咏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