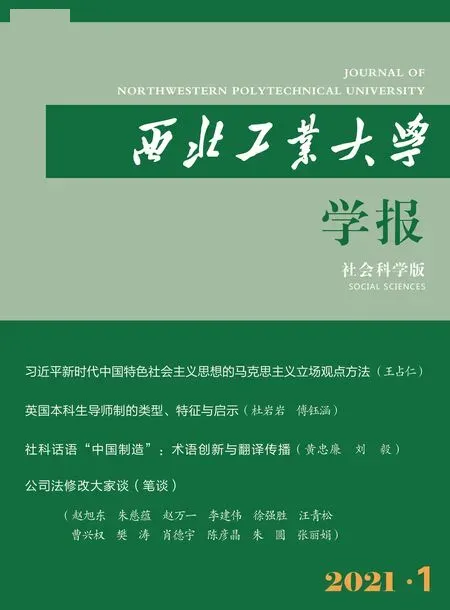比较生态批评视野下早期生态批评的轨迹及其特点管窥
史忠义
学术界一般以为,美国学者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①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是生态批评的肇始,因其肇始的缘故,这部著作不断地提出它的性质问题:这是一部科学普及读物抑或战斗檄文?还是一部意味着平静生活终结的世界末日性质的作品?毫无疑问,它是这一切。但又远超过这些:如果它仅是这些,1962年初版时能引发数十万读者的兴趣吗?
《寂静的春天》1994年再版,美国民主党前副总统艾伯特·戈尔②为作品写了导论。戈尔在导论中强调了这部作品的战斗意义及后来对联邦政策或美国各州政策产生的效果。戈尔指出:“1962年,当《寂静的春天》初版时,环保(environnement)一词甚至不构成公共政策词典的词条”③。蕾切尔·卡逊细数每个人或直接或通过食品的迂回承受杀虫剂的风险。这部首创了责任语言和警惕语言、某种程度上建立了一种文学体裁的作品,以非常独特的方式在美国政治辩论中秉持立场,指责联邦政府对公共政策的调节力度很弱;总之,联邦政府是不负责任的。自此,一种大的分野形成了:应该让地方政府发挥它们的主动性,尤其是各州政府,或者变化的渠道是联邦机构的责任,这种机构构成一种特别强大的杠杆,可以超越由与地方利益相关的政治团体密切关联的内生现象所生殖的安排呢?卡逊希望有一个强大的裁决者。她把自己的作品设想为公民责任的矢量,这是所有环保文学的共同特征,她根据美国政治生活的特殊语境来建构这种特征。在叙述因使用灭虫剂而导致一种有毒蚂蚁种类的灭绝时,蕾切尔·卡逊的矛头直指美国农业部:“简言之,农业部在推行它的计划前,没有就人们对农业部考虑使用的化学产品的已有知识进行丝毫的基础调查,或者做了调查,但忽略了它发现的问题。”④这是一种最清楚不过地呼吁联邦机构更加提高警惕的方式。我们知道,提出对公民负责的要求是文学家的权利,但是这种要求方式还是相对简单了一些。
一、《寂静的春天》与《瓦尔登湖》的简略比较
任何试图抓住科学问题、让科学数据进入民主程序的举措都面对言语的简单直白问题。一种详尽而透彻的方法能够在此处还原它在彼处剥离的内容吗?无须怀疑,蕾切尔·卡逊知道罗列农田里或其他种植场或养殖场所播撒的所有化学产品的名称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在她的作品里还是存在一种与奇葩的化学名词相关的恐惧诗学。七氯滴滴涕或环氧滴滴涕对农业、植物和人类的影响,可谓从漩涡到岩礁;百鸟都死了,没有鸟鸣的世界也没有爱,然而这样的哀鸣何其多也。卡逊的作品里不再有鸟叫,因为它们被毒死了,生态环境受到了污染。环境文学给出的世界是一个濒临死亡的世界。宛如秋末的世界死了,人们不敢肯定来年春天它是否还能复活。我们培育了一个反循环的世界。环境文学展现的是一个无限倒退的世界(regressus ad innfinitum)。
环境文学又是一种详尽透彻的和敞开的文学。它想看清一切,表述一切。由于表述一个没有前途的世界的终结,它得到了传播。蕾切尔·卡逊的作品向肩负生态使命的文学提出了一个问题,同时又重建这种文学:这种文学能够不断地以哀怨模式重述被证实的或依稀窥见的灾难吗?重建而非建立,因为19世纪的亨利·戴维·梭罗(H.D.Thoreau)⑤享有无与伦比的魅力,自从《瓦尔登湖》(Walden Pond,1854)及其长达数千页的巨幅日记发表以来,美国的工业化已经实现,农业革命也发生了,朝着机械化、使用化肥及选择种植品种的方向发展。农商行业诞生了,与之相伴随的,是可疑产品的播撒。由于蕾切尔·卡逊的影响,在人类建立的与土地的关系方面,文学获得了新的思考空间,由此出现了穿越《寂静的春天》的这种详尽透彻的愿望。因而,梭罗与卡逊根本的不同在于,《瓦尔登湖》的作家盘点了一个完整无损的大自然,尽管这种大自然也留下了人们劳作的痕迹,但滴滴涕没有投下对农村欢乐气氛的怀疑。最早的美国生态文学没有抒写危害经验,也没有抒写高度城市化的经验。此后注定投身农业活动的农村变成了某种“大合唱”,用地理学家奥古斯丁·贝尔克(Augustin Berque)酷爱的定义说,就是“属于城市的农村”⑥。城市化深入了农村。阿兰·苏贝尔什科(Alain Suberchicot)显然把梭罗的《瓦尔登湖》视为一部含蓄的生态文学方面的著作⑦。
超越这个基本的区别之外,蕾切尔·卡逊的作品对其享有盛名的前辈的遗产并不陌生。以环保为使命、以生态为题材的文学并非一种决裂,并非从铲除一切原有文学的基础上升腾而来。像所有耐心培育和再培育的文学体裁一样,它与属于一种虚构想象思维模态的过去维持着关系,尤其与梭罗的想象建构起来的世界保持着关系。梭罗的作品反思几乎没有任何素材时如何构筑作品的艺术,无论如何,自然界的物品引起了作家的注意,尽管它们是那样的陌生或者微不足道。从已知走向未知是一道命令。1845年7月6日,当时梭罗正全神贯注于写作与《瓦尔登湖》相关的文字,他在日记中以既感叹又询问的格调写道:“我希望与生活中的事实相遇:生命事实,那是诸神想向我们展示的现象或实在,面对面地相遇,于是我来到了这里。生活!谁知道它是什么,它想做什么?”⑧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面对面的方式:世界有待破译,似乎作家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作者属于他描述的世界;他所描述的材料不在他面前,但是他驻足于它们之中。梭罗设置了这种面对面的场面,然后立即否决它:环境与生态作为概念是互相斗争的。前者设置了面对面场面;但是“家园”(oikos)思想在梭罗那里已经占了上风,因为我们深刻地感觉到,在梭罗那些外表平庸的新教徒模样的异域神的外表下,属于一种囊括个体比例的环境(cadre)概念出现了。
二、让-亨利·法布尔与美国文学的生态意识
许多生态题材的作家的一个特征,就是不断地建构事件。蕾切尔·卡逊以描写场景为特长;她构造种种故事的目的是让一种觉醒翩翩而至。许多作家已经完成了这种觉醒。法国有一个抒写自然的作家叫让-亨利·法布尔⑨,他也是文坛先驱,他有一部著作《昆虫记》在法国文化圈里很出名,第二帝国时期(1879年第1卷问世)出版以来,被一代代学人所阅读,2002年又再版了⑩。法布尔在人们无法叙事的地方开始叙事,意愿是向所有公众发声。在法布尔那里,有关二硫化碳杀虫的看法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苏格拉底式的对话。目的是消灭可能损害收获的象虫(米虫),一个名叫雅克的无姓氏人物出现了,带着内容不确定的瓶子,来保护西蒙大伯粮仓的收获物。他是个好农民,代表一种超越了自己的社会类型,他的姓氏的设想是有意为之。法布尔与其他许多抒写自然的作家一样,注重行为人的个体性,这种个体性在梭罗那里已经出现了。法布尔的行为人都是匿名者,因而很滑稽。当人们看见他们天真地接触现代化学产品的使用时,把人们熟悉的或者可以辨认出来的人士搬上舞台就不能不受惩罚。雅克的两位朋友对他这样说:“埃米尔:哎哟!真臭!这肯定不是清水,这臭味真受不了。儒尔:这是烂白菜发酵后的臭味。人们是用烂白菜做这种毒药吗?”⑪他们像苏格拉底一样饱含讽刺意味。
美国的环保作品沿袭了上述方法,人物众多,但处于隐身状态。他们只是被白描一下,一如法布尔作品里的儒尔和埃米尔一样。这种匿名现象是写作的一种逻辑结果。人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偏移中心的现象,因为作品的核心不是它所包含的行为人,而是自然世界或农村,作品把自然世界或农村作为自己的世界甚至建构它。毫无疑问,法布尔希望建立另一种农村世界:法布尔一方面欣赏这种世界的本来面貌,一方面将其现代化,因为陶醉于、沉溺于一种农村世界容易将其永恒化。由此产生了对这种农业技术及二硫化碳杀虫剂的危险展示的令人震撼的膜拜,当时的意向是表述农村世界应该服务于人们的消费,其时旧体制时期的饥荒并非遥远的过去。法布尔对农村的再现已经把人类的发展与任何阻挡化学在农村的使用可能带来的后果对立起来,以保护收获粮食的品质,因为化学产品也潜在地对农村人口以及所有使用农产品的城市人口带来危险。从这个视点看,甚至“环境”“生态”语词都可能维持它们之间的“中性争执”,这是朱利安·格拉克的漂亮说法⑫,意思是它们之间有高低之争。让-亨利·法布尔在他的叙事里呈现为环保人士,尚未达到深刻的生态意识境界。在法布尔那里,农村的时局为匿名农民的行为者提供了环境,作者在捍卫他们的利益,读者可以从法布尔的作品里感觉到,农村世界应该保留的思想悄悄地前行。
自19世纪起,美国文学很早就善于捕捉有利于再现大自然的机遇,当时自然首先被感知为危险世界,然后感知为可以无限开发的世界;人们过分倾向于把美国文学这种独特的风貌看作美国作家们面对他们置身勘探然后开发背景下涌现出的一种更大的反抗活力⑬。梭罗与自然界保持着信任后者的关系,他也是这方面的先驱,然后才成为法律修订委员,向世界指出了新的价值。然而,从这个视角看,法布尔在许多方面也是一个革新者。尤其是他从1855年开始写的《昆虫学札记》(Souvenirs entomologiques),他还是一系列捍卫法国农村遗产的著作的作者。他是马拉美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⑭的朋友,不乏先驱者应该拥有的好奇心。
三、法国勒芒喂养肥母鸡引起的联想
法布尔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使用自然的问题,这个问题确实是生态作品的问题。因为勒芒的小母鸡要承受残忍的处理,才能从母仔鸡变成肥母鸡:它们被迫使劲吃,被囿禁起来养膘,不再可能下蛋了,与公鸡没什么区别。法布尔详细描写了法国西北部城市勒芒喂养肥母鸡的所有方面。他的意向是赋予自己的作品以技术性,可以向农村世界提供经济发展即人们的发展思路,唯一的目的是改善农村的生活,强化资本和知识方面的弱势群体。勒芒特供母鸡的食用品质面对公鸡的骄傲姿态最终占据了上风。这些母鸡身上蕴含着布尔乔亚阶层的命运和令人怀疑的财富,一个时期内,富人受盎格鲁-撒克逊保健思想的影响下变瘦之前,喜欢向没有财富、无法变胖的人们炫耀他们的肥胖。法布尔很惊奇,他不知道是该欣赏母鸡的肥胖还是欣赏一种严谨的、可以避免过度营养尴尬的节食态度,因此他对勒芒的小母鸡很怜悯。法布尔在食用和不食用这种特殊肉鸡之间犹豫不决,不知所措,因而突出了下述问题的中肯性:人有权食用活禽吗?
于是我们进入了法国人恐惧的核心,这些恐惧诞生于一种普遍的心理活动:害怕超越了家乡的影子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因为爱自由并不比爱家庭能让那些感觉到家乡热情的人们更肥胖。法布尔从自己的担忧逻辑出发,提出了一个伦理问题:
儒尔:我很怜悯这些爬在暗处格子里动不了的禽类,它们被强迫喂食,直到憋气的地步。
保尔:这种怜悯出于一种很自然的仁慈;我赞同;但是怎么办呢?因为小肥母鸡是我们的必需品,还是要下决心想办法让母鸡变成肥母鸡。我们的生活靠动物的生命来维持。⑮
法布尔作为一个生物学家,知道人与动物之间的依存关系,他自然会想到人类犯下罪过导致的过分行为。但是,法布尔关于调节有序的农村生活功绩的见证却把那些活动者置于他的关注的边缘。属于他们的只有对法国社会历史上形成的、很难结合起来的肥瘦两分现象的反映,害怕灾荒这个旧体制时代遗传下来的观念长期在农村肆虐,如同它长期在中国社会肆虐一样,中国社会如今仍然划分为城市和农村,且农村占大部分⑯。这样我们就容易理解,即使在美国,已经实现了食物丰盛的诺言,但食物丰盛的强烈愿望仍然是任何生态思想有可能破碎的障碍,这就解释了环保文学总体上让活动者匿名隐退的原因,因为环保文学的消费目的是盲目的,害怕贪食。这也让我们明白了这类言语碰到的困难,面对发展问题,包括在相对富裕的国家。一方面是环保文学的反抗:最好自我节制;另一方面是补偿:让我们在新的文学界线里彪悍一些;并且获得觉醒。
四、林语堂的风景观
在西方接受教育的知识分子、评论家林语堂(1895—1976)的著作部分在上海发表,部分在纽约出版,他文笔细腻,英文部分很有英语著作的特色。作品强烈地关注风景及其界定,这种界定源自对城市和农村二分法的敏感性。林语堂有一卷英文随笔集(The Importance of Living)尝试捕捉中国文化力量的粗线条。尤其关涉其本根文化的绘画传统时,他曾这样说:“大自然永远是一所疗养院。人应该被安放在自己的位置上,当自然充当背景时,人永远被安放在自己的位置上。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中国画作上,人的影子在风景中被压缩得很小”⑰。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对自然风景的敏感性与风景中人物的可视性相对受限制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反相成的对应现象:这个稍多一点,那个就少一点。中国的环境史真正帮助林语堂建立了他的风景观。中国的风景深受砍林风之害。这种砍林风已有数千年的历史,17世纪达到了高潮⑱。由此引起的环保方面的巨大困难,使林语堂一定会对此做出反应,即他对土地及其资源的过分使用很警觉。两种风景,一种令他心静神清,另一种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与之相反,那时人们尚未发现自己的正确比例及理应占据的位置:“人们经常会忘记自己是何等的渺小和微不足道。一个见过一百多层高的建筑物的人经常变得自恋,而治疗这种让人难以忍受的自恋癖的最好方法,就是通过想象把这种摩天大楼搬到一个不起眼的小丘上,才能知道其大的真正意义。”⑲环保题材的想象永远会碰到对比例的关心,它游移于永远以硕大比例出现的英雄幻想与其反面之间。
林语堂的作品涵盖漫长的历史,但是当他提到简朴生活的必要性时,也涉猎到日常一些琐细的看法,以至于他的想象会受到影响:“我有时会想,没有身体,看着一条清溪却没有脚深入其中以感觉那种清凉的美妙感觉,看着北京烤鸭或长岛冰茶却没有舌头品尝它,看着炸糕却没有牙齿咀嚼它,看着我们亲人的面孔却不拥有他们给予我们的任何感动,这是对一个幽灵或天使的残酷惩罚。”⑳一场古老的中国梦,有灵魂没嗓子,明明一个大活人但就是不消化,不从有限的土地上吮吸众多躯体必需的食物,而儒家宣称他是为没有社会保障、情形严重的年迈父母养老送终的保证。林语堂的梦奇怪地与许多人的物质相对贫困混淆在一起,好像是受美国环保文学众多例子的启示或这些例子消逝的受害者。一切好像一些人的再现性贫困与另一些人必然贫困的再现相呼应。我们这里其实谈到了林语堂的两种思考,一种是对人的正确位置的思考,另一种是对物质贫困和居安思危的思考。中国人一定要改变贫困面貌,改变贫困面貌之后,不忘居安思危。我们可以告慰林语堂前辈的是,我们已经实现了小康社会的梦想,仍在阔步前进。
五、局部污染的全局后果与全局性的环保观
对蕾切尔·卡逊提到的环境破坏,环保文本应该展示生态斗争的典范而做出回应。在这方面,美国作家达芙·威尔逊(Duff Wilson)的作品《宿命的收成》(Récoltes fatales)用文字证明进行中的斗争,他的愿望具有代表性㉑。作品2001年出版时,美国的普利策奖评委会指出,它的背景是农村。书中叙述的大部分事件发生在位于华盛顿州中部一个名叫昆西的农业小镇,人们逐渐发现镇上一家肥料生产企业使用的土壤增肥产品中包含着逐渐扼杀土壤的危险的化学残留物,企业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必须使用昂贵的合法手段处理这些工业产品。这种发生在局部的污染事件其实也是全局性的。因为哥伦比亚河就从昆西镇附近流过,那是整个美国领土最重要的淡水资源之一;那里种植的土豆供应麦当劳餐饮连锁店。环保文学中践行的想象出于一种综合思考,环保性想象融全局和局部于一身,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环保文本的囊括能力是无限的吗?它的计划难道没有限制吗?美国以“别在我家后花园里”(Nimby,“not in my back-yard”)而闻名的任何生态斗争就主张局部地解决环保问题,而非普遍性地解决。这个出现在新闻报纸上的美国术语描述任何生态责任的区域行动的局限性。所有的行为人,不管辩论或斗争的目的是什么,都力图反对这类标签,而达芙·威尔逊作品的行为者也避免不了公共行为正确途径的这种规则。
作为作家,达芙·威尔逊置身于美国文学的悠久传统中,即作家兼记者的传统,从一个具体事件出发建构文本以期检视普遍形势的路子:关注事实的愿望把作家带向一种想象方式,描述的圈子越来越广泛,甚至无止境,这是艾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指示给任何作品的雄心勃勃的任务,也是达芙·威尔逊的雄心。这部叙事的两个人物怀疑他们直接面对的环境的破坏拥有一种非常普遍的意义,并反馈到无限广泛的问题,例如联邦国家监控权力的衔接问题,美国企业的共性无动于衷和腐败、关心利润远胜过环保伦理或伦理学问题。生态斗争的行动者们于是获知,夜间行驶的火车运输的可能是危险的化学产品,随后要掺入正在制造的肥料中,从而逃避废料处理的严格规范。他们试图进行斗争。文本尝试理解斗争的理由、意向和局限性的机遇,那是文学方式而非简单报道的标志。因而环保类叙事及其作者向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想象的方式。威尔逊的这部环保叙事承认他做了选择,尽管以调查为基础。当作家们不能支持过于私人化、极少普遍性、过多装载圈定利益的“别看我的后花园”类方略时,甘冒取消人物特点、剥夺读者了解人物特征广度的权利。私密性某种程度上被否定了,作品的力量删削了人物的个性,而强化了无人称范围。这样构成的文学收窄了自己的对象——生态体系的现状,只想触及一种普遍性的形式,这样就把人物改造成毫无表达力的反应性主体。这里和那里出现的环保文学的一个持久特征,就是人物缺乏厚度,缺乏他们自身特有的模态,我们已经在法布尔的作品里看到了,这是专门的环保文本的一个倾向。它们并不因此而缺乏力量,但是这种力量得益于人们对客体新颖性的陶醉,后者排他性地成就了叙事,直至压缩了这样建构起来的见证人物的厚度。
威尔逊对其实践的局限性不可能没有意识。作品的场景之一叙述一种调解的尝试,调解的对象之一是抱怨者,他的土地染上了毒性,另一方是肥料工厂的厂长,调解人是当地新教的匿名神甫。他们之间的话语随风飘来,威尔逊对听来的话进行调整,以获得控制想象的结果。简单语词表述的弱势混淆了环境灾难的受害者,使读者无法全面看到生态灾难事件中永远凝结在一起的社会关系的全部特点。这难道不是专意于生态问题的文学的一种特点吗?
六、社会关系是法国环境悲剧的基本内容
与这些选择背道而驰,我们从法国文化中找到了与这种想象模态完全相反的东西。西克苏(Hélène Cixous)为木偶剧写的剧作《堤坝上的鼓声》(Tambours sur la digue),还有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与美国的许多环保作品相反,它们恰恰不是上述文学创作的典范:社会关系是西克苏和杜拉斯这两部作品中环境悲剧的基本的物质内容。这是否意味着专业化使作家介入了其他文学选择,例如喻示性和隐性范围的选择,抗衡透彻性和文学工作的注意力,以期让精心建构的人物的私密性所回收的社会张力的幅度从提到的形势中涌现出来呢?
环保素材促使作家谨慎处理社会关系,避免使社会风貌沉重,这并非惊人之举:事实上,任何环保文本迟早都会碰到社会问题,且经常碰到捍卫社会问题的队伍:专门化的作家们对自己说,别干扰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理论上很关注他者的利益,但事实上更关注他们自己的财富。这些在美国写成的环保作品是为“有教养的”中产阶级写的,但是面对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中产阶级从多方面持怀疑态度,因为被繁重的地方税务(而非联邦税)和与居住相关的税务压迫。从这个视角看,朱利安·格拉克(Julien Gracq)的文学创作不乏中肯性。格拉克是地理学家,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大学,他对自己专业的任何支持者和成果都不陌生,该专业造就了他的作家的想象模式,尤其是《大路笔记》(Carnets du grand chemin)的想象模式㉒。在地理这门专业里,环保题材找到了再好不过的语境,因为它的目标就是土地的逻辑性和风景的构成。而格拉克通过他的专业旅程和个人历史,对这一切都很敏感。这是一位很节俭的作家,这使他在自己的写作中严格控制所有属于文学华丽效果的东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德国被俘,在那里写作,他指出:“动笔之前,我用随身带的20分米的尺子,把早晨的黑面包分成五份,这是我们小组交给我的关键活动……”㉓把写作与少吃结合起来颇有意义:节俭和朴素的文学风格也构成一种环保观念。在这些条件下,拥有这样的经验积累,格拉克可以归类到那些认为自然的使用应该得到掌控、属于注重节俭可支配资源的人士中。萦绕格拉克的念头是:风景要空;任何土地上的人口要少。从这个视角看,法国农村是一个巨大的慵懒安静的世界,远离它的大都会,没有任何世界比人迹罕至、处于睡眠状态的世界更使格拉克感兴趣了。同样,在克洛德·卢瓦(Claude Roy)的某首诗里,河流在睡眠,当美国的保罗·斯特兰德(Paul Strand)的摄影作品表述衰弱、沉入正义的平静与和平时,法国农村启示的诗作的上半阕标示的是睡眠的河流㉔。从一把草椅上发出低声的这个法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幸福还是痛苦,稍有一点就满足,这种法国是格拉克、卢瓦和斯特兰德的一种规范,而凡尔赛宫以其奢华赋予国家一个漂亮的门面,其耗资巨大的审美观似有毁坏了农村之嫌,难以征服人心,朱利安·格拉克写道:“自从辉煌世纪远远地姗姗而来时,在我看来,生活环境的美就销声匿迹了,那时在任何事情上,都是抄袭和假冒的趣味占上风,从假古董到‘小天鹅’㉕,从仿希腊的廊柱到假发,不一而足”㉖。假货艺术伴随着消费,炒作代替了非物质价值。任何环保方面的文本都被一种本根主义的批评观所引导,抨击昂贵奢靡之风。
格拉克的风景其实也是道德风景。他踏遍法国的山山水水,在从利摩日去普瓦蒂埃的路上找到了可揭示的题材,那里是经济活力受到遏制的地方,法国在那里“已经看到其农村的坚实基础从深层破裂了”㉗。离开普瓦蒂埃后,问题是要从哪里“开始启蒙之旅”呢㉘?在这样一个问题里,格拉克保持了他的怀疑。从前,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暴力强加给风景。没有湖泊消失,没有河流干涸,没有世界被破坏。然而,应该怀旧式地躲进一种平衡的社会形态,像克洛德·卢瓦的诗句那样平衡、有节奏、音步非常准确的形态吗?发展的热情之前,古老法国的心灵里,有人们没有发现的恐惧感,它们把社会意见不一致和民族分裂的重负沉甸甸地压在人们头上。人们的怀疑情绪冒出来了:如果说屈从于旧体制时期古老的社会分裂现象是法国在敦刻尔克失败的原因,无论如何,克洛德·西蒙(Claude Simon)和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严厉诊断让人们听出了这种战斗色彩不浓的内在原因吗㉙?
七、土地的性质与政治生态的毁灭
格拉克认为,拥有土地性质的民众,土地的地理命运很重要。这种思想从何而来呢?格拉克有可能与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一起说,“唯一真正的地理问题,是使用种种可能性的问题”㉚。格拉克在旺岱的小树林是一块幸运之地,它的脉气并不因此而有所下降(正像总体上的花园之国法国一样),因为它很肥沃,这里或那里关于他父亲幸福生活的篇章证实了这一点,老格拉克骑着马在农场和农民们中间转悠。朱利安·格拉克的地理决定论是一种服从论而非一种必然论,意思是说,一块肥沃的土地以更具体和更权威的方式导向懒惰,无法使人们理解一段政治历史——纳粹主义的危害,而纳粹主义被一种强大的专制性质的虚无欲望所鼓动,准备好在坦克驶过的路上毁灭一切。小树林深处渗透着烦闷的宁静,是一种指示,但从来都不是建构未来的标准。从这个视角看,格拉克是一个服从于环境的作家。法国军队在敦刻尔克的口袋阵中被德军俘获一事使他写出了几页强硬的文字,前面指出这场战役深受“一个醉酒之夜”的影响㉛。面对历史事件,与面对领土一样,无动于衷的态度占了上风,没有任何主动维度。那是因为在民族的秉性里,记忆依然存在。格拉克写出了他的《森林的阳台》(UnBalcon en forêt)。这部作品几乎未能掩饰它的自传性质,格拉克在里边叙述他的战争,“古老的墨洛温王朝的龌龊住所”㉜在战役期间,“依然在空气中飘散着使它起死回生的久违的香味”。说格拉克的环境论是一种臣服的环境论还不够:因为如果文学想象的模式应该存在于虚空中,那么把它置于何处,如何来界定它,才能什么用处也没有呢?龌龊住所生活着人们将要食用的肥猪,或者被蹂躏土地上的农民,还生活着人们将围猎并享受其美味的野猪。格拉克对营养的见解标志着他对环境题材的敏感性,因为法国人忘记了大灾荒,尽管他们曾经逃避灾荒,现在仍心有余悸。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法国被占领时期真的唤醒了这些恐惧。
在格拉克那里,人与土地的关系是纯粹的反应关系,甚至反作用关系,人们反思,在土地与民众的这种关系中,还有什么可以建构起来,或者以某种方式得到解决。艾默生与格拉克一样,在这方面受欧洲腹地战争进程的鼓舞,痛恨被指责把法国逐出欧洲民族长达百年的拿破仑·波拿巴。艾默生无法利用历史的距离感,但是在他献给法兰西民族形象的著名论文中,他把拿破仑·波拿巴展示为一种时势的创造物,迷失在他似乎掌控的历史事件的表面,而他实际上不是主人,由于一种决定论的传播,人们不太清楚历史与拿破仑·波拿巴之间是一种被强制的必然关系抑或反作用的关系:“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人,而这样一个人就诞生了。”㉝格拉克也可能会写出下面的句子:“我们需要一个驻足于风景中的人,而这样一个人就应运而生。”这种先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没有任何失望情绪,促使格拉克走上反对无远见的建构主义,未给清教徒式的可能重建与土地关系的美国思想太大的希望。当人类互相厮杀,竟至在欧洲战争中把农民当成趾高气扬的精英们的炮灰时,人们还能希望以其他方式居住在世界上吗?这是格拉克提出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其著述的进展,格拉克的观点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小说里那些移动的人物形象逐渐变得透明,但仍然没有达到承担一份责任、足以建构一种政治生态的程度,远未达到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酷爱与自然签署合同的程度。在格拉克那里,没有粗暴结局的危险,世界末日之类的危险事件是政治性质的。但是,作家因其透明素材,与专门的生态书写相衔接。这些专门的文本,由于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领土和生态体系,看到的是一个没有物质实体的、被取消的人,其厚度的机遇属于用行动抵制领域。
八、其他可能的题材
道路特别是高速公路或高铁也成为生态批评的题材。有人批评高速公路的严重尾气导致大片森林死亡。近年来也有人批评高铁的振动导致地质灾害。但是,尾气可以通过提高汽车的质量而降低,所谓高铁的振动导致地质灾害的说法尚未获得科学的证据。另外,由于它们大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仍然是世界各国大力发展的国策。
鲁迅先生的《野草》礼赞了野草的生命力。野草本身面对艰难的生存环境,它喻示人类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因而也被视为生态批评范畴的佳作。
大量的知青文学作品也属于生态批评的范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发生在“文革”这种政治生态环境中。不少知青作品都有很透明的特点,当今的回忆性作品比当年的作品更甚。韩少功的知青创作便是一例。他描述了知青物质上的匮乏和精神上的幼稚,描述了当地农村因机械地学习大寨经验,过度使用土地而导致生产力低下的实际情况,描述了农民之间、知识青年之间、知青与农民之间的融洽关系的建立,描述了人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这些都与环境和生态有密切的关系。当然,知青作品也抒写了他们渴望回城,获得深造机会或稳定工作的事实,这些都是很真实的,没有半点作假的文风。这些都说明,从比较生态批评的视野看,生态批评的范围是十分广阔的,某些看似与生态没有关系的东西,其实也属于生态批评的范畴,如政治生态、健康生态、婚恋生态、民俗生态,等等。早期明确的生态批评观念和实践从19世纪下半叶就开始了,今后仍然有着广阔的前途。
“而作为哲学组成部分的(生态)美学则是时代艺术精神的集中反映。时代的变迁必然导致艺术精神的变迁,从而导致美学精神的变迁。人类已经进入生态文明的新时代,无论从理论、社会发展模式、经济建设模式、生活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艺术精神都必然逐步发生巨大变化,由此导致以‘主体性’‘人化自然’为基本内涵的当代美学发生巨大变化。这就是生态美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与经济社会根源。中国生态美学在1992年前后提出,以介绍西方环境美学为主要任务。而真正开始研究生态美学则是生态问题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社会问题的21世纪初期,迄今也就是十多年时间。”㉞生态美学的特点是集中、深刻和新,生态批评的特点是无所不包、针对性强、灵活、重视实效性,批评的内容和语言也很深刻。
注释
① 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她的作品《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引发了美国以至于全世界的环境保护事业。世界卫生组织受其影响,于2002年宣布重新启用DDT对抗流行病。
② 艾伯特·戈尔(Albert Arnold Gore Jr.,一般称为阿尔·戈尔),1948年3月31日出生于华盛顿。美国政治家,曾于1993—2001年担任副总统,后成为一名国际上著名的环境学家,由于在全球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上的贡献受到国际的肯定,因而获得了2007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他曾经提出著名的“信息高速公路”和“数字地球”概念,引发了一场技术革命。
③ Al Gore,«Introduction» in Rachel Carson,Silent Spring,version américaine,1994,p.15.
④ Rachel Carson,op.cit.,édition américaine,p.171.
⑤ 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美国作家、哲学家,超验主义代表人物,也是一位废奴主义及自然主义者,有无政府主义倾向,曾任职土地勘测员。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协助爱默生编辑评论季刊《日晷》。写有许多政论,反对美国与墨西哥的战争,一生支持废奴运动,并抨击逃亡奴隶法。其思想深受爱默生的影响,提倡回归本心,亲近自然。1845年,在距离康科德两英里的瓦尔登湖畔隐居两年,自耕自食,体验简朴和接近自然的生活,以此为题材写成的长篇散文《瓦尔登湖》(又译为《湖滨散记》),成为超验主义的经典作品。梭罗才华横溢,一生共创作了二十多部一流的散文集,被称为自然随笔的创始者,其文简练有力,朴实自然,富有思想性,在美国19世纪散文中独树一帜。《瓦尔登湖》在美国文学中被公认为最受读者欢迎的非虚构作品。
⑥ Augustin Berque,Écoumène :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s milieux naturels,Paris,Belin,p.20 et suivantes.
⑦ Alain Suberchicot,Littérature et environnement,pour une écocritique comparée,Paris,Honoré Champion,2012.本文在写作中参考了该书的某些章节。
⑧ H.D.Thoreau,The Journal of Henry David Thoreau,in fourteen volumes bound as two,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1962,vol.1,p.109.
⑨ 让-亨利·法布尔(Jean Henri Fabre),法国博物学家、动物行为家、昆虫学家、科普作家、文学家,以《昆虫记》(Récits sur les insectes,les animaux,et les choses de l’agriculture)一书留名后世。身为现代昆虫学的先驱,法布尔以膜翅目、鞘翅目、直翅目而闻名,雨果称他为“昆虫世界的荷马”,被世人誉为“科学界的诗人”“昆虫界的维吉尔”,因贫病交加于92岁逝世。
⑩ Jean Henri Fabre,Récits sur les insectes,les animaux,et les choses de l’agriculture,avant-propos de Pierre Rabhi,préf.Pierre Delange,Arles,Actes Sud,2002.
⑪ 同上,第96页。
⑫ Julien Gracq,En lisant en écrivant,in Œuvres complètes,Bernhid Boie &Claude Dourguin(éds.),Paris,Gallimard/coll.La Pléiade,1995,vol.2,p.736.
⑬ 关于这个话题,参阅Alain Suberchicot,Littérature américaine et écologie,Paris,L’Harmattan,2002,尤其是第一节,该节涉猎荒野自然引发的恐惧问题,人们感觉受到大自然的威胁,因为它是陌生的。
⑭ 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年5月20日-1873年5月8日),或译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也译作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英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19世纪影响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支持边沁的功利主义。约翰·穆勒是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的后继者。他把实证主义思想最早从欧洲大陆传播到英国,并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相结合。在哲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论自由》(1859)。
⑮ 同上,第507页。
⑯ 中国历史上不乏灾荒,最近的一次灾荒是发生在1959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
⑰ 林语堂:《自然的乐趣》,见The Importance of Living,cha.10,New York,Reynal &Hitchcock,1937,p.281.
⑱ 林语堂,见前引著作,第282页。
⑲ 林语堂,同上。
⑳ 同上,第26页。
㉑ Duff Wilson,Fateful Harvest,The True Story of a Small Town,a Global Industry,and a Toxic Secret,New York,Harper Collins/ Perennial,2001.威尔逊的著作和文章多次获奖,包括哈佛大学授予的戈尔德史密斯奖(Goldsmith)。
㉒ Julien Gracq,Œuvres complètes,vol.2,Bernhild Boie,éd.,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Claude Dourguin,Paris,Gallimard/La Pléiade,1995,pp.937-1112.
㉓ Julien Gracq,op.cit.,p.1037.
㉔ 原诗译成中文如下:在睡眠中滑过的水流激发了一场梦境/慢悠悠的草丛中芦苇杆窃窃私语/在其朦胧的睡眠状态中永远不知道/水的支配在哪里让位于植物的宁静……参考Claude Roy,La rivière endormie in Claude Roy &Paul Strand,La France de Profil,New York,Aperture,2001,p.69.
㉕ 在旧体制时期,这个术语指称化装的附属品,例如长筒袜、帽子、带子和手套等,参阅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4ème édition,1762,ARTEL Project,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㉖ 朱利安·格拉克:同前引著作,第1042页。
㉗ 同上,第997页。
㉘ 同上,第975页。
㉙ 关于这个话题,请阅读Claude Simon,La Route des Flandres,in Œuvres,Alastair R.Duncan,éd.,collaboration Jean H.Duffy,Paris,Gallimard/La Pléiade,2006,pp.193-367,et Marc Bloch,L’Étrange défaite,in L’Histoire,la guerre,la résignation,Paris,Gallimard/Quarto,2006,pp.519-653.
㉚ Lucien Febvre,La Terre et l’évolution humaine,Paris,La Renaissance du livre,1922,p.425.
㉛ Julien Gracq,op.cit.,p.196.
㉜ Julien Gracq,op.cit.,p.37.
㉝ Ralph Waldo Emerson,Essais and Lectures,Joel Porte,ed.,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3,p.731.
㉞ 曾繁仁:《中西对话中的生态美学》,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