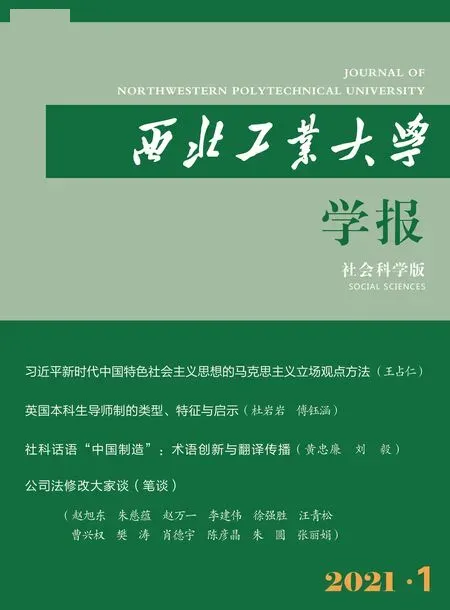彭斯诗歌的中译与苏格兰性
何 宁 栾天宇
作为苏格兰文学的代表和苏格兰民族精神的象征,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对于世界文学具有广泛的影响。彭斯出生于18世纪贫苦的苏格兰乡村,在诗歌作品中歌咏自由和平等,为当时的劳动人民发声。他对苏格兰民歌的收集和整理,不仅让他个人的诗歌创作受益,更为苏格兰民歌的传承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彭斯的诗作质朴却情感丰沛,歌颂家乡苏格兰的秀美风景,充满着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热情,让他成为“苏格兰最具国际知名度的诗人”[1]。自1908年彭斯的第一首诗歌传入中国,彭斯诗作中蕴含的苏格兰性与中国百年来的社会发展相互交织,让彭斯的译介和研究在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不断受到关注,对中国的文学创作和研究影响绵延深远。
一、彭斯诗歌中译与苏格兰风景书写
在20世纪初年,随着西学东渐,不少外国诗人的诗歌作品经由翻译进入中国文坛,成为当时文学发展的一部分。1908年,苏曼殊以一首《熲熲赤蔷靡》将诗人彭斯引入了中国读者的视野。这首发表于1796年的A Red,Red Rose是彭斯的代表作,借红玫瑰的意象抒发了诗人对美好爱情的渴望和歌颂,充分展现了浪漫主义诗歌的特点,情感热烈真挚,用词简单质朴,整体音韵流畅。彭斯正是以这首苏格兰民谣风格的代表作,成为当时中国学人认可的浪漫主义诗人代表。苏曼殊的译诗采用五言古诗体,形式严正,用词古雅,意象突出,从中可以看出《上邪》和《长恨歌》的影子。
熲熲赤蔷靡,首夏初发苞,恻恻情商曲,眇音何远姚。
予美谅夭绍,幽情申自持。沧海会流枯,相爱无绝期。
沧海会流枯,顽石烂炎熹。微命属如缕,相爱无绝期。
掺祛别予美,离隔在须臾。阿阳早日归,万里莫蹰踟![2]
虽然诗歌所蕴含的炽烈之情和浪漫之感并未淡化,但译文的形式与彭斯原作颇为不同,随之隐去的还有原诗的自然与质朴。这一点是当时翻译家不约而同的选择,在同时期的其他诗歌作品翻译中也有明显的体现。这一时期,译者往往会放大诗人某一情感特征,又将自己想要表达和传递的态度包蕴于译作之中。西学东渐时期的翻译文学目的往往并非要忠实地传达原意,而是以西方的文学作品为引,抒发译者自己的情感和文学抱负,“根据本土的文学习惯来重新书写外源文本,借此来表达自我文化形态中的美”[3]。这首《熲熲赤蔷靡》便彰显着汉家外衣下的“浪漫”。
浪漫的炽热之情正是中国文坛对彭斯这位来自苏格兰的诗人最初的形象。周瘦鹃介绍彭斯“为英国大诗人,与拜伦齐名。善情诗,能掬男女之心内之行墨间。似怨慕,似泣诉,无不婉妙”[4],在杂志同期刊载了彭斯的诗歌作品A Red,Red Rose以及这首诗的旧体诗(苏曼殊译)和新体诗“一朵红玫瑰”(张枕绿、秋镜合译)两个译本。新体诗译本在风格和遣词上都与苏曼殊所译《熲熲赤蔷靡》有着明显的不同。虽然也有少数偏繁文言的表达,但译诗整体采用白话文,较为清新自然,在风格上与原诗有所贴近。
我爱像那鲜红的玫瑰,
六月里花纔娇滴滴的放;
我爱像那温和的音乐,
弹出来甜蜜蜜的声音。
我那轻盈的妙人儿啊!
像你这样的美丽,
竟累我溺入深深的爱河;
可是我依旧爱你,我爱,
纵使有一天海枯。
等到那一天海枯,我爱,
连那石头都给太阳晒融了;
我依旧爱你,我爱,
那时生命像飞沙般的乱跑。
同你分别,我唯一的爱,
同你分别一会儿。
我定要再到此地来,我爱,
即使有一万里的路程儿。
(《一朵红玫瑰》,张枕绿、秋镜译本)[5]
作为新诗的奠基者之一,郭沫若也被彭斯这首韵律优美、富有特色的作品所吸引,将它予以翻译。
吾爱吾爱玫瑰红,六月初开韵晓风;吾爱吾爱如管弦,其声悠扬而玲珑。
吾爱吾爱美而殊,我心爱你永不渝,我心爱你永不渝,直到四海海水枯。
直到四海海水枯,岩石融化变成泥,只要我还有口气,我心爱你永不渝。
暂时告别我心肝,请你不要把心担!纵使相隔十万里,踏穿地皮也要还。[6]
郭沫若的译文在诗歌翻译上具有一定的创新,谙熟古文的他采用七言文言旧诗的形式,糅合进白话文的语言,整合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和外国诗歌的特色,与彭斯诗歌原文也较为贴合。但是,郭沫若在诗歌译文中选用的白话文词汇过于直白和口语化,因此译诗整体失之文采和神韵,既没有苏曼殊的古韵之风,也不如张枕绿、秋镜的版本自然本真。
随着彭斯这首名作的重译,彭斯诗歌的中译开始逐渐丰富起来。彭斯作为来自苏格兰的浪漫主义诗人受到中国学界的广泛欢迎。新月派与英国浪漫主义运动有着相似的审美趣味,在新诗创作的过程中,新月派诗人也翻译了诸多英国浪漫主义诗作,其中就包含许多彭斯的诗作,例如朱湘1936年《番石榴集》中的《美人》、梁实秋1920年末刊登在《新月》上的《苏格兰民间诗人彭斯诗歌》等。1929年《新月》第2卷第6、7、8号(1929年9月10日—10月10日)连续刊登了梁实秋翻译的5首彭斯诗歌。[7]
值得注意的是,从内容和主题上看,在此时彭斯的中译诗歌作品中,歌颂苏格兰故国家园秀美自然的诗作得到了特别的关注。对彭斯苏格兰风景诗歌的关注,不仅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出当时学人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同时还影响着当时中国诗人和译者的创作风格。1932年《新世界》第10-11期刊载了三首河流的歌咏诗,其中两首出自彭斯;1934年《新垒》第3卷第2—3期刊载了彭斯译诗《我底心在那高地》;1942年《诗》第1期刊出文新译诗《阿富顿河》,译者在这首诗后附言道,“这首诗的内容虽然和我们现时的生活相去得很远,但是它的清新的风格和写景的自然,确是值得我们这萌芽期中的诗词工作者一读的”[8]。
彭斯咏阿夫东
(苏格兰的小河)的诗
悠悠阿夫东,来自苍翠之山坡。
我为君歌,君莫扬波。
赖君絮语,玛丽睡浓;
君莫扬波,绕其清梦。
彭斯咏杜河
(在南苏格兰的爱尔夏)的诗
清幽杜河的两岸与群山,
为什么充满这样美丽清新?
嘤鸣的小鸟,又为什么这样千啭而不穷尽?
而我呀,又为什么这样颓唐与心身不宁?[9]
与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田园牧歌式的书写不同,也与拜伦笔下澎湃汹涌的大海有异,彭斯诗歌中的自然书写带着对苏格兰家乡的歌颂和赞美,充满了对回归淳朴的向往和浓烈的苏格兰民族自豪感。彭斯对流经家乡埃尔郡的阿富顿河和杜河的深情书写充满了苏格兰风情和他对故乡风土的牵挂和怀念。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民生凋敝、战乱不止,经历着种种社会问题,这让不少诗人将对民族未来发展的希望寄托于自然的治愈力量。徐志摩笔下的《雪花的快乐》(1924)、《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个方向吹》(1928)、《再别康桥》(1928)等诗作的意象和音律都充满了自然的美与智慧,形成了与彭斯诗作的对话。由于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差异,彭斯中译诗歌作品的情感与新月派诗人诗作所表达的情感颇为不同,但两者的诗歌创作同样都将自然作为自由、美、爱情的化身。彭斯诗歌中对苏格兰风景的浪漫主义描写影响了这一时期翻译家对英美诗歌中译的选择,也影响了徐志摩等新月派诗人的创作风格和美学特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借鉴。
在早期彭斯诗歌的中译里,自然与风景的书写蕴含着历史与家园情怀,让彭斯这位“苏格兰诗人”显示出与其他“浪漫主义诗人”的不同。追溯到“苏格兰”最早进入中国视野的时候,它便已经作为独立的地域和民族存在了。魏源在《海国图志》介绍英国的时候清楚标示了苏格兰地图并做了附记。“斯葛兰地,三岛相接,一河中流。东南平旷,西北多山”,而后简述了苏格兰的历史变革,直到“英吉利遂乘间灭之,以伊邻麻社(Edingburthshire)为首部落,设官通商。然其众心至今向士都轧而不向英国也”[10]。对于同一地理疆界的忠诚所生发出的共同体意识正是历史所铸造的苏格兰性,而彭斯及其作品在自然书写中蕴含的苏格兰性也随着他的诗歌为中国学界所认知。
二、彭斯诗歌中译与苏格兰民族精神的呈现
在彭斯的诗歌译介中,吸引中国学界的除了他对苏格兰风景的书写,还有他的诗作中所蕴含的独立坚定的苏格兰民族精神。在早期对彭斯的诗歌翻译中,《苏格兰人》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诗歌所表达的对抵抗英格兰的苏格兰英雄烈士的念念不忘和“不愿死亡,就得战斗”的革命精神,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学者文人的共鸣。1939年《大风》第78期刊登了孙用所译的《苏格兰人》。孙用在译诗后介绍彭斯为“苏格兰的诗人,他的父亲是一个贫农,他自己也是农民……是国家的抒情诗人”[11]。《大风》杂志的发刊词《大风起兮》中写道:“在此全面抗战期间,社会人士尤其是智识阶级,对于精神上智识上之滋养料常感饥荒,而亟欲找得高尚的健全的培养补品。”[12]在民族存亡之际,为《大风》投稿的诗人以笔为刃,投身抗战,保家卫国,爱国主义精神激扬澎湃。彭斯的阶级身份和民族意识让他追求自由的呐喊十分贴近当时的社会现实,也更能引起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共鸣,在让中国学界认识到彭斯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激情之外,更为其诗歌中强烈的民族精神所感染和激励。
在学界对彭斯的研究中,梁实秋认为彭斯是“性情中人,其人其诗不失本色”[13]。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引拜伦对彭斯的评价[14],“斯人也,心情反张,柔而刚,疏而密,精神而质,高尚而卑,有神圣者焉,有不净者焉,互和合也”①。鲁迅认为这既是彭斯也是拜伦自己“恶魔的性格”的体现,他们所反抗和破坏的就是假面具的虚伪,追求和直面的是作为真正的人的坦率和真诚,也正是梁实秋所说的“本色”,是彭斯作为苏格兰人的民族本色。彭斯所生活的时代是苏格兰人民的民族意识觉醒的时代,而浪漫主义思潮的一个核心内容是“欧洲各国文化精英表达自己民族存在的合法性、正统性”[15]。作为追求民族精神的苏格兰诗人,彭斯对待法国大革命的态度和忠于革命的理想“与统治阶级出身的‘湖畔派’诗人形成了极有教育意义的对照”[16],彭斯对统治阶级的批判和对未来世界的信心,以及诗歌作品中的民族主义情结正是他的诗歌被当时的中国学者所译介的一大原因。同时,对于20世纪初期的中国学界而言,翻译彭斯的诗歌可以更多地将外来文化的部分内容纳入到中国本土文学的语境之中,让中国学者文人通过翻译来接触和吸收外来观念和思想,并为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奠定坚实的本土根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彭斯的译介和研究进入了新时代。1959年彭斯诞辰二百周年之际,彭斯的诗歌作品更深入地与中国翻译家和研究者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交流。正如王佐良所指出的,彭斯“不同于一般英国文学史上出现的文人,他是一个劳动人民自己的诗人”[17]。这也是彭斯诗作与其他诗人的作品相比最特别的一点:彭斯始终是从苏格兰劳动人民的角度来看世界、写世界的。他是体验者,而非观察者。从内容和形式上,彭斯始终是在用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方式,站在劳动人民群体中自内而外地抒发情感的,因此在浪漫主义色彩之外也充满着现实主义的力量,正是这种植根于土地的力量,才使得彭斯浪漫主义诗歌中的苏格兰民族精神富有现实性,鼓舞着广大的翻译家和学者投身祖国文化建设。为纪念彭斯诞辰二百周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袁可嘉翻译的《彭斯诗抄》,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版了王佐良的译作《彭斯诗选》。上海外文学会、作协上海分会纪念会发表纪念公告:
彭斯是农民出身的苏格兰诗人,具有浓厚的劳动人民的感情,善于运用强有力的人民语言。他的许多作品都充满了对贫苦农民和其他下层人民的不幸遭遇的同情,写出了他们的劳动、困苦以及纯朴的思想感情,表达了他们争取自由的理想和愿望。[18]
《世界文学》《文学研究》等刊载了范存忠、王佐良、袁可嘉等学者发表的纪念彭斯的文章。范存忠指出,彭斯“表达民族独立思想”的诗歌,都采用歌谣形式。歌谣形式经由彭斯的发展,“不仅是苏格兰农民和平民在劳动中诉说衷情的媒介,而也是被压迫、被掠夺的民族的战斗号角”[19]。袁可嘉将彭斯的作品分成了两类——讽刺诗和抒情诗,认为彭斯的讽刺诗将矛头指向统治阶级和教会,而抒情诗则大都描写人民的生活和爱情,目的在鼓舞人民。[20]他借18世纪苏格兰歌谣的复兴和活跃来说明苏格兰人民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充满了对统治阶级的憎恨和反抗,对于法国革命所象征的民主自由的热烈向往[21],《为那些远行的人干一杯》《苏格兰人》《不管这一切》等诗作都是鲜明的例证。通过对彭斯诗作与民歌关系的研究,袁可嘉力图为中国民歌的发展找寻一条出路,从抒情的主题和现实主义的描写手法两个方面,思考民歌如何在表现爱国精神的同时,不失音乐性和艺术性的美学本质。袁可嘉的研究对彭斯诗歌的苏格兰民歌特质和民族精神加以深入探讨,这也为当时中国文学的“新民歌运动”提供了参考。
彭斯进入中国以来一直受到中国学界的重视,在彭斯诞辰二百周年之际,由于其诗歌的民歌特质和对苏格兰民族精神的书写,让他的诗歌在中国的影响力超过当时其他英美诗人的作品。《西方语文》转载了英共名誉主席威廉·加拉赫(William Gallacher)②在英国《劳工月刊》(Labour Monthly)的纪念文章。文章站在贫苦苏格兰农民的角度,结合历史背景回顾了彭斯的生平,赞扬了彭斯对教会和统治阶级的反抗,称他为“不朽的战士、人民的伟大诗人、抒情歌手和他那个时代的革命者”[22]。彭斯以浪漫主义精神、现实主义手法来为苏格兰贫苦阶层发声,对苏格兰民族独立精神加以刻画,这些对20世纪中期的中国文学具有启示,让更多的中国读者和研究者认识到彭斯作品中独立坚强、宁折不屈的苏格兰民族精神,使得中国学界对彭斯诗歌与苏格兰性的认识更进一步。
三、彭斯诗歌中译与苏格兰文化的传播
从20世纪中期开始,彭斯诗歌作品的中译开始形成规模,其中所蕴含的苏格兰性逐渐得到彰显,而苏格兰文化也随着彭斯诗歌的中译为中国学界所熟悉。约翰·哈钦森认为“信奉文化民族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的道德改革者依靠民族的媒介来传播他们的观点,他们强调原始神话、传统和仪式、地理学、自然历史和民歌,来激起民族情感,然后将国家的不同文化部分融合在一起”[23]。不论是自然地理,还是传统民歌,都在彭斯的诗作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成功地将苏格兰民族的文化融合起来,成为苏格兰文化的代表,得到了当时中国学人的关注。袁水拍在《中原》1943年第一卷第3期上发表译作《彭斯诗十首》③,注中介绍“彭斯为苏格兰诗人,或者称之为‘歌人’更为切当”[24]。而后,袁水拍译诗集《我的心呀在高原》在1944年由美学出版社出版,是当时出版的第一部彭斯的中文诗集。在袁水拍译本的进一步推动下,彭斯在诗歌作品中所传达的对祖国故土的热爱之情,一定程度上成为20世纪中国学界对苏格兰文化认知的文化符号。
彭斯诗歌创作中苏格兰民族特色的方言则是中国学界对苏格兰文化认知的另一重要方面,同时对中国文学的创作也具有影响。彭斯的诗歌从民间语言中汲取艺术的力量,对苏格兰方言的运用与中国古已有之的方言文学相契合。新文化运动摒弃文言,回归白话、回归民众的呼吁为徐志摩运用方言创作诗歌提供了可能。作为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的整体诗歌风格是将真挚和热烈的情感寓于含蓄柔情的细腻之中,但使用方言来表达故乡的风土人情,则赋予他的这些诗歌作品一种自然无雕琢的纯朴风格。《一条金色的光痕》(1924)这首关于乡下老妇人的诗歌就是用徐志摩家乡地道的硖石土白写就。《东山小曲》《盖上几张油纸》《一小幅的穷乐图》等诗中都有硖石方言的运用,《残诗》则是用地道的京白写成。④虽然这些诗歌不是徐志摩的代表作,但这些方言诗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徐志摩对故乡民众的关切之情。方言土白让这些诗歌的情感表达更为亲切自然,抒发的情思更为直接,正如华兹华斯所定义的那样,自然流露的情感是浪漫主义诗歌之所以“浪漫”的质素,而这正与当时知识分子的情感诉求不谋而合。同时,方言也让诗歌的音乐性体现出与众不同的魅力,与彭斯的诗歌风格颇为相似。
彭斯诗歌中的民谣传统是苏格兰文化的基因和记忆所在,也是苏格兰文化为学界所认可的重要载体。在18世纪以来民族思想发展的背景下,彭斯继承并丰富了苏格兰方言文学运动之父艾伦·兰姆绥(Allan Ramsay,1686—1785)等所代表的苏格兰民谣传统,汲取民间文艺的精华,“为英国的浪漫主义做出了贡献,因为民歌的复兴正是这个新的文学潮流的特点之一”[25]。彭斯的诗歌创作通过民谣风格强化了对苏格兰的认同意识和归属感。中国也有民歌创作的文学传统,《诗经》《乐府诗集》等都来源于生活,不仅贴近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而且也充满着时代性和思想性。中国文艺界一贯重视民歌的创作,因为民歌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民间基础,彭斯诗歌的民谣风格也由此得到认可。王佐良认为彭斯诗歌中的苏格兰民歌传统在中国得到了很多关注,也正因这一因素,彭斯和“我们现在的距离也就比英国文学史上任何别的著名诗人都要近些了”[26]。彭斯诗歌中的民谣传统连接了历史与现在、作者与歌者、方言与英语,将苏格兰的文化记忆深深印刻在诗歌当中,也将苏格兰的民族身份深深印刻在每位苏格兰人心中。同时,彭斯诗歌本身的音乐性脱胎于民谣的旋律,一定程度上是苏格兰文化记忆外化的产物,在传承文化记忆和民族记忆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随着文学思潮和文学翻译标准的变化,彭斯诗歌不断得到关注和重译。重译作品逐渐摆脱用西方作品说中国故事的影响,注重对作品文化背景的呈现,译本范围和数量也都更为丰富。以王佐良的译介为例,1959年出版的《彭斯诗选》收录了37首彭斯的诗歌作品,而1985年,王佐良重新出版的《彭斯诗选》增加到61首诗歌,对原有的翻译也进行了润色。为纪念彭斯去世220周年,2016年李正栓出版译著《彭斯诗歌精选》,收录彭斯诗歌108首。至此,彭斯和苏格兰文化进入中国已过百年。
进入21世纪之后,对彭斯诗歌和苏格兰性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研究视角不仅仅从语言层面或翻译本身出发,对诗歌作品艺术性、诗人主体性和民族身份的研究开始成为翻译家和学者关注的重点。《一朵红红的玫瑰》《我的心在高原》等几首脍炙人口的诗作仍然是重译和研究的重点,而对彭斯其他诗歌的翻译和研究较少。彭斯诗歌的苏格兰性开始得到中国学界的进一步关注。宋达探究彭斯的民族主体性,提出“苏格兰文学何所在”,认为自英国文学进入中国以来,学界过多地受到英国文学史家影响,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苏格兰文学的主体性。[27]随着“苏格兰文学”这一概念逐渐得到学界的认可,彭斯作为苏格兰文化的代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赵丹晨在梳理21世纪以来苏格兰文学在中国的研究情况之后,将彭斯作为“苏格兰诗歌之魂”[28],指出了彭斯在苏格兰文学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彭斯的诗歌中译将苏格兰文化引入中国学界,并逐步促成了作为独立民族文学的苏格兰文学为研究者所接受。对彭斯诗歌中苏格兰性的研究,不仅可以让中国读者认识和了解苏格兰文化,同时也为研究世界各国的民族文学提供了借鉴。
四、结语
从清末民初到21世纪,彭斯诗歌进入中国已有百余年的历史,经历了从披着旧诗外衣到苏格兰内核的显露。中国学界对彭斯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从苏格兰风景中的浪漫主义诗人,到书写苏格兰文化的民族诗人,彭斯及其中译可以作为中国认识和了解苏格兰民族文化的起点。彭斯诗歌创作中对苏格兰方言予以创造性的运用,将诗歌创作融入了民族文化建构,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中国学界在翻译彭斯诗歌的历程中,不仅关注作品中的苏格兰性,同时也在译本中融入中国本土文化的元素,让彭斯诗歌的翻译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样本。
注释
① 出自《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第88页。拜伦对彭斯的评论见拜伦1813年12月13日的《札记》(Journals)。今译为:这个诗人,心灵很矛盾,柔弱而刚强,粗疏而细密,空灵而质朴,高尚而卑俗;有神圣的东西,也有污浊的东西。这些都是融合在一起的。
② 加拉赫(William Gallacher,1881—1965),苏格兰人。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英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生于苏格兰的一个工人家庭,卒于苏格兰。青年时代即投身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曾参加英国独立工党、英国社会民主联盟。
③ 包括《克洛顿的悲歌》《朵朵绯红,绯红的玫瑰》《台芒和雪薇娃》《你的友情》《玛契林的姑娘》《唱呀!可爱的鸟儿》《打后面楼梯路来》《我的心呀:在高原》《阿真》《自由树》。
④ 卞之琳先生认为徐志摩诗歌为白话新诗的成功做出了贡献,而方言对徐志摩诗歌的音韵具有重要的影响。参见《徐志摩选集》序和《徐志摩译诗集》序。载卞之琳著:《人与诗:忆旧说新》,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