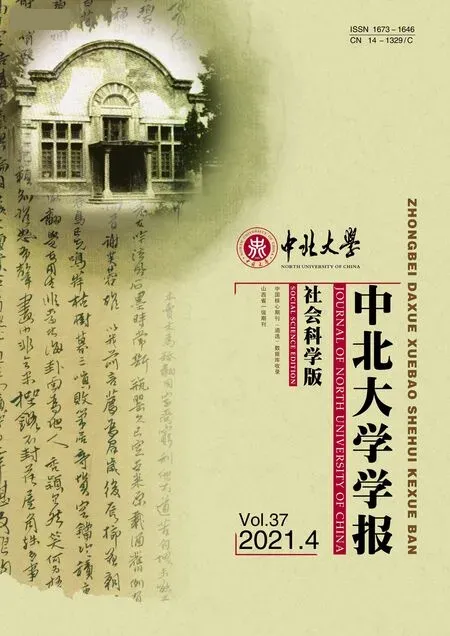佛教中国化视域下诗僧皎然的精神气质
丁建华
(浙江工商大学 东亚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18)
皎然,俗名谢昼,湖州长城人(今浙江省长兴县人),于灵隐寺受具足戒,以文学著称于世,据《宋高僧传》记载,皎然“文章俊丽,当时号为‘释门伟器’”,“凡所游历,京师则公相敦重,诸郡则邦伯所钦”,足见其以佛教僧人身份获得世俗社会极大的肯定。然而,诗文毕竟是语言,而语言恰恰是以“不立文字、 教外别传”为口号的禅宗决意要超越的,连大慧宗杲、 圆悟克勤之“文字禅”都受到禅宗内部异样的审视,更不用说本身就是世俗文化的诗文了,可见,诗与禅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张力。但是,诗文本身也是一种工具,禅宗所批判的只是执着于这种工具,并不批判通过这种工具实现佛教的终极目标,所以,《宋高僧传》特意在对皎然诗文获得社会极大认可之后加了一句“始以诗句牵,劝令入佛智,行化之意,本在乎兹”[1]892。所谓“劝令入佛智”,就是通过诗文来引导社会大众达到佛教所追求的智慧境界,这也就意味着,在佛教的立场上,像皎然这样擅长诗文的僧人,如果不以宗教目标为导向,则背离了僧人的身份。
在皎然的诗文中,存在着一种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既是他本身精神气质的自然流露,又代表他追求与向往的目标。在《戏作》一诗中,皎然将其自由豪放的精神气质展露无遗,“乞我百万金,封我异姓王。不如独悟时,大笑放清狂”[2]216。以一种出世间的超越性态度来面对金钱所代表着的世俗生活,不受其拘束。在这种“逍遥”的精神面貌中,既有佛教的禅味,又有道家的任其自然与狂放不羁。以皎然所代表的诗僧所拥有的、 游走在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精神气质,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思想现象。
1 弃文归禅
贞元初年(公元785年),皎然居住于东溪草堂,之所以选择远离城市的地方隐居,是为了停止继续在诗文上花功夫,因为沉溺于诗文恰恰是与佛教所追求的目标相违背的,“欲屏息诗道,非禅者之意”[1]892。诗文水平的提升并不能直接等同于禅宗的宗教追求,甚至会成为相反的障碍,皎然对此进行了一大段的自述。
诲之曰,借使有宣尼之博识、 胥臣之多闻,终朝目前,矜道侈义,适足以扰我真性,岂若孤松片云,禅座相对,无言而道合,至静而性同哉。吾将入杼峰,与松云为偶,所著《诗式》及诸文笔併寝而不纪,因顾笔砚曰,我疲尔役,尔困我愚,数十年间,了无所得,况汝是外物,何累于人哉?住既无心,去亦无我,将放汝各归本性,使物自物,不关于予,岂不乐乎?遂命弟子黜焉。[1]892
这段话引自皎然《诗式》中的序[3]1,是他本人的自述。皎然认为,不论如何的博识多闻,都与自我真性无关,应当追求不为外物所累的境界,他形容其为“孤松片云,禅座相对,无言而道合,至静而性同哉”,这种既有文人风范的形容,又充满了道家逍遥坐忘的气质,表达了对佛教“出世间”的追求,体认到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世间”羁绊都是一种障碍,所以他才反问“况汝是外物,何累于人哉”?
在“住既无心,去亦无我,将放汝各归本性,使物自物,不关于予,岂不乐乎”中,无心、 无我、 本性都是佛教理论中的关键范畴。不过,正因为是关键性范畴,佛教各个理论系统都会对这些范畴进行诠释,所以意义相对模糊。本性,指的是自我的本来之性,既是在探讨“人性”这一个群体性概念,又是回归到每个具体的个人,在追问个人“我是谁”的哲学问题。在这一问题域中,不论是名字、 关系、 地位等,都不能作为人的真正内涵,可见,本性其实就是佛教对人的本质的理论建构。在佛教理论中,关于人的本质,基本存在两种理解,一种是“空”,另一种是“有”,前者偏向于从条件性与暂时性来解构人,后者以真如、 如来藏等永恒实体[4]1来回应人的本质问题。相比较“本性”具有空、 有两种理解方式,无我和无心则相对偏向于“空”,无我就是通过缘起来解构“我”,无心就是通过缘起来解构“心”“念”。在《禅诗》中,皎然强调的“不动念”其实就是“无心”的意思,“万法出无门,纷纷使智昏。徒称谁氏子,独立天地元。实际且何有,物先安可存。须知不动念,照出万重源”[2]206。可见,在佛教理论的视域中,皎然使用的这三个范畴都在揭示“缘起”的思想。然而,皎然却接着说“使物自物,不关于予,岂不乐乎”? 笔者认为,这种表达在本质上其实违背了大乘佛教缘起性空的理论,接近于部派佛教“说一切有部”万法各具自性而存在的理解模式。当然,皎然的经历中并没有接触阿毗昙(印度佛教说一切有部流浪的经典)的经历,所以,这种理解的来源更有可能是郭象以“独化”诠释过的庄子的“逍遥”理念。正是对于逍遥的精神诉求,皎然放弃了成就自己的诗文,“耻以文章名世”[5]830“后中丞李洪刺湖州,枉驾杼山,请及诗文。昼曰,贫道役笔砚二十余年,一无所得,冥搜物累,徒起我人,今弃之久矣”[5]830。
2 钦慕支公
皎然在《支公诗》中讨论了“支道林”这一人物,“支公养马复养鹤,率性无机多脱略。天生支公与凡异,凡情不到支公地。得道由来天上仙,为僧却下人间寺,道家诸子论自然,此公唯许逍遥篇。山阴诗友喧四座,佳句纵横不废禅”[2]211。支道林是魏晋玄学时期著名的人物,与皎然一样,以文学著称于世,顺应魏晋玄学中的清谈风气,以佛教思想解读《庄子》。
皎然提到的“支公好鹤”这一典故,出自《世说新语》:支道林喜欢养鹤,有人送了他一对小鹤,等小鹤渐渐长出羽翼,时时想要飞,支道林却舍不得它们飞走,就剪断了鹤的羽根,使得它们没办法再飞,两只鹤低下头来,看上去就像人一样沮丧,这让支道林颇为感叹“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所以,等到鹤的羽毛重新长出来,支道林就让它们飞走了。这一典故意在揭示自由是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命的追求,所以,皎然称赞支道林“率性无机多脱略”,其本质还是对道家“逍遥”人格理想的肯定。当然,佛教的理论中也能产生“逍遥”的精神境界,只是因为支道林身在魏晋玄学,又有僧人的身份,所以其思想偏重老庄,还是偏重佛教般若学,很难区别。
在中国佛教思想发展的过程中,支道林处于佛教中国化的开端,在这一阶段中,中国人开始真正地试图去理解佛教思想,出现了以儒道思想理解佛教的“格义”,也出现了对“格义”进行反思的关河旧学。作为关河旧学的代表,僧肇在《不真空论》中对这一时期般若学的中国化诠释进行了归纳,反思性的批判了包括支道林在内的六家七宗。
心无者,无心于万物,万物未尝无。此得在于神静,失在于物虚。即色者,明色不自色,故虽色而非色也。夫言色者,但当色即色,岂待色色而后为色哉?此直语色不自色,未领色之非色也。本无者,情尚于无,多触言以宾无。故非有,有即无; 非无,无亦无。[6]152
支道林作为“即色宗”受到了批判,但《即色游玄论》原文已不见,所以“即色”的意义并不明确,从僧肇的转述看来,支道林以道家的“相待”义诠释了“色即是空”的命题,却没有明白般若学色当体即空的真正意义。
支道林在关河旧学之前,作为融合道家与佛教般若学的人物,不仅熟悉道家理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认可道家思想。他通过道家思想来理解般若学,皎然称其“道家诸子论自然,此公唯许逍遥篇”。这才受到了坚持般若学、 中观学正统思想的僧肇的批判。
与僧肇不同,皎然要把支道林所理解的佛教思想拉回到正统佛学之中,所以他才写下最后那一句“山阴诗友喧四座,佳句纵横不废禅”。可见,皎然对支道林思想中所透露出来的道家逍遥是清楚的,但却并不像僧肇那样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反而是肯定支道林对佛教理论的理解。由此可见,皎然的思想立场,并不像作为关河旧学的僧肇那样坚决地站在印度中观学立场上,而是对佛教中国化维度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持一种肯定的态度。
3 至人顺道
在《万回寺》一诗中,皎然讨论了另一个佛教形象——万回,“万里称逆化,愚蠢性亦全。紫绂拖身上,妖姬安膝前。见他拘坐寂,故我是眠禅。吾知至人心,杳若青冥天”[2]206。万回和尚的形象非常奇特,由于涉及神异,所以在《宋高僧传》被归类为“感通篇”,“逆于常理,感而遂通,化于世间,观之难测”[1]710。万回和尚出家之前的经历已经具备了不同寻常的气氛,他不仅在应该能言语的年龄仍旧不会说话,而且受到同龄儿童的欺侮时也不反抗,时而欢笑、 时而悲哭,嘴角常常留着唾沫,既不轻慢贫贱者,也不恭敬富贵者。然而,最让人惊异的是,他不分酷暑寒冬,终日奔走,口呼“万回”,在《宋高僧传》的记载中,他完全是一个身体、 精神异常的形象。这样的形象在“感通篇”中是颇为常见的,比如河秃的“乍愚乍智”,阿足和尚的“形质痴浊,精神懵然”,待驾和尚的“作为诡异”、 惠忠“不食荤腥、 有异常童”等,都与万回同属一类,僧传的叙事风格往往将这一类神异僧人描述为“不正常”。
这样的“不正常”恰恰是要体现佛教对世间的出离与超越,所以,皎然写到“万里称逆化,愚蠢性亦全”。这一表述与庄子作品当中那些容貌古怪却心性完整的形象非常相似,都是通过一种外在的“不正常”来显现内心的“正常”,然后以这种不正常却正常的形象来揭示世间大部分看似正常却“不正常”的普通人。在庄子那里,那些普通人有时候被仁义等儒家口号所拘束,有时候又被其他一些伦理关系所系缚,无法获得绝对的自由,即逍遥。在佛教中,与庄子的描述极为相似,以至于如果没有最终目标的说明,实际上很难区分这种出离世间的追求到底是属于道家的精神诉求,还是佛教的。
皎然所描述的自我体验也与道家的逍遥近似,“紫绂拖身上,妖姬安膝前。见他拘坐寂,故我是眠禅”[2]206。万回雕像与皎然自己形成对比,万回雕像是拘坐的,即不自由的,皎然自己却能“眠禅”。“眠禅”的意义不是很明确,存在两种理解,眠与禅,或者眠的禅,但不论哪一种,在这句话中所呈现出来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万回因为拘坐而不能逍遥,自己却能够眠禅,并在最后一句中以“青冥天”来比喻“至人”幽远旷然的心境。
站在佛教思想的维度上,我们可以认为,皎然所说的至人心境还仅仅是一种外在的描述,他并未直接揭示这种至人心境的内涵,这与禅宗偈子的内涵相差甚远,比如《无门关》中那首著名的“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7]295。这首诗似乎也是一种出世间的表达,但在禅学乃至佛教理论的整个视域下,则凸显了对代表执着的“闲事”的破斥,并非如道家一样强调对不可名状的“道”的体认与顺应。
皎然的诗文中,顺应自然确实是他“逍遥”精神追求的一个重要侧面,在《送旻上人游天台》中,“真心不废别,试看越溪清。知汝机忘尽,春山自有情。月思华顶宿,云爱石门行。海近应须泛,无令鸥鹭惊”[2]247。虽然这首诗提到了“真心”这样的佛教理论关键性概念,但从全文来看,显然不是宗密所说的四心之一的真心,从“机忘尽”的表达来看,更接近道家顺应“道”的无心,毕竟庄子批判“机心”。由此可以推论,“机忘尽”所达到的境界,并非是大乘佛教所倡导的空之平等,而是“春山自有情”与“无令鸥鹭惊”,与佛教理念中的空相比较,显然更为贴近郭象诠释庄子逍遥所提出来的“独化”。
4 结 语
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教传入汉地后就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而禅宗就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也可以认为是最成功的佛教中国化宗派。禅宗通过它独有的表现形式,一方面展现了深奥难懂的佛教理论,另一方面又实现了佛教在最大范围内的传播,乃至波及文学、 艺术等各个领域。相比较印度佛教擅长的哲学式思辨,中国佛教显然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语言的优美,乃至于在经典翻译的过程中,必然会将语言的优美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这与两国文化的差异息息相关,古代印度流行各种宗教、 哲学流派,比如胜论、 数论等,都具有颇高的思辨水准,反映出普通民众的偏好,而中国传统中似乎从来不重视思辨,稍涉思辨都会被扔进历史的角落,比如传入的阿毗达摩哲学、 唯识哲学等,都没有在中国历史中形成多大的影响。
在重视语言而轻视思辨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诗僧这一群体尤为特殊,以中国文化喜闻乐见的诗词形式来表现佛教思想,代表了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所能实现的较高水准。但是,这也引发了随之而来的问题:形式是否影响了内容?或者更进一步说,是否仅仅具有形式?诗僧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反应佛教理论,又在多大的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一系列问题实际上都是围绕佛教中国化的维度而展开的。
作为诗僧的代表,皎然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并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但其思想中那种纠缠在道家逍遥与佛教缘起性空理论之间的精神气质,却恰恰反映了中国佛教历史上诗僧的普遍状态。如果仅仅凭借其超越于世俗的气质,而认为某一位诗僧已经通达佛教理论,并以诗词形式很好地表现了出来,这恐怕有些一厢情愿了,必须将诗僧的诗词还原回佛教思想的理论建构之中,再加以审视,才能清晰地揭示佛教中国化在诗僧精神气质上的体现,而皎然恰恰是往来于佛教禅学与道家逍遥精神向往之中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