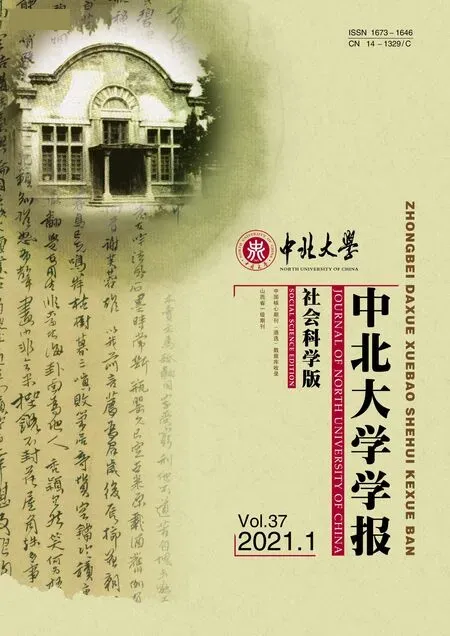异声、 变奏与对话
——论京派散文家的人道主义观
张 颖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初等教育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00)
“五四”京派散文堪称20世纪以来白话散文创作的峰顶, 无论是周作人的随笔, 还是何其芳的纯散文、 沈从文的游记、 萧乾的特写与报告文学……都代表了白话散文在思想性、 艺术性、 现实性等方面取得过的最高成就。 京派作家的创作不止局限于散文, 但绝大多数京派作家都可被认为是“散文性”的——他们对语言的看重使他们的小说创作亦带有明显的诗化、 散文化特点, 因此, 这里所说的“京派散文”亦包括了部分跨文体之作。 通常的文学史叙事将“京派”定义为一个学院派色彩浓厚、 创作态度严肃的自由主义流派, 但“京派”的思想倾向可能并不那么好概括。 文学终究是关乎人的, 借镜“五四”时期被提倡和实践的文学人道主义思想, 或能更好地透视京派思想的复杂性, 以及这种复杂性是如何影响了京派散文传统的生成与发展的。
1 京派人道主义思想溯源
被鲁迅称为“老京派”的周作人曾在《人的文学》一文中提出“人道主义”一说:“却不知世上生了人, 便同时生了人道。”[1]85并将这种人道主义解释成“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这一提法蕴含着周作人彼时的思考。 他曾在《点滴·序言》里说:“单位是我, 总数是人类”[1]236, 这是典型的“人性一元论”观点。 有研究者认为, 周作人的人道主义观受到多方面影响: 日本的新村主义、 二希(希腊、 希伯来)思想、 尼采的超人思想、 佛教思想, 以及中国文化传统里固有的天道思想与自然主义思想等。[2]228-292而其人道主义观发展的早期和后期又有变化——笔者以为, 这其中蕴含着“五四”人道主义观的两面: 救世主义与个人主义, 这两者此消彼长, 构成了周作人思想深处的主要矛盾。
以“救世”一面而言, 儒家的治齐、 仁爱思想不必细说了, 而无论是在本土扎根较久的佛教还是外来的基督教, 都无疑有“救世”一面, 但以佛教思想在知识阶层中的影响最巨。 至于原因, 如周作人所言:“佛教以异域宗教而能于中国思想上占很大的势力……其大乘的思想之入世的精神与儒家相似, 而且更为深切, 这原因恐怕要算是最大的吧。”[3]240以及“佛教来自外国, 而大乘菩萨之誓愿与禹稷精神极相似……”[3]425京派散文家里颇有深受佛教思想影响者。 周作人不必说了, 他有大量散文涉及佛经、 佛教思想, 涵盖了他对道德、 审美、 人性等诸多方面的认识; 其他京派散文家中, 废名是佛教徒, 他的跨文体之作《桥》就充满了诗趣和禅意; 俞平伯的散文中常有色空之辩,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即是典型一例; 沈从文读过《法苑珠林》 《大藏经》等佛教著作, 他的散文《七色魇》即是由佛经故事改写而成, 而在他有关小人物生存状态的描写中, 亦很容易看到一种悲悯的视角。 大乘佛教主张慈悲、 救世, 小乘则谈色空、 解脱, 无论大乘还是小乘, 都曾在很长时间里滋养我们的文艺创作, 京派作家的人道主义观有此烙印是无疑的。
周作人也十分看重基督教:“现代文学上的人道主义思想, 差不多也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 又是很可注意的事。”[1]304他看到了文学与宗教的相通之处, 即“神人合一, 物我无间”[1]304的体验, 赞美福音书上“当爱你的邻舍, 恨你的仇敌”的爱之哲学, 感叹“这是何等博大的精神”[1]299。 这些表述都呼应着他在《日本的新村》中对“人类的运命”[2]226-279的关注, 带有鲜明的乌托邦色彩。 周作人的人道主义观到后来慢慢发生了倾斜——如有论者认为他的“人学”观早在1924年就已经建构完成(以《教训之无用》一文为标志), 并说:“他先前所信仰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中的人道主义理想已被搁置起来, 只剩下了个人主义。”[2]293其实, 与其说是“搁置”了人道主义转向了个人主义, 毋宁说, 他是从人道主义之“救世主义”一面转向了“个人主义”一面。 而这个“转向”的伏笔, 实则早已蕴含在了他早期人道主义观的建构当中。 如他曾说:“文学本为的是发表个人的或社会的情感; 而宗教当初最重要的情感是保全生命, 故发出保全生命的文学。”[1]88这意味着, 他对基督教思想的重视本就包含了对“保全生命”的看重。 他亦曾说:“耶稣说: ‘爱邻如己。 ’如不先知自爱, 怎能‘如己’的爱别人呢?”[1]241他又指出:“不从‘真的个人主义’立脚, 要去与社会服务, 便容易投降社会, 补苴葺漏的行点仁政……”[1]332这依然是强调个人主义应为人间本位主义之前提; 此外, 他在谈论“二希”传统时谈过:“希腊思想是肉的, 希伯来思想是灵的; 希腊是现世的, 希伯来是永生。”[1]304“这两种思想当初分立, 互相撑拒, 造成近代的文明, 到得现代渐有融合的现象。”[1]304他显然认为人道主义即源出于二希传统(灵、 肉二元)的融合。 周作人之外, 基督教对京派散文家的影响或没有佛教那么明显, 但若将京派置于整个现代文学发生的语境中考察, 就会发现他们在观察人、 描写人性的视角、 方式上都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 考虑到佛教虽讲“万物平等”及“慈悲心”, 但佛教又始终强调“无我”, “五四”京派作家作品中流露出的个人主义视角, 就都应源自融合了二希文明的基督教思想。
周作人和鲁迅都曾受尼采《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很大影响, 尤其是那句“下去(undergang), 就是上去”[4]14-15传递出强烈的人间关怀, 而“五四”人道主义思想正是在此种“人间主义”的基石上发展起来的。 “人间”当然包含了个体与群体, 只不过, 鲁迅和周作人的路径一度重合、 终而分歧罢了。 深受布莱克、 惠特曼、 尼采、 蔼理斯等人的人性一元论影响[2]226-279, 周作人的人道主义观最初是比较理想化的, 他认为个体即人类, 这样的人道主义观, 显然是“在‘自我’观念中抽掉了与‘他人’的对立这一部分”[2]172。 其后, 当这对立浮出, 周作人不得不面对内心的矛盾, 作出自己的选择。
作为第一代京派作家, 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主要奠基者, 周作人早年在《人的文学》 《平民文学》等文中系统阐述过人道主义思想。 他的观点影响广泛而深远, 仅就流派影响而言, 可视作京派人道主义观的源头。 京派作家中, 如废名、 俞平伯、 李健吾、 朱光潜、 沈从文等人, 或曾与其交往, 或曾受其感召与启发, 作品中多少都流露过同样的立场与声调。 也因此, 周作人在人道主义观上的矛盾, 亦可视作京派文人普遍具有的矛盾, 只不过一方面因着各人性情志向的差异, 另一方面又被不同的社会现实触及而表现形态各异罢了。
2 作为时代“异声”的京派人道主义思想
“五四”一代作家深受周氏兄弟影响, 就思想倾向而言, 左翼主要受鲁迅影响, 周作人影响所及, 则多为学院派知识分子(当然这只是笼统而论)。 “京派”之形成, 跟《骆驼草》 《大公报·文艺副刊》 《文学季刊》 《水星》 《文学杂志》等报刊有很大关系。 《骆驼草》名义上的负责人是冯至和废名, 但背后的灵魂人物无疑是周作人。 围绕《骆驼草》, 慢慢聚集起一批有相似审美倾向的作者——冯至、 俞平伯、 梁遇春、 沈启无等, “提倡一种雍容、 坚忍的文化精神”[5]297。 “驼群”很快引起左翼的不满和批评, 认为他们都是些“落伍者”, 更有人宣布周作人“命定地趋于死亡的没落”。 身为“驼群”同人, 俞平伯写了《又是没落》一文反驳[5]302, 这可视为京派和左翼最早的冲突之一。 当然, “京派”作为流派的清晰浮现, 跟1930年代的“京海之争”大有关系。 “京海之争”使不同的文艺观、 人道主义观产生碰撞, 其中又以鲁迅和沈从文的观点最引人注意。
起因是沈从文对海派的批评——他在《文学者的态度》 《文人在上海》 《论“海派”》等文中批评了“投机取巧” “见风转舵” “玩票”等“海派”习气。 沈从文倒并不特指居住在上海的作家, 因他也指出:“海派作家及海派风气, 并不独存于上海一隅, 便是在北方, 也已经有了些人在一些刊物上培养这种‘人才’与‘风气’。”[6]56明确将“茅盾、 叶绍钧、 鲁迅”等人排除在外, 鲁迅却并不领情, 很快写了《“京派”与“海派”》 《北人与南人》 《“京派”和“海派”》等文进行批评。 尤其《“京派”和“海派”》一文提及明代小品文的选印, 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题签”[7]313, 将矛头指向了周作人。 考虑到沈从文和周作人的立场、 文艺观并不完全相同, 鲁迅将以沈从文为代表的“第二代京派”与以周作人为代表的“老京派”混为一谈, 显然存在误解。 然而, 这也不完全是误解。 鲁迅的敏锐之处在于——他注意到无论“老京派”亦或是“第二代京派”, 在刻意疏离现实这一点上并无太大区别。 如沈从文就曾批评过那种记着“时代”忘了“艺术”的“新八股”[6]101, 使人联想到周作人也曾借吴稚晖的观点批评中国的“土八股” “洋八股”[8]66。 对此, 鲁迅是不满的。 在《透底》一文中, 鲁迅虽觉得不该提倡八股文, 但对批评“新八股”者论调中隐藏的历史虚无主义是非常警惕的。[9]109由此观之, 鲁迅对沈从文某些观点的批评也不全是出于误会。 这场论争到后来不了了之,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二人的讨论并不在同一层面上: 鲁迅关注现实政治, 属行动层面的问题; 沈从文执着于文学性, 则属于文艺观层面的问题。 无需多言, 这场论争固然使得“海派”成为一不太“光彩”的概念, 而由于鲁迅的批评, “京派”也成了一个涵义微妙的标签。
回到当时的语境, “京派”所发无疑是“异声”, 处处显出不合时宜。 从沈从文所写的《禁书问题》 《记胡也频》 《丁玲女士被捕》等文来看, 他对国民党政府持的是谴责态度。 因《禁书问题》一文, 当时上海的右翼刊物《社会新闻》曾刊文声称沈从文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 这是沈从文不见容于右翼的一个明证。 而当施蛰存写《书籍禁止与思想左倾》为沈从文辩解时, 鲁迅则认为沈不过是“忠而获咎”[7]45。 京派同样不见容于左、 右翼的自由主义立场是显然的。
其实, 遑论政治立场, 就文艺观而言, “京派”同样显出特立独行之姿。 沈从文写作之初曾受徐志摩提携, 跟新月派同人走得较近, 但他的文艺观显然跟同为新月派的梁实秋不同。 梁实秋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中批评了文学中的“抒情主义” “人力车夫派” “平等观念”和“人道主义”[10]14-18, 而这些恰恰都是京派创作的重要内涵。 “京派”与“新月派”同样带有唯美主义倾向, 但“新月派”的唯美剔除了情感、 道德的部分, 这是“京派”和“新月派”的不同; 至于跟左翼比较, 同样受鲁迅影响, 左翼作家笔下的乡土世界一片凋零、 破败, 人民大多过着愚昧而不自知的悲惨生活。 王鲁彦的《柚子》、 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等都在此例。 这些作者多采取启蒙视角, 多少有点居高临下, 而在沈从文的散文集《湘行书简》 《湘行散记》 《湘西》中, 作者则以平视眼光写了一系列乡土小人物。 沈从文生长于“五四”语境中, 思维不可能不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 即如他在《湘行书简》里写的:“多数人爱点钱, 爱吃点好东西, 皆可以从从容容活下去的。 这种多数人真是为生而生的。 但少数人呢, 却看得远一点, 为民族为人类而生。”[11]184诚如张新颖所言:“多数人不追问生命的意义而活着, 少数人因为自觉而为民族的代表, 使生命放光, 这是比较典型的五四新文化的思维和眼光。”[12]98但他的想法很快就发生了改变, 在接下来另一封信中, 他写道:“……这些人不需要我们来可怜, 我们应当来尊敬来爱。 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 却在自然上各担负自己那分命运……我感动得很!”[11]188同样写辛亥革命的题材——在鲁迅的作品中, “华老栓”们无疑是作为被启蒙对象而存在于叙事中的; 而在《从文自传》中, 作者不动声色地写自己小时候看了一个月的杀人, 恰与鲁迅的叙事构成对立或说是补充。 无疑, 他们“看人”的方式并不相同(这当然跟个体的经验有关): 在鲁迅笔下, 人性与人的命运始终是在属人的现实与历史中发生的; 而沈从文的文学世界——“就不仅仅是人的世界, 而是要比人的世界大”[12]107, 因“鲁迅是质疑性的, 沈从文是容纳性的”[12]68; 除了观察视角不同, 更大不同或在于各自与现实的关系。 鲁迅是直接以笔作武器和现实短兵相接, 沈从文虽也认为面对“社会组织不合理处”作家应当“爱憎毫不含糊”[6]85, 但他又认为文艺不该“和政治关系太密切”[6]301。 沈从文的此种看法在“京派”作家中很具代表性, 如周作人对“中庸”之境的追求, 朱光潜的“静穆”说, 梁宗岱的“审美直觉说”等, 从表面看都是指审美境界, 但究其本质, 也都暗含对“文艺-现实”之关系的看法。
“京派”的尴尬或在于: 他们既对权势者的凌砾弱势表达不满, 却又被左翼指责为不关心民生疾苦。 但若能换一个角度看, 会发现在京派的疏离感中实又蕴含着一种超越时代的倾向。 京派的这个特点跟海派很相似——他们同样都注目到了一个永恒的日常。 不同或在于: 京派倾心于乡村世界, 将神性作为普遍人性的理想状态来赞颂, 带有超拔之意; 海派则沉浸于都市世情, 以现代都市的世俗日常作为普遍人性的栖身之所, 相较于京派的超拔, 海派则显出沉堕之姿。 仅就京派而言, 他们内在的“疏离”与“超拔”无疑构成了一种矛盾、 紧张, 使得无论是哪一面都不能被进行得彻底。
3 京派人道主义思想的变奏及其原因
如果不是身处于一个战乱频仍、 家国倾危的时代, 京派散文家内心的社会良心和艺术良心大概会继续保持互不妨碍的平衡。 但“风沙扑面、 虎狼成群”的时代在迫使所有作家做出选择——即便是“京派”最稳固的部分也难免发生动摇。
如果说第一代“京派”的形成跟《语丝》 《骆驼草》等刊物有着密切关系, 第二代“京派”则主要围绕沈从文主持的《大公报·文艺副刊》而形成, 在这份报纸上, 不少京派散文家都发表过作品。 他们在创作上大抵都追求“艺术” “纯粹”, 他们的努力使得现代散文进一步走向了文体自觉。 其中, 何其芳的《画梦录》堪为京派纯散文文本之“最”。 《画梦录》显然受到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 特点是精丽、 抽象而忧郁, 富有象征的诗趣。 以其苦心孤诣的艺术追求, 《画梦录》标志着现代散文文类边界的进一步清晰, 为后世作者提供了艺术散文创作的范本。 除了《大公报·文艺副刊》, 《水星》 《文学杂志》亦显现出京派散文百流汇川的风貌。 《水星》的办刊态度同于《大公报·文艺副刊》, 好些京派散文家的重要作品都曾在《水星》上发表, 如沈从文的《湘行散记》中某些篇目、 李广田的《花鸟舅爷》、 芦焚的《谷之夜》等; 此外, 由1937年创刊, 旋即停刊, 又于1947年复刊的《文学杂志》亦不容小觑。 停刊之前的《文学杂志》所刊载的也多是典型的京派散文。 这些散文多着意经营艺术性, 与现实若即若离, 带有朦胧飘渺的象牙塔气息——这无疑跟《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沈从文、 萧乾的文艺观有极大关系。 萧乾曾在《为技巧伸冤》等文中呼吁过重视技巧, 而沈从文也在《论技巧》一文中强调过:“一个懂得技巧在艺术完成上的责任的人, 对于技巧的态度, 似乎是应当看得客气一点的……人类高尚的理想, 健康的理想, 必须先融解在文字里, 这‘理想’方可成为艺术。”[13]374考虑到现代散文自诞生以来文类边界始终模糊未明, 萧乾、 沈从文的主张就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散文的文体革新。
1937年之后, 京派散文家笔下的风光有了很大不同, “技巧”不再显得至为重要。 师陀早先有散文集《黄花苔》, 集中收录的像《失乐园》 《谷之夜》等名篇, 可以看到师法鲁迅的《朝花夕拾》的痕迹, 怀旧的哀愁与清醒的批判融合成艺术的整体。 而在抗战后, 师陀的文风发生了变化, 写了《上海手札》那样的纪实作品, 于其中揭露汉奸嘴脸, 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行, 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作为报人, 萧乾的散文本就有两种面貌, 他既写过《古城》 《叹息的船》 《苦奈树》那样朦胧婉曲、 有很强抒情性的散文, 也写过《平绥道上》 《鲁西流民图》等反映现实苦难的特写。 1939年以后, 萧乾作为记者去往二战欧洲战场, 更是写了大量的随军通讯和旅途笔记。 对此, 有论者指出: 萧乾实是“介于京派趣味和左翼良知之间”, 是很有见地的; 何其芳则是以散文《回乡杂记》为标志, 从“美丽的辽远的梦”回到了现实的土地。 如他自己所说:“我的情感粗起来了。 它们和《画梦录》中那些雕饰幻想的东西是多么不同啊。”[14]246李广田早期的散文朴素、 恬淡, 后来越来越面向现实, 讲道理、 论艺术的文章多了, 也写了像《冷水河》 《江边夜话》等质朴厚重的散文——如卞之琳评价的:“不能再像东斋日子里那样慢悠悠的走路了。 这都是打上的时代印记和社会印记。”[15]221至于京派的另一人物林徽因, 卞之琳认为她早年写的作品流露出对社会下层的同情毕竟还是隔着一层, 世界仍然在她的“窗子以外”, 后来则来了个“彻底的改变”[15]237, 林徽因在战时所写的书信也可当散文去读, 那里面的确有更鲜明的现实忧患之感……很显然, 特写与报告文学成为战时散文的主流, 这一点, 即连强调过文艺须跟政治保持距离的沈从文也不能忽视。 在《论特写》一文中, 沈从文承认, 特写一类的纪实文字的真实价值, “必然得到重估”, “他的作用在目前已极大, 还会影响到报纸的将来, 更会影响到现代文学中散文和小说形式及内容。”他希望作者能够用笔作桥梁, “渡入思想家领域”[13]471, 这在当时无疑显得理想化, 但这也证明了面对时代沉重的苦难, 作家已无从回避。
京派散文家的这一转向固然有外在现实的促迫, 但在绝大多数京派散文家身上, 本就存在触发这一转折的因子。 包括周作人、 废名等“老京派”在内, 尽管这一流派内部思想色调驳杂, 但他们多持有对底层和弱势的同情。 他们对世事的不能忘怀, 对现实的忧心, 实则根植于我们漫长的文化传统。 诚如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所言:“在中国, 当我们说‘人的本质’的时候, 这个‘人’不是可以和社会割裂开的个人, 而是出于有机的整体中的个人, 即社会性的个人。”[16]156增田涉也曾提及:“以拯救他人为主是大乘佛教, 以救己为先是小乘佛教, 从中国古来不接受小乘而大乘盛行的事实里, 我觉得, 那或者可认为是中国人一般的精神基础吧。 说是在中国文学里没有‘自我追求’, 说是因此就缺乏智性, 但就这样的精神基础看起来, 是没有办法的, 应该说那样要求是无理的。”[17]86可以这么说, “京派”散文家的转向或说是“变奏”, 恰恰证明了鲁迅所说的:“诗文也是人事, 既有诗, 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18]538
京派的这一转向也跟现代文学的发生机制有关。 如有研究者所言:“知识者与政治, 知识者与人民, 正是使现代文学史成其为现代文学史的基本关系, 是规定这一时期文学的基本性质、 基本特征的‘关系’。”[19]115按照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起源》一书的观点, 所谓“现代文学”, 所谓“个体的觉醒”, 都不是不证自明的概念, 而是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共生的。[20]8京派的人道主义观, 也是从“救亡”背景下萌生出的东西, “京派”的转向与变奏也不过是凸显了这一背景的存在。
4 京派人道主义思想的对话性
有关“转向”之后的京派散文家的创作, 有论者言:“所有这些散文创作都偏离了此前纯艺术散文创作的倾向, 已经不能算是文学史意义上的京派散文。”[21]76但1937是否就是界碑式的存在——意味着“京派”的终结呢?无疑, 如同周作人, 以沈从文为代表的第二代“京派”亦拥有某种矛盾与复杂性。 他们以独立之姿开辟文艺园地, 跟同时代的许多其他流派、 思潮形成了一种紧张甚至对立的关系。 但只要将京派后期的创作纳入他们生长、 变化的轨迹去看待, 这何尝不是他们自身内在的紧张与矛盾。 在常见的文学史叙事中, “京派”很容易被描述为“与时代错位的高蹈派”[22]17, 然而, “我们有必要将所有的话语放回到它们共生的语境中, 去理解它们言说了什么和怎样言说的, 它们要求的是话语的权利还是话语的权力”[22]18。 溯源式的辨析, 在任何文学史叙事中都十分必要。
不同时期的“京派”本就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1930年, 沈从文在《窄而霉斋闲话》 《论冯文炳》等文中批评过“京样”文学的“趣味主义”, 批评周作人所表现的“僧侣模样领会世情的人格”, 在废名、 俞平伯等身上导致了一种“趣味的恶化”。 这“趣味的相同”使创作远离“朴素的美”。 并认为废名的某些作品具有“畸形的姿态”和“衰老厌世意识”[13]515, 用语十分犀利; 在另一文章中, 沈从文写道:“要人迷信‘性灵’, 尊重‘袁中郎’, 且承认小品文比任何东西还重要。 真是一个幽默的打算!……试想想, 二十来岁的读者, 活到目前这个国家里, 那里还能有这种潇洒情趣, 那里还宜于培养这种情趣?”[6]93使人想起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对小品文的批评; 沈从文甚至认为废名和穆时英的文字都属“邪僻”[13]148-150一路, 这看起来难以理解, 但他其实是看到了所谓“老京派”和“海派”在“趣味”上的一致, 也即“名士才情”和“商业竞卖”的合流[6]54, 这也近于鲁迅的观点; 沈从文肯定废名前期作品中表现出的“平凡的人性的美”, 但不满于《莫须有先生传》等作品。 他认为“冯文炳君只按照自己的兴味做了一部分所欢喜的事”。 而谈及自己的作品, 则说:“使社会的每一面, 每一棱, 皆有机会在作者笔下写出, 是《雨后》作者的兴味与成就。”[13]150简言之, 沈从文认为废名的创作重个人主义的趣味, 而他自己眼光、 笔触所及是更广大的现实。 单从作品本身看, 也的确如此。 沈从文作品中流露出更多对底层的关怀与悲悯。 汪曾祺评价过:“《新与旧》里表现了这种痛苦, 《菜园》里表现了这种痛苦。 《丈夫》 《贵生》里也表现了这种痛苦。 他的散文也到处流露了这种痛苦。”[23]216-217可以看出, 在人道主义观层面上, 沈从文跟“老京派”有着较大差别——前者文字中有更多个人主义趣味的低徊, 沈从文则一直在用他自己的方式触摸现实, 表达对人的关怀。 沈从文与鲁迅则有许多相通处, 如他们都厌恶虚伪和滥权: 沈从文笔下的乡土、 都市叙事共同构成了他的人性观——他赞美乡土世界人性的质朴、 自然, 批判现代文明中人的狭窄庸懦与虚伪。 而鲁迅也赞许初民的想象力, 认为:“伪士当去, 迷信可存。”[24]30“文明如华, 蛮野如蕾, 文明如实, 蛮野如华。”[25]66二人言说方式或许不同, 但同样关心国民性的塑造与民族的未来。 后人往往易将沈从文视为鲁迅及左翼的对立面, 但沈从文恰是受鲁迅影响而走上创作道路的, 他自言受到鲁迅的译著很大影响, 从而产生“终生从事这个工作的向往”[26]220-221。 以及受到鲁迅创作的“以乡村回忆作题材的小说”的影响, 而获得“不少的勇气和信心”[13]233。 在人道主义观层面上, 沈从文和鲁迅相近, 不过视角、 焦点不同, 表述方式有异罢了。
沈从文之外, 其他京派散文家也都有同情底层的倾向。 如在林徽因的散文《窗子以外》中——作者目光所及, 是农夫、 人力车夫、 缝补的妇女、 买菜的小贩, 颇有些感慨自己是与这类人是隔绝的, 从中也不难看出作者从“窗子以内”走到“窗子以外”的渴望; 凌叔华的《杨妈》 《说有这么一回事》 《搬家》等也是如此, 不过她更多关心妇女与儿童——身世凄苦的女佣、 婚恋不自主的女性、 天真脆弱的孩子等; 萧乾的散文《脚踏车的哲学》对人力车夫生存的勇敢致以赞美, 《链》对航船上扛货苦力的惨死致以沉重的同情; 梁遇春在散文《救火夫》里借赞美“救火夫”这一职业, 表达了对能够救世人于“水火”的人生的向往等, 都是此种救世的人道主义观的体现。
“京派”散文家中, 有少数难以归类, 如萧乾, 但最难归类的或许要算师陀。 王任叔说师陀“背后伸出一只沈从文的手”[27]381, 杨义则认为师陀处在“京派”和左联之间。 师陀自己都不以为然。 在他看来, 京、 海两派看起来是写作态度问题, “骨子里却含政治问题”[27]105, 明确表示自己是“鲁迅的崇拜者”[27]103。 其实从审美上看, 师陀的确近于“京派”。 他的小说亦多关注乡土世界, 许多作品如《果园城记》 《无望村的馆主》等都有散文化特点, 像“夏侯杞”系列, 不但近于何其芳《画梦录》的独语体, 也近于废名《莫须有先生传》那样的趣味人物传。 但师陀对自己被归入“京派”流露不满, 原因即在于那句“骨子里却含政治问题”。 对于沈从文所批评的“差不多”现象, 他是这样认为的:“三十年代由于国家岌岌可危, 部分‘左翼’作家救亡心切, 脱离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 写自己不熟悉的题材, ‘差不多’更盛行, 这是可以而且应该理解的。”[27]380师陀的这个特点, 的确有别于一般京派成员, 这无疑构成了这一流派自身的复杂性或说是弹性。
京派散文家无疑有个人主义的一面, 他们崇尚创作自由, 同时又同情弱者、 关心社会现实, 抗战爆发促使他们自觉地从前一面转向了后一面。 转向之后, 他们的散文创作或许不能被称为典型的京派散文, 但若考虑到他们整个的变化轨迹及内部的复杂性, 则这一转向本身仍是属京派所有。 以《文学杂志》这一刊物为例, 1937年创刊后仅存续数月, 就因抗战爆发而停刊。 停刊之前, 为该刊撰写散文的几乎都是京派文人, 其中有一个在当时并不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杨绛(杨季康), 她最早的散文《阴》 《收脚印》等都是发表于《文学杂志》; 《文学杂志》复刊后的一段时间, 旧有成员固然风流云散, 但又有新人如汪曾祺的亮相, 发表了《礼拜天早晨》 《牙疼》等散文。 杂志存续时间短, 但却让1980年代最杰出的两位散文家杨绛、 汪曾祺先后亮相, 这两位可以说是横跨两个时代、 最能体现京派之延续性的散文家。 诚如孙郁所言, 这是“京派传统在隐秘中存活的根据”[28]。 当然, 时代的变迁不能不在作家身上打上烙印。 汪曾祺的散文《背东西的兽物》写于1948年, 那会儿, 他笔下的“伕子”仿佛无灵魂、 无思想, 与底层人民的隔膜是显而易见的; 1980年代之后, 他则写了《吴大和尚和七拳半》 《闲市闲民》 《二愣子》等小人物素描, 笔下多了烟火气, 也多了对人间的关心。 而他对自己的评价也恰恰如是:“我大概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式的、 抒情的人道主义者。”[29]110再说杨绛, 《阴》 《收脚印》时代的杨绛就散文创作而言并无鲜明的个人特色, 文笔清幽诗意, 也属不食人间烟火一派。 而到了1980年代以后, 《干校六记》 《将饮茶》等散文一转而为风格素朴、 明净、 练达, 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对美好人性的信念。 《老王》 《林奶奶》 《鬼》等作品为小人物塑像, 写得亲切、 细腻而温情。 诚如止庵所评价的:“在她的作品中始终关注着的是人……她并不针对生活发一些具体的议论, 而是直达整个人生, 从而有一种悲天悯人的胸怀。 人道主义说穿了就是对人类的命运的痛苦感受, 在杨绛的作品中表现的也是这个。”[30]19这两位散文家不但延续了“五四”京派散文的审美, 他们的散文中也贯穿着“五四”人道主义精神的回响, 只不过, 这一精神在他们笔下显然是更为平民化了, 而这不妨看作是不同时代的京派散文家之间的对话。
综上可知, 从周作人散文中“激进”与“避世”的消长, 到1930年代京派散文家对“纯散文”的坚守, 再到1937年以后京派的转向、 变奏, 都可以看成是京派人道主义观之复杂性的体现。 这复杂或不仅是京派思想的复杂, 更代表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在启蒙与救亡、 传统与现代、 个人主义与救世主义之间共有的矛盾。 现代白话散文的兴衰始终系于作者心灵的包容、 丰富与活跃程度, 京派散文家思想上的矛盾, 或恰是这种包容、 丰富与活跃的体现。 他们不惮于孤独的坚守, 也不拒绝反思、 变化和突破, 而正是由于这个特点, 他们影响所及, 在1980年代以后, 既有像杨绛、 汪曾祺这样优秀的“嫡京派”散文家的横空出世, 又滋养出了张中行、 季羡林、 黄裳、 金克木、 舒芜等“新京派”散文家异彩纷呈的创作。 相信京派散文一脉仍会流传下去, 与时代、 生活展开一场场新的对话, 并继续丰富现代白话散文的艺术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