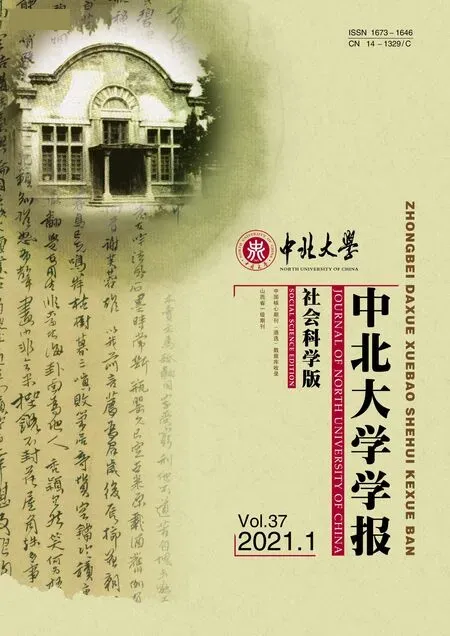论网络剧《长安十二时辰》的审美风格与文化蕴涵
王作剩
(吉首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严肃的历史题材影视剧贵在存“真气”, 能够营造当时真正的社会环境氛围, 实现历史与艺术双重真实的和谐统一, 又贵在重“气质”, 使其别具一格, 自有风韵。 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的网络剧《长安十二时辰》, 虽然开播前经历了延迟播放以及缺少足够的媒体宣传, 但自2019年6月底于优酷网悄然开播以来, 还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 且获得了良好的口碑。 在笔者看来, 该剧之所以能够得到观众的喜爱与肯定, 是因为其成功做到了存“真气”与重“气质”, 自成审美风格。 一方面, 它讲究真实, 存“盛唐气象”的“真气”。 服化道等集精美与真实于一体, 展现了一个熟悉而又陌生、 虚构却又真实的盛唐形象, “让当下观众通过这部剧感受到千年之前大唐生活的烟火气、 人情味”[1], 是一部在硬件层面上彰显着工匠精神与技艺娴熟的典范之作; 另一方面, 它重视艺术创作, 具有“雄浑悲壮”的“气质”。 在叙事较为流畅、 情节足够丰富、 视听语言相当高级与演技堪称精湛等基础上, 散发着一种如杜甫诗歌一般的雄浑悲壮的美学气质, 让观众获得了激动与沉郁俱存的审美体验。 更加令人欣喜的是, 在鼓励积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下语境里, 该剧能够做到既巧妙地缝合进了忧患意识与讽喻修辞等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又极其自然地融入了捍卫百姓权益、 追求精神自由与高扬自我意识的现代精神, 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效衔接和对话, 是一部在软件层面上充盈着现代精神的、 蕴含着文化内涵的文艺作品。 这也正是网络剧等文艺作品应该努力的方向与追求的目标。
1 雄浑悲壮的审美风格
与中国哲学“气论”与“象论”息息相关的“气象论”, 是我国传统文艺理论中的重要范畴。 其中, 南宋诗论家严羽认为“诗之法有五:曰体制, 曰格力, 曰气象, 曰兴趣, 曰音节”[2]7, 他所指的气象则是为气貌与风貌, 即诗歌所展现出来的风格与气质, 既可以指向某位诗人的诗歌, 也可以指向某时期的诗歌。 对于盛唐诗歌总的风貌与审美特征, 严羽概括为“雄浑稚健”, 也就是“盛唐诸公之诗, 如颜鲁公书, 既笔力雄壮, 又气象浑厚”[2]184。 他指出盛唐诗歌区别于其他时代所独有的气象, 即气象浑厚与雄壮, 也使用了“盛唐人气象”[2]157一词。 此后, 便有诗人、 文论家等不断阐发, 直到20世纪50年代, 林庚先生才提出“盛唐气象”这一概念并认为“蓬勃的朝气, 青春的旋律, 这就是‘盛唐气象’与‘盛唐之音’的本质”[3]。 其观点, 也得到了一定认同。 由此, 经过学者的反复阐释、 教师的课堂教学、 影视文化传播等, 青春、 朝气、 魄力等则成为了形容盛唐与盛唐诗歌的关键词, 当国人提及它们时, 便会产生赞美、 肯定、 憧憬等正向态度, 生发出一股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自信感等情感。 因此, 从一定意义上讲, 《长安十二时辰》满足了人们关于“大唐盛世”这一民族想象, 使其具有了“雄浑”的审美风格。
“雄浑”审美风格的表层在于昂扬向上的“象”。 该剧有条不紊地向观众展示着盛唐国都长安美好的一面:极尽繁华、 精致、 有序与国际化。 说它繁华, 是因为上元节这一天的长安, 东市与西市热闹非凡, 人声鼎沸, 华灯满街, 充满着傩戏表演与华车斗彩等, 整个长安沉浸在节庆的热闹氛围中; 说它精致, 是因为大到画栋雕梁与坊楼布局, 小到着装打扮与饮食, 都雍容华贵与高贵得体, 令人生羡; 说它有序, 是因为长安108坊, 整齐而有威严, 人们安居乐业, 东市与西市也井然有序; 说它国际化, 是因为长安聚集着波斯人、 粟特人、 日本人与非洲人等世界各地的人, 他们在长安从商、 从政与从教等, 对长安产生深刻的认同感, 认长安为自己的家。 这些符号所形成的长安表象, 美好而真实, 大气而亲和, 符合当时的历史, 也契合当下受众的审美期待。 它的中层在于画面、 节奏、 音乐等所形成的“气与势”。 整部剧, 叙事繁复但不失圆浑, 造型精致而免于流丽, 志向远大却性格淳朴, 内容充实而又能融于有意味的形式之中, 可谓是气质浑朴自然; 而节奏则急缓有致, 动作凌厉劲道, 场面繁杂大气, 精神昂扬有力, 可谓是气势雄伟壮阔。 它的深层则在于精神, 即人人怀揣着理想, 渴望建功立业与充满朝气的时代精神。 幼童祝玄以一行大师为榜样, 渴望将来为大唐造出利万代与万民而不衰的有用之物; 少年李必与中年徐宾胸怀天下, 怀揣宰相之志; 老年何监老骥伏枥与心忧苍生。 正是这种群体性的对人生价值的高蹈追求, 才正是盛唐气象真正的实质与核心, 也就是雄浑的精神风貌。
众所周知的是, 在一定时空内, 由于教育、 宣传与大众文化等宏观方面的影响, 绝大多数的人们往往对某一事物或者人物有着普遍的固定印象。 这种印象不管是真实的, 还是虚构的, 总是较为单一而非全面的。 那么, 对于盛唐与盛唐诗歌, 亦是如此。 可贵的是, 创作者在塑造大唐盛世与表现雄壮浑厚的盛唐气象的同时, 又打破着这一传统, 使其充满了危机, 且具有了另外一种美, 形成了该剧另一种审美风格——沉郁悲壮。
历史上的大唐盛世, 特别是天宝年间, 存在着日益加深的矛盾与危机, 在繁华之余, 也存在着黑暗与丑恶, 而对于时代有着敏感嗅觉的杜甫等诗人便捕捉到了这种微妙转变。 在诗歌创作上, 既有对自身的怀才不遇而充满了感慨, 更有对盛世与大唐的未来充满了忧虑, 共同唱出了一曲非主流但也不容忽视的时代悲音。 因而, “盛唐气象的基本特质也不是青春浪漫, 而是雄浑悲壮”[4]。 《长安十二时辰》恰好是对这段盛中有危的大唐历史的真实呈现, 蕴含着浓郁的沉郁悲壮之美。
该剧围绕“官兵捉狼”这一事件, 集中塑造了体制内士兵、 官员及知识分子的悲壮群像。 在士兵层面, 该剧通过话语陈述与场景回忆等手段, 运用特写、 慢镜头与悲壮配乐等视听语言, 较为全面地呈现了当时“烽燧堡战役”的惨烈情境:敌人众多, 硝烟弥漫, 乱箭漫天, 刀光血影, 尸体遍野。 张小敬、 萧规、 闻无忌与丁老三等第8团虽然恪尽职守浴血奋战, 但终因援军故意不救而导致211人死亡, 仅有9人存活。 该剧在凸显惨烈的同时, 又呈现出第8团的乐观主义英雄精神。 因此, 极具悲壮之美与崇高之美。 在官员层面, 李必、 徐宾、 姚汝能与崔器等人, 有理想但实现不了。 徐宾有宰相之才, 但久屈于八品小吏, 不被赏识, 终走向自我证明的不归路; 姚汝能背负着家族之荣耀与耻辱而急于重振威望, 终选择了做暗桩的不义之举; 崔器出身卑微而渴望出人头地, 终左右摇摆而被人不喜。 而狼卫曹破延、 萧规、 鱼肠等人, 也是因为理想的破灭而选择了极端之路。 尽管他们因理想的破灭而走向了正义的反面, 但他们仍然值得同情与尊敬, 因为他们是有理想与有良知的悲剧人物。 徐宾的望楼诉说、 姚汝能的望楼传信、 崔器的以死捍卫靖安司与萧规的誓死护旗等行为, 都无比悲壮与崇高。
这种沉郁悲壮的悲音虽不同于青春与浪漫的盛唐气象, 但也不同于懦弱、 悲哀与绝望之音, 而是蕴含着中和、 沉稳、 反抗、 奋斗且有一丝激情的精神底蕴, 介于少年意气与中年平稳之间。 其与雄壮浑厚共同组成了“雄浑悲壮”的盛唐气象, 这正是该剧所具有的独特的审美风格。
2 忧患意识的传统文化蕴涵
《长安十二时辰》不仅再现了大唐盛世的繁华气象, 呈现出了雄浑悲壮的审美风格, 而且还有着深沉的文化蕴涵。 其文化蕴涵, 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 便是巧妙缝合进了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又与讽喻修辞息息相关。
理解中国文化, 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 离不开对忧患意识的深入思考, 可以说, 中国传统文化典籍里与历代仁人志士的言行中无不流淌着忧患意识。 自先秦始, 忧患意识便开始萌芽。 它既可以针对个人, “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与“君子忧道不忧贫”[5]162,166; 又可以由个人上升到国家与民族,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5]276, 忧患的较高境界则为忧国忧民。 近现代学者徐复观一方面指出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 也即是精神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6]18, 另一方面则将其上升到中国人的集体心理结构与精神核心的高度。 其实, 忧患意识并不难理解, 它是国人所普遍具有的一种精神状态与思维方式, 即对现实中的自己、 国家与民族有着清醒的认识、 理性的评价与长远的打算, 能够为了长远的目标与利益而常常反思目前的一言一行并做到“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这种意识长久影响着中国人以及中国文艺作品的创作, 因此, 《长安十二时辰》既可以说是体现了这种意识, 又可以说是这种忧患意识的产物。
该剧的忧患意识主要表现在清醒的危机意识、 恳切的责任意识与赤诚的爱民情怀等方面。 首先, 危机意识。 剧中的何监、 张小敬、 徐宾、 李玙与何孚等人, 无不感到当前的唐朝正遭受着潜在的危机。 何监身为朝廷高位者, 经历过开元盛世的高光时刻, 因此对于天宝年间存在的种种问题而忧心忡忡。 他因玄宗贪图享乐与重用且欲要将权力交付给右相林九郎而饮酒悲吟“昭昭有唐, 天俾万国, 毁了, 毁了, 毁了”并跌落在沙盘上; 长期接触底层生活的张小敬, 面对李必赞美长安而说出“眼前这繁华啊, 未必能长远”; 八品小吏徐宾鉴于唐朝无纸可记案牍而认为“看上去是小事, 可人心的失望就是从这些小事开始的”, 最终可能导致官吏“没了心中热情和尽职之心”, 他也为“塞外战事频繁, 朝中却寻欢作乐, 将财政挥霍一空”的腐败现实而感到悲愤; 太子李玙也看到了盛唐的危机, 他知道“长安虽然看似繁盛, 那只不过是摆在父亲面前的一瓶假花”, 深受税制之苦的百姓将失去对大唐的信心; 即使是户部抄录小吏祝慈也因朝廷的卖官鬻爵而感到深深的忧虑, 发出“长安今日之繁华, 已是在吸万民骨髓, 然而不知还能吸多久”的悲叹。 其次, 责任意识。 当他们看到盛唐的危机并身体力行的去改变它时, 便是一种恳切的责任意识。 何监能够冒死劝谏甚至是批评玄宗且刺杀林九郎, 不能不说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使然; 萧规等第八团誓死不退, 便是要肩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 张小敬有将帅之才, 却甘心做不良帅, 且不顾性命地去追捕狼卫, 这便是负起保卫长安的责任; 李必坚守自己的职责, 全力查案, 因为于他而言, 查明真相才是忠于职守; 靖安司的群吏们, 在危难面前, 虽然有过动摇, 但依然坚守起自己的职责, 与靖安司共患难。 这些行为最终指向了对长安、 盛唐与百姓的爱。
忧患意识落实到行动的另一大表现, 则是下层对上层的真诚讽谏。 讽谏是封建主义时代对官员的道德要求、 行为标准与制度要求, 不仅有谏官制, 而且将“文死谏”视为臣子忠诚的较高标准, 因此出现了魏征、 房玄龄、 姚崇等著名的谏臣, 唐朝尤甚。 而在此剧中, 何监在花萼楼向唐玄宗拼死劝谏, 感人肺腑; 徐宾于望楼舍生死谏, 让人落泪; 八品吏员祝慈向唐玄宗针砭时政, 令人钦佩。 可以说, 该剧通过对何监、 徐宾、 祝慈等群像的塑造, 复活了讽谏传统。 不过, 讽谏具有“逆龙鳞而危身”的风险, 由此, 出现了讽喻修辞, 即“借用寓言、 故事来说明道理, 委婉地规劝、 启发别人或者进行讽刺谴责”[7]542, 在文艺创作与理论上, 便出现了讽喻文艺作品与理论。
值得玩味的是, 如果从内容上看, 《长安十二时辰》里充满了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那么, 若将该剧看作一个整体, 则像是一则寓言, 是对现实的一种讽喻。 换言之, 创作者通过讽喻这种修辞来映照与反思现实, 而这恰好对应了曹盾导演所说的“不论什么题材, 所有创作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 就是要有现实生活做根基, 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1]。 剧作内外的暗合主要表现在, 剧中官商的“强拆民居”与“草菅人命”、 朝廷的“腐败”与“懒政”、 皇帝的“穷奢极欲”与“盲目自信”、 底层的“辛酸”、 “申诉无门”与“极端复仇”, 无不可以从现实中找到对应的现象。 这与其说是黑暗于古今相通, 不若说是创作者的有意而为之。 而且该剧也容易让人由古代的盛唐联想到今天的“崛起的大国”, 其隐藏的语言, 令人深思。 正如剧中祝慈叮嘱幼儿祝玄的那样, “做事当勤谨务实, 不可图表面风光”。 总而言之, 这种讽喻修辞的目的不是非理性的嘲讽, 而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借古讽今, 反思现在与走向未来, 其底色还是忧患意识。
3 以人为本的现代精神蕴涵
文艺创作离不开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的共同滋养, 因此, 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创作除了要做到尊重历史与接近真实外, 还需要融入时代审美、 普世价值、 共同理想与主体意识等, 也就是现代精神。 而将传统与现代融合较好的影视剧, 《长安十二时辰》便是典型案例之一。 它不仅缝合了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 而且凸显了以人为本的现代精神, 即深沉的百姓情怀与高扬的主体意识, 丰富与拓深了该剧的文化蕴涵。
以人为本的现代精神蕴涵, 首先表现在以民为本的百姓情怀。 所谓百姓情怀, 即作为主体的人, 充满了对百姓的尊重、 关心与热爱, 含有民权、 民意、 民生、 民本与民主等思想。 而这种极具现代精神的百姓情怀与传统文化的“民本位”思想息息相关又有质的不同。 在古代, 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与巩固政权的稳定, 知识分子与统治阶级提出一种与“君本位” “官本位”相异的“民本位”思想, 即要求统治阶级以民为重与以民为贵, 用仁爱之心去爱民与护民, 以治世之能去安民、 利民与富民等。 取材于唐朝历史的《长安十二时辰》, 既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但又对其进行了现代性审视与重塑。 正如该剧编剧兼原著作者马伯庸所说:“强调人人平等、 重视每一个体生命价值的认识, 这属于现代人的价值观。”[8]换言之, 他赋予了该剧一种现代性的平民观, 即剧中张小敬等人物的行为动机是建立在捍卫人人平等与尊重每个鲜活的生命基础之上的, 百姓是真正对等于甚至高于统治阶级的, 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百姓而非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者。
做了十年陇右兵、 经历过“烽燧堡惨战”与九年不良帅的张小敬, 见识到了底层百姓的卑微与统治阶层的腐朽, 最终完成了由保卫国家(实质上是捍卫统治阶级的利益)到保护平民百姓的价值观转换。 他评价李必“只知道君王, 可怜”, 去抓捕狼卫不是为了李必升官、 皇帝安全, 而是去捍卫长安百姓的安全; 他质问旅贲军崔器为何不管无名的女人, 是基于“只要是人, 都跟你有关系, 不分三六九等, 你是大唐的兵”的百姓意识; 他谴责姚汝能对人的阶层分类与对生命的漠视, 是因为他认为“平白无故的去叫一个人去死, 不值得骄傲”; 他最终拯救了长安, 却放弃了皇帝的犒赏, 其原因是他仅仅单纯地希望长安人能够万代平安。 此外, 崔器、 徐宾与毛顺等人也持有深沉的百姓情怀。 崔器认为活着的价值便是保护过着平凡日子的长安老百姓, 因此, 他努力上进与渴望升官, 唯有如此才能保护百姓而非仅仅太子一人。 毛顺与徐宾, 共同意识到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与腐败——为了满足唐玄宗的私欲而用去了永州一年赋税去修造精美的玄元巨灯与举办上元节活动等。 他们认为节庆物品越精美就越是废物, 因为那是建立在对百姓的压榨基础之上的, 而且“一文钱, 可以买两个胡饼”, “就可以让一个人多活一天, 让娃娃多活两天”。 何监与李必等人虽然也有百姓情怀, 但终究是偏向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 受传统民本思想的支配。
如果说, 传统的民本思想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 是“君本位”的补充, 是以“民本位”捍卫“君本位”, 其“民贵君轻”的美好愿景终于让位于“君贵民轻”, 那么该剧中的以民为本的百姓观则具有有进步性, 符合现代性价值观。 因而, 这种以百姓为中心的百姓情怀是该剧最为动人的审美价值, 有着独特的文化蕴涵。
该剧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主体精神与自我意识也值得肯定。 所谓主体精神与自我意识, 即是对个体这个主体的确认、 肯定、 尊重与维护, 既包含对自我价值的确认, 也包含对他人价值的尊重, 而且在拥有主体精神与自我意识后, 又能够投身于人生价值的追求之中。 剧中, 张小敬是最具有主体精神的人。 他在人生磨难之中, 逐渐了解了自己并肯定了自己, 也了解了社会与人心, 但他并不像萧规等人那样因为黑暗而感到绝望且走向极端, 而是投身于自己认为对的、 善的与美的事情之中, 尽心尽力地去保护长安百姓的安全。 他的主体精神还在逐渐感化着檀棋等人。 檀棋虽然聪明伶俐, 有能力, 但她始终将自己定位为李必的奴婢, 并不具有自我意识与主体精神。 但正是与张小敬的接触之中, 她才意识到了主体的存在与自由的可贵。 另外, 徐宾、 李必、 程参、 萧规也是极具主体精神的人。 他们既对自我有着成为宰相的期许, 怀揣着“人一生, 总要干一件让自己得意的事”与“守天下百姓”的价值观, 又能在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基础上去努力实现它。 纵然是走向极端的萧规, 也是一个追求人格自由的主体。 但不幸的是, 萧规以及徐宾是缺乏健全人格的, 前者因为绝望与为了绝对的自由而走向复仇与毁灭, 后者因壮志难酬而终为理想献祭。
5 结 语
总之, 不管是在美学追求上, 还是在文化表达上, 作为历史题材的网络剧《长安十二时辰》, 可以说是超越了很多同为历史题材的后宫剧、 历史权谋剧与古装穿越剧, 延续了《琅琊榜》《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等历史题材影视剧对影像审美的精致追求与文化内涵的高度重视, 使其契合了历史氛围, 彰显了精神风貌, 具有了雄浑悲壮的审美风格, 而且融入了忧患意识、 百姓情怀、 主体精神等, 使其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合一, 传统与现代的统一, 具有了丰厚的文化蕴涵。 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发展中国网络文艺、 发扬中国美学、 塑造中国形象与促进中国文艺走向国际的当下语境里, 《长安十二时辰》无疑是一个值得分析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