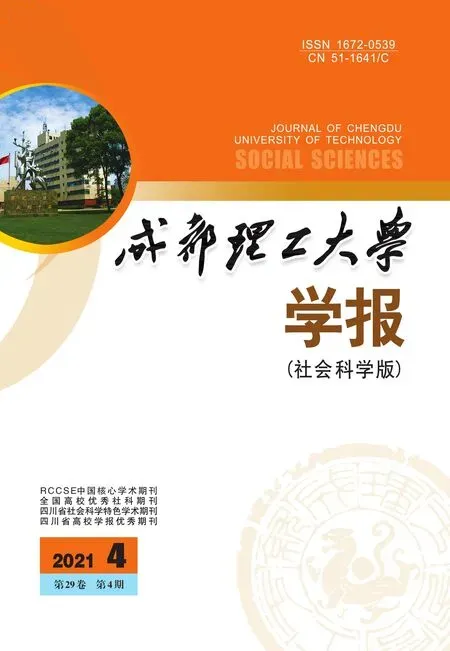加西亚·马尔克斯《迷宫中的将军》的流行病、镜像与现实
张艺莹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的文学作品中,“疾病”是个引人注目的主题。这位哥伦比亚小说家对疾病书写情有独钟,“疾病”意象几乎出现于其各阶段的代表作——无论《百年孤独》,还是《霍乱时期的爱情》《枯枝败叶》《族长的秋天》,均出现各种“病”之身影。
在其凭借《百年孤独》斩获诺贝尔文学奖后的第七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小说《迷宫中的将军》。在《百年孤独》中,作者着眼于家族的兴衰历程。而在《迷宫中的将军》中,其叙事视线由族群转向个体——全书以美洲“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的临终生命历程为主线,描述了其人生最后一年的故事,映射了拉丁美洲的独立进程与作者的晚年哲思,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美洲历史书写的又一体现。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西蒙·玻利瓦尔之眼观照美洲,以被疾病包裹的目光去重新解读这片大陆的流行病与孤独。“疾病”不仅是《迷宫中的将军》的基本色和贯穿主人公玻利瓦尔临终时刻的一系列思维转变与思考,还是作者藉以对拉丁美洲历史与个人获诺奖后对名利与人生全新认知的途径。《迷宫中的将军》中所述之病,可分为两类:一为群体之病,即借由玻利瓦尔行程中沿途所见之美洲大陆瘟疫病况;一为玻利瓦尔的个体之病,展现主人公在“病”之透镜下的所思所感。以“群体之病”的角度看,马尔克斯并非第一次在作品中涉及美洲大陆的瘟疫与“天灾”。他曾坦承,“从俄狄浦斯开始,我一直对瘟疫感兴趣。……瘟疫一直是我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而且是以不同的形式。《恶时辰》中,那些小册子是瘟疫。多少年来我都觉得,哥伦比亚的政治暴力有着与瘟疫相同的形而上学。”[1]162可见,“瘟疫”之于马尔克斯,有肉体(形而下)与精神(形而上)的双重意蕴。在《迷宫中的将军》中,作为传染性疾病意味上的“瘟疫”有多种形式,如天花、狂犬病、淋病。“瘟疫”的每一次出现都对小说叙事有着重要推进。而另一方面,以“个体之病”的角度来打开这部作品,则可发觉玻利瓦尔在其晚年同时罹患身体之病与精神心理之病,即为医学意义上的“心身疾病”。在小说中,美洲的“群体之病”与“将军”的“个体之病”作为两条并行的叙事线,相互分离又彼此缠绕。
一、《迷宫中的将军》的叙事与疾病
探讨《迷宫中的将军》的“疾病叙事”,首先应梳理其“叙事”。小说的主人公为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统帅西蒙·玻利瓦尔。故事从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写起:玻利瓦尔(在国内被排挤后)带领一行亲信沿马格达莱纳河顺流而下,准备离开美洲回到欧洲度过晚年(玻利瓦尔本为血统上的纯正欧洲人)。这场“旅行”的时间自真实历史上的1830年5月起,这时的玻利瓦尔还只有44岁,无论依19世纪还是现今的评判标准都仍在壮年,却已体力衰竭、心力交瘁。由此,作者展示出这位“解放者”的人生终点——辉煌落尽后的孤独与反思。
小说共有八章,结构上可分为两半,各为四章。前半段描写玻利瓦尔的“马格达莱纳河之旅”,此时他带领亲信赶往港口,宣称打算离开美洲。这段旅程的叙事时间为1830年5月8日到23日。而在后半段,玻利瓦尔果然(如同其亲卫军所猜测)并未真的拔营远走,而是找出各种缘由“留守”,在海岸边驻扎六个月,直到其死亡。后半段的叙事时间为1830年5月24日到12月17日。
本部作品具有两条并行的叙事脉络:将军百病缠身的晚年生活以顺叙形式展开;而对于玻利瓦尔所处的19世纪美洲爆发过的几次流行病(军队瘟疫、城市中的天花等)的回忆则通过插叙与闪回方式展现。而进行深入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两条叙事脉络并不是按一定秩序地“你方唱罢我登场”,而是交相错杂、相互掺混。将军之“病”与美洲流行病之间存在极大的应和关系,而在这之下存在的是第三条隐藏叙事脉络——作者的“病”。
二、“病”之大全:美洲之病与将军之病
《迷宫中的将军》中出现过的“疾病”类型,可依据患病之主体分为美洲流行病与将军玻利瓦尔所患疾病。郑理在《论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中的精神疾病意象及其文化意义》中,将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中出现过的“病”分为三类——“流行性疾病:麻风病、天花、霍乱、花柳病(梅毒)、瘟疫等;内科疾病:便秘、肿瘤等;精神疾病:相思病、异食癖、臆想症、焦虑症等”[2]12。若根据这一思路看《迷宫中的将军》,其可以说是一部“病之全书”,这三类疾病在本部作品中均有体现。在这部作品中,既出现了群体之病,也出现了个人之病;既有身体之病,也有精神心理之病;既有流行病,也有非流行性疾病,甚至存在被“讹传”为流行病的非流行病。多种类型的“病”在小说中通过闪回、插叙等方式来回跳跃,构成这部作品中“病的复调”。
首先,作为“群体之病”的美洲流行病,在文中共出现四次,分别为牲畜瘟疫、天花、狂犬病与淋病。
小说中第一次提及的流行病(牲畜瘟疫),是在将军的某次病犯后,向身边的军士说到“又跟圣胡安·德帕亚拉那个晚上一样”[3]38,随即便以插叙形式向读者交代1820年的一段历史。那时,“他已经从西班牙统治下解放了十八个省份,把以前的由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的地区、委内瑞拉特别行政区和基多共和国合并建立了哥伦比亚共和国,自己担任共和国第一任军队总司令”[3]39。看似这是一段美好的记忆,然而,“行军途中,牲口突然传开一场瘟疫,倒毙的马匹在草原上留下一溜十四里长的恶臭的尸体。不少军官灰心丧气,不听指挥,从掳掠中寻求安慰,有的甚至对将军要枪毙违纪军人的威胁加以嘲笑”[3]39。可见,此处提及的这场瘟疫,对于将军当时的战事起到了毁灭性的负面作用。他刚刚建立起共和国本是春风得意之时,却因一场不受控制的动物瘟疫,造成将士离德、军心涣散。而在1830年,当落魄的将军再一次想起近十年前的这段故事,只得悲戚地说一句,这种人心离散“与当年那个晚上一样”。
“瘟疫”第二次出现在小说中,是当将军到达港口城市蒙博克斯。照计划,他应在这里搭船离开美洲。(而这“计划”最后证明只是将军口是心非的幌子,因为他根本连前往欧洲所需的证件都没有准备。)这时,“这个城市遭到战争的破坏,在共和国的混乱中日趋败落,又受到天花流行的再度摧残”[3]88。将军在港口见到不少出天花的人,他们脸上涂满用于治疗的龙胆紫。蒙博克斯(Santa Cruz de Mompox)为哥伦比亚重要城市,拥有悠久历史(建城于1540年),在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世界历史城市名录中占有一席之位。这一城市完整历经了美洲几乎各个重要历史时期——殖民征服时期、独立战争时期、美洲内战时期与现代化时期(现今),它所见证的,自然包含美洲一度泛滥的天花。对于这一大肆蔓延的天花,许多史料将其推给由欧洲殖民者所携带至美洲。然而,对于美洲天花的治疗方式,通常使用的是具有一定致癌性、一般用于生产墨水的碱性染料龙胆紫。即使我们不能以现今的医疗观念评判19世纪的美洲住民医疗方式,但应提及的是,早在1803年(小说叙事时间的近二十年前),便有来自西班牙的传教士医师约瑟·萨瓦尼(Joseph Salvani)等人将当时在欧洲已被证明卓有成效的疫苗带去蒙博克斯[4]1285-1288,但这一疫苗在本部作品中并未提及。将军本打算在蒙博克斯驻扎并寻求军民的支持,而这蔓延的传染病、愚昧与恐慌、挤满了病残患者的城市,又一次使他的计划落空。
小说中所涉及的传染病,除军队中的瘟疫、城市中的天花外,还有狂犬病。当将军一行到达卡塔赫那(这时,他已取得了出国护照,也就是说,又一次声称“马上就要离开了”),却发现城内一片惊慌,原来是“上午有一条得了狂犬病的狗咬伤了几个年龄不等的人,其中有一个不该在那一带晃悠的卡斯蒂利亚白种女人。疯狗还咬了奴隶区几个小孩,终于被人们用石块砸死。死狗给吊在学校门口的树上。蒙蒂利亚吩咐将它火化,不仅为了卫生,还为了防止人们拿它进行非洲巫术。”[3]146此处是将军短暂人生中最后阶段所亲见的美洲图景,即为混乱、愚昧的群体病况。此处,“狂犬病”之病、种族歧视之病、“巫术”愚昧之病混杂晕染出一副丑陋而真实的19世纪美洲的历史景象。持续上演的阴暗环境与美洲悲惨际遇映射在将军眼中,再一次极具讽刺意味地与他的失势落寞相呼应。
小说第四次出现流行病,是在将军听闻自己的老部下苏克雷死于内斗、掌权的桑坦德又推倒了他从前的政令时(这时他仍在卡塔赫那,“将军说他想去欧洲”,但身边人“都看不出将军真有动身的打算”[3]166),军中开始蔓延淋病。“起因是在翁达期间有两个女人每天晚上来驻地鬼混,以后士兵们路过每个地方都寻欢作乐,继续传播。最后没有一个士兵没被染上,正规医师和江湖郎中都束手无策。”[3]166-167而“淋病”这一问题,一直持续到小说结尾,也即玻利瓦尔的死亡。玻利瓦尔的军队无疑是其继续流连美洲的精神支撑,它的存在代表着玻利瓦尔生的希望、重回国内的希望。然而,随着淋病在军中的蔓延,“全城已经知道他们面临的威胁,共和国的光荣军队被看成是传播瘟疫的使者”[3]207。拉丁美洲伟大解放者最大、最后的问题,竟是并不光彩的、令人难以启齿的“淋病”。由此我们发现,在将军人生中的各个关键阶段,都出现了这种“诅咒般”的、使他的伟业功亏一篑的流行病。无法抗拒的命运,构成将军悲剧人生的内核。
在小说的“历史叙事”上,马尔克斯的社会责任感体现为一定的真实性抒写。他从不回避美洲历史的丑陋场景,正如其所说,“我经过长时间的思考,终于懂得了,我的职责不仅仅是反映我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而是要反映本大陆乃至全世界的现实,决不忽略或轻视任何一个方面。”[5]82与玻利瓦尔时期的拉美现实对照,种种“瘟疫”并非杜撰、确有其事,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迷宫中的将军》一作具有写实性与历史真实性。然而,这并不能代表读者可将这部作品全然视为一本“历史纪实类”的读本。因为,从对主人公玻利瓦尔的描写中,我们会察觉出这部作品“真实中的谎言”。若说群体流行病的蔓延在全篇叙事中作为玻利瓦尔潦倒晚年的起因与底色而存在,那么叙事主线上的玻利瓦尔的健康状况则是另一种更加复杂的景象,因为与“群体病”的瘟疫等仅作用于身体的病症相比,将军所经受的“病”不仅在其身体,还在其精神。
将军的身体之病,在小说中似乎较为明确,即“根据病人颈项无力、胸部下陷和脸色枯黄的症状,判断主要原因是肺部损害”[3]215“根据皮肤颜色和晚上发烧,认为是慢性疟疾”[3]217。此外,玻利瓦尔还“患有严重的便秘症,以致面黄肌瘦,高烧不退”。而此时的主人公除去随行医师为其诊断的身体疾病外,还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小说中仅是直言将军经受“谵妄”(小说中主要表现为精神错乱)便有五次,时间上贯穿作品始终。这种病症的出现本就具有讽刺意味,因“谵妄”“常见于老年人”、又被称为“老年期大脑功能不全综合征”[6]263-265,而这对于尚仅有四十四岁的玻利瓦尔,显然来得过早。“谵妄”的主要病征为意识障碍、认知功能障碍等,在小说中则表现为将军最后半年人生的日夜颠倒、情绪波动、幻觉、神情恍惚、冲动行为。一方面,他的确为其所苦;另一方面,这种精神疾病也一定程度上使其没有快速死去(“人们都不明白像他这样瘦得皮包骨头的人怎么还能活着”[3]63)。小说中玻利瓦尔的身体情况经常剧烈地忽好忽坏,而若只考虑生理原因,这种情况并不符合常理,因此有足够的理由推测在其间的心理作用,即使此种“心理作用”脱胎于某种精神疾病。而与此同时,另一明显的故事情节即为军士与医师们出于对玻利瓦尔的恐惧敬畏或心理治疗意识缺乏(毕竟,小说的背景是医疗理念尚不完善的19世纪)。对这一问题,在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对于将军的心身疾病,医师们无一能够起到作用。正如同他们也未能为军队中的瘟疫帮助(如上文所提及的表达,“束手无策”[3]167),当随军医师试图治疗玻利瓦尔,开出的“药方”却只是具有安抚作用的“一大杯葡萄酒、一杯西米露”[3]188。文中医师所使用的治疗理念,仍局限于“自然疗法”手段下将养躯体的方式,而对于将军精神疾病似乎未能进行正式治疗。这又构成了将军晚年“孤独”的另一侧面——其人其病都被置于了“漠视”的角落。另外,若我们将小说中的群体性流行病“拉美之病”与将军的个体身心疾病相联结而重新审视整体的叙事结构,便会得出一个全新发现,即叙事的闪回跳跃恰巧是将军所患精神症(“谵妄”)的体现——他的意识处于一种不受身体主观意愿控制的情况下随时随地跳跃。这并不是主人公在健康情况下的“意识流”活动,而是一种模拟精神病患意识活动的叙事行为。如同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班吉”部分的叙事方式,患有精神疾病的主人公的意识呈现出无理性的特征,因而其记忆(内心独白)常毫无征兆地发生时空跳跃。《迷宫中的将军》中玻利瓦尔故事的叙事时间跳跃中也存在这一“疾病”因素。若我们将主人公“意识流动”之中的另一元素——“睡眠”提取出来,将这两个行为(“记忆闪回”与“睡眠”)并置审视,则会发现另一现象,即对过去的密集回忆常发生于一段突如其来的长睡眠之前。这便又一次侧面证明了玻利瓦尔精神疾病的确有其事。不受控制的精神错乱带来的意识流动耗费了他的体力后使他陷入用于自体精神修复的睡眠,而当他醒来后,又重新进行这一“现实—回忆过去—睡眠”的心理疾病循环。
小说构建出身体病/心理病的二元叙事结构,而这又是另一有趣现象。以病理学角度看,存在随社会历史发展而产生的“文明病”/“传统病”二元对立关系。即在20世纪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通常是感染性疾病;而在20世纪以后,人类的“天敌”变为心脑血管疾病、肿瘤、意外事故、心身疾病等所谓“文明病”(随文明发展水平提升而产生的“病”)[7]3。这两种类型的病症通常集中出现于不同的时代,而在本部作品中,它们交替出现、交相辉映,使得叙事逻辑中的“现在”与“过去”相互掺杂。这又同时暗合了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美学的重要元素之一,即“魔幻时间”——“不同于物理时间,又有别于心理时间,是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流派特有的时间观”[8]59。由此,玻利瓦尔之“魔幻”与拉美大陆之“魔幻”通过“病”这一内核形成连通器,赋予了作品更深层的意义。
在故事的后部,玻利瓦尔本不具有传染性的疾病(无论是身体的还是精神上的)在拉美人民眼中竟成为了一种可怕的“传染源”——“有个桨手莫名其妙地说起坎比略家把英国餐具、波西米亚的玻璃杯和荷兰的桌布埋在院子地下了,怕的是传染痨病。”[3]109“痨病”,即肺结核病,确实具有传染性。然而,玻利瓦尔真的患有这一疾病吗?从文中可得知,没有医师为他下过“痨病”这一诊断,而肺结核病所具有的症状(如咳血、胸痛)也并未发生在玻利瓦尔身上。然而,当谣言这样传播、众人这样相信时,似乎事实真相就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街头巷尾都说将军害的是痨病,马格达莱纳河一带已经人人皆知”[3]109。这又构成了另一种讽刺,即拉丁美洲历史中的“瘟疫”终于“传染”了它的“解放者”,而这“瘟疫”,也不只是生理疾病意义上的“瘟疫”——它更是一种在民众之间大肆蔓延的愚昧、绝望、叛离的“瘟疫”。最终,将军也默认了这种“疾病”的悲哀,对军士下令,“对他们(下属及民众)说,我害的是痨病,叫他们以后别来。”[3]186这种强加的“非病之病”又在新的层面上印证了主人公晚年的凄凉。至此,玻利瓦尔的健康与战争都遭遇了一种彻头彻尾的、莫名其妙的、厄运般的惨败。从前获得的成功与荣誉都在一夕间崩塌、回到原点。马尔克斯完成了他“小说家的诅咒”——“拉丁美洲的历史是一场巨大然而徒劳的奋斗的总结,是一幕幕事先注定要被人遗忘的戏剧的总和”[5]105。
三、“病”与“非病”:“将军”与马尔克斯的“对镜自照”
对于《迷宫中的将军》的作品分类是读者应辨明的问题。这部作品确实具有一定的写实性,例如文中的人物、地名、时间脉络都与真实历史相切合。但同时,其中的虚构成分也是不应被“正史化”的,它归根结底仍是一部“重构性”的文本、是作者依靠想象“黏合”而成的“历史”。史料记载中对于玻利瓦尔的晚年相对匮乏,这种匮乏给了文学作者以想象空间。而在谈及《迷宫中的将军》的创作由来时,作者在小说的“致谢”部分讲述了他的创作初衷:“多年前,我听阿尔瓦罗·穆蒂斯谈起他打算写一本有关西蒙·玻利瓦尔最后一次沿马格达莱纳河旅行的书”“但是两年后,我得到的印象是这个计划已经搁置,……那时我才斗胆请他允许由我来写。”[3]235
阿尔瓦罗·穆蒂斯(Alvaro Mutis)为哥伦比亚著名诗人、小说家,也即马尔克斯的同胞、同事与多年好友。马尔克斯所提及的“穆蒂斯的书”正是其所创作的《最后的面孔》。这部“书”不足万字(事实上,仅有五千余字),且仅描写了1830年6月29日、6月30日、7月1日三天的几个片段——与其说是“短篇”,似乎更是“残篇”。因此,对于好友对这一创作主题的尝试,马尔克斯没有说谎,它的确是“已经搁置”。而在主观层面上,马尔克斯这样说:“除了人物的光荣事迹之外,我更感兴趣的是马格达莱纳河,我自幼就熟悉那条河流。”[3]235
这种说法乍看之下似乎合情合理,但若我们按图索骥,却会发现另一现象。马尔克斯说因自己对玛格达莱纳河的了解而写这部作品,而实质上书中基本没有出现对这条河的景物描写。在小说中,每次提及这一地名,马尔克斯常将其作为“背景”而匆匆带过。例如,“在马格达莱纳河航行期间”“马格达莱纳河上最好的水手”“通向马格达莱纳河的皇家港”……仅此而已,对河上河畔的景貌再无多言。马尔克斯对“马格达莱纳河”意象的“偏爱”显得刻意而表面,这很难不使读者对其“写作初衷”产生怀疑。若是这样,马尔克斯为何“说谎”?或说,他为什么要对“写作初衷”这一话题进行遮掩?或者说,这一“致谢”中的“剖白”是否也是小说虚构的一部分?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马尔克斯的“谎言”(或者说“不甚真诚”)的原因在于,这部作品中存在一种暗含的自传性、一种蠢蠢欲动的“自我意识”。而小说自传性叙事的标志之一,即为全文数次出现的意象——番石榴。
比起“马格达莱纳河”,小说中对“番石榴”符号明显更为偏好。书中数次出现对于“番石榴”的细致描写,如“将军一进门就背靠着墙,对窗台上葫芦瓢里盛放的番石榴弥漫整个卧室的香气感到意外”[3]92、“他坐在吊床上,把盛番石榴的葫芦瓢放在两腿中间,一个接一个把番石榴统统吃光,几乎没有换气的时间”[3]95、“当时他还经受得起番石榴的气味和黑暗中女人的无情”[3]158。整部作品,“番石榴”意象出现十余次,每次的描写均生动有趣、细致入微。然而,“番石榴”作为一种标志性意象,却并不属于历史中的玻利瓦尔,而隶属于马尔克斯本人。他把它与自己的童年相连——“回首逝去的美好年代有关:那番石榴的芬芳、充满香气的回忆”[9]308。“番石榴”于马尔克斯而言,是他记忆中的“美洲味道”,也是他始终抱有的精神支撑。在20世纪60年代,马尔克斯在巴塞罗那居住一段时间后,便迫不及待地回到哥伦比亚。当地的新闻记者问他为何匆忙回去,马尔克斯的回答不免有些稚气:“是试图记住番石榴的气味。”[10]305现有史料并不能为我们指明玻利瓦尔是否也享有这份“番石榴倾向”,然而,似乎可以这样推测,如果以现今的资料连通性都不能得出玻利瓦尔与番石榴之间关系,那么于20世纪查阅玻利瓦尔资料的马尔克斯想来应更没有条件确立玻利瓦尔的“番石榴性”。因此,有理由得出结论,通过“番石榴”这一意象,马尔克斯将一部分自我与小说中的玻利瓦尔所混合。由此,小说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传性。
如果仅通过“番石榴”这一意象仍不能证出《迷宫中的将军》的自传性,那么我们仍有另一可供猜测的“证据”——玻利瓦尔与创作这部作品时的马尔克斯共享同一种心境,即“迷宫心境”。
前文已提及,本部作品生产于马尔克斯获诺奖后,是《百年孤独》的下一部作品。但这时的马尔克斯,对于荣誉与名气感受到的不是享受,却是巨大的压力。一方面,荣誉在为他带来(各种形式的)收获的同时带来了困扰,时间的挤压使得“现在一天能写完一大段落就算万幸了,写作变成一件苦差事”[5]31。另一方面,他却不再能够像在从前的作品中那样,将自身的感受直抒胸臆,因为“责任心越来越强了,现在我决定,每写一个字幕,都会引起更大的反响,会对更多的人产生影响”[5]31。由此,原本“自由写作”的马尔克斯在获诺奖后反而变得“畏首畏尾”,体现之一便在于其“疾病书写”叙事方式的转变。先前的作品中,对于“疾病”的种类常直言不讳,如《枯枝败叶》中医生的异食癖、《家长的没落》中“家长”的焦虑症,无论身体疾病还是心理疾病,马尔克斯均给出了明确“诊断”。而在《迷宫中的将军》中,“疾病”开始戴上了“面纱”,马尔克斯开始“顾左右而言他”。主人公的“病种”变成了一个需要读者与作者(甚至是与主人公本人)去合力“解构”的“谜”。与马尔克斯这段时期的人生经历相联系,这种叙事手法上的转变很难不被归结为一种名利之下的“异化”。此时的“异化”并不指贬义层面,而是马尔克斯在心理上有了“诺奖获得者”的精神负担。这时的马尔克斯,尚不能平和对待“诺奖”的光环,他走上了这个巅峰,却怕自己走不好,也怕自己从此要走下坡路。然而,马尔克斯十分明白,“走下坡路”总是会开始的,“光环”早晚会消退,而问题在于——“我不想跟任何人争名利。……但是一旦登了上来,下一步怎么办呢?要下去,或者争取明智地、尽量体面地下去。”[5]31
“体面”是个关键词,因为在《迷宫中的将军》中,主人公并非“体面地下去”,而是如其所言“在穷困潦倒中赤条条地死去”[5]129。此处,作者与他的主人公形成了一种对立关系。或说,他在借助自己笔下主人公的故事抒发一种成名后的恐惧,即“这个高峰我走上后,该如何下来?”“要怎样走出这迷宫?”对于这些问题,很明显的是,作者心中并没有答案。因而在这部作品中,马尔克斯采用了可以说是一种启蒙主义者的笔法,借人物之口提出自己的疑问,“逼迫”读者与他一道思考、寻求解答。马尔克斯自身情感的被迫“内倾”在《迷宫中的将军》中表现为主人公玻利瓦尔的“外倾”——怒吼、暴躁、疑惑、痛哭,这些被作者压抑的情绪由他的主人公进行宣泄。
马尔克斯会在这个人生阶段想起玻利瓦尔,或许正如其所说,“权力的孤独和作家的孤独十分相似”[10]305。有趣的是,作者在青年时期便有着对玻利瓦尔的认同,不过是在另一方面——当年少的马尔克斯在校时拼字成绩不好,便安慰自己,“听说伟大的玻利瓦尔(和他一样)拼字也很差”[9]53。这似乎是种巧合,无论青年马尔克斯还是老年的他,看待玻利瓦尔形象的侧重点都并不在其功绩,而在其性格或能力上的错陋缺陷。马尔克斯在“玻利瓦尔问题”上并未曾体现出英雄主义的“偶像包袱”,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他能够做到以戏谑嘲讽的“反英雄”手法对其进行描绘、为何他敢于将自身困顿折射于玻利瓦尔。也许正是因为,这一伟大人物在他的概念中,不过是个与他自己一样有着弱点和“精神迷宫”的普通人。由此,作者将困顿、迷茫的晚年玻利瓦尔形象染上了自身之色彩,而文中多次大段抒发的情绪,不仅出于这位“解放者”,而同样出自困于鲜花与荣誉而自觉难以为继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马尔克斯在玻利瓦尔的故事中找到了情感共鸣,而整个叙事也至此达成了形式与内容的回扣。一方面,在玻利瓦尔的叙事圈层中,全美的流行病与自己的身心疾病交替上演,全篇罩满阴云。另一方面,以“番石榴”等元素为突破口,读者得以拨开这层“病”的迷雾看见玻利瓦尔故事中的“自我性”。
四、结语
作为一部历史小说,《迷宫中的将军》一度受到美洲主流媒体的排斥,因其对玻利瓦尔狼狈潦倒晚年的描写实在过于“非常规”。“将军”玻利瓦尔因其建立统一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设想,常被视为拉美独立的化身,而马尔克斯却非要将这一伟大解放者“拉下神坛”。《迷宫中的将军》在美洲的“玻利瓦尔资料”中,无疑是一部“反英雄”叙事作品。它绕过了常被再创作的玻利瓦尔功绩与遗产,而着重描绘这位伟人的“病与残”。“作者似乎要在众多的溢美之词中寻找一些黑暗的裂痕,从而把神圣的‘解放者’从一个个神话中解放出来。”[11]230因此,他着力于表现主人公的悲惨、孤独、痛苦,以此使人物“回归”丑陋与真实。这个“解放者”与先前任何文本中的西蒙·玻利瓦尔都不同,他似乎是个全新的人物:他有洁癖,他疑神疑鬼、多愁善感,他还幽默风趣、时常与身边人开玩笑或讲笑话,他胃口大得惊人,他喜睡吊床……诸如此类,种种细节描写使人物的塑造更加丰盈,跃然纸上。然而,饶是《迷宫中的将军》在历史书写与小说叙事上都有其独特价值,它在马尔克斯作品中的相对“冷待”也是确实的。“小说在墨西哥、哥伦比亚、阿根廷和西班牙等国同时发行,初版只有几十万册,而且反应大大逊色于以前的作品。明证之一是它的第一次印刷几乎是在两年后才售罄的。”[11]233而马尔克斯的担忧与焦虑也成为了现实。荣获诺奖成为他创作生涯的转折点,只不过这一“转折”,不是向上,而是向下。“从此以后,加西亚·马尔克斯似乎不再享有每出一本书都好评如潮的特权。”[11]233
马尔克斯向来不讳言“家长之病”——上校“没人写信”,族长“遭受秋天”,格兰德大妈“出场即为葬礼”……而这次,轮到了“将军”。但同时也可以说,对于大篇幅地细致抒写“家长”精神状况的尝试,到《迷宫中的将军》时才正式出现。而马尔克斯在其“疾病书写”系统中,终于由祖国之病、祖先之病、家长之病、统治者之病写到了自己之病。在小说叙事中,除去对拉美革命时期爆发的大规模流行病描写与作为故事主人公(而不是作为非虚构性历史人物)的玻利瓦尔的身体与心理疾病描写,另一引人深思的现象便是叙事中医疗措施描写的缺失。对于这一“疗愈缺失”现象,我们或可推测为是出于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不通医护知识、为免出错因此不做赘述,但或许也可作另一猜测,即认为这是作者的刻意留白。在此,马尔克斯提出了一个问题——应怎样治疗玻利瓦尔?这不仅是向读者所提出的问题,也是作者向与囚于自身荣誉与骄傲的晚年玻利瓦尔身处相似处境的自己所提的问题。
当被问到“(自己的著作里)你最满意的是哪类书”,马尔克斯言简意赅,“描写孤独的书”[5]77。 “孤独”在人类情感中,是个宽泛的概念。无论疾病,还是荣誉、败落,都会带来各种形式的孤独。而人类该如何“疗愈”这些孤独,便是作者提出的问题。“拉丁美洲的孤独”是美洲文学的一个经典主题、也是马尔克斯几乎于每部作品都会涉及的问题,在《迷宫中的将军》中,这一“孤独”落在了“疾病”。美洲的瘟疫与玻利瓦尔的心身疾病、马尔克斯的焦虑症状共同构成这一孤独的历史与现实。那么,“怎么才能走出迷宫?”对此,马尔克斯早有预言:“孤独的反义是团结。”[5]109来自“疾病”的“孤独”或许暂时不会被消灭,但它永远可被对抗、被挑战。欲走出“迷宫”,委顿原地无济于事,唯有团结或可觅得出路。至于应如何“团结”,作者在文中并未给出具体方式,但我们或许能从马尔克斯的“诗学”中窥见一二。在《百年孤独》中,作者说道:“面对压迫、掠夺和孤单,我们的回答是生活。无论是洪水还是瘟疫,无论是饥饿还是社会政治动荡,甚至多少世纪以来永无休止的战争,都没有减弱生命压过死亡的顽强势头。”[12]25川流不息、不为困境所阻的生命,是玻利瓦尔所未能做到的、马尔克斯极力拥有的,也或许就是“孤独”与“团结”问题的“应许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