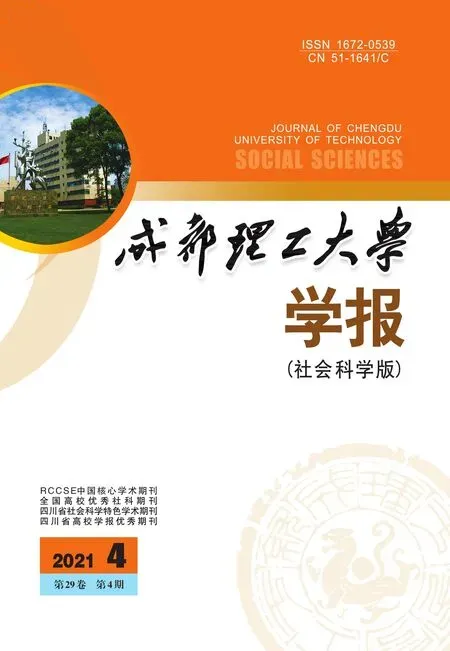儒道西学
——许缵曾思想与治学
吴思增
(华东理工大学 人文科学研究院,上海 200237)
对于明清之际西学输入背景下较早接触西方文化的江南士大夫来说,所受到的冲击无疑是巨大和复杂的,其精神价值的探索之路也必然曲折。在明末清初西学东渐思潮中,许缵曾是重要人物之一,他出身于云间名门望族、天主教世家,官至河南提刑按察使(正三品),后因“康熙历狱”被罢官,重被起用后远赴滇中点用云南按察使司,然不久辞官返里,于四十六岁之时仕宦生涯画上句号。学界对他的研究虽有一定的积累(1),但仍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故本文以许缵曾诗文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其思想构成及治学风格,以观传统文化、西学交织背景下清初部分文人的精神世界及西学对其思想和创作的具体影响。
一、温饱非吾素——个性与事功
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儒学是士大夫安身立命之学,许缵曾亦然。其曾祖许乐善官至通政使,外曾祖徐光启身居宰辅。修德勤读、光耀门楣、传承仕宦名门的家风是许缵曾一生的愿望。直到晚年,许缵曾还做《子夜闻幼儿读书声志喜》云:“寒窓闻夜读,静里一开颜。八代簪缨旧,三余岁月闲。雏莺新学哢,老鹤倦飞还。努力勤修德,春风到远山。”[1]卷二478诗文叙述了累世诗礼簪缨的辉煌,表达了对幼子的期望和勉励。
许缵曾生于明天启七年(1627年),十五岁参加童子试得中生员。他天资聪慧又得名师指点,学业进益很快。顺治五年(1648年),二十二岁的许缵曾中举人,同年冬上京师行卷于王崇简之门,第二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作五言古诗《登瀛州亭言志》“温饱非吾素,岁华徒推迁”表达了建功立业的远大志向,欲驰骋纵横,览名山大川,不愿意在安逸的环境里白白损耗大好年华,“慷慨因起舞,庭月恒娟娟”,意气慷慨,体现了仕途顺遂、乐观积极的精神面貌。
许缵曾为人豪爽,有胆有谋。顺治八年(1651年),二十五岁的许缵曾授翰林院检讨,同年,父亲许远度病重,缵曾回乡探视。中途路过宿州,应宿州长官的邀请休憩一日以观田猎。下午,恰遇响马过街,许缵曾率仆从七人挟弓箭与强盗对峙街市,面对凶悍惯战的强盗,他毫不畏惧沉着应对,在他的指挥下,数十骑响马被擒,可见他并非简单的文弱书生,有英雄侠士的风采。
许缵曾为官能力强,能于复杂局面中应付多方事宜,游刃有余。王崇简之子王熙与其年龄相仿又“同官词林”,为许缵曾《宝纶堂稿》作序记其为官经历:
暨出任方岳陟外台,明刑两河,兼访六诏,屡决大疑,剖大狱,皆经生学士,所欲一见诸施行而不可得者,公恢恢乎游刃遇之。[1]卷一424
由于出色的工作能力,许缵曾升迁顺遂:顺治十四年(1657年),升右春坊、右中允,随驾南郊,接受皇上的赐宴、赐茶;顺治十五年(1658年),升补江西驿传道副使;十七年(1660年),升四川布政使司分守上下川东道参政;顺治十八年(1661年),许缵曾三十五岁,于四月抵重庆,七月间随总督征万州贼寇,后取大昌、大宁、云阳等邑,作《辛丑秋七月从蜀督李少保进勦夔东》(十首)军旅诗,再现了他英姿侠气、朝气蓬勃的青壮年时代,如其八:“天生桥上登临处,蜀国青山楚国云。丙穴风烟应尽扫,语朝先遣大将军。”[1]卷四534蜀山以雄峻挺拔闻名,自然风光壮观秀美,“风烟尽扫”表达了诗人不怕困难、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青”是风景的真实色彩,同时也是心情和精神状态的体现。平乱之后,许缵曾被派赴保宁总理蜀藩政事,他勤奋廉洁,剿抚三家巨寇,料理云南十万移民,又奉命丈量田亩,案牍细末皆出于缵曾之手。
康熙三年(1664年),许缵曾授河南提刑按察使,《鹤沙自序》中讲述了自己刚到任时,面对积攒了多年的难治命案、盗案条分缕析,“以民命为重”,三个月之内“推敲平反,竭耳目之劳,穷日夜之力,开释极刑并大辟重囚一百四十余人,信心而行,竟无驳语取尤者。”[1]卷四571因政绩卓著赢得了地方官员和百姓的信赖。第二年(1665年)夏五月督修汴梁城墙,同年七月,黑堽河涨水决堤,在官民惊慌失措的情况下,许缵曾“烈日浊雨,匹马巡行”,不顾辛劳兼理督办抢堵黑堽河,以保汴梁城。
二、三十年之我非我:许缵曾思想探究
起自晚明的西学东渐思潮带来了科学技术、知识结构的发展和变化,形成了对思想界的冲击。云间在四百年间西学输入中国的过程中承担了桥梁和中坚作用。以明清之际而言,表现在天主教信仰的传入、兴盛,云间成为明清之际中国天主教最发达之所;天主教徒之间、亲西学的云间士人间交往频繁,并自觉形成了接纳西学与实学的观念:西方科技顺应明末实学救世的思潮被广泛传播和利用,融入云间社团“经世”的理念和实践当中。
作为清初思想变革时期的亲历者,云间天主教徒在认识西方、反观自身中,探寻彼此的会通,以耶补儒、儒耶调和,致力于儒学与西学之间的调和会通,目前学界的研究文献多来源于思想家著疏;本文侧重于许缵曾的经历实践和文学创作,则可见在西学与儒学传统交织背景之下,天主教文人对道家思想文化的偏倚,呈现出思想行为的复杂性。
(一)天主教渊源
许缵曾生于天主教世家,自幼受洗,受笃信天主教的母亲影响至深。母亲教名甘第大,是徐光启次孙女,柏应理《一位奉教太太——许母徐太夫人传略》中记载了她广建教堂、致书耶稣会会长请神父之事[2]40。许缵曾一生十分孝顺母亲,高士奇《宝纶堂稿序》中说他“天性最孝”[1]卷一425。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自主意识越来越强,天主教信仰对许缵曾思想和行为的约束减弱,正如黄一农、刘耘华先生所论,他在十七岁离开外家后便不再供奉天主教,授官后不久即蓄妾供神,信仰并不坚定。
然而,许缵曾成年之后外任江西、湖北时都曾经开设教区,传扬天主教,究其原因主要是为了行善尽孝,建天主教堂很大程度上迎合了母亲虔诚信教之意:“其母甘第大随子赴任,所在帮助神父建堂开教,大为神父所仰赖。于是江西之南昌府,湖广之武昌府,均有其所建之堂。”[3]265陈垣先生也在《华亭许缵曾传》中说在甘第大的督促和影响下“四年之间,教众至两千百人”[4]127。
正当许缵曾大展宏图之际,遭遇了人生重大挫折。康熙四年(1665年),杨光先发起教案,斥汤若望西洋新历法十谬,顾命大臣鳌拜不满外邦人参议朝政,支持杨光先,汤若望及杜如预、杨宏量、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有泰等钦天监官员(天文学家)被判处斩。后因天空出现彗星,京城又发生地震,改判汤若望、杜如预、杨宏量免死,李祖白等五人依然被斩,史称康熙历狱,又称汤若望案。许缵曾与佟国器、许青屿三人因信奉天主教、捐献银两、为天主教之书作序等原因被革职罢官。
个人在巨大的时代政治洪流之中,人生际遇往往瞬间改变。时人多为他鸣不平,而许缵曾则表现出超然一面,康熙四年(1665年)至八年(1669年),他先是“与诸老流连匝月”,然后“扁舟归里,闭门静休”,陪伴母亲,“不与尘世争黑白”。康熙八年(1669年),汤若望案平反,康熙帝陆续将之前京察无故被革职处分的满汉官员给还原官,许缵曾也奉特旨以原官起用。然而,此时的许缵曾已无仕宦之心,虽然在母亲劝说下赴京补任,点用云南按察使司。但到任之后,他写下《滇中寄友》三首表达了故土难离之情:“南海名香特地贻,河桥折柳不胜悲。云山浩渺天垂尽,珍重明珰忆别离。”[1]卷四537并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四月陈情侍养,对于他的辞官,友人多表达了惋惜之情,比如王熙说他“有用世之才,而不尽用于世也”[1]卷一425。但许缵曾却安然地享受起读书的乐趣,埋头于学问,他在《鹤沙自序》中说自己“因仕废学,年五十始知读书”[1]卷四568。可见他豁达的个性,能够做到随遇而安,在任则事必躬亲,勉力而为;在野则安恬养志。正如王熙所评其“旷怀高蹈”“任意”“自然”,在不尽用于世的境遇下“忘情于世”,享“园林丘壑之趣”[1]卷一424。
回乡后,许缵曾常怀恻隐之心,行善于乡里,王熙《宝纶堂序》中说:“公生平闻一善言,惟恐不传,行一善事,惟恐不力,盖其志无日不以济人利物为心。”这种一生行善的理念,盖受其家庭和天主教信仰的影响。其在《鹤沙自序》中记载了父母的施粥善举:“会嵗梫流离载道,父弃产易米,设粥以食饥者,四境之内,存活甚众。”[1]卷四568在许缵曾所有善举之中最突出的是建“育婴所”。他不遗余力地助捐资、筹善款,自康熙十四年(1675年)至三十五年(1696年)二十二年间,共收救弃婴5480名,而且“育婴所”也成为许缵曾后半生的“事业”和牵挂。
康熙十九年(1680年)许母辞世,许缵曾决计不仕,追思其母“好生之志,兢兢罔敢懈弛,乃迁育婴所于莱园之东北隅,朝夕将事,以为晨昏定课”。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六十六岁的许缵曾得重疾,第二年(1693年)春,他将田房等家产分给子侄共十五人,随后一边料理育婴所,一边偶邀“同里诸子,恬澹莫逆者,觞詠于莱园”[1]卷四575。“莱园”建于松江府城西门外,是许缵曾晚年所居别业,相传此园为明末清初造园名家张南垣所建,花木葱茏,池馆幽深,中有后乐堂、水镜山房等。
然而,许家家境败落、盛况不再是不争的事实。延经苹《清初天主教文人许缵曾研究》中分析了许家败落的主要原因:由子孙后裔的不肖造成,尤其是缵曾独子许垐不善经营管理,挥霍无度,四十万家产至许垐暮年荡然无存[5]16。许缵曾晚年深受贫病之苦,甚至连治病都无法保证,更谈不上娱情。在《岁寒杂感》诗中,他做了“伤贫不能济友”“伤贫不能育婴”“伤贫不能养病”“伤贫不能娱老”“伤贫不能自遣”等八首“伤贫诗”。如第二首诗中,他为“育婴堂”事业因资金问题陷入窘境而心生愧疚:
育婴胜事道缘深,远近贤豪惠好音。……几年借著逢胠箧,千指啼叽遇绿林。满地呱呱相望泣,欣逢季布一开襟。[1]卷三517
育婴堂因遭遇盗窃而雪上加霜陷入停滞,又因朋友的慷慨解囊而得以维持,所以许缵曾“喜有同志”(注中语),作诗以纪之。在第五首中,他说起家贫造成的种种不便和忧愁:“极目遥天起百忧,寒林漠漠强登楼。花晨丝竹贫难买,社日羔豚愧未周。三泖胜游空有愿,连城古玩苦无酬。柴门剧啄多劳攘,拟泛沧波不自由。”[1]卷三517不仅丝竹古玩这种清雅兴趣难以为继,而且连古代祭祀土神的日子“社日”、民众集会竞技欢宴的时刻,也因无财而不能尽兴娱乐,稻梁肥硕、猪肥鸡壮、丰收在望的祭社聚宴距离许缵曾十分的遥远,所以许缵曾发出了“拟泛沧波不自由”的感慨。第六首诗中,许缵曾用了两个典故:司马相如典裘沽酒、陶渊明温饱难持借以描述自己的窘状:“急雨凄风短景催,中宵不寐起徘徊。相如四壁裘常典,陶令三冬柳渐摧。……富家长鬣矜高会,独有幽人未举杯。”[1]卷三517许缵曾状生计之穷也是诉命运之穷,是个人和家庭危机造成的失意落寞,诗末的“幽人”既是幽居之人,也有品性高洁的意思。
(二)醉心道教
儒、释、道等传统文化资源中,许缵曾对道教及道家思想具有浓厚的兴趣。青壮年时期他就对道教炼丹养生之术颇为好奇:“四十岁以前,梦寐中每见仙山楼阁,主者呼之为玉局中人。”[1]卷一426玉局是道观名,在四川成都。传说李老君曾于此升玉局高座,广宣要法,普济众生。许缵曾在梦中被称为道门中人,可见他兴趣所在。
顺治六年己丑(1649年),许缵曾与钻研道教养生法的高人邓元固相识,二人同榜进士。许缵曾在为道教书籍《金丹节要》写的序文中叙述了二人渊源。十余年后,缵曾赴京就补,邓元固为郎官,二人在京又见。年近六旬的邓元固“神采焕发,须眉如故,且闻其房中执巾栉者,不下二十人”,令许缵曾惊叹不已,得知其与道人的奇遇,且依照道教养生修炼方法“至今无疾痛疴痒,身无疾病然后可求长生”后,许缵曾心向往之,并从邓元固处得到《金丹妙旨》一书,“抄录其书,五日始竟,披览梗概”。但是,许缵曾并没有等到邓元固传授口诀便匆匆赶赴云南按察使任上了,直到他告养归里才真正有时间钻研此部道教经典,由于缺少了“口耳相授”这一最重要的秘密环节,许缵曾无法参透其中奥妙:“慱涉丹书一切三元之学,仅窥栏楯。未得要领。”他为自己错过面授机宜的机会而惋惜:“余胸中眼中但知有清净,而不知有所谓金丹者,明师在前,当面错过,诚可惜矣。”[1]卷五554
除此之外,许缵曾在三十岁时还辑汇了一本道教劝善书籍《太上感应篇图说》。《太上感应篇》的作者是宋代的李昌龄,该书在民间流传甚广,为其增订、注释者层出不穷。然而,用图画的方式来阐发文义始自许缵曾所撰《太上感应篇图说》。李昌龄原书篇幅本不长,仅一千两百余字,但《图说》共八册,不分卷,以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为序,书中有图五百余幅,为清初画家华亭人李藩所绘,木刻名家鲍承勋所刻,其构图繁复,刻画精工,成为清初木刻画的典范之作。这部书始编于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历时三年刊成,可见许缵曾的编纂决心和所下工夫。之所以耗费如此心力汇辑此书,是重在宣扬此书的道德教化作用,通过因果报应之说劝人遵守规范,止恶修善,也因为符合“勉力为善”的宗旨,所以笃信天主教的母亲并未反对儿子的行为,只是让他删除其中涉及佛、道的内容,才准许出版刊行,在《鹤沙自序》中,许缵曾提到了此事:
余母见之,犹以其旁涉二氏,非吾儒本旨,尚湏删削改正,乃可行世。至今生计日疏,无力删刻也。[1]卷四572
母亲的删改要求许缵曾并未真正执行,从他一贯的行事作为来看,既坚持自己的个性主张,又生性至孝,故推知其所辑道教书籍与笃信天主教的母亲意愿相违背,必不忍直接忤逆,而会采取迂回策略、选择有所不为的可能性较大。从这段叙述也可知当时民间社会对于天主教、儒学的看法与知识阶层无异,即寻找二者的相似点互相调和,但天主教与释、道之间则界限分明。
许缵曾亲善道教友人至晚年未变。他为多位道门中人或好道之人写序。如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其六十二岁时,朋友马愚菴分别于三月、五月两次拜访缵曾居所水镜山房,许缵曾为其近体诗集《百幻诗》写序,“诗中大意,皆养生家言,而文采璀璨远胜丹书。”在序中许缵曾肯定了愚菴诗的文采,并指出其诗集的治心、砭世、证道作用:
愚菴精于内视之学,殆欲扫除一切,空诸所有,特借棘猴蚊蜨,逗漏其杳杳冥冥,虚极静笃之旨,读此诗也,以之治心亦可,以之砭世亦可,即以之证道亦无不可。[1]卷五561
除马愚菴之外,张榆阳也是许缵曾非常景仰的一位高道和养生家,他从二十岁起好岐黄之术,钻研中医养生之学,“孜孜以活人为务”。“年三十后,遇明师得闻性命之学,几三元秘奥,靡不洞徹精微,升堂入室。然深自韬晦,……邑之贵人有知其贤者,每侦其入市时,邀致参订,赠以金帛,掉头勿顾也。”[1]卷五562在《送张榆阳还韩城序》中,许缵曾记述了张榆阳的为人和深厚的道教修为,其人有济世胸怀,品行高尚,不阿谀权贵,有傲岸风骨。许缵曾对其清净无为、潜心修道的行为钦慕不已,相较自己不能参透修道要理而深自悔恨:“虽杜门枯坐,不得其门而入”。康熙二十九年庚午(1690年)九月,在观察杨令鸿的邀请下,张榆阳访云间,放舟于“横云山馆”,二人相谈甚深,乃知“先生无书不览,无义弗谈,其言简其意明”,敬佩之情溢于言表。他还特别记述了其修炼状况:
每见其端居大静时,河车过玉枕,声如雷鸣,久而不止。及扪其腹,则丹田中翕翕弹指,宛若婴儿展动。非鼎中有药,腹中有胎,何能见此景象?向所谓长河委宛,汇秀钟灵者,其在斯人欤!在斯人欤![1]卷五562
道教求长生的方法有外丹和内丹之分。“外丹”主要是依靠制造和服食外在药物来保持生命,“内丹”则是依靠自身内在练气的养生方法。文中描述的正是道教内丹的一种修为功法——胎息,相对于普通人的“凡息”而言,用皮肤、肚脐、丹田来呼吸即为胎息,这种神秘的技术晦涩难懂,没有师授往往不能领会。所以许缵曾连连称奇,认为张榆阳深得道教修炼精髓,达到了与道合真。在离开之前,缵曾特意赠送张榆阳一幅家藏古画,并借用杜诗“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诗句写二人离别思念之情:
渭北江南三千余里,他日春云出岫,芳草萋萋,乳燕巢梁,麦雉朝雊,倘篮舆凫舃,重赋远游,不禁跂于望之矣。[1]卷五563
典故出自杜甫《春日忆李白》,后人以“春树暮云”表示对远方友人的思念。除了参与道教的修炼体验以外,他还写了多首悟道之诗。如《依韵和张孝廉咏怀八首》或描绘山人的出尘生活,或描绘隐者的修炼领悟过程,如其一:
山青水绿自年年,独向渔樵暱旧缘。未解黄庭调黍米,漫求脉望蚀神仙。盘蛇峻坂经身试,苍狗浮云过眼前。吾爱吾庐多晏起,柴门长对杜陵田。[1]卷三505
暱是亲近之义,“独向渔樵暱旧缘”把对隐居生活的向往说成是前世“旧缘”夙愿。《黄庭经》是道教五大经典之一,教人如何修炼成仙。其中论及炼内丹,如“内有黍米之珠,落在黄庭之中”是宋朝以降内丹家修炼的上乘功法,其中奥妙非师不可传,所以许缵曾说自己“未解黄庭调黍米”。《脉望》由明代赵台鼎所辑,道法并重,是修习丹道医学的道教书籍,“漫求脉望蚀神仙”写出了道教修炼的艰难。组诗其二云:“……晨昏定课惟高卧,山水闲情发浩歌。……春来静勘参同契,一尺修持一丈魔。”[1]卷三505诗中提到的《周易参同契》是东汉魏伯阳所著的道教早期经典,全书托易象而论炼丹,被誉为“万古丹经之王”。最后一句正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文雅说法,告诫修行者警惕外界诱惑的道教箴言。
(三)心怡老庄
除了道教养生法的吸引力之外,道家超然物外、逍遥自由的人生理念也深深地影响着许缵曾。许缵曾在《庚午冬至夜舟泊千墩》诗中曾经探讨什么是人生“至乐”:
云何为至乐?隔水问渔蓑。簿牒无名姓,江村任啸歌。但知清梦稳,常喜醉颜酡。比夜团蒲坐,儿童笑语多。[1]卷二479
这首诗写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作者六十四岁之时,千墩地处吴淞江边,是苏州至上海的中心水埠。冬至夜,作者泊舟于此有所感触。《庄子·外物》篇探讨了人间是否存在最大的快乐,逐一批驳了世人对苦与乐的看法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至乐在于无为,无为则逍遥。许缵曾诗以形象的生活场景表达了什么是“至乐”。诗中的“渔蓑”代表隐士形象,记载吏事的簿籍文书上没有他的名字,江村渔船上有他自在的身影,“啸歌”显示出高雅闲淡、超拔脱俗的风神,有诗有酒有儿童的笑语,入静时有理趣的探究,平易、安乐,显示出随缘自适的生活状态,这是诗人追求和向往的“至乐”。
人生价值的探索是一个动态过程,引起观念变化的契机可能是名利、衰老、情感……许缵曾正是在三十年经历中参透了人生真谛。他在《同年唐济武诗序》中说道:
余寔粗浮浅劣,谓举天下事皆易与尔。迨余奔走中外,历升沉进退者三十余年,凡可悲、可喜、可惊、可愕之事,皆目观而身尝之。已而乞身归养,事亲课子之外,一事不营。书案绳床,杜门清卧,乃恍然曰:“三十年之我,非我也;三十年前之我,视三十年后之我,亦非我也。”[1]卷五557
年轻时觉得天下无难事,一切尽在掌握,经过了三十余年的升沉进退,许缵曾从宦海沉浮、悲喜无常的人生变化中获得了新的感悟。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绝非趋利避害、功名利禄等外在满足,而在于体识“真我”即对自我的认知以合于天地万物之理。宋代苏东坡谪居黄州时也曾引发“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的思考,慨叹生命不能自主,生起超拔羁绊、遁身江海的遐想。对自我的深刻反思表明诗人达到的哲学理性高度,康熙三十年(1691年)岁末,六十五岁的许缵曾做《辛未除夕》诗:
旧暮升崇冈,极目送归鸟。徘徊生百忧,尘嚣苦未了,吾生逾卦气,琴尊常静好。岁晚烹羔羊,老穉团围绕。俯仰无愧怍,坐对江梅早。今年生不辰,五行互颠倒。干支逢岁尅,剥啄纷相扰。岂无杕头钱,却彼豺狼饱。咄哉柳盗跖,探囊如电扫。宾朋齐太息,室人纷懊恼。流俗更迁移,狂澜沸三泖。瞻彼兰蕙姿,尘埋在台草。矧余一腐儒,屡空奚足道。舍北有山庄,林泉多窈窕。架上余陈编,晨昏足幽讨。披襟一放歌,长贫以娱老。[1]卷二459
《孟子·尽心上》云:“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许缵曾回顾一生,能做到问心无愧,光明正大,襟怀坦荡。诗中用干支、五行、易经学说解释所遇到的各种烦忧事,包含了自嘲的意味。诗中还引用了“盗跖”的典故,《庄子》中假托盗跖与孔子之间的对话,表达了道家绝圣弃智、保身全命的理念,体现了庄子一贯的讽世主题。许缵曾自嘲“腐儒”,描述自己晚年的生活是与诗书相伴,隐于林泉,“披襟一放歌,长贫以娱老”。此诗更接近于理趣诗,有浓厚的道家色彩。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十二月缵曾六十六岁,忽得中风之症,之后将身边妾室数人遣去,调整生活,安心养病。在《定舫杂咏序》中他描述了自己的状态:“壬申季冬廿六日,余猝中风症。痰壅气逆,不省人事,并不知痛癢者三日,晚至除夕乃苏。癸酉新春始能饮食。”[1]卷五560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除夕,许缵曾六十九岁,作《乙亥除夕》,在诗中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
我生席遗荫,少小不知贫,年年逢守岁,枣梨夜杂陈。弱冠入天禄,裘马玉河滨。除夕数宫漏,来朝侍紫宸。壮年岭方岳,四牡日駪駪。御冬缺旨蓄,微禄赖娱亲。滇南归故乡,言采秋风莼。绳床日高卧,萧疏隔世尘。岁晚团圞坐,酌酒话天伦。何期有奇鬼,破壁舞蹲蹲。自言韩退之,揖我为大宾。又言杨子云,逐我常反唇。栖栖无定踪,愿托子为邻。我闻殊不乐,鬼乃意生嗔。一过仓廪空,再过扫百缗。缠绵共晨夕,惝恍徒伤神。童仆久枵腹,儿孙多苦辛。况值分椒夜,盈门剥啄频。对此三叹息,踯躅惟含颦。鬼复慰我言,不如且饮醇。布衣慎怀壁,象齿戒焚身。湛然涵清虚,箪瓢思古人。时序有代谢,穷愁何足论。东风吹草堂,明日岁朝春。[1]卷二460
由少不知贫的优裕,到青年仕途的顺遂、壮年公干西蜀滇南的奔波劳碌,再到晚年的退守田园,虽然清苦但生活也算恬淡自足。在诗中,他把家境由富庶转贫寒的变化,归为“奇鬼”所为:“一过仓廪空,再过扫百缗”“儿孙多苦辛”。“奇鬼”典出于《吕氏春秋》,黎丘山有一奇鬼,喜欢装扮。一次奇鬼扮成他人子,戏弄醉酒的老人。老人回家后责骂儿子,才发现是奇鬼所为。第二天老人又到街市上喝酒,要杀奇鬼,没想到竟然杀死了自己真正的儿子。这个典故常用来比喻困于假象、不察真情而陷入错误的人。诗中其实暗含着许缵曾自比“黎丘丈人”之意,他说自己就是那个无法参透人生无常、困于假象的糊涂人。同时,他又借奇鬼之言来安慰自己,“布衣慎怀壁,象齿戒焚身”,大象因为珍贵的牙齿而遭到捕杀,人因为钱财招祸,这显然是来自道家的祸福观,《庄子·人间世》云:“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因此提倡无用之用,许缵曾安慰自己家业的衰败、晚年的凄凉也许是免祸的福事;诗中又用到老子《道德经》中“被褐怀玉”的典故,充满了得失、藏露、屈伸的辩证思考。“箪瓢思古人”亦折射出安贫乐道、君子固穷的儒家风范。诗尾以“时序有代谢,穷愁何足论”“东风吹草堂,明日岁朝春”作结,体现了一种时序更替的变化思维,可以说,在这首哲理意味强烈的岁暮诗中,许缵曾的精神世界达到了一个更通达的阶段,能够跳出个人的生命局限去看待人生、草木、社会、时空,把变化、衰亡、更新看作是自然之势。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七十岁的许缵曾再次在除夕作诗七律《丙子除夕》:“独坐虗斋早掩扉,静看天牛鸟飞归。晚来斜日怜同调,老去高眠爱息机。”[1]卷三526诗中的“息机”指泯灭机心,语出《楞严经》:“息机归寂然,诸幻成无性。”佛家解释为:本来心性有之,为教法所激发而心动,即意识到由内因与外缘的感应而动心起念,是觉悟的关键。找到了“机心”的缘起,进而身心放下。不贪不求,作身心的调养工夫。“息机”绝非傲世逃避的借口,而是在调节身心的同时,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于万物命理之中,让生命得以永恒,心灵得到久安,这是许缵曾一直寻求的境界。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重阳节,距离他逝世前一年,许缵曾再次以《丁丑九日》诗记慨:“老我尘缘犹未净,扁舟烟水忆沧浪”[1]卷三528,尘缘、六根都是佛教中用语,尘缘未了、六根未净指自己还没有摆脱尘世的困扰,“扁舟”“沧浪”意象则承载着文人淡泊世事、逍遥自由的追求。
综上所述,许缵曾由天主教信仰开始,以儒释道思想的融合为终结,西方天主教对他的影响越来越微弱,中国士大夫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得到滋养,遵循自己的本心,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调节方式。
三、中西结合:许缵曾治学
天主教世家的西学传统为许缵曾打下了良好的西学基础,西学注重实证的科学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加之前半生的仕途生涯开拓了他的眼界,使许缵曾并未偏执于诗文而成为一位开放性的学者。他看重材料搜集的工夫,不作空泛之论,附有大量的实例证论,结论建立在材料的基础之上,比如对云南地理环境的考察;他擅长将知识与现实需求相结合,往往能发前人所未发,比如记录清初烟草的价值;他尊重客观事实,杜绝臆测和假想成分,如对各地民俗风情的记录。总之,西学讲求真凭实据、注重实用性的治学方法还是被许缵曾所接纳并影响了他的学问文章。其诗学思想亦体现了西学与道家思想相融合的印迹。
(一)讲求实证,关注民俗
西学的特点在于“实”与“真”,许缵曾文集也体现了注重学问真实性、实用性的特点。比如《滇行纪程》《东还纪程》及《续抄》是他到西南公干、外任云南及东归时的旅途见闻,文中不仅记述了大量的地理学知识、当地的物候及特产,而且还有精确的配图及注释。许缵曾曾经与西方传教士毕方济谈论烟草,了解烟草的价值与功用,他在《琐碎录》中记载:
数年前,与西儒毕方济问及烟草,毕乃出远西本草翻译示余,为膏为油为末,功用甚多,因备录之,详载医论中。[1]卷九681
烟草是一种原产美洲的经济作物,于明代中后期传入我国。由于烟叶的吸食和生产发展过程给社会带来了不良影响,尤其是种烟大量占用农田引起统治者的忧虑,明清两代都采取过禁烟措施,明崇祯帝、清太宗皇太极、顺治、康熙、雍正帝都曾发布过禁烟令。对于这样一种“敏感”作物,清初对它的认识还比较初级,尤其是在民间,仅限于它的吸食价值。许缵曾则向毕方济请教,发现了烟草的其他功用,尤其是罂粟果实(鸦片)的医疗用途,并将西方植物著作《远西本草》中的相关内容详细记载在医论里,以资日后所用,可见他对于社会具有争议性事物的关注和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
受家庭信仰与游走各地的经历影响,许缵曾的实践经验和见识超过普通文人,他曾写《全省大略》[6]卷十1记载了南方丝绸之路即从“身毒”(印度古称)到川滇的交通要道,可谓是珍贵的文献资料。但是,对于“中国天下观”的执见又让他难以接受西方的宇宙观,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在《滇南分野说》中,他提到了西方人对地球的认识:
近见西洋天地球谓天包大地,天地在天中仅一点,中国在大地中,五大洲之一耳。岂有週天列宿、散列三百六十五度,止分在一洲之理?信斯言也,则星家之言荒谬甚矣。[6]卷十3
许缵曾对西方宇宙观提出了质疑。中、西方天文学有众多相悖之处,如中国天文学家把天空中的可见星分为二十八宿,并对应以中国之九州,总体上还是以地球为宇宙中心、以“中国”为地球中心的“天下观”。天下观与方位、颜色、阴阳五行学说相比照对应,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思维框架,并贯穿整个古代中国科学理论体系,成为认识和解释自然、社会的方法论;而西方天文学家的“日心说”则以太阳为宇宙的中心,地球不过是众星中之一,中国不过是五大洲中之一国。虽然晚明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已经开始瓦解国人的“天下观”,但是到了清初,如许缵曾这般熟悉西方科学知识的士大夫仍然无法接受西方宇宙观。
除了关注天文、地理、经济外,许缵曾在云南担任按察使期间,在巡察、考核吏治、主管刑法的过程中,对云南的风土民情也有深入的了解,不仅仅是云南,可以说,他每到一地都会关注当地的民俗文化。他记载了民间的许多轶事传奇、自然神异之事,如《琐碎录》中的《寿张女鬼》《老人生角》《龙异》《杨应魁业报》等,《发李自成祖墓》中则记述了秦抚汪乔年破闯王祖墓的过程,古人讲风水、龙脉、王气于此可见。许缵曾集中有一专章名为《纪幻》,另有《鹊异》《记异》《獭异》《义犬》《贞雁》等,不仅将民间异事怪闻成文,而且还附上“某某口述”,有整理民间文学之功。
在这些逸闻趣事中,许缵曾时时发表自己的看法,对于社会问题,往往运用儒家学说、佛理加以分析评论,在《琐碎录》中,许缵曾谈到了民间社会的交往问题:
富贵受贫贱人礼,以为当然,此大折福处。亦大敛怨处。湏知其从当卖而来。[1]卷九679
其颇符合儒家“礼主敬”的纲领,《礼记·曲礼上》云:“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礼是强调尊敬对方的,通过自我谦卑的方式来尊敬他人,即使是挑着担子沿街叫卖的“负贩者”也有人的尊严。“礼”不应该以贫富来论,不论何种身份,受人之礼,都需要谦恭的心态,如果把对方的敬意“以为当然”,则“大折福处”。虽然许缵曾是从福报论的角度讨论人际交往原则,亦有正面意义和价值。在《琐碎录》中许缵曾借用佛经论朋友:“佛氏有花交、秤交之喻。花者,因时为盛衰;秤者,视物为低昂也。今之交友,离不得花秤。”[1]卷九680《佛说孛经》中述及四种朋友类型:有友如花、有友如秤、有友如山、有友如地。有友如花者,好时插头,萎时损之,见富贵附,贫贱则弃,这是嫌贫爱富的朋友;有友如秤,物重头低,物轻则仰,有与则敬,无与则慢。也就是说当人有名位权力时对方就卑躬屈膝,阿谀谄媚;人无功名权力就轻慢无礼,看不起朋友。两种如花如秤的朋友都是损友,许缵曾感叹世间大多是花秤之友。
(二)原本经史,发越性灵
许缵曾诗学体现了西学与道家思想相融合的印迹。性灵、格调与神韵,是清代康乾时期袁枚、沈德潜、王士祯三家诗学主张,亦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发展到清代的主要派别。从其诗论中亦可见当时诗坛的焦点:性灵与才学,宗唐与宗宋,复古与变革。
许缵曾文集中有关诗论的文章不多,综合来看,体现了以学问为本的创作理念。《含晖堂诗序》作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序文简述了云间诗学观念的变迁:
忆与尊大人侍御公论诗辇下,其时云间诸子若宋若周若王若顾,秉烛夜谈,每会得诗数十首,诗数少者有罚。其时朝夕讨论,不过欲规取魏晋,揣摩三唐,不失其体裁、音响如是止矣。乃三十年来,作者另出手眼,必求所谓宋人体格,刻意生新,生者且至于聱牙,而新者遂沉于杜撰。[1]卷五552
明末云间派持复古的文学主张,诗学以汉魏盛唐为宗,不以宋诗为意;然而三十年后,云间论诗一度出现了宗宋倾向。许缵曾无意于宗唐或宗宋,他认为唐诗、宋诗各有千秋和妙处,都是在变化中确立自己的地位,文学风气的改变受到时代变迁的影响是自然现象,即所谓“气化所感,习尚所移”,不可“执一端以论诗”。这种观点与推崇“性灵说”的袁枚不谋而合。袁枚认为诗歌不能简单地取法古人:“不可貌古人而袭之”,应该在变化中认识诗歌的价值与作用。
许缵曾认为诗歌的关键在于“性灵”和“学问”:“大雅元音,本之于学问,得之于性灵”。在“性情”和“学问”两者间,性灵必以学问为根本才能产生好诗,这预示了清代重书卷气、主综博、以考据训诂为根基的诗学倾向。蒋寅先生《在传统的阐释与重构中展开——清初诗学基本观念的确立》中指出,诗学在清代不同于以往的最大特点即它是被当作学问来做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出于对明朝衰亡原因的反思。“在清初人的普遍意识中,明人的空疏不学是亡国的祸根。武装反抗失败后,汉文化救亡图存的希望全系于学术之一脉,一种博综的、求实的学问与人生最崇高的价值联系起来。”其实,这种反思在明末士人当中已经进行了。如晚明开始并延续到清初的“经世思潮”试图改变当时空疏的学风,他们面对“士无实学”的风气进行激烈的批判,云间陈子龙《经世编序》言:“俗儒是古而非今,文士撷华而舍实。夫抱残守缺,则训诂之文,充栋不厌。寻声设色,则雕绘之作,永日以思。至于时王所尚,世务所急,是非得失之际,未之用心。”[7]卷二十六438陈子龙反对泥古不化、只注重章句训诂的俗儒,批评崇尚虚华雕饰之作的文人,认为士人的学问和作为应针对社会所需、时事所急,结合具体情况加以变通。
而经世思潮与西学的传播又有着密切的联系。“西学”求真、求实的特点顺应了明末经世救国的需要,云间士人努力把西方自然科学及实证精神引进儒学,如天主教徒徐光启引进西方天文学修订中国历法,促进了云间天文学的发展;孙元化、陈于阶等融合西方科技、造炮制器发展“器物之学”,他们对西方科学介绍和应用的贡献最大,开拓了以“西学”经世致用的风气;明末众多不是天主教徒的儒生也都把“实学”作为自己的学术方向:如崇祯年间集合云间知识层精英力量的“几社”由八股社团向文学、学术团体转变,以复古诗文创作闻名文坛,兼行“务为有用”的经世之学,其领袖陈子龙“功用以济时为大”学术观的形成、《皇明经世文编》等众多实用著述的出现都说明了云间几社社团宗旨和学术重点的移变,这种转变历程也正是西学潜移默化融入云间知识阶层的过程。
“西学”“实学”在明末的苏、松等地成为风尚。明松江府推官李瑞和(1607-1686年)在任七年,曾为上海天主教堂的落成写序文《上海天主堂》,提到了云间西学流行的盛况:天启间“士大夫习西学者,相矜为吾学,已显于唐之世。”“唯利西泰学士,抱绝世之姿,一旦而入中国,其迹奇,其法大,中国贤志之士多宗之。”[8]219这段记载说明云间士大夫以研习西学为荣,“相矜”体现了他们对西学抱持新奇的眼光、接纳的态度并引为时尚。杜登春《社事本末》中记载复社后期“收罗实学,不事浮名,为吴下教子弟第一家法”[9]1003。不仅如此,望远镜、自鸣钟等西洋奇器进入云间百姓生活,方便民生日用的同时也带来了民俗的新变,表现在服饰、饮食与礼仪等方面。可见,明清之际的云间士人或从哲学层面将西学辩证地吸收到实学理论构建中来,或从实践层面将其运用到社会改良过程中去。许缵曾诗学对于学问的重视正是承此一脉。
除此之外,许缵曾《陈绿巖诗序》以“射艺”悟作诗之道,很有庄子寓言的意味:
盖覩于射而有会于作诗之道也。……然当引弓舍矢之际,人各有容,动各有度。……今之为诗者,人握灵蛇之珠,家抱荆山之玉,犹夫射者之人,各有容动,各有度也。然殚思竭虑、撚髭而苦吟者,期有肖于晋唐之貌而已。[1]卷五555
在序文中,许缵曾区别了射箭技艺的高低与作诗层次的差别,不同的诗风各有千秋,正如射手姿态、所达境界不同,此为正常之理。他批评了仅仅追求晋唐遗韵的摹古做法,由此可见,他已跳出云间“宗唐”的诗学观,提出作诗不可一味模仿。在文中,许缵曾还特别描绘了“悬肘之射”:
近岁则见有悬肘而射者。方右臂之持满而发也,拳交于乳,而膊过于眉,如隼之振翼,寉之起舞,能使壮士为之动容,上将为之击节,吾于是喟然曰:“嘻,作诗之道,亦若是则已矣。”[1]卷五555
许缵曾所谓“悬肘之射”与《庄子·田子方》中列御寇为伯昏无人表演的“射之射”相似,即技艺高超的有心之射。然而,比拟于诗,究竟是何种诗风?文中自己作了回答:
吾读绿岩之诗,恍然有悟于悬肘之射。……其所著古风近体,莫不原本经史,发越性灵,窥其意旨,欲尽扫前人之窠臼,穿天心出月脅,徜徉于广漠之野,以自见其云蒸霞举之才。……而绿岩之神氣,直欲帙晋唐而上之。[1]卷五555
不可否认,“晋唐”诗文仍然是耸立于许缵曾等清代诗人面前的一座高峰,但他认为“晋唐”是可以超越的,如何超越?一靠学问,二靠性灵。“原本经史”是强调作诗要重视学问和积累,“发越性灵”即主张诗歌创作要抒发一己之心灵性情,表现真情实感。这与《含晖堂诗序》中的观点一致,即学问为首,是成就诗歌之第一要素;其次注重性灵,学识与天分、才气与艺术构思中的灵机结合并重,才能免于落入“掉书袋”,才能自出新意,即所谓“尽扫前人之窠臼”,达到“云蒸霞举之才”之境地。这里的“才”则有了才学、才气的双重含义,即才能学问的厚积薄发和才华、才情的自然流露。需要注意的是,“悬肘之射”属于有心之射,并非庄子射艺中的最高境界;在庄子那里,射箭的最高境界是无心之射,即“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的“不射之射”,道家讲忘我,这种精神境界与体验宇宙人生之道的“心斋”“坐忘”类似。但是,如果用于比拟作诗则难以具体操作。许缵曾没有落入其中,而是严守他一贯的作诗主张:学问为首,其次性灵,本身即是他讲求实证性思维的体现。
四、结 语
明清之际传教士在文化沟通上所作的贡献虽为副产品,但已对云间社会起了很大的冲击,正如徐宗泽所说:“此种学问,不特当时发生极大影响,即今日,亦保留其权威。”[10]1传教士传入的不仅仅是西方种种具体科学,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治学态度,在层面多样的明末“实学”风气中能够看到较多西学的痕迹,这也是明清之际在华中西文化碰撞的成果之一。可以说,“西学东渐”提供了西方科学与中国传统知识论相结合的良机,带来了云间士人知识结构及学人理念的新变动,西学在云间地区的传播影响了云间学术。
需要注意的是,“儒学本位”仍是云间士人的思想基础,在思想上真正转而信仰天主教者占相当少的数量。西学在云间社会传播引起的思想波澜还表现在治学研究和文学观念上,这种影响往往是隐性和潜移默化的。许缵曾以自身的探索和经历呈现出中西学交织下思想行为的复杂性,在人生困境中,道家思想成为支撑和调节情绪的良好资源,为士人包括天主教徒疏解精神苦闷及压力提供方法及力量。
注释:
(1)陈垣、方豪先生各为之作传一篇,述其一生经历及对天主教的贡献,并就许缵曾多元化信仰的情况做了简要论析,奠定了研究基础。我国台湾学者黄一农先生《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刘耘华先生《清初上海的天主教文人许缵曾再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及其学生延经苹的硕士论文《清初天主教文人许缵曾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进行了文献资料的进一步整理和考述,从家族人物、生平事迹、交友宴集、著述及信仰等几方面,对许缵曾的思想、信仰与情感世界作了进一步研究,认为其人生观由多种价值理念和宗教关怀杂糅而成,天主教信仰融于固有的传统文化熏陶之中,并且这在明清天主教世家后代文人身上,具有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