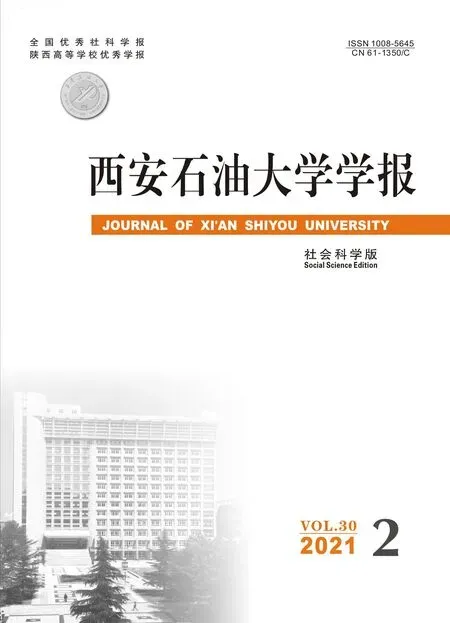“良知坎陷”与“心外无物”
——论牟宗三对王阳明《传习录》“南镇看花”章的现代诠释
赵连越
(河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0 引 言
纵观整个阳明学系统,“心外无物”中所指之“物”更侧重道德实践所带出之“行为物”,因儒家心性之学之传统重在通过自觉地道德实践而成圣,对现象界之“存在物”较少以存有的态度去探究。但是,在《传习录》“南镇看花”一章中阳明又将“物”解释成“存在物”,且明确地表述“岩中花树”等现象界之“存在物”亦不能脱离吾心而独立存在,此种表述在实践哲学系统中则显得刺缪。若阳明在“南镇看花”章中所言之理成立,则吾人可说阳明学“心外无物”思想达至圆极,即“行为物”和“存在物”皆不离吾心。“行为物”不离吾心易理解,阳明曰:“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1]37按牟宗三的诠释,吾之道德本心自发、自律,无条件地供给吾人实践法则,其发于事亲即是孝,发于事君即是忠,“事亲”“事君”依“孝”“忠”等实践法则而存在之“行为物”不出吾之本心也。但“存在物”不离吾心则不易理解。在对此问题诠释中,牟宗三以“良知坎陷论”解决“致良知”过程中“存在物之存在性”如何安顿的问题来讨论“岩中花树”等现象界之“存在物”如何不离吾心之良知而存在。其关于良知坎陷为认知心进而成就知识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现象与物自身》和《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等书中。牟宗三在《现象与物自身》中说:“知体明觉不能永停在知体明觉之感应中,他必须自觉地自我否定(亦曰自我坎陷),转而为知性,此知性与物为对,始能使物成为对象,从而究知其曲折之相。”[2]126“知体明觉”意同于阳明所说之“良知”“本心”,吾心之良知“停在知体明觉之感应中”即良知自持其自己,此时对我这主体而言即呈现一“与天地万物一体”之“与物无对”之境,此时可知物之“实相”而非“曲折相”。当良知“自觉地自我否定(亦曰自我坎陷)”为“知性”时,便可将外物推出去使外物成为认知意义的对象,转“与物无对”而为“与物有对”,成就吾人对外物之知识,故“存在物”不离吾心之良知而存在。牟宗三以此种说法解决存在物如何不离良知而存在的问题,因此他又总结说:“事在良知之贯彻中而成为合天理之事,一切皆为吾之德行之纯亦不矣。而物亦在良知之含蕴中而如如的成为其物,一切皆得其位育而无失所之差。”[3]197
笔者认为,牟宗三关于“心外无物”的讲法过于紧凑,且牟先生并未直接用“良知坎陷”诠释《传习录》“南镇看花”章。故本文在“照着讲”牟宗三“良知坎陷”之思想上有所扩充,以“良知坎陷”为纲骨分三步讨论“心外无物”一问题:第一,讨论“心外无物”中“心”之本意,客观地还原阳明“心外无物”之“心”的本来面目;第二,疏解“岩中花树”等现象界之存在物之存在性的问题,客观地还原阳明“心外无物”之“物”的本来面目;第三,进一步分析牟宗三“良知坎陷”理论本身,从而沟通“心”与“物”两者。于诠释方法上,基本遵义以现代哲学语汇对传统哲学命题予以现代性的创造性诠释,即:“理解既是历史地理解,又是现实地理解,它既着力于借助历史和传统解答人的现实生命诉求,同时又以‘意义的创生’引领人在之后的生命活动和生命走向。”[4]74如此步步为营,一则使读者了解“良知坎陷”,另一则期解决“南镇看花”这一众说纷纭的千古难题。
1 “心外无物”之本意
“心”有多重含义,可为心理学意义的感性心,可为认知意义的认识心,而阳明“心外无物”中所言之心则不同于前两者,牟宗三断之曰“超越之本心”(或曰“超越的道德本心”)(1)此处之“超越的本心”“超越的道德本心”意同于王阳明所言之“良知”,“良知”一词本出自孟子,孟子曰:“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之本意即人之知仁知义之本心,本心能自发的知仁知义即是良知,阳明以良知综括孟子之四端之心,即把良知提升上来代表本心。故本文在用词上“良知”与“超越之本心”“超越的道德本心”混用,以下不再附注。而非认识论中的“认知心”(Understanding)。牟宗三说:“此心须当下认为是超越之本心,不是中性的气之灵之心也。”[3]195“超越之本心”是存有论地讲,相当于“自由无限心”,“气之灵之心”即从能所关系立论的有限的“认知心”。牟宗三进而说:“这(心外无物)也是‘存在依于此心’,但却不是有限心认知的层次,而是相当于巴克莱最后之依于神心之层次。依于神心是存有论的,是纵贯的;依于有限心是认识的、横列的。”[3]187-188牟宗三所说之“神心”即虚说的“超越之本心”,他异质地超越于有限的认知心之上,是“存有论的”、“纵贯的”,其不同于认知层次的“横列的”“认知心”。按牟宗三之意,“心外无物”扩充言之即“物之存在依于超越之本心而非有限之认知心。”然此意是否合乎阳明本意乃至儒家之传统则需要我们进一步讨论。因阳明学承孟子而来,且“心外无物”虽为阳明提出,但其中之理境为正宗儒家所共许且一脉相承,故我们讨论“超越之本心”一语是否成立时从孟子讲起,此是将“心外无物”放在儒家之大传统中而言。
我们先看孟子的文献,孟子曰:
“人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5]212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5]208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5]209
第一条文献中孟子表示良知、良能先天本有,是超越的而非现实的。因“学”“虑”必有待于思辨与经验,“不学而能”“不虑而知”即表示良知、良能不能建立在后天思辨或经验之基础上,因此他不是“认知心”,“认知心”认知外物成就确定的知识必在感性摄取对象之基础上和知性先验所发之范畴之决定下,此与孟子本意相悖。第二条文献中孟子表明心、性、天有内容和意义上之相同处,天道绝对而无限,心、性亦绝对而无限。孟子虽未明确说明心、性、天是一,然已经蕴含此理境。第三条文献中明确提出“万物皆备于我”(或曰“万物一体”),但并非人之外在躯壳与万物为一体,而是需要“反身而诚”,即:通过道德实践的功夫从外在的现实生命这一层上返回来复归于生命本身而可至“万物一体”。“反身而诚”的道德实践之枢机即在发明、扩充本心之“尽心”。结合第二条文献可知,吾人通过道德实践(尽心)所体现(知)之“道德本性”(性)同于天道“为物不贰、生物不测”(《中庸》语)之创生性,“尽心”至其极即与天地万物一体,天地万物亦不离我而存在,即“心外无物”。由此可知:通过“反身而诚”“尽心”之道德实践的功夫可开显“天地万物不离我而存在”之无限境界,即表示孟子所说之心是存有论的、纵贯的、具本体之意义的,故牟宗三判为“超越之本心”不悖孟子义。“超越之本心”具有形而上之绝对普遍性,由此可说“心外无物”也。
孟子后,程明道、陆象山最善解孟子意,我们可再看明道的文献:
“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6]15
“所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只为从那里来,‘生生之为易’,生则一时生,皆完此理。人则能推,物则气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与有也。”[6]33
第一条文献中,明道明确表明人心、人性即是天心、天性;故心、性为具本体之意味之本心、本性。第二条文献中明道言万物皆俱天理,且天理是天地创生万物之动态的创生真机、创生之理,“人则能推”即表明人通过发明本心而自觉地做道德实践可推至、扩充此天理,“推致”天理必然是主观地说,主观之道德实践之枢机在“本心”而不能说“本性”,故主观地扩充、推致“本心”即是扩充、推致具创生性之天理,推致其极则主观之本心与客观天理合二为一,万物不出天理之创生,万物亦不出“本心”之范围,此即是明道语中之“心外无物”。陆象山亦有文献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7]269象山言语质朴简洁,两条文献皆直截明了表示“心外无物”“道外无事”,此心、此理充塞宇宙,一切存在皆在其涵盖中,故象山语中之“心”亦是存有论的“超越之本心”。
我们再看阳明的文献,阳明曰:
“心即性,性即理也。”[1]71
“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使其正者,即人心。”[1]42
“概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1]69
此三条文献重点说明心、性、天的关系。第一条文献表明心性(理)是一、主客是一,其本意或对朱子析“心理为二”而发。朱子曰:“所觉者,心之理也;能觉者,气之灵也。”[8]85在朱子之系统中,性和理超越而挺拔,心则脱落孟子“道德创造之超越的本心”之义而为“气之精爽”“气之灵”,是则心通过格物的方式“横摄地”认知外界事物之理进而依理而行,如此心成气化的认知意义的心,显然不能“心即理”,必是“心具众理”,且此“具理”必是待“格物致知”后经验的具、涵摄的具而非本具、固具。因此,若“心即性,性即理”“心性是一”,则阳明所说的心仍是孟子义的“超越之本心”不能是“能觉所觉”的“认知心”。第二条文献中阳明说,心不杂以感性私欲、不受后天经验因素的影响从而无“分别以从物”即是道心,若掺杂后天经验因素或说顺躯壳(感性)起意即是人心,此时道心转为心理学意义的感性心或认知意义的认知心,此种意义的心是消极的,“心外无物”当指“道心”,不能指“杂以人伪”之“人心”。由此条文献可进一步佐证阳明学中“心外无物”的心亦是“超越之本心”而非后天的“感性心”“认知心”,此不违孟子义。第三条文献旨在说明心体即是道体,道体无外,心体无外,道体有绝对的普遍性而心体亦具绝对之普遍性而感润无外,即“心外无物”也。综合阳明三条文献可知,“心外无物”的心是“超越之本心”无疑。
于儒家之传统而言,孟子、明道、象山、阳明所说“心外无物”之本意是站在通过道德实践的功夫推至、扩充超越的道德本心至其极而与绝对普遍之天道贯通为一的角度所说的“超越之本心之外无物”。因此牟宗三判阳明所说之“心”非“认知心”而是存有的、纵贯的“超越之本心”,是站在儒家之传统上而言,非创新之语。牟宗三首先解决了“心”之含义的问题,如此吾人可说:“心外无物”是“本体论的直贯义”,“超越之本心”既是吾人道德实践之可能的超越根据,又是一切存在之存有论的根据,“行为物”和“存在物”两者均在良知本心的贯彻和涵润中。
2 “存在物”之存在性如何安顿
如上只是纲领性地或笼统地说“心外无物”之实意,但我们仍需进一步从内容上具体地问:“现象界之存在物本身为何种形态的存在”?
我们先看“南镇看花”这一难题: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1]332
本来从实践哲学角度尚可仿佛一二的“心外无物”又卷进一外在的存在物,阳明此处所说之物不再是“看花”之“事”,显然指“岩中花树”本身。如此讲实在是玄妙难解!以今人的思考模式立即可反诘:譬如天地山川无论你知不知它依然千古同在,不能因我们不知它即否定它的存在性,此种说法实在不符合一般人思考模式,故力攻阳明“唯心主义”者多借此说,此即存在物到底是何种存在形态一难题所造成的困境。对“岩中花树”等现象物的存在形态,牟宗三名之曰“现象界的存有”[2]413。依牟宗三,存在物如桌椅板凳等,其是客观的且有存在性的,但不等同于桌椅板凳有实在性且可以绝对客观独立自存。吾人所说桌椅板凳等现象界的一切存在物之存在性必须严格规定在现象界(Phenomenal)而决不可越至本体界(Ontology),现象物之存在性非形而上本体之客观实在性和独立自存性,他们只有生灭无常、刹那变化的现象的存在义而无本体式的、永恒的、绝对的、独立的、实在的存在义。我们不说现象界的存在物不存在或没有存在性,我们只说他有现象义的存在性而无本体式的存在性,此即“现象界的存有”。
进而,我们还需再问:现象界存在物之现象意义的存在性如何建立?西哲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说:“内在的自然学(Immanent physiology)则是把自然视为感觉底一切对象之综集,因而亦就是恰如其被给与我们者而观之,但是其给予我们只是依照先验条件而给与我们,只有在此先验条件下,他使能被给与我们。只有两种这样的对象:外部感觉底对象,这些对象底综集名曰‘物质的自然’(Corporeal nature)。内部感觉底对象,此曰灵魂,而依照我们对于灵魂的基本概念而言此亦曰‘思维的自然’(Thinking nature)。”[9]875康德说我们之所以对“物质的自然”和“思维的自然”有知识(两者之现象意义的存在性对于吾人而能被建立)是因为“物质的自然”和“思维的自然”在先验的条件下给予我们且只有在此先验的条件下才可以给与我们,即被我们所认知。这先验的条件即我们的感性、想象、知性,杂多之外物被吾人感性在时空(依康德,时空是心之主观建构)之表征下摄取,在想象中重现,在知性所发之范畴的先验的决定之下成为一被决定的对象,如此我们始能对现象界一存在物有知识。脱离此三者外界对象不能给予我们,“岩中花树”等现象界存在物之现象意义的存在性对于吾人而不能被建立。知识根本条件并不在乎感觉经验的实际内容,而是在乎知性之先验的建构能力。据此,吾人可说:现象界之存在物无独立实在性,且其对我这个主体而言的现象义的存在性是依我们感性之接受、想象之重现、知性所发之范畴三种先验条件而被建立,此即对现象物之存在性如何被建立之解释。
牟宗三说:“现象者,存在物对一定样式的感性主体而现为如此者之谓也。对象者,一存在物为感触直觉所面对而取著之之谓也。”[2]134若说吾人可认知现象界之存在物即是依照我们人类这一特殊样式的感性主体的感性、想象、知性之先验条件而可能,则同一现象界之存在物对不同样式的感性主体而所现之现象则不同。一存在物对这样的感性主体现为此者,对那样的感性主体又现为彼者,其在其自己之本来面目如何?我们在特殊而有限的感性、想象、知性之先验限制下不能知也。故,我们再次强调:现象界存在物之存在性是基于我们感性之接受、想象之重现、知性所发之范畴三者而建立,“岩中花树”等现象物绝非恒常不变、独立自存的,他们只是依不同感性主体而现不同相的现象,他们没有本体式的绝对客观性,我们不可将其执着为实有,无感性、时空、范畴三者,其现象意义的存在无法建立!
在康德之基础上,牟宗三在《现象与物自身》对现象物之存在性的问题进一步解释曰:“现象之为只是关系是由执念而定住的。因此之故,他们遂得自持其自己为关系,这些关系相就是执相,即由概念之执而执定的定相。概念是方方正正地有限定的,因此,其所决定成的诸关系相皆是定相,这亦即是现象。……知性、想象、感触不过是层层说明而已,知性执定概念,因而执成现象之概念的定相;想象执成时空并就时空而执现规模相;感触的直觉以时空为其形式,遂执成现象之时空相。”[2]253-254
牟宗三所说之“现象之为只是关系是由执念而定住的”意同于康德所说“知性为自然立法”,为沟通本体界与现象界,牟宗三用“执念”(识心之执)来替代“知性”一词。按牟宗三之意,现象物非绝对独立存在之客观实在,只是由“执念”定住的“关系”,且“其所决定成的诸关系相皆是定相。”我们的感性摄取外物,把“物质的自然”给予我们,“物质的自然”进一步在“知性执成概念定相”“想象执成规模相”“感触执成时空相”之层层执成的“定相”下成为一决定了的现象,所谓的现象不过是识心执成的定相,其本质不过是一系列的关系。其在吾人识心下对吾人之认知而言有现象的存在意义,但其本身实不能独立自存,其脱离吾人之识心所呈现之本来面目即“物之在其自己”,我们在有限的认知心之下亦不能知。在此我们只需明白:“岩中花树”等现象界之存在物对于吾人之现象义的存在是基于吾人之识心(感性、想象、知性)三者而建立,其本身之存在由吾人之识心而执成。最后,对此问题牟宗三说:“因此,凡识心之认知地所及者为现象,凡无执心之存有论地所明通而发者为物自身。现象与物自身之超越的区分由执与无执决定也。”[2]135牟宗三在康德之基础上解决现象物之存在性的问题后,继续以识心执与不执来区分现象与物自身进而沟通本体界与现象界。在他看来,有识心之执即有现象,无识心之执即无现象,这也为他的“良知坎陷”埋下伏笔,下文即论之。
3 “良知坎陷”开出“知识”:“未看此花”是物自身,“看此花”是现象
“岩中花树”等现象界之存在物的存在性已明,则“心外无物”中未解决之问题落在存在物和良知本心之关系该如何处理或说良知本心如何负责存在物之存在性上。阳明说:“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坦便是他本体。”[1]270良知是“天理”,他是负责断制吾人之行为之善恶当否的价值判断之最后的标准,而天理不同于存在物之“物理”,存在物之“物理”即物之种种曲折相,良知只是真诚恻坦地知是非善恶,如何成就存在物之物理,即如何负责成就由识心执成的一系列关系这一现实存在物?
对此,牟宗三说:
“吾心之良知决定此当否,在实现此行为中,固须一面致此良知,但即在致字上,吾心之良知亦需决定自己转为了别,此种转化是良知决定坎陷其自己,此亦是其天理中之一环,坎陷其自己而为了别以从物,从物使能知物,知物使能宰物,及其可以宰也,它复自坎陷中涌出其自己而后复会物以归己,成为自己之所统与所摄。”[3]206-207
“识心之执是对反着知体明觉之无执而言。识心之执既是由知体明觉之自觉地自我坎陷而成,则一成识心之执即与物为对,即把明觉感应之物推出去而为其所面对之对象,其本身即偏处一旁而为认知主体……”[2]187
此两段文字即牟宗三著名的且饱受争议的“良知坎陷说”。阳明说良知“生天生地”则良知是一实现原则、创生原则。良知“明觉感应”一物则实现一物,实现之即创生之。若问良知如何实现、如何创生“岩中花树”,按牟宗三之说,则答曰:良知在坎陷中实现之、创生之也!良知本心昭灵明觉之自持其自己时物所呈现的是无物相之实相,即康德所说的“物之在其自己”之“物自身”。具体地讲,通过道德实践而扩充良知本心至其全幅朗现,则现实中的人不再是一有限存在而是一无限存在,而此时现实中的人这一感性主体之“识心之执”即消解为“知体明觉之无执”,所呈现于此无限存在前之物即是在其自己之“物自身”,即实体意义的物之实相。而当“岩中花树”等现象物以现象的姿态呈现于吾人眼前时,则代表“岩中花树”由其“实相”向其“现象”的一种转化,由此我们可认知物之定相。依牟宗三,这种转化即为“吾心之良知亦需决定自己转为了别,此种转化是良知决定坎陷其自己,此亦是其天理中之一环。”“了别”即“识心”,“岩中花树”等现象物现象义之存在性即依吾人之识心对于吾人而被建立起,我们才可以对“岩中花树”有知识。假如“知体明觉”永远停留在“自持其自己”中,其自身亦不能说圆满,“岩中花树”等现实世界之种种存在无法保证。当良知决定坎陷自己以从物并“复自坎陷中涌出其自己而后复会物以归己”时它便完成其辩证地“生天生地”,此即是牟宗三笔下的良知辩证创生现象物。但笔者于此仍需补充说明的是:我们只是于学问之申述上要分解地区分出良知天理和现象物。故,在探究良知与现象物之关系上牟宗三才有此种分解的表述,但于实理上二者冥冥为一,只是一宇宙大化之流行或天道生德之朗现也。
第二段文献与第一段文献意义相通,即:“识心之执是对反着知体明觉之无执而言”,良知无执即无有限定或定相,识心之执即有限定而成定相。无限的良知天心异质地超越于有限的识心之上,因此当他“把明觉感应之物推出去而为其所面对之对象,其本身即偏处一旁而为认知主体”时,对于其自己来说是一种“坎陷”,坎陷自己而扩大自己,同于黑格尔所说之辩证地发展其自己。当它坎陷自己而为识心时,呈现于知性主体前的对象便有现象义的存在性可言,此即良知辩证地实现“岩中花树”创生“岩中花树”。若把识心执成的关系(现象物)执为实有而不能复归于知体明觉,则物即执定成死物。因此牟宗三又说“它复自坎陷中涌出其自己而后复会物以归己。”至此,良知完成其辩证地实现一物之存在。从良知自身的角度讲,“物”是本体论的有绝对客观实在性的存在,良知明觉感应之物是物无物象之“在其自己”之“物自身”。从良知坎陷自己为识心的角度讲,“物”是有种种“曲折相”的无绝对客观实在性的依于吾人感性、想象、知性三者而建立的现象意义的存在,此时之物即识心所执成的定相。此时心理不二、心外有物。若自觉扩充本心、致良知、道德实践至圆融化境,则一切皆是本心、性体之如如朗现、天理天德之大化流行,“岩中花树”等现象物当然不出良知之创生涵润也。
依牟宗三,同一物对自由无限心(良知、本心)而呈现即是“物自身”,对有限心(识心、知性)呈现即是“现象”,实则两者之区分可以打通。良知自持其自己成就“物自身”,良知坎陷其自己成就“现象”,现象物不在良知之创生、涵润之外。此种表述换做阳明的话说便是:“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此是古人松散的语录式的讲法,然不表示其中没有智慧洞见,若按照吾人之梳理给予其现代诠释,则曰:“你未看此花时”即是“你的良知昭灵明觉自持其自己之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即是“吾之良知、本心自持其自己,此时所呈现之物是物之无现象义之实相,即物之如相,即物之在其自己,即物自身”;“你来看此花时”即“良知积极自觉地自我否定,坎陷自己为识心以从物”;“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即“良知辩证地如如地创生、实现此现象义的有物相、定相之物,即被吾人认知心所认知的现象界一现实存在物”;“此花不在你心外”便是“良知、本心之绝对普遍性而可以为一切存有之根据,一切存在皆不离良知之创生涵润也。”此即以“良知坎陷”为纲骨对阳明“南镇看花”章的现代诠释!
4 结 语
学界对“南镇看花”诠释有多种,大致遵循“以中解西”或“援西入中”之诠释法,具代表性的观点大致有四:一是将“心外无物”定义为“主观唯心主义”;二是以贝克莱“存在既被感知”而诠释之;三是认为阳明常是从知识的能所关系立论;四是借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诠释。四种讲法均较符合一般人之思考,但笔者认为:“以中解西”或“援西入中”之诠释法本身无问题,但在诠释时需要以原文献之理境为根据,须遵循“整体性原则”,若孤词比附地看“心外无物”一词,则其所指何意本身就不明,以上四种说法或亦有道理,但是否为儒家哲学系统下之“心外无物”则不能确定。因此,对“心外无物”一问题之诠释须站在儒家通过道德实践而开显之万物一体之圆融之境上,或说吾心之良知纵贯地创生万物之实践哲学系统内而进行诠释,不能脱离孔子“践仁知天”、孟子“尽心知性以知天”之大传统,因西方哲学系统中无通过道德实践而扩充“超越之本心”而至“心外无物”之理境,同为实践哲学的佛道两家之义理形态与儒家亦不同也。儒家哲学系统中,“良知本心”是实有、实理,其达成“心外无物”的功夫是积极的道德实践。然佛家所说的心是“阿赖耶识”或“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二者皆不是实有、实理。“阿赖耶识”是如幻如化的染污心,“如来藏自性清净心”是万法之依止处,只能说破除虚妄无明可见自性清净心。故佛家达成“心外无物”的功夫是消极的非道德实践。道家证成“心外无物”的路数大致与佛家相同,是消极的、非道德的,老子所说的“无”只是消解虚伪造作而显的冲虚境界,“无”不是实有、实理。故三家“心外无物”之形态有根本不同。笔者认为,若将“心外无物”放至儒家“道德实践”之大传统下,则以上四种说法便难以立足,他们与由孔孟而来的道德实践之传统不相应。至于牟宗三的诠释,亦带有“援西入中”之色彩,牟先生通过“良知坎陷”一思想沟通并稳定本体界与现象界,建立起“两层存有”的哲学系统。他虽未直接用“良知坎陷”解决阳明“南镇看花”中所遗留的心外如何无物之难题,但是“良知自持其自己可观物之实相,良知坎陷其自己而可观物之现象”之思想客观地回答了现象物如何不离吾之良知而存在的问题,且牟先生的诠释紧扣孔孟“道德实践”之实践哲学体系,不离儒家所言良知本心纵贯创生万物之大传统,如此可还儒家“超越之本心”与阳明“心外无物”以客观面貌。此是儒家“践仁知天”之古义下的现代哲学语汇之创造性诠释。
综上,我们可说:牟宗三对阳明学的诠释是现代性的、是创造性的,但同时又是紧守其规范而忠实客观的,他将阳明“心外无物”“十字打开,毫无隐遁”,可谓学界对阳明学诠释之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