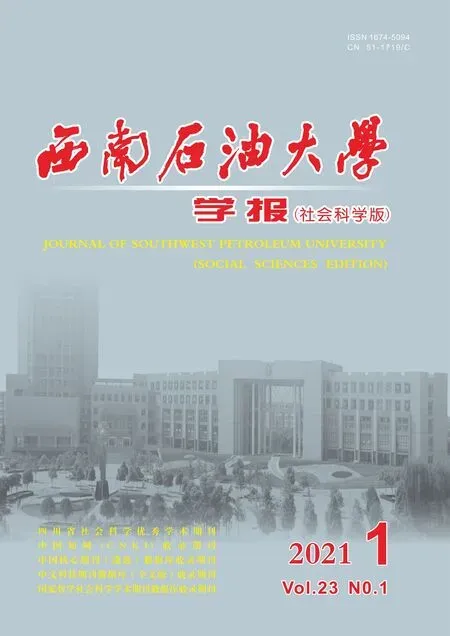新时期中国警匪电影的考索
——从意识形态、现代性体验与新主流话语方面考量
蔡东亮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引言
20 世纪80 年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香港警匪电影通过录像带的方式流入内地,一度成为警匪类型的创作指南和类型启蒙,给人们带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现代性体验。在改革开放后的40 年里,中国警匪电影经历模仿、分离、融合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分别呈现出不同风格特征。当前,警匪电影仍然是中国电影市场的常青树,尤其是近年来的《少年的你》《误杀》《无双》《湄公河行动》《烈日灼心》《扫毒》等优秀影片,更是把警匪电影的创作推向市场的风口浪尖。创作的繁荣,引起热议,也值得研究,中国警匪电影何时潮起?在“红色”类型语境的浸润下,中国是否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商业警匪电影?与好莱坞、香港警匪电影相比,在类型范式与经验上又有何特征?又在各自时代背景下扮演怎样的角色?回答好这些疑问,将是阐释中国警匪电影的关键和重点。
1 警匪电影类型研究的方法:具体性与流动性
同一类型的电影在不同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的背景下亦有所差异。如美国西部片,经百年光影雕刻,已固定一套熟稔的类型样式——拓疆精神、美国神话、纪念碑峡谷等西部元素,被视为美国类型片的麾旗。二战时期德国也拍摄过西部片,20 世纪60 年代更有意大利人拍摄的“通心粉西部片”。比较三者异同,可以明确的是,类型成规趋于一致,但神韵却各有特色。
类型之特色在于神韵,而不在形式,它是类型经验所赋予的独特性表达。当类型经过不断复制、粘贴和演绎,并被固定为某种特定叙事、行为、视觉模式,其内在逻辑的组接便不再依据物质世界,而是把类型经验作为参照坐标[1]。从无到有,从惯例到经验,类型的形成需要积累,而积累的过程又因现实环境的不同而产生细微差异,进而形成类型电影的自我书写,最终在规模化生产的共性中凸显个性,彰显神韵。
安·图德在《类型与批评的方法论》中也表明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类型电影之间的差异并不仅源于影片自身,还存在于特定的文化差异中,对类型的认识应建立在特定的时空之上[2]。因此,具体的现实语境乃至时间节点,都会影响警匪片的创作,抛开创作语境的特殊性而宽泛地研究某一类型电影,既不符合严谨的学理性要求,也非类型电影研究的趋势。
每当学者探索类型片的本质含义,其指称性功能总被反复讨论。无论类型是通用语言、契约关系,还是麦特白所认为的“由制片人、观众等共享的一套期望系统”[3],都在某种层面上揭示类型电影的制作、传播与研讨是基于一种共同认识,即“类型是我们大家相信它该是的那种东西”[2]。
但问题是,类型片的甄别仅仅依靠“相信它该是的那种东西”来界定,是否太过虚无缥缈?它基于何种标准或规则形成一致的经验认同?界定类型的规则或标准是否泾渭分明?大卫·波德维尔与克里斯汀·汤普森在《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中直言:“大部分学者都同意,现在没有一个又准又快的方法来定义类型。”[4]
诚然,对类型片的定义道阻且长,但放弃去定义将会造成另一种更为吊诡的现象——“不易定义,但容易辨认”[2]。或许,类型的暧昧性概念对观众或电影制作人影响甚微,但却对要求学理性的电影研究造成阻碍,形成外延、内涵两空泛的局面,皆不知其具体所指。因此,对类型的研究不应当仅着墨于其所具有的指称功能,更应当注重其词性天然所带有的归纳功能,归纳其具体的类型范式与经验。类型文学研究如此,类型电影研究亦当如此。
考虑到现实语境与时间因素,类型电影不可能保持一成不变,正如电影学者颜纯钧所认为的:类型电影在不断推陈出新,类型的概念也就在被持续建构[5]。对类型电影阐释的价值应当建立于对某一种类型的即时梳理,即一种灵活、动态、具体的研究方法,它不仅强调其类型指称的即时性,亦强调其范式、经验归纳的重要性。只有不断地站在新的时间点、角度重审一段时间内某一类型电影的特征,类型电影的研究才能保障其价值的鲜活生命力。因此,笔者在警匪类型框架下所倡导的是一种动态、即时、具体的研究方法,以此希望来夯实中国警匪电影的基础性归纳,明确其指称及具体内涵。
2 中国警匪电影的界定与流变脉络
2.1 美国警匪片:诞生与演进
警匪片的诞生最早可以追溯至20 世纪30 年代美国强盗片。由于强盗片过多逾越时代观念界限(强调失序与欲望),人们希望通过改良使其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在此背景下,电影制作就从强盗片发展到警匪片,观众对英雄的认同,也从匪徒转移到警察。在片中,匪徒不再受人追捧,警察成为英雄主义新人,情节则着重刻画警匪间剑拔弩张的对立。在影片结尾,匪徒将无一例外地倒在血泊中,而警察将会回到被校正后的美满家庭。这是美国政府经历经济危机后重建秩序、不容外界质疑的一种政治正确的调整。可以说,促成警匪片诞生的是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对失序世界的武力重塑,注定它将成为带有鲜明强意识形态色彩的类型电影。
社会思潮纷繁复杂的20 世纪60 年代,是警匪片发展的另一关键时间。风靡一时的黑色侦探脱下浪漫且绅士的风衣,在黑白颠倒、道义不再的社会里,重新配上警徽、穿上制服寻求正义。但警匪片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像化寓言,是美国神话在西部片后的延续,强调的是主流价值观念的统治力与合法性,与新好莱坞气势汹汹的现代主义反神话、反英雄有明显差异,乃至对立。为了调和冲突,此时的警匪片所塑造的警察不得不站在秩序与反秩序、体制与反体制的混沌地域寻求更高层次的自我救赎,他依靠自由主义的警察守则,依据自己淳朴、善良的品质行事,不再相信政府。警察凭借自身的善良品质战胜邪恶的叙事模式,被布朗概括为校正性主题,它让民众放心,因为美国文化中的优良品质从未消失,并终将战胜敌人获得胜利。它潜藏着一种价值观,教给观众注重家庭和社会责任,轻视让人腐烂的钱权名利。因为英雄的存在,可以矫正误入歧途的世界,警匪电影讲述的就是美国梦如何成真的故事[6]。
20 世纪90 年代的警匪片依旧是美梦成真的神话。略微不同的是,新好莱坞叛逆色彩正逐渐衰弱,警匪片对社会体制的批判,转换为对个别警察的指摘,出现一批黑化警察、表现警察内部斗争的影片,警匪的二元对立被改造为好警察与坏警察的对峙。虽然匪徒的作用被压缩,甚至消失,但依旧延续美国警匪电影的核心——自由主义标准下的正邪博弈,有人将这一类影片称为警察片。
综言之,好莱坞警匪电影包含两个基本子类型——警匪片与警察片,警匪电影的本质特征是国家意识形态矫正经济危机(经济社会)失序情况下的文化产品,带有鲜明的古典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倾向,强调公平、公正、自由等现代价值观。
类型成规方面,布朗将警匪类型概括为五点[6]。一是叙事模式化。主人公是一位具有崇高理想的警察,侦破案件寻找真相是他的唯一使命,他必须对坏蛋以暴制暴,又要求自己化身白马英雄保持平凡与伟大的统一[7]。二是图像符号化——城市与枪。警匪类型把城市作为欲望的舞台,枪被指认为是男性的身份象征,既是身体的,也是文化的,不仅代表男性怒不可遏的威严,更是自由主义精神的象征。三是匪徒、警察英雄化。一般而言,警匪片只打造主流社会认可的警察英雄,但随着警匪类型不断向现实深度靠拢,警察英雄已不能满足观众对社会复杂性的想象,类似《盗火线》《变脸》等塑造警匪双雄剑拔弩张对决的影片成为一种新风尚。四是打斗仪式化。警匪电影终将迎来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打斗和英雄式的凯旋,胜负的分晓只在光影一瞬间,坠楼、葬身火海、饮弹自尽等高度仪式化的结尾,似乎都在迫不及待地宣布主流意识形态的胜利。五是意识形态功能化。警匪片的潜藏文本通常被解读为质疑或批判社会制度,但无论如何,匪徒终将在高度仪式化的结局中被消灭,秩序与失序、个人与集体的冲突与矛盾也随即被象征性解决,校正性主题得以实现。
2.2 “反特片”:并非一种警匪类型
以好莱坞警匪电影作为原型参照,在中国电影百年漫长的岁月长河里,在“红色”类型语境的浸润下,中国是否存在警匪电影?它何时潮起、何时潮落?章柏青、贾磊磊的《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认为中国警匪片类型有反特片、警匪片与公安片[8],它们是否属于本研究讨论的警匪电影?与好莱坞、香港警匪电影相比,它们有何特征?又在各自时代背景下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些疑问将是阐释大陆警匪电影的重点。
笔者不赞同将反特片纳入警匪电影。按照章柏青、贾磊磊的观点,反特片存在于20 世纪50 年代至80 年代中期,如表现境外特务对新政权颠覆的《无形的战线》《羊城暗哨》《南海的早晨》,反映对党内敌对分子斗争的《神圣的使命》《405 谋杀案》《戴手铐的旅客》等。需要承认的是,单从类型成规上看,反特片与警匪电影具有一定相似性——象征主流意识形态身份的执法人员、代表男性气质的枪械驳火与你来我往的斗智斗勇,的确容易让人混淆。但从时间线上看,反特片起始、贯穿于红色政权政治意识最为浓烈的时期,结束于改革开放的20 世纪80年代,因此,它是一种有着强烈意识形态导向的类型片,“包含一个基本冲突,即新生政权对敌对势力的斗争”[9],并“通过反特片的一次次演绎,使观众明白,只要时刻保持警惕,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那么再强大的敌人都能战胜”[10]。反特片所拥有的强烈的意识形态底色,是冷战格局下人类社会两种价值观的斗争。这两种价值观斗争的严峻形态必然在国内被引申为一种文化想象:狡猾的特务与意志坚定的主角通过不断构建与强化通俗易懂的二元对立关系,重申国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然而,作为商业电影存在的警匪类型电影,时刻注意避免纯粹、浅显地强调某一种政治观念的合法性,更多传递的是现代经济社会的普适性价值观,弥合的是国族与区域间的社会性裂痕,但不包括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裂缝。因此,即使反特片与警匪电影在类型构成要件上趋于一致,但仍然缺乏警匪类型的独有经验,故不应被纳入警匪电影的考察范围。
2.3 公安片:一种中国特色的警匪派生类型
如上所述,警匪电影的本质特征是国家意识形态矫正经济危机(经济社会)失序情况下的文化产品。孕育它诞生的社会背景,一定是以经济为导向的现代社会,而非政治导向社会。有学者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电影类型的多样化也是电影题材选择丰富的一个表现,比较典型的有公安热[11]。公安片在类型成规上和警匪片有着极大相似性,如:警察抓小偷、小偷被绳之以法等基本叙事模式,以及手枪、追逐戏、夜幕下的城市等基本视觉图谱。
邓小平在南巡谈话时指出,要一手抓经济改革开放,另一只手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段话点明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发展的两条红线——经济与法制建设。公安片就是两条路线杂糅下的产物,安抚改革开放初期所面临的未知恐惧,解决社会转型所遭遇的矛盾。因此,无论是类型惯例,还是类型经验,公安片都切合警匪电影的类型系统,是“有着鲜明中国特色的‘警匪片派生类型’”[12]。
改革开放为公安片提供了较为健康、稳定的经济取向型社会环境,香港商业电影也通过录像带、配额发行、合拍片等形式陆续进入中国内地。“讲究动感、节奏明快,用流畅、激烈的视觉效果给人以强烈新奇的视觉感受”[13],成为警匪样式呼之欲出的创作标准。但公安片并未抓住时代契机,使自身完全类型化、商业化,政治意涵、教育风格意味仍然浓郁,以一个或几个警察的工作生活作为主线,警匪斗争作为副线,通过警匪对垒或恶性犯罪弘扬法治精神、歌颂人民警察。它们既无法同主旋律电影一样,把宣传教化敞开来表达,亦无法完全商业类型化,在政治性、艺术性与商业性的三方拉扯中,蜻蜓点水,各取一瓢。进入20 世纪90 年代后,在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倡导下,公安片正式进入主旋律电影的创作谱系,警匪类型彻底沦为空架,匪徒沦为背景。一批讴歌人民警察,表现其工作险恶、政治坚定、生活俭朴的影片应运而生,如《龙年警官》《警魂》《警官崔大庆》《天生胆小》《红杜鹃白手套》《刑警张玉贵》等。
如果说公安片是有着鲜明中国特色的警匪片派生类型,并未实现严格意义上的类型化、商业化,那么,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出现的警匪片,如《绞索下的交易》《峨眉飞盗》《蜜月的阴谋》《飓风行动》《最后的疯狂》《代号美洲豹》《女神探宝盖丁》则彻底抹去了宣传教化,加入飞车、追逐、枪战等商业元素,一种动感、时尚的商业气息迎面扑来。
2.4 警匪片:市场经济环境压力下的转型
警匪片作为警匪电影的主要类型,在中国20世纪80 年代中期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对娱乐片的重新思考,譬如1987 年电影学界对娱乐片的大讨论;另一方面是电影市场对娱乐片的大量需求,“娱乐片的产量实际已超越当时中国电影年产量的50%”[14]423。可以说,20 世纪80 年代中期类型电影观念及市场的转向,是公安片蜕变为警匪片的直接原因。
20 世纪90 年代的警匪片因为合拍片(协拍片)的融入而有所变化,形成了两种路线的警匪类型。一种是由境外与大陆合拍的商业警匪片,如《联手警探》《中华警花》《特警神龙》《狭路英豪》《天网行动》《霹雳神鹰》《怒海威龙》《追金行动》等。在合拍片(协拍片)中,内地与香港互动频繁,自然而然地打上港式警匪片的烙印,其优点在于进行完全商业化的尝试,形成传统意义上的警匪片。另一种是内地摄制的警匪片,如《出生入死》《猎豹出击》《黑色走廊》《缉枪行动》《“冥王星”行动》《特警出击》《黑狮行动》等。这些由内地单独制作的警匪片,无外乎是20 世纪90 年代娱乐片浪潮下跟风的产物,融入了枪战、爆破以及搏斗等类型元素,但并未考虑本土警匪类型经验的特殊性,只是简单将香港警匪片的类型元素复制拼贴,题材大都涉及跨国、跨区域犯罪,以迎合彼时观众对现代性的想象。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警匪电影历经岁月的淘沙,风格、样式都几经变化。但无论如何改变,充其量只是两种基本类型——公安片与警匪片内部的翻转腾挪:公安片重人物及意识形态,警匪片重情节与类型元素。把握住这两个基本类型的发展及特征,也就摸准了40 多年来中国大陆警匪电影的创作脉搏。
3 20 世纪80 年代的中国警匪电影:类型起源与意识形态偏移
改革开放后,国家重心由政治属性转为经济属性,各种思想、价值观念面临新挑战,不仅有冷战格局下西方价值观念的外部冲击,也有“文革”时期所遗留的内部痼疾。因此,当中国打开国门,解放思想,放下长久以来所背负的政治包袱,准备迎接新秩序、新社会与新形象时,老百姓紧绷的弦却在前所未有的自由氛围下瞬间崩断,导致犯罪频发。在此背景下,警匪电影有了创作的空间。
3.1 改革开放背景下的类型起源
改革开放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相当特殊的地位,解放思想意味着中国摆脱政治上的精神包袱,将全社会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上,通过经济转型的方式,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因此,经济与市场成为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关键词。然而,社会的转型需要付出代价,虽然经济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改革开放相对自由的政治氛围下,十年“文革”动荡所遗留的沉疴痼疾逐渐显现。因而,对民主和法制的要求,乃是亿万人民发自内心的呼声[15]。“文革”破坏了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更重要的是,“砸烂公检法”的畸形社会观念严重滞缓了中国的法治文明建设。
在这一背景下,在20 世纪80 年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折期中,犯罪现象有所抬头,严重危害了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亟需经济发展与法治建设共同进步的时代背景,成为促使中国警匪电影诞生的直接原因。罪犯的猖獗是中国警匪电影与好莱坞古典强盗片(黑帮片)诞生背景的共同点,但不同的是,在中国特殊的现实语境下,中国大陆导演无法将传奇故事搬演至荧幕。美国强盗片中的匪徒身上带着鲜明的个人自由主义,他们既与代表秩序的警察搏斗,也与其他匪徒火拼,使其犯罪行为超出常规意义的犯罪,成为自由的象征。而在中国大陆的类型语境中,从来没有塑造秩序破坏者(匪徒或强盗)为主角的先例。即使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这条创作铁律依旧不可撼动,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是集举国之力进行的社会转型,集体主义与秩序的维护是保障现代化进程的前提,在某种程度上已上升为一种国家意志。冯小刚曾言道:“《天下无贼》用贼做主角,这是之前绝对没有的,你在歌颂谁?”①冯小刚:没说过“没有提案”发言绝非“炮轰”[EB/OL].(2013−03−08)[2020−05−06].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3/0308/c172318-20718127.html.因此,创作者尽可能地避免让观众对坏蛋产生一种复杂的情感,即使同情也不允许,最后只剩下恨与厌恶。这样一来,罪犯的形象一定是扁平化的,甚至没有人物性格,其犯罪过程几笔带过。警匪电影的核心张力——警与匪之间紧张、胶着的对峙,在类型起源之际就被弱化,其所孕育的也只能是有着鲜明中国特色的警匪电影——公安片,如《神女峰的迷雾》《508 疑案》《蛇案》《梅山奇案》等。
3.2 20 世纪80 年代警匪片意识形态的偏移
改革开放后,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史观潜移默化地取代着革命史观,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观念,西方启蒙主义、自由主义理论涌入中国思想阵地,但其中影响最为深刻的无疑是现代化理论。雷迅马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批美国学者所建立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并不只是人文社科的一种观点或学说,更重要的是它成为冷战格局下,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外交、军事、贸易对抗或打压苏联与第三世界发展的一种意识形态武器②参见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M].牛可,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20 世纪80 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大到国家政策,小到文艺流派,都能感受到鲜明的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意识形态烙印。最为典型的话语方式,就是形成一系列二元对立结构——中国传统/西方现代、文革/新时期、科学技术/封建迷信、愚昧/文明。就文艺界而言,80 年代前中期,在现代化观念的影响下,出现多个学科的文化反思热潮,譬如“文学领域的‘反思文学’向‘寻根文学’的转移,‘现代派’小说、先锋小说的出现和‘现实主义诗群大展’及号称‘pass 北岛’的新生代诗群;以及其他艺术领域内的诸如‘第五代电影’”[16]。但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红色基因已成为中国人民的一种信仰。因此,在80 年代初期就有多次关于现代化或城市化姓“资”还是姓“社”的讨论,而电影理论界关于娱乐片的大讨论,从根本上来说,也是类似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
直到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基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相继取得成果形成的外部压力,电影显现出资本、发展导向的偏移。以娱乐片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电影的生产体制和机制”[14]425,其“产量实际已超越当时中国电影年产量的50%”。市场上的成功,成为中国电影导向发生偏移的佐证。如果说“五代导演”的作品,如《黄土地》是通过否定传统文化表达意识形态的偏移①这里的传统文化不仅仅是指中国传统文化。按照“经典现代化理论”的观念,以传统/现代的二分法认识中国大陆,建国至“文革”的现代化尝试都被定义为“传统”。,那么80 年代警匪片则是通过构建现代性展示、建立发展信仰的价值观念,在思想和文化领域超越“左”“右”、强势/弱势的对立,从而使发展、现代化成为社会共识。
具体来看,80 年代我国的警匪片主要通过两个方面实现意识形态的偏移。一是利用高楼大厦、枪支、酒吧、霹雳舞、汽车等现代视觉图谱的展示,迫使观众切断自身与传统的联系,而沉浸在现代性想象中。比如滕文骥的《飓风行动》,开头便是展示现代中国工业化的一面——轮船、汽车等交通运输与矿业生产。警匪追逐戏码,一般选择手持跟镜头拍摄,保持中景或近景,以便捕捉人物的神情与动作,但《飓风行动》却采用全景摇、移镜头,让观众快速浏览现代性城市的发展面貌。从这一点看,或许编导的意图根本不在激烈、紧张的追逐中营造氛围,而重在展示一种现代性的观赏效果。另一种实现意识形态偏移的方式,则是对红色类型惯例的改写,减弱其类型经验的影响力。在以往反特片或间谍片甚至公安片中,警察即秩序维护者,罪犯即破坏者。在此惯例的影响下,我国电影形成的一套类型经验是:警察理应受到弘扬与赞美,甚至无所不能,总能将罪犯在最后一刻绳之以法。但在80 年代为数不多的警匪片中,有两部影片对此类型惯例与经验做出了改写:警察不一定是秩序的维护者,他也有可能是秩序的破坏者,尽管是无意的。例如,《女神探宝盖丁》就讲述了一个边缘型警察的故事。影片第一次让中国警察的形象发生改变,即警察也可能是秩序的破坏者,甚至是罪犯,让人们认识到警察始终也是一个人,他也有恩怨情仇。此外,《蜜月的阴谋》也是一部对红色类型改写的影片。在以往的类型经验中,罪犯在结尾一定会被代表秩序的警察所击毙,或被绳之以法,但在该片的结尾,警察面对幕后黑手(注:市政府的陈秘书)只能放其逃走,罪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以上两部作品都以极大的想象力,颠覆了作为革命秩序维护者的警察形象。在影片中,创作者希望通过极具反差的警察的形象,迫使观众割断与以往类型经验的联系,坦然地接受新时期语境下的类型经验与意识形态的偏移。
4 20 世纪90 年代的中国警匪电影:主流意识形态、现代性体验与跨国想象
20 世纪80 年代后期,中国电影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格局,艺术片、娱乐片与主旋律电影三强鼎立,艺术电影式微,市场(娱乐)与主旋律(传统意识形态)逐渐成为两种主导叙事逻辑。而90 年代我国警匪电影的两条分支——公安片与警匪片,恰好分别对应这两种主导逻辑。
4.1 回归主流意识形态的公安片
20 世纪80 年代公安片的困局在于,在对警匪类型范式掌握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就试图兼备电影的意识形态教化与商业盈利。直到1987 年电影局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提倡“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后,公安片才找到表达的出口。事实上,主旋律电影的提出,可以视为对之前意识形态混乱格局的拨乱反正。如上所述,现代化发展本质上含有“意识形态西方中心论、一元单线的历史观”,它在80 年代造成意识形态的偏移,进而导致我国的类型电影开始追求现代性或现代化的展示,辅之80 年代宽松自由的创作环境,催生了一大批媚俗、艳俗、粗制滥造的影片。因此,“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提出,自然成为历史逻辑演绎的必然。
在此期间,公安片以警匪间的博弈为基本框架,重点刻画警察的人物形象,通过表现其工作与生活,讴歌赞美警察不畏艰险为人民服务的信仰。以《龙年警官》为例,该片用显性和隐性两种不同方式,塑造出警察是社会主义价值观践行者的形象。在人物形象上,影片并没有按照类型经验,把刑警队长傅冬塑造为无所不能的神,而是充分赋予傅冬丰富的情感生活,把警察当做也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普通人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时需要身先士卒,独自承受伤痛;普通人面对繁如星辰的案件时,无法安顿自己的家庭;普通人拿着微薄的工资,干着“拼命”的活。影片的优秀之处在于,它改变了传统的弘扬警察廉洁为民的刻板宣教方式,而是先让其成为一个人,在关键时刻再推向神坛,观众在具体且生动的情景中,得以切身体会警察的艰辛与奉献精神。
如果说一部优秀的警匪片应该有孤胆英雄或白马英雄,以此符合西方意识形态所弘扬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满足观众尤其是男性观众的英雄梦,那么一部好的公安片则应当塑造生动且感人的警察群像,并以此来弘扬集体主义精神。《龙年警官》就塑造了这样一批可歌可泣的警察:男性之间有摩擦却不影响团结、女警爱慕男警却在最后懂得放手成全、团队既能相互调侃又能在犯罪现场出生入死。集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期的背景下尤为重要。无论是“四个现代化”,还是城市化,要实现物质文明的进步,必须要集全社会的力量来完成。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集体主义应作为重点,通过故事与镜头语言渗入观众的潜意识。该片最后,导演还是通过传统的显性宣扬的方式给影片定性:傅冬率副队长史建新及刑警刘伟抓捕罪犯,但史建新失手摔倒在地,惊动匪徒,双方展开激烈的搏斗;最终匪徒被拿下,但刘伟也因公殉职;傅冬抱起刘伟,在高度仪式化的白雾中,走向脱帽致敬的同事。
4.2 20 世纪90 年代警匪片的现代性体验与跨国想象
一般而言,学界把1978 年至1993 年期间划为我国市场经济探寻阶段,当时人们是摸着石头过河,对现代化或发展主义还有所顾虑,各种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多发生在80 年代。然而在90 年代,尤其在1993 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后,党中央“提出建立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17]。这就意味着从90 年代起,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已经超越意识形态的冲突格局,从实际操作层面上升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改革目标的提出,发展主义、现代化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与警匪片的现代性底色不谋而合,继20 世纪80 年代警匪片的现代性展示后,这种现代性在90 年代很快就由展示演进为体验,观众可以沉浸在林林总总的现代化物件中,并对其展开想象与审美。此时,类型惯例较80 年代警匪片更加类型化,人物更加立体,视觉景观充满想象力,整体弥漫着新潮、商业的气息。
当然,20 世纪90 年代的中国社会,虽然身处经济快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但多数中国人却无法感受现代性体验。实际上,对现代生活的日常体验并不是根本体验,而是“按照意识形态或文化传统来看待世界”[17]。生活在90 年代中国社会的观众,难免受到发展主义与现代化建设等理性逻辑的约束。为了消除被遮蔽的部分,西美尔提出,现代性体验是一种审美活动,时尚、新潮的元素可以刺激这种审美活动,就像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电影所呈现的玻璃橱窗与女明星的诱人身姿。90 年代的警匪片就好比橱窗。一方面,银幕的存在巧妙地在虚拟与现实之间构建起一种暧昧的距离。对于观众而言,通过视觉与听觉的共同作用,高楼大厦、洋房泳池、咖啡酒吧、汽车追击,既触手可及,又可望而不可及。观众通过沉浸在警匪片时尚化、现代化类型元素中,获得一种持续的幻觉体验,进而激发对现代化社会的渴望。另一方面,警匪片类型惯例所要求的现代性元素,无一不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匪徒和警察冲突的原始对决,被置于物质文明发达地区——上海、广州、香港,就如同将野蛮装进精致的玻璃瓶:雄伟靓丽的大厦、窗明几净的建筑、典雅华丽的现代着装、灯红酒绿的酒吧歌厅、代表现代工业想象的汽车追逐与枪械装备,以诱人、傲人的姿态穿插于警匪故事中。这种现代性体验,在发展主义等主流意识形态的加持下成为一种毫不遮掩的勾引——对现代性文明、被压抑人性的渴望。在眩晕的现代性照耀下,文明与原始、克制与欲望、秩序与失序的抵牾,不仅不面目可憎,还显得几番动人。
客观地讲,我国自改革开放后,大到国家政策小至文艺创作,都显现出一种理性、批判性思维逻辑,以及对科学技术的崇拜,最典型莫过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主流话语。这种“崇实尚行、试错创新”的理性回归[18],在一定程度上成为80、90 年代的主导性逻辑,帮助中国在改革开放短短20 年里取得傲人成绩。但成就任何一件事都需要付出代价,现代化进程同样造成了一种可怖的现象——科学主义与理性主义横行,进而导致中国人逐渐远离对传统诗意、美学与精神的追求。就电影而言,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艺术电影在90 年代的式微。人在这样高速发展且崇尚理性、科学的社会中,与现代性产生了一种微妙的距离:一方面,观众对警匪片中的现代性体验感到惊奇,希望靠近并体验现代性,对其展开联想;另一方面,观众又害怕触及现代性,觉得这些电影太假[19]。归根结底,这是个人畏惧落后于国家现代化发展步伐的一种心理表现。
当然,这也是一种类型经验,反映的是中国观众或制作者对警匪片中所展示的现代性想象的既爱又恨。比如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香港,在20 世纪90年代的中国警匪片中,首先是“象征了经济、科技、文化‘先进’‘发达’‘美好’的符号,成为代表社会进步的终极标志”[20],其次才象征欲望、堕落、法外之地。具体而言,在90 年代,无论是在合拍的警匪片中,还是在内地单独摄制的警匪片中,香港都代表文明与进步,常常借助内地警察的视线描绘出其城市的繁华与美好。同时,香港又是罪犯的滋生地,其基本叙事模式可以总结为:香港罪犯潜逃至中国大陆做案或暂避风头,香港警方与大陆警方合作(如果是男女警察合作一般表现英雄救美,比如于荣光、郭秀云、宁静主演的《联手警探》;若是男男合作则表现香港警匪片经典套路兄弟情义,如周晓文导演,姜文、万梓良主演的《狭路英豪》),随后警匪双方在香港或内地展开激烈搏斗,匪徒因大陆警察的严格执法而意图逃回法制宽松易于滋生犯罪的香港。
20 世纪90 年代我国警匪片的跨国想象也是现代性体验的一种。经典现代化理论是一种带有西方意识形态的工具,其最大的作用就是帮助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建立了一套西方价值观念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与贸易体系,若第一或第二世界希望加入全球化的游戏,那么必须由西方意识形态所建立的价值标准评判其是否已经达到一定现代化的规模。简而言之,现代化成为了全球化游戏中的一张通行证,而西方国家既是裁判,也是运动员,其他国家若能参与全球化并成为其一部分,则是裁判对这个国家现代化经济发展水平的肯定与褒扬。因此,90 年代我国警匪片所表现的跨国犯罪与追捕,不仅在于异国奇观的展示,更是90 年代华夏儿女对中国崛起的民族想象,“一种‘无国界’的想象被全球性的犯罪与反犯罪的过程所连接”[21]。
5 “北上”变奏与新主流话语:新世纪以来合拍警匪片的创作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警匪片大多以合拍的方式得以存续,如《大事件》《三岔口》《男儿本色》《证人》《线人》《枪王之王》《毒战》《寒战》《湄公河行动》等。诚然,香港电影对大陆电影市场功不可没,许多坊间故事得以在台面重现。这固然值得为之一振,但毕竟是两种意识形态下的文化冲突,在打起火花之前,也存在长时间的磨合,最典型的就数港式警匪片“港片不港”的尴尬。
5.1 从“热血”到”冷峻“:港式警匪的“北上”变奏
1997 年,香港回归前,香港警匪片贯彻的是港式人文理念,表现人在现实环境下的生存状态。警匪的符号可以是很简单地象征正邪两立的《警察故事》,也可以是道德情义模糊警匪界限的《英雄本色》。无论哪一种,都带有香港警匪片黄金时期的鲜明特点——道德伦理、兄弟情义与感性快感。
CEPA(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英文简称)签订后,在中国大陆市场资本的运作下,香港导演面临两个选择——“北上”融合与本土留守。在资本的号召下,多数香港导演选择“北上”,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港式人文理念的叙事逻辑既不能在内地的社会、政治语境下畅通无阻,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寻找到与内地主流价值合谋的出口。为快速适应新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审查机制,影片常常在这种外部压力制约下简单地填充一些真善美,但大多都是生搬硬凑、阿谀逢迎,所以显得格格不入。对于合拍警匪片来说,“偏理性冲动被置换成了偏智力游戏,偏情感体验被置换成了偏思维愉悦,与此同时,价值指认系统也被置换成了社会秩序”[22]。
例如,《寒战》在外包装上是典型的港式警匪片,但其内核已经发生叙事逻辑的偏离,更倾向于当代观众所熟悉的韩国犯罪片,突出对公权力与制度的反思。在该片中,警队高层间的斗智斗勇以及廉政公署的戏份,似乎都在暗示寒战与政治黑幕剪不断理还乱的暧昧关系。从港式人文关怀下的伦理情义到冰冷制度的权力阴谋,从热到寒,这是香港警匪片融入大陆社会语境的筹码交换,也是一次割肉之举,即通过牺牲港式警匪片一贯的叙事逻辑与经验,换来了一次并不讨巧的类型升级。
5.2 新平台:新主流话语的建构
就内地而言,自1987 年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倡导后,虽偶有《开国大典》《焦裕禄》《孔子》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商业片,但总体而言,还是看重电影的意识形态属性,弱化艺术性与商业性。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基于市场压力,主旋律电影也悄然发生变化。所谓的主流大片或者新主流大片,替代了以往主旋律的称谓,内涵指称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群体的意识形态,而是体现一种普适性的主流价值观,在原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传统价值观念的基础上,通过加入一些西方普世价值观以向市场靠拢,同时通过启用明星、制造奇观性场面,期望在类型化的基础上与主流观众达成主流价值观念的共识。
当前,主旋律电影的困境是如何实现商业化,而港式合拍片的尴尬之处在于,若保持所谓香港制造的本土性则会遭遇意识形态或审查机制的冲突,抛下本土性亦会招来“港味不港”的指摘。二者的诉求明面上看似互补,实则暗流涌动,长时间难以兼容的现实情况似乎预示二者需要一个新的话语平台来搭建两种文化表达的共同认识。与以往的话语平台不同的是,新平台并非只赋予特定群体或政党表达话语的权力,它还应将古今中外凡是有益于表达人类真挚情感的价值观念统统囊括其中。
警匪片作为一种强意识形态电影,必将在新主流电影或新主流话语中承担重要作用。最典型的即为林超贤的《湄公河行动》,影片起码完成两个层面——中国电影与国家层面、中国与全球秩序层面的新主流话语论述。首先,在中国与全球秩序层面,完成国家强势主流话语的表达。20 世纪90 年代我国警匪片的现代性体验中的跨国想象,是带着请求的姿态参与第一世界主导的全球化游戏,并期望得到西方世界的重视与认可,这离不开当时中国社会身处改革开放初期、积极寻求国际地位的历史语境。随着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尤其是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的优越性促使中国实现了2008 年后的经济腾飞①参阅复旦发展研究院《中国崛起是因为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个误解》,http://fddi.fudan.edu.cn/yanjiu/guandian/5810.html.,以及近年来实施的以“一带一路”为中心的走出去战略布局,《湄公河行动》讲述中国公安跨国执法的故事,就从当初期待进入全球化秩序,逐渐走向与秩序共融并宣示中国政府保护中国人民财产和生命安全的决心。
国家与全球秩序间强势话语表达的前提是观众的认同,尤其《湄公河行动》首次涉及成规模的公安跨境执法,如何让观众在刻板、生硬的政治说教外,也能对国家、民族的意志产生高度认同,成为影片制作者首先需要考量的问题。这就引申出中国电影与国家层面的新主流话语——国家意志与个体欲望的有机缝合。因此,《湄公河行动》中的警察形象,从领导到一线干警全部展现出一种浩然正气,都在各自的位置上承担着人民赋予的权力与义务。当然,影片并没有像以往的主旋律电影那样将警察神化,抽烟、粗口、斗狠都成为片中警察的日常生活状态。这样一来,反而使片中的警察获得了一种真实的质感,当危机来临则重拾道义与责任,惩奸除恶,成为现实存在的真实个体。此外,方新武作为影片中唯一的“灰色警察”,先有刑讯逼供,后有公报私仇,体现了一些边缘化处理的特点。但导演又聪明地表现了他大仇得报后的纠结与苦痛:随着方新武驾驶快艇冲向毒枭,卧底警察与毒枭同归于尽。这样处理,不仅升华了人民警察的高尚品格,也使方新武完成了“灰色警察”的主流化转型。
6 结语:从博弈到分立再到融合的大陆警匪电影创作
综上所言,大陆警匪电影其实就是公安片与警匪片两种类型的翻转腾挪。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中国经历了一次从政治主导型社会向经济主导型社会的转变,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倡导下,长期被“政治高压”束缚的中国民众突然获得了空前的自由,无所适从的茫然感油然而生,大批下乡或待业青年走向街头,引发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犯罪激增。因此,为了经济转型的顺利完成,影视作为一种大众媒介必然承担引导、疏通之功用,于是公安片携带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在20 世纪80 年代初首次登场。但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早在80 年代初,在经济改革的浪潮下,合拍片《少林寺》(1982、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垂帘听政》(1983、中国大陆/中国香港)、《火烧圆明园》(1983、中国香港/中国大陆)在中国大陆产生巨大影响。尤其是《少林寺》1982 年在内地上映取得了1.6 亿元人民币的票房记录,商业意识的种子从此开始在中国落地生根。但是,两种社会现象对应两种诉求,商业性与意识形态成为缠绕公安片的两股麻绳,在缺乏相关类型经验的基础上,公安片的创作者试图兼得,必然造成“四不像”的结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话语权得到不断提升的同时,在席卷而来的娱乐片狂潮下,比公安片更加类型化、商业化的警匪片应运而生,时尚化的视听元素成为警匪电影商业化的表征。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的警匪电影的创作因加入曹保平、高群书、丁晟的作者化创作风格,而变得更为复杂,甚至出现商业、艺术与意识形态三方间的拉扯:艺术与主旋律倾向的警匪电影,在类型上缺乏可复制性,在获得口碑的同时也失去商业性;而作为商业片代表的港式警匪片,因大陆社会语境与审查机制的差异,也遇到自身发展的尴尬,即所谓“港片不港”的进退两难。当前,种种迹象无一不显示出我国警匪电影创作瓶颈阶段的来临。这需要一个具有更大包容性的话语平台来融合各种诉求,而中国近10 年天翻地覆的变化,正好提供了时代契机。于是,包含传统主旋律价值观、西方普世性价值观、中国新形象与“中国梦”等时代核心命题,并兼容商业性、国家意志的新主流话语或新主流大片,在一片欢呼声中高调亮相。基于新主流理念而制作的警匪片《湄公河行动》自然将我国警匪电影的创作提升到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