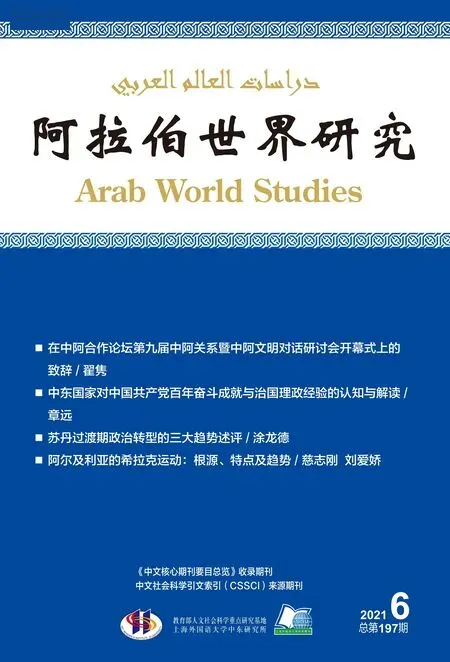阿尔及利亚的希拉克运动:根源、特点及趋势*
慈志刚 刘爱娇
2019年希拉克(Hirak)运动在阿尔及利亚的爆发,这打破了阿尔及利亚自2010年中东变局以来的稳定神话。随着希拉克运动发展迅速,民众的抗议活动席卷全国并危及政府统治,执政长达20年之久的布特弗利卡总统也因此退出政治舞台。这场突然爆发并迅速发展的民众抗议活动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观察和审视这场对阿尔及利亚政局产生剧烈冲击的运动,并进行了热烈的争论,但就希拉克运动根源、特点与发展趋势等核心问题而言,尚有需要更深入进行学术讨论的空间。
一、问题的提出
(一)什么是阿尔及利亚的希拉克运动
希拉克系阿拉伯语,意为运动,阿尔及利亚人称之为人民运动或微笑运动,西方学者称之为“阿拉伯之夏”(Arab Summer)。阿尔及利亚的希拉克运动是2019年2月布特弗利卡宣布将继续参加总统竞选所引发的民众抗议运动。自1999年当选以来,布特弗利卡已执政近20年。2013年布特弗利卡中风后,民众普遍认为当下的政治制度是“伪民主制度”,在这一制度之下的任何选举结果都可以轻易预测。①Frédéric Volpi,“A lgeria:When Elections Hurt Democracy,”Journal of Democracy,Vol.31,No.2,April 2020,p.153.低迷的经济和晦暗不明的政治前景加深了人民的忧虑,抗议活动就此爆发。2019年2月至今,希拉克运动依照其政治诉求的变化,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围绕总统选举的希拉克运动。2019年2月22日,全国多个大中城市爆发希拉克运动,民众手持“没有总统,只有画像”的条幅聚集在街头。官方没有公布参加抗议的人数,但有学者估计,2月22日的抗议人数约为80万人。②“2019-2020 Algerian Protests,”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19-2020_Algerian_protests,上网时间:2020年5月30日。随后几周内,阿尔及利亚的街头出现数以百万计的民众走上街头表达不满。尽管布特弗利卡总统做出让步,称这将是最后一次参选并且不会完成第五任期,但抗议者并没有因此放弃。至4月2日,布特弗利卡正式辞职,根据宪法规定,在总统选举期间将由阿卜杜勒卡德尔·本·萨拉赫(Abdelkader Ben salah)担任临时代理总统。布特弗利卡辞去总统标志着希拉克运动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抗议者并没有因此停止街头抗议,而是把抗议的矛头指向了总统背后的政治精英。迫于抗议形势以及候选人条件不佳等因素,政府取消了原定于7月份的总统选举。当局为了安抚民众,随即展开了以布特弗利卡政府主要人物为目标的反腐行动。9月15日,政府宣布将进行总统选举。抗议者高举“黑帮选举”“腐败统治集团举办选举是给傻瓜下圈套”的标语以抵制总统选举,并要求代总统萨拉赫以及政府内布特弗里卡集团的官员辞职。12月12日,总统大选如期举行。12月16日,宪法委员会宣布,阿卜杜勒马吉德·特本(Abdelmadjid Tebboune)以58.15%的选票胜出,当选阿国总统。①Merrit Kennedy,“Algeria Elects:A New President in Controversial Election,”National Public Radio,December 13,2019,https://www.npr.org/2019/12/13/787789940/algeria-elects-anew-president-in-controversial-election?t=1599006813749,上网时间:2020年5月20日。但官方统计显示,这次选举的投票率仅约40%,特本总统的政治合法性受到普遍怀疑。
第二阶段是关于全面改革的希拉克运动。特本就任总统后,宣布将进行改革,但这仅是重申了2011年布特弗利卡改革措施,并不能够为新总统赢得普遍支持。人们认为,特本是布特弗利卡的忠诚支持者和军方看中的人选。因此,在2019年12月末的骚乱中,抗议者要求将当前的政治体制彻底清除。②Bina Hussein,“Energy Sector Diversification:Meeting Demographic Challenges in the MENA Region,”Atlantic Council,January 1,2020,p.5.2020年年初突然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动荡的阿尔及利亚带来了新的考验,国家面临更为严峻的局势。聚集在街头的抗议者加速了疫情的传播。3月17日,特本总统在电视上宣布,为了防止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禁止一切游行。这项防控疫情的必要措施引发了抗议者的怀疑,他们认为这只不过是政府为了阻止他们走向街头的策略,而且抗议者采取了防护措施,比如戴口罩和手套。在总统宣布禁令的当天,仍有数百名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受访者萨米拉·梅苏奇(Samira Messouci)称,这种病毒在全世界都存在,世卫组织没有将阿尔及利亚列为危险国家,政府只是“拿出冠状病毒的故事”来阻止希拉克运动。在她看来,唯一真正的危险是政府试图维持权力。③Farid Alilat,“Algeria:Hirak at the Time of Coronavirus,”The Africa Report,March 24,2020,https://www.theafricareport.com/24997/algeria-Hirak-at-the-time-of-coronavirus/,上网时间:2020年6月8日。但是,希拉克运动的主要支持者,包括被监禁的活动家卡里姆·塔布(Karim Tabbou)、人权律师穆斯塔法·布查奇(Mustafa Bouchachi)和前部长阿卜杜拉齐兹·拉哈比(Abdelaziz Rahabi),都敦促抗议者暂停游行,避免政府以此为借口进行打压。3月20日,阿尔及利亚抗议者首次没有在周五举行反对统治精英的示威游行活动。但是,希拉克运动并没有因为不能上街游行而停止,抗议者在社交媒体上依然很活跃。不久之后,人们再次走上阿尔及利亚街头进行抗议并持续至今。
(二)关于阿尔及利亚希拉克运动的学术争论
希拉克运动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该运动发生的原因,呈现的新特点和发展趋向进行了探讨,综合起来有以下三类观点。
第一,“阿拉伯之春2.0版”。自2010年年底起,中东地区政局风云突变。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政权先后更迭,其连锁反应搅动了整个地区的政治生态。西方将这一政治现象称之为“阿拉伯之春”。西方提出的“阿拉伯之春”是一个带有价值判断的概念,是以实现西方的民主化模式作为对阿拉伯国家变局的政治期望。如美国学者阿尔弗莱德·斯泰潘(Alfred Stepan)和胡安·J·林茨(Juan J.Linz)认为,对“阿拉伯之春”的观察应聚焦于三大主题: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中民主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威权主义与民主混合政权的特征;苏丹主义(Sultanism)①最早提出“苏丹主义”概念的是马克斯·韦伯,他在《经济与社会》中将“苏丹主义”视为世袭家长专制政权(Patrimonianism)中的极端类型,特指一种在行政管理方式上游移于自由的、不受传统约束的任意专断范围内的世袭统治。其后,美国胡安·J·林茨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进一步丰富其内涵,并用该词代指任意使用权力的、退化了的家长制权威类型。的本质及其民主化转型的含义。②A lfred Stepan and Juan J.Linz,“Democratization Theory and the Arab Spring,”Journal of Democracy,Vol.24,No.2,April 2013,p.15.随着中东政治局势逐渐失控,宗教极端主义异常活跃,各种人道主义危机频频出现。西方学者又将其称为“阿拉伯之冬”(Arab Winter)。显然,西方试图将2010年以来中东剧变的原因归结为阿拉伯国家民众追求民主的反政府运动,但这种观点忽略了中东变局的深层历史成因和国情的特殊性。2019年以前,阿尔及利亚并未受到中东剧变的强烈冲击,因此有学者称它为“动荡地区的稳定之岛”③Dalia Ghanem-Yazbeck,“Limiting Change Through Change:The Key to the Algerian Regime's Longevity,”Carnegie Middle East Center,April 2018,https://www.jstor.org/stable/resrep21001.4?refreqid=excelsior%3Ada8e6ae29a202f6cba715dbfe3fb5565&seq=2#metadata_info_tab_contents,上网时间:2020年4月15日。。记者卡迈勒·达乌德(Kamel Daoud)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阿尔及利亚是“阿拉伯世界的一个例外”④AnneWolf,“The Myth of Stability in Algeria,”The Journal ofNorth African Studies,Vol.24,No.5,2019,p.707.。但阿尔及尔大学的布希娜·切里特(Boutheina Cheriet)将所谓的“阿尔及利亚例外论”归因于独立以来阿尔及利亚威权主义政治体系的保守性,认为它并没有解决政权的合法性问题。①Boutheina Cheriet,“The Arab Spring Exception:Algeria's Political Ambiguities and Citizenship Rights,”The Journal ofNorth African Studies,Vol.19,No.2,2014,p.143.俄罗斯学者阿列克谢·M·瓦西里耶夫(Aleksey M.Vasiliev)和娜塔莉亚·A·哲利提娅(Natalia A.Zherlitsina)也认为,虽然阿尔及利亚试图展现一个摆脱了内部分裂和极端主义的地区大国形象,但各种矛盾叠加的现实使其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②A leksey M.Vasiliev and Natalia A.Zherlitsina,“Algeria:A Regional Leader or a Potentially Unstable State?,”Outlines ofGlobal Transformations,Special Issue,2019,p.98.对于2019年阿尔及利亚的希拉克运动,非西方学者更多地将其与2010年以来中东范围内的“阿拉伯之春”相比较,称之为“阿拉伯之春2.0版”。不论是“阿尔及利亚例外论”还是“新版本的阿拉伯之春”,它们在本质上仍是西方对中东变局话语系统的延续。
第二,“革命”操控论。从中东变局以来阿尔及利亚的官方立场来看,它更多的是将这场地区范围的政治动荡描述为外部势力对阿拉伯国家稳定局势的破坏。这一论调显然是不希望这场动荡波及自身而抛出的阴谋论。但从中东变局的发展过程来看,西方国家在其中确实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推动中东地区的“民主化”变革是西方自20世纪末以来的既定战略,它无视中东地区的具体国情,试图通过价值观念的输出和培育亲西方力量等方式来移植西方式的民主经验。虽然肇始于突尼斯的中东变局的发生充满偶然性,但在其后的中东“多米诺”骨牌效应中,西方国家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学者观察到,在这场地区变局中,与西方关系较为密切的国家相对稳定。③Vera van Hüllen,EU Democracy Promotion and the Arab Spring: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Authoritarianis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5,p.150.因此,部分阿拉伯学者在思考中东变局的根源时,发现了西方在阿拉伯街头政治中所起的作用。阿尔及利亚学者艾哈迈德·本萨阿达(Ahmed Bensaada)在《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和《八年后:阿尔及利亚的“春天”》两部著作中聚焦21世纪以来西方国家通过资助中东阿拉伯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对相关人员提供培训、控制社交媒体和制造“革命”话语等方式,称其对阿尔及利亚正在发生的抗议运动进行渗透,以达到控制抗议运动走向的目的。鉴于此,本萨阿达认为,阿尔及利亚希拉克运动的发生恰好是西方在中东制造的“革命”模式的翻版。④[法]埃里克·德塞纳等:《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王朔、周谭豪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Ahmed Bensaada,“Huit ans après:la«printanisation»de l'A lgérie,”https://ahmedbensaada.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75:2019-04-04-22-50-13&-catid=46:qprintemps-arabeq&Itemid=119,上网时间:2020年4月20日。
第三,国家治理衰败论。对于2010年以来的中东剧变,部分西方学者试图将其与全球频发的抗议运动相联系。巴黎政治学院教授贝特朗·巴迪(Bertrand Badie)认为,阿尔及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动荡是由全球化所引发的全球性政治信任危机的一部分,与美国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法国的“黄马甲”运动等具有相同的起因。①Bertrand Badie,“L'acte II de la Mondialisation a Commence,”Lemonde,November.8,2019,https://www.lemonde.fr/idees/article/2019/11/08/bertrand-badie-l-acte-ii-de-la-mondialisationa-commence_6018418_3232.html,上网时间:2020年3月16日。这一观点试图为中东变局提供一种宏大的全球性视角,但却忽视了引发阿拉伯国家动荡的具体原因,因此也遭到了阿拉伯学者的反对。突尼斯学者里达·谢努菲(Ridha Chennoufi)明确表示,将突尼斯革命放在西方国家革命的背景下是错误的……虽然突尼斯革命及其引发的类似运动都渴望社会公正和尊重个人自由,但事实上,阿拉伯革命是在相当具体的情况下出现的。②Ridha Chennoufi,“Political Power,the Maghreb Space,and the“Arab Spring:A Reading through Ibn Khaldūn's Looking Glass,”Philosophy East and West,Vol.69,No.3,2019,p.657.因此,对阿尔及利亚希拉克运动根源的判断,更多学者主张危机内生性的观点,而全球化所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只是这场危机的外部加速器。就职于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阿梅尔·布贝克(Amel Boubekeur)③Amel Boubekeur,“Demonstration Effects:How The Hirak Protest Movement is Reshaping Algerian Politics,”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Vol.25,No.2,2020,p.2.认为,阿尔及利亚希拉克运动的发生源于该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缺陷所造成的社会分裂,阿尔及尔大学政治学学者穆罕默德·亨纳德(Mohamed Hennad)亦认为,当前阿尔及利亚政治局势的核心问题是政权的合法性危机。④Mohamed Hennad,“Le Pouvoir Refuse D'admettre Qu'il y a Une Grave Crise de Confiance,”le 04-10-2020,https://www.liberte-algerie.com/actualite/le-pouvoir-refuse-dadmettrequil-y-a-une-grave-crise-de-confiance-346656,上网时间:2020年10月5日。另一位阿尔及利亚学者范西亚·泽拉利亚(Faouzia Zeraoulia)则认为,现在发生的希拉克运动主张一种否定官方叙事的反叙事,它不是一种孤立的或个性化的情感表达,而是人们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记忆的系统反思。⑤Faouzia Zeraoulia,“The Memory of the CivilWar in Algeria:Lessons from the Past with Reference to the Algerian Hirak,”Contemporary Review of the Middle East,Vol.7,Issue 1,2020,p.5.除此之外,乔治·乔费(George Joffé)、弗雷德里克·沃尔皮(Frédéric Volpi)以及达莉亚·加尼姆·亚兹贝克(Dalia Ghanem-Yazbeck)等学者也将希拉克运动爆发的原因更多地集中在国家内部,分别观察到长期以来政治体系的弊端、经济发展的持续低迷以及年青人数量激增带来的影响等。不过,多数学者对阿尔及利亚新一轮政治改革趋向的讨论仍然陷入了西方民主化模式的窠臼,尽管政治民主化并不是引发这场政治运动的根源与解决问题的出路。
总体来看,国内学者对阿尔及利亚希拉克运动研究鲜有学理分析,也没有专题性著述对该问题进行系统总结。国外学者在概念阐释、案例分析和逻辑推理上做出了积极的探索,部分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前瞻性,但仍存在不足之处:第一,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更多地关注于阿尔及利亚希拉克运动的某一具体方面,忽略了对这一政治现象的整体结构性根源的考察,从而造成相关研究对希拉克运动的归因较为碎片化;第二,学术界注意到了希拉克运动与2010年以来中东变局的延续性,但对希拉克运动呈现的新特点的探讨尚且不足,从而导致无法为对阿尔及利亚政治发展趋势的讨论提供理论支撑;第三,受西方“民主化”话语体系的影响,国内外学术成果更多体现为民主化和身份政治等时下流行模式化的分析路径,缺乏对阿尔及利亚希拉克运动历史根源的深入讨论。
二、阿尔及利亚希拉克运动爆发的根源
希拉克运动的目标从最初要求布特弗利卡下台,逐渐转变为反对精英集团统治,要求国家进行全面改革的系统性运动。追根溯源,本次抗议活动的根本问题仍在于阿尔及利亚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集中爆发,从而造成民众开始对统治集团及其统治秩序产生怀疑,进而出现对现状不满和对国家体制进行否定的反抗情绪。
(一)经济结构的单一性增加了政治体制的脆弱性
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初,法籍农场主、企业主和技术工人等群体的撤离使土地无人耕种,机器残损不全,工厂无人管理,经济陷入半瘫痪状态。在自管运动①20世纪60年代阿尔及利亚独立之际,大批殖民者撤离阿尔及利亚,留下大量农场和工厂等“无主产业”。阿尔及利亚工人自发填补产业空白,积极恢复国民经济生产。本·贝拉总统通过政府主导自管产业的管理,逐步将其制度化。自管运动对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初国家经济的恢复起到了巨大作用,并成为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的典型特征。的推进下,国家成立初期经济社会的混乱情况基本稳定。直至布迈丁时代,阿尔及利亚明确确定了“工业化”和“国有化”的经济发展战略,使国民经济逐渐步入正轨。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使产业结构严重失衡,自政府执行工业化发展战略后,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迅速提升,1963年为35.3%,1976年工业产值提高到57.7%,1977年达到65.5%。①赵慧杰:《列国志·阿尔及利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页。经过20世纪70年代大举发展工业的举措,至80年代初阿尔及利亚已形成以油气出口为主体的工业体系。1980年开始,阿尔及利亚向市场经济过渡,90年代全面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出台推动经济多元化多种政策,并在平衡产业结构中取得一定成效,但产业单一化特征仍非常明显。据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阿尔及利亚经济严重依赖其碳化氢产业部门的收入,碳化氢产业部门约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0%,占95%以上的出口收入和预算收入的60%。②Anissa Benramdane,“Oil Price Volatility and Economic Grow th in Algeria,”Energy Sources,Vol.12,Issue 4,2017,p.340.总体来看,由于阿尔及利亚的经济依然依赖油气资源的出口,当国际环境出现波动时,这种依赖资源型经济的弊端较为明显。
得天独厚的油气资源和碳氢化产业是阿尔及利亚政府的重要政治资本,以石油美元为基础的福利分配是构建政权或领袖合法性的特殊路径。政府通过垄断福利分配,满足民众对物质生活的期望,从而将经济资源转变为政治资源。③慈志刚:《阿尔及利亚政治稳定结构探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2期,第29页。因此,有学者认为,在阿尔及利亚,国家统治者和公民之间的社会契约模式是国家用石油和天然气的收入为公民提供服务,以换取社会对专制政治制度的默认。④Sarah Feuer,“In North A frican Unrest,Competing Visions of a Post-Arab Spring Order,”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No.1162,April 16,2019.p.3.随着全球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价格暴跌,政府不得不增加部分税收,同时提高燃料、电力和天然气的价格。再加上政府削减了向贫困人口提供的补贴,使社会上经济问题迅速增加。经济上的危机同样打击了阿尔及利亚的中产阶级,政府减少了社会援助计划,并解雇了40%的政府雇员。⑤A leksey M.Vasiliev,Natalia A.Zherlitsina,“A lgeria:A Regional Leader or a Potentially Unstable State?,”p.102.2011年阿尔及利亚面对中东变局的浪潮,政府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暂时平息了社会上的不满声音。但到了2019年的经济形势还没有从2014年的油气价格暴跌中恢复,财政无法再负担起平息动荡所需的巨额账单。为了维持公共事务运转,阿尔及利亚的公共债务逐年上涨,政府债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由2015年的8.7%骤增至2019年的46.1%。⑥“Algeria GDP and Economic Data,”Global Finance,2017,https://www.gfmag.com/global-data/country-data/algeria-gdp-country-report,上网时间:2020年6月18日。
除了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民生问题一直困扰着阿尔及利亚。从20世纪80年代起,普通民众的处境明显恶化。由于国际油价大跌以及国内冲突的影响,1986年至1999年期间,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590美元下降到1,550美元。①Michael J.Willis,Politics and Power in the Maghreb:Algeria,Tunisia and Morocco from Independence to the Arab Spring,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258.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油价的大幅上涨和1999年以来国内冲突的结束,但经济形势并没有明显改善。近几年来,阿尔及利亚失业率从2016年的10.6%上升到2017年和2018年的11.7%,再到2019年的12.5%,②“Algeria GDP and Economic Data.”呈逐年上涨趋势。失业问题在年轻人中表现尤为明显。据统计,2015年阿尔及利亚15~24岁的青年人中就业者仅占28.3%③Pamela Abbott and Andrea Teti,“Young People in North A frica Not in Employment,Education or Training,”Arab Transformations Project:Arab Transformations Policy Brief 9,September 2017,p.2.,2011年以来处于啃老状态的比例始终维持在21%以上④Ahmed Driouchi and Tahar Harkat,“Counting the NEETs for Countries with no or less Data,Using Information on Unemployment of Youth Aged 15-24:The Case of Arab Countries,”Munich Personal RePEc Archive,May 23,2017,https://mpra.ub.uni-muenchen.de/79330/,上网时间:2020年7月12日。。经济发展前景的暗淡,使移民人数激增,从2015年至2017年,阿尔及利亚和欧洲逮捕的阿非法移民人数增加了两倍多。⑤智宇琛:《阿尔及利亚政局走向何方》,载《中国投资》2019年第8期,第81页。值得注意的是,在移民中出现了许多文化水平较高的人群,人才流失很可能会导致阿尔及利亚国内经济和政治问题进一步恶化。
(二)政治体系的内在积弊侵蚀政权的合法性
自独立以来,阿尔及利亚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在探索与尝试的过程中,其政治体系不断自我巩固,造就了极强的适应性。希拉克运动可被看作是该政权与社会适应过程中的一部分,但其超强适应性背后所隐藏的是阿尔及利亚政治体系中长期以来的积弊。
第一,多元民主外衣下的威权政治实质。1989年阿尔及利亚的政治体制从单一政党体制开始转向多党民主政治体制。在进行多党民主政治体制的尝试时,由于改革过于激进以及对国内情况分析不足,导致初次尝试失败,但建立多党民主政治体制的进程并没有因为国内冲突而止步。1997年6月和10月,新一届立法选举和地方立法选举先后顺利进行,组成了由多党参加的立法机构,标志着阿尔及利亚的一党制政治已经逐步转向多党制民主政治。⑥赵慧杰:《列国志·阿尔及利亚》,第110页。尽管政治舞台上出现了许多新生力量,但在民主政治的外表下依然是被垄断的政治权力。无论实行的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其政治秩序的内核一直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军队对政治生活的干预。在阿尔及利亚,军队始终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在2016年的阿拉伯民意指数中,46%的阿尔及利亚人信任政府,而76%的阿尔及利亚人信任军方。①2016年对“是否信任政府”的统计显示:信任态度占比46%,不信任态度占比50%,弃权占比4%;“是否信任军方”的统计显示:信任态度占比76%,不信任态度占比22%,弃权占比2%。See Dana Alkurd,“Public Opinion and The Army:The Cases of Algeria and Sudan,”Analysis from the Arab Opinion Index,Vol.2,No.2,2019,p.103。军队干预政治却又深得民心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形成原因有二:一是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军队为非殖民化所做的贡献得到民众肯定;二是在阿尔及利亚独立以后,军队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除了民众赋予军队的合法性使军队具有一定程度的权威以外,军方在阿尔及利亚的政治舞台上一直居中心地位,甚至自独立以来的历届总统都具有军方背景。2019年抗议者通过希拉克运动迫使军方多次推迟总统选举,但12月特本的当选就是军方对希拉克运动的回应:军方向民众妥协,使特本成为首位不具有军队履职经历的总统,但同时也表明,军队仍然控制着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发展进程,军人干预政治的传统仍然在延续。阿尔及利亚左派评论员穆罕默德·哈比(Mohamed Harbi)调侃说,阿尔及利亚“不是一个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一个有国家的军队。”②Michael J.Willis,Politics and Power in the Maghreb:Algeria,Tunisia and Morocco from Independence to the Arab Spring,p.82.
另一方面,政治精英统治秩序的固化。阿尔及利亚政治秩序排斥新生政治力量。国家独立初期,由于法籍行政人员的撤离,行政体系陷入瘫痪,新政府中除了技术职位,行政官员多为独立战争时期的老兵担任。因此,脱胎于军人的行政官僚和技术人员构成的专家队伍共同组成了政治精英团体。行政体系的运行主要依赖于行政官僚与技术专家的协作与分权,排斥普遍性的群众参与。这些政治精英所构建的政治秩序相对比较稳定,而新生的政治力量缺乏进入统治集团的路径,行政体系与社会沟通受到阻塞。随着阿尔及利亚社会的进一步分化,政治精英的封闭性越来越招致社会不满情绪的出现。另外,政治精英严格控制任何与政府相关的社会舆论。情报部门是阿尔及利亚精英权力结构中的重要一环,它履行“政治警察”的职能,对各政党、工会、媒体和民间社会组织进行密切监控,达到对社会舆论进行控制的目的。此外,尽管阿尔及利亚宪法赋予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但实际上批评国家公务人员或国家政策的言论是为国家所不允许的,该言论的发表者可能会受到罚款或逮捕。例如,2015年记者兼人权活动家哈桑·布拉斯(Hassan Bouras)在调查一桩腐败案时被捕,因其侮辱政府、冒犯一名司法官员和一名执法人员而被判一年监禁。
第二,政治腐败泛滥。政治腐败在阿尔及利亚建国后一直存在。由于国家对核心经济部门的垄断,权力寻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布特弗利卡执政时期,公共权力与经济利益的交换更为频繁,腐败现象亦愈演愈烈。根据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腐败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显示,阿尔及利亚在全球180个国家中位列105名(2018年)①“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18,”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January 2019,https://www.transparency.org/en/cpi/2018/index/dza#,上网时间:2020年7月16日。、106名(2019年)②“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19,”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January 2020,https://www.transparency.org/en/cpi/2019/index/dza,上网时间:2020年7月16日。和104名(2020年)。③“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20,”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January 2021,https://www.transparency.org/en/cpi/2020/index/dza,上网时间:2020年7月16日。阿尔及利亚的腐败现象尤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经济利益换取选票。在宪法修正案表决与布特弗利卡第三任期进行选举之前,议会代表以及一些政府高级官员的薪资上涨了30%,但实际上他们原本的薪资相较于普通民众而言已经相当可观;另一方面,政府高官的腐败情况也十分严重,而且通常在被指控的情况下也不会受到任何惩处。例如,时任矿业和能源部部长与国家石油公司(Sonatrach)首席执行官查基布·凯利尔(Chakib Khelil)被正式指控挪用公款和洗钱,但他在美国流亡三年后,于2016年5月返回阿尔及利亚,却没有因指控而遭受审判。④Ratiba Hadj-Moussa,“Youth and Activismin Algeria:The Question of Political Generations,”The Journal ofNorth African Studies,Vol.24,Issue 6,2019,p.22.尽管在2019年布特弗利卡辞职后,阿尔及利亚已经展开反腐工作,但这项工作实际上是针对与布特弗利卡利益相关官员的清洗运动,腐败问题在阿尔及利亚仍然根深蒂固,难以有效治理。
(三)人口结构年轻化削弱了政治统治的权威性
青年人口问题在近年来中东国家社会上普遍存在。青年数量的增多作为人口优势可以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做出巨大贡献,但如果国家无法将青年人的力量融入到社会发展进程之中,那么青年人口问题将成为国家潜在的隐患。根据阿尔及利亚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9年至2019年阿尔及利亚人口年轻化趋势虽然有所放缓,尤其是中位年龄从24.5岁增加到27.7岁,但2019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仍高达60%。①“Démographie Algérienne(bis)—2019,”Office National des Statistiques,April 2020,http://www.ons.dz/IMG/pdf/demographie2019_bis.pdf,上网时间:2020年7月20日。如此庞大青年群体的多数在社会发展中陷入困境,成为希拉克运动爆发的助推器。
首先,青年人职业发展遭遇挫折。独立以来,阿尔及利亚初等教育的普及推动了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加,全国大学生人数从1999年的42.5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170万人,20年间增加了4倍。②Laurence Thieux,“Algerian Youth and the Political Struggle for Dignity:Evolution,Trends and New Forms of Mobilisation,”The Journal ofNorth African Studies,Vol.26,No.2,2019,p.4.学历的提升使学生及其家人对就业前景报以极大期待,但现实情况不仅没有达到预期,反而连基本的就业也成了问题。现实的遭遇增加了个人对发展规划前景的挫败感。当青年踏出校园成为社会上失业大军中的一员,在自我期望与现实的落差之间,部分青年再次受到来自贫富差距的冲击。当城市里的青年人在环境优雅的咖啡厅里享受生活时,贫困地区的青年们最多只能出现在清真寺、足球场或俱乐部等场所躲避现实的残酷。个人境遇的挫败与群体的异质性使这一充满活力的群体变得尤其哀怨。
其次,青年人政治参与陷入困境。一方面,政治参与热情不高。选举是政治参与最直接的方式,能够参加选举意味着公民参与了国家管理。在阿尔及利亚,关于参与投票和社会团体的法定年龄是18岁,有资格成为议会议员的法定年龄为23岁。阿尔及利亚政治体系的封闭性特征大大降低了选举过程的重要性,导致阿尔及利亚选举的投票率一直不高,青年人愿意参加投票的人数还不到20%。在议会中,出现了年轻议员应该进入议会而大龄议员却不愿离开的矛盾。据统计,2013年阿尔及利亚30岁以下议员的比例仅占1.1%。③Thierry Desrues,Marta Garcia de Paredes,“Political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of Young People in North Africa:Behaviours,Discourses and Opinions,”Revista de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Mediterráneos,No.26,2019,p.12.
另一方面,政治途径受限。近年来,传统政治参与的途径愈来愈不受信任,一些政党或者社会组织不能及时消解社会不满与正当诉求,无法充当政府与社会的调解人这一角色。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第一,进入21世纪以来,地方性的抗议活动屡见不鲜,主要诉求无非就是住房、就业等基础性的社会需求问题,这恰恰证明了传统沟通途径不能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民众积累的不满与诉求只能以抗议的形式表达。第二,作为社会主要力量的青年人对于加入社会组织以及政党的兴趣不高。2012年,接受调查的阿尔及利亚年轻人中,有4.7%的人表示自己是某个协会的成员,1.5%的人隶属于某个工会。①“Les Jeunes Tournent le dos aux Partis Politiques,”Algeria-Watch,August 28,2017,https://algeria-watch.org/?p=39654,上网时间:2020年8月2日。调查显示,只有1%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是政党成员或参与过政党活动,43%的受访者表示对政党持负面看法。②Laurence Thieux,“Algerian Youth and the Political Struggle for Dignity:Evolution,Trends and New Forms of Mobilisation,”p.7.政府对公共空间的管制加速了传统途径的衰落,特别是2012年1月政府通过关于社会团体的法律,社会团体获得法律承认的认证规则变得更加复杂且难以满足,大大制约了社会团体的活动空间。第三,青年人缺少表达合理诉求的途径。阿尔及利亚宪法序言中将青年人定义为:青年人应是国家克服经济、社会和文化挑战承诺的核心,并将继续支持这一承诺主要受益者的后代;宪法第37条将青年表述为建设祖国的主力军,国家应确保提供发展和增强青年能力所需的一切必要条件。③Thierry Desrues,Marta Garcia de Paredes,“Political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of Young People in North A frica:Behaviours,Discourses and Opinions,”p.10.政治精英意识到青年群体的活跃程度高,并且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故而在统治中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但在实际操作中,青年群体并没有得到宪法中规定的“必要条件”,反而在政治参与中受到限制。2019年2月,因为没有表达不满与合理诉求的平台,青年们聚集到首都的体育场馆表达愤怒与沮丧。
最后,青年人与上一代人的代际问题。当前的青年群体大多是内战期间甚至内战之后出生的,他们对国家历史的了解都来自书本与他人的口述。第一,独立战争期间获得民众大力支持的军队在青年群体中的威望远远不及上一代人,军队精英所独有的政治合法性受到动摇,为希拉克运动后期要求的提出做了准备。第二,没有亲身经历那段漫长又惨痛的内战记忆使他们具备了系统改革政治的勇气,这为希拉克运动的长时间持续提供了心理暗示。无论是在希拉克运动爆发初期布特弗利卡针对第五任期所做出的让步,还是后来当局针对腐败官员所做的让步,都不能使希拉克运动像2011年骚乱一样被平息。这恰恰证明了政治精英对老一代人的让步策略在年轻人的身上将越来越不起作用。
(四)网络媒体的发展增添了政治发展的风险性
媒体舆论对于社会关系建构的作用不可忽视,它不仅可以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是可以承载各种形式的竞争与互动。互联网作为新兴媒介,对2011年的中东变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次抗议运动也同样离不开网络媒体的加持。2003年,阿尔及利亚开始接入宽带互联网,由于网络成本高,电脑价格的昂贵,直到2010年其互联网普及率仅为12.5%,2011年增长至14%,2019年已经达到49.2%。①Zofia Sawicka,“New Media?New Algerian Arab Spring?,”Torun International Studies,No.1,2019,p.79.这解释了2011年阿尔及利亚网络动员失败的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希拉克运动网络宣传成功的原因。
美国互联网专家克莱·舍基(Clay Shirky)认为,“脸书”“推特”“油管”、博客和手机等社交媒体在政治领域的使用改变了社会运动的传统组织方式,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来源,降低了协调成本,提高了信息交流的速度。②Clay Shirky,“The Political Power of Social Media:Technology,the Public Sphere,and Political Change,”Foreign Affairs,Vol.90,No.1,p.41.互联网本身所具有的受限小以及实时性等特点,使其成为组织宣传希拉克运动的最佳方式。一方面,与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形式相比,互联网受政府的舆论控制更小。在阿尔及利亚,统治精英严格控制与政府相关的任何不利舆论,甚至不惜逮捕拘留等措施惩治“发表不当言论的人”;再加上总统选举过程中电视广播的应用,使传统媒体被人们公认为“国家媒体”。与之相比,作为新科技革命的产物,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大大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这大大降低了国家对信息传播进行干预的可能。
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实时性使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民众变得亲密无间,从而实现了跨地域交流。广大民众将互联网作为宣泄情绪与交流的主要场所,国内一些政治精英的腐败丑闻在互联网上的迅速蔓延,再加上民众看到了其他国家正在发生的进步,这大大增加了民众的心理落差。面对各自生活的困难,互联网在民众之间建立了共情关系。得益于互联网本身的特征以及阿尔及利亚民众的共情,2019年2月22日抗议活动的爆发缘于人们收到了一条带有详细指示的匿名信息。信息内包括在特定城市举行集会的时间和地点,要求携带乐器和哨子,而不是旗帜,以示这将是一次完全和平性质的活动。同时,它还告诫人们不要与安全部门发生冲突。③Zofia Sawicka,“New Media?New A lgerian Arab Spring?”.随后在希拉克运动的整个进程中,都离不开网络媒体的使用。
三、阿尔及利亚希拉克运动的新特点
希拉克运动自2019年2月份爆发持续至今。纵览其发展过程,本次抗议运动与2011年前后的抗议浪潮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更多呈现的是全然不同的特点。与2011年相比较,这次抗议运动似乎更像是民众进行社会参与的工具,抗议者试图重塑国家政治参与机制,以达到变革整个国家政治体系的目的。通过抗议者的持续性施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和廉政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发展。
第一,抗议主体的年轻化。世纪之交,约什·马丁(Josh Martin)曾预言:“忘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吧,对阿拉伯国家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来自那些邪恶科学家的实验室,而是阿拉伯家庭中无以计数的摇篮。”①Josh Martin,“The Population Time Bomb,”The Middle East,November 2003,p.7.如今看来,这似乎已经变成阿拉伯世界的现实。阿尔及利亚青年人占人口总数的绝大部分,这一主要在“黑色十年”前后出生的群体成为社会运动的主要力量。这些青年受宗教或世俗因素限制较少,更能接受开放的思想;他们不再停留在对内战的反思,而是更关注现实的政治和经济需求。正如一位参加希拉克运动的青年学生所言:“我为年轻人而战。我和我的朋友们正在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我们正在做我们长辈们没有完成的事情。过去批评我们的老年人现在发现我们有能力有所作为。该由我们挺身而出了。我们无所畏惧,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愿意做任何事情。”②Sabri Benaly Cherif,“Nothing Will Fall from the Sky:Algeria's Revolution Marches on—Photo Essay,”African Arguments,December 18,2019,https://africanarguments.org/2019/12/18/nothing-will-fall-from-the-sky-algeria-revolution-Hirak-marches-on-photo-essay/,上网时间:2020年7月14日。走出校园学生在就业与生活上的情况,远远不及他们想象中的愿景,而且无法看到改善的希望。就在青年们苦苦挣扎于现实的无助中时,布特弗利卡宣布仍要参加下一届的总统选举,这一消息点燃了青年们的愤怒,这些熟悉现代网络工具、政治态度活跃且激进的青年人群纷纷走上街头,并成为希拉克运动的主力军。
第二,抗议者身份的同质化。现代社会的内在特征是异质的,同时也为多元价值的共生创造了空间。沙德利总统时期的市场化改革加速了阿尔及利亚的社会分化,并沿着不同的认同边界出现了身份政治的分裂与对抗,这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其一是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的身份之争,导致了柏柏尔之春的出现;其二是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之争,导致了长达十年的血腥内战。因此,布特弗利卡执政初期的首要任务是重新实现民族团结,模糊不同身份的政治表达,为实现社会安定创造条件。近年来,柏柏尔人运动再次复兴,但在这次抗议运动中,柏柏尔人非但没有借希拉克运动的兴起发难,反而与其他抗议民众一同为民主斗争。对执政当局的不满成为不同身份的抗议者实现联合的基础。尽管当局曾警告称不允许携带除国旗外的其他旗帜出现在抗议活动中,试图以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的矛盾为切入点,使希拉克运动从内部瓦解,但这种计划显然没有成功。在阿尔及利亚讲柏柏尔语的地区,同样使用“没有柏柏尔人,没有阿拉伯人,没有种族,没有宗教!我们都是阿尔及利亚人!”作为抗议运动的口号。①Sarah Feuer,Carmit Valensi,“Arab Spring 2.0?Making Sense of the Protests Sweeping the Region,”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No.1235,2019,p.2.除了柏柏尔人问题以外,宗教问题也是阿尔及利亚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在经历了内战以后,伊斯兰政党的影响力正在减弱,普通民众对其思想和主张往往并无好感。早在示威游行的第二周,社交媒体上的公民就呼吁抗议者要提高警惕,特别是防止伊斯兰主义者对该运动的“劫持”。例如,2019年的抗议活动中,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阵线(Justice and Development Front)领导人阿卜杜拉·贾巴拉(Abdallah Djaballah),被抗议者高喊“滚开”赶走。②Dalia Ghanem,“The Shifting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Islamin Algeria,”Carnegie Middle East Center,April 2019,https://www.jstor.org/stable/resrep20971.3?refreqid=excelsior%3Aa74-d0dd229c5e0a4c946ef1f08a1fe1b&seq=2#metadata_info_tab_contents,上网时间:2020年5月30日。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包括柏柏尔人在内的学生、工人以及伊斯兰主义者在内的抗议者虽然在希拉克运动中具有身份同质化特征,但当面对提出更为具体的要求时,往往并不能达成一致。
第三,抗议方式的和平化。阿尔及利亚人认为,非暴力抗议和社交网络是为阿尔及利亚民主未来而战的最佳途径。③Zofia Sawicka,“New Media?New A lgerian Arab Spring?,”p.85.希拉克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非暴力倾向,抗议者竭力避免与警方产生任何冲突。从抗议活动的秩序与纪律来看,数以百万计的抗议者走上街头,他们抛弃了2011年在街头政治中打砸抢等行为,而是采取一边手拿横幅游行,一边高喊和平的理性方式进行斗争。因此,这次抗议运动又被称为“微笑革命”。抗议者在示威活动中向警察递送鲜花,并且幽默地将室内养殖的绿色植物带到了抗议活动现场浇水,以此回应警察向他们喷射水枪的威胁。在秩序井然的抗议活动结束之后,街道上没有残留任何痕迹,甚至抗议现场留下的垃圾也被抗议者清理。这次抗议运动采取和平化的斗争方式的原因在于民众拒绝任何以意识形态的分界线。他们主张通过纪律性较强的和平抗议,以向政府施压的方式来达到斗争的最终目的。同时,军方也改变了对希拉克运动的否定立场,在运动初期便赞扬并承认了民众运动的合法性,来确保军队对未来政治发展进程的影响力。
第四,抗议周期的常态化。希拉克运动自2019年2月开始持续至今,每周都有抗议者走上街头。除了一些律师、法官和学生等民间组织会在一周组织几次游行以外,抗议活动基本都是在每周的星期五进行。甚至是在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的情况下,抗议活动仍继续进行,只不过希拉克运动会依据相应的政治主题而出现人数和区域的变化。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阿尔及利亚政府于2020年3月开始禁止示威活动,由此引发异议。抗议者认为国家利用他们不在街头而拒绝进行有意义的改革,并以抗击疫情为籍口来消极回应民众对宪法改革的广泛要求。例如,学生促进变革联盟(Students Rally for Change)认为,希拉克运动必须避免被当局指责阻碍政府抗击新冠疫情措施的实施。①George Joffé,“COVID-19 and North A frica,”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Vol.25,Issue.4,2020,p.520.虽然疫情使民众无法像以往那样走上街头,但是抗议活动并未停止,在社交媒体上表达政治主张成为新冠病毒疫情背景下希拉克运动的“新常态”。
四、阿尔及利亚希拉克运动的发展趋势
阿尔及利亚希拉克运动是中东剧变以来阿拉伯国家发生的规模最大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对阿尔及利亚的传统威权主义政体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这场社会变革的发展趋势,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中东剧变中极力推动“民主化变革”的美国和欧洲也对此纷纷予以表态。与强力支持突尼斯、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反政府力量不同,欧美对阿尔及利亚所发生的希拉克运动态度相对谨慎很多。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罗伯特·帕拉迪诺(Robert Palladino)表示,美国持续关注阿尔及利亚的希拉克运动,支持阿尔及利亚人和平集会的权利。②“The United States on Tuesday Expressed Support for the Rightof A lgerians to Protest,after Thousands Took to the Streets to Oppose President Abdelaziz Bouteflika's Bid for a Fifth Term,”France 24,March 6,2019,https://www.france24.com/en/20190306-usa-backs-algerians-right-protest-bouteflika,上网时间:2020年6月28日。而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发言人玛雅·科齐扬契奇(Maja Kocijancic)则声明,欧盟希望阿尔及利亚人能够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在域外国家不直接推动社会激进革命的前提下,阿尔及利亚希拉克运动的未来发展主要取决于各方政治力量的互动博弈以及政府对引发希拉克运动的核心问题的回应。
第一,阿尔及利亚希拉克运动可能会走向分化。布迈丁执政后基本结束了本·贝拉以工人自管为特征的大众动员政治,在经济上推行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特征的工业化,将民众排除在管理体系之外,在政治上则奉行“福利换稳定”的治理模式。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市场化改革,大众参与国家管理的愿望与行动在民主化改革以后才大规模产生。但随后的十年内战,再次凸显了稳定的重要性。直到2010年以来的中东剧变,为民众提供了重新反思国家治理模式的契机。这种反思以2019年布特弗利卡宣布参加第五任期的竞选而转化为行动,希拉克运动由此爆发。从当前形势看,希拉克运动仍会继续对阿尔及利亚政权构成挑战,但从运动的内在特点来看,它存在着分裂化的趋向。
首先,希拉克运动的最初阶段是集结社会各阶层所形成的反布特弗利卡连任的抵制阵线,其反对派特性决定了这一阵线是能够模糊意识形态等身份特征的暂时性联合。希拉克运动的发展也证明,民众不断通过网络空间等媒介构建新的反抗主题,来保持运动的凝聚力。但希拉克运动的未来则取决于政治诉求的趋同和政治共识的达成,从现阶段看这是无法实现的。
其次,希拉克运动的内部成分复杂且参与动机多样化。希拉克运动虽然强调不以某种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同质化特征,但这并不能掩饰抗议者身份和思想的多元性。各种不同身份的抗议者虽然都主张政府进行改革,但对改革的目标则完全不同,因此就出现了部分抗议群体在目标实现后从希拉克运动中撤离,并转变为政府的支持者。另外,虽然希拉克运动反对各反对派政党和政治组织主导运动的发展,但这些政党和组织不愿意错过这次政治投机的机会。因此,随着政府改革措施的持续推进,希拉克运动存在继续分化的可能。
最后,希拉克运动存在民粹主义的特征。当前希拉克运动的超党派特征使其排斥政治精英的参与,短时间很难达成核心诉求和立场,这就会出现抗议者为了抗议而坚持抗议局面。他们不与当局进行和解,双方始终处于胶着状态。如果一直无法和解,那么希拉克运动很有可能会因为抗议者的疲倦而无果而终。
第二,阿尔及利亚政府对希拉克运动的基本应对策略。军人对政治的干预在阿尔及利亚独立以后的历史上并不鲜见。1965年布迈丁通过政变的方式推翻了本·贝拉的领导,使阿尔及利亚政治重新回归革命时代的“集体领导”;1992年军方发动政变结束了选举进程,成功阻止了伊斯兰拯救阵线登上权力之巅,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2019年军方对政治的干预亦是对军方在政治进程中“纠错”传统的延续。鉴于希拉克运动对布特弗利卡政府政治合法性的破坏,军方在这场政治运动中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阿尔及利亚政治发展进程的方向。人民军参谋长艾哈迈德·加伊德·萨拉赫发表电视讲话,按照宪法第102条,要求布特弗利卡辞职,这成为军方与布特弗利卡政权割席决裂的标志。根据阿尔及利亚的历史经验,军方干预政治是阿尔及利亚下一步政治改革的前提,而军人对新政治制度创建的参与才是政治体系系统化变革的第一步。因此,从以往军人干政后短期策略来看,政府会采取相应措施来满足社会的基本诉求;从长期策略看,政府会重新修订宪法来满足改革呼声,并重新开放各层级的议会选举。特本政府试图通过大力反腐和推进经济改革,来破解阿尔及利亚当前的政治难题,但现阶段仍在延续的抗议运动说明,这些措施还尚未达到预期的效果,特别是政治领域的改革仍是希拉克运动的核心诉求。就当前阿尔及利亚形势而言,协调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关系是实现从混乱到稳定的关键步骤。首先是协调政权内部的权力关系。在军方的支持下,特本政府以反腐之名对布特弗利卡的亲信及其掌控的部门进行了初步的整肃,但军方并不愿完全推翻传统的政治体系,而是希望在宪法框架下完成新的权力安排。这一安排既要考虑政权内部的权力平衡,也要兼顾社会对政治改革的呼声。因此,现阶段的改革尚处于军方还政于民的过渡时期。其次是协调政权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军方意识到,一年来的希拉克运动已经创造出独立于政权之外的政治表达空间,民众通过这一非传统政治参与途径对政权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因此,政府必须继续推进改革,来疏导公共政治空间积蓄的政治力量,重新建立政权的合法性基础。2020年11月1日是阿尔及利亚打响武装反抗殖民主义第一枪的纪念日,政府选择这一天进行宪法草案公投毫无疑问是希望借助其象征意义来重新建立凝聚力。①Naila Benrahal,“El Djeich,àPropos du Référendum Constitutionnel,”L’Algérie Sera Plus Solide,November 10,2020,https://www.elmoudjahid.com/fr/nation/el-djeich-a-propos-du-referendum-constitutionnel-l-algerie-sera-plus-solide-1487,上网时间:2020年11月10日。
第三,阿尔及利亚政府与社会互动的可能结果。特本执政以来试图构建一个新阿尔及利亚的形象,他试图重新建立政府与社会新的互动模式,努力改变以往政治精英所主导的“唯发展”理念,关注社会民众对改变现状的普遍诉求,使当前的改革继续向前推进。首先,发展多元经济成为改革的重点。当今经济全球化趋势并未因世界经济低迷而走向衰弱,阿尔及利亚的经济结构过于依赖石油、天然气等资源,资源型的经济更容易受到国际资源环境的影响。在过去的历史中,国际资源价格的波动都会严重影响阿尔及利亚的经济,自20世纪末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政府已经着手开始调整经济结构,但是国内经济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油气资源。阿尔及利亚《自由报》发表社论,认为必须改变石油作为巩固政治体制的能源这一现状,并使之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工具。②Hassane Ouali,“Conjurer la Malediction,”Liberté,October 4,2020,https://www.liberte-algerie.com/editorial/conjurer-la-malediction-5671,上网时间:2020年10月7日。阿尔及利亚正在将公共资金继续向劳动力需求较多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倾斜,同时采取鼓励措施,发展多元经济模式,提升国内市场的经济活力,实现经济稳步增长。
其次,在不破坏现有政治体系前提下推进政治改革。当前青年人对于政治精英在独立战争和内战期间所建立的政治合法性越来越持怀疑态度,况且政治精英对权力的垄断以及其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使青年人认为当前政治精英的统治是不合格的。政府对社会的普遍心理做出及时反应,2020年10月4日,特本在部长会议上发表了持续推进改革的决议,强调加强司法和法治,以推进政治民主进程,恢复国家威望。但阿尔及利亚宪法草案公投23.7%的低投票率就是人们反感现实威权主义政治的明证,希拉克运动要求系统变革统治秩序,改变现状已经成为社会上普遍的心理。
最后,当前新冠疫情态势为政府的改革提供了一个缓冲期。自2020年10月以来,全球疫情传播重新出现转折,阿尔及利亚受疫情影响,医院重新出现病患增加而医护人员和医疗设施短缺的情况。特别是11月份以来,新冠疫情重新成为公众辩论的主要议题,社交网络上对病毒的恐惧超过了对政治变革的关注。虽然新的宪法修正案公投受到一定程度的抵制,但疫情造成的混乱局面为政府依照新的宪法修正案进行有序改革提供了契机。按照宪法修正案所构建的改革议程,政治空间将会对社会逐步开放。新冠疫情的持续为改革议程的执行减少了阻力,同时,改革议程的落实也会进一步催化希拉克运动内部新的分化,这场新冠疫情的流行期或许能够成为政治改革的过渡期。
总之,阿尔及利亚希拉克运动的爆发需要将其放在阿尔及利亚政治发展的进程中审视,其原因是在社会与政治体系发展过程中长期积淀形成的。在中东变局浪潮中,阿尔及利亚政治精英得益于经济情况暂时良好能够给予民众经济上的让步,及时将骚乱平息,然而骚乱产生的根源并未得到清除。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希拉克运动可被称为阿尔及利亚迟到的“阿拉伯之春”。但阿尔及利亚的希拉克运动所体现出来的特点又使其与中东其他国家的政治剧变区别开来。这次希拉克运动对阿尔及利亚威权主义政权政治合法性提出了新的考验,政权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可能成为影响地区整体政治生态的新变量,值得对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