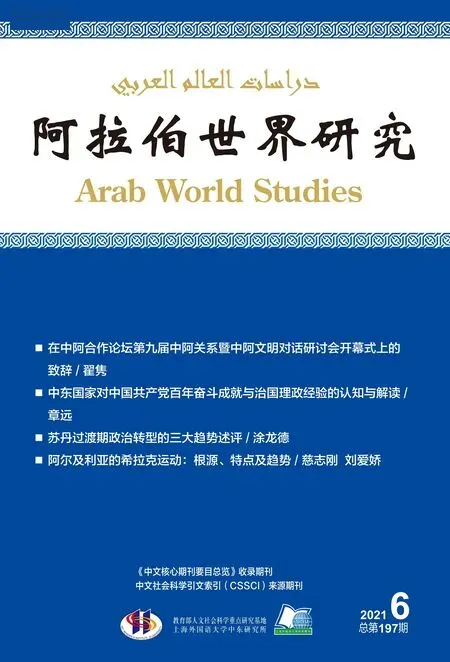21世纪以来巴勒斯坦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内涵、实践与挑战
成 飞
2021年5月10日,巴勒斯坦政治派别哈马斯(Hamas)和以色列之间时隔七年再次爆发激烈冲突。截至5月21日双方实现停火,此轮冲突共造成巴方232人死亡、1,900余人受伤;以方12死亡、300余人受伤。媒体对巴以冲突的惯常描述试图向公众传递两个信号:一是巴以是两个权力平等的行为体;二是巴勒斯坦人的抵抗只是单一的武装暴力。这种媒体叙事掩盖了两个最基本的事实:一是巴以之间权力高度不对称;二是除武装暴力手段外,非暴力抵抗构成了巴勒斯坦人日常对以斗争的主要形式,却极易被舆论所忽视。21世纪以来,作为巴勒斯坦人对以斗争的一种策略,非暴力抵抗运动日益成为巴勒斯坦问题走向最终解决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自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Intifada)爆发以来,基于大众的非暴力抵抗运动逐渐成为巴勒斯坦社会反对以色列占领、争取生存权与民族自决权的一种潜在趋势,是当前巴勒斯坦精英与民众主流政治话语的一部分。21世纪的巴勒斯坦非暴力抵抗运动始于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民间对以色列修建隔离墙的抗议。在2009年第六届法塔赫大会(The Sixth Fatah Conference)上,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将非暴力的“大众抵抗”(popular resistance)确定为巴勒斯坦对以斗争的主要政策之一。①“The Palestinian Popular Resistance and Its Built-in Violence,”The Meir Amit Intelligence and Terrorism Information Center,June 9,2013,https://www.terrorism-info.org.il/Data/articles/Art_20515/E_015_13.pdf,上网时间:2020年1月15日。该政策于2016年第七届法塔赫大会得到重申。巴勒斯坦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兴起虽受到地区和国际局势的影响,但本质上是巴以实力不对称的结构性产物,也是当下巴勒斯坦社会权力结构变化的反映,代表了未来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斗争的一种趋势。鉴于当前巴勒斯坦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弱势处境,对非暴力斗争方式的关注与分析有助于学界认识国际话语体系中巴勒斯坦单一、刻板的暴力形象背后的真实面貌,进而更加深刻地了解巴以冲突的本质与常态。
一、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中“非暴力”的内涵及其特征
非暴力抵抗作为人类文明进程中围绕斗争而形成的主要行为方式之一,其最本质特征是暴力的缺场。自20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形形色色的社会变革更多付诸的是非暴力抵抗的方式。而在全球化与通讯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这种方式已上升为一种变革的政治理念,基于这种理念而形成的非暴力抵抗学说正日益受到重视。当前,非暴力抵抗学说大致可分为道德伦理型与战略实用型两种,前者以甘地(Mohandas Gandhi)为代表,后者以吉恩·夏普(Gene Sharp)为代表。
甘地非暴力思想的典型特征是强烈的宗教伦理道德色彩,主要源自印度教与佛教中的“不伤生”原则,即对一切生命不加伤害,可视为一种爱的表达。①杜星、王巍:《非暴力作为解决冲突之法:甘地的政治伦理》,载《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3期,第24页。在甘地看来,这种“爱”等同于“非暴力”、“真理”与“神”。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甘地主张以“文明”的方式与敌人进行斗争,而这种“文明”的方式正是甘地非暴力思想中“爱与道德”的体现。甘地将“非暴力”视为一种基于爱与怜悯的生活方式,然后以此为手段达到最终“感化”和“净化”敌人心灵的目的。②孙艺桐:《甘地和平主义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第21页。
与甘地非暴力思想中过于强调道德伦理等和平主义信条不同,以吉恩·夏普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或战略学派更注重非暴力抵抗的方法与实用性。他们不需要实践者“爱”他们的敌人,也不需要改变他们。③Michael J.Carpenter,Unarmed and Participatory:Palestinian Popular Struggle and Civil Resistance Theory,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Victoria,2017,p.38.非暴力抵抗取决于人们的具体行动,而非信仰。④G.Sharp,Sharp’s Dictionary of Power and Struggle,Oxford:University Press,2012,p.7.夏普在概念上将非暴力抵抗降为一种功利主义或工具主义的手段。换言之,夏普的非暴力抵抗学说完全是基于实用主义基础之上的、以行动方式为导向的学说。1973年,夏普在《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学》一书中列举了198种非暴力抵抗的手段,根据其战略功能将其分为三大类:一是抗议和劝说,包括象征性的姿态和行动,旨在表达对某些政策或法律的和平反对,或说服他人接受特定的观点和行动。二是不合作,即限制或保留某些现有的经济或政治关系。三是直接干预,包括运用直接的物理障碍改变给定的位置,消极地破坏正常的或已建立的社会关系,或积极地通过创造性的行动,形成新的自主的社会关系。⑤G.Sharp,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Boston:Porter Sargent,1973,pp.109-445.
夏普的暴力抵抗学说实质上也是一种权力理论,其基本的理论假设为:统治政权的运行得益于公民的服从与合作,但两者构成的是一种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当统治政权实施不公的政策及由此附带的暴力行为时,公民的非暴力抵抗具有道德优势,可抵消权力不对称所带来的不利局面;具体而言,即有利于赢得舆论中的合法性,给统治政权造成压力或增加其统治成本。①Howard Clark,People Power:Unarmed Resistance and Global Solidarity,London:Pluto Press,2009,p.215.非暴力抵抗的特征据此可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它是一种积极的反应,而非被动的行为,其实施的目的是影响任何特定冲突的过程和结果。其次,它是一种抗议、抵制和干预的策略,不等同于谈判或调解等一般性的解决冲突的策略工具。再次,在多数情况下,非暴力抵抗是在制度化的渠道之外运作。从次,不论冲突中是否存在暴力行为,非暴力抵抗的效果可以独立评估。最后,非暴力抵抗具有潜在的、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但所面临的风险与道德困境相对较小。
就理论类型而言,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非暴力抵抗属于战略实用型的非暴力抵抗。作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中倡导的一种战略概念,“非暴力抵抗”最初由被誉为“巴勒斯坦非暴力之父”的巴勒斯坦裔美国人穆巴拉克·阿瓦德(Mubarak Awad)②20世纪80年末,穆巴拉克·阿瓦德被以色列当局以“安全威胁”为由驱逐出境。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其分析框架主要是对夏普的非暴力抵抗学说的继承。需要指出的是,现代非暴力理论多数情况下的分析焦点主要集中在主权国家内部,分析对象主要是公民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对抗。而巴勒斯坦面临的情况则是反抗外国占领的民族解放斗争,因此必须将其置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具体的历史社会环境中加以分析。
首先,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策略,现阶段巴勒斯坦非暴力抵抗运动可定义为:在冲突或易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当解决不满和寻求变革的传统制度途径无法实现时,个人和集体为改变压迫或不公正的条件而采取的、主要以非暴力为特征的、社会各阶层参与的抵抗运动,是一条介于甘于被征服与暴力反抗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从性质上来看,巴勒斯坦非暴力抵抗运动则是一场反对以色列占领、争取生存权与民族自决权的民族解放运动。
其次,外部角色在巴勒斯坦非暴力抵抗中的特殊作用主要基于三点:一是巴以之间实力严重不对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控制是全方位的,既体现在军事方面,又体现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巴勒斯坦缺乏足够的资源与力量同以色列进行对称性对抗,因此必须借助外部角色的参与。二是国际法规条约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建立以1967年边界、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是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并以联合国242号和338号决议等作为其合法性保障。以色列的长期占领、非法定居点的持续扩张、隔离墙的修建等行为不仅是对巴勒斯坦人生存权和民族自决权的侵犯,更是对联合国有关决议、《日内瓦公约》等相关国际条约法规及国际共识的违反。这为国际社会支持或参与巴勒斯坦非暴力抵抗运动提供了道德和国际法意义上的正当性。三是以色列生存与发展的高度对外依赖性。以色列国土狭小、资源匮乏、市场有限,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和市场高度依赖外部世界,特别是欧美国家。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顽固立场及违反有关国际法,可能转化为国际社会对它的外交和经济制裁,这无疑将对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与政策产生巨大影响。
最后,非暴力斗争与巴勒斯坦本土抵抗文化“苏木德”(Sumoud)在内涵上契合度较高。阿拉伯语中的“苏木德”①该词对应的英文是“perseverance”或“steadfastness”,意为“坚持不懈”。一词在词义上近似于“抵抗”,其更为准确的解释是“以一切手段保持坚定”。②Michael Bröning,The Politics of Change in Palestine:State-Building and Non-Violent Resistance,London:Pluto Press,2011,p.136.在被占领土特殊的社会结构条件下,“苏木德”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又是一种战略思想,强调通过日常行动、忍耐与抵制以色列的统治政策,维持巴勒斯坦人的特性、文化、传统与习俗,即一种民族的集体认同。③Fadi Zatari,“Palestinian Culture of Sumud,”Daily Sabah,April 4,2018,https://www.dailysabah.com/feature/2018/04/04/palestinian-culture-of-sumud,上网时间:2020年6月25日。作为抵抗方式的“苏木德”有消极与积极之分,但本质上都是注重在当下保持自我,为未来的自决、自由和平等开辟新的视野和希望。积极的“苏木德”接近于一般语境中的非暴力抵抗,但内涵更为丰富。
非暴力斗争在巴勒斯坦特殊的历史社会条件下具有深厚的思想土壤。非暴力抵抗早已根植于巴勒斯坦集体对外来强权占领的回应当中,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爆发的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至今仍是巴勒斯坦非暴力斗争的典范。进入21世纪后,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的爆发为巴勒斯坦非暴力斗争的再次涌现提供了条件。非暴力抵抗运动作为一种新的战略趋势,代表了巴勒斯坦对以斗争在政治策略上的一种进步。
二、巴勒斯坦非暴力抵抗运动的阶段与实践
2000年至2004年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是自巴以“和平进程”开启以来双方经历的最暴力、最血腥的一次冲突。从结果来看,此次冲突不仅彻底打破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社会有关各方协助下巴以之间形成的和平政治氛围,一定程度上也宣告了巴勒斯坦武装暴力手段在斗争策略上的失败。在巴以实力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暴力冲突除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外,还给巴勒斯坦社会带来巨大的心理创伤。在“9·11”事件后所形成的以“反对极端暴力”和“反恐怖主义”为特征的国际政治舆论环境中,自杀性炸弹袭击不仅激化了以色列社会对巴勒斯坦人的仇恨与不信任,而且还强化了巴勒斯坦人在国际话语中单一刻板的暴力恐怖的形象,最终为以色列更加激进、强硬的报复性行动留下“口实”。这种内外环境相结合,为巴勒斯坦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兴起提供了新的社会与政治空间。该时期的巴勒斯坦非暴力抵抗运动以民间抵制以色列修建隔离墙为起点,其发展至今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一)反隔离墙运动
2002年6月,以色列以安全为由宣布沿1967年巴以边界线修建隔离墙,但其实际路线不少已深入至巴勒斯坦境内,这意味着约旦河西岸的土地将被大面积侵占。隔离墙经过的许多地区,居住与生产区域分离,对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生活构成巨大威胁。因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第二次大起义期间功能缺失,以非暴力形式表现的反隔离墙运动由此展开。该时期反隔离墙运动呈自发性和地方化特点。
从实践架构看,反隔离墙运动主要由互为关联的三部分构成。首先,组建立足当地社区的抵抗机构“大众委员会”(Popular Committee)。布德鲁斯(Budrus)村是西岸地区开此组织先河的代表。①Michael J.Carpenter,Unarmed and Participatory:Palestinian Popular Struggle and Civil Resistance Theory,p.132.当地民众借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的经验,以社区为基地成立抵抗隔离墙的“大众委员会”。但具体到各地大众委员会建立所基于的政治组织结构时,则具有较大差异,具体可归为两类:一是已有的政治派别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所确立的政治组织结构;二是当地活动人士重新倡导设计的政治组织结构。作为一种决策和行动指导机构,各地大众委员会整体呈现草根性、自愿性、包容性的特征,其核心成员和一般成员背景多样,涉及巴勒斯坦各政治派别及社会各领域,后者如商人、学生和妇女团体等。②J.Norman,The Second Intifada:Civil Resistance,New York:Routledge,2010,p.1.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有法塔赫和哈马斯等政治党派人士参与,但参与者多基于个人立场,而非政治党派的立场。大众委员会的组织理念和架构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实现反隔离墙运动在社会动员潜能上的最大化,即参与的大众化。但在内部分工上,大众委员会除动员民众、协调活动的功能外,还设专人负责培训现代传媒通讯工具的运用,联系和团结以色列和平主义者及国际活动人士。所有这一切当时都服务于保卫即将因隔离墙修建而被侵占的土地。但从长远来看,大众委员会这一在组织方面具有开创性的举措成为日后巴勒斯坦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一大特点。
其次,组建活动的国际化网络。通过与国际活动人士建立联系,将巴勒斯坦人抵抗隔离墙修建的斗争国际化,构成了巴勒斯坦非暴力抵抗运动的重要一环。巴勒斯坦人与国际人士联合反抗以色列占领的历史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当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与欧美国家左翼政党及知识分子建立了紧密联系,这些国际活动人士在以武装斗争为特征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巴以和平进程的开启,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参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活动人士与以往相比表现出了不同特征。
一是整体上的去意识形态化。相较于之前统一的意识形态色彩,如今的国际活动人士更多是立足于多元价值追求基础上的专业活动人士,如人权活动家、环保主义者、反资本主义和反全球化主义者等;①A la M.Alazzeh,Non-violent Popular Resistance in TheWest Bank:The Case ofthe Popular Struggle Committees,Ramallah:Birzeit University Press,2011,p.33.二是非暴力理念取代武装暴力反抗的革命理念追求;三是与之前武装反抗阶段相比,现今的国际活动人士直接进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参与抵抗行动。同时,与其他国家行为体和国际机构提供的支持不同,国际活动人士参与反隔离墙运动及整个巴勒斯坦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最终目的在于结束以色列的占领,因此其基于的是一种政治考量,而不仅是人道主义的视角。由此,在具体的功能表现上,除在共同行动中起到保护巴勒斯坦人的作用外,国际活动人士最主要的作用是自我转化为一种“中间人”,通过媒体和自我叙事,将巴勒斯坦人的斗争国际化,从而转化为对以色列的一种国际压力。
最后,反隔离墙运动中的具体非暴力实践。这些实践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在隔离墙现场进行有组织的、以民众游行抗议为主、直接干预为辅的非暴力抵抗行动。抗议者在行动前经常采取说服性行动,如以递送信件等形式向隔离墙修建现场的以色列士兵表明,其抵抗目标在于保护自己的土地,而非针对以色列人。②J.Norman,The Second Intifada:Civil Resistance,p.39.在游行抗议运动中,巴勒斯坦人借助许多创造性的“工具”进行象征性抵抗,如巴勒斯坦国旗、象征回归的钥匙、“万人坑”、葬礼、音乐、演讲等。③Michael J.Carpenter,Unarmed and Participatory:Palestinian Popular Struggle and Civil Resistance Theory,p.140.直接干预则集中出现在修建隔离墙的施工过程当中,主要采取“围堵”、“占领施工机器”等直接的身体干预形式。在此基础上,活动者还进行了许多创新性的直接干预。例如,在以色列方面强制移除橄榄树的过程中,抗议者组成“人链”,与橄榄树捆绑在一起,阻止以方对巴方土地的侵占。①Mala Carter Hallward,“Creative Responses to Separation:Israeli and Palestinian Joint Activismin Bil'in,”Journal ofPeace Research,Vol.46,No.4,July 2009,p.548.第二,向以色列高等法院提起诉讼。以色列和平人士,包括退伍军人和前国家安全情报人员,通过向以色列高等法院请愿,发起反对强制侵占巴勒斯坦土地行为的法律战。②根据以色列法律规定,只有以色列公民才有资格向本国司法系统提起诉讼。此类行动在反隔离墙运动发起时就已存在,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以色列公民的参与,以及以色列司法系统在程序上的相对独立性使其具有可行性。第三,星期五游行抗议的制度化。在反隔离运动的日常非暴力行动中,星期五的游行抗议尤为重要。它是当地民众在行完聚礼后由大众委员会协调、组织发动的,其规模甚于平日,并有大量国际活动人士和以色列和平人士参与。抗议期间,为吸引媒体和保持舆论关注度,活动者结合、借用不同主题和载体进行创造性抗议,如“灾难日”(Nakba Day)等历史意义重大的纪念日、热点事件或流行文化等。随着大部分隔离墙工事的完成,星期五的游行抗议逐渐取代了每日的抵抗活动,成为巴勒斯坦非暴力抵抗运动具有象征性的制度化抗议行动。
随着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的结束,国际媒体与舆论对隔离墙问题的关注度持续增强,反隔离墙运动也在不断的非暴力抗争中取得了实质性成果。布德鲁斯村于2004年4月凭借非暴力抗争最终迫使以色列当局将隔离墙路线撤回至以色列边界一侧。这一胜利激发了从拉马拉、萨尔菲特(Salfit)到耶路撒冷地区所有受隔离墙影响的农村地区有组织的非暴力抵抗。此后,包括比杜(Biddu)、拜特·索瑞克(Beit Sourik)及阿布迪斯(Abu Dis)等在内的数个巴勒斯坦村庄,通过非暴力抗争在不同程度上挽回了被以色侵占的土地。③Michael J.Carpenter,Unarmed and Participatory:Palestinian Popular Struggle and Civil Resistance Theory,p.138.同年7月9日,国际刑事法院正式宣布以色列修建隔离墙的行为违反国际法,应立即终止,同时拆除已修建的隔离墙,并对巴方相关自然人和法人予以相应赔偿;④Leah Friedman,“Leg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Wall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Advisory Opinion),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July 9,2004,”Australasian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http://www.austlii.edu.au/cgi-bin/sinodisp/au/journals/SydLawRw/2005/37.html?query=,上网时间:2020年6月27日。7月20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要求以色列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裁决。这些判决和决议为隔离墙的定性和反隔离墙运动的合法性确立了国际法依据。以色列政府于2005年宣布修改隔离墙路线,新规划的隔离墙路线所侵占的巴勒斯坦土地与之前相比减少了近一半。①R.Dolphin,The West Bank Wall:Unmaking Palestine,London:Pluto,2006,pp.59-60.
与此同时,作为一种斗争策略,反隔离墙运动中的非暴力抗争在符号性策略与舆论传播方面也获得了显著进展,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拉马拉地区的比林。比林将已有的斗争成果与非暴力抗争方面的创新及舆论营造相结合,使其成为巴勒斯坦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圣地”,由此形成的特定叙事以各种方式“走向”国际。除借助一般媒体外,比林的成就还表现在三个特殊方面:一是比林成为许多国际政要、公众人物及普通民众造访巴勒斯坦的代表性地点,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历史学家艾兰·佩普(Ilan Pappe)、“圣雄”甘地之孙拉吉莫罕·甘地(Rajmohan Gandhi)、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之孙马丁·路德·金三世(Martin Luther King III)等。②Iyad Burnat,Bil’in and the Nonviolent Resistance,n.p,2016,p.10.二是在相关国际人士和组织的赞助下,比林当地的活动家行至欧美国家,进行关于巴勒斯坦人反隔离墙运动的巡回演讲。三是通过现代影像技术传播巴勒斯坦人的遭遇和抵抗。2011年,比林当地农民伊马德·博纳特(Emad Burnat)与以色列导演盖伊·戴维迪(Guy Davidi)联合拍摄纪录片《五台破相机》(5 Broken Cameras),以反讽的方式记录了比林民众对隔离墙的抗争经历。③Marwan Darweish and Andrew Rigby,Popular Protest in Palestine:The Uncertain Future of Unarmed Resistance,London:Pluto Press,2015,p.78.该片成当年在多个国际影展评价甚高的获奖记录片,并于2013年获第85届奥斯卡金像奖(Academy Award)最佳记录长片提名。
综上所述,虽然非暴力抵抗在反隔离墙运动中成就有限,未能实现最终目标,但仍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反隔离墙运动有利于改善巴勒斯坦人“暴力”“恐怖”的刻板形象。由于国际话语权缺失,巴勒斯坦人的国际形象多以极端、狂热的暴力形象出现在西方媒体叙事中,特别是第二次巴勒斯然大起义中的自杀性袭击,使得这种形象进一步固化。而通过网络、媒体及国际活动人士与以色列和平主义者的传播,非暴力抗争有利于展示巴勒斯坦人“求和平”与“受压迫”的形象,增强其斗争的合法性。其次,反隔离墙运动有利于强化非暴力行动的有效性。在奥斯陆协议所确立的巴以特殊互动政治框架下,暴力手段缺乏相应的政治空间,而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的灾难性后果则是对其有效性的否定。作为一种斗争策略,虽然非暴力行动在反隔离墙运动中所取得的成就有限,但毕竟是在巴以权力非对称结构下的一次难得的胜利,尤其是国际刑事法院、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针对隔离墙问题的判决与决议,为其在国际层面奠定了合法性基础。诚如一位参与法律诉讼的以色列律师所言:“如果没有当地民众持续进行的抗争,这一切都不会发生。”①Michael J.Carpenter,Unarmed and Participatory:Palestinian Popular Struggle and Civil Resistance Theory,p.152.
(二)反占领运动
非暴力行动在反隔离墙运动中的有效性及其所获得的舆论关注和外部支持,使得反隔离墙运动逐渐在政治话语和实践中升级为一场规模更大的反占领运动。
首先,非暴力斗争由民间自发行动上升为官方政策。2009年8月,法塔赫在伯利恒召开第六届代表大会。此次大会的最主要特点是弱化“武装斗争”的政治基调,将基于比林反隔离墙斗争经验的“大众非暴力抵抗”确立为对巴勒斯坦以斗争的主要政策之一。同时,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公布总理萨拉姆·法亚德(Salam Fayyad)制定的第十三个政府计划。在这个为期两年的国家建设计划中,政府决定成立“隔离墙与定居点事务部”(Ministry of the Wall and Settlement Affairs),以促进和保障受隔离墙和犹太定居点影响地区的稳定和基本需求,支持民众进行和平、非暴力的抵抗行动。
巴勒斯坦官方公开将非暴力抵抗视为反抗以色列占领的政策,其原因主要基于四点:一是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的离世。阿拉法特的去世,为以阿巴斯为首的温和势力主政和调整对以政策提供了机会。在第六届法塔赫大会上,许多“元老派”失掉了在各委员会中的领导席位,而新进的“少壮派”多是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时期的领导者,是非武装斗争的倡导者,他们甚至呼吁将“武装斗争”从党纲中删除。②Ibid.,pp.178-179.二是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间武装暴力手段的失败,以及以色列军事行动所造成的毁灭性后果。三是反恐和去暴力极端主义的国际政治环境。“9·11”事件之后,“反恐”成为国际政治的主流话语。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巴极端派别发动的自杀性炸弹袭击使巴勒斯坦人的形象在西方主流媒体和国际舆论中更加僵化、扭曲,这严重损害了巴方对以斗争的合法性基础。2009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发表演讲称 “只要巴勒斯人继续从事暴力活动,就不可能获得胜利”①A la M.Alazzeh,Non-violent Popular Resistance in TheWest Bank:The Case ofthe Popular Struggle Committees,p.38.。四是非暴力行动在反隔离墙运动中被证明有效以及民间社会对其认可度的增加。
其次,建立统一的组织协调机构。巴勒斯坦官方接受非暴力抵抗政策,并将非暴力抵抗政策作为挑战以色列占领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政治精英与底层民众之间在对以斗争上的某种联合,在组织方面体现为“大众斗争协调委员会”(Popular Struggle Coordination Committee)的建立。大众斗争协调委员会诞生于2009年4月举行的第四届比林非暴力斗争年会期间,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资助,属于半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其宗旨一是确立对以斗争的一致战略,为约旦河西岸各大众委员会提供一个统一的指导、协调平台;二是克服民众抵抗运动呈现的碎片化和地方化现象。除此之外,作为第六届法塔赫大会决议的具体体现,官方还成立了大众抵抗民族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Popular Resistance);同时,法塔赫内部其他派别又另行组建了大众抵抗高级后续委员会(Popular Resistance High Follow-up Commission)。②Marwan Darweish and Andrew Rigby,Popular Protest in Palestine:The Uncertain Future of Unarmed Resistance,pp.109-110.统一协调机构的建立,不仅联接了民间各大众委员会与官方的主要党政机构,而且还与一些地方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建立联系,使整个西岸地区迅速形成一个以反对以色列占领为宗旨的松散政治联盟,为进一步的动员和抵抗行动提供了条件。
最后,斗争目标由抵抗隔离墙修建的地方性单一目标,转变为涉及整个西岸地区、以反占领为宗旨的多元目标。反占领运动在地理范围上超越了之前反隔离墙运动所局限的农村地区,其针对的目标也从反隔离墙运动中的单一目标转向与以色列占领有关的所有目标。因此,在具体行动方面,除各种游行示威等常规抗议外,反占领运动中的直接干预和不合作的非暴力行动开始增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非暴力抵抗行动主要有以下五类。
第一,“凿墙”行动。首次以隔离墙为目标的“凿墙”行动是在2009年由西岸各抵抗委员会联合组织的。在舆论宣传中,巴勒斯坦人将“凿墙”行动视作类似于南非反种族隔离的行为。这种象征性抵抗的目的在于通过被以色列视为挑衅的行为,引发媒体和国际舆论的关注。出于这种目的,活动人士经常将其与重大的历史事件相联系,如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柏林墙倒塌事件。
第二,封堵道路。西岸地区的犹太定居点与以色列本土之间主要由纵横交错的高速路网和专用通道相连接,因此封锁和堵塞这些交通要道成为反占领运动中主要的行动策略之一。例如,2012年,通过大众斗争协调委员会的组织协调,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部分欧洲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下,150名国际活动人士和2,000名巴勒斯坦人参与了对90号和443号公路的封堵。①Michael J.Carpenter,Unarmed and Participatory:Palestinian Popular Struggle and Civil Resistance Theory,p.198.特拉维夫与耶路撒冷之间高速公路由此中断,数千名犹太定居者被迫滞留数小时,以色列政府不得不进行有限的军事动员。此类非暴力行动将犹太定居者的日常生活纳入抵抗行动之中,以此表达一种强烈的反抗意识。正如一位组织者所言:“只要定居点与定居者仍然继续困扰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就不能正常生活下去。”②Activestills,“Photos:Palestinians Block Route 433 to Protest Settler Violence,”+972 Magazine,October 17,2012,https://www.972mag.com/photos-palestinians-block-route-443-toprotest-settler-violence/,上网时间:2020年6月28日。
第三,复垦计划。以色列法律规定,超过三年未利用的土地直接收归政府所有。这一规定事实上为以色列吞蚀和占领巴勒斯坦土地提供了所谓的“合法性”依据,特别是在其完全控制下的约旦河西岸C区。约旦河谷地、南希伯伦等是C区巴以关系最为紧张的地带。当地的犹太定居者与巴勒斯坦人围绕土地展开的日常争夺异常激烈。为应对由此造成的不利局面,巴勒斯坦民众联合专业活动人士实行复垦计划,将长期废弃和未利用的土地以及以色列政府计划侵占的土地重新加以开垦利用。在此过程中,巴勒斯坦地方政府通常也会参与其中,并提供一定的物资支援。2012年,纳布卢斯(Nablus)市政府向复垦行动中的当地农民免费提供了数台拖拉机,用以快速耕种靠近犹太定居点的土地。③Marwan Darweish and Andrew Rigby,Popular Protest in Palestine:The Uncertain Future of Unarmed Resistance,p.91.复垦行动体现的是巴勒斯坦人的“苏木德”精神,即在自己的土地上坚定不移地生存下去,就如他们的口号所言:“生存就是抵抗”。
第四,宣誓主权。此类非暴力行动的主要目的在于在被占领土上制造一种既成事实,以宣誓主权,其中较为典型的当属2013年在东耶路撒冷附近的行动。2013年1月,约250名活动人士和志愿者在东耶路撒冷与马阿勒·阿杜米姆(Maale Adumim)定居点之间的巴卜·沙姆斯(Bab al-Shams)搭建了20座营帐,以期造成既定事实,抵制以色列在该地扩张定居点的企图。除此之外,修复在以色列控制地区的废弃村庄也是宣誓主权行动的表现形式之一。宣誓主权行动从现实政治、社会和历史三个层面引发了巴勒斯坦社会的共鸣。此类行动既表达了巴勒斯坦人对巴以现实政治状况的不满与反抗,又是其渴望回归正常生活的一种呼吁,同时也是对1948年和1967年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大灾难的一种积极回应,是对其“回归权”的坚定表达。
第五,经济抵制。2010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发动经济抵制运动,目标为西岸地区犹太定居点生产的商品。为有效执行这项抵制行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一方面与西岸地区的工商界联合成立卡拉马基金(A l Karama Fund),以协调政策、宣传和鼓励巴勒斯坦民众抵制定居点商品;另一方面通过立法将抵制行动转化为政府意志。2010年4月,阿巴斯签署总统法令,禁止销售定居点商品,违法者最高可处两年监禁、罚款1.4万美元。①Marwan Darweish and Andrew Rigby,Popular Protest in Palestine:The Uncertain Future of Unarmed Resistance,p.83.在具体操作层面,政府一方面在市场交易中打击销售定居点商品的行为,并将查获的定点商品集中销毁;另一方面通过卡拉马基金雇佣专门的巡视人员挨家挨户进行宣传,宣传内容包括认识和鉴别被抵制的定居点产品。同时,民众需签署“尊严誓言”(Dignity Pledge),以表明决心抵制犹太定居点产品。②Ibid.
政府发动的经济抵制行动在民众中获得了较为广泛的支持。根据巴勒斯坦政策与调查研究中心2010年6月的民意调查显示,72%的巴勒斯坦人支持经济抵制行动;③Palestinian Center for Policy and Survey Research,Palestinian Public Opinion Poll No.36,June,2010,http://www.pcpsr.org/sites/default/files/p36e.pdf,上网时间:2010年7月1日。该中心2015年3月的民调显示,85%的巴勒斯坦人支持抵制以色列产品。④Palestinian Center for Policy and Survey Research,Palestinian Public Opinion Poll No.55,April,2015,https://www.pcpsr.org/sites/default/files/poll%2055%20fulltext%20English%20final.pdf,上网时间:2020年7月1日。作为针对以色列占领所发起的一项不合作运动,经济抵制不仅有效调动了民众的抵抗意识,而且使其成为巴勒斯坦在常规冲突中对抗以色列的常态化工具。例如,为回应2014年以色列对加沙的入侵,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将抵制的产品范围从西岸定居点扩大至整个以色列;次年,针对以色列暂停转交代收税款的举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选择性地对以色列的六家食品企业和医药公司的产品进行抵制。⑤Haggay Etkes and Michal Weissbrod,“The Palestinian Boycott of Israeli Goods:Economic Ramifications,”Strategic Assessment,Vol.19,No.3,October 2016,pp.19-20.
作为一项非暴力行动,经济抵制较强的动员性及实践上的常态化主要缘自巴勒斯坦在以色列军事占领下所形成的极度不平等的经济依附关系。以色列长期的军事占领和强权行为,使得巴勒斯坦人在个人和集体层面形成了强烈的愤恨心理。在所有代表和象征以色列的符号当中,日常商品是巴勒斯坦人直接接触的最为紧密和广泛的具有“以色列或犹太”属性的具体存在。因此在冲突背景下,巴勒斯坦人的愤恨心理极易转化为整体性的民族主义情绪。在相比暴力抵抗所需付出高额代价的情况下,抵制以色列商品的非暴力行动则合乎逻辑地成为抵抗运动的不二之选。
以反占领为主题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是反隔离运动的进一步升级。官方政策的确立、统一协调组织的建立及实践形式上的多样化,表明非暴力抵抗已经在巴勒斯坦社会趋向一种共识。虽然至今仍在进行中的反占领运动实质成效有限,但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继续破除西方主流媒体中巴勒斯坦人单一的“极端暴力”形象,揭示巴勒斯坦对以斗争中更为普遍且被忽略的一面。其次,持续的非暴力行动有利于在巴勒斯坦社会中培养一种大众抵抗文化,而在当前巴以政治谈判停滞的情形下,这对于提振武装暴力手段“退场”后消沉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士气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巴勒斯坦非暴力抵抗运动在形成巨大的政治气候之前仍面临一系列挑战。
三、巴勒斯坦非暴力抵抗运动的问题与挑战
从反隔离墙运动到至今的反占领运动,西岸地区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虽然已构成当前巴勒斯坦政治主流话语的一部分,但产生的实质影响有限。当前,非暴力抵抗运动面临来自巴以双方不同层面的一系列问题的掣肘与挑战。
(一)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非暴力抵抗运动缺乏建设性回应
面对巴勒斯坦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兴起,以色列社会自下而上缺乏应有的建设性回应。
首先,以色列社会响应巴勒斯坦非暴力行动的和平运动十分有限。伴随西岸地区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兴起,以色列社会致力于结束占领、实现巴以和解的和平运动亦趋于活跃。除“现在就要和平”(Now Peace)、“检查站观察”(CheckpointWatch)、“人权拉比”(Rabbis for Human Rights)等传统团体外,以色列国内近年来还涌现了“抵抗隔离墙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s Against the Wall)、“不服从妇女运动”(Lo Metsaylot)、“记忆”(Zochrot)等一批新的和平团体。这些和平团体的主要成员是以色列社会中少数具有左翼倾向的中上层精英群体。①Om ri Arens and Edward Kaufman,“The Potential Impact of Palestinian Nonviolent Struggle on Israel:Preliminary Lessons and Projections for the Future,”Middle East Journal,Vol.66,No.2,Spring 2012,p.248.他们的实践活动或在以色列本土以街头抗议和舆论宣传的方式进行,或直接进入西岸地区与当地巴勒斯坦活动人士联合行动。但其“反占领、求和平”的话语在整个以色列社会至今仍处于边缘地位,动员能力十分有限。
一方面,尽管以色列和平活动者反对政府扩张定居点、违反人权及集体惩罚巴勒斯坦人的政策,但其在以色列本土的抗议行动是在国家的制度渠道内进行的,是以色列多元社会中一种正当性的利益诉求表达,如此也就避免了与政府的直接对抗。正因如此,他们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就十分微弱。而对于这些和平活动者而言,如果在以色列社会进行制度渠道之外的抗议行动,很容易与政府产生直接对抗,导致的后果会危及他们的精英地位及其所取得的社会成就,这种高昂代价是需极力避免的。
另一方面,以色列公众对和平运动整体表现冷淡。以色列公众对巴勒斯坦被占领的现状不予关注,尤其是隔离墙修建之后更甚。诚如一位以色列和平活动者所言:“以色列公众对结束占领缺乏兴趣,因为占领与他们无关,对他们的生活没有影响。”②Marwan Darweish and Andrew Rigby,Popular Protest in Palestine:The Uncertain Future of Unarmed Resistance,p.127.这种认识同样体现在以色列主流媒体的基本立场当中:“对于巴勒斯坦或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事,我们不想将其带入公众的视野当中,因为他们不感兴趣。”③Ibid.此外,在媒体的引导下,以色列公众往往将巴勒斯坦非暴力抵抗行为视作安全事件,经常透过暴力威胁的“棱镜”视之。其关注点不在于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其根源何在,而只在于如何处理抗议事件本身。在这种逻辑下,巴勒斯坦非暴力行动者往往被视为扰乱秩序、骚扰和袭击以色列士兵的狂热分子。这种主流舆情使得以色列和平活动者在其社会中自然地成为被边缘化的对象,他们更被一些右翼势力视为犹太民族利益的威胁和叛徒。随着以色列社会的日益右倾,这种认知倾向无疑会日趋强化。
其次,以色列官方一如既往的强硬政策阻碍巴和平进程。自2009年起、特别是2011年中东剧变后,以色列官方开始将对巴勒斯坦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关注提升至战略层面,重点防止其由地方转变为全国动员。但这种战略上的重视并未转化为对巴勒斯坦人的建设性回应,而是延续了其一贯的强硬政策。在舆论宣传中,以色列政府及其宣传机器将巴勒斯坦非暴力抵抗运动视作一种根植于暴力文化之中的非理性行为,透过安全视角,重点突出和强调其背后所隐藏的潜在暴力因素,甚至将各类非暴力抵抗行动冠以“恐怖主义”之名,如经济抵制行动被宣传为“经济恐怖主义”。①Michael Bröning,The Politics of Change in Palestine:State-Building and Non-Violent Resistance,p.156.面对巴勒斯坦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兴起,特别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参与,以色列政府定期发布专门性的“巴勒斯坦煽动指数”(Palestinian Incitement Index),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制裁相关参与人员。在西岸地区,以色列军队对于巴勒斯坦人的非暴力抗议一如既往以橡皮子弹、催泪瓦斯或逮捕和行政拘留等强硬措施回应。以色列政府的这种强势回应,本质上仍是巴以权力不对称态势之下的强权思维的体现,其背后既有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也是其过度迷信军事力量等硬实力是解决冲突的唯一有效手段的表现。
综上所述,对于巴勒斯坦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兴起,除少数和平主义团体外,以色列社会从公众到官方,缺乏整体的建设性回应。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色列社会看待巴以关系的视角,是一种泛化的安全观念。作为以色列官方意识形态宣传中的核心组成部分,这种泛化的安全观念的建构既缘于建国前犹太人在历史上作为流散族群所遭受的种种迫害的历史记忆,以及自建国后阿以战争及延续至今的巴以之间紧张对立的冲突态势,也出自以色列—犹太权力精英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话语叙事的塑造。这种安全视角背后是以色列人自我定位的“受害者”角色和排他性的民族利益。
(二)巴勒斯坦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凝聚力和社会动员能力不足
目前,掣肘巴勒斯坦非暴力抵抗运动发展壮大的首要因素,主要缘于巴勒斯坦内部,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巴勒斯坦社会内部的分裂。这种分裂的表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以色列占领造成的地理空间上的破碎与分裂。根据《奥斯陆协议》的规定,作为巴以和平进程的一部分,约旦河西岸被划分为A、B、C三区。其中,A区由巴方控制,B区由双方共管,C区由以方控制;再加之散落在西岸地区为数众多、规模不等的犹太定居点,以及为其配套的专用通道等基础设施、路障、“安全区域”和军事检查点、封闭区域等,将整个西岸地区在地理空间上切割得支离破碎,使城乡各地之间的人员流动与联系变得困难重重。其次,政治上的分裂。21世纪以来,巴勒斯坦最重大的政治灾难莫过于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之间的公开冲突。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各自为政,使得党派主义文化盛行的巴勒斯坦在政治上进一步分裂。政治上的分裂与地理空间上的破碎相结合,直接导致以家族认同为特征的地方政治的抬头。①Jacob Høigilt,“Nonviolent Mobilization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Popular Resistance and Double Repression in the West Bank,”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52,No.5,2015,p.639.在此背景下,巴勒斯坦社会内部各政治势力之间内斗加剧,消解了其有限的政治动员能力,进而极大限制了非暴力行动者建立强大社会动员网络的能力。
第二,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网络的松散与多元利益诉求下的生存竞争的强化。早在2010年,加沙与西岸地区的本土非政府组织就已达2,400个左右,包括慈善团体、以发展为导向的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及其他以服务公众利益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组织等。②Karin A.Gerster,Palestinian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Their Socio-Economic,Social and Political Impact on Palestinian Society,Ramallah:Rosa Luxemburg Foundation,2013,p.21.虽然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众多,但就非暴力抵抗运动所需的组织支撑力量的现状而言,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缺乏有效协调整个社会网络的主导性组织力量。尽管为响应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发展而成立“大众斗争协调委员会”(PSCC),但同时与之并存的还有“抵制隔离墙运动”(STWC)、“大众抵抗民族委员会”(NCPR)和“大众抵抗高级后续委员会”(PRHFC)。这四个组织虽都是基于指导、协调非暴力抵抗运动需要而设立的,但互不统属,其背后涉及不同政治派系之间的分歧与竞争。如“抵制隔离墙运动”背后是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FLP)和巴勒斯坦民族倡议(PNI),而其他三个委员会则分属法塔赫内部的不同派系。由于缺乏统一、一致的协调组织力量,在非暴力行动中,各草根组织之间在倡议、宣传及实践等方面的相互排斥与竞争,极大削弱了整个非暴力运动在组织上的凝聚力。
其二,资本稀缺导致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去民族主义化”的趋势加强。《奥斯陆协议》签署后,以西方为主的外部资本以援助的形式进入巴勒斯坦。在巴勒斯坦资本极度短缺的情况下,西方资本成为支撑和维持整个巴勒斯坦组织体系运转的关键。具体到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西方资本可占其年度预算的72%左右。③Ibid.,p.22.在此情况下,“亲资本”政策成为这些组织发展的必然结果,突出表现许多以自愿和互助为宗旨的草根组织,按西方资本运转的制度要求向类似于西方社会专业化组织的方向转变,而“专业化”也成为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能否获得西方资本援助的主要依据。同时,缺乏能力或缺乏意愿向专业化转变的组织则逐渐被边缘化,尤其是民族主义色彩强烈的草根组织。结果,为获取西方资本以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许多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竞争加剧,导致“去民族主义化”的趋势加强。而获得资金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则必须按资助者的议程运作。因此,许多非政府组织原本适应巴勒斯坦具体历史社会发展所需的功能趋于弱化。有学者坦言,这些西方资本资助的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与自己的民众逐渐疏离,它们工作的趋向主要在于迎合其资助者的需要,而不是巴勒斯坦民众的真实需求。①Benoit Challand,“Looking Beyond the Pale:International Donors and Civil Society Promotion in Palestine,”Palestine-Israel Journal,Vol.12,No.1,2005,p.23.
第三,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非暴力抵抗运动中的角色愈加矛盾。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是现阶段巴勒斯坦国家主权的象征与代表。但是,相比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通过革命而建立的民族主义政权,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产生更多是多方利益博弈的结果,即《奥斯陆协议》的产物。这就意味着其只能在后者所确立的制度框架内行使有限的自主权。这种自主权力的先天不足一定程度上导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未尽的民族主义运动中经常性地充当一种矛盾性的角色。
一方面,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及其民族国家利益的代表者与维护者,在解放被占领土、建立主权独立、完整的巴勒斯坦国等未尽的民族事业当中,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有着天然的责任与义务,这也是其合法性的最主要来源。在当前武装暴力手段失效、政治谈判未果的情形下,作为一种新的民族主义趋势,非暴力抵抗运动代表了巴勒斯坦相当一部分主流民意。因此,不论从民族利益,还是从巩固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的角度出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将非暴力抵抗运动作为对以斗争的一项政策都具有无可置疑的合理性。
另一方面,作为《奥斯陆协议》制度安排下的产物,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受制于与以色列签订的各项制度规则。例如,巴以安全协调制度规定,巴安全部队有义务与以色列军方合作、共同维护西岸地区的安全秩序。在这种以色列利益所主导的制度内涵中,巴勒斯坦非暴力抵抗运动是一种非法行为。是故,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经常以维护秩序、避免冲突激化为由限制甚或压制西岸地区的非暴力抗议行动。许多巴勒斯坦活动人士因此抱怨其在被占领土上面临着两个政权的“双重压制”。②Andy Clarno,“Securing Oslo:The Dynamics of Security Coordination in the West Bank,”Middles East Report,No.269,2013,http://www.merip.org/mer/mer269/securing-oslo,上网时间:2020年7月26日。但对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而言,如果公开全力支持非暴力抵抗运动,则势必与已有的制度框架发生冲突,进而受到以色列的报复性制裁。例如,根据1994年巴以双方签订的《巴黎经济议定书》(ParisEconomic Protocol)规定,以色列可凭借关税代收权暂停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转交代收税款,而这项税款是后者年度财政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持其正常运转的关键所在。这种制度的结构性约束决定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中的矛盾性角色,因此也就无法使其在目前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中承担起实质性的领导角色。
概言之,在以色列社会缺乏建设性的回应下,巴勒斯坦非暴力抵抗运动面临的首要问题仍存在于其自身内部。自巴以和平进程以来,巴勒斯坦社会日渐加深的内在破碎状态,即地理空间、政党组织、民间社会的分裂与竞争以及强有力的领导角色的缺失等,最终导致了整个非暴力抵抗运动在社会动员及凝聚力上的不足,使其产生的实质性影响有限。这种内在分裂如果无法得到弥合,特别是法塔赫与哈马斯之间各自为政的政治分裂局面,会极大地限制巴勒斯坦非暴力抵抗运动在未来的发展壮大。
四、结语
巴勒斯坦非暴力抵抗运动是基于巴以权力不对称基础之上的现实主义考量,是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失败后针对巴以冲突不对称态势的务实调整。从反隔离墙运动到至今的反占领运动,巴勒斯坦人以战略实用型的非暴力学说为指导,不断在具体的非暴力实践中进行创新,使抵抗以色列的行为从基于基层社区的民间的自发斗争上升至官方对以斗争政策的一部分,进而转变为官民共同参与的以“反占领”为主题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代表了巴勒斯坦对以斗争在政策上的一种进步。从一种积极的角度来看,巴勒斯坦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意义在于:首先,它展示的是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失败之后,巴勒斯坦人不屈服于以色列军事占领及压制的抗争姿态与斗争精神。在不断的实践当中,这种抗争姿态与斗争精神逐渐强化了以非暴力为特征的大众抵抗文化,为将来更大规模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奠定了基础。其次,它有利于破除巴勒斯坦人在西方话语中“极端暴力”的刻板形象,凭借国际法及道德方面的优势,增强其在国际舆论中斗争的合法性。最后,它有利于提振武装暴力手段“退场”后消沉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士气,为其未来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战略方向。
但截至目前,西岸地区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整体上仍呈现地方化、分散性及草根主导的特征,对现阶段整个巴以局势并未产生实质性影响。尽管如此,作为一种对以斗争的新的战略趋势,巴勒斯坦非暴力抵抗运动是一种长期策略,对未来巴以局势存在以下两方面的潜在影响。
第一,赢得国际舆论中的“合法性”之战。由于在巴以冲突中的硬实力及话语权优势,以色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其在国际舆论中关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强权扩张政策及对巴勒斯坦人权侵犯的问题。而对于巴勒斯坦的强硬派、特别是哈马斯等派别的抵抗行动,以色列在话语宣传中则常以安全威胁的名义重点突出对方的极端暴力性,并将其行为不加区分地直接定性为恐怖主义行径。以色列在西方话语霸权的维护下,凭借这种话语优势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避重就轻的舆论输出,致使巴勒斯坦对以斗争的合法性并未在国际舆论中得到普遍而充分的认可。然而,作为一种新的抵抗策略,巴勒斯坦非暴力抵抗行动的优势恰恰在于其能够弱化以色列以安全为由的话语宣传效果。并且,通过网络媒体、国际活动人士及其国际动员网络等将巴勒斯坦人的真实处境及其遭遇向外传播,加深国际社会对巴以局势的认识,进而有利于巴勒斯坦赢得对以斗争在国际公众舆论中的“合法性”之战,最终为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创造有利条件。
第二,巴勒斯坦非暴力抵抗运动在未来的发展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得不到建设性的回应时,这种不确定性就有可能再次转化为巴以之间新的极端对抗。如今,巴勒斯坦问题在国际事务中日益边缘化。与此同时,以色列社会却不断趋于右倾,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日益强硬,对西岸领土吞并的可能性不断增大。这些因素都有可能使巴勒斯坦非暴力抵抗运动走向反面,进而为下一轮由极端情绪所主导的暴力对抗打开大门。这不仅对巴以双方而言是一场灾难,更有可能引发地区新的动荡。
不论如何,就目前巴勒斯斯坦非暴力抵抗运动的现状而言,首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仍然是结束法塔赫与哈马斯之间的对立局面;同时,发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民族主义运动中的领导角色,团结巴勒斯坦各党派、社会各阶层,真正形成一种可持续的大众非暴力抵抗运动,以此引发国际社会的巨大关注与支持。如此,或许能纠正巴以之间权力不对称的态势,最终推动巴以政治谈判出现实质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