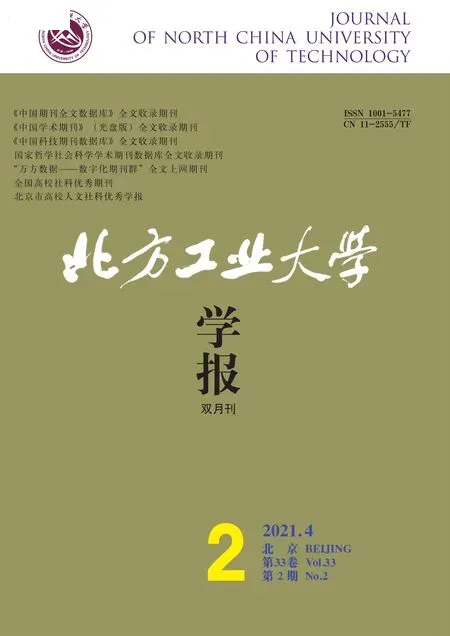早期电视研究中的受众“主动性”辨析*
王 怡
(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100144,北京)
传播学领域对电视观众的研究热潮,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发端的电视产业第一个黄金时代。在持续的二十年间,大量经验研究都在试图为电视观众画像,这些对电视观众收视动机、行为和满足感的研究,既离不开使用与满足理论的支持,同时也为该理论提供源源不断的生命力资源。而研究者们之所以对它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一个重要原因是,受众的“主动性”从来都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既不能概括电视观众收视时的所有状态,也不能指代电视和观众之间的全部关系。要梳理清楚这个命题,有必要回到1960—1980年代,审视这段早期电视研究历史中“主动的受众”和“被动的受众”之间的角力。
1 “顽固的受众”
人们对大众媒介即寄予期望又忧心忡忡的矛盾心理,是引发受众研究最初的原因。普通公众、父母、媒介文化批评者们担心,“被动的受众”会被人利用、受到伤害。人们对儿童的担心更深,害怕他们被动地沉溺在一个接一个的媒介中——从连环画、电影、到广播和电视——这也正是传播学早期媒介效果研究的主要战场,担心儿童的辨别力被腐蚀、创造力被扼制、阻碍他们健康人格的成长和良性社会化过程。
这种担心随着1960年代美国第一个电视黄金年代的到来而越来越强烈。以当时利润最高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首的电视网的管理者甚至提出“最不讨厌的节目理论”[1],理论假设观众通常会选择最不讨厌的节目观看,即使可供选择的节目非常有限——这也导致当时美国商业电视网普遍对提高节目质量不那么感兴趣,电视观众在他们心目中只是“市场份额”,是被动地被低质量节目吸引、满足广告商收视率需求的数字符号罢了。
从佩恩基金研究到施拉姆的电视与儿童研究,无一不是出于对大众媒介的设防和对“被动的受众”的保护心理所进行的。鲍尔(Raymond Bauer)在《顽固的受众》中描述了当时人们对受众的这种刻板印象:
当普通公众和社会科学家谈及广告或者某些人的宣传时,……往往被认为是一种人对人的剥削。这种模型的影响是单向的:仅仅是传者对受众做了什么,而传者通常被赋予相当大的权力去对受众为所欲为。这个模式最糟糕的结果就是人们常挂在嘴边的“洗脑”、“隐性劝服”和“阈下广告”。[2]
紧接着,鲍尔又引用戴维森(W.Philips Davison)的一段论述进行反证,认为受众并不被动,大众传播实际上是个“交易过程”,参与交易的双方,即传播者和受众都想从中获利。
有时候,操纵者确实能够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来强调某种需要,或者通过展现一种远比现实夸张得多的变化,从而使他的受众陷入一场糟糕的交易中。但是,受众也可以讨价还价,恰如许多被忽视或误解的传播者所付出的惨痛代价。[3]
戴维认为一方面媒介难以在受众那些“有所需求”的选择下真正牟利,另一方面,受众也常常会被媒介欺骗。这是一种看上去没有立场的结论,毕竟,戴维森不是一个社会哲学家,也没有为文化工业辩护,只是作为一个具有丰富的经验研究阅历的学者,去描述当时确实存在的一种现状。
传播学早期研究往往缺乏对受众接受信息时的复杂性的重视,在效果研究中,对受众的关注严重不足。鲍尔作为一位心理学家,从专业角度发现大众传播的信息接收方的心理过程远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或者那样悲惨——默默承受着大众媒介对注意力的压榨以及对意志的控制。所谓“顽固的受众”,就是指那些“并不总是有选择性地注意,但是常常有选择性地去认知,并且对不需要的信息加以抵制的人”。[4]尽管关于看电视这个行为到底是被多大的能动性所驱使,依然存在很大的争论,但是至少,受众在传播理论中不再被描述为一个被动的牺牲品。
2 仪式化观看与工具化观看
2.1 为“破”而“立”的“主动性”
对于一个学科领域出现的新理论,如果不能清楚了解它的学术背景,以及它究竟要“破”什么,就不能真正懂得它要“立”的新内容,哪怕这些内容不完美。
卡茨(Elihu Katz)在1970年代提出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假设,就是为了反驳当时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对传播学效果研究狭隘视野的批评。卡茨提出传统的效果研究可以有新的发展空间,也就是从对媒介的测量转而进行受众的测量。如果受众是被动的、无能的、仅仅受到媒介强大力量影响的,那么对受众的研究便毫无意义;相反,如果如卡茨所言,这种新的理论空间存在的前提,必须是受众具有“主动性”,唯有如此,他对贝雷尔森的反驳才能立住脚。
拜欧卡(Frank Abiocca)在《受众的对立概念:大众传播理论中的主动与被动》中曾这样认为学术界关于“主动性”和“被动性”之间的胶着状态:
在过去四十年的研究中,理论界出现了一场拔河比赛。在绳子的一端,我们能发现主动的受众:充满个人主义、不受“影响”侵袭、充满理性和选择性。在另一端,我们却看到被动的受众:他们是循规蹈矩、轻信他人、道德沦丧、脆弱的受害者。绳子的每一边都有很多重要的媒介理论家,凭着他们对世界现实的感知而用力拉拽。[5]
对比卡茨在《个人对大众传播的使用》[6]和鲁宾(Alan M. Rubin)在《媒介效果的使用与满足视角》[7]中分别提出的五个“使用与满足”理论基本假设。可以发现,鲁宾所提出的理论假设在三个方面和卡茨的相同:肯定受众主动性确实存在;对媒介的使用与满足贯穿在传播过程中;不同媒介之间存在竞争。同时,鲁宾删去了卡茨关于研究方法和价值判断的假设:不再认为受众个人提供的资料是唯一研究素材,因为他们的表述会受到各种内因与外因的影响,在研究中有越来越多的方法被补充进来;不再强调价值中立,这有可能引来不必要的学术道德谴责,而文化的问题其实是可以在更深入的动机和满足中去挖掘;同时承认媒介确实会对个人产生影响,甚至由于某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原因,人们还会对媒介产生依赖。显然,鲁宾的调整对受众在传播活动中的“主动性”做了调和,这种调和正是长时间以来对传统的使用与满足研究的众多质疑的一种回应。
正如温德尔(Sven Windahl)所言,“主动性”这个概念的含义,很容易将受众形象导向超理性和极具选择性,正因如此,引发了很多质疑。基帕克斯(Susan Kippax)和默里(John P. Murray)的研究表明,虽然电视观众都同意自己看电视存在“逃避”的目的,但是很多人却无法说出具体哪些节目帮助他们达成了这些需求。[8]之后,基帕克斯又在对电视、电影、报纸和书籍综合研究后发现,受众使用媒介和自己的需求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相关性。[9]这不仅是因为大众媒介的扩散特性使得特定媒介的用途很难识别,还因为受众在选择媒介时根本不主动。这种现象似乎在“媒介濡化”(media enculturation)视角中找到支持:商业电视的内容提供了关于社会价值统一的象征性信息,而电视观众主要采取非选择性的习惯性模式。这些对受众媒介选择和习惯的研究结果,明显站在了“主动”的受众观的对立面。
2.2 仪式和工具的分化
顺着这个脉络,“主动性”不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观众在某些场合或与媒体使用的某种动机相关联时会更活跃,而其他情况下却可能相反。
鲁宾在对1980年代广受欢迎的电视节目《60分钟》进行了大规模量化研究时,确定了两种类型的观众:第一种观众对《60分钟》很忠诚,定期观看并从中获取信息和娱乐,但他们不会过度收视,也不把看电视当做消磨时间的事情,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依恋”“目标导向”“选择性”[10]等既感性又理性的矛盾动机;第二种观众则是用电视来打发时间,他们对信息的搜索和获取往往来自各种各种的节目,而非专注于该节目。
在之后的研究中,鲁宾通过对626个原始样本数据分析,再次测量动机与这两类电视观众的相关性:习惯性收视者出于打发时间的目的,更多收看娱乐节目,电视节目观看量大,并与电视表现出一种亲和力,即“认为电视内容是对生活的一种相当真实的描绘”[11];选择性收视者则不会逃避和忘却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喜欢看新闻、谈话和竞赛等高质量节目。
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之后,鲁宾总结道,每个电视观众每一次对电视的使用都有可能是“工具化或仪式化观看”[12],或二者兼具。仪式化观看出于习惯,频繁观看,满足转移注意力的需求,并且对电视作为提供满足的媒介相当重视;而工具化观看是目标导向的媒介内容使用方法,满足信息的需求,具有选择性,观看不频繁且不太在乎电视的重要性。这种概念的界定说明“主动性”会有不同的类型和程度。
随着仪式化观看与工具化观看浮出水面,使用与满足理论中所强调的“主动的受众”在鲁宾的研究中分化。尽管仪式和工具依然是一种含混的二分法,但它们的界定表明,看电视绝对不是单一的行为;“主动”的判断也绝不是“是否看电视”以及“看什么内容”可以明确的。
3 寻找“被动的受众”
尽管鲁宾的仪式化观看和工具化观看为使用与满足理论关于“主动性”界定的问题缓解了一些尴尬,但如何界定“主动的受众”这一概念,始终像在“混乱的理论和信仰的棋盘中最关键的一颗棋子”。拜欧卡在对前人研究进行总结分析后,归纳出“受众主动性”的五种表述方法,即“选择性(selectivity)、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意向性(intentionality)、卷入(involvement)和抵制影响(imperviousness to influence)”。[13]显然,对“主动的受众”的各种界定其实都没有在同一个层面正面交锋,甚至很多有重叠,但有一点是很多研究者都同意的,即“主动性”不是一个固定的临界点,而更像是处于黑与白之间拥有无限可能的灰色,即便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和语境中,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都会显示出不同的灰度。
既然“主动性”从来就不是一个明确的概念,为什么它始终作为使用与满足理论的核心存在?而在“主动性”光谱另一端的“被动性”却被忽视和冷落?
3.1 大众社会理论中的“被动的受众”
“顽固的受众”和“抵制影响”这两个词来自于鲍尔,也成为“主动的受众”时代到来的宣言和研究范式转变的里程碑。
鲍尔在《顽固的受众:从社会传播视角看影响过程》中借伊西多·尚(Isidor Chein)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后者从人文主义角度反驳当时心理学界普遍将人类视为“无能的反应体”和“机器人”的观点,提出“心理学家对一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始终保持坚定的信仰……但是我们能给机器人什么样的尊严?”[14]
鲍尔借伊西多·尚之笔发出的质问,正是针对当时整个社会科学界对大众媒介的批评浪潮——由大众媒介带来的糟糕的东西正在被电视带入每个家庭,而他们有责任去拯救每一个抽象的个体。在鲍尔看来,受众正在用他们“顽固”的心理与所有的广告和宣传做抵抗,并提出了主动与被动的二分法,以及一个“单向影响”的模型——“交易模式”。
鲍尔试图找回的这个人的形象,正是经典自由民主的核心——理想的独立公民,他们是理性和自决的,自由地追求生命、解放和个人财产。这种个人形象受到批判派理论家的不满,他们指出,当一个社会充斥着大规模生产以及大规模生产出来的共识,并以此为主导时,这个社会中是没有民主可言的。鲍尔进而提出质疑“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中人的模式——我们运行社会的模式——和我们的科学模型——我们用来运行科学的模式——是否应该相同”[15],在他看来,人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是两回事,人是可以自由甚至顽固的,哪怕他所处的社会完全不给他机会甚至会泯灭他的任性。
从这个辩论中可以看出,大众社会理论家对受众的印象是整齐划一的、混乱的、轻信的、对宣传毫无抵抗的乌合之众。直到现在,关于这种“被动的受众”的描述依然存在,无论在地铁还是在家中,大众媒介里到处是完全相同的内容和形式,人们看到的都是一模一样的物理图像;他们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无选择地接受消费主义带来的“美好”事物,坐在电影院里被好莱坞洗脑,轻易地被互联网上的言辞刺激……
所以“被动的受众”不仅仅是大众社会理论的一个阶段,更是存在于很多人对大众传播效果的恐惧感中。某种程度上,涵化理论也传承了这种“被动”传统,曾经对大众社会的恐惧,变成了格伯纳(George Gerbner)笔下灰色而缓慢的“主流化”:
人们出生在以电视为主导的符号环境中——看电视是一种塑形器和某种生活方式与观点最稳定的部分。它将个体与一个更大的由电视搭建起来的人造世界联系起来,……支配他们的信息来源,继续暴露在电视信息中很有可能重申、确认、滋养他们的价值观和观点。[16]
3.2 被消费主义掩盖的“被动的受众”
在大众传播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对“被动的受众”的拒绝,而最有效的方法便是质疑“大众社会”某些概念的有效性以及大众媒介的传播优势。作为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先锋倡导者,布鲁默(Jay G.Blumler)就曾强调“要用一种全新的个体形象——为满足自己的目的而积极选择节目、文章、电影和歌曲的人——取代效果研究中所隐含的作为被动牺牲品的受众”。[17]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提出对布鲁默美好愿景的批评,包括认为他的理论是粗糙的假设、折中主义、陷入功利主义逻辑陷阱等等。
然而,谁又是“主动”的受众?“主动”的证据又是什么呢?在鲍尔的表述中强调“交易”里有一个“选择”,它是锚定在确保有一个独立的、甚至顽固的公民存在。自由选择,便是受众“主动性”的标志——而在另一个领域,它意味着一个“健康的”政治环境。
在美国的灵魂深处,自由和消费主义被紧紧捆绑,“主动的受众”不是卢梭笔下的公民,而是一个现代公民消费者(modem citizen-consumer)。“自由选择”是在市场聚宝盆里的选择,没有什么比将选择——选择大众媒介产品的行为——美化为个人主义和行动主义的标志,更适合这个以大众消费为典型特征的社会。“自由”通过否定大众传播的效力实现,并通过“选择”的次数成倍增加。由此,“被动的受众”理论家如此害怕的“消费”被改头换面,本应支持“被动性”的证据被置换成了“主动性”的注脚。
在随后众多的研究中,宣告“被动的受众”的死亡似乎成为一种学术仪式,同时,追求“主动的受众”成为当务之急。进而,在研究中,把这种假定用大量的数据变成“经验的现实”——这也导致了许多“主动性”概念的漏洞和理论的困境。
3.3 探问“主动”的合理性
可以发现,“主动的受众”是通过对“被动的受众”的否定和死亡宣言来定义的,那么,在“主动”的美丽新世界里,真的不存在惰性和消极吗?
前文曾经提及,在“主动性”原理中,包含实用性、意向性、选择性和卷入等概念。但是当深入探究这些概念时,就会出现令人不安的困惑:那个被称之为“主动的受众”是否只是一个影子?
首先来看“实用性”的基本概念。布鲁默对它的定义是“大众传播为人们所使用”[18],进而将“使用(use)”作为主动性的一个指标。但使用与满足研究者是否真的曾经得到过与“‘使用’大众媒介”相反的回答?显然没有!因为目前能看到的研究都是针对媒介使用者进行的;那些从不接受大众媒介内容的人,几乎无处可寻,即使有,也不会被请到研究者面前,因为他们对研究者来说没有价值。如果以这种方式定义“主动”,它怎么可能不打败它的对手——那些被动的“不使用”者?
再来看“意向性”,类似的问题浮现出来。意向性被布鲁默定义为“媒体消费由事前动机引导”。[19]然而,在研究中,几乎看不到类似于被访者回答他们看电视源于“绝对没有理由”的数据。这是因为使用与满足研究所广泛采取的“自我报告”方法,本质上是对一个人行为合理化的邀请。按照这个方法论逻辑,“被动性”的存在需要由“对无动机行为的自我报告”来定义的话,它的缺席就不足为怪了。
“选择性”概念遇到的问题更大。事实上,受众几乎不可能在使用媒介时完全不做选择,至少他要选择是打开电视还是拿起手机,浏览报纸的时候必须选择先看头版还是副刊。所以“不选择”的受众根本不存在。另一方面,研究往往将偶尔有针对性地调换电视频道视为“主动”,但这里存在一个矛盾的现实,即具有高度选择性、喜欢看特定节目的观众,往往懒于探索新的节目,对其他节目存有偏见——这些人反而比选择性低的“频道跳虫”显得更加不主动。
此外,“选择性”的概念通常被认为是个人属性,但是利维和温德尔(Levy & Windahl)却认为,“选择性”的主要成分来自于大众媒介的属性:
作为受众“主动性”的一个表现形式,对媒介资源的选择受制于受众成员可能获得的选择数量……传播技术的发展大大拓展了受众的选择技能,这也导致他们选择性水平的提高。[20]
利维和温德尔的潜台词是,只要给予“主动的受众”更多选择,就可以让他们变得更加活跃——这与他们自身无关。这是否意味着,仅仅靠更多可供选择的媒介产品,就可以驱散大众社会中的“乌合之众”?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卷入”,它被利维和温德尔定义为某种程度的认知和情感唤醒,或者是处理媒介信息时对图式的使用——而这在认知心理学中被视为是所有正常人都会拥有的信息处理模式。如果一个电视观众在看电视的时候处理信息、使用图式,实际上就是在看的时候去想了一下,仅仅凭借着“想(think)”就去简单定义“主动性”,显然,“主动性”是无法不合理的。除了脑死亡,还有什么可以让一个人变成“被动的受众”?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我思,故我主动”。
从以上“主动性”概念基本组成部分所存在的问题中,可以看到这个术语之圆滑,令其几乎无法被证伪。通过定义,受众几乎不可能不主动。
4 “主动性”背后的意识形态承诺
虽然“主动的受众”最初的目的是展示个人如何不受媒介的操纵,但是,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表明,“主动性”必须只能被视为是传播活动中的一个变量,否则就会使其变成一个不可证伪的概念,失去了科学价值。恰如利维和温德尔在1984年的研究中,便将“主动性”辩证地转化成了它的对立面,来自鲍尔的“抗渗性”被消解了:
受众的主动性与满足感在传播过程中是重要的变量。……更主动的人不仅能从媒介使用中获得更多的满足,与此同时,这种在媒介前的积极表现以及令人满意的曝光度将会使他们受到更多影响。相反,不那么主动、满足感低的人,也许才是最“顽固”的受众。[21]
既然“主动性”已经成为了一个伪命题,传播学者们依然继续围绕这个理论困境提出了未来研究发展的措施,不愿将使用与满足理论放弃。为什么尽管不断有“被动的受众”形象浮现,但“主动性”仍然让研究者着迷?拜欧卡的回答很有启示性——因为美国传播学经验研究者已经将“主动的受众”视为信条,一个包含着个人理性、独立、泰然自若的自由民主理想的意识形态承诺。所以,坚持受众的“主动性”探索以及对“被动性”的鄙视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这也间接阻碍了对“主动的受众”更加全面客观的解析。
如果真如拜欧卡所说,所有的科学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那不难想象,改变一个人的科学模式去适应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模式,要远远比要求真实的社会变成那个理想社会更容易。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主动的受众”的概念缘起就是一种由幻灭感孕育出来的过度反应。
我们可以看到,用认知独立、个体自由、抵抗影响去定义“主动的受众”显得多么繁冗而又单薄。它试图掩盖受众所做的一切……每一个悸动、每一点想法、每一次选择——有心或无意的——都被当做“主动”的证据记录在案。在极端的“主动—被动”二分法公式中,只有撑在电视机前的僵尸才能被视为最受鄙视的“被动的受众”。……我们作为社会科学家,当看到感知、反射甚至选择时,有必要感到惊讶吗?当我们“主动的公民”在大众媒介这个“购物中心”里无比庸俗地拎着各种粉色、蓝色或红色的购物袋时,我们应该宣布他们是自由的、主动的、抵制影响的吗?[22]
大众传播者要求对缺乏清晰度的媒介效果(甚至常常是失败的媒介效果)作出解释,而这似乎干扰了社会科学领域对社会系统的设想。在拜欧卡眼中,那些一直坚定地抱着“主动的受众”信念的理论家,真正的目的只是通过宣称人们已经是自由的,而让他们以为可以摆脱媒介的影响。但这样做的副作用却是社会科学自己放弃了职责,以达到自我保护。
5 小结
从1960到1980年代的二十年间,众多关于电视观看行为的研究对“主动性”的表述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受众的“主动性”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点,这不仅仅体现在从“主动”到“被动”之间有着复杂的个体差异缓冲带,还体现在不同的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以及他们不能摆脱的科学研究内部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博弈与调和。也正因如此,“使用与满足”通常都是人们进行新媒体研究(无论是彼时的电视研究还是当下的互联网研究)的首选理论框架,因为每当人们面对新的媒介技术和内容时,往往最急于探求为什么和如何去使用它,这也使得“受众的主动性”成为传播学领域最具生命力的理论命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