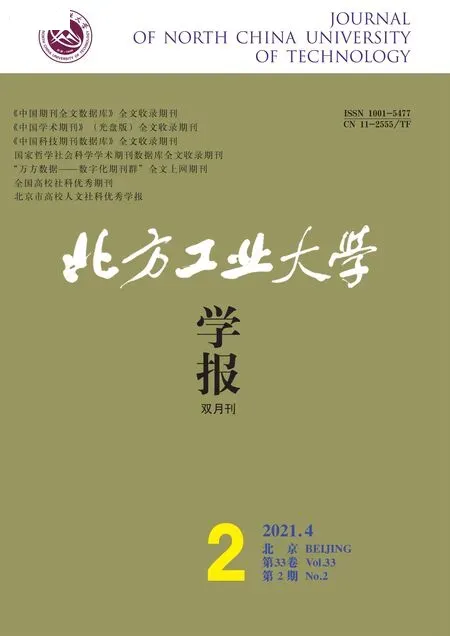论《金瓶梅》中的命相叙事*
万晴川
(扬州大学文学院,225002,扬州)
《金瓶梅》为读者展示了一幅色彩斑斓的明代风俗画卷,举凡命相、占卜、下棋、双陆、投壶、抹牌、蹴鞠、斗百草、跳百索等民俗和娱乐活动,应有尽有,五彩缤纷,既是明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成为作者塑造人物形象、构建故事情节的一种艺术手段。对于《金瓶梅》中的相术活动描写,陈东有教授最早做过考察[1],但他主要是考证第二十九回吴神仙相面断语的出处并对其进行文化阐释,其实,小说中多处出现看相占卜的描写,值得拈出专门探讨,本文就对其在小说中的思想和艺术功能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1 明代社会生活的反映
《金瓶梅》中大量出现看相占卜的描写,与明代的政治环境和社会风俗密切相关。永乐年间解缙等编辑《永乐大典》,辑录明代之前的各类术数著作,朝廷对这类典籍也很重视,颁发给各地学校,以供诸生学习。明廷将术士视为一种特殊的人才,非常重视,据《明实录》第128卷载,朱元璋认为龟卜可用以“断国家之事”,因而专设卜筮之官。陆容说:“洪武中,朝廷访求通晓历数,数往知来,试无不验者,必封侯,食禄千五百石。”[2]俞汝楫《礼部志稿》记弘治十一年十二月,钦天监掌监事太常寺少卿吴昊上书,建议在全国访取精通天文、历算、相面、演禽、观梅、拆字等术士。[3]朝廷给予这些术士很高的待遇,金忠,袁珙父子、汤序、邵元节、万祺、顾翊等,皆以占卜看相之术跻身高位,以致文人士大夫欣羡不已,大家聚在一起,“大都讲些堪舆话,又说些星命学”[4],甚至“人人能讲,日日去讲”。[5]宋濂在《禄命辨》一文中说:一些大儒“也于禄命家无不嗜谈而乐道之。”[6]明代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如靖难之役、英宗复辟、宁王之乱等,无不与术士的推动有关,朝廷选拔储君,也很重视术士的意见,据《明史·袁珙传》载:“帝将建东宫,而意有所属,故久不决,珙相仁宗曰:‘天子也。’相宣宗曰:‘万岁天子。’储位乃定。”[7]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民间就更为盛行,以术谋食者多如过江之鲫,黄省曾在《难八字射决论》中云:“治其术者,上自京师大藩,每方不啻千万,虽乡邑之小亦有百辈盘集,以蚕食于其间。”[8]《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描写道:“街上、客店里以及所有其他的公共场所都充斥着这类占星家、地师、算命算卦的……人不分高低,平民与贵族,或读过书的和文盲,都在受害者之列,甚至城内的高官显宦及皇上本人都不能例外。”[9]一些名相士收入颇丰,如兰溪杨子高挟相术走天下,“家致万金”。[10]以前被术士视为秘籍的数术著作得到系统整理和出版,传播广远,使相术观念深入人心,所谓“福星高照”、“难星临头”、“吉人自有天相”、“红鸾照命”、“白虎临宫”等大量与相术有关的词汇演为口头谚语,对民俗民风产生了巨大影响,人们往往把自己的婚姻、科考等重要的选择权交与术士,黄省曾在《难八字射决论》谈到明人迷信命相术的情况时感叹道:“一世之人承迷袭暗,举皆崇信而乐尚之,自公卿至于庶民,一切没溺,其必验引荐者为之先容,延款者为之倒屣,凡诞举一子,经营片事,罹构末疾,斛天水之官服,贾干利求名,莫不取决于斯流,是以工学而糊食者,纷纷也。”[11]冯汝弼《祐山杂记》中《文章卜命》篇说:“士之急功名者往往惑于命星之说,视其予夺为欣戚。”[12]有的父母为让子女在一个好时辰出生,甚至做出了极端愚蠢的事,如冯梦龙《古今谭概》中《专愚部第四》记载:“苏州徐检菴老而无子,晚年一妾怀孕,徐预使日者推一吉时,以其尚早,劝令忍勿生,逾时,子母俱毙。”[13]以前由于行业竞争激烈,术士往往把自己的技术神化为“天机”、“秘藏”,所谓“非亲不传,非故不授”,但随着各种术数著作的刊行和流播,所谓“秘藏”不再是秘密,相士通过学习,可以兼擅数种术技,而由于这类知识得到普及,一些闺阁少妇、农夫村妪、渔夫樵子都略知一二,甚或精通此道。
大约产生于万历年间的《金瓶梅》就是这种社会背景下的产物,小说中写到了形形色色的命相之士,表现了他们的生存状态。最著名的就是第二十九回出现的吴神仙,他称“自幼从师天台山紫虚观出家”,云游各地,因往岱宗访道,道经清河县,周总兵邀请至家,为其母治疗目疾,周守备又推荐给西门庆看相。西门庆见吴神仙“头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履,腰系黄丝双穗绦,手执龟壳扇子,自外飘然进来。年约四十之上,生得神清如长江皓月,貌古似太华乔松”。“忙降阶迎接,接至厅上”,西门庆问道:“老仙长会那几家阴阳?道那几家相法?”神仙道:“贫道粗知十三家子平,善晓麻衣相法,又晓六壬神课。常施药救人,不爱世财,随时住世。”西门庆听言,益加敬重,夸道:“真乃谓之神仙也。”相毕,西门庆封白银五两以谢,吴神仙再三辞却,说道:“贫道云游四方,风餐露宿,要这财何用?决不敢受。”(本文引文皆从崇祯本)西门庆不得已,拿出一匹大布,神仙方才受之,稽首拜谢。可见,这类相士知识结构庞杂,精通算命、看相、占课和治病等,以术干谒,周旋于朝廷官员之间,类似于明代的山人,受到雇家礼待。第七十九回,西门庆病危,吴月娘使小厮往周守备家请吴神仙,贲四说:“也不消问周老爹宅内去,如今吴神仙见在门外土地庙前,出着个卦肆儿,又行医,又卖卦。人请他,不争利物,就去看治。”月娘连忙就使琴童把这吴神仙请将来,酬礼也是一匹布。吴神仙真名“奭”,“神仙”是他的绰号,就像《魏忠贤斥奸书》中的“李瘤仙”,《梼杌闲评》中的“赛神仙”等,绰号表示他的术技之高,声誉之隆,而道士的身份和仙风道骨的姿态又无疑能为他加分。作者以春秋笔法,讥刺吴神仙自命清高,虚饰矫伪,他既行医治病又卖卦看相,示人以“不争利物”的印象,虽不收银钱,但却不拒布匹。这类术士地位较高,在官员士大夫的交际网络中起着纽带作用,在小说中是周守备与西门庆联络感情的中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西门庆死后,他的侍姬庞春梅不久就琵琶别抱,成了周守备的如夫人。吴神仙在小说中出现三次,分别是第二十九回看相、第六十一回李瓶儿病重(拟请他来,但因外出未到场)和第九十一回来看治病危的西门庆,李瓶儿病死是西门家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吴神仙可谓是西门家盛衰的见证人。比吴神仙低一层级的另一个术士是真武庙的黄先生,第六十一回李瓶儿病重,服药无效,西门庆旋即差人拿帖儿往周守备府去请吴神仙,周府回说吴神仙云游武当去了,然后又推荐了真武庙外“打的好数,一数只要三钱银子,不上人家门”的黄先生,西门庆随即使陈敬济拿三钱银子,迳到真武庙门首黄先生家,见门上贴着:“抄算先天易数,每命卦金三钱。”黄先生可能是真武庙道士,有自己的摊位,明码标价,拒绝上门服务。
更次一等的就是在街上设摊摆点,如第九十一回写西门庆死后,李衙内看上了孟玉楼,但孟玉楼年龄大于李衙内,媒婆陶妈妈担心李衙内不要,于是想给她算个命。“二人走来,再不见路过响板的先生,只见路南远远的一个卦肆,青布帐幔,挂着两行大字:‘子平推贵贱,铁笔判荣枯;有人来算命,直言不容情。’帐子底下安放一张桌子,里面坐着个能写快算灵先生。这两个媒人向前道了万福,先生便让坐下。薛嫂道:‘有个女命累先生算一算。’向袖中拿出三分命金来,说:‘不当轻视,先生权且收了,路过不曾多带钱来。’”他的收费又低于黄先生,但与黄先生一样,都张贴广告,标明服务价格或原则,就像《西游记》中写到的袁守诚卦摊,“招牌有字书名姓,神算先生袁守诚”。
地位最低的是“流动商贩”,如第四十六回写吴月娘因在大门里首站立,见一个乡里卜龟儿卦儿的老婆子,穿着水合袄、蓝布裙子,勒黑包头,背着褡裢,正从街上走来。月娘使小厮叫进来,在二门里铺下卦帖,安下灵龟,说道:“你卜卜俺们。”那老婆扒在地下磕了四个头:“请问奶奶多大年纪?”卜毕,李瓶儿袖中掏出五分一块银子,月娘和玉楼每人与钱五十文。这类术士与第九十一回薛嫂提到的“过路的先生”一样,穿街串巷,摇铃鼓锣,游食四方,地位低下,询问吴月娘的年龄时,还要扒在地上磕头。还有一类术士为人看相算命纯粹出于个人爱好,如第九十六回水月寺火头叶头陀,不会看经,只会念佛,善会麻衣神相。他为陈敬济看相,没有索取任何报酬。
将上述术士服务报酬按照明代官方定价折算成“文”单位,吴神仙是500万文,黄先生30万文,摆地摊的术士是3 000文,“流动商贩”老婆子是5 100文,可见差距巨大,考虑到摆地摊的术士没有标价,且媒婆声称路过身上没带钱,而卜龟儿的老婆子所得带有赏赐的意味,以此推知,以宗教身份的术士地位最高,“流动商贩”的报酬最为微薄,地位最低。其次,服务于西门庆家的命相术士各个层次的都有,既表现了当时人们迷信命相的社会风气,也塑造了当时的术士群像。
2 相术的写人功能
命相观念对当时的文学、书画创作甚至文艺批评都产生过深刻影响,就小说而言,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和唐宋传奇基本是叙述相术故事,但明代小说已不仅是传播命相故事的载体,而是将命相观念内化为一种艺术技巧和审美意趣。命相术对《金瓶梅》中人物形象塑造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隐”和“显”两种形式,“隐”体现在人物外貌的静态描写,“显”则是小说中大量命相活动的描写。
第一种以武大郎外貌描写最为典型。《金瓶梅》第一回写武大郎:“人见他为人懦弱,模样猥蕤,起了他个浑名叫做三寸丁谷树皮,俗语言其身上粗糙,头脸窄狭故也。只因他这般软弱朴实,多欺侮也。”潘金莲见武松身材凛凛,相貌堂堂,身上恰似有千百斤气力,心里寻思道:“一母所生的兄弟,怎生我家那身不满尺的丁树,三分似人七分似鬼。奴那世里遭瘟撞着他来!”这里描绘了武大郎的身材、脸型、皮肤和性格等,他身材矮小,像长不大的丁树,“头脸窄狭”,体型呈倒丁字形,头尖下大,乃所谓“獐头”。按照相术观念,此乃恶相。《相术集成》中云:“上尖者不利,下尖狭者贱无下梢。”[14]《恶死歌》云:“额尖通口聚,虎口遇豺狼。”[15]金张行简《人伦大统赋》云:“欲察人伦,先从额上。偏兮贱夭,足恶。”元薛延年注曰:“额骨偏斜窄狭侵天部,当夭;贫贱亦为足恶之人。日月骨缺陷者,偏横狭者,命夭贱,薄促行,凶恶。”[16]显然,作者描写武大郎“头脸窄狭”,乃是暗示他命中低贱,并将遭遇“财狼”,不得善终。姚灵犀在《瓶外卮言》中指出,《金瓶梅》中“谷树皮”之“谷”字应是“穀”字,音构。“穀树皮可以为纸,又言皮有斑白之别,武大诨号之谷树皮可读为谷,又可读为构,当以读谷音为正。此树之皮,想不独粗糙,或正如人而之白廯,俗名白癜风者,故以形容武大之丑耳。”[17]可见“榖树皮”是形容武大郎皮肤粗糙并有白斑,旧题南唐宋齐邱《玉管照神局》中云:“智慧察其皮毛,苦乐视其手足”,注云:“皮肤细腻,毛发柔泽,主多智。”[18]就是说,从一个人的皮肤纹理和毛发色泽,可以判断他的智商。相术受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认为人的肌肤就像大地的纹理,以细腻、清晰为好,粗糙、凹凸为恶。王朴《太清神鉴》卷五“骨肉”云:“肉欲香而暖,色欲白而润,皮欲细而滑,皆美质也。肉重而粗,皮硬而堆块,色昏而枯,皮黑而臭,癃多者,非令相也。”[19]所以,武大郎皮肤粗糙似穀树皮,不但形容其丑,且表现其智商之低,对此小说也有描写。第三回写王婆安排西门庆和潘金莲私通,有诗曰:“阿母牢笼设计深,大郎愚卤不知音。”第四回郓哥称武大郎为“肥鸭”,坐视老婆偷情而不知。当他听说潘金莲有外遇时,就要去捉奸,郓哥道:“你老大一条汉,元来没些见识!那王婆老狗,什么利害怕人,你如何出得他手?他二人也有个暗号儿,见你入来拿他,把你老婆藏过了。那西门庆须了得,打你这般二十来个。若捉他不着,反吃他一顿好拳头。他又有钱有势,反告你一状子,你须吃他一场官司,又没人做主,干结果了你性命!”可见武大郎确实头脑简单,考虑不周,后来在捉奸时被西门庆踢中心口,卧床不起,又威胁潘金莲要将此事告知武松,终于促使潘金莲下了杀心。总之,武大郎的性格和命运,都隐藏在其外貌特征中,类似描写还有武松等。其次是“隐”和“显”的结合,如潘金莲,她作为张大户的婢女出场时,“出落得脸衬桃花,眉弯新月”,第二次则是透过西门庆的视角,对她的发、眉、口、鼻、腮、脸、身段、手、腰、肚、脚、胸、腿等肢体器官与姿态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描摹,按理说,潘金莲的肚、胸等隐秘部位,西门庆这时是不可能看到的,所以这些描写不尽合理,曾庆雨教授认为这是作者采用无实体叙述者视角造成的。[20]笔者则认为这可能是说书全知视角叙事留下的遗痕,在说书或受说书影响的小说中,人物一出场,一般都会对他进行全方位的描述。在潘金莲的外貌特征中暗含相学密码,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潘金莲的某些外貌和性格特点,第三次是吴神仙看相,她“只顾嘻笑,不肯过来”,吴神仙相道:“此位娘子,发浓鬓重,光斜视以多淫;脸媚眉弯,身不摇而自颤。面上黑痣,必主刑夫;唇中短促,终须寿夭。” “发浓鬓重”、“脸媚眉弯”照应前面西门庆看到的“黑鬒鬒赛鸦鸰的鬓儿,翠弯弯的新月的眉儿”,又增加了斜视、身摇、唇短等外貌和姿态特征,并预言她“终须寿夭”。《西岳先生相法》云“眉如新月曲,夜夜唤新郎”[21],《麻衣秋潭月论女人》:“眉浓发厚腰肢折,私地随人走外州……看人斜视并回顾,淫荡精神贱有余。项短发浓腰背露,未出闺门早克夫,膝摇背耸多淫荡。”《鬼谷相妇人歌》:“见人掩面嘻嘻笑,爱唤他人作丈夫。”[22]《人伦大统赋》卷上“斜盼者人遭其毒,凝视者自克其形”句,薛延年注云:“斜盼之人,谓眼神侧视,必遭毒而亡,或至兵死。”[23]由此可见,潘金莲弯眉、斜视、见外人嬉笑等外貌和动作特征,皆暗含她轻佻、淫荡的性格特点和惨死刀下的命运结局,她的外貌和性格特点愈来愈丰盈。又如孟玉楼的外貌,也是通过西门庆初见时的视角进行描写:“月画烟描,粉妆玉琢。俊庞儿不肥不瘦,俏身材难减难增。素额逗几点微麻,天然美丽;缃裙露一双小脚,周正堪怜”。孟玉楼身材匀称,后来吴神仙也基本围绕着这一特征下判语,只是多了“威媚兼全财命有,终主刑夫两有余”这一重要信息,但没有展开。至第四十六回刘婆子为玉楼卜龟,这一信息才基本清晰,刘婆子揭起第二张卦帖来,“上面画着一个女人,配着三个男人:头一个小帽商旅打扮;第二个穿红官人;第三个是个秀才。也守着一库金银,左右侍从伏侍”。这里暗示西门庆还不是她的最终归宿,前一任丈夫是商人,已死;第二任丈夫西门庆是商人兼官员;第三任丈夫是读书人,都是富贵人家。第九十一回写西门庆死后,陶妈妈和薛嫂儿为孟玉楼说媒,嫁与县太爷的李公子,但孟玉楼年纪比李公子大六岁,怕他不要,想改小几岁,于是找了个过路的算命先生算算。那先生捏指寻纹,把算子摇了一摇,开言说孟玉楼克过两夫后,“往后大有威权,执掌正堂夫人之命”,四十一岁时生一子,六十八岁寿终,富贵荣华,夫妻偕老。这样,刘婆子的卦象所暗示的信息至此彻底明朗,孟玉楼的故事也就完结,作者于是腾出笔墨来集中描写陈敬济和庞春梅两个重要人物。西门庆初会李瓶儿时,她的外貌描写只有简单几句:“生的甚是白净,五短身材,瓜子面儿,细湾湾两道眉儿。”至吴神仙看相,才加以细化,增加了“眼光如醉”、“眉眉靥生”、“卧蚕明润”、“体白肩圆”、“山根青黑”、“法令细缰”等特征,点出其偷情、克夫、死于鸡犬之年等行为及结果。第四十六回卜龟,与孟玉楼一样,说出她曾嫁过三个丈夫,并在她和孩子身边画着“青脸獠牙红发的鬼”,婆子解说时又说她“吃了比肩不和的亏,凡事恩将仇报。”“又一件,你老人家今年计都星照命,主有血光之灾,仔细七八月不见哭声才好。”这些都预示,李瓶儿死于遭潘金莲暗算和花子虚冤鬼报仇,时间在其子夭折之后。第六十一回李瓶儿病重,西门庆请真武庙外的黄先生为她算命,黄说李瓶儿今年计都星照命,又犯丧门五鬼,灾杀作炒,照应前面卜龟婆子的解说,判定李瓶儿噩运难逃。西门庆和吴月娘的写法也是一样,第一回写西门庆时,只简单说他“生得状貌魁梧,性情潇洒”,“秉性刚强,作事机深诡谲”。第二十九回吴神仙冰鉴,因为西门庆是家主,比其他人多了一道算命程序,判语对他的相貌和性格进行了更详细的补充,并警告他说:“八字中不宜阴水太多,后到甲子运中,将壬午冲破了,又有流星打搅,不出六六之年,主有呕血流浓之灾,骨瘦形衰之病。”第六十二回西门庆请五岳观潘道士为病危的李瓶儿驱邪,潘道士作法失败,说李瓶儿不可救,辞行时嘱咐西门庆今晚切忌不可往她房里去,恐祸及己身。但西门庆未听劝告。至第七十九回,西门庆命悬一线,吴月娘再请来吴神仙,吴神仙先诊了脉息,说“病在膏肓,难以治疗”。月娘问“先生还有解么?”吴神仙答道:“白虎当头,丧门坐命,神仙也无解,太岁也难推。造物已定,神鬼莫移。”彻底宣判了西门庆的死刑。第二十九回吴神仙给吴月娘看相,说她“泪堂黑痣,若无宿疾,必刑夫”。第四十六回吴月娘请刘婆子卜龟卦,通过卦象和刘婆子的解说,进一步归纳吴月娘的性格特点。
要之,《金瓶梅》中的人物塑造,除通过人物语言、行为体现外,命相描写是另一种重要的方式,其中又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描写是以作者为视角的静态描写,如武大郎等,其外貌特征中隐含着他的性格特征和命运结局;第二种是李娇儿、西门大姐等,在吴神仙看相之前,没有对她们的外貌进行过描写,读者对她们形貌和性格的了解,基本上是通过相士的判语;第三种是西门庆、潘金莲、孟玉楼等,既通过作者或西门庆的视角,对人物的形貌和个性进行描述,又通过相士的判语再进行丰富和补充,“隐”“显”互文,反复皲染,使人物形象愈加突出,又为后来的故事情节埋下了伏线。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相士的判语代表着作者的总结和评价,是一种特殊的批评方式,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既对人物的过去进行总结,又启示他(她)后来的结局。命相观念脱化为一种多维度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使得人物形貌描写具有了丰满的意涵。
3 命相判语的结构功能
很多学者都曾指出,《金瓶梅》因袭、改造、仿拟和镶嵌过其他许多文本,这是一种重要的互文现象。其实,小说中描写到的多次看相算命活动,判语之间遥相呼应,同样彼此形成互文,判语之间互为阐释、补充和深化,作者通过这种方式,再三皴染,使人物的外貌和性格特点愈加细腻和饱满,之前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习惯于一次性就把人物外貌写完,《金瓶梅》的笔法显得更摇曳多姿;而每一次的看相算命活动,都是一次预叙,并为读者制造了悬念。术士的判语,对塑造人物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总结之前有关此人的描写,以点睛之笔,揭出他的形象特征。这可说是相士的视角,也可说是为作者或读者代言,堪称一种特殊的批评方式。如第二十九回吴神仙相孟玉楼的判语:“口如四字神清澈,温厚堪同掌上珠。威命兼全财禄有,终主刑夫两有余。”张竹坡夹批道:“一句风采,二句性情,三句命运,四句作者患难,所以云作者遭史公之厄而著书也”。[24]即谓这四句判语,分别写出了孟玉楼的风貌、性情和命运,但张竹坡说第四句是“作者患难”,则未免牵强附会,其实是隐示孟玉楼会克死两个丈夫。又如绣像本李娇儿判语眉批云:“只十六字,形容李娇儿不堪晤对”,潘金莲判语眉批云:“嫣甚,媚甚”,李瓶儿判语眉批云:“可爱”,“画”,庞春梅判语眉批云:“四语是春梅一幅小像。”[25]由此可以看出,相术判语具有写人功能,西门庆头圆项短、体健筋强、天庭高耸、地阁方圆、皮肤细软丰润、两目雌雄、贪淫多诈、中岁耗散;吴月娘面如满月、唇若红莲、声响神清、手如干姜、泪堂有黑痣、眼下有皴纹;西门大姐鼻梁低露、声若破锣、面皮绷紧、行如雀跃,等等,都以命相判语的形式,从多视角、多侧面对人物的外貌和性格进行描述。刘勇强先生指出:“吴神仙对西门庆及妻妾的评论,外在于具体描写之上,到是可以看作作者的评论的。”[26]就是说,作者通过吴神仙代言,对西门庆及其妻妾进行评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为读者暂作一总结。判语还揭示了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如吴神仙相毕,西门庆回到后厅问月娘:“众人所相何如?”月娘认为女儿西门大姐和春梅两个没说准,特别是春梅:“我只不信说他春梅后来戴珠冠,有夫人之分。端的咱家又没官,那讨珠冠来?就有珠冠,也轮不到他头上。”按理说,庞春梅是丫鬟,不是西门庆的妻妾,虽已被西门庆收用,但还没有名分,地位最低,是没资格参与进来的,西门庆教吴神仙相她,就已经表明了他与春梅的关系非同一般,西门庆笑着向月娘解释,说庞春梅正好站在我身边,可能吴神仙误以为是我女儿,接着又去外面椅上坐着,令春梅提一壶梅汤来喝,半日,“只见春梅家常露着头,戴着银丝云髻儿,穿着毛青布褂儿,桃红夏布裙子,手提一壶蜜煎梅汤,笑嘻嘻走来”,春梅听说西门庆在后房已喝过梅汤,于是拿梅汤在冰里湃过,然后递给西门庆,并为他打扇,顺着追问月娘与西门庆的谈话内容,西门庆实话实说,春梅道:“那道士平白说戴珠冠。教大娘说‘有珠冠只怕轮不到他头上’。常言道:‘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从来旋的不圆砍的圆,各人裙带上衣食,怎么料得定?莫不长远只在你家做奴才罢!”这段对话,将此时西门庆和庞春梅的心情摹写得纤毫毕现,“梅汤”与春梅的名字有一个字相同,西门庆已在吴月娘房中喝过,出来后又指定春梅提一壶梅汤来喝,可见西门庆对她的宠爱。而因为相士的判语很好,春梅也心情舒畅,“笑嘻嘻走来”,但又担心触犯吴月娘,所以很想得知吴月娘的看法。在听了西门庆的转述后,庞春梅说的一番话,凸显了她“心眼只宽”的个性。
其次,命相判语在小说结构中有更重要的作用。第二十九回吴神仙给西门庆妻妾看相算命,第四十六回一个乡里老婆子给吴月娘、孟玉楼、李瓶儿卜龟儿卦儿,第四十七回东京报恩寺僧人相扬州苗员外,第六十一回真武庙精通先天易数的黄先生为李瓶儿算命,第九十六回善会麻衣神相的叶头陀为陈敬济看相。尤以第二十九回和第四十六回的集体看相术活动最为重要,这两回在词话本和崇祯本中都反映在回目中,词话本第二十九回为“吴神仙贵贱相人”,崇祯本为“吴神仙冰鉴定终身”;词话本第四十六回“妻妾笑卜龟儿卦”,崇祯本“妻妾戏笑卜龟儿”,都说明是该回的重要内容,而其他相术活动皆未出目。张竹坡指出,第二十九回“乃一部大关键也。上文二十八回一一写出来之人,至此回方一一为之遥断结果。盖作者恐后文顺手写去,或致错乱,故一一定其规模,下文皆照此结果此数人也。此数人之结果完,而书亦完矣。”[27]该回通过吴神仙的判语,对前二十八回写到的主要人物“一一为之遥断结果”,即做一个小结,同时,又为后面的内容“一一定其规模,下文皆照此结果此数人也”,就是说,吴神仙的判语预示了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命运结局,从作者的角度而言,在结构上不但回环兜锁,而且成为全书的叙事纲目,又制造了悬念,如在兹堂第二十九回文龙评曰:“作者借相士点破诸人终身,不过玉楼得好结果耳。何能详言其暖昧之事乎?若都指出金莲谋杀亲夫,瓶儿气死本夫,不但无此情理,亦无此神仙。世无此事,书不成奇矣。”[28]第四十六回文龙又评曰:“故借龟卜一层,先明示诸妇结果。龟婆未必如此之神,亦如前神仙之谈相云尔。”[29]从读者的角度而言,这无疑为后文埋下了多条伏线,设置了种种悬念,成为促使读者继续阅读下去的动力,这些主要人物有了结果,全书也就宣告完结。张竹坡指出第四十六回:“此回自吴神仙后,又是一番结果也”。[30]这句话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一是第四十六回是继第二十九回之后比较大型的看相算命活动,又再一次预示了月娘等人的“结果”;二是在第二十九回至四十六回间,发生了许多事件,都应验了吴神仙的一些判语,“卜龟儿,止月娘、玉楼、瓶儿三人,而金莲之结果,却用自己说出,明明是其后事,一毫不差。而看者止见其闲话,又照管上文神仙之相,合成一片”。[31]即与第二十九回“照管”——相互照应,月娘、玉楼、瓶儿之后事是通过卜龟预叙的,但潘金莲却是通过她自己之口说出的。文中写刘婆子刚走,潘金莲和大姐接着从后边出来,潘金莲笑道:“我说后边不见,原来你们都往前头来了。”月娘道:“俺们刚才送大师父出来,卜了这回龟儿卦。你早来一步,也教他与你卜卜儿也罢了。”金莲摇头儿道:“我是不卜他。常言:‘算的着命,算不着行。’想前日道士打看,说我短命哩!怎的哩?说的人心里影影的。随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沟里,就是棺材。”结果一语成谶,潘金莲最终死于武松利刃之下,暴尸街头,无人敛埋。第九十六回,张竹坡又评云:“此回叶道相面,单结敬济。盖上回冰鉴为众人一描,后回卜龟又一描,方将众人全收去。夫既遮遮掩掩将敬济隐于西门庆文中,则不必急为敬济结束。今既放手写敬济,是用于将到守备府中,即为之照冰鉴、卜龟一样结束,以便下文一放一收而便结也。”[32]就是说,陈敬济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是西门庆的女婿,西门庆称他为“我儿”,在西门庆死时,他还作为儿子披麻戴孝,特别是西门庆死后,陈敬济与庞春梅成为小说的“主脑”。在第二十七回,张竹坡批云:“此回是金莲、玉楼、瓶儿、春梅四人相聚后,同时加一番描写也。玉楼为作者特地矜许之人,故写其冷而不写其淫,春梅又作者特地留为后半部之主脑,故写其宠而亦不写其淫。”[33]即谓在前面没有渲染春梅的淫行,是为后面留出余地。在第二十九回吴神仙为西门家集体看相时,也唯独遗漏了陈敬济,按照张竹坡的解释,一是“盖大姐相而敬济之结果已过半矣。故此不相陈敬济”,二是“盖西门之待敬济半以奴隶待之,故不入敬济”。[34]就是说,西门大姐已相,从她的判语中已可知陈敬济的信息;其次,西门庆对陈敬济奴隶视之,不会给他看相的机会。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在人物的设计上,陈敬济是西门庆的“接班人”[35]、“衣钵传人”[36],苏曼殊说他是西门庆的“倒影”[37],是西门庆荒淫生涯的延伸,在西门庆死后成为叙事中心,延续西门家族的故事,因而放置后文补充为他“冰鉴”,这样就使小说写来富于腾挪变化。叶头陀的判语,既是对陈敬济前半生的绾结,也预示其即将进入守备府中并最终被杀的结局,此即所谓“收”与“放”。张竹坡的评点指出了第二十九、四十六、九十六三回中看相算命活动描写在全书中的结构功能,可见作者运用了互见法,通过看相算命描写,数次提示小说中重要人物的命运结局。
《金瓶梅》不但通过命相描写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塑造人物和结构全篇,宣扬宿命观念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是《金瓶梅》的基调之一,除相术外,小说还利用谶语等作为伏线,如第六十一回写西门庆要与病中的李瓶儿交欢,李瓶儿被缠不过,笑道:“谁信你那虚嘴掠舌的。我到明日死了,你也舍不得我罢。”第二十一回写西门庆与众妻妾猜枚行令,各人酒令都隐含了自己的个性和命运,如潘金莲的酒令:“鲍老儿,临老入花丛,坏了三纲五常。问他个非奸做贼拿。”第三十一回,西门庆加官生子,生日当天开宴庆贺,并有演出,薛、刘二太监所点曲词,或为“叹浮生有如一场梦里”,或为“想人生最苦是离别”。李瓶儿死时,应伯爵和西门庆都梦见玉断簪折。这类例子很多,加重了小说中的色空、劝惩佛道主题。词话本入话从项羽、刘邦贪色而误大事的故实说起,引入正题,叙述潘金莲的故事。崇祯本入话则以吕洞宾的诗开头,进行议论,归结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到不如削去六根清净,披上一领袈裟,参透了空色世界,打磨穿生灭机关,直超无上乘,不落是非窠,倒得个清闲自在,不向火坑中翻筋斗也。”结尾由普静禅师幻度,月娘省悟,舍子出家,为西门庆赎罪,只是词话本和崇祯本第一百回的回目不同,词话本为“普静师荐拔群冤”,崇祯本是“普静师幻度孝哥儿”,从回目看来,词话本强调群体解冤,而崇祯本更看重西门庆个人的罪恶。总之,小说以玉皇观始,以永福寺终,一热一冷,因果报应,寓含劝惩,在西门家族中,只有所谓“秉性贤能”的月娘和“温柔和气”的玉楼有较好的结局。
《金瓶梅》这种结构方式后来为《小奇酸志》《醒世阴阳梦》等众多小说所模仿,其中《红楼梦》最为突出,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回批》第九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批曰:“我读《金瓶梅》,读到给人相面,总是赞赏不已。现在一读本回,才知道那种赞赏委实过分了。《金瓶梅》中的预言结局,是一人历数众人,而《红楼梦》中则是各自道出自己的结局,教他人道出,哪如自己说出?《金瓶梅》中的预言,浮浅;《红楼梦》中的预言,深邃。所以此工彼拙。”[38]哈斯宝可谓目光如炬,与《金瓶梅》比起来,《红楼梦》可谓不着痕迹,更为巧妙。
陈东有教授已指出,吴神仙等相士的判语多是抄袭《神异赋》等相术典籍[39],这样,有时作者难免会考虑不周,照抄而未做相应改动,以使与小说中人物的命运结局契合,因而有时会产生扞格不通的现象,如说西门庆“天庭高耸,一生衣禄无亏;地阁方圆,晚岁荣华定取。”西门庆三十六岁即暴亡,与“晚岁荣华定取”不符。又如说西门庆“临死有二子送老”,官哥儿是在西门庆加官进爵生命中最辉煌的时刻出生的,但不久夭折;孝哥儿是西门庆的遗腹子,后为死去的西门庆赎罪而出家,西门庆死时无一子送终。或许有人会理解为术士吹捧西门庆的谄词,但从小说的描述看来,吴神仙、黄道士等术士皆非贪钱谄媚之辈,就是刘婆子的判词,也是实话实说,不乏恶判,而且后来大都应验,所以,这只能理解为是作者抄袭相书时未及堵塞的纰漏。
绾而言之,《金瓶梅》中的命相活动描写,既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作者又利用明相观念,刻画人物形象,建构故事情节,可谓一扣多响,对读者深化对小说的理解大有裨益。通过考察《金瓶梅》与命相术的关系,可以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野,这既是考察明代社会的一个切口,也是理解命相观念如何内化为一种小说艺术技巧和审美情趣的一个很好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