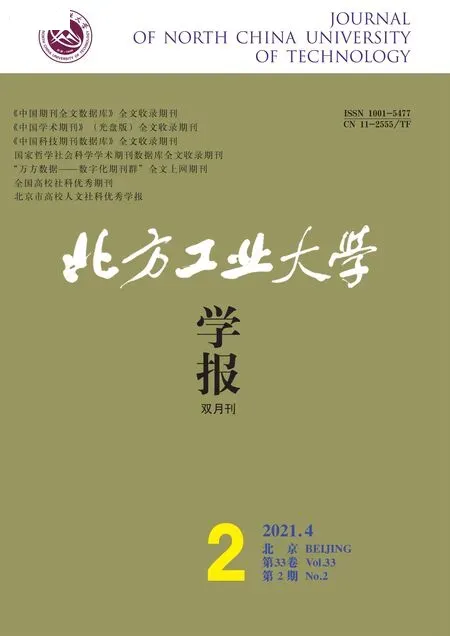《金瓶梅》中的漆器书写
熊 敏
(云南省烟草公司昭通市公司,657000,昭通)
《金瓶梅》①中大量存在的漆器以一种细枝末节的琐碎状态分布于故事的各个角落,作者不厌其烦地对文本中漆器的工艺技法进行描述,当我们惊艳于这些漆器的华美与精致的同时,不难发现作者通过漆器不动声色地向读者展示了故事的脉络,作品中的漆器隐含了作品的诸多线索,它们或彰显人物身份,或刻画人物性格,或展示家庭兴衰,或反映社会风尚,让读者于琐碎之中品味出无限烟波。
1 彰显人物身份
“银镶雕漆茶钟”作为《金瓶梅》中第一次出现的精品漆器,其华丽登场是在西门庆与孟玉楼“相亲”之时(第七回):“说着,只见小丫鬟拿了三盏蜜饯金橙子泡茶,银镶雕漆茶钟,银杏叶儿茶匙。”“银镶雕漆茶钟”所采用的施漆工艺应是被称为“金银胎剔红”[1]的技法,具体方法是用金或者银等贵重金属作胎,在漆胎之外用漆堆积达数十层,再进行人物楼台花草的雕刻,刀口要露出金质或者银质的胎子来。“银镶雕漆茶钟”在此处出现,足以证明其主人家道殷实。
西门庆在与潘金莲打得火热的时候,卖花翠的薛嫂儿寻到了西门庆说一桩亲事,对象是“咱这南门外贩布杨家的正头娘子,手里有一分好钱,南京拔步床也有两张……”作者虽然交代了“西门庆只听见妇人会弹月琴,便可在他心上”,但一个素未谋面的寡妇,真正能打动西门庆的还是“手里的一分好钱”,因为他即将嫁女,正是使钱的时候。孟玉楼的价值很快便体现出来了,六月初二孟玉楼过门,六月十二陈宅就娶西门大姐过门,“西门庆促忙促急,攒造不出床来,就把孟玉楼陪来的一张南京描金彩漆拔步床陪了大姐”,在此姑且不论“拔步床”的形制,单看其施漆手法,就知非常珍贵,它采用的是“描金加彩漆”[2]两种工艺的结合,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纹饰相结合的各种漆器被称为“斒斓”。[3]“描金”即漆地上加描花纹的做法,具体做法是在一件已经完成的器物上用笔蘸漆描画,画完入阴室,等到干湿程度最适合的时候取出,用丝绵团蘸泥金粉,着在漆器上,以致显露出泥金的花纹。[4]“彩漆”就是在光素的漆地上,用各种色漆画花纹的做法。[5]由此可知这张“南京描金彩漆拔步床”是如何的珍贵,用来做女儿的嫁妆,绝对是拿得出手,撑得住场面的。西门庆和孟玉楼的结合,是西门庆“一生多得妻财”的第一步。
如果说西门庆和孟玉楼的结合是西门庆“一生多得妻财”的第一步,那么李瓶儿嫁给西门庆,带给西门庆的财富,则最终成就了西门庆“大巨家”的地位。伴随李瓶儿出场的,是一件“雕漆茶钟”。“雕漆”[6]是用漆在漆器胎骨上层层积累,多的有堆积五六十道乃至上百道漆的,到一个相当厚度,然后用刀雕刻出花纹的做法。这样的雕漆茶钟,虽然不像孟玉楼家的“银镶雕漆茶钟”直接使用贵重金属做胎,但也是精美异常。除此以外,李瓶儿家里又有装“蟒衣玉带、帽顶绦环”等物的“四口描金箱柜”、又有盛放“金寿字簪儿”的“小描金头面匣儿”;嫁给西门庆后,自己房里又有“洒金炕床”,又有“描金炕床”。这些精美的漆器,也如同孟玉楼的那张“南京描金彩漆拔步床”一样,彰显出李瓶儿殷实的家底。
除此以外,漆器被用于彰显人物身份的还有多处,例如西门庆到东京给蔡京拜寿时住在蔡府管家翟谦家里,翟谦款待西门庆时所用的剔犀官桌上列着“几十样大菜、几十样小菜”。“剔犀”[7]是用两种或三种色漆在器皿上有规律地将每一色漆上若干道,积累起来,然后用刀刻出云钩、回文等图案,于是在刀口的剖面出现了不同的色层。文中交代“只没有龙肝凤髓,其馀奇巧富丽,便是蔡太师自家受用,也不过如此”。由此可见作为蔡府的大管家,翟谦本人的家底是如何的雄厚。
2 刻画人物性格
第二十九回,西门庆来到潘金莲房中“看见妇人睡在一张新买的螺钿床上。原是因李瓶儿房中安着一张螺钿敞厅床,妇人旋叫西门庆使了六十两银子,也替她买了这一张螺钿有栏杆的床,两边槅扇都是螺钿攒造”。“螺钿”[8]即用蛤蚌壳作原料,经过加工嵌入漆面作为装饰。明中叶以后的螺钿漆器以薄螺钿比较普遍,讲究“精细密致如画”,而在颜色上,则是“质地宜黑不宜朱”,以黑漆地为主。
潘金莲这张螺钿床花了六十两银子,较之她才嫁给西门庆的时候花十六两银子买的那张“黑漆欢门描金床”价格自然不能同日而语。西门庆愿意为潘金莲花六十两银子买这张床,首先当然是李瓶儿进门后,他的财富积累达到一个新高度,六十两银子对于他来说也算不上什么。另外,这与西门庆平常使钱的方式也有关系,对于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花多少银子都可以。显然,潘金莲在他心中的地位、潘金莲带给他的快乐自然值得这张六十两银子的螺钿床,不然他为什么不买给孙雪娥、不买给李娇儿,单单买给潘金莲呢?
这张螺钿床是比照李瓶儿房中的螺钿床购置的,自然是精美异常,但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潘金莲非要时时处处攀比李瓶儿呢?如果说仅只是因为李瓶儿有钱,那么对待同样有钱的孟玉楼,她为何又没有如此放肆呢?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潘金莲处处攀比李瓶儿的根源还是来自于她的“不甘心”,来自于她“争强不伏弱的性儿”,对于潘金莲这样一个除了自己一无所有的人来说,以李瓶儿为目标,并将之攀比下去,同时牢牢把握住西门庆这个人,是她在内宅之中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生存需求。
3 展示家庭兴衰
第二十回“西门庆自从娶李瓶儿过门,又兼得了两三场横财,家道营盛,外庄内宅焕然一新,米麦陈仓,骡马成群,奴仆成行……又打开门面两间,兑出二千两银子来,委付伙计贲地传开解当铺”。自此,西门庆的生活品质上了一个新台阶,各种精美的漆器在不经意间,鲜活在西门府家常生活的各个场景:家中用来款待应伯爵和韩道国的是“雕漆茶钟”(第三十四回);“彩漆方盒”端着盛放酥油白糖熬的牛奶子的“银厢雕漆茶钟”(第六十七回);“描金厢子”是吴月娘正房里用来放皮袄的(第四十六回);吴月娘用“小描金碟儿”盛放点心款待两个姑子(第三十九回);“小描金盒儿”被西门庆吩咐王经用来装玫瑰花饼给韩爱姐送去(第七十一回);四个“螺钿大果盒”是与乔大户家结亲的时候装礼品用的(第四十一回);“罩漆方盒儿”是盛放食物的食盒(第四十五回)等等。
如果说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漆器被作者看似随意地散放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那么全文中有两处特定场景的描写,便是作者专为鼎盛时期的西门府所设置的。
西门庆生子加官后“新近收拾大厅西厢房一间做书房,内安床几、桌椅、屏帷、笔砚、琴书之类”(第三十一回)。作者在此交代了破落户财主出身的西门庆有了专门的书房,至于书房中的具体陈设,作者则是巧妙地通过韩道国和应伯爵的视点呈现出来:第三十四回,韩道国因自己老婆和兄弟的事要求西门庆,于是邀上应伯爵一起到西门庆家中的书房等候,在韩道国和应伯爵的眼中,书房里有这样一些精美的髹饰家具“六把云南玛瑙漆减金钉藤丝甸矮矮东坡椅儿”、“一张大理石黑漆缕金凉床”、“两边彩漆描金书橱”、“黑漆琴桌”、“螺钿交椅”。可以想见,在韩道国与应伯爵这样的人眼中,这样的热闹体面的书房,代表的是怎样一种不可企及的财富与地位。当财富化为实实在在、让人目眩神迷的具体物质的时候,这种外在的视觉冲击往往会使生活水平低于此的人内心产生强烈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激励,这种否定和激励交织出一种拼命追求财富的动力,这正是促使韩道国默许自己老婆与西门庆偷情的原动力。
第四十五回,西门庆的解当铺送进来一座“三尺阔、五尺高,可桌放的螺钿描金大理石屏风”和“两架铜锣鼓连铛儿”,总的只当三十两银子。此处“螺钿描金”应为“描金加甸”[9]即同时采用描金与螺钿两种做法,使一件漆器上具备描金的花纹和嵌钿的花纹。西门庆自己对这架繁复精美的大屏风自然是喜爱的,再加上应伯爵指出:“哥,你仔细瞧,恰相好似蹲着个镇宅狮子一般。”更是抓住了他的心思。此时的西门庆官运亨通、生意兴隆,正是如日中天的鼎盛时候。当物质满足了个体的基本生活需求以后,追求物质形而上的象征意义,便成为个体精神上的需求。西门庆家那么大的住宅,正好需要一个所谓的“镇宅”。但屏风却不是他买的,而只是白皇亲家抵押在他的当铺,用来借高利贷的,随时都有可能被赎回去,因此他问“不知他明日赎不赎”。这个时候应伯爵的回答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没的说,赎什么?下坡车儿营生。及到三年过来,七八本利相等。”要说西门庆为何总是那么信任和依赖应伯爵,只因应伯爵对世情的洞察,对事件的认知,总是一语道破天机,深得西门庆的认可。从这个事件,我们可以透过西门庆的泼天富贵的表象看到社会财富不再只是集中在皇亲国戚手中,作为商人出身进而加官进爵的的西门庆,正在成为掌握这些财富的新主人。
然而,西门府中金彩辉煌的各种漆器,随着西门庆的过世最终也黯淡了光辉。潘金莲争强不伏弱要来的螺钿床,被用来抵还孟玉楼的拔步床,陪嫁到李衙内家;孟玉楼原先那张陪嫁西门大姐的“南京描金彩漆拔步床”被吴月娘抬回来后只卖了八两银子,用来打发县中皂隶;至于李瓶儿房中价值六十多两银子的的螺钿床,也只卖了三十五两银子。没有了西门庆的西门府,正如同当初典当“螺钿描金大理石屏风”的白皇亲家一样,都是“下坡车儿营生”。家中各种贵重的髹饰家具,被一一贱卖,曾经富贵滔天的一个家庭,最终衰败如此,这种前后环境变化的巨大差距,让人感叹的是世事无常,所以不怪做了守备夫人的庞春梅游玩旧家池馆的时候“那星眼中由不的酸酸的”。
如果说各种精美漆器反映出西门府家运的兴旺发达和精致的生活水平,那么一件出现在韩道国家的“红漆描金托子”则更加耐人寻味。韩道国一家三口原本是住在县东街牛皮小巷,位置偏僻,但是因为与西门庆有了牵扯,曾经穷困潦倒的韩道国一家最终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上了“红漆描金托子”这样精致的漆器。由此我们可以窥见韩道国一家发家致富的道路,更可以看到小说所处的那个笑贫不笑娼的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们为了追求物质,可以没有底限地出卖任何可出卖的东西,包括身体,也包括灵魂。
4 反映社会风尚
说到《金瓶梅》中的漆器,不得不说的还有几件被明确冠以地名的漆器:一是六把“云南玛瑙漆减金钉藤丝甸矮矮东坡椅儿”(第三十四回);二是一件“云南玛瑙雕漆方盘”(第三十五回)。
这六把“云南玛瑙漆减金钉藤丝甸矮矮东坡椅儿”应是髹饰工艺中的“百宝嵌”[10]与藤编工艺结合的产物。通过这几把东坡椅,我们可以得知或许在晚明时期,云南的藤编家具已经很好地与髹饰工艺结合在一起了,并得到了北方市井群众的认可和喜爱。而“云南玛瑙雕漆方盘”(第三十五回)则是“百宝嵌”和“雕漆”的结合。作为明代漆器的两个主要流派之一(浙江嘉兴漆器和云南漆器),云南雕漆和永乐、宣德时代浙江嘉兴系统不露刀痕、注重磨工、浑厚圆润的风格大不相同,它的风格是“不善藏锋,又不磨熟棱角”。云南雕漆之所以能自成一派,其原因是:“唐之中世,大理国破成都,尽掳百工以去,由是云南漆织诸技,甲于天下……元时下大理,选其工匠最高者入禁中。至我国初收为郡县,滇工布满内府。今御用监、供用库诸役,皆其子孙也,其后渐以消灭。嘉靖间,又敕云南拣选送京应用。”[11]因此,这件云南玛瑙雕漆方盘在此出现绝非偶然,它与百宝嵌和云南雕漆的兴起和流行息息相关。
除了大量精美的家具以及日常生活用品,髹饰工艺还被广泛地运用于房屋建筑,从蔡太师府邸“绿油栏杆、朱红牌额”的“学士琴堂”到朱太尉家中“周围都是绿栏杆,上面朱红牌匾”的“执金吾堂”;从孟玉楼前夫家中的“朱红槅扇”、王招宣府的“朱红匾”到临清第一的谢家酒楼“周围都是绿栏杆”;从吴道官“金钉朱户”的玉皇庙、“朱红亮槅”的松鹤轩到“正面三间朱户”的晏公庙。无论阶层、无论场所,只要是有条件的,均会用红色或绿色的油漆装点房屋。我国漆器,自古即尚朱色,因而经籍中有不少丹漆,彤漆的记载。而绿漆又称为“绿沉漆”,指深绿色的漆,讲究光泽鲜明。在房屋装饰中大量运用明快的红漆和绿漆,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大众的审美情趣。
如果说《金瓶梅》是一副中国工笔画的话,那么其中的漆器必定是浓墨重彩、不可或缺的色彩之一,它们与故事中的饮具、餐具、服饰、家具等等生活用品共同构建了小说纷繁复杂、五彩斑斓的庞大背景,为故事情节的开展铺设道路,为人物的言行叙说和心理活动搭建平台,是作品隐含的叙事密码,其间隐藏着故事发展的脉络。
注释:
① 《金瓶梅》的版本系统分为“词话”与“小说”,本文材料内容来源根据为“词话”本。
—— 墨彩描金瓷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