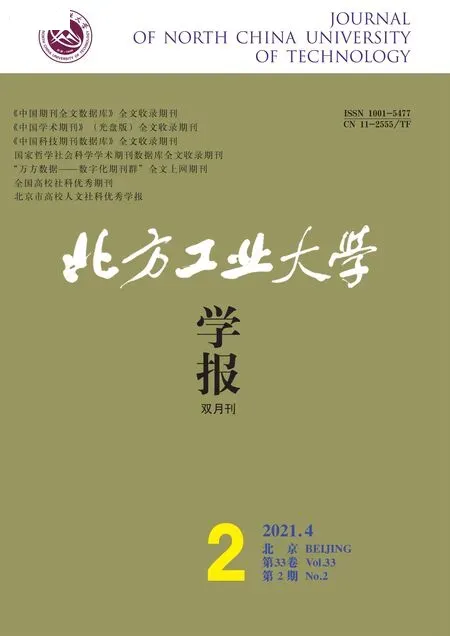探寻《金瓶梅》的传世密码
卜 键
(文化和旅游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100080,北京)
在我国的古典小说中,很少有一部像《金瓶梅》这样为恶名缠累、屡遭禁毁。改革开放之后,相关的出版与研究渐入佳境,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情形,可即便在40年后的今天,《金瓶梅》在不少人心目中仍顶着个禁书、淫书的帽子,阅读和研究它都要有一些勇气。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作品相比,《金瓶梅》似乎一直走在一条窄路上,却也是屡禁不绝、历劫更生。
寻觅《金瓶梅》的文本魅力和传世密码,抉发其内蕴的丰厚价值和多重意义,似应拆解一些疑问和话题:有关《金瓶梅》“诲淫”的说法是怎样形成的?该书是否被污名化,是不是真的被禁过,经历了一个怎样的禁毁过程?它拥有一个怎样的作者,产生于哪一个时代,又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凡此种种,学界已有过广泛探讨,又很难达成共识,本文试着做一些归纳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求其文学意义。
1 “诲淫”的表与里
《水浒传》“诲盗”,《金瓶梅》“诲淫”,是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其荒谬自不待批驳。而《金瓶梅》自带污点,又被严重污名化,亦毋庸讳言。
所谓污点,是指它的不少章节存在着淫秽描写——性心理、性现场、性过程、性施虐,包括一些淫词浪曲随处可见,有的比较隐晦,也有的写得非常细致、直露,不堪入目。1980年代以来,多家出版社经过批准,刊行了《金瓶梅》的不同版本,有全本,也有删节本。学界对于删节的做法不太认同,但客观来说,其间也有一番苦心。
至于《金瓶梅》的被污名化,或怎样被污名化,也是说来话长。这部产生于明代中晚期的小说,从诞生之日起,贯穿整个清朝,一直到今天,都有人(包括没有读过的人)将之称为“淫书”,乃至指为“淫书”之首。其实淫秽的描写在书中只占极少的部分。1990年代,在已故冯其庸先生的指导下,我与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的白维国研究员合作,用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认真地校注过《金瓶梅》。遵照规定,我们做了比较彻底的删节,也只删掉约计4 000字。相比于全部书近百万字的总量,这个比例实际上是很小的。[1]下过此一番功夫,始知《金瓶梅词话》中的涉淫文字也是千差万别:有从前人作品中直接拿来就用的,如一些描绘性场景、性器官的色情小赋,当时的流行小说中随处可见;也有在写作过程中随笔点染铺陈,或着意渲染,以吸引眼球的。“诲淫”之诬妄,大约得自这些地方,却只是眼见其“表”。
至于“里”,也就是该书性描写的主要目的,则在于精心结撰人物形象,在于彰显情欲泛滥的危害,在于对生命意义和生存法则的思考。如第二十三回西门庆与宋惠莲在山子洞中的淫媾,那种隆冬时节的彻骨之寒,使一场偷情欢会演为遭罪,演为潦草匆迫和嘟嘟囔囔,加上外面还有一个听墙根的潘金莲,逼肖真切,一色白描,命意并不在淫事上。再如第七十九回“西门庆贪欲得病”,则写主人公最后的淫纵,从主动变为被动,从施虐变为被虐,肉体之乐化为彻骨锥心的痛,进而化烟化灰,笔触冷然,且不无悯恻。这样的性描写,重在刻画人物性格与生命的悲哀,是书中的精彩笔墨,不宜也不必删节。
记载缺略,很难确知该书经历了怎样一个创作与流传过程。它是文人独立写作的,还是在“历代累积”的改定的?是坊间先有了一部众口传唱的词话,是作者有意选择了词话的形式,抑或说唱艺人将文人小说作了改塑?那些个淫秽文字是原创的,还是后人添加的?所有这些都存在不同说法,存在激烈争论,应也能在细读原作中得到提示开解,也就是说阅读和研究都要由表及里,体味作者的良苦用心经命意所在。
2 “兰陵笑笑生”的隐喻
《金瓶梅》的作者,至今仍是一个谜团。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早的版本,是明代万历末年刊刻的《金瓶梅词话》,又叫做“词话本”,署名“兰陵笑笑生”,也就是作者。但是“兰陵笑笑生”是谁?学者们根据这五个字追踪、寻找,拿着一顶尺寸凛然的帽子去寻找那合适的脑袋,发现不少人都有几分相像,很多时候又都认错了路头。
一般说来,“兰陵”指的应是地名,如山东的峄县即古兰陵,张远芬兄提出贾三近说,即由此而来。但江苏的武进古称南兰陵,南兰陵也可以叫兰陵,所以就争执不休。如果思路再开阔一些,应能联想到兰陵笑笑生或有所隐喻。在中国历史上,“兰陵”二字挽结着一些人物与故事,内涵早由单纯的地名溢出,或也具有着某种精神层面的暗示。而对“笑笑生”三字,吴晓铃先生也有过发现,曾有过一首《鱼游春水词》即署此名,是否就是“兰陵笑笑生”,那就不好论定了。
对于《金瓶梅》的疑似作者,研究界先后提出的有李开先、王世贞、屠隆等说法,各下了一番功夫,也都缺少过硬的板上钉钉的证据。我也曾写过一部研究《金瓶梅》作者的书,现在虽未改变观点,却也不坚持,为什么?还是那句话,缺少板上钉钉的铁证。所以,在没有新的可信史料发现之前,对于“作者是谁”,不必花大的力气折腾来折腾去地去说了。
综合内证和外证,可以大致推定《金瓶梅》的作者主要生活在明朝嘉隆年间。他应该是一位名气很大的文人,在朝廷里面做过官,而且担任的是比较重要的官职。阅读小说中描写朝政、国家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内容,你会发现他对京师和朝廷着墨虽不太多,但非常了解,运用纯熟,一些仪节和场景,绝非一个乡间老儒或说书先生所可悬揣。这位作者应该遭遇过宦场风波,故而有着对权奸操弄国事的痛恨,也有着较为豁达的人生态度;其在退休后回到县城生活,所以才会有书中对于县邑各色市井人物的那种入木三分的刻画。
关于兰陵笑笑生的籍贯,个人强烈认为应该是在山东一带,这也是前人有过说法,但至今仍备受质疑,应予重申。作者人生经历与生活环境,不可避免地要在作品中显现。比如《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不太熟悉小县城的市井,在家族败落以后,他回忆和书写的仍然是京师贵族的生活;而兰陵笑笑生非常熟悉市井,尤其是小县城的市井人物,一落笔便觉须眉生动。
3 《金瓶梅》的写作特色
依照今天的标准,《金瓶梅》应该不能算是一部原创、独创之作。
《金瓶梅》中有不少东西来自《水浒传》,那些文字好像“零部件”,比如一篇写景韵文、一个抒情小赋、一首诗、一段文字啦,往往从其它书里面拿过来就抄到书里了,就像是组装车辆的零部件一样。原创,较多属于今天的概念,讲究“无一字无来历”的前贤似乎并不太重视这个。《金瓶梅》的作者也如此,不太考虑独创的问题,描写日常景物有时懒得去费事儿。比如说雨景,古典小说里有很多写雨的精彩笔墨,兰陵笑笑生到了要写雨的时候——像第四回王婆打酒遇到大雨,就随意抄来一段,嵌入后并无违和感。作者博览群书,显然对于俗文学,对于小说、戏曲、民歌、谣谚,也包括对联谜语等非常熟悉。他是一个典型的拿来主义者,从来不避讳“抄袭”,凡是自己看上的,认为有用的,拿起来就放进自己的书中。
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明清两朝的小说家没有稿费,也没有工资,有的只是写作冲动和可能得来的名声,当然也有可能带来麻烦,甚至灾难。他们对于署名很谨慎,原因也在万一被发现有影射等等的东西,可能就会倒大霉,不是有没有稿费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脑袋的问题。所以他们经常署的是笔名、别号,乃至假名。与此相关联,他们对“抄袭”则很大胆,觉得有用就拿过来,自己不在乎,读者也不挑剔。
当然这只是指一些枝枝叶叶,并非一部书的整体布局、情节主线、整个作品主人公的塑造,如果这些都抄袭,就不能称之为作品了。其实创作和抄袭的不同,当在能否赋予一部小说以文学的生命。兰陵笑笑生大量使用其他书上的故事、人物、诗文片段,却是化用和重铸,是再创作,是用这些材料建筑自己的文学大厦,建构一部全新的伟大小说。
整部《金瓶梅》的大框架,取自《水浒传》中的武松故事。《水浒传》有“武十回”之说,就是主要写武松的十回文字。过去的章回小说,一般有百回之多,但在大叙事中套着小叙事,段落性很强。兰陵笑笑生就把其中的“武十回”拿来,加加减减,扩充开来。好像是从《水浒传》砍下的一根树枝,栽到泥土里,又长成的一棵新的参天大树。《水浒传》里面的一些内容,当时流行的话本小说、流行的戏曲里面的一些人物,一些大大小小的故事,直接化为兰陵笑笑生的写作元素,催生了浑整且别开生面的《金瓶梅》。
在这样做的时候,兰陵笑笑生具有强烈的文学自信,这是需要强调的一点。凡是拿来的东西都是为我所用的,经过一番解构重构,故事好像还是那个宋朝故事,人物也有很多的《水浒》故人,但已自成一家,举手投足之间,散溢着明朝中晚期的风格色泽——
武二郎虽然还是个打虎英雄,但从水泊梁山的江湖,走入小县城的官衙和市井,由闯荡江湖的铮铮铁骨,变得喊冤叫屈,苦苦哀求,也由主角变成了配角。而原书中那个被武松三拳两脚当场打死的西门庆,由一个市井小混混,变为富甲一方的商人;再由富商变成官员,而且是主管刑狱治安的官员;接下来由副职变成正职,成为一部新书的主人公,意气风发地又活了七年。大家注意,本书中西门庆的故事只有七年,是没有打死他,是活下来了,但是活了多久呢?短短的七年。他最后死在了潘金莲的床上,此时的武松还在外地服刑。
看似无意之间,兰陵笑笑生做了一个重大改变:在《水浒传》中,作恶与报应相连。武松出差回来,立即给哥哥报仇,将西门庆痛打致死。而在《金瓶梅》中,原作中那种立刻实施的为兄复仇,让读者看得痛快淋漓的手起刀落、溅血五步,被改换成一种自然的死亡,不是被打死、药死、砍死,而是死于绣榻之上、温柔乡中。西门庆在政商两界正混得风生水起,所有的日子都那么风光和快意,却在穷极欢乐时突然发病,经历短暂的折磨后一命呜呼。这是其自身病痛的折磨,更是他的自作自受,是伴随着长期放纵的自我砍斫。不比不知道,《金瓶梅》所凸显的生命法则和生存理念,比起原书中那种血腥报复,显然更为深邃警策。
从另一个角度讲,西门庆的死也算作“暴亡”,并非正常的死亡。他才33岁,他的事业正如日中天,财富正滚滚而来,但是嘎嘣就死翘翘了,能算是自然死亡吗?兰陵笑笑生在全书开始的时候,就作了一个声明,说自己写的是“一个风情的故事”,主要指的就是西门庆与潘金莲、李瓶儿等人的爱欲纠葛。他们曾经有过很多的快乐时光,他们之间也不是一点爱情也没有,但人品太差,道德太差,害人、互害,最后害了自己。通观全书中的情色描写,主要用以来刻画人的生命之脆弱,以一个个纵恣放荡的场景,以争风吃醋和害人手段,最后达到的是一种痛彻心扉的反省。“风情的故事”,也指西门大院内外那些偷偷摸摸、永不间断、不择地而生的私情。不是一件两件,是一件接着一件的私情。不仅仅是西门庆,也不仅仅是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个女子,还要加上更多的青春之躯,无一不是跃跃然走向死亡。
《金瓶梅》中的情色,较多的是基于现实主义的描写,是对社会堕落、人性丑恶的揭露和抨击。我们说它是一部明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就是依据这些作出的判断。
4 从一则记载看《金瓶梅》的禁毁之实
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明清两朝都曾对《金瓶梅》实施过厉禁。这种说法虽不能说错,但过于笼统,而笼统含混的表述往往会遮蔽真相,造成误导。
从今天所能得见的档案文献,未见在国家层面上对这部书发布过正式的禁止文告,明朝没有,清朝也没有。清顺康雍三朝颁布过禁售淫词小说的诏敕律令,没有提出具体的书名;乾隆朝曾禁刊《水浒传》,并开列“禁毁小说戏曲数目”,其中不包括《金瓶梅》。地方政府曾经发布过禁令,像江苏等地方,但推行既不彻底,也未被推广到全国的范围。
清道光间山东布政使王笃①的《两竿竹室文集》中有一则记载,写宠臣和珅在军机处开讲《金瓶梅》,被同僚王杰当面嘲讽之事,曰:
蒲城家省厓相国谓予曰:昔文端公在军机与和珅同列,遇事忿争,怒形于言,人多为公危,公亦以同事龃龉,非协恭之道,屡乞解罢枢务,而高宗不允。不得已数请病假,有至五月之久者,高宗知公深,不之责也,痊即仍入枢垣,故当时有“三进军机”之说。
此一段先作铺垫,应对涉及到的人物和语词略作介绍:文端公,即王笃的祖父王杰,乾隆二十六年状元,一生讲求操守,居官至廉,逝后谥文端。而“蒲城家省厓相国”,乃道光朝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字省厓,陕西蒲城人,与王杰籍贯韩城相距不远。王鼎的爷爷王梦祖为王杰未第时的亲密文友,族人也系从山西迁陕,因此称为本家。王鼎于嘉庆元年中进士,曾应邀到王杰府上,多蒙奖掖,终生执晚辈礼,对于当时军机处(即枢垣)的描述很真切:和珅恃宠骄纵,在朝廷内外呼风唤雨,纵是王杰也不无忌惮,故多次上疏求退;而王杰也是乾隆帝发现和重用的人才,二十六年(1761)殿试后御览前十卷,亲自将之从探花拔为状元,后见其人品贵重、学问博雅,一直倚重有加,号为“特达之知”。
清廷自雍正朝设立办理军机处,位于隆宗门内,紧挨着皇帝理政的养心殿,遵旨办理军国要密,很快就形成超越内阁之势,称为“枢垣”“枢务”。乾隆末年至禅让期间,内阁首辅兼首席军机大臣阿桂常患病休假,次枢和珅主持枢阁机务。阿桂于嘉庆二年秋病逝,和珅接任首辅和首枢,巴结讨好、依附趋奉者甚众,董诰、刘墉、纪昀等资深大员亦避其锋芒,只有一个王杰敢于与之抗衡,此处说到王杰虽“遇事忿争”“怒形于言”,心下仍不自安,请辞复请假,应是真实可信的。
接下来的话,也出自王鼎之口,说的是和珅在军机处会食时开讲《金瓶梅》的故事——
又言:一日诸公在军机会食,和相谈论风生,语近谐谑,文端厌之,起就别案,展纸作字。和言已,众冁然,公独若不闻者。和颔之,顾问公曰:“适所谈之故事,王中堂知出于何书?”公曰:“不省也。”和曰:“出在《金瓶梅》上。”公艴然持笔,拍案厉声曰:“此等混张书,我从来不兴看的!”和惭而哂曰:“天下岂皆正经书耶?”由是衔之益切矣。[2]
军机会食,指的是在直军机大臣一起共进工作餐。和珅是在乾隆四十一年春入军机的,年仅26岁。逾十年之后,王杰始以兵部尚书兼军机大臣,时已年过花甲,位次排在和珅之后。两人同在枢垣长达12年,跨越乾嘉两朝,此事发生在什么时段?推测大约在乾隆帝禅让之后。其时首枢阿桂年老多病,和珅管理日常事务。军机处本为机要缜密之地,大员素来崖岸自高,不苟言笑,即便是封疆大吏来京也不与之私下接触。而和珅主事后风格一变,历来肃静的军机处热闹起来,入京外臣熙熙攘攘,和珅与人相见常会调笑戏谑,此时又公然在会食时讲起《金瓶梅》来,毋怪王杰勃然作色。
弘历晚年基本不在皇宫长住,故这次会食,推测是在圆明园的军机茶房昨斋庭。小小院落整洁清幽,又称“军机别院”。查当时军机大臣,除却阿桂、和珅与王杰外,还有福长安、董诰、台布三人。福长安与和珅关系亲密,台布资历甚浅,而董诰则是个文怯书生,故王杰虽拂袖离席,他们仍稳坐听老和讲完,然后是陪同嘻嘻笑乐,以示愉悦与嘉许。如果没有王杰后来的一闹,应该说讲座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关于和珅曾读过《红楼梦》,并听乾隆帝揭示“明珠家事”一节,见诸曾国藩幕僚赵烈文的《能静居笔记》,通常以为是可信的。这一条和珅讲述《金瓶梅》的记载,应更为真实。王笃的信息源为生性端谨的道光朝大学士王鼎,时为庶常馆庶吉士,很有可能就是由同乡先辈王杰亲口告知。出乎常人意料之外的,是大清军机处竟然有人开谈《金瓶梅》。据王杰与其他军机大臣的反应,和珅所讲,应是其中的“黄段子”,且也有可能是“系列讲座”。时值白莲教在湖北、四川等地接连起事,上皇与皇上日夜焦灼,军政事务繁密紧急,每次会食时讲上一段《金瓶梅》,众枢臣开怀一笑,顿忘烦累,不亦乐乎?
此事乍看有点儿不可思议,实则不足为奇。不是说《金瓶梅》曾长期被禁毁吗,不是说顺康两朝颁布了禁毁淫词小说的律例吗?实则多为民间之禁,卫道者之禁,也有地方官府之禁,尚未见清帝下旨将该书明确列入禁毁名单。而另一个方面的证据是:康熙四十七年,内翻书房即将《金瓶梅》译成满文,刊刻印行。早期的翻书房多由皇帝交办译项,职司綦重,位于隆宗门内北房(即后来的军机直房),似也有理由推测康熙帝读过此书。《啸亭续录》卷一:“有户曹郎中和素者,翻译绝精,其翻《西厢记》、《金瓶梅》诸书,疏栉字句,咸中綮肯,人皆争诵焉。”[3]足以证明此书在满洲勋贵中之流行。和珅读的是满文版还是汉文版?根据现有资料难以认定,但通晓四种文字的他两个文本都能阅读。其在军机处吃饭时引为谈资,在别的场合自也会谈到,应无异议。
王鼎讲述这段往事,王笃记下这次交锋,自是以大贪官和珅为反衬,塑造王杰的醇儒形象。王杰一生崇尚理学,立身诚敬,风骨气节凛然,由此事也得以呈现。可也不得不说,王杰身上的道学气息甚浓,未经亲自阅读,仅据耳闻,就将《金瓶梅》斥为“混张书”,对文学的感觉远不如老和。其也反映了儒学正统人士对该书的评价,一种当时的主流观念,无他,仍是将《金瓶梅》目为淫书。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官学私塾,以及绝大多数的读书人家,自觉地实施着持久的禁锢。
王杰的言词也可证明,《金瓶梅》的被禁,是由于它顶了一个“淫书”的名声。淫书,当然是一个很可怕的说法,但应知道,中国古代有很多优秀的小说,第一流的小说、戏曲作品,往往被戴上这个帽子。比《金瓶梅》早的《西厢记》,与《金瓶梅》差不多同时流行的汤显祖的《牡丹亭》,晚于《金瓶梅》约两百年的《红楼梦》,都曾被一些道学家指为“淫书”,不只一部《金瓶梅》。张竹坡将《金瓶梅》称为“第一奇书”,强烈反击流行的“淫书”之说,又说《金瓶梅》是一部“史记”,说其作者必然能写出像司马迁《史记》那样的巨著。这些话有一点拔高,意在回怼那些恶评,也不算太离谱。
5 《金瓶梅》的意义
在流传至今的三个版本系统中,《金瓶梅词话》最有文学价值。理由有两点:其一,它是《金瓶梅》最早的版本,是以后各本的祖本;其二,它对人情世态的描写最为生动,人物现形象也最为圆整。
词话是一种可以讲唱的小说,里面有大量韵文,像《三国演义》开篇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就被认为是词话的遗留痕迹。《金瓶梅》中的词话痕迹更强:开篇先有“词曰”四段,说的是归乡退隐的闲适,“茅舍清幽,野花绣地”,“且优游,且随分,且开怀”;接下来又有《四贪词》,依次解析“酒色财气”对性命的戕害,皆从贪欲上落笔;再下来在第一回,又用一首词开始,该词出自宋人卓田,标名《题苏小楼》,本为哀婉佳人薄命,却扯到了汉高祖刘邦和楚霸王项羽身上,不是讲他们的盖世功业,而是说像他俩这样的一代英豪,都因为一个女子而英雄气短。作者用了四个字,叫“豪杰都休”,也就是俗谚所说的“英雄难过美人关”。此乃作者的历史拼接,也是一种大手笔,在潘金莲登场之前,先让虞姬和戚姬做一个简短铺垫。尤其是戚姬,已经贵为皇妃,仍处心积虑为儿子赵王如意争夺皇位,最后死得极其凄惨。作者遥遥设墨,以西汉初年帝妃之恋的悲情故事,将人性的贪欲之害铺展开来,为后世的女性,也为本书女性之命运作一引子。
明代的小说高度繁荣,出版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一批杰作。但很少有一部书能达到《金瓶梅》之深刻厚重,形象鲜活,刺世警世,勾魂摄魄,一经流传就吸引着一代一代的读者。鲁迅先生曾说自从有了《红楼梦》,一切传统的写法全都打破了,前移两百年以论《金瓶梅》,似乎更允当。毛泽东主席一向提倡读书,曾要求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阅读《红楼梦》,而且要读五遍;也讲过应该读一读《金瓶梅》。他说《金瓶梅》写的是真正的明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的残酷本质,描写了统治者和被压迫者的矛盾,有的章节写得很细致。他还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4]读《红楼梦》,从中的确可以看出《金瓶梅》的影响,两书颇多可供联想和比较之处,比如李瓶儿的出丧和秦可卿的出丧,确实有很多近似和相通之处,但是由于家族的层级不同、人物的身份差异,区别也很明显。
鲁迅先生论《金瓶梅》,有八个字最为精警,即“描写世情,尽其情伪”。这个“伪”,就是“虚情假意”的意思,穿越人间世相那种表面上的温馨热络,点出其最本质的内涵。[5]兰陵笑笑生在书中大写声色犬马,文字却透着一副从容冷峻,在不动声色的叙写中,嘲讽世人和市井,嘲讽那些虚情假意和万丈红尘。那是明代人的生活,是他们的生命的悲哀。或者有很多也是今人的生活,是我们今天的生命的悲哀。数百年过去了,人性的贪欲,仍是人类远不能摆脱的精神痼疾,而《金瓶梅》致力于揭示的,正是贪欲之恶,以及造恶者的自我毁灭。
回顾《金瓶梅》的传播史,可以说是一部充满着争议争论的学术史,污名与正名,痛责与赞美,禁毁与珍藏……皆在其中,该书的强大生命力也由此显现。很喜欢东吴弄珠客在卷首小序中的一段话,曰:
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
是啊,《金瓶梅》就在那里,斯人斯情就在那里,怎么读则是你自己的事。东吴弄珠客为读者预设了阅读的四重境界,其实区别甚难,就一个人而言,可能会“四心”具足,也会因年龄阅历的增长而变化;而领悟越深,越是会从心底涌出一种浓重的悲悯,包括芸芸众生,也包括西门庆、潘金莲、陈经济、春梅等恶人丑类。
这才是《金瓶梅》的传世密码,也是它的价值和意义。
注释:
① 王笃,字实夫,号宝珊,道光六年丙戌科二甲进士,担任过广东粮道和山东布政使。他是王杰次子垿时的的第二个儿子,有《两竿竹室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