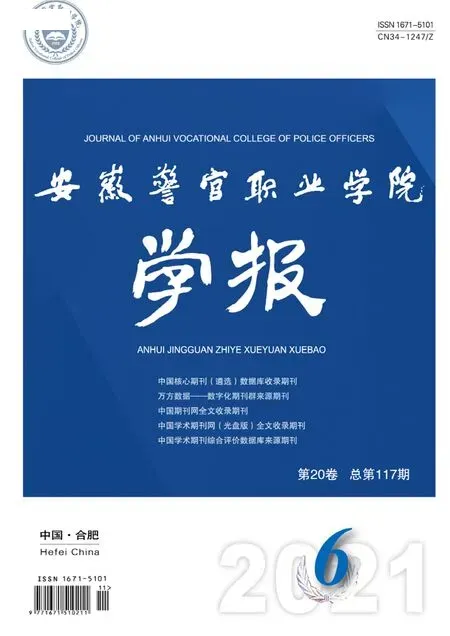网络领域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侦查对策研究
叶 静
(安徽公安教育研究院,安徽 合肥 230031)
一、当前背景
根据2020年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国信息网络技术的门槛逐步降低,互联网普及率逐年上升,网民规模日益扩大。网络购物、网络支付、网络视频、网络直播、在线教育、在线医疗、在线政务等网络业务发展如火如荼。面对庞大的网络红利,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不断滋生蔓延,整体趋势活跃多发,组织成员众多,破坏力成倍增加,并且有向黑社会犯罪愈演愈烈的势头,严重破坏了网络空间和现实生活。总体上,传统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向网络空间延伸,信息网络成为扫黑除恶的新阵地。2021年,在前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基础上,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持续推进。同时,随着《民法典》《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法律的颁布实施,网络领域的法律规定不断细化,网络涉黑犯罪成为信息时代理论和实务讨论的新课题。
二、网络领域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样态
打击网络领域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前提是厘清网络黑产犯罪。网络犯罪是指针对信息网络实施的犯罪,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犯罪,以及其他上下游关联犯罪。①2021年,最高检发布《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规定》,其中第二条明确界定了网络犯罪。网络黑产犯罪实质上是以网络信息技术和系统为行为手段或者侵害对象而形成的犯罪产业链。上游负责提供各种网络黑产资源、中游负责开发定制网络黑产工具、下游负责将网络黑产成果交易变现。[1]根据形成方式不同,网络黑产犯罪可分为原生型和嫁接型。原生型网络黑产犯罪是指直接源于互联网服务技术而产生的犯罪,例如AI类网络黑产犯罪、区块链类网络黑产犯罪;嫁接型网络黑产犯罪是指传统黑色产业与互联网服务技术结合而形成的犯罪,例如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网络敲诈勒索。
网络领域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属于网络黑产犯罪之一,实现了“互联网+涉黑”的融合,既搭上信息技术的快车道,又保留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质,形成完整的网络涉黑产业链。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核心是“控制”,这是与其他普通犯罪区分的关键。网络涉黑犯罪相当于线下涉黑犯罪在线上的运作,那么其本质依然是有组织犯罪。根据网络黑产犯罪的分类,网络领域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同样应当区分“涉黑犯罪的网络化”和“网络化的涉黑犯罪”。[2]前者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利用网络实施传统涉黑犯罪,后者则是基于网络生态环境下滋生的新型涉黑犯罪。
目前,网络领域涉黑犯罪主要表现为“涉黑犯罪的网络化”。网络“套路贷”“裸聊”敲诈、恶意索赔、负面舆情敲诈、网络水军滋事、网络暴力传销、网络“软暴力”催收,这些成为公安机关打击的重点方向。具体样态有以下几类:利用信息网络威胁他人,强迫交易;利用信息网络威胁、要挟他人,索取公私财物;利用网络辱骂、恐吓他人或编造、散布虚假信息破坏社会秩序或公共秩序、寻衅滋事;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黄赌毒”、暴力传销、套路贷、非法讨债。与此同时,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更迭,基于网络技术和服务产生更多的新型涉黑组织,“网络化的涉黑犯罪”成为新样态。物联网、区块链、无人驾驶、大数据、云计算,这些最强劲的“风口”,在涉黑组织眼中无非都是“入口”。例如,涉黑组织根据网络生态规则,利用流量劫持、恶意网站、木马病毒、黑客渗透等方式,称霸网络空间,实现非法控制,谋求经济利益。
三、网络领域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认定特征
网络领域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不仅具有网络黑产犯罪的个性特征,而且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共性特征。虽然网络涉黑犯罪有着与线下涉黑犯罪不同的特点,但是两者之间共性大于个性,最终的落脚点在于有组织犯罪。因此,从有组织犯罪的角度,认定网络领域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时,仍然应当依照刑法规定的四大基本特征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分析相互间的内在联系,依法予以认定。
(一)犯罪组织严密化
与普通犯罪不同,黑社会性质组织层级分明,核心成员基本稳定,纪律约束严明。[3]现有案例显示,网络涉黑犯罪呈现出明显公司化运作的特征。
第一,组织成员众多。网络空间是虚拟的数字世界,弱化了时间与空间的影响。基于互联网的高度开放性与交换性,网络涉黑犯罪的参与成员人数更多。黑社会性质组织之所以能称霸一方,与其规模密切相关,一个独立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至少有十人①2015年《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具有一定规模,人数较多,组织成员一般应在10人以上。”,多则数百上千,甚至上万人。如果成员零零散散,就不能形成长期存续的组织,无法实现垄断地位。第二,组织结构紧密。黑社会性质组织结构基本固定,形成组织领导者→重要成员→普通成员的金字塔式结构,呈现出垂直权力层级。内部管理极其严苛,存在组织纪律或者活动规约,上层成员拥有绝对控制权。与传统的组织方式不同,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涉黑成员之间一般通过即时通讯工具、通讯群组、电子邮件、网盘等信息网络方式联络。②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18〕1号)。通常,网络涉黑组织以合法公司为幌子,以“公司化运营”形式实施管理,有组织有目的地从事网络涉黑业务,并制定严厉的奖惩制度约束成员。
(二)目标经济利益化
攫取经济利益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最终目标,经济实力更是支持其发展壮大的基础。[4]放眼全球,网络黑产总体规模极为庞大,涉及的经济总量也颇为巨大。到2021年,互联网黑灰产将给全球造成高达6万亿美元的损失。③来源于世界经济论坛在《2020年全球风险报告》中发布的数据。网络空间已成为涉黑组织争夺的重要地盘。
在发展初始阶段,传统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通过开设赌场、敲诈勒索、贩卖毒品、组织卖淫等方式完成资本积累。在具备一定资金实力阶段,黑社会性质组织多以犯罪所得进行所谓投资,进一步聚敛财富。无论其财产是通过非法手段还是合法方式获取,只要将其中部分或全部用于违法犯罪活动或者维系犯罪组织的生存、发展,即可体现目标经济利益化。④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法发〔2009〕382号)。虽然涉黑组织入侵网络领域大肆从事犯罪勾当,但是其攫取经济利益的目标始终未变。例如,典型的网络“套路贷”涉黑犯罪,借助网络平台设立皮包公司,以民间借贷为幌子,招募成员从事网络放贷业务,通过恶意虚增债务或制造高额违约金,胁迫被害人及其特定关系人,非法侵占公私财物,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三)手段软暴力化
传统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般以暴力犯罪手段为主,手段凶残,危害性极大。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涉黑犯罪则是以新兴非暴力犯罪行为①《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18〕1号)规定:以组织的势力、影响和犯罪能力为依托,以暴力、威胁的现实可能性为基础,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或者影响正常生产、工作、生活的手段,属于《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五款第(三)项中的“其他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所谓的“谈判”“协商”“调解”以及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手段。作为重要犯罪手段。总体上,网络领域涉黑犯罪实现了“硬暴力”向“软暴力”的转化。
由于网络空间的虚拟性,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无法使用各种刀具、枪械、爆炸物,实施绑架、抢劫、杀人等各种严重暴力犯罪,更多的选择使用“软暴力”。“软暴力”主要表现为以滋扰、纠缠、哄闹等方式取代直接的物理暴力加害,使他人产生心理恐惧或者形成心理强制,影响正常生活和工作的精神暴力手段。②来源于《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18〕1号)。“软暴力”表面上比较温和,但造成的伤害却是现实存在的,对被害人影响深远。[5]因此,从侵害法益的角度考量,“软暴力”与“硬暴力”实际上具有同质性,完全可以将“软暴力”纳入暴力的范畴。[6]例如典型的网络“裸聊”敲诈,涉黑组织以“裸聊”引诱被害人下载安装木马APP,诱使被害人露出隐私部位并录制视频,以在网络直播平台、微信朋友圈等曝光隐私,或将不雅视频发送至被害人亲友为要挟索取公私财物,导致被害人精神受到严重伤害,破坏社会公共秩序。
(四)作案集中化
传统黑社会性质组织集中于特定行业或者区域,划定势力范围,形成绝对垄断优势,具有强大独占性。当前,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涉黑犯罪更多集中在网络新兴行业和特定网络工具。
在网络新兴行业,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搭建钓鱼网站和制作木马程序,垄断网络金融、网络视频、网络电商等领域,打压妨害其他竞争者,形成绝对霸主地位,误导与危害社会公众。例如,典型的网络负面舆情涉黑案件,俗称“网络黑公关”。网络涉黑组织依照客户指令,密集发布负面信息,组织水军进行炒作,恶意诋毁竞争对手,劫持公众舆论,损害竞争对手商业信誉与商品声誉,侵害社会价值体系。与此同时,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犯罪集中于特定的网络工具。常见计算机犯罪工具有多种,如活动天窗、特洛伊木马、数据欺骗、计算机病毒等。互联网应用产品若自身存在漏洞或缺陷,往往会被犯罪分子传播放大,并利用到网络涉黑犯罪中。网络黑色产业链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制售流量攻击工具,攻击效果远远超过传统攻击。通常,门户网站、应用软件、接码平台、注册账号、网上群组,成为网络涉黑犯罪的重灾区。
四、网络领域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侦查对策
互联网虽然属于虚拟空间,但是活跃其中的依然是现实世界中的人,所以仍然属于法治社会的范畴。即便存在技术防范手段,法律规制仍然必不可少,两者之间是并行不悖的方案设计。对于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涉黑犯罪,不能让其大行其道,而是应当加强管控和打击。与以往线下涉黑犯罪不同,网络涉黑犯罪具有作案远程化、涉案范围广、犯罪成本低、取证难度大等特点。[7]只有建立新思维和新策略,综合运用各种侦查对策,才能彻底斩断网络涉黑犯罪产业链。
(一)加强涉黑情报工作,依托信息技术挖掘犯罪线索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日益更新的信息技术带来海量信息资源,为公安工作提供了新的工作思路。对于隐蔽性极强的网络涉黑犯罪而言,涉黑情报工作的质量直接影响案件的后续侦查。
1.广辟情报信息来源。一方面,群众是情报的主要来源,争取群众支持是扫黑取得胜利的关键。公安机关可将传统传媒与新兴传媒相结合,充分宣传打击网络涉黑犯罪的有效战果、法律法规、举报方法及奖励政策,鼓励群众挺身而出积极检举揭发,特别是提升学生、老年人等易感群体的风险识别和防范能力。另一方面,涉黑情报的重要渠道是刑事特情,建设特情可以高效获取涉黑组织内部的重要情报。网络涉黑犯罪隐蔽性极强,建设刑事特情具有操作空间。根据IT行业的规定,黑客主要分为“黑帽子”和“白帽子”两类。其中,利用网络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黑客称之为“黑帽子”,而帮助维护网络安全的黑客则是“白帽子”。因此,在熟悉黑客群体的前提下,在白帽子黑客群体中建立刑事特情,可以明确网络涉黑犯罪的发展动态,提前发现预谋犯罪线索,为后续侦查提供技术支持。
2.建立扫黑情报网络。一方面,公安机关对接其他部门形成横向合作网络。加强与文体、网信、工信、金融、市场监管、互联网企业等部门的业务合作,建立数据信息的收集与共享机制,掌握该类犯罪的发展动向和变化趋势。具体来说,针对非法“养号”交易、搭建非法网站、开发销售非法软件等问题,公安机关联合行业主管部门建立网络安全防护网,通过情报及时预警处置,堵塞风险漏洞。另一方面,公安机关开发各类平台系统形成纵向监测网络。借助信息技术,建立智能化扫黑平台,运用数据摸排的方式,拓宽涉黑犯罪线索的收集渠道。例如,在全国搭建“套路贷”犯罪监测预警平台、“裸聊”敲诈勒索案件串并系统,实时监测网络涉黑犯罪趋势。通过扫黑平台对汇总线索综合研判,精准打击涉黑犯罪的重点目标,有效提升整体侦查效能。
(二)运用秘密侦查手段,深入调查搜集证据
网络涉黑犯罪依托网络技术,犯罪成本更低,犯罪手段日趋智能化,犯罪规模迅速扩张,侦查难度愈发加大,普通侦查手段不足以应对。当普通侦查手段难以取得突破,无法获取关键证据时,秘密侦查手段则成为更优选择。
1.开展内线侦查,查清犯罪内幕。网络涉黑成员一般通过假冒他人身份、设置动态网址、搭建境外服务器、利用虚拟币交易、设计复杂加密算法等方式,隐藏身份、逃避打击。网络涉黑组织犯罪手段的远程化,为开展内线侦查提供了可能。如果开展内线侦查,侦查人员需要借助网络平台和技术,在虚构网址、账号、身份的掩护下,打入犯罪成员经常混迹的论坛、QQ群、微信群内部。在潜伏一段时间后,取得组织成员的信任,获取聊天记录、交易记录等电子证据,彻底查清结构层级、涉案账号、作案方式等重要信息。在此过程中,内线侦查人员需要严格保密,加强自身的保护,防止涉黑组织的反扑与报复。
2.运用技术侦查,获取犯罪证据。由于涉黑犯罪的复杂性,公安机关在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时,可以使用技术侦查措施。技术侦查可以更高效地确定侦查方向和范围,实现精准打击。针对网络涉黑犯罪的特点,公安技侦部门应及时采取技术手段,对账号买卖、违法犯罪网站、非法软件、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等问题重点侦查,深度挖掘网络涉黑犯罪的新特点,查明势力范围、成员结构、犯罪方式。例如,网络涉黑组织通常依赖“黑卡、黑号、黑设备、黑软件”从事犯罪活动。因此,以上述为侦查范围,追踪为犯罪分子提供推广、技术、账号、平台等源头性软硬件设备和服务的行为,开展全链打击。。
(三)全力追捕组织成员,全面追缴“黑财”
网络涉黑组织人员众多,扩散能力强,倘若不将主要组织成员如组织者、领导者、骨干分子全部抓捕到案,就会造成更严重的法益侵害。同时,全面追缴“黑财”,切断网络涉黑组织的资金来源,才能从经济上彻底击垮涉黑组织。
1.全力追捕犯罪嫌疑人。网络涉黑组织成员一般具有较强的网络技术能力,反侦查意识明显。敌暗我明,追捕的难度比普通犯罪更大。为确保抓捕工作顺利进行,必须先根据多方线索追查,揪出涉黑组织的重要成员,然后再跟进深挖其他犯罪成员。在此过程中,需要各地公安机关的通力配合,才能实施统一行动实施抓捕。对于外逃藏匿成员,可充分发挥“科技+传统”的优势互补,以传统排查为基础,以刑事技术为突破,持续收网抓捕,直至将涉黑在逃人员追捕到案。
2.全面追缴“黑财”。网络涉黑犯罪交易变现快,受害人众多,涉案金额巨大,追缴“黑财”势在必行。打击网络涉黑犯罪的关键在于控制网络货币的恣意流通、紧盯网络犯罪的资金流向和通道转变,重点侦查大量购买空壳公司、批量注册第三方账户等异常行为。一方面,公安机关需要与人民银行、证监、税务部门共同建立查控平台,运用查封、搜查、冻结等方式彻查“黑财”的性质与范围,增强打击黑财的合力。另一方面,公安机关需要对涉案财物要严格审计评估,准确把握“黑财”认定范围,做好甄别与核查工作,确保查控无死角。同时,应当注意依法规范涉案财物处置,明确区分“黑财”与合法财产,避免扩大打击面,保护合法财产,保障合法经营。
(四)开展国际和区际警务协作,建立扫黑全球化体系
网络涉黑犯罪具有跨国性与跨境性,打击此类犯罪最大的挑战是归因难,网络的全球化发展让调查变得更加困难。因此,惩治跨国性跨境性的网络涉黑犯罪,单方面的努力是不够的,更需注重国际法与国内法的配合,更需加强国际与区际的警务合作。
1.加强国际警务协作。打击有组织犯罪,离不开多层次、全领域的国际警务协作。网络涉黑犯罪本质上属于有组织犯罪,显然适用这一国际准则。鉴于网络的无国界性,有的涉黑犯罪主体藏匿于境外,利用境外服务器在境内实施网络犯罪;有的涉黑犯罪主体在境外利用虚拟货币变现通过网络涉黑犯罪获取的“黑财”,试图逃避警方打击。由于司法体系、工作机制、语言文化的不同,侦查人员在当地推进工作异常艰难。对此,各国需要注重涉黑犯罪情报共享、打击非法加密货币、缉捕遣返犯罪分子等各种形式的合作。例如,东南亚地区是网络犯罪的重灾区。在中国和柬埔寨执法合作框架下,两国警方密切协作,集中打击网络涉黑等突出犯罪,组织力量捣毁一大批网络赌博、网络诈骗、网络色情、网络敲诈勒索窝点,共同对抗跨国涉黑犯罪,成为国际警务合作的成功范例。
2.加强区际警务协作。网络涉黑犯罪属于非接触犯罪,时空跨度大,基本都是跨区域有组织作案。由于互联网经济更为发达,网络涉黑犯罪在珠三角、长三角、港澳台地区肆意扩张。在境外黑社会的影响下,这些地区的涉黑组织利用网络平台招募马仔,不断更新犯罪手段,不断扩大犯罪影响,侵蚀互联网秩序。因此,公安部门应当建立区际警务协作关系,共享情报信息、实现个案合作、组织联合行动,将网络诈骗、网络传销、网络敲诈勒索等新型跨境网络涉黑犯罪纳入联合打击范畴,最终形成优势互补和快捷高效的警务利益共同体。例如,广东省公安厅联合港澳警方设置联合打击有组织犯罪工作室,通力协作开展联合打击行动。在扫黑区际合作方面,粤港澳三方合作取得了明显实效,成功侦破了一批跨境涉黑犯罪案件。
五、结语
国内外犯罪形势仍然错综多变,叠加疫情的冲击和影响,网络领域成为犯罪分子的新选择。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信息网络相结合,活跃多发态势不减,呈现出各种新动向。实践中,认定网络领域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存在诸多取证难点和法律适用难题。公安部门需发挥信息技术优势,转换应对思维,将此类犯罪消灭在初始阶段,防止其演变成更为严重的黑社会犯罪。总之,无论涉黑犯罪发生在网络领域还是现实空间,只要存在就必须精准打击,彻底清除,避免扫黑斗争的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