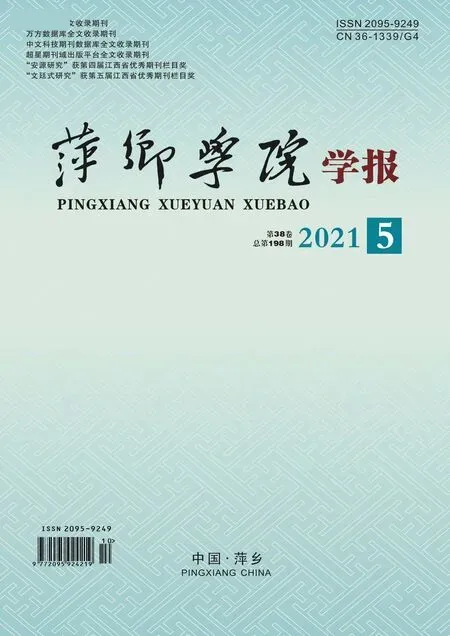不同场域中女性命运的诠释——评《四个四十岁的女人》
孙海龙,罗淑容
不同场域中女性命运的诠释——评《四个四十岁的女人》
孙海龙,罗淑容
(萍乡学院 人文与传媒学院,江西 萍乡 337000)
小说《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将四个作为时代新进入者身份的女性,放置在充满新旧观念冲突的家庭和社会场域里演绎人生命运。她们最终要么像蔡淑华和魏玲玲一样臣服于固有力量的支配,选择做一位贤妻良母;要么如钱叶芸誓与传统势力决裂,不惜付出身败名裂的代价。作为四个人“圆心儿”的柳青,选择了游离于家庭、婚恋等传统场域之外的美的场域。美的场域里冲突力量之间关系相对松散,鼓励个体自由追求人生价值,柳青最终实现了自己诗意性的人生价值。
《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场域;命运;诠释
胡辛小说《四个四十岁的女人》①以20世纪80年代为创作背景,塑造了“憨大姐”蔡淑华、“布谷鸟”钱叶芸、“百灵儿”魏玲玲和“嫩叶子”柳青四个女性形象,以四人阔别二十年后偶然重逢作为故事的切入点。四人利用儿时扔纽扣的小游戏,随机轮转,轮到谁,谁就要根据纽扣的正反面来决定讲述自己二十年里发生的喜悦或者悲伤的生活经历。四个“人到中年万事休”的女性在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时,发现即便在可以自由选择人生的年代里,每个人也无非是围绕着事业、家庭、理想、奋斗、爱情和婚姻像扣子一样“轮轮转”。蔡淑华、钱叶芸、魏玲玲三位女性的人生经历揭示出女性无论如何挣扎也难逃家庭、社会等场域规训的命运,唯有像柳青一样沉浸在美的场域中才能体验到诗意人生。
场域类似磁场,是人活动的所有区域,既包括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也包括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架”[1]。“整个社会是一个‘大场域’,而高度分化的‘社会小场域’就是‘子场域’”[2]。每一个场域中都有一种无形的活动规则与意识体系,这种规则意识会塑造场域中行动者的习性,熏陶他的观物意识。“行动者一旦进入某个场域,必须表现出与该场域相符合的行为,顺应场域中的‘游戏规则’”[3]。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大场域”的话,那么家庭、婚恋和个人审美追求形成的美的场域则是不同的“子场域”。家庭、社会场域内部行动者为了占有资本都会形成冲突的关系。新进入者会处处受到场域内保守的规则意识的施压,直至塑造成该场域内普遍期望的样子。
一、家庭场域中的贤妻良母
家庭是伴随每个人一生的活动场域。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在中国的家庭生活中,人们普遍接受的是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工,对女人的要求是做一个贤妻良母,久而久之这一观念就变成了家庭场域内稳定的规则意识。现代女性一直在寻求自我独立,这与家庭场域内的规则意识构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无论是五四时期鲁迅的《伤逝》、凌淑华的《女人》、白薇的《悲剧生涯》,还是20世纪80年代张辛欣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王安忆的《锦绣谷之恋》和《弟兄们》、张洁的《方舟》等作品,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矛盾的描写。矛盾的解决要么是女性离家出走,要么是通过“雄化”身份过着男人一样的生活,要么凭借姐妹情谊构成合力与男性竞争。作品中的蔡淑华和魏玲玲也遇到了这样的矛盾,不同的是她们并没有采取与传统家庭彻底决裂的方式来解决,而是慢慢接受了现实,顺从了家庭场域规则意识的规训。这是一种更为接近现实的结局,或者说是从一个更为现实的角度回答了鲁迅“娜拉走后”的问题。当四个人相遇时,大家公认蔡淑华是“上有公婆,下有儿女、夫唱妇随,你可算得上‘全福人’呵。”这里的“全福人”指的是老人健在,儿女双全,丈夫有不错的工作,家庭生活幸福美满。这样的家庭生活,自然让钱叶芸、魏玲玲和柳青三个人羡慕不已。不过,当听了淑华的自我描述后,我们发现这位“全福人”的身份,是她二十年来不断地做出让步换来的,或者说这个身份只属于贤妻良母的女人。婚后的她,曾经很热爱自己的事业,做一名热心的妇联干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发现“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即丈夫和孩子对她工作的不理解。孩子们埋怨她关心不够,认为她是不称职的母亲。丈夫认为她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到别人家的事情上,认为她的工作根本不值得一提。为此,她与丈夫大吵过,还一度认为“我不相信,非得做一个不合格的妇联干部才配做及格的姆妈。”这是个体对家庭场域内规则意识的反抗,可惜的是家庭场域规则意识的力量过于强大,她不得不妥协,选择成为一个“业余时间把家务事全包了”的姆妈。通过这一“资本”的置换,她最终才使自己成为一名“全福人”。蔡淑华在短暂的挣扎后,没有选择持续的反抗,反而认为“我是憨人有憨福”,从内心深处接受了被塑造后的“贤妻良母”形象。
魏玲玲形象比蔡淑华更具有反抗意识,但是二人殊途同归。年轻时候的魏玲玲曾梦想自己能成为第二个林巧稚,抱着终身不婚的打算。她曾是一名出色的助产士,被老表们“大鸣大放”过,可是在三十岁的时候却步入了婚姻家庭。虽然她知道“为丈夫和子女做出牺牲,是可贵的,但不能算崇高的。因为这种爱,尚未跳出一个小家。”她也曾发出过疑问:“难道女人追求的目标仅仅是做贤妻良母吗?”但是,结婚后,她还是被家庭场域内的规则意识所驯服,为了丈夫和儿子,改了行,把所有精力“一门心思放在丈夫的冷暖营养和当好儿子的‘家庭教师’上。”
正如小说开篇所说“她们毕竟是世俗之人,话题很快转到百分之九十九的女人们的中心要旨——孩子和丈夫上来。”这就是家庭场域的强大力量,一旦女性迈进婚姻家庭的场域,就会慢慢被塑造成该场域所希望的形象。
二、婚恋场域里的“正经女人”
按照布尔迪厄的论述,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员,每个人都要在不同的时空里选择处于某一个场域。无论你选择何种场域,你要么选择被该场域的规则意识所驯服,接受被期待的形象;要么选择与此抗争到底,拒绝被该场域打造。可是一旦你选择后者,就不但会被当下场域驱离,而且会继续受到它反向力的施压。钱叶芸一直站在家庭场域规则意识的对立面,导致她婚姻生活的不断失败。她像“一片落叶飘零,像一朵浮云游移”。钱叶芸只是渴望自己在家庭婚姻中,可以保持事业的独立和爱情的纯粹,可这与家庭场域中规则意识要打造的贤妻良母形象相背离。当她不堪忍受婚恋场域内规则意识的强大施压后,她选择了走出家门迈入社会。
早年的钱叶芸是剧团的二牌花旦,事业红红火火,坚信艺术家的青春不能耗费在十月怀胎中,崇尚不早婚。但是,后来她遇到了比自己大两岁的校友小孙,很快“丘比特”的箭射中她和小孙的心。两人情投意合,相处一段时间后,在小孙发誓结婚后可以暂时不生孩子的前提下,她答应了跟他结婚。婚后没多久,她就不断面对来自婆婆逼迫她生孩子的压力。婆婆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对家庭场域内的规则坚信不疑。她自然地认为女人结婚就要传宗接代,时时含沙射影地讽刺她,“养了只鸡婆不下蛋呀!我独门独苗的要断香火啦。”面对压力,钱叶芸开始选择了妥协,同意为丈夫生孩子,但是她知道这是自己暂时的让步,所以给第一个孩子起名为让让。因为第一个孩子是女孩,所以她又不得不被要求再生一个。在接连生了两个女孩后,曾经信誓旦旦答应尊重叶芸自我选择的丈夫小孙,也站在了婆婆这一边,认为“女孩子不是崽”。他不断劝说叶芸再生一个,直到生了男孩子为止。最后引爆了叶芸内心的反抗,她将第二个女孩子起名为婷婷,谐音停停,就可以看出她已经下定决心不再继续生孩子了。我行我素的叶芸,背着丈夫和婆婆偷偷做了节育手术。丈夫和婆婆知道这个事后,家里就像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全都炸了锅。随着家庭矛盾的不断升级,来自婚恋场域的反向力也开始向钱叶芸袭来。好事者说她心术不正、作风腐败,丈夫小孙也不再信任她,二人选择了离婚。家庭的破裂,让钱叶芸走向了社会,婚恋场域内的规则意识通过人言的反向力不断对其进行塑造。在当时人的婚恋观念中离婚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一旦婚姻生活失败,责任一定在女人。风言风语不断向叶芸袭来,婆婆到处说她是狐狸精,说她是“女到三十的老妈妈”是没人要的女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和实力,钱叶芸选择了闪婚嫁给了剧团的化肥大哥,可婚后不到一年,就遭到了丈夫的家暴。她再一次选择离婚,离开家庭。家庭场域中的反向力和婚恋场域里的规则意识不断对其进行建构,她这一次离婚失去了“女人最宝贵的东西——名声”。在世人眼里她是“狐狸精”,还要不断受到“清白女人鄙薄的斜视,高贵女人冷峻的搜索,好事女人的编造,善良女人的怜悯”和“正派男人的躲避,轻狂浪子的挑逗”。最终她选择嫁给一位退休老干部,本以为这样可以逃离原来的工作环境,摆脱那些绯言绯语。可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由于二人年龄差距过大,结婚当天,老干部的儿女合寄来了四字“贺信”——“狗尾续貂”来嘲讽和挖苦她。叶芸最后总结道:“自己是一次出嫁,两次改嫁,讲时髦一点,也就是三次结婚、两次离婚。”这样的经历无论是在刚刚兴起新思潮的20世纪的80年代,还是在婚姻已经很自由的今天,都足以让人唏嘘不已。其实她只是不想过传统两性婚恋观中所谓的“正经女人”般的生活。即女人一旦步入婚姻生活就要放弃自己的事业,依附男人,成为传宗接代的机器。她拼命逃离不适的婚恋生活的物质禁锢,却逃不掉婚恋场域反向力的精神规训的束缚。最终自己失去了喜欢的事业,丢了名声,成了大多数人眼里的“不良妇女”。类似的描写我们可以在同时期张洁的小说《方舟》中看到,不同的是《方舟》中的三位女性(梁倩、荆华、柳泉)通过“雄化”的身份理想化地实现了“方舟并骛,俯仰极乐”[4]的人生。而作品的叶芸依然保持着女性身份,承受着社会场域里的规则意识的不断施压。即使她清醒地认识到“听说古代把妻子比作衣裳,我看,妇女解放嚷了一个世纪,也不过由男人的汗衫衬衣上升到两用衫、大衣之类罢了”。
婚姻的失败导致叶芸走出家门,却无意间跌进被“人言”织就的社会漩涡。在那个时代,社会上人们普遍接受的婚恋观点是:离婚的女人是不正经的女人。正如钱叶芸自己所说“在世人眼中,我不过是一个轻薄下贱、水性杨花的女人,有谁知我正是为了追求做一个真正的女人才如此身败名裂呢?”难道女人真的无法“拥有自己的节日”,不能做真正的自己吗?并不是这样,作家站在女性的立场上为女性设计出了一条可以实现自我的崇高之路,那就是小说中柳青走的路。
三、美的场域里的诗性体验者
一个人的活动不仅受家庭、社会、学校等物质空间场域的影响,也会受美的场域的精神空间影响。所谓美的场域是指“社会文化时空中制约社会审美变化的氛围”[5]。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呈现给人们的是一个开放与民主、平等与自由、个性与独立并存的社会文化时空,这种文化时空影响下的美的场域与家庭和社会场域不同,内部的冲突力量相对松散。它鼓励场域内的成员实现自我,追求个性,超越一己私利的追求。柳青就是在美场域内演绎出自己与众不同的人生价值。她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参加工作没多久又失去了母亲,没有兄弟姐妹,终身未嫁、无儿无女,一直处于家庭场域之外。
柳青从小就有超越精神,年轻时候曾充满锐气地说:“我就不信,女的超不过男的?”这种不服输的向上精神就是一种美的精神,时刻鞭策她不断超越自己,致使每次考试她都能拿到第一名的好成绩。她曾经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但是由于大学读的是师范专业,毕业后就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投身农村建设,她选择去大山里支教,做一名乡村女教师。在支教过程中,她爱上了一位一起支医的医科大学生。不幸的是这位大学生在一次抢救病人的过程中,失足落崖而牺牲。二人在超越自我、奉献他人方面情投意合。大学生去世后,柳青精神里把这种一己的男女情爱不断放大,正如她自己说的“是他的对人民博大深沉的爱激发了我,是他对事业不屈不挠的爱振奋了我!”她甘愿“默默无闻”在农村支教十五年,最后在得知自己身患乳腺方面的绝症时,她依然能坦然面对,说每个人最后“终须一个土馒头”。她向大家淡定而平静地吟诵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5]来表达自己面对生死时的淡然自若。因为她虽然失去了一些普通人整日沉陷其中乐此不疲追求着的小我之爱,却得到了更为博大崇高的爱的馈赠。当柳青要离开自己支教的农村到大城市去治疗疾病时,她看到了为她送别的盛大场面。校长带着连夜赶了四五十里山路的学生向她送别,本是农忙时节,村民们不惜放下手中的活,来了“黑压压的一片人”来送她。学生和家长把他们最珍贵的营养品——鸡蛋,全部拿出来塞进她包里,全汽车的人都在等她,不约而同把1号座位留给她。她深刻感受到“真的,我是幸福的,真正幸福的。真的。”她被当地人视为“文曲星”“顶梁柱”,当地人给予她“人世间最崇高,最纯贞的爱”。
美的场域内的规则意识一步步把柳青培植成为一名不断燃烧自己奉献他人的崇高者。所谓“崇高的本源始于超越常人的高度,它的转义则指向超越性,由于超越的过程伴随着对阻碍的克服,所以崇高的审美情感既有面对挑战的痛感,也有实现超越之后的愉悦”[7]。柳青正是这样一位不断克服人生中各种困苦与阻碍,最终感受到了崇高事业带给自己莫大的幸福感的女性。正是基于这一点,其他三位女性最后才一起向柳青说道“你永远是我们的圆心儿”。
社会生活中,我们每个人可以在不同的场域之间穿梭,可以超越单一场域的实体结构。但是我们无论怎么选择,都无法逃脱当下所处场域内的规则意识的无形强压和强势建构。大多数女人要么像小说中蔡淑华和魏玲玲那样,年轻时候曾经向所处场域内的规则意识发起过反抗,可最后依然是握手言和,乖乖做一名“贤妻良母”。要么向钱叶芸那样抗争到底,最后也只能是身败名裂。正如小说中所描绘的“闹市中喧嚣的声浪不可阻挡地阵阵涌来,何处的收录机开足了音量,贝多芬的交响乐《命运》在空中震荡。”作为女性作家,胡辛没有满足仅仅渲染女性的人生困境,这与同时期的《方舟》有别;也没有沉浸在女性身体的私欲描写,这又与铁凝的《无雨之城》、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和卫慧的《上海宝贝》迥然不同。如果说从五四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作家都围绕着“爱”来描写女性独立的话,那么我们在柳青身上则看到了不一样的表述。柳青不是像《伤逝》中子君那样一味地想成为男人爱的对象,也没有一味地沉浸在追问“你为什么爱我”(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珊珊的追问),而是要追求爱的本身。这种爱是一种心灵的满足,她更为享受的是对异性、对他人和对事业的“曾经爱过”的诗性体验。
我们虽然无法摆脱场域的规训,但我们有自由选择被何种规则意识规训的权利。正如柳青一样,可以选择一条成就本心的人生之路,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把她的选择看成是对孔子“吾与点也”[8]的现代注解。其实何止是女人,大多数人在四十岁后,回望自己人生路时,都会发现选择会对一个人的人生产生重要的影响。
①本文引用的原文均出自胡辛:《四个四十岁的女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1] 布迪厄, 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M]. 李猛, 李康, 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133-134.
[2] 毕天云. 布迪厄的“场域-惯习”论[J]. 学习探索, 2004(1): 32-35.
[3] 布尔迪厄,华康德. 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 李康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129-130.
[4] 费振纲, 胡双宝, 宗明华编. 全汉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316.
[5] 封孝伦. 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3: 317.
[6]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中国古代散文[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 268-269.
[7] 陈榕. 西方文论关键词:崇高[J].外国文学, 2016(6): 93-111.
[8] 钱穆. 论语新解[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2: 317.
Interpretation of Women’s Fate in Different Fields——Comments on
SUN Hai-long, LUO Shu-r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Media, Pingxiang University, Pingxiang Jiangxi 337000, China)
The noveldepicted the life story of four women of the new era who were set in the family and social field full of conflicts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new ideas. Among them, some submitted to the domination of traditional forces and chose to be a good wife and mother; like Cai Shuhua and Wei Lingling; some, like Qian Yeyun, spared no efforts to break with traditional forces even with the cost of all her reputation. Liu Qing, the “center of the four”, chose the field of beauty other than the traditional fields such as family and society. In the field of beau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licted forces was relatively loose, which encouraged individuals to pursue life value freely. Liu Qing finally realized her poetic life.
; field; fate; interpretation
2021-08-02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JC20210)
孙海龙(1984—),男,黑龙江大庆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学理论与批评、中国现当代文学。
I207.3
A
2095-9249(2021)05-0075-04
〔责任编校:吴侃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