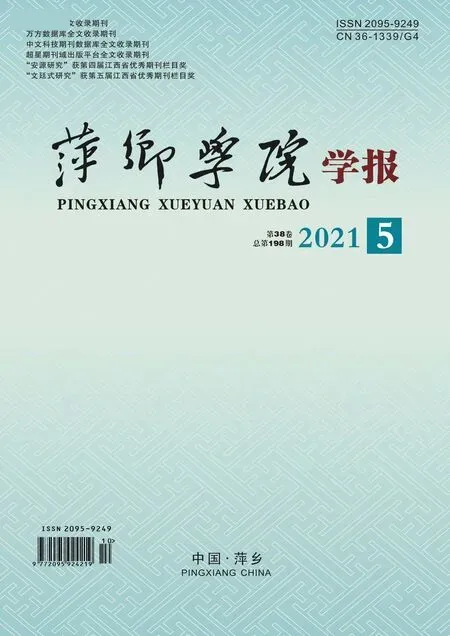三十年来明清佐杂官研究的基本态势
崔健健,施惠芳
三十年来明清佐杂官研究的基本态势
崔健健,施惠芳
(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目前学界关于明清佐杂官的研究,呈现出分歧较大、讨论激烈、蓬勃发展的基本态势。20世纪80年代末,其开始进入史学研究的视野,学界围绕行政体制、下沉分辖现象和区域化特征等,展开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讨论和探究,经过三十余年的努力,研究成果颇丰。特别是研究者以“次县级行政”观点为基本切入点和重要延伸点,通过群体宏观描述和个体微观探析的研究模式,考察了明清佐杂官的具体“政治行为”和“政务运作”,阐发了其与地方正印官的职权分配以及与“皇权不下县”政治格局的内在联系,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其在地理分布、权责分派等层面呈现出的明显的区域化特征。
明清;佐杂官;基层政治;综述
明清州县官作为地方行政长官,掌治一方的行政、司法、教育、征税、赈济诸权,是典型的“亲民之官”,有“民之父母”之称;其品秩、职掌、选拔、除授、考绩、升转、惩戒等情况,也长期受学界的关注,研究成果颇丰。而相较于知州、知县等正印官,由佐贰官、首领官、杂职官组成的佐杂官群体,因未被纳入州县主干行政系统,且相关文献资料稀缺的缘故,往往被学界所忽视[1]。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数量可观的档案、地方志、民间契约文书等原始史料陆续被发掘、整理,并应用到史学研究中来,一大批专家学者对明清县以下基层政治的运行状况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在此背景下,明清佐杂官开始全方位地进入史学研究的视野。
一、关于佐杂官行政体制的研究
解读古代职官史或者考察某一具体职官,其行政体制往往是第一出发点,也是研究工作的重中之重,明清佐杂官亦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末,明清佐杂官的行政体制问题开始纳入史学研究的范畴。刘子扬[2]、刘鹏九、王家恒、余诺奇[3]等对清代县佐贰、典史以及巡检、驿丞、闸官、税课司大使、县仓大使、河泊所官、医学、阴阳学、僧会司、道会司等一众杂职官的建制、品秩、职掌、升转、补授等情况进行了初步考察。后柏桦、张振国、吴大昕、吴吉远、那思陆、王兆辉等大批专家学者陆续参与到讨论中,经过四十余年的努力,已初步形成两种研究模式——对佐杂官群体的宏观描述和对某一佐杂官个体的微观探析。
学界对于明清佐杂官群体的宏观描述,主要集中于其建制、品秩、选拔、除授、职掌、社会影响等问题。在为数不多的关于佐杂官的专题性研究中,申立增[4]对清代佐贰杂职官的建制、选任、职掌、管理等作了系统考察。鞠枭磊[5]对清代州县佐杂官员惩戒的条文规定、基本类型和程序进行了全面考证,对其历史作用和不足之处作出了客观评价。张振国[6]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刊布的档案,就清代佐杂缺等级划分的原因、标准、等级类别、任用方式及变革,进行了探讨,并对政府普遍将佐杂缺划分为要缺和一般缺两个等级的合理性,给予了充分肯定。
此外,吴大昕对明初杂职官制度的研究,多有建树。其《明初的杂职官制度》一文认为,明初杂职官制度延续元制的特征十分明显,不仅具有独立于州县的衙署、隶属自身衙门的胥吏与户役、独立的会计单位,而且独立执行职务,并由中央机构进行考核[7]。其《明代杂职官员出身考论》一文指出,明初的杂职官与其他官员一样,经由举荐而来,差别仅在于品级,而非正途与异途的区分;后随着科举制的恢复,儒士逐步退出杂职官群体,杂职官的出身由荐举逐渐转为吏员,形成了杂职官与吏出身者逐渐混同的情况[8]。柏桦关注的重点在于明清佐杂官具体的“政治行为”和“政务运作”。其《明清时期府县官政治行为之考察》一文通过考察明清府县正佐监督与正官负责机制,发现明初佐貳官与正官分庭抗礼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正佐监督机制也得以发挥功效,永乐以后府县政务逐渐以正官为中心,佐貳官则成为闲员[9]。柏桦与李静合撰的《明清时期府县官对下政务运作》一文,在考察地方档案、契约文书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考证了府县佐杂官参谒正印官时所遵循的礼仪规范[10]。织田万、吴吉远、那思陆、王兆辉、茆巍等学者就明清佐杂官的司法权问题,展开了讨论。织田万[11]、吴吉远[12]、那思陆[13]等坚持认为明清佐杂官参与了地方政府司法事务的多方面工作,具有一定的司法职能,但决断权在正印官手中。王兆辉、刘志松[14]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清代法律对州县佐贰官的司法权严加限定,但在实际治理中又采取了调和策略,导致佐贰官在勘验、缉捕、审断、执行等方面拥有不同程度的司法权。茆巍[15]则以命案与审理权的关系特征为出发点,通过大量的文献考证,发现清代佐杂逐渐获得命案的检验权,且配有仵作,其权限亦逐渐完整,从原来需印官覆验发展到直接由佐杂在验后填格取结即可,进而指出佐杂在州县之下发挥着一级审判机关的作用。
学界专家学者对于明清某一佐杂官个体的微观探析,主要表现为对其行政细节的深入解读和挖掘。其中,对于巡检的研究最为集中,成果也最为丰厚。川胜守[16]对明代江南巡检司运作的细节,以及佐杂官与水闸防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揭示。王伟凯[17]明确指出,明代的巡检司仅与里甲、老人相互配合,并不代辖村庄,主要职责是对流动人口进行全面的防控。胡恒[18]将巡检司视为最基层的国家行政机构之一,认为其在整个清代呈现波浪式的发展态势,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顺治、康熙朝为缩减期;雍正、乾隆朝为高速增长期;嘉庆以后趋于稳定期。又受人口、空间、区位、市镇、治安等因素影响,巡检司的空间分布极不平衡,呈现东密西疏、南密北疏的分布特征,与胡焕庸人口线相一致。李克勤[19]以清代广州府属众多巡检司为例,解读了其司署规制、皂役配置、官俸役食、巡检其任等基本情况,揭示了其维持治安、封建教化、地方赈济、听讼断狱、办理河务等主要职责。左平[20]以南部县衙档案为出发点,揭示了清代巡检因需而设、因需而裁移、实际职权大小与其驻守地点密切相关的特点。
而对于典史和州县长官根据辖区地理、交通、物产等情况所设驿丞、闸官、税课司大使、仓官、河泊所官,以及各县常设医学、僧会司、道会司等杂职官的研究,成果亦令人注目。如陈阳[21]以典史执掌的转变为切入点,对明清典史进行了考证,发现明中叶以后典史虽名为幕职文吏,但实掌县尉权柄,清代典史逐渐取代县尉一职,转而为执掌治安管捕的属官,即出现文武易帜的情形。于宝航[22]对明中后期驿丞群体的身份和心态进行了探究,认为驿丞虽然出身卑微、品秩低下,但对于政治系统的运行具有重要作用,这种矛盾的身份影响到他们的心态,造成明中后期驿递系统的种种弊病。于琪[23]对明清闸官的设置、历史沿革、职能及过闸人员作了初步考证,认为其作为运河基层管理组织中必不可少的官职,对运河的畅通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李龙潜[24]以“明初对商税的政策和市场管理”为引,具体考证了明代税课司、局的沿革,征收商税的税目、税则和征收商税制度的演变。周琳琳[26]以明代府州县仓官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仓官的具体职责以及基层社会影响,借此透视了明代府州县仓的运作特点[25]。马晓菲对明代僧官制度的内容、设置及演变等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明代官方设立的用以处理佛教事务的僧纲司、僧会司等机构,在事实上成为世俗官僚系统的一部分。狄鸿旭[27]结合地方志、档案等资料,对清代县级层面的医政机构医学署的职员编制、管理机构、实际运作、衰落情况、社会影响力等进行了具体分析,对医学署的衰落与民众就医选择之间的关系特征进行了深入阐发。
二、佐杂官下沉分辖引发的讨论
长期以来,学界普遍以县为中国帝制时代国家政权的最低等级,知县掌一县之政,“靡所不综”,属于“一人政府”。然近年来,傅林祥、贺跃夫、胡恒等一批专家学者通过考察明清档案、地方志等资料,注意到明清之际的基层行政发生了巨大转型,很多地区的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在县治以下有明确辖境这一现象。由此,他们开始质疑“皇权不下县”的传统认知,提出了“次县级行政”的观点,即佐贰、典史、巡检的辖境构成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区划,进而试图为清末民初以来“县下设治”的行政区划传统找到历史渊源。
不可否认,学界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忽略”了明清佐杂官的行政体制,“低估”了其基层治理功能,以致其普遍被认为是帝制时代的“冗官”。20世纪90年代起,傅林祥、贺跃夫等学者利用明清档案、地方志等资料,重新审视明清基层行政区划的问题后,提出了“次县级行政”的观点。傅林祥[28]《清代的次县级政权与辖区》一文认为清代巡检司辖境大多属于“次县级政区”。其[29]《清雍正年间的次县级行政机构及其职能探析》一文又按照职能的差异,将清雍正年间的次县级行政机构分为三类:第一类仅有治安职能;第二类具有治安和司法职能;第三类还可以征收钱粮,已经与知州、知县的职能相接近。贺跃夫[30]指出清中叶以后,随着人口的巨大增长和基层社会控制的复杂化,清政府为维持和加强其在基层的行政控制网,通过在州县以下析分出“次县级行政单位”的方法,扩大了基层管理体制的规模。随后,更引发了关于明清基层行政区划的大讨论。后继学者中,以胡恒为代表,对“次县级行政”的学术观点持明确的认同态度,他通过考察明清广东基层管理体制的转型问题,发现“捕巡官员在基层社会发挥了有限但又广泛的行政职能,与乡绅形成共治乡村的关系”,且其辖区有了统一的“司”的名称,是县下一级区划逐渐确立之基本趋势的重要反映[31]。以张研为代表,则坚持“地方政权最低一级为县”的传统观念,从而否定了“次县级行政”的观点,他认为清代地方政权最低一级为县,县以下行政区划是法定社区与传统自然社区的结合,亦是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固有权力在制度层面上的契合点[32]。
同时,关于“次县级行政”的讨论不仅局限于明清基层行政区划的范畴,更是直接波及“皇权不下县”这个近年来广受关注的学术话题。20世纪40年代后期,费孝通提出著名的“双轨政治”格局,认为在此格局之下,帝制时代的乡村属于“自治”的范畴[33]。至20世纪60年代,萧公权[34]指出,帝制体系中乡村“自治”是人们的一种错觉,乡村属于政府“控制”的范畴。此后,立足于“乡村自治”还是“乡村控制”的分歧,又陆续展开了“皇权不下县”的争论。而当学界对什么是“皇权”以及“皇权”怎么样才算“下县”难以达成共识时,明清州县佐杂官下沉分辖现象一度成为此争论的重要突破口。魏光奇[35]通过探讨清代“乡地”的问题,发现雍乾以后出现州县佐贰、杂职开始负责统辖乡役组织的制度,这意味着在州县之下划分了职能单一的行政区、设置了国家正式官员,“皇权不下县”的体制被打开了“缺口”。胡恒[36]承袭这一思路,利用文献资料考证,具体梳理了清代佐杂官分区管辖乡村的类型,指出自雍正中期开始,原本在县衙办公的佐贰官纷纷驻扎乡村要地,分区进行统辖;驻扎县城的典史分管城郭及其周边区域;杂职官也分管一定的辖区,并逐步具备较为完整的行政职能,提出这一基层政治的新动向说明清代乡村并非是一个皇权远离、绅权统治的区域,从而否定了“皇权不下县”关于县以下不存在行政机构的理论根基。张海英[37]具体考察明清政府利用佐贰官、巡检司、驻镇官员等对江南市镇进行管理的政治模式后,提出古代国家权力的直接延伸,绝非只到县一级,而是延伸到了县以下,突破了“国权不下县”的传统。
张研、王印红等学者则对明清“次县级行政”能够证明“皇权下县”的观点和研究模式提出了质疑。张研不认同“次县级行政”的观点,并遵循魏光奇、胡恒等学者的研究模式,否定了“皇权下县”的看法。如其《对清代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的考察》一文以清代广东为重点,通过考察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的实况、依据、性质,发现佐贰、典史、巡检不可能在其分辖之地负全面之责,成为有如知县的“亲民之官”,且佐贰、巡检数量过少,其辖属之地没有典型代表性,从而否定了清代“皇权不止于县”的猜想[38]。王印红针对魏光奇、胡恒等学者以县下设置次县级行政机构和官员为明清“皇权下县”的直接标志这一研究模式,发表了不同观点。王印红与朱玉洁[39]提出,皇权是否下县,应从其是否对乡村社会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来理解,而非仅将其局限于县以下是否设置正式的行政机构或官吏的形式;事实上,明清佐杂官为代表的皇权依附势力,是皇权渗透到乡村治理、汲取社会资源以及稳固其统治的凭借,在调节乡村社会中的矛盾与冲突、维护乡村秩序以及推行皇权独尊思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对佐杂官区域化特征的关注
在明清佐杂官研究的过程中,很多专家学者有意或无意地捕捉到了明显的“区域化特征”。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佐杂官的基层定位问题。明清佐杂官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每一地区因独特的地理、交通、物产、人文等情况,导致其在基层政治中的定位不尽相同;同一区域的很多佐杂官也因建制、分布、具体职掌等经常变迁的缘故,难以准确判定其发挥的基层行政功能。二是相关研究资料的问题。目前学界关于明清佐杂官研究的主流文献是地方志,他们的撰写、成书虽然奉行官方政府所要求的客观、实际的编纂原则,但绝大部分内容还是服务于地方文化的,极具地域特色,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掺杂了一部分编纂者自身的主观情感和社会认知。
明清时期,数量庞大的佐杂官进入乡村后,呈现出鲜明的“区域化特征”。一方面,全国各地的佐贰、首领、杂职官的权责比重有着明显差别。太田出、尹章义、李良品等学者通过综合考察某一地域单元佐杂官的行政、安保、司法、经济、军事、教化诸权,得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结论。如太田出[40]经过详细考察清代江南三角洲地区分防市镇的佐杂官,认为其权责广泛,包括治安、司法、教化以及公共事业,渐有成为“地方主官”的趋势。尹章义[41]以清代台湾新庄巡检为研究个案,发现新庄的分防巡检除了“稽查地方”,还有行政权、保安权甚至一定的司法权。李良品、罗婷[42]通过探析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巡检司的职能、配置与待遇,得出“中央王朝在西南民族地区广设巡检司的目的在于从行政、经济、军事三方面对该地区乡村社会实施有效管控”的结论。胡恒[43–44]以钱粮征收为突破口,探讨了清代佐贰官与“钱粮征收之责”的关系特征,发现清代福建、甘肃地区较为普遍地存在着可以“征比钱粮”的分征县丞,既有钱粮征收之责,又往往具备刑名之权,拥有相对独立的行政能力。吴佩林[45]则以基层社会的司法权为突破口,考察了清代四川南部县县丞、巡检的审判权和裁断权,认为“清代县丞、巡检通常在地方司法中无审判之权,裁断权只能交由正印官处理”的传统开始被打破,南部县的县丞、巡检在其管辖区具有独立的司法裁断权,为官方所认可,并为维护地方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明清佐杂官因当地独特的地理、交通变迁,而呈现出极具地域特色的空间分布特点。赵思渊[46]通过考察明清时期苏州地区巡检司分布变迁情况,发现由于裁革等原因造成的巡检司辖区的虚化以及一条鞭法的展开、嘉靖倭患泛滥、清军入关等因素,使得江南地区的巡检司辖境很难视作一种“次县级政区”。王伟凯[47]认为明代湖北所辖武昌、汉阳、黄州、承天、德安、荆州、襄阳、郧阳八府的巡检司在设置与分布上有一定的特点与规律:设置时间主要集中在洪武和成化年间,分布上呈明显的区域集中,并且与卫所分布相互补充,从而造成明后期巡检司部分职能的弱化,进而使该地区的基层管理出现了部分失控。廖望、黄忠鑫[48]在分析明清肇庆府属漠阳江流域、潭江流域及云浮山区、西江干流沿线、绥江沿线、贺江沿线的佐杂分防情况后,发现明初肇庆府巡检布局以西江沿线及瑶区山地为控扼对象,集中于阳春至新兴一线的军事要隘;清雍隆年间开始全面推行佐杂分防,在明代西江布防的基础上强化了对海防与南部驿路的控制,巡检集中进驻于人口稠密的墟市地方。韩虎泰[49]具体考察晚清广州府巡检司的设置数量和分布地域后,发现广州府与广东其他地区相比存在着明显差异,广州府区各县之间呈现出沿海和平原地区分布集中、沿山和内陆地区分布稀疏的地理差异。林玉茹[50]利用量化统计方法,对清代台湾港口的空间结构作了研究,其中对鹿港巡检、新庄巡检驻地的考证,揭示了台湾地区港口规模与衙门等级、行政附属商业机能复杂程度以及人口规模之间的正比例关系。
再有,众多专家学者注意到,明清佐杂官研究中广东省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张研[38]认为:“广东佐贰、典史、巡检均有辖属之地;巡检数量居全国之首,且几乎每县均设,这在全国均属绝无仅有。”胡恒[31]也曾提及清代佐杂分防制度中广东省的特殊“地位”——巡检司有无辖区,与明清之际基层行政管理模式转变关系甚巨;一直到明朝末年,基层行政转变最为激剧的广东省只是在局部地域出现了巡司辖属乡都的记载。美国学者安乐博[51](Robert J.Antonym)对清代广东的基层政治也有所关注,其《广东省各州县官员、国家和地方社区:1644—1860》(Subcounty Officials,the State,and Lacal Commun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1644—1860)一书详细考述了清代该地区州县佐杂官的分布、变迁、职权、运作细节,以及在维护社区治安、加强传统教化、自然灾害管理中扮演的极其重要的角色;特别强调了在社会变动时期,佐杂官作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媒介,扩展了清朝国家权力,强化了政治统一和社会经济稳定,并非是闲散冗员。
四、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关于明清佐杂官的研究,主要呈现出分歧较大、讨论激烈、蓬勃发展的基本态势:
其一,关于明清佐杂官研究的分歧,主要存在于认识论层面和方法论层面。在认识论层面主要表现为:佐杂官是否为封建帝制时代的“闲曹”“冗官”;明清县治以下佐杂官是否有明确的辖境;佐杂官在自己的辖境内是否有独立的行政、司法、经济、军事、教化、安保诸权;佐杂官下沉分辖是否为全国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县级衙门是否为皇权统治的终点;“次县级行政”的观点是否成立、是否具有主观性和片面性;“次县级行政”与“皇权不下县”之间是否有直接联系等。在方法论层面主要表现为:学界对一些专家学者利用“次县级行政”观点的成立来论证明清“皇权”已经“下县”这一研究模式的三种不同态度——认同、辩证看待与质疑。可以预见,在更多的文献史料被发现、整理,并充分应用到史学研究之前,这种学术分歧还将继续存在。
其二,关于明清佐杂官的激烈讨论,主要围绕其行政体制(包括建制、历史沿革、品秩、衙署、属员、选拔、除授、升转、奖罚情况等)和基层权责(包括行政、司法、安保、经济、教育、征税、赈济、教化、公共事业等)展开,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一些成果也引起了学界普遍的关心和注目。由于各地独特的地理、交通、物产、人文、风俗等客观因素,以及研究资料(如档案、地方史志、民间契约等)中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浓郁的地域特色、厚重的地方文化等主观因素,明清佐杂官也相应地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化特征,为一批学者所特别注意。而这些佐杂官的群体性特征有哪些?区域化特征是否只是其群体性特征的“异象”?如若不是,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又是什么?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思考、探究,且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其三,关于明清佐杂官研究的蓬勃发展,主要是受近年来学界兴起的“理论创新”“视角创新”“方法创新”的学潮影响。无论是关于其行政体制的具体考证,还是对其下沉分辖现象和区域化特征的激烈讨论,其研究维度从“传统制度史”走向“人的制度史”“活的制度史”[52]的趋势日益明彰。在此趋势之下,长期以来学界关注较少且不甚着力的驿丞、闸官、仓官、河泊所官、茶引批验所大使、草场大使、税课司大使、递运所大使、铁冶所大使、医学、阴阳学、僧会司、道会司等杂职官,开始陆续走进史学研究的视野。同时,这些佐杂官员的吃喝住行、言谈举止和其他日常生活行为,交际亲朋、应酬故友的过程中所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乃至心态情感变化、身体健康状况、官场竞争压力等,都将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
就近三十年来学界关于明清佐杂官研究的已有学术成果,史料需求,理论、视角与方法来看,对其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从研究资料来讲,地方档案、地方志和民间契约文书是研究佐杂官行政体制和基层职能的史料基础,特别是在解读其下沉分辖现象和区域化特征时,是不可缺少的史料支撑。如目前已被广泛应用到佐杂官研究中的《南部档案》《巴县档案》《淡新档案》等地方州县档案,展示了当地佐杂官员不同于传统印象的“鲜活”的历史面貌,且其史料价值尚待深入发掘。另外,明清《实录》、官箴书和部分文人笔记文集等,也偶有关于佐杂官的零星记载,可作为重要的“辅证”,却往往被忽视。随着后续研究的持续展开,这些记载也需要系统地搜集、梳理。从研究视角来讲,随着明清地方志、民间契约、州县档案等基础史料陆续被发掘、归纳和整理,佐杂官研究的史料需求逐渐有得到满足的趋势,而以其在基层的建制分布、权责执掌和社会效应为基本视角,通过考察“次县级行政”观点的成立与否,来讨论“皇权”已经下县或仅止于县一级,是值得肯定和延续的研究模式。从研究方法来讲,首先宏观整体研究与微观个案研究要紧密结合起来。对佐杂官群体进行宏观描述,和对某一佐杂官个体进行微观探析,是目前学界已较为成熟的两种研究模式;而以其基本“政治属性”为“桥梁”,将两种研究模式紧密联系起来,综合考察佐杂官群体和个体之间的公共性、差异性,全方位展示其在基层治理中扮演的政治“角色”,是很有必要的。其次,文献资料与考古实物也要相互印证。明清遗存下来的县署衙门,是解读佐杂官的一个主要突破口;其直观呈现的公文疏章、司署规制、皂役配置、官俸役食等,或间接折射的辖区分划、职权分配、官场体面、社会地位等,是全面认识和定位佐杂官的重要线索。最后,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是解读明清佐杂官的必然趋势。随着历史研究开始注重“人”的历史,明清佐杂官员的身体、言谈、行为、衣冠,甚至心理、情感、观念、思想等,都终将被纳入史学研究的范畴;在运用历史学方法进行考察研究的基础上,合理应用政治学、统计学、民俗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的一些科学理论与方法,是极具学术意义的尝试。
[1] 左平. 清代州县佐或杂职官员研究述论[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6): 5-9.
[2] 刘子扬. 清代地方官制考[M].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1988: 112-114.
[3] 刘鹏九, 王家恒, 余诺奇. 清代县官制度述论[J]. 清史研究, 1995(3): 37-47.
[4] 申立增. 清代州县佐贰杂职研究[D].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 2006: 3-6.
[5] 鞠枭磊. 清代州县佐贰杂职官员惩戒研究[D]. 重庆市: 西南大学, 2017: 10-11.
[6] 张振国. 清代地方佐杂官选任制度之变革[J]. 历史档案, 2008(3): 64-67.
[7] 吴大昕. 明初的杂职官制度[J]. 明代研究, 2019(32): 11-54.
[8] 吴大昕. 明代杂职官员出身考论[J]. 社会科学辑刊, 2017(2): 126-136.
[9] 柏桦. 明清时期府县官政治行为之考察[J]. 南国学术, 2019(3): 453-466.
[10] 柏桦, 李静. 明清时期府县官对下政务运作[J]. 古代文明, 2021(1): 126-136.
[11] 织田万. 清国行政法[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156-160.
[12] 吴吉远. 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研究[M]. 北京: 故宫出版社, 1998: 102-108.
[13] 那思陆. 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 271-279.
[14] 王兆辉, 刘志松. 清代州县佐贰官司法权探析[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4): 161-166.
[15] 茆巍. 万事胚胎始于州县乎?从命案之代验再论清代佐杂审理权限[J]. 法治与社会发展, 2011(4): 95-103.
[16] 川胜守. 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M]. 东京: 汲古书院, 1999: 663-666.
[17] 王伟凯. 试论明代的巡检司[J]. 史学月刊, 2006(3): 49-53.
[18] 胡恒. 清代巡检司时空分布特征初探[J]. 史学月刊, 2009(11): 42-51.
[19] 李克勤. 清代广州府属巡检司研究[J]. 广东史志, 1994(3): 45-49.
[20] 左平. 从档案看清代州县巡检及其衙门[J]. 四川档案, 2010(4): 15-16.
[21] 陈阳. 典史之历史源流及其发展[J].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4): 107-110.
[22] 于宝航. 明代中后期驿丞群体的身份和心态[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4): 125-128.
[23] 于琪.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闸官研究[J].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2): 136-138.
[24] 李龙潜. 明代税课司、局和商税的征收——明代商税研究之二[J].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7(4): 95-118.
[25] 周琳琳. 明代府州县仓官研究[D]. 东北师范大学, 2013: 2-5.
[26] 马晓菲. 明代僧官制度研究[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7: 160-174.
[27] 狄鸿旭. 清代“医学署”初探[J]. 满族研究, 2015(2): 59-64.
[28] 孙进己. 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59-68.
[29] 傅林祥. 清雍正年间的次县级行政机构及其职能探析[J]. 清史研究, 2011(2): 60-67.
[30] 贺跃夫. 晚清县以下基层行政官署与乡村社会控制[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4): 82-89.
[31] 胡恒. “司”的设立与明清广东基层行政[J]. 清史研究, 2015(2): 111-136.
[32] 张研. 清代县以下的行政区划[J]. 安徽史学, 2009(1): 5-16.
[33] 费孝通. 乡土重建[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2: 35-54.
[34] 萧公权. 中国乡村: 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M].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591-596.
[35] 魏光奇. 清代“乡地”制度考略[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5): 64-78.
[36] 胡恒. 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27-85.
[37] 张海英.“国权”:“下县”与“不下县”之间——析明清政府对江南市镇的管理[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1): 145-159.
[38] 张研. 对清代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的考察[J]. 安徽史学, 2009(2): 5-18.
[39] 王印红, 朱玉洁. 从明清小说管窥传统乡村治理中的“皇权”下县[J]. 青岛行政学院学报, 2020(1): 48-53.
[40] 张国刚.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0: 105-116.
[41] 尹章义. 新庄巡检之设置及其职权、功能——清代分守巡检之一个案研究[J]. 食货月刊, 1981(1): 389-404.
[42] 李良品, 罗婷. 论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巡检制度[J]. 三峡论坛, 2015(4): 39-46.
[43] 胡恒. 清代福建分征县丞与钱粮征收[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12(2): 45-57.
[44] 胡恒. 清代甘肃分征佐贰与州县分辖[J]. 史学月刊, 2013(6): 57-65.
[45] 吴佩林. 万事胚胎于州县乎——《南部档案》所见清代县丞、巡检司法[J].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9(4): 30-37.
[46] 赵思渊. 明清苏州地区巡检司的分布与变迁[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10(3): 33-48.
[47] 王伟凯. 明代湖北八府的巡检司设置与分布[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3): 365-369.
[48] 廖望, 黄忠鑫. 明清肇庆府州县分防佐杂建置研究[J]. 地方文化研究, 2018(6): 81-94.
[49] 韩虎泰. 晚清广州府巡检司的地域分布特征初探——以《宣统三年冬季职官录》的记载为中心[J]. 地方文化研究, 2014(1): 48-58.
[50] 林玉茹. 清代台湾港口的空间结构[M]. 台北: 知书房出版社, 1996: 129-143.
[51] Robert J. Antonym.Subcounty Officials, the State, and Lacal Commun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1644—1860[M]. New York: 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2002: 106-128.
[52] 邓小南. 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J]. 浙江学刊, 2003(3): 98-102.
The Basic Situation of Assistant Officials Research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CUI Jian-jian, SHI Hui-fa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China)
At present,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assistant official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hows a basic situation of big differences, fierce discussions and vigorous development. At the end of 1980s, it began to enter into the field of historical research. The academic circle began to discuss and explore from the outside to the inside and from the shallow to the deep around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the stepwise division of jurisdiction and features of regions. With more than 30 years of efforts,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quite abundant. Taking the viewpoint of “sub county-level administration” as the basic point and important extension point, through the research mode of group macro description and individual micro analysis, the research investigated the specific “political behavior” and “government operation” of assistant official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expounded its intern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power distribution of local officials and “imperial power does not go down to the county”. To a large extent, it reveals its obvious regiona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assignment.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ssistant officials; grassroots political; the research overview
2021-08-31
崔健健(1994—),男,甘肃定西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史。
K248
A
2095-9249(2021)05-0063-06
〔责任编校:王中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