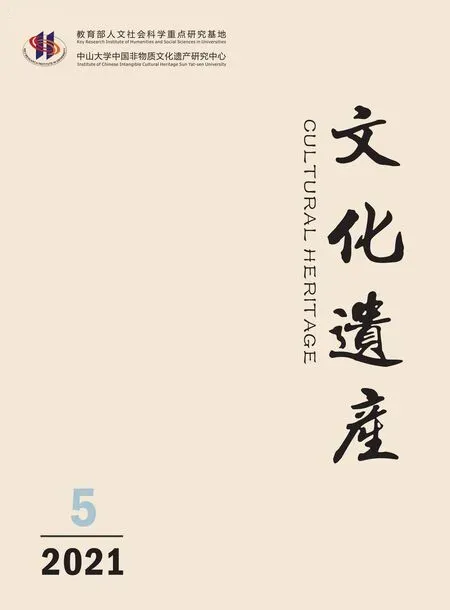“允许商业化但不能过度商业化”:不同遗产理性带来的规范难题*
[意]Chiara Bortolotto 著 马庆凯 译
2019年,《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名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导下的全球购物》的文章,讨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名录如何被文化产品消费者用于挑选有“历史意义的艺术品和手工艺品”。作者指出,这些名录不仅强化了这些被认定为非遗的手工艺品的商业价值,也给文化购物者提供了“真正的无形的体验”。例如,文章把2011年被列入奥地利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维也纳咖啡馆称为“当疲惫的购物者需要休息时的理想休息驿站”。(1)Tanya Mohn,“Global Shopping With UNESCO as Your Guide.”New York Times,2019.https://www.nytimes.com/2019/11/21/style/global-shopping-unesco-guide-germany-hungary.html(accessed May 2019).
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框架中,被认定为遗产、需要保护和传承的对象是“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2)UNESCO,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Paris:UNESCO,2003),Article 2.,而不是它们的结果与产品。然而,被当做市场上流通的商品、激发全球消费者兴趣的恰恰是后者。正如这篇文章指出的那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为非遗赋予了关键的象征性附加值,在全球范围内有潜在的经济影响,因此实质上已成为文化消费者青睐的大型市场。营销专家认为,这些遗产名录作为“事实上的品牌”,为非遗提供了令人向往的支持和正式的认可,其效果与特许经营体系类似。(3)Bailey Ashton Adie,“Franchising Our Heritage:The UNESCO World Heritage Brand.”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4,(2017):48-53.毫无疑问,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品牌效应并不是总能改善当地社区民众的生计,在不公平、欠缺包容性的发展模式中,当代民众也常常成为受害者,(4)Jaume Franquesa,“On Keeping and Selling: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eritage-Making in Contemporary Spain.”Current Anthropology Volume 54 (3),(2013):346-369;Michael Herzfeld,Evicted from Eternity:The Restructuring of Modern Rome.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9);Michael Herzfeld,M,“Engagement,gentrification,and the neoliberal hijacking of history.”,Current Anthropology,52(51),(2010):S259-S267.但是许多国家依然提名非遗项目,争取被列入非遗名录,部分原因是希望获得经济收益。(5)Kyoim Yun,“The Economic Imperative of Unesco Recognition:A South Korean Shamanic Ritual.”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52 (2-3),(2015):181-98.
成员国提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争取被列入各类名录,显然有经济因素的考虑。对于古迹、遗址等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商业化可以说是外部因素。但是对于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文化实践来说,商业化常常并非外部因素,而是其内在组成部分。而且,这类实践中有一些恰恰是商业活动,(6)Tomer Broude,“Mapping the Potential Interactions between UNESCO’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gime and World Trade Law.”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 25 (4),(2018):419-448.其生命力依赖产品的市场化。换句话说,市场是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一种“活态遗产”的其中一种因素。例如,对于“那不勒斯披萨饼制作艺术”“格拉斯地区香水技艺”“比利时啤酒文化”以及“韩国泡菜的腌制与分享”和“朝鲜的泡菜制作传统”等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类非遗名录的项目来说,售卖披萨、香水、啤酒和泡菜维持着它们的生命力。
在过去十年,随着“可持续发展”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话语中占据越来越中心的位置,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市场的复杂关系的关切逐渐增多。人们意识到需要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层面问题,这一快速变化在2016年版《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业务指南》中体现了出来。这一文本中,增加了一个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全新章节,其中一节明确谈到了“包容性经济发展”(7)UNESCO,Operational Directiv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Heritage -Intangible Heritage -Culture Sector -UNESCO.(2018),chapter 6 https://ich.unesco.org/en/directives.(accessed May 2019).。尽管官方文件中出现了这一转变,在实施《公约》过程中有规范力量的管理者并不能坦然地接受“市场并非文化遗产的敌人”这一观点。(8)Lucas Lixinski,“Commercializing Traditional Culture:Promises and Pitfalls in the Convergen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nd Cultural Heritage Law.”Annali Italiani Del Diritto d' autore,Della Cultura e Dello Spettacolo,29 (2020):1-15.这种不安基于这样一种看法,即遗产是一种符号商品,其目的并不是在常规经济活动中进行交换。(9)Pierre Bourdieu,“The Market of Symbolic Goods.”Poetics 14,(1985):13-44.在致力于遗产保护的官方群体中有一种强烈的困窘情绪,他们一方面面临压力,要承认商业化是许多“活态遗产”表现形式的内在属性,另一方面仍持有这样的看法,即一种被升格为遗产的实践如果被商品化,其文化价值将面临威胁,即便那些基本上属于商业活动的项目(如手艺或烹饪技艺)也是如此。他们在这两者之间左右为难。
本研究意在探究这一难题,分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固有的模糊性。这一管理工具夹在不同的遗产思维之间,这些思维涉及到“客观的、可见交易背后的”文化代码(10)Igor Kopytoff,“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Commoditization as Process.”In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edited by Arjun Appadura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64-92,64.。我的分析将聚焦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场域下“有能力、有权威谈论遗产、为遗产发言”的人士(11)Laurajane Smith,Uses of Heritag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6),12.。我认为,他们在规范非遗保护时遇到的难题特别有意思,其原因是,通过将某些非遗保护的方法称许为“最佳保护实践”或认定某些实践不合适而予以禁止,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了“良好的”遗产治理,由此规范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官方表述。换句话说,他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里制造了一种“权威化遗产话语”(12)Ibid.。
规范非遗遇到的难题——商业化
地方上的遗产实践者像企业经营者一样行事,使用广为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的概念和语言,努力将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为有文化特色的产品和服务确立价格。(13)Lynn Meskell,“The Nature of Heritage:The New South Africa.”(Oxford:Wiley-Blackwell,2012),207.他们不仅将这些文化资产视为“资本积累的新基础”(14)Rosemary J.Coombe,“The Expanding Purview of Cultural Properties and Their Politics.”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 5 (1),(2009):393-412,402.,也将其看成是有力的为地方赋权、增强韧性的工具。有学者指出,这种商业化与确立文化身份并不一定是矛盾的,事实上还会为地方经营者带来能动性与自我认同的建构,这些会激发文化生产者的自豪感而不会造成分化。(15)John L Comaroff,and Jean Comaroff Ethnicity,Inc.Chicago Studies in Practices of Meaning.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9).
在实践中,“遗产经营者”(16)Richard Pfeilstetter,“Heritage Entrepreneurship.Agency-Driven Promotion of the Mediterranean Diet in Spai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1 (3),(2015):215-31.会采用多种权宜之计,有多样的、混合的评估模式,因此缓解了作为群体认同化身的遗产与遗产的可转让性之间的矛盾。例如,这种紧张关系在一个墨西哥银矿合作社中得到了解决。在这个合作社中,“将文化遗产作为一种财产传给未来合作社成员的传统……让当地的参与者即便在将白银提取出来用于商品交易时,仍可以坚称白银是不可转让的”(17)Elizabeth Emma Ferry,“Inalienable Commodities:The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of Silver and Patrimony in a Mexican Mining Cooperative.”Cultural Anthropology 17 (3)(2002):331-58,346.。地方上参与非遗领域工作的行动者以相似的方式,基于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主观理解与每种状况的特殊需求,非常务实地运用《公约》。他们有创意地理解遗产和市场存在的交集,有时有策略地使用几个组织机构和法律来强化自身实践的合法性,即便这些组织和法律基于完全不同的逻辑。
2017年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那不勒斯披萨手艺”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它展示了地方上的遗产经营者如何有效地运用不同的遗产保护体制。在为了说服意大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支持这一提名而发起的请愿网站上(18)“Protect Italian Pizza with Recognition from UNESCO World Heritage,”change.org,accessed May 8,2019,https://chng.it/2RdDtTbWdq.,列入这一名录被表述为保护意大利产品免遭不合理使用的一条途径,清晰表达了这一努力的经济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将保护披萨以及相关产业免受‘假冒意大利产品’现象的侵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那不勒斯披萨的认可是一次保护‘意大利制造’品牌机会”。
在一次有关这次申请的访谈中,这一项提名和请愿的主要推动者(意大利前农业部部长、环境部部长)解释说,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攸关国家品牌的推广。他说,正是为了避免对这一手艺的不合理使用,他此前才接洽世界贸易组织,申请将“那不勒斯披萨”这一名称在“欧盟传统专门加工工艺标识”的法律框架下进行保护(19)Alfonso Pecoraro Scanio,“Introduzione.”In #PizzaUNESCO:Orgoglio Italiano,edited by Massimo Boddi,(Ariccia:Aracne,2015):7-12.。那不勒斯披萨手艺事实上也受到了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20)Benedetta Ubertazzi,“EU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International Review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mpetition Law48,(2017):562-587.,就像许多和其他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类名录的非遗实践有关的产品一样。
迪肯(21)Harriet Deacon,“Safeguarding the Art of Pizza Making:Parallel Use of the Traditional Specialities Guaranteed Scheme and the UNESCO Intangible Heritage Conven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 25 (4),(2018):515-542.曾经对上述烹饪手艺得到遗产和知识产权法双重保护的例子进行了分析,她强调两种体制基于不同的假定,有不同的法律效果。她解释道,这种差异与保护对象的表现形式和保护的方法有关。一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目标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文化过程,通过名录体系等提高人们意识的工具确保它们的动态发展和传承。另一方面,“欧盟传统专门加工工艺标识”制度致力于保护的是非遗相关产品的名称,而不是一个特定社会文化群体里产生的知识与技能。然而在实践中,“欧盟传统专门加工工艺标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都被用作品牌推广的工具,以增加机构(分别指欧盟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赋予的合法性。地方上的行动者介绍非遗实践及其产品的名称并对其作出描述时,往往会强调它们的悠久历史和地理渊源,这就赋予了它们真实性的光环,从而强化了它们的商业潜力(22)Ibid.。
在地方上,不同的法律体系、机构、思维框架可以并存、相互补充,地方上行动者有策略地加以利用以服务于地方上的目标。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瓦努阿图沙画就是这样一个案例,它展示了瓦努阿图对财产和转让的本土化理解如何缓解了遗产和市场的两极化。这样,“原本被认为是大相径庭的领域产生了联系”,遗产成为“交换的媒介而非有边界的物体,是一种有助于建立关系的工具而不是所有权的终点”。(23)Haidy Geismar,Treasured Possessions:Indigenous Interventions into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13).
与地方上的遗产从业者相反,由于执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官方机构确定遗产定义、保护目的、主导政策原则,确立“全世界适用的规则”(24)Michael Barnett,and Martha Finnemore,Rules for the World: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Global Politics.(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4).,其内部的遗产行动者就难以自由自在地运用《公约》了。由于被期待做出有依据的、客观的评估,从而被用于某些政治决定,他们也要处理同样的问题,却持有不同的立场。他们的评估需要与他们介入的法律政策体系保持一致。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职责是,从《公约》的角度、秉持《公约》的原则和精神来思考问题。
下面将要分析的主题是这些处于管理规范位置的遗产行动者。尽管他们也会介入到非正式的场合中,比如公开辩论或能力建设工作坊,他们作为规范者往往在更加官方的场合中发挥作用。在缔约国大会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等《公约》的管理机构中尤其如此。缔约国大会掌管着《公约》管理的职责,而政府间委员会则规定着软规则(25)Peter Bille Larsen,“The Politics of Technicality.Guidance Culture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In The Gloss of Harmony:The Politics of Policy-Making in Multilateral Organisations,edited by Birgit Müller,(London:Pluto Press,2013),75-100,75.,这些软规则主导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规范性表达。这个委员会由外交官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政府专家组成,负责将各成员国提名的非遗项目列入世界名录。他们对非遗项目的审议以“评审机构”的推荐结果为基础,而这些评审机构由活跃在非遗领域的民间社会组织代表和在政府下辖的遗产机构工作的个人组成。
对于在评审机构或政府间委员会国家代表团服务的管理者来说,将某一非遗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录被视为非常微妙的责任,因为它确立了一项先例与范例,由此在实践中界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就像2010年在内罗毕举行的一次委员会会议上一位阿尔巴尼亚的代表指出的那样,这一责任如果涉及到经济议题则会更加敏感。这位代表强调“将公约削弱为接纳各种形式的商业化和民俗化、模糊不清的工具”将会削弱《公约》未来的公信力。
市场侵入遗产庙堂引发的痛苦
当有关遗产和市场的关联的争论进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规范语境中时,它引发了人们的争议与忧虑。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审机构与政府间委员会频繁地提出与经济有关的议题,尤其是在手工艺和食品有关的非遗项目提名中。事实上,尽管它们在地方上引发了遗产从业者的兴趣,在国际层面介入《公约》执行的管理者往往倾向于以怀疑的态度看待后者。例如,一位来自西欧某国、自《公约》诞生以来就积极介入其实施的政府专家向我吐露了其看法,认为大家从来没想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会与食物或烹饪技艺有关。事实上,当与食物有关的非遗项目引发的争议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出现时,将自身视为《公约》精神倡导者的官员和专家们表达了共同的关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不应该变成世界各地菜肴的食谱(26)Chiara Bortolotto,and Benedetta Ubertazzi,“Editorial:Foodways 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 25 (4),(2018):409-18.。这些提名有显著的商业效果,显然导致了人们对和食物有关的提名的疑虑。的确,许多此类项目乃是由对经济的侧重所驱动,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遗产名录被视为一项附加的“认证体系”,以促进农业、食品产业发展。(27)Raúl Matta,“Food Incursions into Global Heritage:Peruvian Cuisine’s Slippery Road to UNESCO.”Social Anthropology 24 (3),(2016):338-52.Chiara Bortolotto,“Como Comerse Un Patrimonio:Construir Bienes Inmateriales Agroalimentarios Entre Directivas Técnicas y Empresariado Patrimonial.”Revista Andaluza de Antropología 12,(2017):144-66.Voltaire Cang,“Japan’s Washoku as Intangible Heritage:The Role of National Food Traditions in UNESCO’s Cultural Heritage Schem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 25 (4),(2018):491-513.Julia Csergo,“Food As a Collective Heritage Brand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 25 (4),(2018):449-468.Antonio Da.Silva,“From the Mediterranean Diet to the Diaita:The Epistemic Making of a Food Label.”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 25 (4),(2018):573-95.
2010年被列入名录的“地中海饮食”和“法国传统美食”是第一批造成很大争议的提名。在政府间委员会的会议之前,围绕这两个项目出现了密集的“后台”外交协商。然而,在政府间委员会举行公开辩论对申报进行评估时,官方的批评并未出现。最初推动“地中海饮食”项目提名的四个国家中的其中一个国家的代表将这一提名称为“奇迹”。她与另外三个国家的代表本来预计委员会评估申报时,会出现有关这一非遗项目的“商业轨迹”的“大问题”,并为此准备了回应。尽管官方很克制,各国政府代表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通常在非正式的交流中对此进行评论,围绕他们认为的、融入遗产场域的艰难尝试发表看法。例如,一位来自东南欧的遗产专家向我吐露,她对于“地中海饮食”被列入名录有多么地反对,她认为这并不符合《公约》规定的非遗项目的范围。她评论说,“根据定义来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基于非遗事项的文化价值将它们列入名录,而‘地中海饮食’的商业层面使得它并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范围里”。尽管最终得以列入,由于其明显的商业影响,“法国传统美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场域依然被认为是“极不愉快的”。(28)Chiara Bortolotto,“Como Comerse Un Patrimonio:Construir Bienes Inmateriales Agroalimentarios Entre Directivas Técnicas y Empresariado Patrimonial.”Revista Andaluza de Antropología 12,(2017):144-66.
然而,这种“不愉快”才刚刚开始。“法国传统美食”被列入名录后的下一个十年里,围绕其他一些提名出现了相似的困惑,包括“比利时啤酒文化”和“那不勒斯披萨手艺”。它们常常被称为“啤酒”和“披萨”,仿佛它们的官方全称中的“文化”与“艺术”两词不过是托词而已。因此,在非正式的交流时,这些例子一再地被认为是从《公约》诞生以来最“可耻的”入选项目。对于“那不勒斯披萨手艺”被列入非遗名录,尽管官方没有明确发出反对的声音,但是在其被宣布列入名录的几分钟后,一位先生走近我,绝望地摇了摇头,表达了他的沮丧和忧虑。他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舞台上付出最多、最坦诚、最令人尊敬的参与者之一。“这一次真的意味着《公约》已经死了”,他说。
国际遗产专家往往使用“极不愉快”“耻辱”等词汇形容有策略地将《公约》用作市场营销工具、推广商业流通中流行商品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往往服务于大公司的利益。一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查机构的成员这样向我表达了他的立场,他说他不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化利用行为本身,毕竟“社区需要生存”,但是他警惕的是那些将《公约》用作“资本主义行为的品牌”的霸权式利用方式。然而这些年来,即便有些项目知名度远远不及披萨或啤酒,也会受到有关将非遗商业化利用的批评。白俄罗斯毛毡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尽管白俄罗斯代表团持有反对意见,指出三十个毛毡制作者只是以家庭作坊的规模工作、并没有开经销店,“圣诞节时仅仅出售了几百条”,这个项目最终仍然没能在2011年入选。同年,来自韩国的韩山苎麻纺织工艺因为其商业意味遭到了负面的评价。2015年埃塞俄比亚提交的“西达摩人的新年庆典”也经历了类似的遭遇。
“允许商业化,但不能过度商业化”
上述例子说明,对在国际层面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确立标准的人来说,遗产与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在一场有关非遗商业化影响的辩论中,一位西欧国家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评论道:“众所周知,世界上有两个群体:‘古代人’和‘现代人’,即前者倡导对《公约》进行严谨的解读,后者则倡导对《公约》进行自由的解读”。为了在这两种观点之间取得折衷,政府间委员会引入了“允许商业化但不能过度商业化”的观点。这种相当模糊的解决方法的优点在于它具备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实际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化到底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创意经济”的形式,还是一种对文化和社会实践的威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没有做出明确回答,因此也阻碍了普遍规则的建立。
审查机构一再重申,商业化并非“先验的不合格要素”或“必然不受欢迎”,因为它可以为“持有者”带来收入。然而,它同时警告道,“过度”商业化“可能会损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和文化功能,以及其生命力”。委员会坚持必须在市场与非遗保护之间保持平衡,重申商业化“不能过度”,也不应将“保护”降级为次要目标。然而,过度的商业化并非仅仅被视为程度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从市场化中获利的行为者的合法性。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好的”或“坏的”商业化还取决于“社区”的能动性及其在非遗商业化中的角色,即“社区”是商业化的推动者还是“受害者”。
上述担忧与多萝西·诺伊斯描述的“一则有代表性的趣闻轶事”相呼应,在这则轶事中,“一家跨国公司侵占了一个孤立的原住民群体的文化创造”她认为,在这样的例子中,来自外部的“剥削”和社区内部的“利用”或“发展”之间似乎泾渭分明,“社区/非社区……看起来是二元对立的”。她认为这种区分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概念一致(29)Dorothy Noyes,“The Judgment of Solomon:Global Protections for Tradition and the Problem of Community Ownership.”Cultural Analysis 5,(2006):27-56,31.。换言之,通过凸显社区外产生利润的商业活动,“过度商业化”被等同于对不合理利用和脱语境化的关注,这两个概念属于知识产权保护机构的逻辑。
尽管《公约》最初是出于对“掠夺”“破坏性的文化转移”或“不合理利用”的关切,事实上,它明确了一种随着《世界遗产公约》的诞生而发生的从财产体制到遗产体制的转变。财产体制着重于“所有者通过疏远他人、利用财产、排除他者的能力展现他的控制权”、而遗产体制则基于呵护、传承、珍惜这些物品或遗产地的责任。(30)Lyndel V Prott,and Patrick J O Keefe,“‘Cultural Heritage ’or ‘Cultural Proper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 1 (2),(1992):307-20,310.如果说“商品化是文化财产这一概念所固有的”(31)Michael F.Brown,“Heritage Trouble:Recent Work on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Propert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 12,(2005):40-61,45.,那么文化遗产的概念就是在强调传承和共享的价值。这两种体制代表了基于权利和伦理的“不同的遗产”(32)Valdimar Tr.Hafstein,and Martin Skrydstrup.“Heritage Vs.Property:Contrasting Regimes and Rationalities in the Patrimonial Field,”In Jane Anderson and Haidy Geismar edited Routledge Companion to Cultural Property,(Oxford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7),38-53.。根据本迪克斯(Bendix)和哈福斯坦(Haftein)的说法,这种遗产体制的转变可以理解为两种构成集体的原则,用排他性/包容性来理解。他们认为,“知识产权的主题默认是有排他性的,可能会被不合理使用,并有权得到补偿;文化遗产的主题往往是有包容性的,在这一主题中,集体的“我们”被恳求要团结起来,阻止文化的退步和损害,避免文化被他者偷走”(33)Regina Bendix,and Valdimar Tr Hafstein.“Culture and Property.An Introduction.”Ethnologia Europaea 39 (2),(2009):5-10.。
确实,法学领域的研究已经强调了这些不同的保护路径之间根本的“哲学差异”和“相互竞争的目标”。(34)Lucas Lixinski.“Commercializing Traditional Culture:Promises and Pitfalls in the Convergen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nd Cultural Heritage Law.”Annali Italiani Del Diritto d’autore,Della Cultura e Dello Spettacolo,29,(2020):9,15.具体到实际保护的对象来说,它们的逻辑是存在矛盾的:知识产权工具旨在保护特定文化实践的产品,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聚焦于社会文化过程本身。(35)Chiara Bortolotto,“From Objects to Processes:Unesco’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Journal of Museum Ethnography 19,(2007):21-33.
在最初酝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时,各国代表摒弃了在知识产权制度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初观点,因为这不仅“将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变成一种商品,而且变成一种财产化的商品”(36)Lucas Lixinski.“Commercializing Traditional Culture:Promises and Pitfalls in the Convergen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nd Cultural Heritage Law.”Annali Italiani Del Diritto d’autore,Della Cultura e Dello Spettacolo,29,(2020):1-15。他们最终同意要从宽广的角度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聚焦于文化过程的传承,而非聚焦于以知识产权为基础、对非遗的法律保护,或这一过程的最终产品的商业化利用。(37)Janet Blake,Developing a New Standard-Setting Instrument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Elements for Consideration. (Paris:UNESCO.2020)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2/001237/123744e.pdf (accessed April 2019).
因此,“允许商业化但不能过度商业化”的概念在《公约》中内嵌了专有的逻辑,事实上在这个管理工具设计之初,这一逻辑就被禁止了。《公约》的出现反映出有必要允许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某些形式的市场化,以使其成为“活态遗产”,完全扎根于社会中。然而,这也揭示了《公约》固有的模糊性。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依然是在独立于市场的遗产保护体制内构建的。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显然采用了一种“新的价值排序”,即包括经济价值在内的使用价值要优先于其他价值。事实上,这两种管理体制基于完全不同的经济假设,并且由不同的价值体系支配,这两种价值体系分别强调遗产经济中所谓的“存在”价值和“使用”价值。(38)Michael Hutter,and David Throsby,“Value and Valuation in Art and Culture: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In Beyond Price:Value in Culture,Economics,and the Arts,edited by Michael Hutter and DavidEditors Throsby,(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1-20.
虽然地方上的遗产经营者创造性地找到了处理这两种管理体制带来的相互冲突的道德经济的办法,从规范者的视角看,这种模糊性是令人困惑的,因为规范者的视角应当与《公约》的基础性的遗产逻辑相一致。换句话说,处于危机中的这种规范视角反映了有关两种保护方式的国际辩论的多元化,即一方面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框架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另一方面是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框架下保护传统知识。事实上,不同组织内部发展出来的国际法律体系已经制定了具体的保护框架(39)Sun Thathong,“Lost in Fragmentation:The Traditional Knowledge Debate Revisited.”As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 (2),(2014):359-89.,这些保护框架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框架下建立,有着不同的关切点与目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将传统文化实践视为“知识产权”,是 “财产”,可以在市场经济中转变为商品。因此,其目的在于防止它们遭到不合理利用,对产权所有者而非实践本身有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建立了名录,旨在提高公众对特定社区文化表现形式的认识,寻求促进不同“遗产持有者”群体之间的文化交流(40)Bernard Debarbieux,Chiara Bortolotto,Hervé Munz,and Cécilia Raziano.n.d.“Sharing Heritage?Multi-State Nominations to UNESCO’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sts.”Territory,Politics,Governance.,将这一过程视为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41)Lucas Lixinski,and Louise Buckingham,“Propertization,Safeguarding and the Cultural Commons.The Turf War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raditional Cultural Expressions.”In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edited by Valentina Vadi and Bruno De Witt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5),160-174.。
结 论
事实上,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术语是创造出来的,以对市场做出负面反应”(42)Lucas Lixinski,“International Heritage Law and the Market.”International Heritage Law for Communities 3 (2),(2019):127-67,136.,有关非遗商业化的问题在执行《公约》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密切相关。这一事实表明在一个“旨在将物品脱离商业场域,为了思考、回忆和乐趣保护它们”的遗产体制中表达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困难(43)Michael Hutter,“Economic Perspectives on Cultural Heritage:An Introduction.”In Economic Perspectives on Cultural Heritage,edited by Michael Hutter and Ilde Rizzo,(Basingstoke:MacMillan Press,1997),3-10,8.。
虽然官方认可有必要平衡非遗和市场,认为这对于确保非遗生命力至关重要,但从规范性视角介入的行动者却面临着违背遗产基本原理的“痛苦”,因为《公约》是在这类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些行动者共同关心的是,人们对“文化产品”(即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可以市场化的部分)的兴趣可能大于对产生这些产品的文化过程的兴趣,即对《公约》倡导的保护工作的实际目标的兴趣。从这个角度来看,必须管控、规范商业化。该法规的条款旨在区分“好”的、会让“社区”获益的商业化,与对非遗进行“不合理利用”和“去语境化”的“坏”的商业化。
然而,我认为,“允许商业化但不能过度商业化”这一想法表明,《公约》执行过程夹在管理传统文化的两种逻辑之间。这些逻辑反映的是不同的道德经济,即基于排他性的专有知识产权制度,以及基于包容性和共享性的遗产管理制度。因此,在《公约》的框架内,“允许商业化但不能过度商业化”的原则体现出的是一种脆弱的平衡,突显了这两类管理制度遭遇时的艰难与二者之间的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