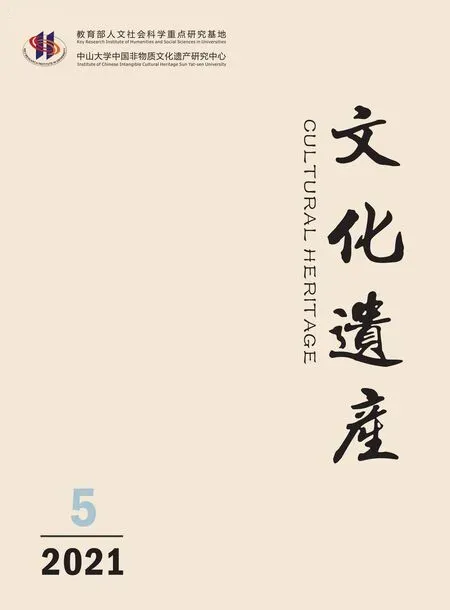希腊财政紧缩政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化*
[希腊]Panas Karampampas 著 张 煜 译
一、希腊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化:应对希腊财政紧缩政策
本文分析了希腊现行的财政紧缩政策如何促使当地遗产从业者开始施行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本研究聚焦于他们如何增强公民的韧性以应对“危机”,如何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制订国家战略,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当地市场重新焕发活力。本文并非另外一篇所谓“希腊经济危机”的民族志,但“危机”确实是希腊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迅速转变的背景和催化剂。
不少学者(1)Robert J.Holton,“The Idea of Crisis in Modern Society.”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38 (4)(1987):502-520,502;Kathleen Stewart,and Susan Harding.“Bad Endings:American Apocalypsis.”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8,(1999):285-310;Robin Wagner-Pacifici,Theorizing the Standoff.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60-63;Claudio Lomnitz,“Times of Crisis:Historicity,Sacrifice,and the Spectacle of Debacle in Mexico City.”Public Culture 15 (1),(2003):127-47;Rebecca Bryant,“On Critical Times:Return,Repetition,and the Uncanny Present.”History and Anthropology,27 (1),(2016):19-31.认为,危机是不同时期的分界点,会使人们重新理解未来。然而,本研究认为,危机不应当被视作一个转折点,或者某个会破坏时间连续性或使时间“冻结”的事件。危机是一段较长的时期,在此期间,冲突、暴力、纷争、赤贫、各种各样的创伤事件被植入到社会结构中,最终与社会结构无法区分(2)Henrik Vigh,“Crisis and Chronicity: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Continuous Conflict and Decline.”Ethnos73 (1),(2008):5-24.。就像在希腊危机中,人们的生活从未在时间上冻结,他们仍旧继续生活,适应日常生活中各种重叠交错的危机,例如经济危机或“难民”危机(3)C.Nadia Seremetakis,Sensing the Everyday:Dialogues from Austerity Greece. (New York:Routledge,2019);Neni Panourgiá,“The ‘Greek Crisis’and the New-Poor.The Being,the Phenomenon,and the Becoming.”In Critical Times in Greece:Anthropological Engagements with the Crisis,edited by Dimitris Dalakoglou and Georgios Agelopoulos,(Oxford:Routledge,2018):132-47;Elisabeth Kirtsoglou,and Giorgos Tsimouris,“Migration,Crisis,Liberalism:The Cultural and Racial Politics of Islamophobia and ‘Radical Alterity’in Modern Greece.”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00 (10),(2018):1-19.。因此,危机是一种已经成为常态的慢性病。这并不意味着人们遭受的苦痛正在减少,或者他们本就应当遭受苦难(4)Henrik Vigh,“Crisis and Chronicity: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Continuous Conflict and Decline.”Ethnos 73 (1),(2008):5-24.。塞尔吉奥·维撒柯夫斯基(Sergio Visacovsky)(5)Sergio Eduardo Visacovsky,“When Time Freezes:Socio-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on Social Crises.”Iberoamericana -Nordic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udies 46 (1),(2017):6-16,10.认为,危机是一种“必要之恶”,它会带来改变,而我不赞同这种观点。
在危机时期,人们对时间的理解是不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失去了它们的秩序,变得支离破碎,并且这种时间的“碎片”经常与各种秩序联系在一起。人们常常重新想象过去的危机,将它们与现在的事件相比较,并用它们来解释当前情况。(6)Veena Das,Critical Events: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on Contemporary India.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Daniel Martyn Knight,and Charles Stewart,“Ethnographies of Austerity:Temporality,Crisis and Affect in Southern Europe.”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27 (1),(2016):1-18.在希腊,人们希望现在的危机早日结束。然而在塞浦路斯,人民无法想象未来,因为他们的过去是一个从未被治愈的创伤。更具体来说,一些希腊人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的军事入侵解释“三驾马车(7)“三驾马车”是一个术语,特别是在媒体中,用来指由欧洲委员会(欧共体)、欧洲中央银行(EC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组成的决策小组。对希腊的经济占领”。他们期待着摆脱三驾马车的掌控、获得“自由”,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希腊人从德国人手中重获自由一样。因此,曾被视作是遥远的或单一的事件,现在却被认为是有联系的。这也导致历史事件因为当前事件被理解、解释和重现。正如许多希腊人在经济危机头几年所感受、回应和讨论过的,他们认为自己正生活在纷争的中心(8)Daniel Martyn Knight,“Cultural Proximity:Crisis,Time and Social Memory in Central Greece.”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23 (3),(2012):349-74;Daniel Martyn Knight,History,Time,and Economic Crisis in Central Greece.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5).。在分裂的塞浦路斯岛上,土耳其族控制的北塞浦路斯和希腊族控制的塞浦路斯共和国之间的边境经历了约三十年的封闭,终于在2003年开放。边境的开放使人们回忆起战争、强制移民,并重新想象他者的土耳其族人和希腊族人。人们开始反思他们的经历,“边境的开放将当下带入人们的意识中,创造了一种我们通常没有的关于当下的意识或概念”(9)Rebecca Bryant,“On Critical Times:Return,Repetition,and the Uncanny Present.”History and Anthropology,27 (1),(2016):19-31,20.。
危机将自身强加在相关从业者和机构之上,造成了一种有序的无序状态;(10)Michael Taussig,The Nervous System. (New York:Routledge,1992).面对危机,从业者和机构没有分裂,而是努力调整、适应、重组、重新配置,以适应持续的危机,在持续的动荡中寻找到新的稳定性。人们在危机期间,想到现状可能长期持续,未来存在不确定性,经常出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因此,他们宁愿保持一种“稳定的不确定性”,而不是去适应一种可能更糟糕的未来(11)Daniel Martyn Knight,“Time of Crisis:Permanence as Orientation.”American Ethnologist Website.Accessed April 2019,http://americanethnologist.org/features/collections/orientations-to-the-future/time-of-crisis-permanence-as-orientation.。
因此,在本文中,危机被视为一种背景,一段极不愉快的时期,它包括了快速变化、不稳定、失控、挣扎与再适应。将危机理解为背景,能使我们研究人们如何在充满困难、创伤的环境下,应对斗争并试图找到一种新的控制感和平衡,以及人们如何通过社会性想象和历史事件来想象、预测(或不预测)以及预知未来(12)Henrik Vigh,“Crisis and Chronicity: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Continuous Conflict and Decline.”Ethnos 73 (1),(2008):5-24;Charles Taylor,“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Public Culture 14 (1),(2002):91-124;Cornelius Castoriadis,The Imaginary Instit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Polity Press,1987);Dilip Parameshwar Gaonkar,“Toward New Imaginaries:An Introduction.”Public Culture,14 (3),(2002):1-19.。这一理解也受到古希腊语危机(krísis)的原意启发,即“判断”“决定”和“竞争”。因此,这项关于危机的民族志研究也调查了危机时期对话者的决定(或不作决定)和判断。本文探讨在“危机”时期如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创造动力,并使之成为这一领域变革的基础。人们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加大了非遗与市场的联系,以此促进经济恢复。
二、研究方法和研究参与者
自2017年2月开始,我在希腊文化体育部下辖的现代文化遗产局(DMCH)开展了民族志研究,此外对希腊不同的非政府组织(文化协会)(13)文化协会是非营利非政府组织的同行,它们的主要目的是发展或实践任何可以被纳入所谓“文化”这一大类的东西。和文化遗产从业者进行了研究。研究参与者包括现代文化遗产管理局的官员、负责执行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希腊国家科学委员会成员、学者和其他遗产专家,以及社区代表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称之为“非遗传承人”的人们。本文基于以上研究撰写而成。
在与我的研究参与者进行了两年的日常接触后(2017-2019),我还围绕关键问题对关键参与者进行了半结构化、开放式的深度访谈。这让我能够深化分析,以更结构化和更集中的方式获取数据,并通过观察扩充数据。这两年的经历帮助我建立了与研究参与者之间相互信任的关系,这种关系使得我能与他们讨论一些私密的话题。本来即便是在确保研究的保密性的情况下,这些话题都很难得到讨论。
三、希腊批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与希腊“危机”
希腊国会于2006年12月(根据法例第3521/2006号)批准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非遗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首次在希腊出现。然而,直到2010年西班牙、希腊、意大利以及摩洛哥开展合作、成功将“地中海饮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才开始被提及。这一最广为人知的非遗名录明确了“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提高对其重要意义的认识和从尊重文化多样性的角度促进对话”(14)UNESCO,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Paris,17 October 2003,Article 16.。2012年现代文化遗产局开始积极地实施非遗公约时,非遗的概念开始在希腊得到传播。与此同时,产生了希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其概念开始吸引大众的关注。这一概念传播的核心是现代文化遗产局如何通过媒体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除此之外,现代文化遗产局的小型团队不断在全国范围内的非政府组织、文化组织、地方政府以及遗产从业者中间传播非遗的概念,组织所谓的“非遗认知活动”。然而,伴随着其它因素的改变(15)Chiara Bortolotto,Philipp Demgenski,Panas Karampampas,and Simone Toji,“Proving Participation:Vocational Bureaucrats and Bureaucratic Creativity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ESCO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ocial Anthropology,28 (1),(2020):66-82.,非遗的概念传播也激发了利用非遗达到商业目的的可能性。
非遗公约在希腊的最初实施与所谓的“希腊危机”发生于同一时期。“希腊危机”的其中一个方面是人们如何看待自2008年以来一直持续的财政紧缩政策,以及导致赤贫、收入与财产缩减的一系列改革措施。(16)Daniel Martyn Knight,“The Desire for Disinheritance in Austerity Greece”Focaal 80,(2018):30-42.与此同时,上文中也提到,财政紧缩导致经济上的限制。不仅如此,由于这种紧缩政策,人们被迫降低他们的生活标准,失去正常的生活状态,甚至丧失了人性的尊严,不得不接受过去被认为是“贫穷”或 “战后”的生活条件,因紧缩政策失业的人更是如此。因此,财政紧缩也是一种经济结构的调整。鉴于此前财政支出被过度使用,当实施财政紧缩政策时,所有公民都被强制纳入其中,在消费时会有严格的自我约束。(17)Laura Bear,Navigating Austerity:Currents of Debt along a South Asian River.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当现代文化遗产局的官员在制定一项及时、实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战略时,他们尝试通过非遗克服“危机”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他们的目的是增加当地产品的销售量,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并且通过展现“希腊人的辛勤劳动”,改善希腊的国家形象,从而扭转外界对于希腊人的负面刻板印象,包括“懒惰”和“落后”。这些负面印象在希腊财政紧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被强化了(18)Michael Herzfeld,“The Hypocrisy of European Moralism:Greece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Aggression -Part 1.”Anthropology Today,32 (1),(2016):10-13,12.。这些举措与希腊国家科学委员会实施非遗公约的目的一致,该委员会的使命是协助非遗公约的实施,尤其是谋划和评估相关政策(19)“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ICH”,accessed October 22,2019.http://ayla.culture.gr/en/purpose/ethini_epistimoniki_epitropi_gia_ti_symvasi/.。在2012年12月举办的第一次会议中,非遗公约与市场化被明确地联系在一起,委员会成员提出,应当基于“国家可行性”和“可持续性(传统手艺的保护与推广)”,优先考虑 “设计得完备”的申遗文本。(20)第九次国家科学委员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会议档案5/12/2012。因此,国家科学委员会与现代文化遗产局力争通过非遗市场化与可利用的工具,促进公共利益,本案例中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即为这种工具。(21)Laura Bear,and Mathur Nayanika,“Remaking the Public Good:A New Anthropology of Bureaucracy.”The Cambridge Journal of Anthropology,33 (1),(2015):18-34.在实践中,这一战略在2013-2016年间开始浮现,希腊开始优先考虑将非遗项目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名录,这些名录都展现了“希腊人的辛勤劳作”,包括传统工艺和农业技术,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商品销售。除此之外,具有表演性质的元素,例如民间舞蹈、习俗以及庆典也同样得到发展,以吸引游客、助推当地经济。过去两年,这样优先考虑的项目数量有所下降,现代文化遗产局不再局限于他们过去四年尝试推动发展的项目类型,更多地依赖于一些“遗产社区”提交的项目。不过,现代文化遗产局的官员仍然鼓励遗产从业者提交他们在2013-2016年间宣传的非遗项目。
非遗公约的实施经常会遇到困难,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持续的财政紧缩和人力资源的匮乏导致公共资金的减少。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现代文化遗产局仍然尝试在公共教育中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视作一种应对危机的工具,改变希腊的负面形象。此处我想引用该机构官员的话:
当我们开始着手规划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非遗公约的主要机制)时,我们对于希腊国家生产力的认知处于一个非常低的起点。此外,希腊在世界范围内的形象由于各种各样的指控受到影响。通过名录,我们希望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希腊遗产。我们的目的是强化希腊现存传统中某些方面的竞争力,这些方面不仅仅能够引导我们度过财政与金融的危机,也将会帮助我们找到在经济领域中可持续发展的方法。(22)原文出自2017年4月5日,在圣尼古拉奥斯 (克里特)举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意识活动”。
这段引自2017年该机构主席的公开讲话,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意识活动”的公开演讲中被反复提及,用于解释为何重点关注农产品、农业技术以及其他传统工艺技术。近期一些与上述工艺技术相关的项目,包括克里特岛奥斯特罗西亚编织技艺及其保护实例、阿卡迪亚地区的石材工艺、传统的天宁岛大理石制作工艺、以及传统木制造船工艺都已经被列入希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最近与农业食品相关的项目是“合作与团结:皮利翁扎戈拉地区的农业合作社”、“圣托里尼葡萄栽培和酿酒传统技艺”以及“季节性迁移放牧的牲畜耕种技艺”。
(一)木制造船工艺
木制造船工艺(或地方造船工艺)是现代文化遗产局第一次将国家战略应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在此再次引用该机构的文件:
我们也从过往的经济研究中了解到,建造服务于休闲项目(游艇与海洋旅游项目)的木船计划极富经济潜力,这种潜力也为一些遭受重创的地区,例如港口城市帕拉马、西罗斯群岛等失业率高的船厂创造出数量可观的就业机会。
木制造船工艺于2013年被列入希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希腊也有意将其提名,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立的《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正如该项目被列入希腊非遗名录时的表格所指出的,“对于木制船手工艺人的支持政策应该是跨领域的,文化、旅游、船舶、地方发展领域都应给予支持”(23)K.Damianidis,“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lement Form:Wooden Ship Building.”In National Inventor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Greece(Athens:Ministry of Culture and Sports,2013.)accessed October 26,2020.http://ayla.culture.gr/en/xilonaupigiki_wooden_shipbuilding/.。现代文化遗产局主要通过开展与当地遗产从业者的合作,以筹集到建造工艺学校的资金。他们将通过学校培养新一代的造船者,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并且改善希腊某些群岛的经济状况。
同时,在立法层面对政策进行改革也势在必行。这具体指的是,欧盟议会以及欧盟理事会通过了减少职业捕捞证的法规(24)欧洲议会和欧洲联盟理事会2014年5月15日关于欧洲海洋和渔业基金的(欧盟)第508/2014号条例,废除了欧洲议会和理事会的(欧盟)第2328/2003号条例、(欧盟)第861/2006号条例、(欧盟)第1198/2006号条例和(欧盟)第791/2007号条例以及(欧盟)第1255/2011号条例。,希腊是如何执行这一法规的。这一法规规定,渔业从业者如果注销他们的证件,将会得到一笔丰厚的资金。他们可以改变原有的职业,接受新的职业培训,开展新的生意,并且接下来几年经济上有保障。希腊的立法委员还增加了新条款,规定从业者必须销毁他们的船只,以防止无证非法捕捞的现象。此规定导致木制船大量被销毁,船只的数量减少,许多传统的造船者失业,因为他们之前的工作大都是船只维修,而不是造新船。
现代文化遗产局对此规定做了另外一种解读。船主可以选择将船只改造为休闲船只,理想情况下这些改造的船只可以用于旅游业。一些船只没有被销毁而是被捐赠给市政当局,大部分的船只被捐赠给爱琴海造船与海事博物馆,仍然有少量木质船只继续为船主所用。此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是Erasmus+(25)这是欧盟为支持教育、培训等领域的科研合作等开展的项目。,此项目使人们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充满希望,但是项目开展并不顺利。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前任管理机构(名为“公共投资计划”)承诺提供20万欧元的资金,这笔资金可以让现代文化遗产局及其合作伙伴准备教学手册和相关课程,以达到建造工艺学校的基本条件。然而,在完成这笔资金所需的审批流程前,管理机构发生了变更,2019年希腊大选产生新政府后,这笔资金正在被重新讨论。
正如木制造船工艺被列入希腊非遗名录时表格中所陈述的,“把旅游行业与造船联系起来应当是头等大事”。现代文化遗产局的以上努力迈出了第一步。这些努力也有助于创造“市场上的商机”,(26)英文版本的详细阐释:http://ayla.culture.gr/en/xilonaupigiki.wooden.shipbuilding/,访问日期:2019年10月22日。技术娴熟的手工艺人可以利用这些机会。因此,当配备新技术的船只取代木制船之后,此前通过捕鱼业和贸易发展起来的部门受到了冲击。现代文化遗产局尝试着为这一部门寻找新的发展机遇。此外,受希腊法律的影响,木制船几乎消失了。目前,在以旅游为中心的新的遗产政策指导下,现代文化遗产局力图重振这一行业。
(二)“合作与团结:皮利翁的扎戈拉农村合作社”
“合作与团结:皮利翁的扎戈拉农村合作社”于2018年2月被列入希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由扎戈拉农业合作社提名,这是合作社在希腊间接推广其产品的营销计划的一部分。这一方法也可能被推广到国外。2020年3月,合作社提交了将这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优秀实践名册》的申请。
扎戈拉农业合作社是希腊最古老的合作社之一,于 2016年迎来成立100周年纪念,其主要产品是扎戈拉苹果。庆祝纪念活动的筹备工作始于两年前,当时聘请了一位拥有数字民俗学和教育博士学位的专家,专门从事档案研究和文化管理。此人还负责设计了为期一年的百年庆典活动,其目标是通过营销策略为该合作社建构以文化为中心的新形象,即树立具有社会责任感、对当地和希腊社会有积极影响的形象。该专家还建议,选择一项与合作社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去申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此,他联系了现代文化遗产局,并向我解释:“现代文化遗产局的官员喜欢该倡议,他们建议该元素可以侧重合作和团结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有创意,决定和合作社讨论一下。”这种建议源自于现代文化遗产局提出的提升希腊人良好形象的策略。例如,刻画希腊农民勤劳的形象,一反人们持有的希腊人懒惰的负面刻板印象。专家将建议传达给合作社董事会,他们也喜欢这个想法。通过强调“合作和团结”概念,董事会旨在树立一个有吸引力的、积极向上的合作社形象,这也将有助于其进一步扩大规模。他们将增加成员,扩大合作社,吸引更多扎戈拉附近村庄的利益相关方加入。
专家准备好了提名文件,2017年秋末,合作社委员会收到消息,现代文化遗产局对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列入该项目持肯定态度,文化体育部部长随后确认了这一消息。项目列入的非正式新闻出来的时候,恰逢持续近两年的百年庆典结束。因此,在余下的活动中,该非遗项目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消息被大力宣传,这有助于合作社身份的重塑。这次宣传通过一次全国学校艺术竞赛,影响了许多小学生及其家庭,此次竞赛是由教育研究宗教部与合作社共同赞助的。
2018年夏天,在我对扎戈拉的一次实地考察中,合作社委员会、扎戈拉的成员和人民开始把他们的非遗叙述集中在“合作”和“团结”上。他们详细阐述“自合作社成立以来,合作和团结已成为其遗产的一部分”,还具体说明了这些品质如何使他们的村庄从其他希腊城市中脱颖而出。这些提名后的叙述表明,扎戈拉人试图通过展示他们具有其他希腊人所缺乏的品质,来提高他们的社会资本,因此,遗产再次被用来获得新的道德利益。尽管如此,这些人都不清楚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与合作社的关系是什么。然而,他们仍然热衷于准备提名,以便将他们的非遗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优秀实践名册》上,从而吸引外界的注意,让更多人关注他们的苹果。
四、遗产从业者对政策的反应及几点总结性思考
在本文中我试图通过这些例子,讨论如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制定作为一种手段,增强公民对“危机”的抵御能力,并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制定国家战略与发展方案,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振兴当地市场。现代文化遗产局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它通过“提高人们非遗认识”的活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希腊,并与市场建立了紧密联系。这些活动作为传承和传播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战略的一种方式,激励遗产从业者为他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定保护计划,通常将他们与市场联系起来。目前,希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的大多数项目都在保护计划中涵盖了市场化。然而,这是提交列入表格者的个人决定,并不是现代文化遗产局强加的。“诵唱艺术”、“希腊的都会音乐”以及“扎戈里和科尼萨村庄的神圣森林”,并不像希腊国家级非遗目录中的大多数项目那样与市场有联系,因此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当地遗产从业者萌生了振兴木质造船技艺的兴趣,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博物馆,作为推动当地非遗保护的场所,来自国家战略的支持又推动这一博物馆进一步发展。同样,在扎戈拉农村合作社这个案例中,市场是预先存在的,当地遗产行为者将它作为对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战略的连接点。扎戈拉选择通过申请非遗,将他们已有的遗产实践进行调整,并用新的术语建构新的形象。传统技艺和表演的遗产化提升了它们在“遗产”这个标签下的地位,旨在增加它们的“可销售性”。与此同时,它有助于消除它们的市场化可能带来的任何负面联想。在希腊,从被认为是“传统”的东西中谋得经济利益是经常受到批评的,表演项目尤其如此(27)Panas Karampampas,“(Re)Inven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ought the Market in Greec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27(6),(2021):654-667.。
因此,在希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申遗经常被用作一种手段,帮助希腊人抵御来自媒体的负面信息。例如,扎戈拉人会强调自己的“合作和团结”以及收获作物时的“辛勤工作”。对遗产从业者来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意味着对其特殊性的一种认可与来自国家层面(或潜在的国际层面)的承认(28)Regina Bendix,“Heritage between Economy and Politics an Assess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In Intangible Heritage,edited by Laurajane Smith and Natsuko Akagawa,(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253-260.,这表明对希腊人的负面刻板印象在他们身上不起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申遗将地方遗产工作者与国家官员联系起来,让他们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合作。这似乎并不常见,因为人类学研究表明,在大多数时候,国家通过官方机构促进公益事业时,会在机构内外造成冲突,各机构各行其事。(29)Jennifer E.Telesca,“Consensus for Whom?Gaming the Market for Atlantic Bluefin Tuna through the Empire of Bureaucracy.”The Cambridge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33 (1),(2015):49-64;Daniel Miller,“Turning Callon the Right Way Up.”Economy and Society 31 (2),(2002):218-33;T.Mitchell,“The Properties of Markets.”In Do Economists Make Markets?On the Performativity of Economics,edited by D.Mackenzie,F.Munieza,and L.Siu,(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244-75.由于各自目标不一致,结果往往偏离国家代表的预期。(30)Max Weber,“Parliament and Government in Germany under a New Political Order.”In Political Writings,edited by P.Lassman and R.Speir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130-271;Arjun Appadurai,“The Ghost in the Financial Machine.”Public Culture,23 (3),(2011):517-39;Anna Tuckett,“Strategies of Navigation:Migrants’Everyday Encounters with Italian Immigration Bureaucracy.”The Cambridge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33 (1),(2015):113-28;Laura Bear,and Mathur Nayanika,“Remaking the Public Good:A New Anthropology of Bureaucracy.”The Cambridge Journal of Anthropology,33 (1),(2015):18-34.然而,在本文讨论的案例中,如木制造船的案例,我们发现当地的遗产工作者,例如木制造船者和博物馆代表与国家官员合作,以获得资金来使设计的保护政策落地,创建新的体系,例如技术学校,以向其他人介绍木制造船。此外,他们试图保护木船免受破坏,并打算重新解读希腊管理部门对《欧盟职业捕鱼管制条例》的解释。
在上述情况下,所谓的“希腊危机”导致了一种紧急情况,这种情况是一种“逐渐形成的状况”(31)Homi K.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 (Abingdon:Routledge,2004),59.,激励人们迅速行动,寻找新的解决办法并进行合作,以便为他们的日常问题找到迅速和切实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2003年的非遗公约在希腊危机时期的实施,为潜在的变革、改善当地遗产工作者和他们身边人的生活提供了另一个可能的方向。通过这种方式,遗产从业者旨在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同时也要重拾失去的骄傲和尊严,摒弃消极的刻板印象,强化其积极的形象。这项工作是通过地方遗产工作者与公共机构、非政府组织合作进行的,他们做出集体决定,试图在这漫长的危机中为自己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