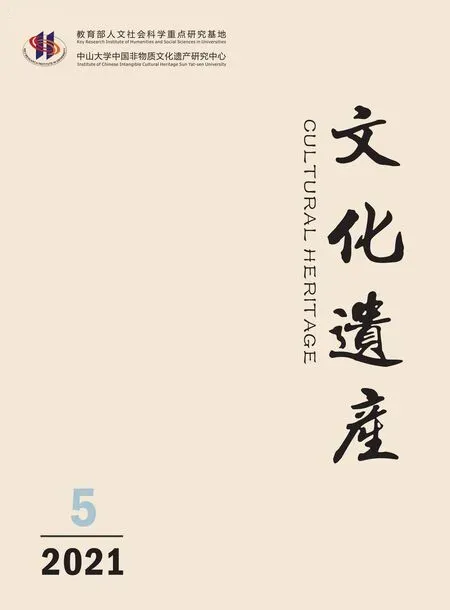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市场:自我经营的非遗传承人*
[德]Philipp Demgenski,Christina Maags 著 张 煜 译
一、引言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旨在提高公众认识,加强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保护,使传统文化习俗免受全球化和社会转型带来的破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各国政府制定法律,设立机构,推进研究,建立诸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等保护措施。尤其是对社区层面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受到特别关注,以增强其“创造、维护和传播”遗产的能力(1)UNESCO (2003).2003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https://ich.unesco.org/doc/src/15164-EN.pdf (accessed April 2019).。虽然建成遗产的保护(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经常与旅游业联系在一起(2)Enrico Bertacchini,Saccone Donatella and Santagata Walter,“Embracing diversity,correcting inequalities:towards a new global governance for the UNESCO World Heritag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17 (3),(2011):278-288.,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管理者和学者们强烈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化,强调旅游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相容(3)Lucas Lixinski,“Intangible heritage economics and the law.Listing,commodification and market alienation”.in Safeguarding Intangible Heritage. Practices and Politics,eds.Natsuko Akagawa and Laurajane Smith(London:Routledge,2018).。正如博托洛托在本期文章中所讨论的那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管理者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原因在于,非遗与新自由主义和市场逻辑密不可分。与此相关的论点可以分为两个方面:首先,全球遗产管理本身可以看作是新自由主义的延续,就非遗而言,通过呼吁赋予“社区”的权力,本质上促进了自治,社区居民必须适应新的评估方式,并思考自己的所作所为。其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政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实际上是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出现和产生的,可能无意间受其逻辑影响(4)John L Comaroff,and Jean Comaroff,Ethnicity,Inc.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9).。例如,通过全球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遗产项目导致了各式各样的商品化,这直接促进了全球旅游业的发展。因此,在更基层的层面,地方为文化从业者提供条件,帮助其遗产成为“文化资源”,并在市场上出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出发点是好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文件被曲解,被挪用,违背了文件的初衷。
我们将在本文继续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市场和经济方面的用途,并将目光转向中国。我们探究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将非遗市场化看作是促进非遗保护的手段。我们也将试图阐明,非遗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产生并受其影响。为此,我们比较了文化从业者在山东和江苏这两个省份的非遗保护实践,着重探讨他们如何使用非遗平台,把遗产作为“文化资源”来宣传和销售。文化从业者是在非遗的保护下自我经营的从业者。官方的非遗制度使文化制度化,并将从业人员与国家联系起来;但它也为从业者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能让他们像在过去数百年中所做的一样,凭借自己的手艺谋生。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里,参与者们面对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权力等级,获得成功的机会也不同,但非遗不应为这种结构性不平等负责。无论有没有非遗,结构性不平等始终存在。接下来,我们将介绍中国的非遗保护体系,然后再介绍比较案例研究的结果。
二、中国非遗保护体系
众所周知,自2004年签署《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建立自己的非遗保护框架和体系。此后,确定了非遗的要素,编制了非遗名录,设计了法律文本,非遗的概念在媒体、公众和文化从业者中产生了广泛反响。2011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但不同之处在于,它反复使用了“优秀”和“真实性”等术语,这些术语同时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的重要特征,但被有意排除在非遗公约之外(5)Chiara Bortolotto,“Plac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Owning a Tradition,Affirming Sovereignty:The Role of Spatiality in the Practice of the 2003 Convention.”in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edited by Michelle L.Stefano and Peter Davi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7),46-58.。例如,该法的第1条规定,该法的存在是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此外,第4条规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注重其真实性……”(6)“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人民网,http://ip.people.com.cn/n1/2019/0704/c136672-31214011.html,访问日期:2020年7月29日。。因此,在中国施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时,其政策和法律中有选择地采纳和融合了不同的概念和内在价值体系(7)Christina Maags,“Creating a Race to the Top:Hierarchies and Competition within the Chinese ICH Transmitters System”,in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Making:Experiences,Negotiations and Contestations,eds.Christina Maags and Marina Svensson (Amsterdam: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and IIAS,2018).。在此过程中,它还延续了一种与世界遗产遗址相呼应的宣传逻辑,遗产保护与发展旅游业相联系,并把非遗作为一种商品加以利用。
然而,不仅是中国非遗立法的框架推动了这种思路。该条法律第37条还直接点明,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用于商业目的,特别是鼓励和支持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优势,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非遗的市场化可以作为保护非遗的一种措施。不仅法律条文中推崇非遗市场化,国家级和省级行政法规(例如江西省的非遗政策)(8)“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江西省人民政府网,http://www.jiangxi.gov.cn/art/2015/7/1/art_5304_342400.html,访问日期:2017年12月29日。以及一些中国学者(9)张春慧、吴美珍:《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阈下龙泉青瓷文化民宿的营销策略研究》,《市场营销》2019年第 6期。张健:《非物质文化遗产浏阳夏布旅游商品化研究》,《遗产与保护研究》2018年第3期。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当地社区需要使用和销售与非遗相关的产品,从非遗实践中获得经济收益,以此保持遗产相关性和可持续性,提高年轻人的兴趣,使其接受这种传统技能的培训。然而,很多人反对将非遗视为经济发展的资源,认为这样做可能不利于非遗保护(10)黎大志、刘托、季铁:《市场化环境让非遗文化难以独善其身》,《教书育人》2014年第 12期;鲁平俊、丁先琼、白晋湘:《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状态评价的实证研究》,《体育科学》2014年第11期。。
非遗实践与遗产点或文物不同,它由一个人或群体表达,并受到文化知识和技能的限制,因此,非遗的市场化最终依赖于拥有这些知识和技能的文化从业者。中国政府用多层次的非遗名录保护非遗,是为了提高中国公众对非遗实践的认识。此外,它还创建了第二个名录,即“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列出了能够执行第一个名录中非遗实践的文化从业者。这个非遗传承人名录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3年设立的“人类活态珍宝”计划相呼应(11)UNESCO (2019).Living Human Treasures:a former programme of UNESCO,https://ich.unesco.org/en/living-human-treasures (Accessed April 2019).。非遗传承人名录允许国家在一个文化主管部门的认定下,确定某些文化从业者是非遗实践的“代表性传承人”。这些从业者成为了某个项目非遗实践的代表。但是,由于这些人在被认可为“代表性传承人”后,就能在各自的领域中对真实性作出解释并掌握话语权,所以一些生产文化商品的商家渴望成为非遗传承人(12)Christina Maags,“Creating a Race to the Top:Hierarchies and Competition within the Chinese ICH Transmitters System”,in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Making:Experiences,Negotiations and Contestations,eds.Christina Maags and Marina Svensson (Amsterdam: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and IIAS,2018).。此外,除了获得社会声望,他们还代表了中国官方的非遗实践,因此在以表演或文化产品形式展示非遗实践时,包装、宣传和销售中可以使用中国官方非遗的标志。中国采取了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县级市四个行政等级的管理框架,工作中聚焦于非遗名录,非遗传承人名录将非遗变成了社会威望的来源,而社会威望的高低取决于这个人被认可的级别(13)Ibid.。
事实上,正如一些传承人着重指出的那样,在谁被认可为“代表性传承人”的问题上,经常存在激烈的竞争(14)Ibid.。一位省级传承人长篇论述了在他的村子里只有一位老人是国家级的,“这是多么的不公平”,他认为实际上,他在相关实践中更擅长。当被问到他是否希望现在的那位国家级传承人能快点过世,这样他就有可能晋升为下一个国家级时,他半开玩笑似地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其他非遗传承人也说,一旦他们跻身名录,他们的文化产品就能以比从前高得多的价格出售。在与一位省级传承人谈到她家传统的白酒酿造生意时,她表示,她现在一瓶酒的售价是她进入传承人名录之前的十倍。此外,她还开设了网店,把自己的酒卖给亚洲各地的海外华人(15)Xiaoyan Su,“R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Modernity,Tourism and Shaolin Martial Arts in the Shaolin Scenic Area,China,”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33:9 (2016):934-950.。
随着国家对非遗市场化的支持和非遗的兴起,中国国内的非遗保护框架有时受到批评,被认为过于商业化,评估时过多地考虑了协助地方提高GDP的因素(16)刘苗苗:《警惕非物质文化遗产“异化”》,《瞭望》2015年第31期。。正如张小军和张晓松(17)张小军、张晓松:《文化?文物?———简论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文物化’困境》,《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1年第3 期。所论述的,中国的非遗保护系统“有文物,但没有文化”。他的意思是,我国的非遗法类似于文物法,本质上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简化为商品,从而使其可以在市场上销售,这剥夺了他们的文化价值。许多批评中国推动非遗市场化的研究都提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业中的商业化(18)Gary Sidely,“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and Ancient Tea Horse Road of Southwest Chin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China in Transition -Social Change in the Age of Reform),1 (2)(2010):532-545.Tim Oakes,“Heritage as Improvement:Cultural Display and Contested Governance in Rural China.”Modern China,39 (4)(2013):380-407.Xiaoyan Su,“R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Modernity,Tourism and Shaolin Martial Arts in the Shaolin Scenic Area,China,”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33(9)(2016):934-950.。在探讨“大众商业旅游”与“文化遗产保护”是否能兼容时,西格里(19)Gary Sidely,“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and Ancient Tea Horse Road of Southwest Chin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China in Transition -Social Change in the Age of Reform),1 (2)(2010):532-545:538.认为,大众旅游实际上导致了野蛮商业化和当地传统文化的扭曲,而不是“保护”,在此过程中,当地人“重塑”和“重新包装”了他们的传统,以适应游客的消费欲望和需求。
非遗市场化的一个普遍结果是,某些群体能够参与该过程并从中受益,而其他无法参与的群体则因此被边缘化(20)Xiaoyan Su,“R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Modernity,Tourism and Shaolin Martial Arts in the Shaolin Scenic Area,China,”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33(9)(2016):934-950.。由于名录的确立,文化场所和实践可能被官方承认或被排除在官方认可之外(21)Valdimar Hafstein,“Intangible Heritage as a List:From Masterpieces to Representation”.In Intangible Heritage,eds.Laurajane Smith and Natsuko Akagawa(London:Routledge,2009).,某些社区和文化从业者可能无法得到官方认可和经济收益(22)Christina Maags,“Creating a Race to the Top:Hierarchies and Competition within the Chinese ICH Transmitters System”,in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Making:Experiences,Negotiations and Contestations,eds.Christina Maags and Marina Svensson (Amsterdam: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and IIAS,2018).。
尽管非遗市场化可能对当地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影响,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作出最终的判断。相反,正如我们在一开始所提及的,我们想提出的观点是,非遗的概念正好出现在一个特殊时期。当时中国正在经历一些根本性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非遗的概念恰好在市场改革如火如荼的时候出现,该阶段倡导人们成为自我经营和负责任的主体,人们不得不“下海”,不完全依赖国家,以个体经济的方式谋生(23)Nancy Chen,“Introduction.”,inChina Urban:Ethnographies of Contemporary Culture,ed.Nancy Chen(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1),1-23.。正如许多学者所论述的那样,这造就了具有自我经营精神的个体,他们遵循利己的原则(24)Li Zhang,and Aihwa Ong,“Introduction:Privatizing China:Powers of the Self,Socialism from Afar.”in Privatizing China:Socialism from Afar,eds.Li Zhang and Aihwa Ong,(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8),1-20.Lisa Hoffman,Patriotic Professionalism in Urban China:Fostering Talent. (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10).Arthur Kleinman,“Quests for Meaning.”inDeep China:The Moral Life of the Person:What Anthropology and Psychiatry Tell Us About China Today,eds.Arthur Kleinman,Yunxiang Yan,Jun Jing,Lee Sing,Everett Zhang,Tianshu Pan,Fei Wu,and Jinhua Guo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1),263-91.。在此背景下,非遗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资源,不仅使之前被忽视和处于法律边界的文化从业者(25)Yongjia Liang,“Turning Gwer Sa La Festival int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tate Superscription of Popular Religion in Southwest China.”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1 (2)(2013):58-75.;Bingzhong Gao,“How Does Superstition Becom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Postsocialist China?”Positions:Asia Critique 22 (3)(2014):551-72.合法化;也给了他们一个特殊的平台,让他们能把文化实践变成一种谋生手段。因此,正如我们下面的案例研究所表明的,与其排斥或阻碍非遗实践,不如将非遗置于市场,使其可以获益,市场应该被视为非遗保护范式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在大型企业追求拥有“非遗认定”的情况下,非遗与市场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就变得显而易见,即将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孔府菜就是其中一例。孔府菜申遗是由私营企业家,特别是曲阜市及其周边地区的酒店经理,以及当地山东省烹饪协会和市级官员共同发起和推动的。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加强孔子品牌,将成千上万来曲阜朝圣的游客资本转化为经济收益(26)Philipp Demgenski,“Culinary Tensions:Chinese Cuisine’s Rocky Road toward Inter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tatus.”Asian Ethnology 79 (1)(2020):115-35.。这一案例将孔府菜用于商业和营销,并把它作为代表真实性的标志。这个例子很典型,因为中国各地的地方精英如企业家热衷于借此来创造个人利益,从官方非遗申报程序提供的商业机会中获益。但是,通过以下案例研究,我们发现,并不是只有精英才能从非遗市场化中受益,他们也不是唯一具有商业思维的群体。非遗为社区,特别是文化从业者再度提供了以商贸为生的机会,就像千百年来前人所做的那样。但是,与过去相比,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于国家改革,文化从业者已经有了自我经营的能力,并为盈利所驱动。
三、案例研究
(一)案例研究1:山东省
首先,我们将目光转向杨家埠,该村位于山东省潍坊市郊,是这熙熙攘攘城市中的一小部分。它以两项国家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闻名:木版年画和风筝。2014年,基于这两项遗产,文化部评定潍坊杨家埠民间艺术有限公司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现今,杨家埠随处可见生产和销售木版画和风筝的小型工作室和公司。在村庄的边缘还有一个号称杨家埠大观园的地方。在大观园的尽头,有两间工作室,一间是画木版年画的,一间是刻板的。这两间工作室就可以作为非遗市场化的两个不同的例子。在画版画的工作室里,三位女传承人坐在桌子一边,主要为游客服务。她们受雇于潍坊杨家埠民俗艺术有限公司,每个月可以拿到2000元基本工资。她们在工作时间创作的木版画并不属于她们,而是归大观园所有,售卖给游客。这导致她们工作积极性偏低,只有出现游客的时候才会积极工作。比如2017年夏天实地考察时,当我们走近工作间,从玻璃窗中看见传承人们正坐在桌子旁聊天、喝茶。但当我们开门的时候,她们迅速坐直,并开始了她们的画图工作。过了一会儿,在我们问过几个问题之后,她们意识到我们是来做调查的,并非“普通”游客,于是又放松了。等到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她们早已放下工作,开始喝茶。她们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这些传承人已不再练习手艺,只是完成交易。
但当我们参观“雕刻从业者”的工作室时,情况大不相同。工作室里的氛围与前者截然不同。三个传承人正坐在一个长桌旁埋头工作,不太情愿地与我们交谈。我们后来得知,他们在大观园工作室工作,每个月只能得到400元,但他们做出来的艺术品不归大观园所有,而归他们自己,他们可以自行售卖。一个木板雕刻者告诉我说:“每个月给你400块钱。你刻的板是你自己的。对光刻板的那些人,他们在家也是刻板,你在这里也是刻的。在这里还能拿400块钱。所以他们愿意做。给他一个工作室,还给一个宣传平台。”
以上的例子均说明了非遗正在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化。然而,当“版画工”被大观园雇佣并从事“雇佣劳动”,为游客进行所谓的“前台表演”(27)Erving Goffman,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London:Penguin,1990).时,“雕刻工”则为他们自己工作。因此,他们的表现更符合芭芭拉·科尔申布拉特-基布列特(28)Barbara Kirschenblatt-Gimblett,“Playing to the Senses:Food as a Performance Medium,Performance Research.”A Journal of the Performing Arts,4 (1)(1999),1-30.提出的“日常展演”,这很明显地体现在他们是如何在大观园的限制之下从事自己的日常工作。在两个案例中,从业者们都在追寻着各自的文化“贸易”,以获得经济利益,或从广义上说,为了获得市场。但是,后者更接近、更符合非遗的理念和精神。这也与我们开始提到的观点相近,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利润为导向的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中,文化从业者已经被“灌输”一个概念——根据市场逻辑来联系和构思他们的实践。
(二)案例研究2:江苏省
与山东省的情况一样,党和国家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宣传,为非遗传承人开辟了新的机遇。比如在南京市,南京博物院组织了一个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用来展示江苏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这个展览就像一个小型会议中心,陈列了省级以及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相关实践。参观者初入展厅便能感受到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的多元性和丰富性。然后,他们会被带着通过一条弯弯的小路,进入一个有十个隔间的房间,每个隔间都有一个非遗传承人在表演和售卖他们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从传统的戏曲面具、药垫、地方刺绣产品到皮影人偶、传统灯笼,应有尽有。
这里的情况与在杨家埠工作室时有许多相似之处。实际上,一些文化从业者并没有利用这个空间去工作,因为他们在江苏省已经有了至少一家(有时甚至是几家)商店,来出售他们的非遗产品。事实上,摊位上的一些工作人员并不是商店图片和证书上显示的非遗传承人,而是他们的学生或同事。他们主要负责管理商店,向参观者展示一些技艺,并销售非遗产品。就像杨家埠的例子一样,展厅的展览已经成为了一个“前台”,在那里,他们仅仅是在参观者走过他们的摊位时“表演”所代表的非遗实践。事实上,其中一个刺绣的商店似乎成了一个标准的商店,而不是一个游客可以了解当地非遗实践的空间。正在工作的是两个渴望展示公司产品目录的年轻女孩,而唯一体现非遗实践的传统物品则是放在商店中心的织布机。
其他的商店也在不知疲倦地制作他们的文化产品。比如说传统的灯笼制作人在与我们聊天的时候依旧在不断做灯笼,并尽力去吸引路过者来到她的隔间看灯笼。她透露过去无法依靠制作灯笼谋生。但现在,她在这个展位能够把它们卖给感兴趣的游客。过去,她曾试图寻找其他的商业模式,比如开设网店。然而,尽管她可以合理合法地称呼自己为官方认可的非遗传承人,但网上的竞争实在太激烈了,她很难以一个可盈利的价格出售她的灯笼。对她而言,非遗给与她平台成为文化经营者,她可以自豪地将她的传统产品出售给珍惜它们的消费者。对她来说,制作灯笼不仅仅是一种“表演”,更是她生活的基础。
除南京博物馆外,非遗传承人还获得机会,在南京市民俗博物馆和夫子庙等公共空间展示他们的非遗实践,售卖相关文化产品。例如,南京市民俗博物馆由政府将一座古老的建筑——甘家大院改造而成。这个当地的遗址让游客有机会在清朝的建筑和花园中漫步,还可以在沿途房屋的各个房间里遇到不同的非遗传承人。类似的有形和无形遗产的综合性推广也可以在靠近夫子庙的传统庭院中找到,这为非遗传承人提供了表演和销售其非遗产品的工作空间。然而,与更负盛名的南京博物馆相比,这里的非遗传承人经常把他们的摊位作为工作场所,热情地欢迎所有路过的人了解他们所“代表”的非遗实践。
无论是民俗博物馆还是夫子庙旁边的四合院,其商业策略都很明确:博物馆选址在一个即将会开满商店和餐馆的“老区”,夫子庙早已被繁华的商业区包围。因此,传统的非遗工作室将被整合并加入到它们周围的商业综合体中。但它们仍然被人为建起的砖墙隔开,因为对于博物馆来说,要买票才能进去。走过夫子庙地区,很明显可以感受到非遗传承人正面临着来自墙壁对面普通商户的激烈竞争。其他销售商正在以低得多的价格销售非遗传承人所称的“虚假”非遗产品——这些产品是由机器制造,大规模生产的。一位传统的木雕师虽然谴责这种做法,但还是称赞了政府的倡议,认为如果不是政府开始支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她将很难以木雕为生。同样,一个市级的陶器传承人指出:
“要说帮助是一定有的,作为传承人会相对比其他更好一点。不过,因为你毕竟是做这种手工艺品的,我认为你肯定要用这些名声来提升它的产品价值”。
尽管非遗传承人项目为她提供了相较于其他“普通”文化从业者的竞争优势,但也增加了她手工艺品的价值,使她有理由提高价格。尽管她无法与“假冒”的非遗产品竞争价格,但她仍然可以利用自己的工作室展示技能,并根据官方认可的技能来证明自己的价格,这让她的产品具有了一种其他人没有的真实性。
四、对比与讨论
与所谓精英掌控了非遗、利用非遗资源获取经济利益的视角不同,我们在非遗展览和工作室的调查表明,非遗传承人对展示、售卖他们的产品的机会不但很欢迎,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也以此维持生计。无论是杨家埠的雕刻者,还是南京这家博物馆的灯笼制作人和木雕人,他们都强烈支持非遗市场化,认为这是他们继续以“贸易”为生的一种方式。如果没有市场化,要做到这一点会更困难,甚至完全不可能。非遗平台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向游客和其他类型的消费者推销他们的文化产品。
这个案例研究也表明,正如任何其他行业一样,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类似于一个运动场,选手们之间实力悬殊。某些非遗传承人经营大型企业或工厂,使用非遗的标志只是为了促进销售。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明显看出,企业家试图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潮流,以分得一块“蛋糕”,有时会利用他们的社交网络来获得非遗的头衔(29)Christina Maags,“Creating a Race to the Top:Hierarchies and Competition within the Chinese ICH Transmitters System”,in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Making:Experiences,Negotiations and Contestations,eds.Christina Maags and Marina Svensson (Amsterdam: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and IIAS,2018).Selina Chan,“Mass Participation and Commodific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A Case Study of Quyang’s Stone-Carving Skills in Heibei,China”.Conference Paper at the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of 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Hangzhou,China,(2019).。因此,既有的社会经济权力关系会影响非遗的市场化,但并非决定其市场化。同样,和其他市场一样,拥有“非遗认证”的力量导致了“假冒”非遗产品的市场化。这可能对非遗传承人产生不利影响,因为他们将在一个已经高度专业化的市场中面临更激烈的竞争。正如研究表明,这种竞争不仅在夫子庙等旅游景点显现,还存在于网上,因为在网上更难区分非遗产品的“真”“假”。然而,这种现象也不是由于非遗保护和推广本身造成的,而是许多企业家面临的一个常见的问题,尤其是在奢侈品行业(30)Klaus-Peter Wiedmann and Nadine Hennigs,Luxury Marketing. A Challenge for Theory and Practice.(Wiesbaden:Springer ,2013).。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上升,它更有可能被伪造。
公允地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并不意味着非遗市场化。正如学者们(31)Xiaoyan Su,“R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Modernity,Tourism and Shaolin Martial Arts in the Shaolin Scenic Area,China,”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33:9 (2016):934-950.Yujie Zhu,Heritage and Romantic Consumption in China. (Amsterdam: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and IIAS,2018).指出,市场化可能导致文化实践根据游客需求而改变。如上所述,由于非遗实践和传承人有的被列入名录,有的不被列入,非遗平台可能边缘化那些没有名气和赚钱少的人。不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提高了公众的意识和兴趣,并为文化传承者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来继续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展实践活动,维持生计,即使有些人比其他人受益更多。因此,我们同意苏的观点,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化是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实用途径,但这也导致了不同从业者之间的差异”(32)Xiaoyan Su,“R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Modernity,Tourism and Shaolin Martial Arts in the Shaolin Scenic Area,China,”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33:9 (2016):934-950,945.。在本文中,我们聚焦非遗范式如何以多种方式促使文化实践者参与身边的改革与发展动力,并最终凭借自身权利成为自我经营的生意人。因此,与其他中国人一样,文化从业者也成为了自主经营的个体,他们遵循盈利的逻辑和自我保护的伦理。尽管他们是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运作的,国家依旧会通过法规和国家项目,对非遗进行保护和推广。
五、结论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设想的那样,鉴于非遗保护将非遗市场化视为潜在威胁,那么建立一个非遗体系来培养自主发展、具有商业头脑的文化从业者似乎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宗旨背道而驰。然而,我们的研究表明,情况未必如此。一方面,非遗属于它的“持有者”。如果这是他们的意愿,市场化可能非常符合非遗的精神。另一方面,尽管其后果(传承人之间的竞争、社会的分化、文化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可能与非遗的理想(保护、文化传播、社区凝聚力)形成鲜明反差,但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悖论,不认为理想的遗产与其经济化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也不认为它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种补救或替代,而将非遗制度视为全球新自由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同样,在中国改革时期,体制塑造了特定类型的自治主体。他们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打理自己的经济生活。我们认为,文化从业者也是如此。非遗使文化制度化,将从业者与国家联系起来,并提供了更多市场化的机会,让从业者在保护下实现自我经营。
对非遗实践的批评往往包含当代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结构性社会经济问题。我们需要更加谨慎,不要把政治经济问题、结构性不平等和权力等级制度都归咎于非遗。因为无论有没有非遗,这些问题依旧存在。换句话说,过分看重非遗,并将其视为对现存社会经济问题的一种拯救或弥补,这种想法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