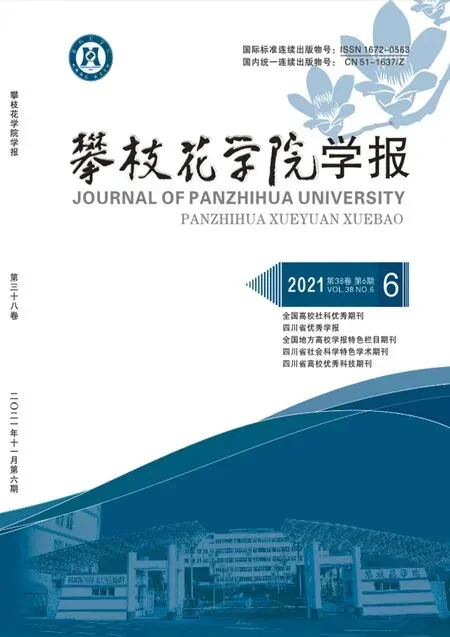未尝一日不燕饮:晏殊词中的名士风流
付佳奥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晏殊“富贵气象”源于吴处厚《青箱杂记》中记载的“公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唯说其气象”[1]46。后人以此论其文学审美与艺术心态,遂成老生常谈。然而,因为这则材料中晏殊自引“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与“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皆属诗例,故论者往往将焦点放在晏殊诗上,而论珠玉词者罕有对词中富贵气象的专门研究,往往从燕子、夕阳等意象出发,分析其生命意识。富贵气象与生命意识二者在晏殊身上关联之紧密,及其在文学史上所延续的脉络,反倒为人所忽视。
富贵气象和晏殊的生命意识是相表里的。安史之乱以来,社会结构和心态均发生转型,至宋初已有了较明显的变化,文人眼中的生命忧患意识亦是如此。晏殊的“富贵”强调“富”而须“贵”,重清闲、燕饮而不重物质享受,是名士风流的一种变转,与他对人生忧乐的理解息息相关,极富时代意味。进而使其词用语富有象征性,反过来促成了“气象”的形成。
一、“富贵气象”是名士风流之变转
晏殊出身不高,但一生仕途较为顺利。早获赏识,真宗每有咨访,“用方寸小纸细书”[2]10196。仁宗即位后,他作为东宫旧僚,更蒙恩宠。晏殊是“平民社会”[3]2中宋代君王重用文官集团政策下推举出来的代表人物,故其词自云“太平无事荷君恩”(《望仙门·玉池波浪碧如鳞》)[4]137。他事君诚谨保守的政治态度和所作内容空洞的寿词、颂词也引起了一定的争议。晏殊词既有“诗意的生命之光”[5],也不乏内容苍白之作,二者之间并非割裂,他的诗词之间亦不可划界而治。统率其创作的正是“富贵气象”。“富贵”是晏殊人生的常态,虽有贬谪,“未尝去王畿五百里”[6]414,但他并不沉溺于物质享受,以节俭闻名,这是论其心态的基点。一言以蔽之,即“处富贵如寒士”[7]193。晏殊处富贵之中,对富贵所保留的这一层距离奠定了他的诗词风格。在此有必要对这一点再做析论。
(一)清雅自如
晏殊处富贵之方式首先表现为“清贵”。学界历来对晏殊事君诚谨保守的态度和他刚简的性格、诗词中的富贵悠游和史载为人之清寒之间所呈现的矛盾存有疑惑。针对前者,邵明珍对他的仕宦经历进行梳理,认为他并非混迹官场的圆滑之徒,务进贤材,促成庆历新政,体现出一种了不起的政治品德[8]。晏殊在高位所展现出来的为人清寒亦与之紧密相关,体现出他政事之外的生活态度。广受征引的一则轶事可以充分地展现这一点:
晏元献为枢密使时,西师未解严。会天雪,陆子履与欧公同谒之。晏置酒西园。欧即席赋诗,有“主人与国同休戚,不惟喜悦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馀万屯边兵”。晏由是衔之,语人曰:“韩愈亦能作言语,作《裴令公宴集》,但云‘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6]294
欧阳修为晏殊所提拔,词风亦相似,但二人从政态度之不同导致了后来改革阵营的分裂。在这则轶事中,欧阳修直言敢谏,较符合现代人对良臣的评价标准,而晏殊所衔则极易受到误解。宋初科举、仕宦之风气仍有唐代的余波,故晏殊援引韩愈为例。裴度和晏殊一样,都面临军国大事的压力,但韩愈并不像欧阳修一样犯颜直谏,这并非二人品性有别,而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对燕集场合的认识有所不同。唐代延续着南北朝以来的政治体系,“清”是极其重要的标准,与“浊”相对。前者取超脱之姿态,而后者偏指对庶务的纠缠。所谓“富贵气象”,其重点在于“贵”而非“富”。“富”是基础,果能超脱,即为“清贵”,富而不贵则沦为“贪浊”,即晏殊所言“乞儿相”。唐代名相张九龄即是这一标准的代言人,晏殊早年受赏识时曾被寇准质疑其出身于江外,而宋真宗即以张九龄亦来自江外反驳之。燕集是体现宰臣清雅自如最重要的行为方式,至韩愈时这一标准虽然已经有所动摇,但仍然有大批拥趸,故韩愈作诗云“钟鼓乐清时”。
这一理念可以回溯至东晋名相谢安。谢安再起东山,也面临着外敌巨大的压力,然而史载其“对客围棋,看书既竟,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徐答云:‘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心甚喜,不觉屐齿之折”[9]2075。这样的矫情镇物为初唐所修史书频繁提及,论人时亦以喜怒不形于色为褒扬语。以谢安此举为风流姿态,则裴度、晏殊之理宜同。归根结底,这是东晋以来的一种常见的执政方式。无独有偶,东晋中兴功臣王导在后世也受到了和晏殊相类似的指责,王导主张的清静为政,被认为是“愦愦”,“看似煌煌一代名臣,其实乃并无一事”[10]591。《梁书》云:“(何)敬容久处台阁,详悉旧事,且聪明识治,勤于簿领,诘朝理事,日旰不休。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敬容独勤庶务,为世所嗤鄙。”[11]532由此可见,“清”的标准自晋以来便有其延续性,就算到了北宋初期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吕蒙正、李沆、王旦身上都能看到它的影子。
安史之乱加快了唐代社会结构的崩溃,经历了唐末五代的战火和劫难,社会发生了大转型,史学界论之已详。在这个背景下,晏殊作为枢密使,面临与西夏的战事,仍有效仿前贤的意识,但他所提拔的后辈们仕宦态度已有所转变,以欧阳修为代表的新兴士大夫阶层正在飞速崛起,勇于表达政治诉求,而晏殊的理念就显得保守起来了。晏殊以神童受擢,虽然不是门阀贵族,却享受了旧时门阀贵族一般的待遇,颇能持重以事君、诗酒以自逸。宋代那些环绕着晏殊、为人耳熟的故事,皆说明他在仕途上十分谨慎,为他赢得良好的政治声名。如沈括《梦溪笔谈》所载“晏元献不隐”:“公语言质野,则曰:‘臣非不乐燕游者,直以贫,无可为之具,臣若有钱亦须往,但无钱不能出耳。’”[12]86又如魏泰《东轩笔录》所载,晏殊虽然位极人臣,但能廉洁自守,以致病卒后坟墓为盗所掘,所见“供设之器,皆陶甓为之,又破其棺,棺中惟木胎金裹带一条,金无数两”“盗失望而恚,遂以刀斧劈碎其骨而出。”[13]78可见,晏殊并未沉溺在“富”字上,而是很快对其进行了超越。他一方面在政治上有相当的作为,一方面却秉承着清寒的生活态度;一方面大量提拔后进,一方面又不满于革新的激进,前后并非不谐。只是随着时代变迁,逐渐难以为后进所理解,因此晏、欧最终不免分道扬镳。
(二)主人心态
“清”理念的主导下,晏殊极好燕饮,却不沉溺于鲜肥美味或声色娱乐。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
晏元宪公虽早富贵,而奉养极约,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但人设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实蔬茹渐至,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数行之后,案上已燦然矣。稍阑,即罢遣歌乐,曰:“汝曹呈艺已遍,吾当呈艺。”乃具笔札相与赋诗,率以为常。前辈风流,未之有比。[14]35
这样的燕饮态度使其词和花间词人以及欧阳修、张先等辈皆有所不同,娱乐性大为降低,故而又衍生出张舜民《画墁录》所载他和柳永之间审美分野的故事。即便在这样的场合,他所好的也是樽酒相对之欢如,是“风骨清羸,不喜肉食,尤嫌肥膻。每读韦应物诗,爱之曰‘全没些脂腻气’”[1]47。燕饮赋诗是晋宋以来文人雅趣的展现,以此对抗人世的代谢,金谷、兰亭之会为人所艳称,至唐人王勃、李白集中,燕饮诗序更是历历可见。晏殊和时人最大的不同,也就是他处富贵之方式的第二个特点,是他的主人心态。
晏殊在罢相之前仕途较为通达,故在文人往来之间常以燕饮主人公身份出现,以此为一生之乐。另一则轶事可供参照:
晏元献早入政府,迨出镇,皆近畿名藩,未尝远去王室。自南都移陈,离席,官奴有歌“千里伤行客”之词。公怒曰:“予生平守官,未尝去王畿五百里。是何千里伤行客也![6]414”
在这场为送别而设的燕饮中,晏殊不免有些反应过度。此事真伪难考,不过和欧阳修宴席上因言致隙相参照,应非偶然。这恰恰反映出晏殊之燕饮,是以“我”为主,作为富贵之主、人生之主,享受宾客往来之趣的燕饮。由此,晏殊对“燕”意象的使用就绝不仅仅是论者所谓春光之象征、时间之载体,而更深一层的含义在于富贵人家的主人心态。以其代表作《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为例,中云“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4]21,为千古名句。这一句除了以花落之无奈与燕返之多情,暗喻生命的有限和无限,引人沉思之外,其实还有一层蕴意。即以“我”为主,亭台为“我”所有,因此燕子年年可以复归。此句又被他用到《示张寺丞王校勘》诗中,云“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游梁赋客多风味,莫惜青钱万选才”[15]74,连用梁园、张鷟两个典故,意思就更为直露了,其徘徊所思的是延赏文章,“燕”所象征的正是宾客燕集。又如“燕子欲归时节,高楼昨夜西风。求得人间成小会,试把金尊傍菊丛”[4]15,燕子之归与人间小会并列为期待之事。《鹊踏枝·槛菊愁烟兰泣露》中云“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4]38,摹写秋景,燕子飞去,反衬自己的孤清,如同他在《蝶恋花·梨叶疏红蝉韵歇》中所说的“谁教社燕轻离别”[4]146,故作怨语,抒发内心的感伤,虽写景物,实寓人事。
晏殊词中燕意象常常与燕饮场景在上下片分举,成为一种惯用结构。如《清平乐·春来秋去》上片云“燕子归飞兰泣露,光景千留不住”,与“槛菊愁烟”语极相似,而下片云“酒阑人散忡忡”[4]48;《采桑子·樱桃谢了梨花发》上片云“燕子归来,几处风帘绣户开”,下片云“且酌金杯”[4]57;《踏莎行·绿树归莺》上片云“绿树归莺,雕梁别燕,春光一去如流电”,下片云“尊中绿醑意中人,花朝月夜长相见”[4]110;《蝶恋花·一霎秋风惊画扇》上片云“珠帘不下留归燕”,下片云“四坐清欢,莫放金杯浅”[4]141。在这些词中,燕子既意味着明媚的春光,也意味着与宾客相聚的欢乐,而词人本身“有我”之姿态分外明显。晏殊为别人作祝寿词时也用此技法,如“杏梁归燕双回首,黄蜀葵花开应候。画堂元是降生辰,玉盏更斟长命酒”[4]84“朱帘细雨,尚迟留归燕。嘉庆日,多少世人良愿”[4]102,这些词中,他则将主人形象暂时过渡到了寿星身上。
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燕意象不仅有象征春光的一面,也有因其生活习性而衍生出来的另一层含义,即衔泥筑巢、寄人檐下,在诗中十分常见。杜甫尤擅发挥,如“可怜处处巢居室,何异飘飘托此身”(《燕子来舟中作》)[16]2498“旅食惊双燕”(《双燕》)[16]1193“焉能作堂上燕,衔泥附炎热”(《去矣行》)[16]302“巢边野雀群欺燕”(《题郑县亭子》)[16]588等等。白居易写燕的诗也很多,《感兴》云“幕上偷安燕燕窠”[17]2427,《晚燕》云“人间事亦尔,不独燕营窠”[17]636,用意在于以燕自戒。纵有“谁家新燕啄春泥”[17]1614之句,也下意识地用了“谁家”二字。刘禹锡“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18]310为千古名句,亦不免乎此。晏殊不仅从不写燕子的可怜之处,且反用刘禹锡诗意作词。他以自身为王谢,自然视堂前帘下的燕子尤为有情,将其质性和明媚的春光融为一体,故其词又云:
东风昨夜回梁苑。日脚依稀添一线。旋开杨柳绿蛾眉,暗拆海棠红粉面。
无情一去云中雁。有意归来梁上燕。有情无意且休论,莫向酒杯容易散。[4]74
此词为晏殊在宋仁宗庆历四年所作,时在汴京,在私第中宴请中书省、枢密院同僚。作此词时晏殊正是一生声望最隆之际,上片写春景见来,光鲜景丽,下片以雁、燕对比,着意以无情、有意相区分,结句虽云“休论”,实际“已论”。座客和作此词,靡然向风,不敢改首句“东风昨夜”四字。杨湜所寻得的当时三阙和词,写的也都是春日丽景,却无一人敢再以燕入词。以此次燕集观之,燕意象所寓意的主人心态是十分明显的。
他的诗作较之于词,有时则流露出更明白的意思,如“谢堂新句入清歌,雨箔风帘有燕过”(《次韵和参政陈给事寒食杜门感怀二首其二》)[19]402,“谢墅林亭汴水滨,偶携佳客共寻春……朝中九列无间暇,愿作新诗赠季伦”(《寒食游王氏城东园林因寄王虞部》)[19]402,“文酒雅宜频燕集,谢家兰玉有新丛”(《留题越州石氏山斋》)[19]398,频繁怀想谢氏风流。然而谢氏所处的时代为门阀贵族时代,“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的理念到了晏殊的时代不能不发生变转,这些芝兰玉树非家族所有,只能延请而来,一如燕之飞入帘幕。因此晏殊语富贵不云金玉锦绣,所自称的诗句中却有“帘幕中间燕子飞”之语。他大量提拔后进,且说“春风不负东君信,遍拆群芳。燕子双双,依旧衔泥入杏梁”[4]54“晚雨微微,待得空梁宿燕归”[4]60,以象征化的语言强调燕子的守信。理解这一点,有助于加深对晏殊“富贵气象”的认识。
综上,晏殊在创作中既以燕子作为欢愉时刻的载体,又进一步强调燕子的有情与守信,实即自矜主人身份,这种处世态度使其在宋初广泛地援引后学,与之燕饮欢如,视为幕中客。而他或许也隐隐地感知到时代不同,这种主人身份是不可久居的,在词中不免流露出“山长水阔知何处”式的伤感和怅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晏殊的“富贵气象”,实即名士风流在新型社会结构中的一种变转。
二、生命忧患意识的转型和晏殊词中忧乐
经历了中唐北宋社会结构的转型,缺乏门阀世代相传的根基,晏殊所怀想的风流变得难以长久。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晏殊虽然广泛地提拔后进,但其影响力到晏几道入狱时已消亡殆尽。人生的有限在宋初再一次成为了文学作品的经典命题,和宴饮密切相关的词体反映尤多,晏殊亦为这浪潮中的代表人物。
自汉魏以来,对人生苦短的歌咏极繁。无论是《薤露》之歌,还是曹操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短歌行》)[20]349、曹植的“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赠白马王彪》)[20]454、阮籍的“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咏怀诗八十二首其三》)[20]497,均对此持以无可奈何的态度。于是在魏晋时代,药、酒、玄言流行一时。“痛饮酒,熟读离骚”成为了对抗时间的方式,前者指向燕饮,后者指向文学创作,金谷、兰亭之会适得其时。面临沉甸甸的死亡,只有俯仰宇宙之间,留下自己的文字,才能超越时空。唐代安史之乱爆发后,生命之忧患再度如狂澜般席卷而来,大历诗人重发忧生之嗟。例如大历十才子中的李端,少年扬名,但一生都在和时间抗争,由道入儒,由儒又转向释家寻求帮助,然而均无所获,只能作诗寄给引导他学佛的畅当、晚年所师从的名僧皎然抒发自己的内心感伤。底层民众遭受着更大的痛苦,托名王梵志的诗中更出现了对生命的质疑之声:“我昔未生时,冥冥无所知。天公强生我,生我复何为?无衣使我寒,无食使我饥。还你天公我,还我未生时。”[21]729王梵志诗中关于生死的理解较之文人更为直露,以《虚霑一百年》《人生一代间》为题的就有多首,《身如破皮袋》《身如内架堂》《此身如馆舍》等诗也反映出时人对“世无百年人”人身物质性的认识,人生忧患成为了底层人民最关心的话题。原本生命的困境在于有限,而到这个时段,有限的生命也成为了负担,左冲右突而不能出,等待着普遍意义上的信仰重构。
白居易是扭转颓波的关键人物。他面对这种困境一开始也常怀忧生之嗟,对个人形貌的变化甚是在意,感叹“万病皆可治,唯无治老药”(《叹老三首其一》,)[17]517。衣若芬在研究白居易写真诗、对镜诗时便指出他自三十四岁作《感时》诗即已忧心自己的身体,此后反复以诗来记叙自我形象的转变。然而,白居易或许也没有想到自己年寿颇永,晚年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转,“用‘喜老’试图淡化或消解‘老’所伴随的疾病、所暗示的死亡”[22],是“我今幸得见头白,禄俸不薄官不卑。眼前有酒心无苦,只合欢娱不合悲”(《对镜吟》)[17]1420。白居易的“喜老”虽然建立在他从容中隐的基础上,但并不强调金玉锦绣的物质享受,而注重从享受有限时光的角度打破老来之嗟,也就和《代悲白头翁》等诗中反映出来的“苦老”传统完全不同。他的态度极大地影响了经历唐末五代的离乱、入宋之后得到重用的士大夫,“白体”流行一时。会昌年间,白居易等九老于白家聚会,共同赋诗为乐。此事为宋初文人广效之,如“吴兴六老会”“吴郡十老会”“睢阳五老会”等等。这说明在诗歌和行动上效仿白居易,成为宋初文士对抗时间,打破人生如寄、成为生命之主的一种普遍方式。
在白体诗人之外,邵雍也以他富有理趣的诗增添了“喜老”在平凡生活中的意味。不仅作《年老逢春十三首》,以组诗的形式将老与春之间的隔阂打通,其诗又云:“况复筋骸粗康健,那堪时节正芳菲。酒涵花影红光溜,争忍花前不醉归”(《插花吟》)[23]148-149。邵雍认为人生的有限已是定数,在他眼中虚过百年犹如未生,这就将重心由增加生命的长度或是寻求来生的寄托,彻底转向了对有限时光的珍视,肯定个体生命的价值,“若无人之情,徒有人之形”(《人灵吟》)[23]296,“照临之间,不忧则喜。予何人哉?欢喜不已”(《欢喜吟》)[23]189。邵雍对生命的思考比白居易更上一层楼。白居易“喜老”的基础是其个人悠游之晚年,而邵雍则将其推广至时代的太平,只要天下无事,便足可“吾生独何幸,卧看洛阳春”(《举世吟》)[23]161了。
晏殊词正和邵雍诗处在同一平面上。晏殊词得之于花间、南唐,处于太平之世,在生命意识上有鲜明的宋初痕迹。无可否认,宋初词人对生命的认识仍有其局限性,但也应注意到,他们的欢歌盛宴不是简单地对悲剧进行淡化,而是在有限的条件下充分享受人生之春天。在白居易重新发现有限人生的快乐之后,享乐的外部条件在数代人的思索中一步步降低,降低到“孔颜乐处”,实际上已无需任何外部的要求,人生之乐既不是年轻人的专属,也不是富贵者的财产,甚至是否太平也不必强调了。晏殊词中所流露出来的哲思尚未达到融通的境地,未能抛却快乐的外部条件,却也因其理性与感性并存、令词短小留有余地而更具诗意。
燕饮与“喜老”相结合,就有了《谒金门·秋露坠》中所说的“人貌老于前岁,风月宛然无异。座有嘉宾尊有桂,莫辞终夕醉”。[4]13虽言时光飞逝,此词用语并不悲凉,“座有嘉宾”句,可由曹操《短歌行》远绍《诗》中《鹿鸣》《子衿》二篇,意蕴更深。然而,佳筵易散,待燕饮散去,仍会如《清平乐·春来秋去》中那样生出忧患之感:“酒阑人散忡忡,闲阶独倚梧桐。记得去年今日,依前黄叶西风。”[4]49他在四季循环中感到惆怅的不是年龄的老去,而是燕饮的散场。宴会过后的空虚感正衬托出词人对于生命的多情。晏殊词每言黄叶、西风、鸿雁等秋景,皆有所寓意,如其著名词句“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便被王国维认为是“悲壮”和“忧生”。写秋景的两首《诉衷情》,一云重阳将近,“凭高目断,鸿雁来时,无限思量”(《诉衷情·芙蓉金菊斗馨香》)[4]94,一云人散之后,“谢娘愁卧,潘令闲眠,心事无穷”(《诉衷情·数枝金菊对芙蓉》)[4]95,皆由自然景物的变迁过渡为人聚还散的离别。晏殊所期待的并不是人生沉浮之间的再度得意,而是系之于一生的“有情”,故其词云“当歌对酒莫沉吟,人生有限情无限”(《踏莎行·绿树啼莺》)[4]109。更进一步地说,在放弃了关于生命无限的幻想、充分认识到悲欢祸福之相倚之后,人们才真正意义上成为了生命的主人,才更懂得珍视生命的价值。从这个角度上说,晏殊词也在享乐之外提升了词体的格调。这里不妨以他的一首《蝶恋花》为代表:
南雁依稀回侧阵,雪霁墙阴,偏觉兰芽嫩。中夜梦余消酒困,炉香卷穗灯生晕。
急景流年都一瞬,往事前欢,未免萦方寸。腊后花期知渐近,寒梅已作东风信。[4]147-148
这首词写冬景,也写急景流年中对往事的追忆,但从冬景中看出兰芽的萌发,从寒梅看出东风的渐近,和雪莱《西风颂》异曲同工。晏殊常哀伤春天的远去,在秋冬之际却不过分沉浸在萧瑟之中,而能看到春天的到来,这是他目光的长处。
这种心态当然也有它的条件,即前述清贵之生活。人生遭际的有情与无情并不见得一直保持四季一般的规律。晏殊对此也有所感触,如“梧桐昨夜西风急,淡月胧明。好梦频惊,何处高楼雁一声”(《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4]59,同样写昨夜西风,和“独上高楼”句相较,更隐隐暗示出心中对变故的忧患。在这种忧患之中,自己所援引的后进和平时聚集的宾客,这些春天里守信而又多情的燕子,是他所倚仗的后盾。当他们彼此出现矛盾的时候,晏殊很快就被罢相了。
今天评价晏殊其人,应充分考虑安史之乱以来社会心理的变化和宋初文人对生命问题的反思。在这样的背景下,晏殊对富贵、生命的体认,对宾客、风流的向往,也就有值得沉思之处,而不是对前代忧生传统简单的复写或富贵人生中的无病呻吟。他所着意描写的四季循环、歌筵舞席中的种种意象,也因此有了丰富的象征意味,反过来衬托他富贵悠游、享受人生的心态,共同促进了“富贵气象”在多个维度上的塑成。
无论是“东风昨夜回梁苑”,还是“昨夜西风凋碧树”,晏殊皆以自我的眼光,审视自我的生命,有着自我的期待。因此,他以清自守,处富贵如寒士,却有着主人心态,好宾客而日日燕饮,以此来实现建功立业外的生命之乐。词不能涵盖晏殊创作的全貌,但却能充分地展示他的名士风流,他的词和为人之间并无矛盾割裂之处。
同时,他的语言得之于冯延巳而又对其进行了个人化的改造,使其措词充满象征意味,有助于“气象”的生成。这一点也被宋初词人所继承。写富贵而不言金玉锦绣只是晏殊词的一重相,他写宾客往来却就春光燕子细细写去,写人生盛衰也只以自然物象拟之,绝无对即席所见的觥筹歌舞之铺陈,而将其提炼为切挈高妙、渣滓尽去之话,雅而不欲,有风流蕴藉的整体风貌。因此,非富非贵的读者也能够从晏殊词中得到相关“富贵气象”的共鸣,因为人人都是生命的主人,都曾拥有生命的春天,并拭图用回忆、聚会、饮酒、写作等方式将其留住或延长。欧阳修曾有和晏殊一样的感触:“游人散尽笙歌去,始觉春空。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24]4-5“归来恰似辽东鹤……谁识当年旧主人”(《采桑子·平生为爱西湖好》)[24]9。时移世变,晏几道也曾道“从今屈指春期近,莫使金尊对月空”(《鹧鸪天·晓日迎长岁岁同》)[4]329,但后来不免说“罗幕香中燕未还”(《鹧鸪天·一醉醒来春又残》)[4]313,只能反主为客,以“梦魂”踏过“谢桥”,向人寻去。秦观“郴江幸自”之词,苏轼“缥缈孤鸿”“一蓑烟雨”等句,虽性情不同,语言上均受此沾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