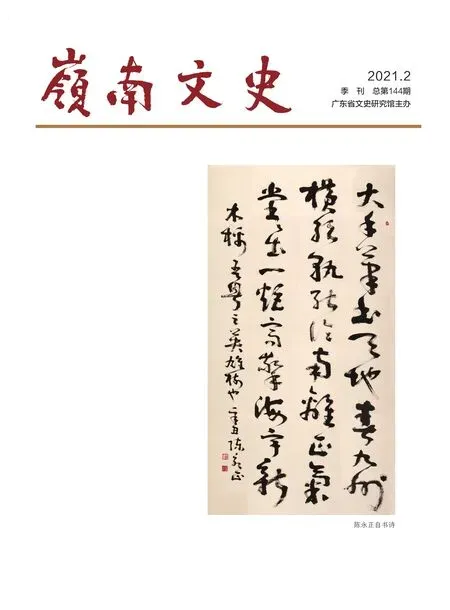读朱光文《番禺蓼涌四村历史文化论集》
李 博
《区域社会的结构过程——番禺蓼涌四村历史文化论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0)由广州市番禺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朱光文著。内容主要涉及今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板桥、南村、市头、罗边四村的历史,是朱光文先生对番禺暨珠江三角洲镇村历史文化细化研究的最新成果。作者在此领域已耕耘多年,先后出版了《番禺文化遗产研究》(2011)、《番禺历史文化概论》(主撰,2017)两部概论性著作,《名乡坑头:历史、社会与文化》(主撰,2013)、《省会海门番禺名镇——石楼地区历史、社会与文化》(2017)两部镇村研究著作,发表论文多篇。
一、主要内容评述
全书分导论,上篇、下篇及附录四部分。上篇为区域内四村的个案研究;下篇为三个专题研究,最后以南村邬氏宗族家训、重要人物小传,今南村镇范围内主要宗族的科第职官表,和有关海云寺、员岗崔氏宗族的三篇论文,以及坑头村历史文化概述等为附录。在导论部分,作者即首先指出蓼涌区域的地理环境基础——珠江后航道(沥滘水道)的最大支流。这一基础赋予该区域独特的交通枢纽地位,北宋时即曾设“蓼涌渡”,之后随着村落的发展、经济社会活动的展开,以及今日仍然兴盛的民间诞会、仪式信仰等,均由此演生而来。
上篇四村四论。第一篇主要探讨板桥村黎氏宗族从明中期黎瞻取得功名之后至清末,其祖先谱系不断被塑造、凸显的过程,尤其是其女性祖先黎道娘形象的“正统化”,以及抗清志士黎遂球由清初遗民记录,至清中期逐渐进入官修志书,最终以“黄牡丹状元”的文学形象被推举为岭南先贤之一的经过。第二篇主要关注南村邬氏宗族的发展与整合、祠堂营建与改作、里坊聚落演变的过程。无论是祖先谱系的梳理,还是祠堂的营建,固然包含了后世子孙维护和壮大宗族的努力,但其背后还有更重要或者说更深层的因素——这些物质和文化层面的建构,往往是特定时期经济、政治诉求的手段。刘志伟教授的开拓性研究即表明,番禺沙湾何族对祖先谱系的梳理,对珠三角普遍流传的珠玑巷移民传说的附会,背后就是明清时期何氏开发并掌握了大规模沙田,作为控产机构的何氏宗族进行自我整合以及与小榄何氏等开展区域间宗族联盟的需求。[1]本书关注的南村邬氏宗族的兴起,即与邬鸣谦在清嘉庆年间(1796-1820)开始参与沙田开发有关。其后邬氏家族财富不断积累,在咸丰年间(1851-1861)的太平天国运动中,更是积极参与团练运动,成为地方事务的主持者,至民国年间邬氏仍为南村首富。
第三篇则主要呈现市头村作为龙舟活动“市头景”所在地,其龙舟活动中神明崇拜、龙船会组织、探亲交流背后的经济、社会、历史内涵,也关注到改革开放后传统复兴过程中,宗族组织、华侨和港澳同胞、政府、企业起到的作用及其对“传统”本身的影响。龙舟活动中的村落、组织关系,背后是该区域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所依存的水运网络,也涉及一些宗族关系等问题,与陆上乡村诞会中的村落联盟并不重合。[2]第四篇以罗边村清末富商罗镜泉对教育的重视以及取得的硕果为基点,挖掘了元代以后罗氏家族的家族建构与教育教化史。除经济实力的壮大外,家族教育对宗族延续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在传统社会,获得功名的官绅群体往往是宗族整合、谱系建构的重要推手。而清末以后,罗镜泉家族更是以其后代的教育成就,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番禺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乡村建设运动,这也是罗氏大族地位得以维系的重要原因。
上篇的写作方法,四篇论文都以历时的方式展开,其所关注的重点是村落的形成、宗族发展和文化建构、今存遗迹及仪式等环节。另外,四村的研究各聚焦一个侧面,分别关注乡村宗族的文化表征、诞会活动的物质基础以及维系宗族延续的重要因素等内容。四篇文章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关怀,就是该地区乡村社会的历史变迁问题。作者试图通过对每一个案不同侧面的讨论,达到“互文见义”的效果,以构成蓼涌地区村落、宗族、文化发展的全貌。
下篇以该区域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关键问题为切入点,探讨清末团练组织与地方社会、民间诞会与社会变迁、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三个问题。美国汉学家魏斐德早在20世纪60年代即曾揭示,清末广州及附近地区的团练运动是影响广东、中国近代史进程的重要因素,也由此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他在《大门口的陌生人》一书中还热情呼吁:“让我们致力于地方史的研究吧。”[3]本部分第一篇文章所关注的蓼涌乃至番禺沙茭地区的团练运动,其实也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是它的延续。在研究视角上,某种程度上也是其细化和深化。清咸丰年间(1851-1861)团练运动的兴起,建立在地方宗族掌握巨大财力的基础上,也是官府给予团练组织合法地位的结果。有组织的团练,在基层以社学、书院的形式发展,逐渐成为华南社会实际上的基层权力机构,这也是至今乡村诞会活动中仍可见到的“五乡会”“十乡会”等村落联盟的历史基础(参见本书第174-176页《社庙与村落联盟表》)。而第二篇紧接着讨论这些村落联盟在民间诞会中的作用,其实也是通过诞会中祭祀、巡游等仪式表征的变化,探讨该地区社会变动、权力重组的过程。作者尝试证明,“东山社”祭祀主神从南海神到北帝的变化,其实也是板桥黎氏在地方的影响力逐渐被南村邬氏取代的过程。而更大范围的北帝诞会巡游和联谊,正是从清咸同年间至民国年间历次地方动乱(包括宗族械斗、盗寇威胁及后来的日伪统治等)中,该地区各村落之间御寇联防的结果。这一过程也可以从当地流传的不同时期北帝显灵的传说得到验证。第三篇主要关注20世纪30年代陈济棠治粤时期设立的番禺“模范县”及“蓼涌民众教育试验区”的问题,其中也可以看到四村借原有资源在这一运动中起到的不同作用。
就目前研究而言,专论中所涉及的诸如地方团练运动等问题的研究不可谓不多,也已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但本书的特色在于,作者始终坚持地方视角,努力从地方社会具体的历时变化入手,将地区、国家层面的重大事件与乡村的社会、文化变动相结合研究。其目的就在于揭示乡民们是如何从具体的利益、诉求出发,面对具体的问题,利用宗族组织、村落联盟等手段,维护其所处的乡村、地区秩序的。而今天仍然存续于民间诞会等活动中的仪式关系,正是这些特定阶段历史事件的遗留,其背后隐藏着地区、国家的历史。如此展开研究,相当于赋予我们所习闻的框架式、粗线条的历史叙述以筋骨血肉,使之更加充盈、具体,其实也正与刘志伟教授曾提倡的“人的历史”的理念若合符节,即“我们的历史分析以人作为逻辑出发点,那么在人的行为之上,有或强或弱的国家权力存在,有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还有不同形式的法律制度等东西,都要进入我们的视野,从而得以由人的能动性去解释历史活动和历史过程。”[4]
在史料上,除政府文书、地方史志外,本书也利用了大量族谱、碑刻文献及田野访谈材料、地方耆老的回忆文字等,也吸收了学界关于各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在上篇、下篇七篇论文中均有体现。作者善于结合方志与各种地方文献,梳理揭示地方历史文化变迁的过程及其文化建构。如对板桥黎氏祖先谱系的建构、龙舟活动的社会历史背景的讨论等,多有精彩之处。
二、价值和问题
本书的价值与存在的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讨论。
首先,本书作为一部“村史”。现阶段的村志、村史编纂者,一般为本地耆老或外聘团队,前者熟悉乡村情况,但多未受过系统的史学训练,编修质量难以保证;后者具备专业知识,但往往对乡村并不熟悉,容易出现“隔靴搔痒”的问题。[5]而本书作者不仅史学科班出身,且长期从事珠三角历史文化研究,还承担着番禺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相较于一般的学院研究者有较大的资料和田野调查经验优势。书中除方志、族谱外,使用了大量碑刻、访谈材料,都是作者一次次普查、访谈的成果。在对地方的熟悉程度上,作者也不逊于乡村耆老,在某些方面的资料掌握上甚至可以说超越了当地人。[6]但本书意图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尝试探索乡村史志书写的新模式。如作者曾在《名乡坑头》中所坦言的那样:“我们尝试借鉴长时段、总体史的史学理念,去重构坑头村及周边地区的区域乡村社会文化史,书写一部新型的乡村志书……看到禺南地区区域社会历史演变的缩影。”[7]也就是说,面对乡村,我们看到的不应只是乡民引以为豪的祖先故事、祠堂建筑和仪式场面,也不只是作为广府城市地区发展史的附属,而是至今仍然生生不息的宗族、人群生存繁衍、经济开发、文化创造的历程。在城市化高歌猛进的今天,这种研究的意义不可谓不重要。不然,将来的人们可能很难想象,在城市高楼夹缝中的青砖祠堂、简陋小庙,端午节锣鼓喧天的龙船景,以及带着“村气”的地铁站站名等这些彰显的物质、文化符号背后所蕴含着何种意义。
但是,就“村史”而言,笔者认为仍有必要区分“村志”与“研究”两种意义的村史。前者重在存史,同时蕴含着当地村民的乡土情感和自豪感,以及行政指导下的“教化”意义,是一种历史记录;而后者旨在梳理村落形成、社会文化演变的过程,是对村落发展史的梳理和总结,是一种历史认识。二者不相同,也并不冲突。本书显然更偏向后者,主体部分上、下篇即属后者,但同时也在努力兼顾前者,试图使两者互相补充证明,融为一体。那么,如果可以增加附录内容,将与该地相关的史料,重要者、不经见者全文收录,单行易得者著录并撰解题,以便读者“按图索骥”,当会大大增强附录的意义。
其次,“区域研究”与其说是针对某个特定区域的研究,不如说是以“区域”为视角的研究。无论研究对象是村落、流域、政区或者其他,都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将研究对象放在区域联系中进行考察。如著中所言:“作为一个小流域或村落群的蓼涌区域,是一个既相对稳定,对(又)动态开放的空间……蓼涌的历史可以是大谷围、番禺县、珠三角乃至岭南社会的一部分,也可以是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乃至)全球史、世界史的一部分。”[8]这一点并不夸张。蓼涌先贤在维护番禺的地方稳定、经济发展方面曾发挥重要作用,也曾参与近代以后的留学运动、国际贸易。在这一意义上,本书上编的“个案”也是区域研究,下编定名为“区域”就显得多余。它实际上是以蓼涌流域或更大范围的专题研究,定为“专题”或更恰当。
而另一方面,本研究也是一项历史人类学研究。题目中“结构过程”一词,即刘志伟教授对萧凤霞教授提出的“structuring”一词的翻译,意即个人在历史或社会中不断创造关系和意义的网络(结构)又受其影响的永无止境的过程。[9]程美宝教授也曾指出,区域史研究“在于明白过去的人怎样划分,在于明白这段‘划分’的历史”,其实也是这一意思。[10]作者细致关注蓼涌宗族族谱编纂、祠堂营建、神明崇拜的变迁过程,其所关怀的,实际上就是在这些乡村社会文化建构活动背后,蓼涌、番禺乃至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社会变迁的历史。通过作者对这四个村落及所在区域的细致研究,人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明清以后珠江三角洲的历史,了解今日所见社会、文化现象从何而来。而专题研究中清末盗乱中“盗匪”与地方宗族的关系、民国蓼涌民众教育试验区等问题的探讨似仍有继续深入的空间。
最后,本书每篇之后都配有图片,使读者在文字论述之外,可以直观地了解该地区的聚落形态、建筑风貌、仪式场景等,是一大优点。但美中不足的是,由于过于追求齐整,其中的地图与其他图片按同一规格排列,导致很多内容细节难以辨识。如导论中所附清末至20世纪40年代蓼涌流域地图(第16页),对理解前文所述蓼涌地区时空变迁非常重要,应适当加大排印尺寸。而一些呈现村落风貌、仪式现场的照片,则可在保证相当清晰度的前提下加以压缩。另外,书中引文偶有标点错讹,再版时可以加以改进。
总体上本书是一部“解剖麻雀”之作,为人们了解珠江三角洲地区历史时期、特别是明清以后乡村社会的变迁提供了一个“显微镜式”的窗口,也为珠三角乃至中国乡村社会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对话的样本。朱光文先生从事番禺暨珠三角历史文化研究近二十年,不仅情感所系,用力深勤,也在不断地尝试新的研究视角,从聚落、建筑、文化旅游、乡村社会史,到历史人类学、区域史,本书可谓其多年精耕细作的成果,期待朱先生未来有更多创获。
注释:
[1] 参见刘志伟:《祖先谱系的重构及其意义——珠江三角洲一个宗族的个案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第18-30页;刘志伟:《宗族与沙田开发——番禺何族的个案研究》,《中国农史》1992年第4期,第34-41页。
[2] 作者也曾专文讨论沙湾司龙舟习俗与当地砖瓦业生产所依存的市桥水道水运网络之间的关系。参见朱光文:《水运社会的地方文化网络——以宋以来广州府番禺县沙湾司砖瓦业和龙船习俗为中心的考察》,《历史人类学学刊》第16卷第2期,2018年10月,第43-92页。
[3] [美]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王小荷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6页,1988。
[4] 刘志伟、孙歌:《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上海:东方出版中心,第21-28页,2016。
[5] 张丽蓉:《改革开放以来村志编修的分析与思考——以广州地区为中心》,《中国地方志》2016年第10期,第32-38页。
[6] 朱光文先生曾编纂《南村人文读本》(后改为《南山记忆——南村镇历史文化通识读本》)、《禺山记忆——番禺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识读本》等针对中小学的乡土读本,实际上也亲身参与了当地乡村记忆的保护与传承。
[7] 朱光文、陈铭新:《名乡坑头:历史、社会与文化》。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第230-232页,2013。
[8] 朱光文:《区域社会的结构过程——番禺蓼涌四村历史文化论集》(《番禺文史》第二十九期)。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第12页,2020。
[9] 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54页。
[10] 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31页,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