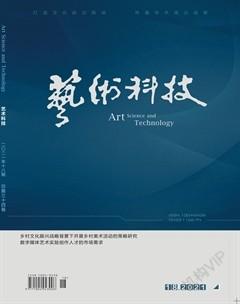《论语》“性相近,习相远”中“性”“习”二字探微
摘要:《论语》阳货篇中“性相近,习相远”一句历来注解众多,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句中“性”“习”二字的理解不一,各执己见。大多数学者对此句的注释都集中在“性相近”上,难免会陷于释“性”的泥潭,而遗忘了澄清“性”与“习”二字关系才是该句的最终指归。文章立足《论语》文本,以此章为核心,对流行的注释逐一分析与评述,再基于诠释史的角度对“性”“习”二字进行深入探讨。从字源意义着手探明“性”“习”二字的真实原意,并采取语义学分析及以经解经的研究方法深掘孔子赋予“性”与“习”的真实关系。
关键词:《论语》;“性”;“习”;诠释
中图分类号:B2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8-0-03
1 “性相近,习相远”历代注释梳理
《论语》阳货篇中“性相近,习相远”句是我们理解“性”“习”二字关系的重要途径。然而孔子之后的学者对“性相近,习相远”的注释众说纷纭,说法不一。在众多的注释学者中,代表人物主要有范宁、王弼、朱熹等人。文章分析这几位学者对此句的注释,以期在众多学者的诠释基础上找到一种既能与孔子本人思想相契合又能在当今具有较强生命力和较高价值的新诠释。
范宁在《论语注》中言:“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斯相近也。习洙泗之教为君子,习申商之术为小人,其相远也。”在范宁看来,生而好静是人人都具有的天性,性不仅有静的一面,还有感物而动的一面。在“人生而静”的一面大体相同,在“感物而动”的一面具有差异性,所以说“性相近”。然而范宁认为人们选择的所习之术并无好坏之分,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选择学习“洙泗之教”的可能成为仁人君子,选择学习“申商之术”的可能成为小人。因所习内容的不同造就人们不同的人格与价值观,故言“习相远”。然而范宁并没有指出后天所习造成的“相远”与人性“相近”之间有什么联系,对造成“习相远”的具体过程也略过不谈,所以范宁对“性相近,习相远”也只是一种较粗浅的注释。
王弼在《论语释疑》中以“静”界定“性”。“不性其性,焉能久行其正,此是性之正也。若心好流荡失真,此是性之邪也。若以情近性,故云性其情。情近性者,何妨是有欲。若逐欲迁,故云‘远也。若欲而不迁,故曰‘近。但近性者正,而即性非正;虽即性非正,而能使之正,譬如近火者热,而即火非热;虽即火非热,而能使之热。能使之热者,气也,热也。能使之正者,仪也,静也。又知其有浓薄者,孔子曰‘性相近也。若全同也,‘相近之辞不生;若全异也,‘相近之辞亦不得立。今云‘近者,有同有異。取其共是无善无恶则同也,有浓有薄则异也,虽异而未相远,故‘近也。”[1]王弼通过性之“浓薄”来注释“性相近”的问题,但其对“习相远”的注释仅有一言:“若以情近性,故云性其情。情近性者,何妨是有欲。若逐欲迁,故云‘远也。”蒋壮力先生对此有独特见解:“如果说王弼是把心感物而萌动称为情,心随物流荡称为欲,那么‘情与‘欲付诸行动则称为‘习,亦即王弼所说的‘迁。‘情离性尚近,‘欲离性也不太远,若欲而不迁终究离性不远而为‘正,在所习之事上就不能称为‘恶。若身‘逐欲迁即付诸行动,那么‘欲即便离性很近,所习之事也不能称为‘善。即行为之善恶源于情欲之正邪,‘习在两者转化中起关键作用。”[2]笔者也认同此观点,“习”不仅能够改变我们对世间万物的态度和看法,更重要的是“习”对个人主观将情欲转化为行为之善恶有很重要的作用。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其有如此诠释:“此所谓性,兼气质而言者也。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则皆不甚相远也。但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于是始相远耳。程子曰:‘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则性即是理,理无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3]朱熹把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他指出孔子所言之性既非纯善的天命之性,也不全然是气质之性,而是“兼气质而言”,既有天命之性亦有气质之性,即孔子所言之性必是两者共同存在的状态。他认为气质之性固然有美恶之不同,但于最原初的“性”而言,则皆不甚相远也。人人都有天命之性,因气质不同故而可说“性相远”。但朱熹的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一旦出现混合,就不好谈及“性相近”问题。
综上可知,第一,各家在注释“性相近,习相远”时并没有真正落到“性”“习”二字上,也没有将其放到《论语》文本的真实语境中考量;第二,注释“性相近,习相远”时,他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释“性”上,而忽略了“习”的重要性;第三,在注释“性相近,习相远”时,要么只抓住“性”相近的问题,要么只抓住“习”相远的问题,对“性相近”与“习相远”之间的联系却略而不表;第四,注释“性”的过程中要么使用“气”或“天理”来言性,要么使用“善”来描绘性或者以“静”来界定性;第五,注释“性相近,习相远”时大多以孟子性善论为理论背景来言说,因此难免会陷入单一局面,然而孔子所言之性,并没有指明是善是恶,全是后世学者根据自己所学赋予“性”字个人解释,最终偏离了“性”的真正内涵。
2 从字源意义上探讨“性”“习”二字的内涵
《论语集释》有言:“性者,生也。情者,成也。性是生而有之,故曰生也。”由此可见,“性”字是由“生”字衍生而来的,若想知道“性”字的实际内涵,必须追溯到“生”字。然而对于生字,往往会理解其为“生长”或“生生不息”之意。“生”字从产生之时,人们便将其定位为生长,随着时代的演变逐渐变成含有生存的状态的指称,其中包含了生命、生存的本能和欲望等含义。在春秋时代关于人的定义问题中,慢慢延伸出“性”字问题,“性”用以指称人本身的存在,或者存在者的实质及趋向,甚至还指称“人”本身的存在意义问题,也与当时所处的时代有关。由此可见,“性”字应是从“生”字衍生而来,亦可说“性”字和“生”字的意义一样,或者说“性”字中包含“生”字。那么从字源意义上来看,“性”字是否也具有“生”字相关的特性呢?
从字源的角度说“性”字是从“生”字衍生出来的,这是大家认同的。然而“性”字具有特指含义,必在“生”字的所有指称中有其专门意义,此处不能不加以注意。然“性”之为义,自是指与“生”具来者也。实际上就是说,从“生”的意义上来看,人人共具最基本的东西就是“性”,因而言“性相近”,相近者是从本质上而言的,在量上则各有不同。人的本性是具备生命力的、创造力的、向上提升能力的。正如《礼记·中庸》所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荀子·正名》篇亦有记载:“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可见性的本质:心生为性。
关于“习”字,《说文》曰:“习,数飞也。”本义为鸟多次飞翔。《论语》中“习”为其引申之义,指人与外界事物之间频繁的实践活动。康有为先生有言:“习有本于家庭,习有由于师友,习有因于习俗,习有生于国土。或一人一时之习,或数千万里数千万年之习,熏染既成,相去遂远,乃至居行好尚亦复是非悬反者。”[4]康氏此语中的“习”有熏习之意,有助于我们真实理解“习相远”的真实内涵。“孔子但言性相近,意在于警人慎习,非因论性而发,故不必直断以善与”,由此可见,孔子所言之“性相近”并不是让后人着“性”字研究,而是着“习”字研究,“性相近”意在告诫我们要慎习。不要在“性相近”的“性”字上下功夫,而应该转变思路,向“习相远”的“习”字深入,进而真正弄懂孔子赋予“性相近,习相远”的真实含义。人与人天生本没有差别,全因个人后天所习及所习态度不同,进而有不同的人生进路、个人关怀。
3 以语义学和以经解经的方式探析“性”“习”二字的关系
首先可通过语义学对“性”“习”二字进行词性分析,进而弄懂“性”“习”二字的关系。然而纵观《论语》全篇,对“性”“习”二字的谈论较少,孔子更是不直接言“性”。因而对“性”“习”关系的探析只能落到“近”“远”二字之上。对于“近”“远”二字的词性问题,学界也有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近”和“远”两字应为形容词。因人性本初都无任何分别,故相近;然而后天的习或者习染造成不同的状况发生,也就是习相远。也有学者认为“近”和“远”两字应为动词,即将“近”释为使……亲近;“远”释为使……疏远。这样就有两种解释:其一,“性”使人与人相互亲近,“习”使人与人相互疏远;其二,性使人与道亲近,习使人与道疏远。这样就避开谈“性”“习”的问题,只把重心放在“近”和“远”二字上。笔者也比较认同这种方法,这样会减少很多主观臆想,直接从“近”和“远”的语义出发判定“性”与“习”的关系。
“近”字在《论语》中出现共有九处,《论语》文本中也有两处间接将字译为“近”的意思。其一,四处“近”字表示程度上无限接近,如《论语·学而》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论语·子路》子曰:“刚毅、木讷,近仁。”《论语·泰伯》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论语·子张》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其二,两处“近”字表现地理位置的接近,如《论语·子路》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论语·季氏》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其三,三处“近”字表现时空上接近,如《论语·雍也》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卫灵公》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阳货》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其四,两处其意训为“近”的含义,如《论语·先进》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学而》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将“庶”与“亲”字都训为“近”之义,其中提到“庶,近也,言近道也”“亲,近也”。
“习”字在《论语》中出现三次。《论语·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般人通常会把“习”字理解成“温习”“实习”,但最恰当的解释应为“实践”“践行”之义。杨伯峻先生认为:“此处的‘习更应理解为‘演习‘实习之意,因孔子当时所讲的功课,一般都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和平民生活密切相关,像礼、乐、射、御必须要有演习才可得之,所学必要有所习。”[5]《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习”字有醒悟践习的含义,所传必要有所习。
也可通过“以经解经”的方式弄清“性”“习”二字的关系。《易经·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6]阴阳之道造就世间万物的存在,无论如何,总会有以下三种情况出现:阴阳平衡、阴多阳少、阳多阴少。只要事物都是由阴阳构成并存在于天地之间,就一定会有此三种情况发生,必定会出现“性相近”的情况。如果出现阴多阳少或者阳多阴少,则与孔子的“习相远”相通。《中庸》中“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7]与郭沂先生的《性自命出》校释“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相对应,但两者各自描述的“性”的内涵有所不同。前者谓“喜怒哀悲之气,性也”,此性显然是气质之性;后者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性”是“道”的来源,无疑属于义理之性[8]。大戴礼记曰:“分于道之谓命,形于一之谓性。”由于大家都是听取同一天命,然而每个人接受的天命不一,按照天命行事形成的性就不一样,故而言之“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4 结语
历代学者对“性相近,习相远”的诠释都没有抓住此句的重心,大部分学者都是抓住“性”字进行深入探讨,从而陷入研究人性论的泥潭。然而受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两种不同路向的人性论的影响,就与此句原意产生偏差,不能得孔子之真义。应通过对“性”“习”二字字源意义的分析得其真实内涵,利用语义学和以经解经的方式弄清“性”“习”二字的真实关系,即《反身录》所言“习能移性,亦能复性”。
参考文献:
[1] 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9:1522-1523.
[2] 蒋壮力.对“性相近,习相远”的一种新诠释[J].文化研究,2011(2):161-162.
[3]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176.
[4] 康有为.论语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258.
[5] 杨伯骏.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6:3-4.
[6] 王弼.周易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236.
[7] 王国轩.中庸[M].北京:中华书局,2016:56.
[8] 郭沂.性自命出[J].管子学刊,2014(4):99.
作者简介:杨伟(1997—),男,贵州铜仁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