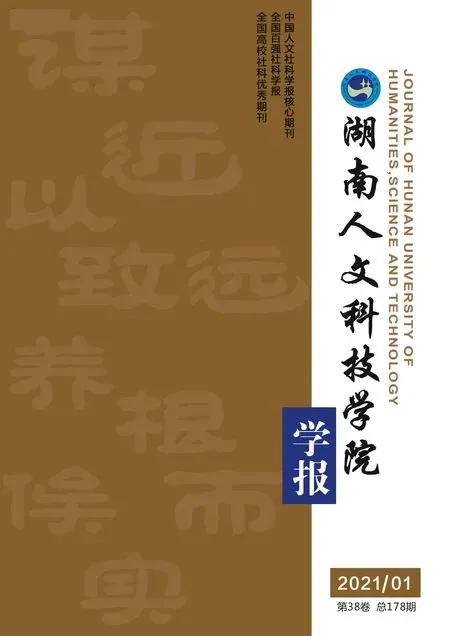以血缘为基础的儒家伦理及其管理实践
刘亚梅
(湖南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421002)
陈来曾说“伦理学所重视的观念,其社会基础是共同体的结构、形态及规模……而伦理准则、规范、观念……来源于共同体生活的需要”[1],血缘共同体的家庭是共同体的一种典型形态,儒家伦理正是一种基于血缘建立起来的伦理。
血缘关系具有十分明显的特点:首先,血缘关系不能够被选择,人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因此它具备“宿命”的非理性的特点,所以儒家伦理提倡的人义务或责任是早于个人的存在的;其次,血缘关系具有排他性,是否具有血缘关系是识别家庭、家族共同体成员的唯一途径,儒家伦理据此而提出爱有等差之别,对远近亲疏的共同体成员有区别;最后,血缘是永恒的,个体的死亡并不影响血缘在后代身上的延续,它能够通过生物意义上的传承而获得不朽的生命,因此,祖先崇拜也是血缘伦理的产物。后人所做的不是西方的“荣耀上帝”,而是使家族与祖先荣耀。另外,由于血缘的不可选择,人与人所处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固定的,儒家所建立的伦理秩序都体现出十足的人的情感特色。
由于这些原因,儒家伦理提出了“孝”“爱有等差”“慎终追远”等概念。儒家伦理对中国、中国人的影响渗透在方方面面,不一而足,本文且从以“孝”治家国、以及家产制和社会心理、村落自治与乡绅政治这三个方面来讨论儒家伦理对社会实践的影响。
一、“孝”与以“孝”治家国——儒家伦理的核心观点之一
儒家把“孝”看作是最基本的美德,也是儒家伦理的核心内容。在《论语》《孝经》这两部经典之中不无强调“孝”的重要性。“善事父母曰孝”,《说文解字》中解释“孝”由“老”与“子”两个部分构成,有为子承老的意思。“人之行,莫大于孝”,孝敬父母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是天经地义之事。“孝”作为处理子女与父母关系的准则,子女对父母负有绝对的义务,可以以“天赋义务”的概念来定义儒家这一家庭伦理原则。
“孝”的义务在儒家那里是先天性的并且是不对等的,即只要存在父子的结构,子就有对父母的孝义务;此外,子女孝敬父母的义务要大大重于父母对子女慈善的义务,“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岂有君而可叛者乎?”即使父母不“慈”,子女也不能因此而不孝,故而,王常柱称“慈孝伦理效用的闭路循环是一个重孝轻慈的失衡循环。”[2]
“孝”的概念纵向延伸,就要不只对父母“孝”,还要对父母的父母——先祖也要孝。于是,儒家在确立规范时就有了一种泛孝主义的倾向,孝道的概念就不仅仅局限在有血缘关系的父子,而是运用到有血缘亲疏关系之外的领域,甚至是没有血缘关系的领域中。“其内在的精神理念与相应的行为法则被运用到非血缘性的关系对象之中”[3]如此一来,子女除了要对父母敬重,还要承认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都是祖先留下来的,对先祖要“慎终追远”,祭祖就成为“孝”中的重要一部分。翟学伟先生就此点评“一个人存在的理由在于其祖先,其祖先存在的理由在于他还有后代。这就是尊尊亲亲作为宗法核心的来源”[4]。
这种作为家庭伦理的“孝”的理念,被董仲舒等人扩展成了社会伦理、政治伦理,成为“事亲、治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原则,甚至是一种充沛宇宙之间而能贯通天地人三才的孝的宗教”[5]。“以孝治天下”就是“孝”从家庭伦理走向政治伦理的一个具体例子,也是泛孝主义的一个具体体现。
汉朝推行“以孝治天下”,在人才举荐上“举孝廉”、为“孝亲”立法解决子孝与父母违法的矛盾、对不“敬老”“养老”的人实行处罚。“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一个对父母“孝”的人才能“忠”于君主,才能对朋友“义”,才能够具备其他美德,故称“孝”是百德的首要。汉朝统治者将君民关系拟比成父子关系,将朋友关系拟比成兄弟关系[6],将“孝”之伦理的秩序——“尊尊”的对象扩大,“尊尊”的内涵就演变为就成为“尊君”“事长”,而社会上的非血缘关系也类似地被拟比成宗法关系而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一个大家族。百姓对这种扩大了的意义上“孝”的履行,统治者“治”的目的就达到。
这种扩大的“孝”的观念实质上是家庭伦理打破血缘的限制向社会伦理的延伸,“孝”的伦理不仅仅再限制于家族内部,这种“泛孝主义倾向”导致了“泛家族主义”的倾向,乡党、会馆、郡县都能基于某些理由而形成泛家族意义上的共同体。但是这种“孝”的内涵不论如何变化,最终都可以归结为“道德个体向伦理实体的认同与回归。这种认同与回归既包括生命个体对生命之源的价值认同,也包括道德个体对家庭、宗族以及国家的伦理认同和精神溯源。”[7]
二、家产制与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儒家伦理的经济实践与社会心理
血缘关系的特点决定了人际关系有亲疏和远近之别,因此儒家提出“爱有等差”,这种“等差”就是亲疏远近的差别,这种差别体现在中国人生产和生产资料分配中。
中国人采用的是一种以家族为单位的集体生产方式,这种集体方式紧紧依靠血缘捆绑,韦伯《儒教与道教》一书中称此为——家族共产制,也称“家产制”,这种家产制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家庭管理方式,他描述道:“精根细作的农业耗费大量时间与劳动力,因而人们以固定的方式居住在土地上,加上繁重的工作与资源的匮乏,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的生产方式成为最佳选择。这种以家族为单位的家产制还是‘儒教精神的根本结构形式’”[8],除了平时的劳作生产,业余时间的教育、休闲、宗教等活动也以家庭为单位开展,这也是儒家伦理形成的经济根源。这种相对而形成的血缘伦理又极大地强化了家庭成员的关系,并最终导致传统中国人社会取向中“家族取向、他人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四种社会心理”。
家族主义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不论是在传统的中国社会,还是在现代的中国社会,家族主义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社会的基本结构与功能单元是家族而不是个人,家族是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核心,其保护、延续、和谐、团结、富足和荣誉极其重要,因而形成中国人几乎凡事都以家为重的家族主义。在家族取向下,家庭成员具有强烈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荣辱感,个人为轻,家族为重,一切以家族为主,具体来说,家族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因此,为了家族的生存和延续,个人屈从在家族之下。在家族共产制之中,成员在分家之前,会以种种方式增加家族财富。在个人利害与家族利害相冲突的时候,以家族利益为取向(家族取向)。
这种家产制带来的弊端则是,个人在经济上不能独立,那么就难以产生观念上的独立,“由于没有这种独立与自主性,那么在表达立场与意见时就没有个人独特见解,而以他人的意见为意见”,导致传统中国人缺乏独立性,西方“原子式”的个人主义永远不会形成,这种生产的管理方式也直接导致了以“他人为取向”的心理。这种基于家庭血缘关系必然导致集体主义观念的产生,没有个人主义的意识也就不可能出现西方意义上的“个人”的观念,更难以产生基于独立个体的明确界定的权责概念。
此外,加上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之别,因此在生产资源的分配上也是遵循儒家“爱有等差”的观念,内部关系明确稳定的家族家产制从最亲近之人开始分配,论亲疏道远近,这就导致了中国传统的“关系取向”的心理。这种关系取向在日常生活中具有的特征是“关系中心”和“关系决定论”,对方与自己所处的关系决定了如何对待对方和其他相关的事项。人际关系是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层面,梁漱溟把中国人这种凡事以关系为依托的文化特征叫作“关系本位”。
在以家产制经营的农业时代,物资并非总是充裕的,为避免家产分配时争端产生,长者被赋予绝对的的权威,由此形成了以父系为主轴的内部管理方式。在这种制度下,父亲是家庭的权威和领导者,对中国人而言父权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孝”与“尊”的观念被有意地强化,“嫡庶”“尊卑”的等级也被强化,不同的角色要严格恪守相应的德性和规范,“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叶”“父为子纲、夫为妇纲”的观念则确立了家庭中成员相应的德行以及家庭中等级与差别。对父权的服从扩展到社会之中,就体现在人们对权威的崇拜上。
正如此前所言,父权的权威并不局限在家庭内部,通过董仲舒等人以阴阳五行学说解释“三纲六纪”这样的发展,它与君权渐渐结合,正如冯天瑜先生所说,“孝”的延伸使得父权、官权和君权异涵同构,使得家国同构。只要血缘关系还存在,“孝”的要求就有实践的必要,君主权威就不容撼动。君臣与父子关系的拟比还使得这种原本局限在家族内部的权威与君权渐渐结合。这种延伸使得父权、官权和君权异涵同构,权威的强化就造成了传统中国人“权威取向”的社会心理。
总而言之,儒家伦理强化下的家产制使人们形成了“家族取向、他人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四种社会心理”[5]。
三、村落自治与乡绅政治——儒家伦理的基层政治实践
韦伯则在考察中国社会时,指出家产制对中国政治的两种特殊影响:一方面它与官僚制度结合也形成“家产官僚制”——文官集团为代表——也就是韦伯指的经科举制而为官的儒教徒;另一方面导致了一种与集权专制相背离的“村落的自治”。依笔者看来,“村落自治”的形成有两个原因:一是政府力量十分有限而无法控制乡村地区;二是中国乡村的聚落形式以血缘为主(以姓氏为村落名称)。一村一姓氏是常见的现象,村民之间的邻里关系常是亲属关系,村中最年长或最权威的人最具话语权,一般是族长或者知识阅历最丰富的人,村落中有一套依照家庭伦理而确立的家庭规范能够自主地进行内部管理,而拒绝“非血缘”关系的人插手,形成了乡村自治。如刘署辉与赵庆杰先生所言,“血缘宗法制度的建立,使得传统伦理具有极强的自组织性”[9],这还间接使得一个十分有中国特色,牵涉国家、村落和地方乡绅三角结构的——“乡绅政治”的产生。
乡绅的“绅”则多指有做官经验或做官可能的士人,“乡”则不仅仅指的是乡村,而治指以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宗族与家乡,仅从这个词义我们就可以推演出乡绅角色与地方宗族千丝万缕的联系。秦晖先生有言:“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与韦伯对中国古代官僚制度有限性的观点不谋而合,封建帝国的统治既有正式的官僚制度,还有“非正式”的乡绅政治,他们作为“非正式组织”将国家政府与乡县地方串联起来。封建帝国的统治既需要正式的但有限的官僚制度,也需要这种非正式的乡绅政治,费孝通先生将此称为“双轨政治”。如果将秩序分为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严格来说,乡绅并不是政治秩序中的任何一阶层而是社会秩序中的代表,它具有多种角色,独立于政治秩序之外的社会秩序,一方面它地方社会权威的代表,代表地方社会权威与政治权威进行沟通;另一方面,乡绅们常常是本宗族内的精英,充任长老或者权力轴心。
从对地方政治权威的影响上来看,尽管县政府以下设有里社和保甲行政组织,但是这些政治权威或角色大多是地方乡绅或乡绅势力的代表人,他们能对地方政治有绝对的影响力。
历朝朝廷为了避免官员一地方宗族抱团,官员是不被允许在自己的出生地任官,也不允许在其在某地的任期超过三年,由于这种流动性,这就导致官员在初步熟悉一个地方的政务之后就立马离任到一个新地方。初来乍到的外地官员就不得不仰仗当地通晓世俗事故的师爷或者幕僚来指引,而这些地方非编制的幕僚们则通常与地方乡绅势力有密切的往来,其结果就是,实权落在了非官方的本地僚属手中,而官方任命的督察很大程度上却对此胥吏事务毫无监督的可能。乡绅通过这种方式与地方政治权威捆绑在一起,“形成地方上盘根错节尾大不掉的割据性势力,对中央集权产生严重威胁”[10]。
而地方上的经济组织和乡党宗族也凭此形成小团体——这些团体的领导人物往往是具有强烈地方主义情感的乡绅势力或其代表人,乡族宗族与乡绅势力在地缘上居于亲近性,政治上具有极强的自主性和自治性,两厢结合,地方就极容易脱离甚至是抵抗中央政治权威的现象。
对更底层一些的村落来说,它们通常以具有血缘关系的宗族为单位建立村落,“村庙和缙绅来主持日常事务”是常见的,在宗族内具有声望的精英们——乡绅对家族内事务有充分的发言权和决断权,能够充任家族长、私设刑堂,依“家族法”治理村落。可以说,在这种村落中形成了“扩大的家庭共同体”,对国家正式权力的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
乡绅对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21世纪初,吴从环的考察的报告中就指出政治权力从党组织向非正式组织的位移:村民自治权力的正式位移从党组织、基层政府向经济组织位移(厂长、经理),权力非正式位移至乡村精英、宗族组织以及宗派组织,但是随着近年来乡村合并以及现代化新农村的建设加快,乡村自治政权又回归基层政府。但直到现在,村落自治仍然不能摆脱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双轨”模式[11]。
四、结语
总而言之,儒家伦理的本质上是一种血缘伦理。儒家伦理的核心概念是“孝”,这种“孝”道随着历史发展的需要内涵逐渐不断扩充,从直接的父子结构推导出非父子结构的“泛孝主义”,从对父母的孝扩展到祖先和君主;在生产实践上也以血缘家族为单位进行经济活动,确立了家庭为单位的“家产制”,并使人们形成了具有“家族取向、他人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12]四种社会心理;在基层政治实践上,则形成了乡村自治和乡绅政治。
儒家伦理的确为人们确立了一整套适应社会的规范,对我国社会和文化影响深远,但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加快,传统儒家思想的核心——“孝”发展至今,在内涵和外延上均发生改变,“孝”由对双亲的“顺”转化为“爱”,由单向的“尊尊”转为双向的“支持”,“孝”的外延也从家到国的“泛孝主义”缩小为对先祖的慎终追远。
当下,我国经济上虽不复农耕时代的家产制,但家族和家庭观念仍然在国人心中占据重要位置,在市场经济中,家庭仍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当代中国人的心理取向逐渐由大的家族取向逐渐转为小的家庭取向,他人取向逐步向个人取向转变,但在处理社会关系时仍避免不了关系取向和权威取向两种社会心理。此外,随着乡村合并加上城市化进程加快,乡村自治政权的位移虽又回归基层政府组织,但乡村精英、宗族组织的影响还是挥之不去[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