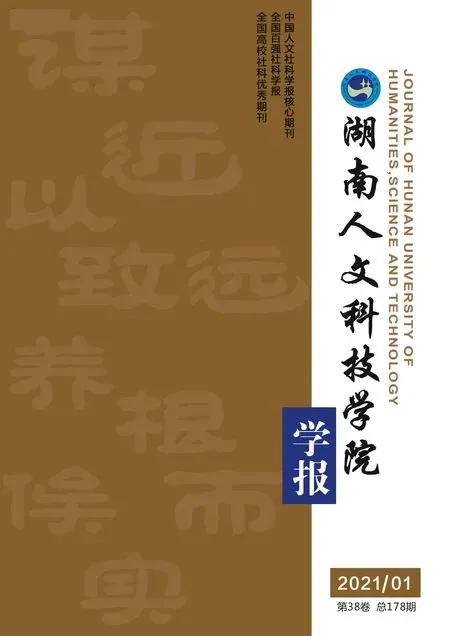治生与治身:罗拱诗、罗泽南祖孙的抉择偏离
王澧华
(上海师范大学 对外汉语学院,上海 200234)
论及罗泽南(1808-1856)的生平、志节与事功,论者多溯源罗泽南的祖父罗拱诗(1755-1830)。这是因为,罗泽南先后有数篇诗文,追忆其祖对自己人生道路的设计、指引与期望。
本文试图探寻,罗氏祖孙的人生规划,其动机渊源、家世遭遇与目标追求的因果、代价与利弊,是否还有不太为人深究的隐微之处?
一、“谋生”与“进身”
(一)罗拱诗的家世与家境
罗氏先祖的家世与家境,罗泽南所撰家传以及同时代人曾国藩(1811-1872)、郭嵩焘(1818-1891)所撰墓志铭、神道碑与年谱,皆语焉不详,现据仅存材料,略为钩稽于下:
据佚名编、郭嵩焘校《罗忠节公年谱》①,曾祖罗日阮,祖罗拱诗,皆因罗泽南之战功貤赠通奉大夫,“赠”而非“封”,即为身后荣誉;
据罗泽南《先大父六艺公事略》,称“吾族世耕稼,无仕达者”[1]126,则高曾以下皆为世居山乡无功名之人;
据《事略》,罗拱诗“昆季四”,兄弟四人中,罗拱诗为“季嗣”;“伯兄亭树公壮岁有声庠序,教诸弟极严肃”[1]126。据罗泽南《伯祖亭树公传》,“伯祖父讳芝,字亭树,魁五公之长嗣也”“少习举子业,不售,习射”“初为武生,屡应乡试不第”[1]121。武生,即武生员、武秀才,罗泽南于三位伯祖父仅为大伯祖立传,似二、三伯祖亦无甚可述者。
罗泽南的父辈,据《事略》,有年少辍学者(父亲罗嘉旦,或叔父罗泽曙),据《年谱》,有授徒于家者(从父罗简拔),有设馆于外者(族父罗巨卿),但皆无科举功名。
据《事略》,罗拱诗以“家益贫,出为人治贾”“客衡(阳)一年”“客安化二年”“客陕西兴安州五年”,终以盗匪劫掠行商而退还湘乡,“自伐木竹,诛茅,构屋里中,沽酒米为业。十余年中,得鬻田十亩余,自耕之”。据此,则罗拱诗大体经历了为人负贩、回乡开店与购置薄田三阶段。起初“凡所贸易之处,即命子从师以受业”,以“所得之直为子读书,罄之不少吝”,终因“归湘旅橐萧然,吾父以贫故废学”,及至罗泽南十岁外出读书,罗拱诗“年将七十”,而“家中食不足,且负债”,只能“悉售田以偿之”,以致“日尝不举火”,而罗泽南“馆中食缺,”罗拱诗只能“典衣质之”[1]126-127。
(二)罗拱诗对罗泽南的人生规划
罗泽南在《先大父六艺公事略》一再称述:罗拱诗“生平以不学为憾,思欲所以竟其志”,“呜呼,先大父之所以贻我后人者至矣”,“以生平未学之故,欲竟其志于后嗣,不以困苦易其心”,所以,无论是在衡阳、安化还是陕西,他都一直把儿子带在身边,就地从师读书,直至返乡后才因贫辍学。及至若干年后,稍有积累,随即“以置学田课士为急务”,首开罗氏宗祠家塾,故“(罗)泽南四岁后即授书”,10岁又离家外出就读此时,尽管罗家已经返贫,甚至到了将田产悉数变卖来还债、家中无米为炊的地步,罗拱诗还是一旦得知孙儿在学馆缺食,马上“典衣给之”,“寒暑之服,屡质之于市,得米,令家人省食,或两升,或三五升”,罗拱诗亲自送到学馆,“至则殷殷诫之”[1]127。
对此,罗泽南除了在《事略》中深情回忆,还一再作诗感戴:
《壬辰五月先祖忌日述痛》:榴花零落影参差,试罢归来黯自悲。回首当年无限恨,寒衣典尽送孙时。(先祖在日,屡次典衣送泽南应试)[1]9
《补裘痛怀先祖》:冷雪凝阶二月初,羊裘补得胜华裾。风霜记否当年苦,典尽春袍送读书。[1]21
曾国藩所作《罗忠节公神道碑铭》特意表彰:“公少就学,王父屡典衣市米,节缩于家,专饷于塾。”[2]343佚名撰、郭嵩焘审定之《罗谱》则转述罗泽南自述:“馆中饔飧不能继,(祖父)恒典衣质物易食食之”,“一布袍亲持入典肆者六七次,皆为予读书也”[3]2。
罗拱诗之所以不惜因学返贫,据《事略》,称“公曰:‘贵贱有命在,惟多得读书明理者,便算是一家之幸。’”[1]126又据《年谱》,转述罗泽南自述:“(祖父)尝曰:‘吾之以汝读书者,欲汝明大义,识纲常,不坠先人之清德也。’”[3]2读书明理,或许有些拔高,如《事略》所载“人有欲泽南习他艺以觅生者,公曰:‘吾不能以田地贻子孙,独不能以书贻之乎?命应饿死,不读书遂能免耶?’”[1]126读书不过是习艺觅生的途径之一,《论语·卫灵公》的“子曰:‘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明清乡学的必备书《增广贤文》所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做官”论早已沦肌浃骨、深入人心,只不过,不如“读书明理”说那般冠冕堂皇。且看《年谱》所载“外大父萧蔗圃公每指先生(谓罗泽南)属元初公(即罗泽南父亲罗嘉旦,字元初)曰:‘此子不凡,虽极不给,必资之读。他日大门闾者,必此子也。’”[3]1读书只为门户计,毫无遮掩,却更真实。罗拱诗的长兄早年专心科举,“壮岁有声庠序”[1]126,侄辈授徒为生,亲家萧积璋(号蔗圃)发愤读书、教书为业,终生为一秀才功名而应考不息(罗泽南《外祖萧公蔗圃先生传》),这些,可能才是罗拱诗“一布袍亲持入典肆者六七次”,“典尽春袍送读书”的真实用心。
综上所述,罗拱诗起初因负贩不足安生、半途而废,转而因开店谋生而初步脱贫,随即因兴学课孙而返贫,由此可见,在他的心目中,“谋生计”不如“谋身份”,不惜赌上一切代价,将罗家的希望寄托在孙儿读书成才上,最大的投资,意在最大的回报。
(三)身份的诱惑与罗家的代价
同为湘乡县的山乡老农,二十四都的曾玉屏(1774-1849),全家老少,力田为业,勤劳脱贫,专供长子长孙,专心读书应考,两年之间,曾麟书(1790-1857)、曾国藩父子接连考中秀才,儿子青出于蓝,第二年中举人,三应会试,终于成进士,点翰林,此后短短十年,官居礼部侍郎,十个月后,曾玉屏含笑而逝。
这对祖孙的“读书做官”之路,应该就是罗拱诗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只可惜,在此前一二十年,罗拱诗就积贫而逝世了(享年76岁,与曾玉屏同)。先是两年之内,罗拱诗接连丧亡了两个儿媳,一个孙子一个曾孙女;罗泽南则在失去祖父、失去母亲、失去兄长之后,五年之间,接连失去了三个儿子,一个妹妹,一个侄儿,妻子哭瞎了眼睛。据郭嵩焘所撰《罗母周夫人墓表》,罗泽南在省城长沙应考秀才落选,“贫不能具舟车,徒步归所居罗山,用夜半到家。会旱,见所艺田皆荒,呼门入,闻夫人张氏哭声,所生子又殇。启盎无储米,就枣突爇水为炊,则夫人以痛子故,目尽盲,不辨火有无,忠节公怆然自伤”[4]485。对此,曾国藩所撰《罗忠节公神道碑》、李元度(1921-1887)所撰《罗忠节公别传》,皆有沉痛记述。
据《别传》,因为“家酷贫”,罗泽南“溺苦于学,夜无油,把卷读月下,倦即露宿达旦”[5]137,15岁(虚岁,下同),仍旧读书乡村,其母“得一掬米与食,就馆曰:‘尔他日无忘此苦!’”[3]219岁才第一次参加童子试,落第回乡,当年就开始在石冲的萧家作私塾谋生;而据《曾文正公年谱》,曾国藩18岁则是在父亲任教的石鱼百鲁庵学馆读书;截止到28岁,罗泽南转蓰椿树坪、新塘、江家塘七八处而且几乎一年一换授徒谋生的时候,同样截止到28岁,曾国藩却在衡阳、长沙、北京从师深造,科试、乡试、三次会试直至殿试,一路获取秀才、举人与进士功名;《罗谱》记载的是“每夕携学徒所馈肴馔归供大父”[3]3,《曾谱》记载的是曾国藩会试落第,过金陵,以所贷百两银钱“尽以购书”,其父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曾国藩“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户者几一年”②。
由此可见,士绅身份的诱惑,读书做官的前途,让罗曾两家都有过举全家之力以供一人的血拼,都不惜举债以搏,志在必得,只不过,限于家产与个人选择,罗泽南与曾国藩的早年遭际,判然两途。
二、“立业”与“修身”
罗氏家业不及曾氏,固然是曾罗二人云泥之隔的物质基础与客观原因,但其间的个人选择也占据很大影响。
大体说来,罗泽南并未如曾国藩全心致力于科举考场,而是据曾国藩《罗忠节公神道碑铭》所述,一边教书为生,“假馆四方,穷年汲汲”,一边却又“以为天地万物本吾一体,量不周于六合,泽不被于匹夫,亏辱莫大焉”,转而“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人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年逾三十,乃补学官附生,逾四十乃以廪生举孝廉方正”[2]343-344。如此看来,罗泽南颇有“修身”重于“立业”的倾向。
19岁开始教书为业,到46岁带勇上阵,罗泽南私塾从教27年,轮换东家15人次,33岁考中秀才,41岁补廪膳生,44岁举孝廉方正,如《神道碑铭》所称“藉课徒取资自给”,“尝以试罢,徒步夜归,家人以岁饥不能具食”[2]343。这样的人生经历,似乎并不算出类拔萃。而曾国藩,则是23岁中秀才,24岁中举人,28岁中进士、点翰林,39岁官居礼部侍郎,44岁统帅湘军出征,走上封侯拜相之路。无论功名与功业,罗泽南与曾国藩,差距都很大。除了客观原因,是否还有主观因素?
据《年谱》,试看罗泽南的授课之际的修身活动:
三十一岁,馆陈宅,著《常言》,后改定为《人极衍义》。先生曰:“予迩年始得宋儒之书读之,因复求之四子六经……知圣贤之道,不外身心,往日之所学,末学也……课读之暇,披览旧典,心有所得,随笔之于书,名曰《常言》……又作《上达图》以弁其首。《上达图》者,所以辨人禽之界限,正学者之趋向也。
三十二岁,馆陈宅,作《悔过铭》……与(刘蓉)语《大学》明心之道,孟容(刘蓉)叹服,订交莫逆……书札往来,彼此规劝,考求先圣贤为学之要旨,身体力行,至明且笃,时人咸倾慕焉。
三十四岁,肄业(长沙)城南书院,著《周易朱子本义衍言》。时宁乡刘公典、浏阳谢公景乾与先生共几砚,讲习讨论,互相砥砺。
三十七岁,馆善化贺孝廉修龄宅,著《姚江学辨》。
三十九岁,馆贺宅,著《孟子解》。
四十一岁,馆左刺史辉春家……改定《人极衍义》。
四十二岁,馆左宅……时前任云贵总督贺公长龄、太常寺卿唐公鉴皆家居,先生往语学问,甚洽,过从无虚日。著《小学韵语》成。
四十三岁,馆左宅,著《西铭讲义》成。[3]5-8
不难看出,身为人师的罗泽南,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了课堂教学之外的个人修为上。讲解课文,答疑解惑,批改作业,启迪写作思路,促使科举有成,乃是东家(聘任方)对西席(受聘者)的基本要求;身为塾师,7次应试童生试,13年后才获得秀才资格,而且止步于此,而对性理之书却乐此不疲,“副业”冲击“主业”,作为一名坐馆为生者,似乎无以自解。
再从《罗泽南集》摘录有关言论:
《号悔泉说》:甲午秋,八月几望,梦书一联,云“悔当年未培心地,从今日立定脚跟。”……因以培源为字,悔泉号之,作悔说以自警焉……古之人曰省曰耻、曰惧曰克、曰反曰复曰新,皆此悔心为之起也……余今年二十九矣,回首生平,过端丛集,大抵由于不知悔……能不痛哉,能不惧哉……惟能站定脚跟,培植本原,庶乎可以为人矣。[1]84
《悔过铭》:……一言之失,驷不可追;一行之失,药不可医……诵圣贤之明训,守父母之遗肢,惩其既往,救之将来,或庶几其无大疵。[1]86
《西铭讲义》:……人有斗屑之量,有沼池,有江海之量,有天地之量。《西铭》之量,天地也……人惟有物我之私,便不能上达天德……“敬”字是圣学彻始彻终功夫。若不居敬,纵教识得‘乾父坤母’、‘民胞物与’,终是空头大话,与自己身心曾不相涉,如游他人广夏之中,万阁千楼,终非己有……不愧屋漏,即《大学》《中庸》慎独功夫。人所不知,己所独只之地,不令有一毫之或差,始为不愧……[1]143,145174
《人极衍义》:天地之道,曰“诚”而已矣……今夫为学之道,果何如哉?内以成己,外以成物而已……立一身之主宰,而提万事之纲者,其维心乎……常人之心,役于物者也,物胜则理灭,心为物夺也;君子之心,役物者也,因物付物,顺乎理之自然者也……[1]189,191-193
《姚江学辨》:充阳明之学,是不至毁灭天地、消融民物而不已也……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 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曰亲,曰仁,曰爱,施之固自有等差也。阳明于家、于国、于天下,概谓之曰“亲”,不已流入墨氏之兼爱乎?不显率人人于无父之教乎?几何而不沦于禽兽也![1]232,236
《读孟子札记》:“义”“利”二字,王伯之所由辨,亦千古治乱所由分也……“义”之与“利”,正“天理”“人欲”分途处,其间不可容发……读《孟子》者,能先于此见透,洗涤利欲,拔本塞源,庶乎可以励圣贤之功修,而语三代之盛之治矣……[1]275
整体上看,从作《号悔泉说》《悔过铭》开始,直到《人极衍义》《姚江学辨》,坐馆授徒的谋生立业,似乎逐渐让位于修身养性的道德至上。
三、罗泽南“悔过修身”对罗拱诗预设的背离
(一)罗拱诗的自弃于商,押宝于读
应该说,“藉课徒取资自给”,舌耕谋生,仰事俯畜,这是千百年间底层书生的主要谋生方式。当年罗拱诗以世代无士绅,以不学为憾事,从而全力培养儿孙读书,开店售卖酒米,一旦有所盈余,便急于开设宗学,课读子孙,目标不外乎脱离农商、提高身份。
限于历史、社会的先天不足与地域的农耕谋生传统,罗拱诗从外出经商因求安生而轻易返乡,这一点,与徽商的走出山乡、走向远方、渴望发家致富形成很大反差;同时又自轻其业,不但没有让儿子从小见习、子承父业,反而是将替人贩运的所得工价,用于供给儿子就地读书,“凡所贸易之处,即命子从师以受业”,甚至是一而再,再而三,“客衡一年,令读书于衡;客安化二年,读于安;客陕西兴安州四年,读于陕”,而且是“所得之直为子读书,罄之不少吝”[1]275。这是罗家的第一次方向性决策,利弊得失,似乎不难判断。
经商之路半途而废,罗拱诗返乡开店,山乡沽酒米,做小本生意,盈利未必高于湘南、湘中与陕西的远途贸易。即便是罗家上下“最勤俭”,十余年也只能“鬻田十余亩”,且“自耕之”。而罗拱诗又做出了人生第二个重大选择,首倡宗族兴学之风,“以置学田课士为急务”,而其初衷,不过是“吾族世耕稼,无仕达者”。由于盈利没有投入扩大再生产,罗家很快因学返贫。
罗拱诗的第三次抉择,就是在因学返贫之后,仍旧一条路走到黑,不惜全家节衣缩食来供给孙子罗泽南的学费与伙食。上引罗祖“一布袍亲持入典肆者六七次”,罗母“得一掬米与食,就馆曰:‘尔他日无忘此苦!’”尽管读之鼻酸,但是面对乡邻的规劝,“人有欲泽南习他艺以觅生者”,换来的却是罗拱诗的昂然不顾:“吾不能以田地贻子孙,独不能以书贻之乎?命应饿死,不读书遂能免耶?”[1]126
只可惜,罗拱诗的的自弃于商,押宝于读,罗家等来的却是10年之内,死丧11人。罗母去世13年、罗祖去世9年之后,罗泽南“七应童子试不售”[3]6,最终在33岁才考取一个秀才功名,痛惜祖父与母亲不得分享这份来之不易的荣耀,但随后并没能跨入举人的缙绅行列。如果不是后来的创办湘勇、上阵拼杀,罗家的家境,大概很难有根本性的改善。
(二)“此路不通”“走独木桥”与“自我超升”
罗拱诗早年既已弃农服贾,为何中年自弃于商?因为此路不通。
第一,旧中国农耕社会,重农轻商,朝野上下,千百年来,观念上已经形成“沉重的阴影”。
第二,湖南地处内陆,历史上一直缺少通都大邑,各州县大多散落丘陵与内河,百姓习惯于低水平自给自足,商品需求少,市场不发达,经商资本不足,小本经营,利润刺激少,加上产业链不发达,致使湖南经商风气不高,经商出路不畅。
第三,截至20世纪以前,湘乡缺少大商贾,缺少本地商群的成功经验与巨商示范。罗拱诗既然已经投身商贩,却几乎不切实际地携子随读,薪资随得随散,没有资金积累,只能长期处于负贩转运的帮佣底层。
第四,民生不能免于饥寒,商旅容易遭受劫掠,据《六艺公事略》载:“陕西山最峻险,深箐穷谷,群盗啸聚,其中无赖子好结会出入,咸以刀槊自随。”对此,罗拱诗的选择是,相比于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返乡可以求得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尽管“归湘旅橐萧然”[1]126,但终究强于留陕同乡群的罹难无归。
一方面是“此路不通”,另一方面,科举入仕的大门又似乎面向大多数人开放,罗拱诗的长兄就曾经“少习举子业”,尽管“不售”,转而“习射”,但罗拱诗还是将希望寄托在儿孙身上,儿子因贫废学,他又把孙子带上了科举这条“独木桥”。
读书应考,科举入仕,这是明清时代平民百姓改变个人命运进而改变家庭命运的首要选择。相比于重农轻商这一“沉重的阴影”,读书,科举,更像是两只“隐形的巨手”,驱使无数寒门子弟寒窗苦读,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结果可想而知;曾麟书应童生试17次,43岁侥幸成为荷叶曾家的第一个秀才;曾国藩科举场上屡败屡战,除了家境支撑,还因为他多少算个“学二代”,而罗泽南则没有这么幸运了。
失望之中,罗泽南无意接触到了儒先性理之学,即30岁前后因为同馆教书的王&(上下爾)云的汲引,这才初读《性理》一书,于是幡然悔悟,感叹往日之所学皆为“末学也”。一如“读书入仕”的社会舆论,春秋战国酝酿的孔孟之道,两宋明清的程朱理学,道德至上,则是乡村中国的另一种舆论熏陶。试文是否中式,取决于考官的程式标准,而心性的自我修炼,欲望的自我克制,私心的自我责难,苦难的自我忍耐,圣贤的自我期待,所有这一切,几乎都无假于外求,前引“立一身之主宰,而提万事之纲者,其维心乎”,“人惟有物我之私,便不能上达天德”,“悔当年未培心地,从今日立定脚跟”,如此言说,便一发不可收拾。在写给朋辈与友生的文字往来中,这样的砥砺与说教,成为这位塾师的常态表现:
《学问》:人欲行道,必先存理;人欲存理,必先扩识;人欲扩识,必先立志。其所为立志者何?曰:“学圣人也。”[1]51
《与谭砚农书》:人之为学,必先立志……夫所谓立志者,志为圣人而已矣。……治国平天下,必先格致、诚正、修齐,始为有本之学……是必从依大本大原上做去,始为有原之学,徒讲求钱谷兵刑,抑末矣。[1]91-92
《与某友书》:若只系情科第,已是逐外面作人,已非君子所以用心也……夫道德仁义,赋之自天,操之自我,我欲为之,气数不得而阻之;富贵贫贱,命之自天,操之自天,我欲争之,天未必遂与之。舍其操之自我者,慕其操之自天者,幸而得固吾命所当得,苟不能得,即终日夜营求,又何益于分毫哉?……天理人欲,界限争在丝毫,此心不入于义,即入于利,其间原无立足之地。[1]95-96
《复某友书》:前蒙惠书,教弟以揣摩时好,弋取功名,其爱我诚切。然弟有所见,有陈不得不陈之于足下者。……今日取士,必由科举,吾亦惟按期课文,试期至,则应之,技之售不售,是固有命存乎其间,非吾之所能为,固不必先为之虑也。……吾之志,固已有所在,虽有笑我迂者,亦不能为之辞矣。[2]98-99
《耻不逮斋记》:李子希庵从余游,日与讲论正学……吾与希庵讲论有日矣,孔孟程朱未尝一日离诸口。[1]74-75
“若只系情科第,已是逐外面作人,已非君子所以用心也”“其所为立志者何?曰:‘学圣人也。’”调门已是越来越高。“揣摩时好,弋取功名”,在罗泽南看来,纯属道德提升的羁绊,祖父罗拱诗当年的典衣送米,外祖父“大门闾”的美好期待,母亲“尔他日无忘此苦”的悲情叮咛,所有“治生”的家庭责任心,几乎最后都被“治身”的道德使命感淡化了。罗氏全家节衣缩食以供一人的超负荷投资,在罗泽南归心理学的“品德升华”中,似乎并没有收获得当年预设的回报。而其中年,仗“忠君”“杀贼”之气,书生上阵,以《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之义为制胜之道[6]773,以“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为舍生成仁的临终绝笔[5]141,则又将湖湘理学精神施之于战场,军功报国,军功发家,一时成为湖湘基层民众改变命运的主要途径。
罗拱诗的弃商返农,押宝于读,倾家荡产以求一第,罗泽南的教书为业却又轻视科举、偏重道德、困乏其身而以天下为己任,探究罗氏祖孙二人的两次抉择,两次取舍,应该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湖湘历史人文舍生取义的某些地域与时代特征。
注释:
①《罗忠节公年谱》二卷,同治二年附载于《罗忠节公遗集》后。检《郭嵩焘日记》,咸丰十一年三月廿二日载:“编校《罗忠节公年谱》,为罗两明世兄属撰忠节公《志铭》,余允以《年谱》当先为之编定也。”同年七月十四日载:“校订《罗忠节公诗文》……其子两明谋刻其遗文,属予校定也。”十月二十日“校正《罗忠节公年谱》并其《诗文集》寄静斋,顺致静斋一信,以寿山促予赴益,静斋又约忠节各种即日发刊,故赶为之。”同治元年七月初三日:“为《罗忠节墓铭》。成静斋以左景乔所撰长至四千言,属予重撰。细阅景老原文,亦只序得忠节战功,不能得其全神。”据此,知《罗谱》似先已撰成,郭嵩焘只是沿罗泽南子允作(字两明)的托请,故自谓之“编校”“校正”。为罗家编刻《罗集》者成静斋,名果道,字伯敬,号静斋,湘乡人,同治九年(1870)中举,官常宁训导。
②冠名黎庶昌、实为曹耀湘撰,梅季、喻盘庚标点,《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页。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43-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