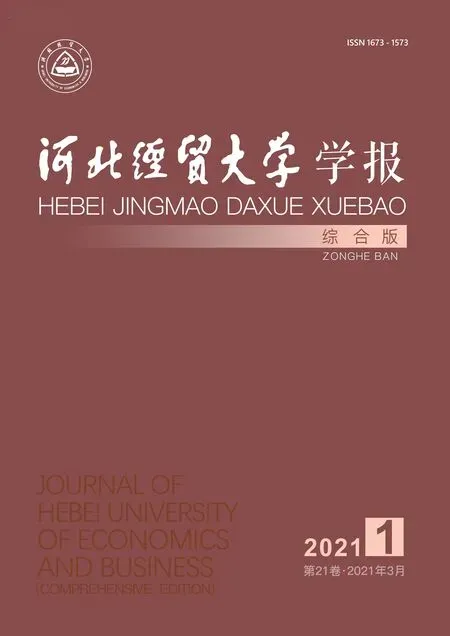巴金致孙陵书简两通考释
杨华丽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1331)
一、两通书简的原貌
“巴金书信面广量大,这是没有疑问的。”[1]267巴金研究的资深专家李存光先生的这一判断,有着切实的依据与支撑。迄今收录巴金书信最多的《巴金全集》之“书信编”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卷“是集巴金书信大成者”,“共收入1935年至1992年书信约2,000封,受信人近200位(含机构22个)。”[1]268然而据李存光先生掌握的情况,“迄今为止,已发表的和存放在公共机构的巴金书信共计约2,600封左右”[1]268,而这“仍然只不过是一角而已”[1]269。据他估算,“不计‘文革’中空白的5年(1967—1971年)和1995年后的9年(尽管仍有零星书信),从1921年到1995年,按70年时间算,最保守的估计,即使平均每年仅写信100封,书信的总量也超过7 000封,而实际数字,肯定会大于这个估算。”[1]270存世且已被关注的2 600封和估算的7 000封书信之间的确存在不容忽视的差距,而那四千封以上未进入我们视野的书信,或如李存光先生论及的那样遗失甚至被销毁在特殊时代,或因收信者的种种原因而未让那些书信浮出历史的地表。前一种情况,李存光先生已为我们梳理出一些,诸如巴金自己曾在迫不得已的状况下烧毁其大哥的全部来信、杨静如与王仰晨曾遗失或烧毁巴金的书信、巴金的侄儿李致曾在“文革”中被迫交出巴金给他的四十多封信等[1]269,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些特殊的因由”之一斑。与之相比,后一种情况同样复杂,一些收信者并未受到关注因而欠缺系统整理与研究则是原因之一。巴金致孙陵的两封书信消失在学界视野之外,就属于这种情况。
笔者发现的这两封书信,发表于桂林出版的《笔部队》第一卷创刊特大号。该期面世时间为1940年1月15日,“编辑人”署“孙陵”,“发行所”署“前线出版社(桂林府后街)”,“经售”署“生活书店”。这两封信被命名为“寄自上海”,与靳以寄自重庆(2封)、(姚)雪垠寄自南阳(1封)、(张)铁弦寄自河口(1封)及名为《淮上归来》的(臧)克家来信(2封),一起被放置于“作家消息”栏目下,呈现了该刊出版前这几位作家致孙陵信的主要内容,展示出这些作家的乱离状况,对了解作家们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中如何坚持文化抗战、理解作家们与编辑孙陵的交往情形等具有重要价值。较之于靳以、姚雪垠、张铁弦、臧克家的书信,巴金这两封信字数稍多,因而紧接着鲁彦的小说《杨连副》之末尾,被排在刊物第52页。为更好地展开研究,笔者先将这两封信的具体内容照录于此。
寄自上海
(一)
孙陵先生:
信收到。知你安抵桂林,很高兴。一年来常常想起你,也曾各处打听你的消息。你前信我接到了。后来去香港曾托一个朋友带一封信给你,大概你们错过了,以致你未能见到那信。你的红豆故事已由我编在文丛里,不知见到没有?我在桂林因不知你地址,未寄去。我一月前由香港返沪,最近不拟他去。我近来身体不好,打算休养一下,同时在翻译一本克鲁泡特金的书。明年将去昆明再转四川或桂林。你的行止怎样?我想明年我们总可以见面。杨朔最近来一短信。我在桂林时我们时常在一起玩。×××已去昆明读书。她也记挂你。上海空气很不好,我又常病,(都是小病),但我不想离开。在外面跑了一年没有什么成绩。我现在打算住些时候写点译点东西出来,再往内地跑。否则过几年我的外国文会全忘了。你觉得怎样?别话下次谈。
祝好
十九日
(二)
孙陵先生:
信收到,好些天就预备写信给你,都被一些杂事打岔了。我近来身体不大好,做事比较慢,又在读外国文。克鲁泡特金有册狱中记,我几年前就翻译了一点,后来因为别的东西便将他搁下,这次预备将牠(即“它”,整理者注)译完,又有两部译稿已早出版,但内有不妥处,拟整理重印。还有一部未完长篇,也要把牠完成。这些事做完我便可以去昆明了。上海情形不好,我想早日离开。但以上的事情又非在上海做不可。在内地我没有参考书。去年曾带了些书出外,你在汉口看见的我的那箱子,终于在湘桂路上失掉了。幸好只是几部字典。以后也不敢再带书出去。我出去我们可以见面。不过我恐怕我要到暑假才会在昆明。你那时还在桂林否?我打算在昆明过暑假,然后去桂林。我怕你等不到那时候。但是我相信在内地我们总可以见面,而且我有不少的话和你说。我在沪虽然寂寞,但我差不多整天在家读书译书,倘使身体好的话,我可以写出不少的东西,可是现在不行。冬天一过也许会好一点。《自传》原书确是不错,罗曼罗兰自己承认说,受了牠很大的影响。(探检)是科学名辞,意义较(探险)广,辞源上说得明白,许多人都以为(检)字错了,其实不错,桂林有图书馆,杨朔在那里时常常借书。你如不走也正好借这机会一面读书一面做事。杨朔有信来没有?你如有信给他可代我向他问好。我有一本散文集出版,你的通信处是否变更,我想送一本给你。别话后谈。祝
你好
十月卅一
从上述两封信看,巴金曾在战事初起后在汉口与孙陵见过面;分手后,巴金“一年来常常想起”未见面的孙陵,也曾各处打听他的消息;巴金还将孙陵的文章编入刊物《文丛》;孙陵曾致信巴金,在未收到巴金回信后继续给他写信,告诉他自己已“安抵桂林”的消息,而巴金在香港就曾托一个朋友带信给孙陵,接到孙陵信后又再次给他回信,表达着听闻他安抵桂林后的欣喜;巴金和孙陵还积极地策划着何时见面。显然,两人的交情并不浅,他们之间的往返通信应属于频繁之列。但遗憾的是,经笔者查阅1993—1994年间出版的《巴金全集》“书信编”、2003年大象出版社出版的《佚简新编》[2]、2008年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写给巴金》[3],以及2009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信函卷·第一辑》[4],仅《巴金全集》第22卷收有巴金1946年7月14日致孙陵的一封短简,而无巴金其他时段致孙陵的书信,也无孙陵致巴金的任何一封信函。笔者发现的那两封信,目前仅有唐金海、张晓云先生关注过,在《巴金年谱》和《巴金的一个世纪》都有提及。《巴金年谱》1939年7月下有这样的内容:
十九日 致现代作家孙陵信,载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桂林《笔部队》(创刊号)第一卷。云“近来身体不好,打算休养一下,同时在翻译一本克鲁泡特金的书”,打算在上海“住些时候写点译点东西出来,再往内地跑”。[5]527
而在《巴金的一个世纪》中,与此相关的信息内容如下:
七月十九日 致信孙陵,载桂林《笔部队》创刊号。云近来身体不好,打算休养一下,同时在翻译一本克鲁泡特金的书。[6]206
《巴金年谱》1939年10月下有这样的内容:
三十一日 致孙陵信(按:此信与7月19日致孙陵信,合题为《寄自上海》),载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桂林《笔部队》创刊号。云:“近来身体不好”,感到“寂寞”,但仍坚持“读外国文”,“预备短期内”译完克鲁泡特金的《狱中记》,并告之“打算去昆明过暑假,然后去桂林”。[5]531
而在《巴金的一个世纪》中,与此相关的信息内容如下:
十月三十一日 致信孙陵。此信与七月十九日致孙陵信合题为《寄自上海》,载一九四○年桂林《笔部队》创刊号。云:“近来身体不好”,感到“寂寞”,但仍坚持“读外国文”,“预备短期内”译完克鲁泡特金的《狱中记》,并告之打算去昆明过暑假,然后去桂林。[6]207
两相比较可知,《巴金的一个世纪》中关于这两封信的信息,与《巴金年谱》中的差异甚小。撰写者将这两条信息均置于1939年之下,将两封信的时间具体化为“七月十九日”与“十月三十一日”,体现了他们的基本判断。不仅如此,两位先生对相关信息的摘录显然都来自原信,因而所言也颇为准确。但或许是因撰写体例的关系,这两封信的全貌并未在这两本书中得到披露。遗憾的是,继《巴金年谱》(1989年)、《巴金的一个世纪》(2004年)出版之后,2004年至今问世的巴金书信集已有多种,如2008年大象出版社的《写给巴金》、2009年文化艺术出版社的《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信函卷·第一辑》,但这两封信始终都未获得面世的机缘,亦未受到其他人的关注。而当我们将两封信的原貌加以呈现后就会发现,第一封信末尾只署了“十九日”而无年月,第二封信末尾署了“十月卅一”而无年份,因此其准确写信日期并非不言自明。另外,从原信来看,巴金的言辞还透出一些重要信息,诸如他的香港之行,他此期在上海的著译计划及其对上海的观感等。为廓清相关问题,笔者将这两封信加以披露,并加以考证与释读,希望能引起学界对巴金与孙陵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探析。
二、两通书简的写作年月
在统计《巴金全集》“书信编”中相关年度里巴金的书信数量时,李存光先生都用了约数而非确数,其原因在于“巴金写信多不署年份,一些信件因受信人误记或误断收信年代,致使所标的年份不确”[1]268。巴金致孙陵的这两封信就都没署年份,而且第一封还没署月份。孙陵当年编辑时因时间距离颇短而并不会“误记或误断收信年代”,也不会“误记或误断”巴金第一封信中缺失的月份。但隔着久远时空距离的我们,只能根据巴金这两封书信及其周边信息中的蛛丝马迹来判断它们写于何年何月。唐金海、张晓云先生将两封信的写作时间分别锁定于“七月十九日”与“十月卅一日”,而又都置于1939年之下,是他们根据相关情况进行的判断。今日的我们在面对这两个文本时,毫无疑问应感谢他们的既有探索提供给我们的基石意义,但同时也应重审这种判断的准确性与合理性。
(一)考察两通书简的写作年份
首先,这两封信均载于《笔部队》第一卷创刊特大号,而该刊的面世时间是1940年1月15日,因此,这两封信的写作年份,只能是1940年1月15日之前。从孙陵在《笔部队》创刊号上所编辑的靳以、臧克家的书信来看,都是写于较早者置于前,写于较后者置于后,巴金之信被刊载时也应采用了同样的编排方式。从内容上看,巴金在第一封信中明确提及获知孙陵抵达桂林后的欣喜之情,第二封信言及的翻译、写作诸事又明显是对第一封信中相关言说的承续、展开与修正,故而这两封信间隔的时间不久,而且第二封信写于第一封信之后。因此,第二封信的落款“十月卅一”,就将巴金这两封信的写作时间,缩小到了1939、1938、1937年10月31日及其之前的某月19日。
其次,巴金在第二封信中明确提到了他在汉口提着大箱子逃难一事,从那以后他与孙陵已一年左右未再见面,所以他说“一年来常常想起你”。故而,巴金去汉口且与孙陵相见的时间是确定巴金这两封信写于何时的关键。我们知道,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在汉口召开,巴金其时还在上海忙碌,却被推选为四十五名理事之一[7]。1938年4月1日,署名莹的作者在《自由中国》的“文化消息”栏中发表了《巴金靳以将来汉口》一文[8],预告了巴金、靳以的行踪。但那个时候,巴金和靳以选择一起去了广州,并积极筹划《烽火》的复刊和《文丛》的出版事宜。1938年五六月间,巴金才和靳以一起去了汉口,但在那儿停留时间甚短。毕修勺曾回忆说,“一九三八年五、六月间,巴金也到武汉,我曾到旅馆里去看过他;我也曾告诉陈诚巴金在武汉的事。陈要我转达巴金,他将命令政治部和《扫荡报》给他一个名义,请他到前线去采访战况,写些文章。我把这个意思面告了巴金;巴金摇头。他不久就离开武汉到桂林去了。”[9]巴金的确是“不久”就离开了,因为6月6日巴金已经在广州而且遇上了大轰炸。这次异常短暂的武汉之行后,1938年9月上旬,巴金第二次去武汉。这次他和萧珊、林憾庐一起,经过整整七天的辛苦跋涉才终于抵达。就在这次的武汉行中,《自由中国》同人招待过他,《巴金年谱》记载说此期巴金“出席《自由中国》社同人举行的招待会”[5]503,那么,巴金肯定见到了《自由中国》社的主持人孙陵。也就是说,巴金和孙陵这次相见的时间——1938年9月上旬,应该就是他信中所提及的“一年来常常想起你”的计算起点,也应该就是巴金第二封信中所说的“去年”孙陵看见他带着书箱逃难的时间。那么,巴金的第一封信也就应写于1939年9月,或至少应是1939年,而非1938年或1937年。
最后,在巴金这两封信中的许多说法,均表明他的写信时间是1939年。比如第一封信中提到的“×××已去昆明读书。她也记挂你”中的“她”,当然指的是巴金的恋人陈蕴珍,而她是1939年夏考入中山大学外文系,又于该年转入了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就读。又如,第一封信中巴金提到自己“在外面跑了一年没有什么成绩”,这“一年”的时间,正是巴金离开上海与回到上海之间的时间差。我们知道,巴金在“八一三”淞沪战役之后,在上海参与了《呐喊》周刊的创办,该刊出到第3期时更名为《烽火》,另行计算刊期,在上海继续出版至第12期(1937年11月21日)。1938年4月,巴金和靳以一起离开上海去了广州,在那里复刊了《烽火》。此后,巴金辗转漂泊于武汉、香港、桂林、长沙等地,一直“在外面跑”。巴金此处“跑了一年”之后的时间,显然应是1939年。再如,第二封信中,巴金提到他“去年曾带了些书出外”,前面已言及“去年”是巴金在武汉见着孙陵的1938年,那么写信的“今年”自然就该是1939年。
综上可知,巴金致孙陵的这两封书简均应写于1939年。进一步说,第一封写于1939年某月19日,第二封写于1939年10月31日。
(二)考察第一通书简的写作月份
唐金海、张晓云两位先生在两本书中均认为该信写于7月,估计与他们整理的巴金去香港的线索有关。1938年九十月间,时在广州的巴金经常遭遇大轰炸,有时巴金就躲到香港去避难。在《巴金年谱》中,撰写者引了巴金的回忆文字——“我就到香港。那时我的行李放在萨空了处,后来他回上海,把我的东西转给萧乾”[10]——来作为支撑。由于萧乾在香港编辑《大公报》副刊《文艺》的起始时间是1938年8月13日,而巴金1938年10月20日才离开广州,1938年11月8日抵达桂林,因此,巴金去港避难的行李后来由萨空了转存萧乾处是完全可能的。《巴金年谱》1939年6月下即有这样一条信息:
同月 赴香港,到萧乾处取衣箱。(按:此衣箱原来寄放萨空了处,萨空了离港后,转寄萧乾处)“我去香港取回我在一九三八年广州沦陷前存放在香港友人处的衣箱。六月去港,住了不到一月。”[5]526
或许正是基于巴金的这一说法,唐金海、张晓云先生将巴金信中“我一月前由香港返沪”的时间确定为6月,由此推出他写信给孙陵的一月后就是7月。然而巴金此处所言的“六月去港”并未准确到具体日子,因此他回上海的时间可能在6月下旬,也可能在7月上旬或者中旬。
显然,要解决第一封信的写作月份问题,最关键处的确就在巴金言辞间的“六月去港,住了不到一月”,以及巴金致孙陵信中那一句“我一月前由香港返沪”。然而在现有的各种年表传记中,都没有准确提到巴金去港与返沪的时间,这确实给我们进一步辨析造成了困难。笔者广泛搜集资料,发现了以下几则材料,或有助于厘清这一让人困惑的问题。
首先,《巴金年谱》上册所载1939年7月的条目中,有这样一条:
同月 在港迎接途经香港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书的萧珊,并应邀一同参加萧乾的宴请,同席者尚有田一文等人。不久,在送别萧乾赴英国、送别萧珊前往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读书后返沪。[5]528
此段文字涉及了巴金在香港迎接萧珊、送别萧乾、送别萧珊与返回上海这四个时间,而又呈现出一个先后承接的序列关系。为弄清其间的关系,我们先来考察巴金在港接送萧珊去读书一事。我们知道,萧珊1939年夏天的确去了昆明读书,但她去昆明后先考的是已内迁至云南的中山大学。1939年8月4日,《中央日报》昆明版上有一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招收转学生》的广告,明确了该校二、三年级招收转学生若干名,男女兼收,而“办法分考试通信两种”,“凡有志转入本大学肄业之学生已到云南者须参与转学考试,经录取后为正式生”,招收的院系年级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文学院 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历史社会学系哲学心理学系二三年级”。报名期限及地点是“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在昆明大西门外龙翔街本大学招考办事处”,考试时间及地点是“考试九月一日起,时间地点报名期间公布”[11]。萧珊参加了这次考试而且被录取为外国语文学系的转学生。1939年9月,巴金“获悉萧珊考入昆明西南联大外语系,并偕女友王育常同住老西门外文林街女生宿舍”[5]531。考虑到香港到昆明所需的时间、萧珊考中山大学所需的时间、萧珊参加西南联大转学考试所需的时间,巴金在香港送别萧珊极可能是在7月而非8月。另外,年谱中提到巴金“在送别萧乾赴英国”后才离港返沪,这时间不确。因为萧乾于1939年9月1日才离港赴英读书。在当天香港的《大公报》副刊《文艺》上,他发表了《一个副刊编者的自白——谨向本刊作者读者辞行》,其中就有这样的言辞:“当您翻着这份报纸时,我便已登了一只大船。”[12]如果巴金送萧乾离开香港后才返回上海,最早就已是9月上旬,而他给孙陵写第一封信是在他回上海一月以后,那就得是10月了,这与那两封信所言的内容及其时间差不相吻合。换句话说,巴金并未等到萧乾最后离港的日子,而极可能是在他送别萧珊之后,就与将要离港的萧乾作别,然后离港返沪。与巴金送别萧珊去昆明是在7月一样,巴金辞别萧乾的时间,或也是那个时候。
其次,巴金在1939年8月12日曾写了一封信给杨静如,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信收到。知道你和蕴珍很熟,我很高兴。我早就希望你们能成为好朋友,现在知道这情形更放心了。……我哥哥还没有来。我写了信去催他。……[13]9
这里透出几条需要注意的信息:第一,巴金写信的1939年8月12日,是在收到杨静如告知她和陈蕴珍“很熟”的信息之后。杨静如曾回忆她自己去昆明的经历:“一九三八年八月,经过一个月的旅行,通过滇越铁路到达昆明,同一些平津流亡学生一道进了西南联大”[13]7。1939年8月,杨静如马上进入大二,对昆明已很熟悉,因此,陈蕴珍去昆明时,巴金曾拜托她去车站迎接。此后,萧珊在昆明的学习与生活均得到了她的不少照顾。巴金在这封回信中得知她和蕴珍已“很熟”,由此可以推知,杨静如写给巴金的信最迟要8月初发出,而她和陈蕴珍见面、熟悉起来的时间至少得是7月下旬。即是说,萧珊抵达昆明的时间得在7月,而她离开香港的时间,也应在7月。第二,巴金该信落款只署了“八月十二”,未标明年份。从信中所提及的“我哥哥还没有来”可知,当时的巴金正担心其三哥李尧林的情况。而李尧林抵达上海的时间是1939年中秋节。因此,该信被杨静如置于1939年之下是准确的。与此相关,在整理出的该信右上方有一个邮戳一样的标记,里面竖排写着“八月 寄自上海”,由此可知,巴金写这信时已经在上海。那么,巴金离开香港的时间,就极可能是在7月。
最后,关于巴金去香港、在香港的行踪,笔者查到了一则名为《巴金在香港》的报道。其中有这样的表述:“主持中国最前进的一个出版集团,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日前由上海来到香港,……在香港为料理各事,大概逗留三四周,以后要到国内看看,收集各方面的材料。”[14]从文字来看,这则报道是记者采访了刚到香港的巴金后所写,当时巴金还有好些事情需要去料理,故而记者说巴金“大概”会在香港“逗留三四周”。该则报道发表于1939年8月12日的《西安晚报》,估计有着曲折的发表历程。如果考虑到巴金去香港的时间以及这种发表的曲折,我们可以推知其写作时间是7月上旬。
综合以上论析,笔者倾向于认为,巴金1939年6月去了香港,在那儿迎接了萧珊、作别了萧乾,一直待到了7月上旬,然后带着自己避难时候的行李回到了上海。8月12日,巴金给杨静如回信,对她与陈蕴珍已成为好友感到非常高兴。8月19日,巴金给孙陵回信,谈及自己“一月前由香港返沪,最近不拟他去”,以及在上海多写多译的计划。10月31日,孙陵的复信已到了好多天,巴金再次回函,告知孙陵更为详实的计划。而这后面两封复函,即本文一开始披露的两通书简。
三、两通书简的多重价值
将巴金的这两封与孙陵的信放置于相关的时间与空间线索中,对我们认知1939年前后的巴金具有重要价值。
首先,这两封信的面世,为我们认识巴金1939年8—10月的著译工作及其计划、身体状况及其行程打算提供了重要入口。在第一封信中,巴金提到了自己正在“翻译一本克鲁泡特金的书”,又说自己打算在上海“住些时候写点译点东西出来”;对身体状态的描述是“不好,打算休养一下”,“上海空气很不好,我又常病,(都是小病)”,而他当时却“不拟他去”,想在上海作出一点成绩后“再往内地跑”。然而对于去哪里,何时去,他并没有明确,只说“明年将去昆明再转四川或桂林”。两个月后所写的第二封信中,或许是回应孙陵的疑问,巴金对著译计划、未来行程打算等都说得更为明确。在翻译方面,巴金明确告诉了他自己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狱中记》,而且补充说明道:“我几年前就翻译了一点,后来因为别的东西便将他搁下,这次预备将他译完”。除了详细告知孙陵关于《狱中记》的翻译情况外,他还新提及整理重印另外两部译书的计划:“又有两部译稿已早出版,但内有不妥处,拟整理重印。”对于写作计划,第一封信中并未说明,只是含混地表达了要多写点东西出来的愿望,但在第二封信中,巴金明确说:“还有一部未完长篇,也要把它完成”。对于身体状况,第二封信中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表述。他最初只简单告诉孙陵他身体有点不好、常生小病、打算休养的情况,到了第二封信中,巴金重提自己“近来身体不大好”,紧接着加上了“做事比较慢”,可见身体状况已影响到了他的工作状态。在随后的文字中,巴金不无遗憾地说:“倘使身体好的话,我可以写出不少的东西,可是现在不行。冬天一过也许会好一点。”与第一封信中偏于乐观的表达相比,这里已流露出对身体及其影响工作状态的担忧。与此相应,他在8月时虽感觉到“上海空气很不好”,然而常生病的他却“不想离开”,到了10月,他在“上海情形不好”之后紧接着就说“我想早日离开”了。至于离开上海去内地的打算,巴金在8月的信中只言及会往内地跑,但何时出去、走怎样的路线,则并没有明确下来,“明年将去昆明再转四川或桂林”的表述,充满了不确定性。到了10月,这些不确定性明显减少。他说把翻译任务、创作未完长篇的任务完成,“便可以去昆明了”,而这个时间“恐怕”是“暑假”。之后他说,“我打算在昆明过暑假,然后去桂林”。验诸巴金1939—1940年的著译状况、行止安排,这里所说的一些信息就都能落实。在著作方面,巴金提到的未完长篇即《秋》。该书稿完成于1940年5月,后由开明书店出版;在翻译方面,巴金译完了克鲁泡特金的《狱中记》,修改了旧译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改名为《面包与自由》,后来又重新出版了克鲁泡特金的《我底自传》;在行止方面,巴金1939年8月至1940年5月间异常辛苦地闭门笔耕,到1940年7月才离开上海,去昆明与萧珊一起过暑假,随后开始在重庆、桂林、贵阳等大后方城市间辗转漂泊。
其次,这两封信涉及到巴金1938年11月8日—1939年2月间在桂林的一些史实,为我们探析他1940年年底在桂林的遭遇提供了一点线索。1938年11月8日,巴金经过漫长而艰难的逃难历程后终于抵达桂林,住进漓江东岸福隆街的林憾庐家。从那时至1939年2月的短暂时间里,巴金在桂林经受着大轰炸的考验,遭遇了异常艰难的出版环境,却在桂林印出了两期《文丛》,即《文丛》第4期与第5、6期合刊。1938年11月25日,巴金将从广州逃难时带出的《文丛》第4期“浇成铅版、印成书,送到读者的手里”,了却了一桩心愿,同时“作为对敌人暴力的一个答复: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毁的”[15]。1939年1月5日,巴金在桂林为《文丛》第5、6期合刊写了《写给读者》。1月12日,巴金在致信杨静如时曾说:“我这几天正为《文丛》的事忙碌着。要到五六期合刊出版,我的工作才告一段落,这个月底我便可以走了。”[13]6《文丛》第5、6期合刊出版于1939年1月20日,然而巴金计划的1月底离开桂林却没有实现。个中缘由,或与过温州去上海的路途颇不平坦,需要请国民党官员给予照顾有关。笔者在《宋云彬日记》中曾看到这样的内容:“鲁彦得讯,其眷属过温州,仗伯涛之助,得安然乘轮赴沪。巴金亦将去上海,特为写介绍信一封,致伯涛。”紧接着1939年2月13日这则日记的,是次日的“李伯涛来函”[16]18,其具体内容应与他答应给巴金方便有关。显然,王鲁彦眷属经温州去上海而受到李伯涛之助的事实,促使巴金如法炮制,请宋云彬帮忙。此后,巴金和萧珊才一路有惊无险地从桂林辗转回到了上海。
然而,巴金与宋云彬的交情并不深。在宋云彬桂林时期的日记中,仅在1938年12月19日、1939年2月11日、1939年2月13日提到巴金。第一处内容为:
“午与鲁彦、舒群、巴金、杨朔、张铁弦、丽尼在桂南酒家午餐,商讨出版文艺综合半月刊,定名为《一九三九》,拟于明年一月五日出创刊号。”[16]3
巴金仅仅是被邀请者之一,而该刊物后续也没能出版。到了1939年2月11日,宋云彬晚上和舒群、傅彬然“在天南酒家吃饭,并饮三花酒约半斤。舒群先回其寓所。彬然偕余回寓,巴金、鲁彦亦相继来,谈至十时始散。”[16]18巴金、鲁彦与宋云彬谈的具体内容并未被他记录,但估计巴金曾言及拟离开桂林而请他帮忙一事。于是,仅仅两天后的2月13日,宋云彬日记中就有帮巴金向伯涛写信请他照顾的记载。可见,巴金与宋云彬的交往,远远赶不上他与杨朔、鲁彦的交情。宋云彬帮他忙,或许是他此期利用职位之便所做的顺水人情而已,是他此期帮助很多文化人的行为之一。或许正是因为两人交情之浅,1940年年底桂林文坛出现那股“研究巴金”“批判巴金”的潮流时,宋云彬才会在其中摇旗呐喊。
最后,巴金这两封信写于沦陷期的上海。透过其中隐晦的言辞,我们其实能品味到巴金困居上海期间的文化窘境以及他巧妙的文化抗战策略。这与《巴金在香港》的报道有关。该报道节选如下:
巴金在香港
主持中国最前进的一个出版集团,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日前由上海来到香港,他主持出版的两个丛刊(即文化生活丛刊及文学丛刊)的作品,的确予中国今日新文化运动以有力的推动,自抗战爆发,巴金仍把握着时代的潮流,稳稳的站立在他自己的岗位,始终留在上海,担负起文化界的抗战任务,虽然上海沦为孤岛以后,他并未因环境的恶劣而稍为动摇了他的岗位半步……他对记者谈起上海最近出版的情况……他说上海现在关于抗战的书籍受到摧残,虽然日本人还未能直接到租界来搜查,明目的逮捕,但他们当向工部局要人。现在最可恶还是自己中国人,所谓工部局下的“包探”,他们敲诈,没收,逮捕,使得出版界的工作人员到感到相当的恐怖的威胁,但虽在这样困难环境下,文化抗战的工作仍继续运行着,不过大家都学得更技巧了。最后谈到他最近的作品,他说他正在努力于一部长篇作品,《激流》,计划要写成六巨册,现在已经完成了二本,今后当然要继续把他完成。在香港为料理各事,大概逗留三四周,以后要到国内看看,收集各方面的材料。[14]
这则报道较为全面地呈现了记者对巴金从事的文化抗战工作的崇高评价、巴金对上海出版界情况的介绍,以及他自己的创作计划。如果说,这里面所言的“自抗战爆发,巴金……始终留在上海”的描述有失准确,让我们稍显遗憾,对巴金肖像的描写显出特有的香港眼光,但终究让我们因看到了战时的巴金形象而略显欣慰,那么,作者转述的巴金眼中的上海出版界,则因其透出了当时特有的意识形态氛围,而给了我们重审巴金致孙陵信函的新眼光。从报道中可知,1939年的战时上海出版界人士深感威胁,因为抗战书籍受摧残,日本人向工部局要人,工部局下的中国“包探”还不断实施敲诈、没收、逮捕等行为。在这样的“困难环境”下,巴金和其他作家一样,不得不采取更为巧妙的表达策略,曲折地进行文化抗战。巴金对于上海出版界状况的这种描述,展示了并不美好的政治生态,使得我们在重读他致孙陵的两封信时有了新的联想。在第一封信中,他有这样一句:“上海空气很不好,我又常病,(都是小病),但我不想离开。”在第二封信中则有这样的句子:“上海情形不好,我想早日离开。”显然,巴金特意拈出来加以强调的“上海空气”,既可能是实指上海的自然空气,也可能在隐晦地指向上海沦陷后糟糕的意识形态空气,而“不好”的“上海情形”,更直接地指向了不利于上海进步文化界进行文化抗战的意识形态背景。也就是说,1939年8月至10月困居于上海而想全力翻译、著述的巴金,一方面不得不忍受身体病痛的折磨,另一方面不得不抗拒整个恶劣政治生态的困扰。当他写信给朋友孙陵时,巴金只能隐晦地传达内心感受,而绝不能畅所欲言。可以这么说,此期的巴金,是在内外交困中顽强地进行着他寂寞甚至孤独的文化抗战。
四、余论
李存光先生曾用“折射心灵的多棱镜”来命名巴金书信,认为研究巴金书信之于走近巴金心灵具有重要价值,“书信可以使我们看到巴金更多方面的活动情况和人际关系、人际交往,看到他不同时期内心世界的更多侧面,看到他对彼时发生的各种大小事件更为真实的想法,甚至可以看到他的某些处事方式和性格特点。进而大有助于我们了解彼时的时代风习和特征,辨析考订巴金生平思想的若干疑窦。”[1]270然而,学界对巴金书信的研究“显得十分薄弱”,“巴金书信的价值和意义,似乎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除山口守教授对巴金与西欧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往还书信所作的系统考证、诠释和研究外,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我国学者发表有分量的论文,更不要说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了。因此,对于巴金书信的研究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和深化。”[1]274为促进巴金的书信研究,李存光先生曾说“要作整体观照,切忌断章取义”,为此,“就要做理清文本线索这个最基础的工作”,而这个基础工作,又可以从“纵的线索即时间线索”以及“横的线索即空间线索”两个方面来展开。在横的线索的研究中,“按信中涉及的问题、事件、情况等作专题研究”是其中重要一类。那么,一直以巴金为挚友的孙陵,是抗战时期与巴金有过深入交往的文人之一,将新发现的巴金致孙陵书简两通插入巴金书信的时间和空间线索中,恰是可以推进巴金研究的重要尝试,对于尚十分薄弱的孙陵研究而言亦具有重要价值。笔者此处对那两封信写作的准确时间的考证,及在此基础上所做的一些阐发,仅仅是诸多可行路径之一。更多巴金书信的发掘、考证与研究,尚需学界同仁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