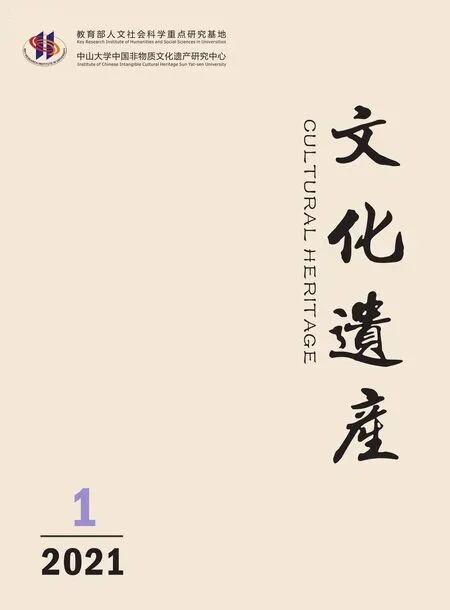现代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达与叙事
朱 伟
“当人类越来越了解外界与自身,依然需要幻想性的艺术创造。嫦娥住在广寒宫,玉兔在捣药,那棵桂花树开得正好,人物、动物、植物、建筑物,那是另一个世界。尽管我们已经知道月球不过是一个星体,但还是要保留这个美好的传说。尤其对孩子来说,刚刚认识月亮的时候,应该听到这样的故事,人类也需要保持这样的童心,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智慧,也是我们幸福感的来源。”(1)蒋肖斌:《一个节日的保护与传承:我们为什么要过中秋》,东方网,http://news.eastday.com/s/20180925/u1ai11845855.html,访问日期:2020年8月8日。2018年,刘魁立先生的这一席话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人们在关注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本体之余,让“为何保护”这一问题重新荡涤心灵,但是这背后隐藏着现实与艺术二元世界的话语体系。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探讨保存传统社会的文化表达,才更让人感觉真实与紧迫,或许只有“越来越了解外界与自身”,才能认识什么是“幻想性的艺术创造”,毕竟传统上二者是合而为一的。在某种意义上说,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之为“遗产”,正是由于社会认知发展带来的艺术创造与现实生活的脱钩。目前,关于非遗的表达与叙事也正在面临着一种抉择——是单纯尊重传统而成为现代语境中的“遗产”,还是抛开“地方性”成为追随社会发展的时代叙事?当然,还可以选择延续传统与追随时代的“中间道路”。对此,非遗实践中已经有不同方式的探索,但应当认识到,诸多文化事项虽然被具象为一个个非遗项目,并纳入国家保护体系之中,但是其文化的核心与根脉,仍在地方性的话语表述当中,正如广寒宫、玉兔、桂花树等意象都是建构在嫦娥奔月的传说之上,而非全人类共通的文化符号。
“过去,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文化交往通常是有限的,有时受地理或生态条件所限,有时是主动抵制与他者的互动”(2)阿尔君·阿帕杜莱:《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刘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28页。——这是传统社会的常态,表达与叙事往往是在社会文化内部进行,共同的文化逻辑是传统语境的前提。但是,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群体、社会之间持续的交往与互动,构成了当代社会的主流趋势与基本语境,而书籍、照片、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新媒体等间接沟通方式的增多,导致了人们“自主权的丧失和内部平衡的松懈”(3)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面对现代世界问题的人类学》,栾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7-28页。。或者可以认为,现代语境所对应的是对于传统的跨越,不仅仅是文化上的、社会上的跨界,还有场景和沟通方式上的转变,等等。当然,列维-斯特劳斯对于“不完美的艺术”在日本与西方社会中的相似表达,及其所代表的对于传统的普世观照,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借鉴。(4)列维-斯特劳斯提及欧洲对于所谓“原始”艺术的关注,与日本“不完美的艺术”的表述,其实是类似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面对现代世界问题的人类学》,第113-122页。近年来,“见人见物见生活”这一表述已经成为非遗保护最核心的话语,这背后隐藏着对于非遗存续现状的隐忧,以及发展的抉择。非遗要进入现代生活,其首要面临的问题就在于对民间话语与文化逻辑的转述。这种转述不单是语言的,行为、情感、认知等方面,乃至于表达方式都需要被关注。伴随着这种转述的知识再生产过程,民间话语被纳入更广阔的话语体系,从而成为地方性与全球化之间的衔接点。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与现代语境、全球化趋势等相背离的,是对于非遗的双重定位:一方面,人们强调非遗的地方性,及其在反抗全球化语境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地方性又成为非遗表达转述的桎梏,“保生存还是保文化”的矛盾不仅仅是小民族面对的问题,对于中华文化也具有普适意义,生存需要成为非遗接受现代表达与叙事、融入普遍意义观的根本动力。这个过程的是非对错难以判断,人们往往处身其中而摇摆不定,这也代表了社会普遍的态度。
一、 源自地方性的非遗叙事
非遗的地方性来源于其社会文化的“文法”,“有同一个文化的文法”是人们能够彼此之间进行表达、交流和理解的基础(5)麻国庆先生将文化的“有形”与“无形”之间看做“表达”与“文法”的差异,认为文化的表达是其外在的、可观察的部分,文化的文法“是深化在同文化个体中的内化的逻辑”,并且将非遗划分为“文化的表达(如艺术、音乐、文学、宗教、戏剧,以及像视觉、听觉、味觉所表达出来的文化的信息等)和文化的文法(如感觉、心性、历史记忆、无意识的文化认同、无意识的生活结构和集团的无意识的社会结构等)”。人们之所以能够熟悉彼此的行为模式,主要在于“有同一个文化的文法”。麻国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的表达和文化的文法》,《学术研究》2011年第5期。。如同世界上不同文化对于善恶、美丑的认知标准是不一样的,我们就常常惊诧于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审美;同样是神州大地,南北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性知识,笔者到广东学习生活近20年仍说不清楚,广州人吃鸡“有鸡味儿”是一种怎样的味道——与其说这种味道来源于舌头的感觉,不如说是建构在一种隐性的地方性知识之上,广州人说“无鸡不成宴”,孩子们对于“鸡味儿”的理解,就是每一次宴会从父母、家人的交谈中得到建构与强化。
事实上,我们对于宇宙、时空的感觉与认知,也是在这样的言传身教中得以建构,比如对于时间秩序的敏感性,来源于民间社会一整套的知识体系,北方民谚说“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隔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这种将时间与物候关系密切联系起来的表述,基于细致入微的观察,是与中国农耕社会的习惯联系起来的。当然,由此延伸而来的“数九寒冬”等地方性知识,也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笔者小时候家乡河北仍有“进九”“出九”的说法,人们也会对照着议论今年是冷了、暖了,以及春耕的时序等等;但是在广东,关于“数九”的说法基本不可闻。这种差异源于两地物候条件的不同,广东人重“冬至”,称“冬至大过年”,但是,冬至在广东民间的认知中是传统节日(6)张振江、陈志伟:《麻涌民俗志——岭南水乡社会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2页。,而不是农耕时序,冬至过后,广东民间也并非依靠“数九”来确定 农业生产耕作的时间。
这些就是农民认知中的天时,基于中国社会的“小传统”,而对于文人来说,时间的序列与农耕社会是大体一致的,但却有另外的传承方式,“我还记得,甫能握笔的时候,每个识字的儿童,在冬至那天都会分到一张‘九九消寒图’,用以描红的空白字: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从冬至第二天早上开始,每天在空格上按照笔序填上一个笔画——八十一天后,已是柳条垂丝,春天来了。对于传统中国的儿童,这就是一种注意时间的教育。中国人对于时间的敏感,也就是在这种环境之中培养出来的习惯。”(7)许倬云:《中国文化的精神》,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第27页。如今,互联网上流传着各种版本的“九九消寒图”,可以是“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也可以是一支九朵九瓣梅的图画,更可以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九个字等等,由此可见这种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变迁。也不得不说,随着农耕生活的远去,虽然“九九消寒”仍是各种各样的图示与场景,但是背后的时间感已经慢慢消失了。
“九九消寒图”与“数九”只是中国人时间认知体系的一部分,从更长时间段来看,则是“二十四节气”对于一年的划分,以及干支纪年的六十花甲子等。2016年,“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8)“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中国古人将太阳周年运动轨迹划分为24等份,每一等份为一个“节气”,统称“二十四节气”。具体包括: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二十四节气”指导着传统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是中国传统历法体系及其相关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四节气”形成于中国黄河流域,以观察该区域的天象、气温、降水和物候的时序变化为基准,作为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的时间指南逐步为全国各地所采用,并为多民族所共享。作为中国人特有的时间知识体系,该遗产项目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资料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 http://www.ihchina.cn/directory_details/12084,访问日期:2020年8月8日。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对于“二十四节气”的定位并非是单纯的时间知识体系,也包括了这基础上的实践活动,这也是文化的文法与表达的统一。作为二十四节气项目申报基础,我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有“农历二十四节气”,以及浙江、贵州、湖南、广西等地申报的九华立春祭、班春劝农、石阡说春、三门祭冬、安仁赶分社、苗族赶秋、壮族霜降节等。可见,二十四节气的观念与实践并非局限在汉族群体中,在苗、壮等民族中也有相应的民俗活动,而且各地区、民族对于节气的关注也并不一致。这些都是各地在二十四节气的知识体系中延展出来的独特风俗,是地方性表述。二十四节气的更替,是基于季节变化、气温变化、降水量变化、物候现象或农活的更替等(9)许倬云:《中国文化的精神》,第22页。,这些原则建立在中国传统农耕生活基础上,细微的变化都会对农作物的生长产生影响,如今的生产生活方式让我们不再关注这些细节变化,农业机械的应用让人们不再关注土壤的变化,水利灌溉的便利让大自然的降水成为可有可无的需求,农药的使用让昆虫、鸟兽等都与农业脱离了关系,而城镇化的发展让人们彻底脱离了农耕的生活。虽然,中国人的认知中还有“二十四节气”等一整套的观念,但是其日常实践已经越来越少了,人们对于这种时间秩序的感觉也将日渐淡化,或许可以认为,“二十四节气”代表的中国人的时间秩序,正向着一种符号化的表达发展。
我们强调中国人时间认知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并非来自于博物馆的藏品或碑刻的记忆,而应当是日常生活当中延续的,既有人们对于宇宙和时空的隐性认知,也有族群共同的仪式生活。在数九寒冬、二十四节气乃至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等时间体系的文化表达中,所隐藏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法,是根植于中国农耕文明的时间逻辑与工具体系。如今,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乡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趋向(10)石郑:《流动人口健康自评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江汉学术》2020年第2期。,让我们对于时间的认知也在发生着转变,基于西方文化传统的时间表达与中国传统的时间表达并行不悖,我们用公历计算年份、月份、星期、工作日,甚至小时、分钟等,这是我们与世界的衔接;同时,也在中国传统的时间体系中,标记着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等节日,这些节日所呈现出的民俗形态,是对中国人的社会、文化、信仰、情感、认知等方面的呈现(11)“中国的节日体系是一种成熟的文明的缩影。它既是我们先辈长期不懈地探索自然规律的产物,包含着大量科学的天文、气象和物候知识,也是中华文明的哲学思想、审美意识和道德伦理的集中体现”。高丙中:《民族国家的时间管理——中国节假日制度的问题及其解决之道》,《民间文化与公民社会:中国现代历程的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0页。。这些既是对于文化表达的延续,也蕴藏着文法的传承。
二、脱离传统的非遗话语权
文化的文法是地方性知识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属于“无意识地传承”,而对地方文化的表达则是“有意识地创造”(12)“今天,不同国家、地域和民族的文化其“无意识地传承”传统,常常为来自国家和民族的力量进行着 ‘有意识的创造 ’,这种创造的过程正是一种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实际也是一种文化重构的过程”。麻国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的表达与文化的文法》。,如今,在社会参与非遗的实践中,既有基于文化传统的“有意识地创造”,也有脱离传统的再创造,站在不同角度的人们会有不同选择。这种选择背后隐藏着人们对于话语权的博弈——延续文化传统的表达强调传承人的作用,而脱离传统或是反抗传统的“再创造”则关注他者介入所扮演的角色。同样是关注传统文化,不同的话语体系被创造并成为群体的表达符号,如国家话语以“非遗保护”强调主体地位,艺术界多以“民艺复兴”隐喻传统文化的自在状态,而“文化创意”则带有更多的实用主义的目的。
2015年,作为职业策展人的左靖在《碧山》策划了“民艺复兴”“民艺复兴续”两期,并在《民艺复兴 道阻且长》中称:“在我们从事百工调研的所有目的中,最重要的,是向手艺人学习,探索新旧事物的融合,实现民艺再生。即希望搭建一座设计师、艺术家与民间手艺人进行合作的桥梁,改进和创新民间手艺的工艺和设计,使之适应现代生活的需求,让手艺以及手艺所承载的农耕文化因子传承下去。”(13)左靖主编:《碧山·民艺复兴续》,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卷首语。可以看到,即使抱着民艺复兴的目的,在这里笔谈的也都是艺术家、策展人、设计师和研究者,没有一位是民间艺人、非遗传承人。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艺术家、策展人、设计师等所做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与列维·斯特劳斯对于探险的批判是一样的(14)“现在,探险已成为一种生意。探险者并不像一般所想的那样,辛勤工作努力多年去发现一些前所未知的事实;现在的探险不过是跑一堆路、拍一大堆幻灯片或纪录影片,最好都是彩色的,以便吸引一批观众,在某个大厅中展示几天。”克劳德·李维史陀:《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14页。。其中,有一位研究者笃定的说,“在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羊拜亮所掌握的黎族原始制陶术确实已经更换了主人”(15)谭红宇:《对真实的理解与还原:我拍〈泥中有我〉》,左靖主编:《碧山·民艺复兴》,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207页。。或许这一观点有独特的语境,但其背后是艺术界对非遗保护介入文化传承发展的隐性批判,也正是二者之间的区别所在。
其实,不管是艺术家、策展人、设计师或研究者,在不同的场域中发出声音,或是从自身的角度,或是以非遗传承人代理的身份——传承人在这些场域中是缺位的。这些声音一方面为诸多的传承人建构出一种泛化的形象,或是默默无闻的匠人,或是遗世独立的隐者,等等;另一方面也在建构一种话语权力——为传承人代言的权力,艺术家、策展人、设计师和研究者向圈内、学界乃至社会传达出传承人的欲望与诉求,传递传承人背后的文化与情感。作为文化持有者的传承人,则被簇拥在众多艺术化、学术化的表达之中,对于非遗传承人来说,以这样一种方式,是否能够真正的融入现代社会呢?
面对当代艺术、当代设计,非遗所面临的窘境是什么,或许可以从一件作品的创作中得到启示。2011年,以“from余杭”为主题的“余杭纸伞的未来”专题展览在米兰设计周一鸣惊人,而以纸伞技艺制作的《飘》的椅子,成为文化创意设计的经典。其策展人详细梳理了“from余杭”的策展工作流程:“第一阶段是研究分析余杭纸伞的优缺点,然后针对其缺点一个个寻找解决方案;第二阶段是改进,从油纸伞的使用体验、防雨性能、重量、材质意义上进行改良。……最具启发性的还是第三阶段的工作……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纸伞的衍生产品上,一根毛竹,五根棉线,十八张宣纸,三十六根伞骨,七十多道工序,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仅是纸伞而已。……从伞到灯,从灯到收纳容器,最后到纸椅,仿佛越走越远,但始终沿用纸伞的制作工艺。”(16)周舟:《从融化到融解:来自「融」的实验》,左靖主编:《碧山·民艺复兴》,第58-59页。策展人或设计师更加强调结果的发散性,从纸伞到纸椅的转折具有符号化的意义,设计师也说,“对于当代设计来讲,手工艺只是个载体,它并不是必需的。手工艺出现的意义仅仅在于,当你的设计需要涉及手工艺的时候,你就去研究它。当你的设计中不需要手工艺出现时,不要强求自己特意运用一些手工艺在其中,不要为了拯救手工艺去做一些设计,这是一个伪命题。”(17)周舟:《从融化到融解:来自「融」的实验》,第60页。应当承认,设计师有其立场,“设计时代的来临,意味着过去的文化的教条都不存在了,生活方式已没有限制的条件,完全由个别消费者所决定。从另一个角度看,世上各民族的文化传承不再被视为规范,而是庞大的资料库,供设计者自有取用。这是一个失去共通准则的时代”(18)汉宝德:《文化与文创》,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110页。。但是,这种设计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文化失去其社会背景与固有逻辑,设计师既可以用纸伞技艺制作椅子,也可以在上面绘画、雕刻……全世界的文化元素和符号都可顺手拈来,荟萃在同一件作品上。可以说,失去了社会伦理规范的艺术创作过程,对于传统文化发展是一种悲哀。
延伸来讲,近几年在非遗保护领域中职业策展人的出现,确实为各种非遗展览带来了新意与亮点,但是过于注重设计感而忽视文化逻辑、注重物的堆砌组合而轻视人的位置等问题已经逐渐反映出来。这些主题展览中,传承人的位置是可以被取代或撤销的,表明了人的位置无足轻重,这与单纯从设计的角度策划一场展览又有何区别呢?当然,不管是从设计角度,还是策展的角度,这都提出了关于话语权的问题。我们看到,非遗传承人的话语权正在受到冲击,失去了原本已缺乏的与外界对话的权力,他们被掩藏在设计或展览之中,成为一件附属品,一如20世纪初许多关于原始文化的展览(19)“作为展品,附属国的人们被说服去为观众提供生存在别的世界的经验;他们置身于‘真正’的村庄,按要求为参观的人群重新表演他们的日常生活。” 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86页。。在非遗保护的各种展览中,活生生的传承人被“陈列”与“安排”在展览空间中,成为展览艺术呈现的附庸,甚至成为众人关注的“表演者”。“2009年2月的‘传统民间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展出了超过2,300件中国传统工艺品。来自130个国家级和省级的非遗艺人即席演示。从这个角度看,这次的展览比其他非遗的相关展览更为‘活灵活现’。然而,如果没有艺人坐在展览陈列前面,这次展览和此前其他展览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20)金瑾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性——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例》,廖迪生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东亚地方社会》,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香港文化博物馆2011年,第431-432页。
如今,这种展览的呈现方式,已然成为非遗展陈的主流,因为缺少了“人”的参与,确实很难表现非遗的“活态性”。有研究者关注到这一点,并尝试进行改变,将传承人作为展览的核心——2016年,“云泽芳韵土布展”作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性别与民俗”工作坊的配套展览,其关注的张凤云、杨美芳两位农村妇女,分别是山东鲁锦和上海土布的传承人。“该展览共展示了分别来自中国鲁西南和上海地区的两位女性非遗传承人不同人生阶段的一百多件手工纺织作品。展览通过对作品、技艺以及个人生命故事的入微解读,试图构建起时代、家庭、女性与纺织的社会全景,以期唤起观者对于中国传统手工织布技艺这一非遗事项的关注。”研究者将该展览作为“自我民族志书写”指引下的非遗展陈,在其叙述过程中不乏作为“他者”的解读,如第三部分“母亲”的描述:“从把嫁妆中几件自己的夹衣改为孩子穿用,以及一些拿到市集售卖的布匹,可窥探到两位女性沉重的家庭经济压力,须通过更多的纺织劳作来补贴家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阶段随着工业化机械纺织品大规模进入民众生活,纺织原料有了部分改变,图形与花样也受到了一定影响,这暗示着两位女性既有对新生事物的尝试与接纳,却也固执地坚守着手工织布的代际传承。”(21)关于“云泽芳韵土布展”的案例研究,详见方云《跨学科视域下的博物馆非遗类展陈——以“云泽芳韵土布展”为例》,《东南文化》2018年第1期。此外,以展厅的空间区分对应地理空间,以纺织品色调与图案等代表地域文化特色,以织机暗喻时光如梭,但两位活生生的非遗传承人仍只是展览互动中的“表演者”……
其实,不管是设计师、策展人还是研究者,相对于处身民间的非遗传承人,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有一种优越感,这大概与个人的修养、情感等没有直接关系,而是这些角色互动中所赋予的一种话语优势。这种优势源自于二者在文化生产与消费体系中扮演角色的不同。全球化大市场体系下,生产与消费的时空错位(22)“生产与消费的时空错位,这是当下全球化大市场体系带来的弊端之一,也将是文化创意产业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必然面临的问题”。朱伟:《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意产业》,《文化遗产》2015年第4期。,给设计师、策展人、研究者、艺术家等各色人物成为中间人的可能——他们既把普世的价值观念、审美追求等传递给传承人,也将传承人的自我表达转述成艺术化表达。传承人却往往处于局外人的状态,(23)田阡:《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路径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4期。或成为被艺术话语摆布的表演者,成为现代艺术表达的附庸,如同安顺地戏在《千里走单骑》中被称为“云南面具戏”一样(24)邓尧:《传统守望: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问题调查与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65-170页。,这其中并不仅仅是关于非遗署名权或版权的问题,更多的是话语、权力带来的伦理问题。
三、谁来讲好非遗故事
传承人作为让非遗绵延不绝的核心,其地位不可替代,而非遗传承人发出自己的声音,让时代、社会真正认知非遗,而非循着他者的声音进行表演,这应当是让非遗“见人见物见生活”的基本要求。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要让非遗传承人的声音有力量,就不能以敝帚自珍的心理来重复古人的故事,更不能以抱残守缺的态度来应对时代的发展,当然也不能单纯的为他人作嫁衣裳——这应当是传承人在传承发展中要把握的尺度。要讲好非遗的故事,也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传承人对于承载的非遗资源要有清醒的认知,对社会、时代也要有所关注,“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时代怕是一去不返了。要如何通过讲好非遗的故事,让其融入现代生活,佛山木版年画传承人刘钟萍的探索与尝试,或许对我们有几分启发。
木版年画从来不是日常生活必须品,而是传统春节祈福纳祥的民俗用品,冯骥才先生称其为“年俗艺术”(25)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的价值及普查的意义——〈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总序》,《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佛山木版年画历史起于宋、兴于明,盛行于清代至民国初期。佛山木版年画以用途分为如下几类:一是门神画、门画,供岁时节庆张贴在户门、厅门、房门等处,以《持刀将军》《加官进爵》《财神》《状元及第·天姬送子》等为代表;二是神像画,是人们请回家以祈求驱邪镇宅、福瑞降临等,传统上这是佛山木版年画的大宗,有《北帝座镇》《关帝座镇》《和气生财》(26)俗称“和合二仙”。《天官赐福》《引福归堂》等;三是观赏画,即用于观赏的木版年画,有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画(含戏出年画)、装饰画、祥瑞画等种类,如《水浒传》《二十四孝图》《封神演义》《八仙过海》《童乐图》《老鼠嫁女》等;四是民间工艺配画,即为佛山彩灯、剪纸、扎作等民间工艺和商品包装等提供配料,如《夜战马超》灯画、《陈姑追舟》剪纸配料等;五是信仰祭祀用品画,常见有纸马、神衣、符箓、签解、疏咒、冥钱等;六是商业广告画,多为利用木版刻印工艺的商业宣传广告等;七是其他类型,如描红习字贴、稿纸、信笺、地契、税单、地图、戏桥、合同、条例、榜文等。(27)程宜:《佛山木版年画历史与文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9-70页。佛山木版年画“鼎盛时期,拥有200多个生产作坊,4000多名从业人员”,到20世纪末,“冯炳棠……目前是佛山木版年画唯一能将雕版、套印、开相、写花、描金、填丹等整套工艺流程全部熟练掌握的艺人”(28)程宜:《佛山木版年画历史与文化》,第276-277页。。
笔者与佛山木版年画接触近十年,起初每年有年轻人学习年画,但每年换不同的面孔,只有刘钟萍走出了自己的年画之路,其网名“年画女侠”更为年轻人所熟知。如今,“年画女侠”已经成为佛山木版年画在年轻人中的代言人。她把传统年画与人们的心理需求结合起来,创造出“诸神复活”系列的年画解读。比如,将传统年画《持刀将军》解释为“掂过碌蔗”;《和合二仙》称为“喜神”,被赋予“脱单神器”的寓意;《状元及第》称为“考神”,寓意“逢考必过”;《天姬送子》是儿女双全的“二胎神器”;《财神》的小目标是“赚一个亿”;《紫薇正照》为“新房入伙镇宅神器”……这些对传统年画的阐释既源自于传统的民俗寓意,又结合了当代的网络语言,让年画受到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喜爱。同时,这种做法也让年画逐渐突破了只在春节期间张贴的传统。当然,这种尝试也带有强烈的个人特性,她把年画店称为“解忧年画店”,她抓住了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点,不仅让“年画重回春节”,而且让年画满足人们越来越多样的预期,这是对于美好生活的真正回应。如同陈岸瑛所说的,“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上,古今其实是相通的。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他乡遇故知,也同样是现代人的憧憬,虽说换了场景,可内在的情感还是类似的。”(29)陈岸瑛:《年画如何走进新年俗场景》,《光明日报》2019年1月30日第13版。如今,我们仍很难说佛山木版年画真正实现了复兴。一方面,家家户户贴年画的旧俗确实已经远去了,年画从传统年俗的必需品变成了如今的文创产品,虽然受到人们的喜爱,但其赖以存续的文化生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另一方面,“诸神复活”对于年画图案意义的解构,也突破了民间艺术的边界,传统上“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民间艺术,是基于地方性的文化表达,而在现代语境下的佛山木版年画,不仅仅是其叙述方式和内容,其背后隐藏的地域界限、文化逻辑也被网络叙事所同化了。
现代语境下的非遗叙事,不仅仅是通过对于文化传统的重新阐释,使非遗从地方性话语转换为现代性的文化表达,进而赋予其普遍性的意义;另一方面,也通过现代传媒等手段对传统知识与实践有选择性的处理,进而构建出非遗的新形象与业态。这种方式在现代市场化的运作体系中屡见不鲜,许多企业、传承人和非遗从业者不断尝试将品牌与非遗直接等同起来,其中尤以饮食类项目为多,比如“鹃城牌”之于郫县豆瓣传统制作技艺、“全聚德”之于烤鸭技艺等等。笔者也曾经探讨过关于凉茶文化表达的转型。喝凉茶原本是岭南民间养生保健的一种文化实践,对应岭南湿热的地理和气候环境,带有强烈的地方特性,是中医“冷热”观念在地化所形成的民间认知与实践,其中有一整套的文化认知,比如什么人适合喝什么凉茶、什么症状需要喝什么凉茶、什么时节应该喝什么凉茶……,这些都是广东人心照不宣的经验。直至如今,老广州人心中的凉茶就是街边的凉茶铺子、大铜壶,而王老吉也只是岭南数十种凉茶品牌之一。就是这样一个老字号,通过“怕上火喝王老吉”这一广告词,曾经成为全国人民眼中凉茶的代表,其市场销量也呈几何级数增长。(30)朱伟:《文化创意语境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博学刊》2018年第4期。王老吉的火爆也带动了广东凉茶行业的市场化运作,基于现代叙事所建构出的“品牌”也成为争议的焦点。如今,关于凉茶的叙事各式各样,但是都没有如同“怕上火喝王老吉”一样,建构出一种符号化的形象——其中“怕上火”这一概念,将凉茶与中医的阴阳平衡的观念,以及民间对于“上火”“热气”等的认知相衔接,让凉茶具有了一种文化上的功能。这一点确实抓住了消费者的心理。
在这些案例中,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是非遗传承人还是从业者,他们在面向公众、面向媒体、面向现代的叙事中,并不是把非遗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事项来进行表述——整体表述应当是文化传承的职责,而非社会和公众的关注点。他们通过选择一些特殊的符号、形象和知识,并将之加以放大或改造,使之成为与现代生活相衔接的渠道。佛山木版年画的“诸神”,传统中没有保佑生二胎(儿女双全)、逢考必过、赚一个亿……那么直接、那么具象的功能,但正是对诸神功能的重新阐释,让不同人群的心理需求得到满足。关于凉茶的叙事则是将其与“上火”的认知对应起来,并进行无限放大,诸如工艺、配方、种类等都进行了模糊处理,特别是岭南地方传统中不同凉茶对应不同身体症状的知识,被这一叙述所格式化了。可以说,这些叙事方式是基于传统的,而非凭空捏造出的创意,但这些叙事的成功之处在于对传统知识的改造,而非整体的照搬。
四、结语
如今,非遗融入现代生活、“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已经成为社会共识,非遗保护与传承面临着新的转型发展期,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将非遗作为一种文化资源,越来越多的现代表述融入对于传统文化的叙事之中。这在为非遗传承发展提供了新的面向的同时,也对于传统的表达与叙事产生了冲击与影响。过去近二十年间,伴随着不同话语介入非遗保护与传承中,非遗传承人进行着不同的选择,有许多传承人仍旧“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守着传统的手艺与记忆;有许多传承人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交界的门口,有“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之惑;还有许多传承人已经在前路禹禹独行许久,有“谁与我逝兮,吾谁与从”的感慨;更有许多传承人彻底抛开了传统的束缚,拥抱新的世界。
面对传承人的不同选择,以及社会的不同面向,我们应当对非遗的表达与叙事予以审慎的关注,既要避免非遗脱离其存续的文化背景和文化逻辑,成为一种纯粹的庸俗化表达;也应当避免单纯以“遗产”自居,无异于将活生生的文化送入供人指指点点的展柜。在现代语境下,让非遗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让传统文化重回生活,这一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在于:谁在掌握文化表达的权力,表达对象又是谁,传承人处于何种位置;对于非遗的表达与叙述是否代表文化持有者的认知与意愿,是否能够完整呈现其框架、细节乃至文化背景;是否对某些隐性知识进行了取舍;文化表达是否会对原有文化形态产生影响,等等。在“不断发展的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混乱以及交通和沟通方式的快速增长打破了这些障碍”(31)此处“障碍”是指“人类以社群的形式长久地分开生活,而且无论是从生物学角度还是文化角度来看,每个社群都是以不同的方式演进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面对现代世界问题的人类学》,第124页。的同时,现代语境给非遗,特别是传承人所带来的,是一种艰难的抉择,这种困境如同幻灯片一样,被投射在人们在现代语境下对于非遗的表达与叙述之中。或许,要达到刘魁立先生所期许的,“使某个地域或民族的非遗具有全人类意义,受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关注和保护,美美与共,世界大同”(32)刘魁立:《非遗的赓续,靠传承,也靠传播》,杨红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传承到传播》,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Ⅲ页。,这便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理想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