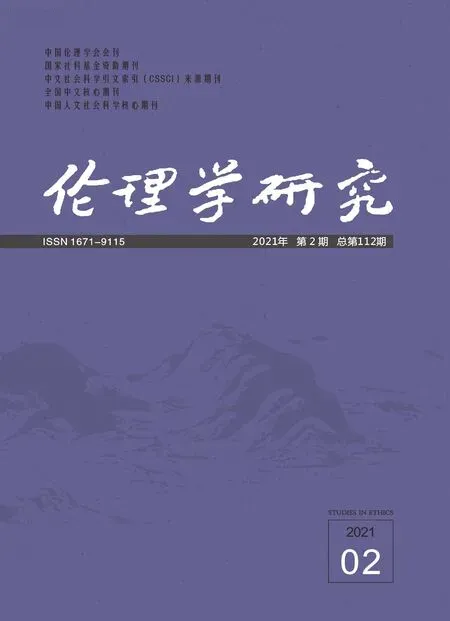论杜威对康德义务论的批判
康德的义务论作为西方义务论伦理学的典型代表,深刻地影响了康德之后的伦理学发展。由于康德过于苛求行为的道德属性只在于对道德法则的纯粹符合,而排斥一切经验因素作为道德动机的内容,这与现实的道德经验存在一定的张力,由此招致诸多伦理学流派的批评,包括功利主义、情感主义、自然主义等,它们认为康德的义务论与现实道德行为的某些属性、特质或价值相背离。不过这些伦理学流派也仅是强调道德行为的某个或某些特征,而并未真正地从完整的道德生活出发,其自身的理论依然面临着各种挑战。而杜威的情境伦理学把道德行为置于整个真实发生的道德生活过程之中,一切道德的规则和价值都来源于道德主体的伦理世界之中,正是基于此种伦理学立场,杜威坚决批判康德义务论,认为康德义务论的问题源于未奠基于真实发生的道德行为,进而导致对义务概念的误解,杜威对康德义务论的批评不仅仅限于义务论本身的理论问题,而是进一步指出义务论问题只是整个康德哲学体系的二元论问题在伦理领域的表现,他试图从源头上诊断康德义务论问题的哲学根源。
一、社会关系中的义务:杜威的义务观
杜威理解道德现象的视角是一种发生学的立场,他认为若没有基于这样一种道德如何发生的实情来讨论道德问题,产生各种纷争和诘难是难以避免的,而他认为一切道德行为都发生于道德世界之中,对道德行为的理解和探讨也须处于这一前提之下。杜威对道德世界的理解和他的经验自然主义立场紧密相连,我们形成关于世界的认识之前我们已经处于世界之中,我们时刻在通过各种经验的方式与世界打交道,认识只是我们打交道的方式之一。同理,道德世界只是我们所经验到的世界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我们基于道德方式所经验到的世界,所以承认我们已处于道德世界之中的事实是谈论一切道德问题的前提。道德世界并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与人的活动紧密相关,杜威说:“(在道德世界中)存在着某些必须持续被满足的意欲、某些要求合作性活动并在人们之间建立起固定关系的目的。”[1](P294)杜威认为道德世界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道德生活本来就是包含欲望满足的,任何一种把欲望排除于义务准则考虑之外的理论都是对道德生活的误解,把欲望满足和义务分离开来的结果就是取消了行动的动力,进而把道德行为变成一种对外在法则的顺从[2](P285);其次,伦理世界中的个人都是与他人处于协作的活动之中,由此也就形成了整个社会关系,脱离社会关系来谈论任何道德规则或价值都是抽象的;最后,伦理世界中的道德法则不是人为任意制定的,而是用来表达行动主体的意志之间的某种关系,这些道德法则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一种能动的关系,它可以把不同的个人统一起来,并且让他们拥有共同的目的和承担义务[1](P297),所以义务的产生并不是个人意志的结果,而是在道德法则所表现的能动关系中发生。
接下来一个问题是义务为何会发生于社会关系之中?杜威认为这是个人要实现个体性而必须履行的活动。在杜威的理论中,个体性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指特定的能力,包括特殊的性情、气质、天赋、爱好、自然倾向等;另一方面则是特定的环境,包含个体的特殊位置、情境、环境、机会等,它不是物理环境,而是与行为者实践相关联的道德环境。个体性中的能力与环境是相互依存的,正是能力才使得环境成为相对于个体而言的环境,而能力只能依赖于环境才能成为真正的能力,否则就是空洞的。所以任何个体性的实现都需要个人能力和道德环境相统一,这种统一的获得就是个体性不断实现的活动,任何个体性的形成都是在特定环境中把个人能力展现出来的结果。杜威用功能这一词语来表达个体性中这两方面的联结,个体性的不断实现就是越来越好地履行其功能,而这两个方面缺失任何一方都不会让个人实现自己的功能。杜威举例说,履行一个学生的功能,不仅仅是内在地培养趣味的事情,也要符合各种外在的要求,包括老师的要求、他人的要求等。如果没有内在的自然倾向,那外在的符合就是僵化的举止或者单纯的服从,如果没有外在的要求符合,那内在的自然倾向只是一种消极的欲望[1](P285)。所以,外在的与要求相符合就是义务,它是与内在的自然倾向相联结,而且义务并不会让内在的欲望任意表达,而是把欲望转化成为一种更自由的形式,义务变成欲望的法则。而义务作为一种来自道德环境的符合性要求,实质上也就是来自社会关系,这一社会关系是个人实现其个体性的外在条件,所以义务的具体内容也是由社会关系来规定的。
杜威把义务奠基于社会关系之上,这一社会关系并不是后天人为建构的,而是随着每个人作为个体一诞生,社会关系就成了人的一部分,没有社会关系也就无所谓个体,杜威说:“社会纽带和联系,是出于本性的、必然发生的,就像它是肉体性的一样。”[2](P290)正因为社会关系是人的本性之一,所以由社会关系所产生的义务就不是外在的,也不存在不自愿的问题,义务成为自己去行为的内在动力。杜威还举了一个有关孝敬义务的例子,如果只从道德动机的纯粹性角度来看,孝敬父母的义务很难普遍一致地成为个人心甘情愿的内在动力,因为孝敬自己的父母有可能与自己的某种欲望相冲突,比如孝敬父母的同时可能会丧失另一个人生重要机会,这就让孝敬变成一种被迫行为。但是在杜威看来这种解释完全是外在的,任何个人都生活于家庭关系之中,也就处于父母与后代的关系之中,由这种关系所提出命令或要求都是个人作为其中一员的整体表达,对自己父母的热爱推动着去回应孝敬父母的要求,即使这一要求与自己的某种欲望相对立,个人并不会把这一孝敬当作异己的东西,而是出于家庭关系的内在本性,是因为自己是家庭关系中的一员。正是因为社会关系的内在本性,使得义务成为自己内在的行动动力,比如爱护国家的义务不是因为国家给自己施加了某种外在的压力,而是因为自己属于社会的一员;帮助朋友的义务不是因为来自某种道德信条,而是因为自己与对方是朋友关系。由此可见,杜威把传统义务论的纯粹义务转变为一种由特定社会关系所生发的一种义务意识,所有的义务都是特定情境中发生的。
履行源于社会关系的义务之所以是自愿的,因为这是自我实现或自我完成的内在要求和外在条件。在杜威看来,这一自我实现就是善,也是行动的目的和理想,但这行动的理想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情境中的,杜威把它称为预见中的目的(end-in-view),它是与行动后果连在一起的,任何行动的展开都是朝向某种目的,这一目的就是预期的后果,此后果便是自我实现,所以对预期后果的追求也是履行义务的内在驱动力。正如前文所述,基于个体性角度来说,对预期后果的追求也是个人欲望的展现,义务和欲望是互为作用的。在此,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欲望,杜威认为传统义务论把欲望贬斥为一种放纵的、低级的自然倾向,这实际上是对欲望的错误理解,杜威认为人类的欲望分为两种,一种是即时直接的欲望,表现为当下满足自然本性的欲望,另一种是作为整体的人的欲望,是为遵循周围环境需求的愿望,表现为通过考虑到长远后果而激起的欲望,是对预期目标的欲望。但是,这两种欲望会经常出现冲突,当下欲望的满足可能会损害长远目标的实现,所以这时候道德就能够协调两者的关系,但是道德不是否定欲望的存在,而是让它转化成比原来更为适当的形式,并逐步变成预期的行动,所以在“道德上不存在欲望和思想的分离,因为正是思想与欲望的结合使得一种行动称为自愿的”[2](P241)。任何观念若没有与欲望相结合,它就只是一种纯粹观念而已,而不会转变为现实的实际行动。
正是因为社会关系都是具体时空中的,义务的产生也必然是情境之中的,不可能根据某种固定的外在法则来判定行为的道德属性,因为有可能同一种行为在不同情境中的道德属性是相异或相反的。任何义务行为都是作为某一个特定的历史过程,履行义务作为动机和追求预期目的作为后果,都是这一过程的组成部分,强调任何一方面都是对这一真实发生的道德经验的人为割裂。在杜威看来,传统义务论者过于强调行动的动机作为衡量道德属性的标准,后果主义者重视行为后果来评价行动的道德属性,这都是对道德诸要素的选择性重视,并未真正地反映真实的道德生活经验[3](P46)。这种选择性的重视实质上是从一种理论反思的视角来看真实的道德行为,如果以一种参与者的视角来理解道德生活,就不会把道德行为中的动机或后果独立出来变成决定性的因素。在杜威看来,这样的一种对待道德生活的理论态度反映的是悠久的西方哲学传统,即二元论的传统,“杜威把动机与后果作为独立道德评价的做法视为古老二元论的另一负面遗产,此二元论把世界分割为可变的自然世界和不变的超越性世界”[3](P48)。换言之,传统西方伦理学无论义务论还是后果论,都接受了西方理智主义传统,认为道德生活是变动不居的,自身不能提供道德行为的规则,而只能依靠理论认知的方式来为道德行为提供固定的行为原则,每一行为的价值就在于与固定原则的符合与否。由于这一原则不是源于实践活动,对道德行为来说依然是外在的,由此以康德为典型的传统义务论始终都面临如何让普遍的义务原则变成道德主体具体的义务意识和道德动力。而杜威的义务立场是直接针对康德义务论的,杜威通过对康德义务论的分析和批判,既展示了传统义务论的理论困境,同时也呈现了杜威义务观的合理性。
二、杜威对康德形式义务论的批评
根据康德的立场,实现行为的道德价值不能去预期任何后果,也不考虑一切经验内容,而只需让行为的准则去符合实践法则的普遍要求即可,康德把这样的一种要求称为义务,康德试图通过这样一种只符合纯粹法则要求的义务论,来使道德变成像自然领域一样可以奠基于普遍规律之上,因而称之为“为义务而义务”。但是在杜威看来,康德把义务规定为对道德法则的无条件服从而排除一切经验因素的考虑,而现实中的行动者都是充满冲动、欲望、情感和目的等自然禀赋的直接行动者,这就意味着康德所规定的道德义务是与行动者的自然禀赋直接对立的。杜威认为康德的义务论面临两个难题:第一,由理性的意志所产生的普遍法则意识如何转变为具体的特殊的意志意识,后者是每一个具体行动的推动力;第二,纯粹的义务意识如何确保让行动者愿意无条件地去履行这一义务呢?[4](P277)杜威的这一批评是直击康德义务论要害的,康德在论述道德法则的现实性时也确实面临这一问题,一方面有限理性者意识到纯粹理性要求自己按照法则的普遍性来行事,同时又认识到普通理性让自己选择自爱原则或幸福原则来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康德把这一矛盾的解决寄托在意志对实践理性法则的尊重而产生的无条件服从之上,这便是绝对命令的服从,但是这种服从的前提是行动者认识到这是最高的善,而这在现实的道德经验中是无法确保实现的,康德也只能把它当作是一种应当。
毫无疑问,杜威并不认为康德诉诸绝对命令的方式解决了义务论中所面临的问题,只是把这个问题展现得更加彻底而已。因为在杜威看来所有的行动都是具体情境中的,如果以普遍的法则来决定具体行动的准则,那首要的问题是如何把基于纯粹理性的普遍法则要求转变为具体情境中的行动准则。根据康德对普遍法则的规定,行动者愿意让自己的行动准则变成普遍的法则,但是所有的行动都是具体情境中的行动,不同行动的情境并不相同,当然也就不存在普遍一致的行动准则。由此,杜威极力反对把康德的义务论作为日常行动的道德基础,他说:“康德信奉的逻辑使得他强调说义务的概念是空洞的和形式的。它告诉人们,尽义务是自己最高的行动法则,可是一谈到人的义务具体是什么便不作声了。”[5](P125)很明显,康德的义务论是不可能规定具体行动中的义务内容的,因为一旦道德的动机涉及经验内容,那就有可能使道德不是出于义务了,最后导致道德行为的准则不可普遍化和道德价值的丧失。因此,康德的义务只能是行动者在自身中对道德法则的意识、尊重和履行。杜威认为康德的义务完全是一种内在意识的问题,同时也是纯粹的形式主义,当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把具体的义务内容和准则让渡给外在的权威。一个持康德义务论立场的人可能是一个完全顺从外在权威的人。杜威说:“缺乏内容的义务准则自然有助于圣化和美化现行国家秩序可能规定的那些具体义务。”[5](P126)在杜威眼里,康德的义务论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无法为具体行为提供道德指导的问题,而且可能会因为无法确定义务准则的困境而服膺于外来的权威[6](P543),所以杜威才说康德的道德哲学可能会带来一种服从天职的社会和国家哲学。
杜威认为康德的义务论的困境根源在于被传统的二元论立场所桎梏,传统二元论把世界划分为现实的可变世界和理想的不变世界,这是为了满足确定性的需求而人为地割裂统一的经验世界,包括自然世界和道德世界[7](P104)。而康德的道德哲学立场正是基于这样的二元论路线之上,他把道德经验中的现实经验当成是无序的,有待认识主体根据实践理性给意志提供的道德法则来对其进行规整,决定行为的道德价值的正是这一法则,服从来自理性的这一道德法则就是人的义务。康德的义务论未能考虑“是什么”的现实问题,而只一味追求可普遍化的“应当”,而这在杜威看来正是康德义务论的最大问题。杜威认为“康德伦理学的失败之处:在区分‘应该是什么’与‘是什么’的时候,它剥夺了后者,即现存的社会世界以及具有一切道德价值的个人的各种欲望;而通过同样的区分,它又把应该的事情指责为贫乏的抽象。”[1](P283)在杜威眼里,如果作为道德要求的“应当”不是来自现实世界的“是”,最后这种“应当”只会沦为美好的愿望而已。虽然康德也把作为义务的“应当”变成现实性的基础奠定在自由意志之上,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行动者必定会按照实践法则的要求来行事,但是康德无法解释自由意志的来源,只能说它是一个理性事实。这一理论困境的根源在于康德未能从真实的道德生活出发。我们现实的道德生活本来就是集自然欲望和行为准则于一体的经验整体,追求冲动、欲望、欲念和强力的满足和解放是人的自然倾向,这就是我们道德生活的“是”。
当康德未从道德现实的“是”出发来考虑“应当”时,这一“应当”当然也不会适用于现实的“是”。康德的义务论完全排斥欲望对道德行动的参与,无论这种欲望是为自己的善还是为他人的善。康德对欲望持否定的态度实际上是对现实“是”的否定,康德义务论的目的是让行动者追求一种基于“应该”之上的“是”,或者说追求在义务前提之下所建构的道德现实。在杜威看来,这种把义务与欲望置于完全对立的立场并不会导致真正的道德行为的发生。他说:“现实的欲望或欲念不是它们所应当是的东西。这种说法就其自身而言很正确,但当康德接着说,就像他实际上所做的那样,应当是的东西就不能是现存的东西,欲望本身不能带入与原则的和谐关系之中,他就使道德生活不仅成了一个谜,而且成了一个没有答案的谜。”[1](P282)这实际上是把现实的道德生活认作不道德的东西,急需外在的道德法则来拯救现实的道德生活,这无疑是缘木求鱼的事情。
杜威认为普通行动者都是根据道德行为后果以及所处的环境来理解义务概念的,因为所有的道德行为都是发生于情境之中。但是康德把义务概念抽象成为形式上的与法则相符合之后,义务就变成了一个脱离现实经验的对象了。杜威说:“在‘为义务而义务’这种观念形成时,情况就是这样。此时,义务这一观念被与具体处境的要求隔离开了,它变成了一个偶像。”[2](P285)杜威认为任何现实的义务观念一定包含对后果的考虑,因为行动者必须基于现实后果的考虑来理解义务观念。杜威认为康德对义务的阐述也离不开对后果的涉及,他说:“康德陈述的道德法则的另外一个公式表明,康德的普遍性虽然不是以正式理论的形式,但在实际上暗含着对社会后果的考虑,而不是不考虑一切后果的。”[2](P285)杜威为何会这样说呢?因为康德在谈论义务法则“除非我愿意自己的准则也变为普遍规律,我不应行动”的时候,其中的“愿意”已经预设了对后果的考虑,即允许行动者通过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是否接受别人也以自己的行为准则用于自己身上,也就是是否接受自己的行为准则用于自身的后果。而且康德在多处阐述关于诺言的例子时也印证了这一点,通过作出假诺言来帮助自己脱离困境,行动者是否愿意让它变成一条普遍规律?很显然,行动者是不愿意让假诺言变成普遍规律的,“因为按照这样的规律,也就不可能作任何诺言。既然人们不相信保证,我对自己将来的行为,不论做什么保证都是无用的。即或他们轻信了这种保证,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回报于我。这样看来,如若我一旦把我的准则变为普遍规律,那么它也就毁灭自身”[8](P19)。
很显然,在杜威看来,康德为了让普通理性者能够遵守道德法则的要求,也是承认了行动者会基于现实后果的考虑来理解义务的原则,这也是康德为什么要从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来过渡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的原因,但是他囿于自己的先验哲学立场而不承认义务概念来自现实的道德经验。杜威认为康德的这一做法让义务概念脱离了它本来所依赖的道德生活经验,而变成了一个抽象和空洞的原则,实现这种义务需要对一切自然善进行排除,道德就是意志对道德善的追求同时不考虑对自然善的满足。在杜威看来,如果基于康德对善的理解,会出现可笑的事情。杜威举了一个关于母爱的例子来说明:一个母亲基于自己的本能会毫无保留地照顾自己的孩子,毫无疑问这位母亲的行为从自然本性上来说是善的,既满足了自己对孩子的爱,同时又促进了孩子生存的需要。但是,如果基于康德义务论的立场,这位母亲要使自己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善的,就必须抑制住自己对孩子本能的爱,不能让它成为自己行为的动机,而是让对普遍法则相符合的义务成为自己去对待孩子的动机,结果就是“她的行动如果出于本能之爱,在道德上就不是善的;如果在后果上促进了她年轻孩子的福利,在道德上也不是善的。”[2](P281)最后的结果就是母爱是非道德的,这在杜威看来是有违常理的结论。
三、两种批评与回应
对于杜威把义务观念奠基于社会关系之上并以此来批评康德义务论的做法,当代学者提出了一些质疑,其中最为典型的质疑之声有两种,其中一种是对杜威把义务奠定于社会关系之上做法的可行性质疑,以实用主义哲学研究专家托德·莱肯(Todd Lekan)为代表,另一种是对杜威用参与者视角代替康德旁观者视角的合理性质疑,以伦理学专家黑尔(R.M.Hare)为代表。杜威把义务概念建立于社会关系之上,他并不认为这是自己所提出的一种理论假设,而是基于道德生活的发生过程所揭示的结果。我们的社会关系作为联结不同个体的纽带,它总是携带或蕴含着某种公共利益和价值,它是每个道德主体的意志表达,也是每个道德主体追求个人之善所依赖的前提,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个体必然会对这样的公共利益和价值有所体认和感受,体认后的结果就是主动接受和履行由社会关系所产生的义务。托德·莱肯对杜威的立场提出质疑,他认为杜威把义务奠基于社会关系之上的做法过于理想化,因为即使杜威考虑到不同的社会关系具有不同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价值利益,所产生的义务是不同的,但是杜威没有考虑到处于社会关系中的行动者是否能够理解和知悉自己所处的位置,以及由此社会关系位置所蕴含的义务内容。托德·莱肯并不认为所有人都能做到这一点,他说:“至少关系中的单方面有能力把自己设想成有责任作出并接受要求的道德行为主体。然而,涉及小孩及其他有感知能力而理性未成熟的存在主体的主张的事例证明,这部分群体并不总能清楚表达他们的要求,甚至对他们在关系中所处的角色并无概念。”[9](P141)在托德·莱肯看来,小孩就未必能够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位置,更何况其中所包含的义务主张。可以说,托德·莱肯的这一质疑对杜威的义务观构成了某种挑战。
如果从整体上来把握杜威的义务观,就能够发现托德·莱肯的质疑实际上是一种误解,他并未对杜威的义务立场构成真正的挑战。杜威认为不具备成熟理性的人并不会面临无法发现和履行由社会关系所产生的义务的问题。以孩子为例,“孩童生来就是一个家庭的成员,随着他的成长,他发现他人具有某些他必须予以尊重的东西,就是他会偶然接触到财产制度。当他成长得足够大时,他发现他必须顾及家庭外的人的行动,就像尊重他自身的行动一样,于是他发现了社会,这个词在狭义上是指特殊的亲密关系或交往关系”[1](P294)。杜威并不是以一种静态或固定的视角来看待孩子的成长环境,而是从一种生存论的视角来看待孩子社会关系的形成。孩子的社会关系是随着他的世界的展开而不断形成的,他会逐渐地发现社会关系的差异和不同要求。但是这里的“发现”并不需要达到托德·莱肯所理解的理性认知,而是随着孩子参与共同行动而引发的心智行为,这种心智行为是通过行动的方式把社会关系的意义呈现出来,比如在家庭生活中,小孩子有些行动需要得到父母的许可、禁止、帮助甚至是强迫、命令等,小孩子在这样的共同行动中逐渐领会自己在家庭生活中的位置,能够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情与其他行为之间的关联。杜威说:“明白一件事物的意思,并不只是对这事物有了感官上的知觉而已,而是能够考虑这事在全盘行为中的地位而反应,是能够预知这事物与自己彼此影响的趋向和可能带来的后果。”[10](P28)孩子正是在这样一种家庭生活实践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位置,能够通过自己与父母的互动建立意义关联,否则自己的行动就会处处碰壁,孩子最后能够理解来自父母的命令和要求是什么,并且知道即使自己有抵触心理也必须参与其中,久而久之就会把这些要求和命令与自己所依赖的家庭关系联结在一起。这是一个实践认知的过程,而不是托德·莱肯所理解的理性认知。
杜威认为康德义务论是在传统二元论思维下采取旁观者视角的结果,应该以参与者视角的义务立场取而代之。当代伦理学专家黑尔(R.M.Hare)对此表示质疑。黑尔认为杜威试图以参与者立场把义务观念奠基于道德生活的做法不具有现实性,因为杜威忽视了道德反思对于义务观念形成的重要性。如果把义务只置于道德主体的道德经验历程之中,道德主体无法从参与者的视角抽身出来的话,他只能停留于“直观层次”(intuitive level)来理解义务观念,而由于人的直观能力的局限性,这决定了他不能完全把握到义务观念的全部面貌。黑尔甚至认为处于此种状态的人都无法弄清颜色和道德属性两者的实在性差异[11](79)。他进一步说,正是我们从来就没有只停留于“直观层次”,而是同时进入到了“批判层次”(critical level),我们才能说我们对某个或某类对象有不同的道德关注,比如在对待朋友和对待陌生人时表现出不一样的情感倾向。我们对某个对象可能会产生一种直接的义务感,正如杜威在分析个人处于社会关系中所产生的直接义务感一样,但是黑尔认为此种直接的义务感并不能变成行为的道德理由,只有进入到“批判层次”的反思阶段,个人才能从这种直接的义务感中发现真正的行动理由。为此,黑尔反驳了杜威关于母爱的例子,他说如果母亲身上有一种博爱的倾向,对所有人都施予同等的爱,那她的孩子们就不可能获得额外的母爱,但是现实中为何母亲对自己的孩子会给予无限的爱,就是因为她意识到这是她的孩子,把她的孩子与其他人区分开来这是一个反思的结果[11](P137)。黑尔认为康德从一种旁观者的理论视角来反思行为的道德根据,让行动者思考是否愿意让自己的行为准则变成普遍的法则,这一做法既是道德行为发生的条件,也是道德理论产生的必要手段。因此,黑尔认为杜威直接从道德生活中产生义务行为的做法过于理想化,不具有现实可行性。
很明显,黑尔对杜威的观点是存在误解的。黑尔看到了杜威从道德生活中的参与者视角与旁观者视角的区分来批判康德义务论,旁观者视角是以一种理论反思的态度对待道德生活,而忽视了反思道德生活的前提即自己也已经处于道德生活之中。在杜威看来,康德义务论的困境正在于此。但是杜威并不反对置于道德生活之中以参与者的视角来反思批判道德行为,反思本来就是道德生活的重要部分,而且是道德理论或思想得以产生的契机。为何会如此呢?因为道德主体在道德生活中很容易出现价值信念冲突,按照之前的道德习惯已无法处理目前的道德问题情境,必须经过反思批判的过程,把相对立的价值、信念、原则和目的进行反思,然后寻找某种适合的原则来作为自己做选择的依据,“在面对道德困惑,开始怀疑如何做是正确的或最好的,开始通过那种将把他引到他认为是可靠的某种原则的反思来寻找其他方法”[2](P209)。为此,杜威还举例说,一个爱国的公民被国家命令要支持对另一个国家的战争,热爱国家和遵守法律已成为他的习惯,按此习惯他理应支持国家的战争行为,但是他又知道这场战争是不义的,他应该反对这场战争,两种价值信念存在冲突,这时他无法按照原来的道德习惯进行选择,“为了做出决定,他被迫进行反思。道德理论就在于他现在正进行的那种思考的一个一般化的扩展”[2](P211)。因此,杜威非但不排斥反思在道德行为中的作用,而且把它置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杜威所反对的是把自己从道德情境中抽身而出的静观式反思。基于此,黑尔的质疑并不构成对杜威的反驳。
结语
杜威的义务论完全是置于他的经验自然主义体系之下,他反对任何超出道德经验之外的道德理论,一切道德理论和价值都发生于经验之中。义务作为道德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不但属于道德生活,而且源于道德生活,前者表明不存在如何从纯粹的义务形式变成情境中义务内容的问题,后者暗示了义务很自然地就是道德主体的行为动机。杜威不满康德义务论的关键之处在于康德无法证明道德主体对纯粹实践理性法则的尊重如何变成现实的道德动机,原因就是康德完全忽视了真实发生的道德生活历程,当然也就无法揭示义务的真实性。道德生活形成义务最直接的环节就是社会关系,正是社会关系让每一个人能够确立自己作为个体在群里中的位置,同时也就规定了个体的义务内容。这一义务内容并不是外在力量所强加的,而是随着自己与他人交互活动的展开而产生的,它既是个人自我实现的需要,也是与他人顺利进行交互的必要条件,义务的权威来自共同体的要求与利益。社会关系作为个体的道德环境是处于情境之中的,所以由社会关系所规定的义务也只能是情境性的,义务的普遍性无法按照康德所要求的一致性来实现,只能基于社会关系的互惠性原则。杜威坚持一种情境主义的义务观并不追求建立一种脱离经验的道德理论,而是致力于解决道德主体在道德实践过程中所出现的情境问题,任何道德理论和思想都只是人类道德实践过程中解决问题的可用资源。义务必须成为个人道德实践中可达到的道德理想,而不能是无法触及的空洞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