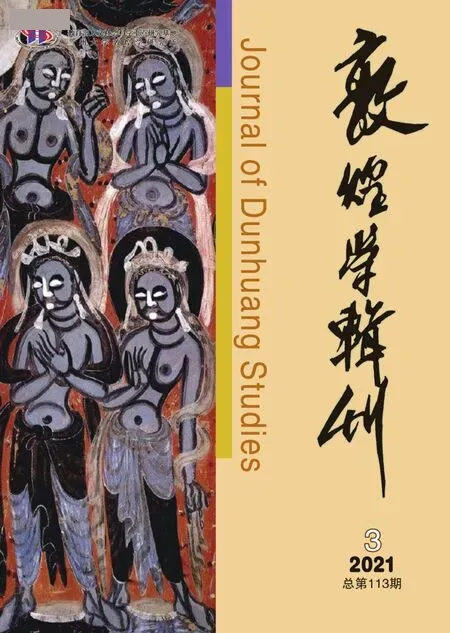兰薰桂馥 恩泽长留
——怀念关注与支持新疆龟兹石窟研究事业的前贤
霍旭初
(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2)
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从文艺工作转到文物工作岗位,主要工作对象是新疆历史文化遗产中驰名中外的龟兹石窟。面临这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和责任所负,犹如千钧重担压身。但我知道,眼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学习、再学习,尽快用与文物工作相关的知识武装自己,然后是实践、再实践,踏遍石窟开展观察、思考与资料的积累。于是如饥似渴地读书买书与踏遍石窟,劳神与劳力相结合成了我新生活的常态。中国学者提倡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精神,我是有深刻体会的。在这个历程中,我有机会接触到我国著名的学术先辈,他们中有享誉世界的硕德大师,也有才华横溢的学术新秀。他们的卓越成就与学术风范是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中,获得最宝贵的财富之一。他们对我的恩泽,不是仅对我个人的施与,而是他们对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敬畏与忠诚的体现。龟兹石窟研究事业取得令人触目的成绩,与这些对龟兹石窟事业关怀备至和倾力支持,甚至献身的精英们的贡献密不可分。关心与支持龟兹石窟事业的精英前贤很多,我这里仅回顾与我接触交往较多、受其影响较深的几位前贤的往事。
一、瀚海文豪——忆冯其庸先生
青年时,我读过冯其庸先生《红楼梦》研究文章,对这位“红学”泰斗,早有敬仰之情。后来又读过冯先生一些文史篇章,进一步领略了冯先生的博学。我喜欢书法,冯先生的书法令我久久注目品味。多年来,冯先生一直是我崇仰的国学大师之一。可我只是一介之士,仅有想拜见这位贤达之愿望,而无与冯先生谋面的机遇与途径。
自我从艺术创作转到新疆佛教艺术研究岗位上之后,在不断充实基础知识中,又读了不少冯先生的国学文章,特别是关于西域文明的论述,使我受益匪浅,觉得一下子与冯先生的思想贴近了许多。虽然没有当面聆听过冯先生的讲授,但我自当是冯先生的学生。冯先生的国学思想与著作,是我研究龟兹学重要的知识与理论源泉之一。
我与冯先生是有缘分的,虽然与先生见面次数不多,但先生对我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最初与冯先生发生联系是1994年,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筹办“纪念鸠摩罗什诞辰1650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前,决定在克孜尔石窟树立鸠摩罗什铜像,筹备组同志一致意见,请冯先生题写像名。经过联系,冯先生欣然应允。我们很快得到了冯先生题写的“鸠摩罗什像”,从此先生的墨宝就与鸠摩罗什铜像珠联璧合地伫立在克孜尔石窟前,供八方游人瞻仰与观赏,成为新疆著名旅游景观之一。
1995年8月,冯先生第五次来新疆考察,8日抵达克孜尔石窟,遗憾的是,当时我不在克孜尔,没有见到景仰多年的冯先生。后来我回到克孜尔,时任龟兹石窟研究所所长的陈世良先生,将冯先生署名赠我的《瀚海劫尘》图册转给我。同时告知我,冯先生关心地询问了我的情况。我迫不及待地翻开图册,首先拜读了冯先生的“自述”,刚看了几行就深深吸引了我,先生在赞颂玄奘排除万难的伟大意志力后,写了“不有艰难,何来圣僧?”先生思路和逻辑之不凡,使我更为钦佩。当我看到先生叙述“大西北”情结的文字,特别是“我向往中国的大西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坚信伟大的中华民族必定会强盛!而强盛之途除了改革、开放、民主、进步而外,全面开发大西北是其关键。”我领略了一位不仅仅是才华横溢、诗画纵横的贤人,而且是心系祖国、纵观古今的爱国精英的襟怀。所以他涉大漠、历雪岭、踏玄奘之足迹,扬“中国脊梁”之精神,寻访新疆历史古迹,完成了十次新疆探察的壮举。尤其是看了先生《玄奘取经东归入境古道考实——帕米尔高原明铁盖山口考察记》后。对冯先生追寻圣迹,探索真理的豪情,肃然起敬。冯先生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训的典范。先生的这种精神给予我长期扎根龟兹石窟,在“西域佛教”领域苦苦求索,探秘真髓,以巨大的感染和激励。
冯先生深深热爱龟兹这片土地,对龟兹的山山水水充满至爱,他两首《题龟兹山水》诗:
(一)
看尽龟兹十万峰,始知五岳也平庸。
他年欲作徐霞客,走遍天西再向东。
地上仙宫五百闉,赤霞援接北天门。
平生看尽山万千,不及龟兹一片云。
(二)
流沙万里到龟兹,佛国天西第几支。
古寺千相金拨落,奇峰乱插赤参差。
曼歌妙舞归何处,西去圣僧亦题词。
大漠轻车任奔逐,苍茫唯见落晖迟。
第一首气势磅礴,意冲霄汉;第二首怀古情深,隐喻幽远。
我1958年入疆,曾走遍大半新疆,越大漠、穿戈壁、踏草原、登雪岭、游林海、驻绿洲,深刻感受到新疆山川的壮美秀丽,新疆悠久而厚重的历史文明和当今各民族的灿烂文化,都使我倾心陶醉。而龟兹之地更是我魂牵梦萦的热土,揭示龟兹佛教与石窟的奥义,是我后半生追求的目标。对龟兹的感情,我没有文采的笔力,抒发不出深埋内心的情怀。冯先生这些绝句,拨动了我的心弦。每当我往返于库车、克孜尔石窟之间,经过盐水沟,看到“刺破青天锷未残”的千峰叠嶂时,总要联想起先生荡气回肠的诗句,顿时心潮澎拜,激情满怀。
与冯先生会面,终于到来。我有幸于2004年9月21日在新疆军区第三招待所拜见了冯先生。冯先生热情接待,攀谈许多。鉴于先生刚从南疆考察归来,奔波劳累,不忍久留,就告辞了。初见冯先生,他那魁梧身躯、博学善谈、音容笑貌,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从此我与冯先生“神交”结缘多年,冯先生也在不断关注我的情况。有一件事让使我永铭在心:上世纪80年代,随改革开放的深入,新疆历史文化研究进入了发展新阶段,各类研究成果纷纷涌出。佛教艺术研究硕果不断,研究形势令人可喜。但是,在新疆也出现了一些违背历史,不严肃的论说。如龟兹石窟壁画中有“生殖崇拜”“龟兹石窟裸体壁画领先世界”“裸体是对佛教‘禁欲主义’的挑战”“画师有意突出裸体以宣扬‘人性’”等,甚至与鸠摩罗什“破戒”拉扯上。还有对壁画内容作断章取义、望文生义式解释,壁画内涵被扭曲。另外一种现象,是根据壁画上不可靠的迹象,就论断某物品的年代,做出了不符历史的结论。凡此种种,给学术上造成很大的麻烦。这些学术上“急功近利”,追求“轰动效应”的不良之风,在新疆有蔓延之势。针对这种现象,新疆一些学者,开始发表争鸣和辩真的文章。因为情况比较复杂,总感觉缺乏理论要领,需要有纲领性的理念作引领,直至赵朴初先生发表了《佛教画藏系列丛书总序》,才有了明确的方向和理论指导。赵老这篇纲领性文章,是佛教义理与佛教艺术研究的科学辩证法。我拜读后,思想豁然开朗。随即写了一篇《赵朴初先生〈佛教画藏系列丛书序〉释读》作为学习心得与思想武装,想以此对上述现象开展进一步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文章发表后不久,就从北京朋友处传来冯先生表示赞赏与支持的口信。冯先生的鼓励,使我信心倍增,勇气大振。
我觉得,学术道德与治学态度是个根本性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搞学术离不开“二重证据法”的准则。许多人都说学术要“考证”。但态度不端正,“考证”就不靠谱。关于“考证”,我曾学习过古人的“考证学”,拜读过季羡林先生关于“考证”的论述。上述文章发表前,我又重温了冯先生为柴剑虹先生《敦煌吐鲁番学论稿》所作的《敦煌吐鲁番学论稿书后》中的重要论点:“当前学术界有一部分人对考证颇有微词,觉得考证烦琐,考证似乎是多余的等等。我认为这种认识是不对的,甚至是危险的。可以说研究中国的文化历史而不作考证,是根本研究不下去的,只要在传统文化领域内的研究,就离不开考证。剑虹同志的文章之所以有很强的说服力,就是因为既有‘考’而且更有‘证’。有的‘考证’之所以遭人讨厌,是因为实质上根本不是考证,只是冒用‘考证’这个容易唬人的名字,在‘考证’的名字掩盖下骋其臆说而已。”先生这段精辟论述,我体会甚深,新疆佛教艺术研究上的许多问题,就出在冯先生指出的症结上。
冯先生许多有关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学的论述,对我的影响也是很深刻的。关于“国学”,冯先生说:“国学作为一国经典之学,不是一成不变的,隋唐时期的国学要比春秋战国时期的丰富,明清时期的国学要比隋唐时期向前发展。随着历史的发展国学越来越丰富。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我们应将西域学、敦煌学、简帛学、汉画学列入国学研究范围,国学才能发展。在东西方文化交汇融合的同时我们应当立足于国学,因为她是中华民族之魂。”(《冯其庸谈国学》)。季羡林先生也说:“国内各地域文化和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就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后来融入到中国文化的外来文化,也都属于国学的范围。”(《季羡林说自己·镜头人生》)。二位大师的论断,是我们立足“国学”,开展“龟兹学”研究的思想基础与行动指南。
对于龟兹佛教艺术,冯先生也是用力观察与精心研究的,《对新疆石窟艺术的几点思考》一文,涉及到龟兹佛教艺术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如龟兹壁画的绘画技法、菱形构图的含义、“有翼神像”与乾闼婆、飞天的来源、克孜尔“画家洞”画师的族属与画具等,都细致观察、入微考证,旁征博引、见解独到,足见先生深厚的研究功力。为当今龟兹石窟艺术研究的学术表率。
冯先生走了,请允许我按佛教理念来思维,用佛教语言来譬喻,如今冯先生的“生身”已经“解脱”,进入了“无余涅槃”的境界。而先生的“法身”(精神与思想)仍在世间,先生的“遗法”(作品与言论)常驻人间,与我们永远在一起。就我而言,我的陋室悬挂着先生赐予我毛主席“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词句的匾额,每日抬头可望。先生的《瀚海劫尘》与《冯其庸书画集》等著作,就在手边。如果去到我的工作单位,首先进入眼帘的是“新疆龟兹研究院”的墨迹,然后即可看到“鸠摩罗什像”“耆婆湖”(为鸠摩罗什母亲而立)的题书。如果到古龟兹故地——库车县,“龟兹乐舞广场”和“苏祇婆之像”苍劲有力的墨迹伫立在县城中心广场上。先生还有一幅献给龟兹音乐源泉“滴溜成音”的题字,但遗憾没有镌刻出来。冯先生对库车建立“龟兹乐舞广场”非常重视,当时请冯先生赐墨时,先生年事已高,身体羸弱,但他欣然答应,提笔挥成。这是冯先生奉献给他热爱的龟兹土地最后的遗珍。
最后,我想用先生《瀚海劫尘》的自题诗,来表达对尊敬的瀚海文豪——冯其庸先生的怀念之情:
瀚海微尘万劫波,天荒地老梦痕多。
我来吊影沦漪促,留与沧桑劫后佗。
二、良师益友——谭树桐先生
1987年初冬的南疆,虽然风和日丽,但已是寒风箫瑟,朔气袭人。但更让人寒心痛楚的是:10 月 24 日我国著名美术史专家谭树桐先生在赴克孜尔石窟途中,于乌什塔拉镇东一个道班前,所乘汽车发生车祸不幸遇难。噩耗传来,震惊了全国美术界。我国失去了一位成就斐然的学者,新疆学术界失去了一位可敬的良师益友。
谭树桐先生青年时期就读著名的北平京华美术学院,师从美术大师黄宾虹。毕业后从事美术教育工作。解放后在中央美术学院和文化部艺术局工作。1958 年到中国美术研究所从事中国美术史研究。改革开放后,谭树桐先生将研究方向从中原文化转向边疆民族文化,从传统绘画转向宗教美术。于是他遍历我国南北诸石窟、寺院,多次越天山,历大漠考察新疆佛教遗址。他还赴印度、缅甸等国访源寻迹。谭树桐先生在深厚的功底基础上,广收博取,厚积薄发,在佛教艺术等领域取得瞩目的成就。
谭树桐先生先后 6 次来新疆,除了考察古代艺术外,还对当今新疆美术创作研究,给予热心的关怀和帮助。当然,贡献最大的还是在新疆古代艺术方面的研究。1981年由谭树桐先生任主编,日本美乃美出版社出版的《新疆の壁画》2卷本,是新中国建国以来首次介绍以克孜尔石窟为中心内容的新疆石窟壁画大型图册,图册中刊载了谭树桐先生的《克孜尔壁画赏析》(日文)文章。图册在日本编辑出版后,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对新疆古代艺术走出国门,展示龟兹石窟壁画艺术,弘扬中国优秀文化遗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考察和掌握新疆古代艺术遗产基础上,谭先生写出了一批有质量、有特色的文章。代表作有:《丹青斑驳 尚存金碧——新疆石窟壁画艺术赏析》《龟兹菱格画和汉博山炉》《阿斯塔那唐墓佣塑艺术》等。这些文章既有宏观的文化交流背景阐述,又有微观的艺术技法的剖析,是新疆古代艺术研究的佳作,对当时刚刚起步的新疆古代艺术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与促进作用。尤其是《丹青斑驳 尚存金碧——新疆石窟壁画艺术赏析》一文,对龟兹石窟壁画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探索研究,不论是洞窟形制、题材内容、艺术形象、艺术技法和历史背景都有很深的考析。是当时龟兹石窟艺术比较全面而深入的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论述。给新疆石窟艺术研究者以很深的影响。
谭先生在敦煌艺术研究上也有很深的造诣,《敦煌彩塑漫谈》《敦煌飞天艺术初探》《敦煌唐塑和南禅寺彩塑艺术比较研究》等也都与新疆佛教艺术有关联,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谭树桐先生十分关注新疆石窟研究事业的发展,特别是龟兹石窟,给予更多的热情与支持。1986年,《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编辑出版工作启动。这是全国规模巨大的美术工程。新疆的任务是编辑《新疆壁画全集》6卷本。我有幸进入了编辑组。在这之前,我与谭树桐先生有过交往,畅谈过新疆艺术的各类问题。《新疆壁画全集》编辑组成立后,我们新疆的同志有一个愿望,即请谭树桐先生参与和指导全集的编辑工作。谭树桐先生得知后欣然应允。记得是在新疆军区文工团招待所,我和谭先生共同进行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编目工作。谭先生十分认真地选择图片,仔细加注拍摄要求,对重要图版还附以内容解说,并草拟出编目的纲要。在他的全力帮助下,我们很顺利完成了正式拍摄前的准备工作。
1987年秋,编辑组再次与谭树桐先生达成协议:在他出席“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 后,来新疆指导《新疆壁画全集》编辑组工作。谭先生来到乌鲁木齐后,我们再次讨论了《克孜尔石窟》3卷的编目等事宜。这次接触中,谭先生与我交谈了很多佛教艺术的问题,如犍陀罗、马图拉佛教艺术的起源、演变、特征、传播等。他还介绍了考察印度的所见所闻和体会感想。通过交谈,我们产生许多共识,对古代新疆的灿烂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有较深的认识。对我刚从艺术创作转行到古代艺术研究、种种困难缠绕着我来说,谭先生的帮助与启发,犹如清泉浸田,旱地逢雨,受益匪浅。
谭先生一向有宽厚待人,助人为乐的美德,我亦有体会。1986 年一次交谈时,谈起印度艺术美学问题,我非常想了解印度音乐舞蹈的美学理论。谭先生回到北京立刻给我寄来 《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复印本,这对提升我的印度艺术美学知识,借鉴观察龟兹石窟壁画乐舞形象,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谭先生还在多方面给予我帮助与关怀,使我感受到一位贤者高尚的修养与无私的襟怀。
1987年10月那次赴克孜尔石窟,本应是我陪同谭先生的,但因临时改变,由贾应逸女士陪同前往。我在新疆军区俱乐部门口送谭先生上车出发,万万没有想到此次分手,竟然是永别,同车而行的还有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做碳14测定的两位专家。这次事故致使谭树桐先生遇难,贾应逸女士与一位从事考古年代研究的专家受重伤。这次不幸的意外事件,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给我们留下无法抹去的痛苦记忆。新疆学术界的同仁久久沉浸在悲痛之中。我参加了新疆各界为谭先生逝世举行的追悼会,并参与后事的处理工作。不久,我去了北京,拜访了谭先生的夫人吴乃梅女士。吴大姐见我,倾述悲痛,令人心碎,其悲伤欲绝之情难以言表。在吴大姐叙述谭先生的一生的经历故事中,我也在脑海中不断演映着谭先生的音容笑貌和与我交心的难忘情景。吴大姐失去亲人,我失去良师益友,新疆石窟事业失去忠诚的朋友和知音,其悲哀莫大矣。
谭先生离开我们后,每当我们赴南疆经过谭先生遇难处时,凡乘研究所的车,我都要下车伫立几分钟,默哀致敬。凡乘长途班车经过此地,也要行注目礼,默念致哀。直至南疆铁路修通,往返改乘火车为止。1994年 9月 “纪念鸠摩罗什诞辰 16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克孜尔石窟召开。开幕的前一天晚上,我和贾应逸、赵莉女士在石窟大门外,面向东方焚烧了一张写有“请谭树桐先生光临会议”的请柬。藉以表达我们对谭先生的思念和尊敬之情。我们想,谭先生是为了龟兹石窟艺术事业而殉职的,当年他看到的克孜尔石窟是尚未维修前的凄凉景象:交通极为困难、设施破旧不堪、生活十分艰苦。如今克孜尔石窟经过修复建设,已经旧貌换新颜,而且,龟兹石窟研究所已成为有一定实力的研究机构,学术研究取得初步的成绩,研究队伍正在不断扩大,并且能举办国际学术讨论会。我们想让谭先生来看看他所付予希望、做过贡献、献出生命的龟兹石窟的新变化,与我们一起分享这些新成果。请柬的灰烬乘风而去,寄思传向苍穹。此时,我们内心似乎得到了抚慰和宁静。这个行动,也是我与贾应逸女士、赵莉女士向谭先生去世 7周年的一次虔诚的祭奠。
谭先生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他对龟兹石窟事业的奉献精神、严谨学风和人格魅力是我们永远学习和效法的榜样。
三、影响我学术成长的段文杰先生
自从我转行从事新疆石窟艺术研究之始,首先进入脑海并向往的就是中国石窟研究事业的旗帜——敦煌莫高窟,然后就是常书鸿、段文杰、史苇湘、霍熙亮(因为是本家记得特别牢)等等敦煌的旗手们。由于常书鸿先生很早离开敦煌,没有机会拜访聆听教诲。而段文杰先生一直在敦煌主事,故而有较多机会亲自拜访先生,并接受先生的当面教诲。段先生十分关心新疆石窟事业的发展。他的关怀是全方位的。不仅在研究领域给予多方面指导,而在人才培养方面,先生给予特别关注。先生多次指出“新疆石窟必须由新疆各族学者来深入研究”“新疆石窟研究的专家就出在新疆。”段先生不仅如是说,也用实际行动直接关心和帮助新疆石窟研究人员的成长。这种关怀体现在《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新疆壁画全集》筹备、编辑、审稿、出版的全过程之中。我这里仅谈一谈段先生对我个人有重要影响的几件事:
1.1985 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乌鲁木齐召开学术讨论会,我提交了《浅论克孜尔石窟伎乐壁画》文章,由于会议要我代表新疆艺术界作综合发言,故我自己的文章没有在会上宣读。会议期间我非常想与敦煌的学者接触尤其是想拜见段文杰先生,但那次会段先生没有出席。我就找到樊锦诗先生,将我的论文送给她,请她交转敦煌研究院。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从《新疆艺术》编辑部转来的敦煌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的信。要我与他们联系,并说要邀请我为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人员。后来我到敦煌研究院见到当时学术委员会的谢生保先生,他向我介绍了情况:是段先生提出要学术委员会设法与我取得联系,希望我能成为研究院兼职研究人员。这件事是我事业道路上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我转行走上石窟研究事业后,曾经产生过迷茫和徘徊。段先生这一有力的推动和鼓励,使我奠定了走石窟研究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段先生的提携,如同给了我一双翅膀,让我在“学术的天空”里飞的更快、更高。
2.1986年起,我参加了《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新疆壁画全集》编辑组的工作,分工负责《克孜尔石窟》三册的编目、编辑、拍摄、研究、撰文等。开始编辑组就遇到种种困难。特别是总编委要求全集要按时代顺序编排。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新疆从来没有单独进行过这项研究。段先生知道我们的困难后,满腔热忱地鼓励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干下去。段先生的鼓励为我们注入了巨大精神力量。促使我克服许多困难,完成了任务。撰成了克孜尔石窟艺术年代分期的《丹青斑驳 千秋壮观》一文的初稿。不久我们去敦煌,将文稿送给段先生审阅,他认真审读文章后,首先给予热情的肯定和鼓励,同时提出了修改意见。我们根据段先生的宝贵意见,进行了修改、补充。最后终于靠新疆自己的努力,完成了克孜尔石窟艺术的初步分期意见。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分析大量资料、参照前人成果、反复排比对照写出的篇幅较大的学术论文。尽管此文存在不少问题,但毕竟是自力更生的产物。段先生也是从这点出发,对新疆同志取得的成果,表示出由衷的喜悦。我的这一步,又是段先生在关键时刻,送来“雪中送炭”样的最宝贵的精神支援,才使得我们有勇气、有信心顺利完成了任务。
3.从事新疆石窟艺术研究后,敦煌研究院是我最乐意去的地方。身为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人员,就把敦煌研究院当作自己的家。段先生是我的家长和导师,研究院其他老一辈专家成为我的良师益友。只要有机会就赴敦煌取经讨教。有一次在北京,我去段先生居所拜访先生。先生热情接待并与我畅谈一番。段先生满怀深情地对我讲,新疆石窟大有作为,一定要坚持研究下去。他对新疆同志取得的成果,再三表示高兴和祝贺。随之先生语重心长对我说:“我们搞敦煌艺术,已经几十年了,应该研究的东西,已经不少了,有些问题清楚了,有些还没有搞清楚。要解开敦煌壁画的许多谜,钥匙就在你们克孜尔”,当时我一阵惊讶,段先生这句话我一时还难以理解消化。经段先生详细分析,我才理解他深邃的见识。随之我对段先生的崇敬之意又有一层升华。我回来后对段先生这段话,久久回味不尽。段先生研究敦煌艺术成就斐然,但他的视线没有停留在一个地区,他放眼西域以至世界看佛教艺术,这才是一位“大家”所具有的目光和襟怀。段先生这段话,一直在我心中回荡,我在后来的一些研究中,深受段先生的影响,在某些问题上,就是按段先生的理念,扩大视野,驰骋思路取得某些进展的。
4.我研究佛教艺术,开始也是停留在艺术形态的描述上,过了一个较长的阶段,我意识到:艺术的形态,只是佛教义理的表相。如果不理解佛教思想,表相的东西,再研究也不可能寻到它的本质,甚至会走到反面。正如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的对佛教艺术中某些形象的错误论说一样,陷入到歧途之中。如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裸体形象,就出现论说偏颇的问题。壁画音乐舞蹈形象研究,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也曾有过游离佛教义理之外的茫然时期。不久我开始从佛教思想入手去解释石窟壁画中的各种艺术形象。《浅论克孜尔石窟伎乐壁画》就是我从佛教义理研究克孜尔石窟艺术的第一篇文章。这可能正是段先生注意我并设法寻找我担任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人员的原由吧!后来段先生曾就此问题与我交谈过,记得是在莫高窟段先生办公室,话题是从办公室坐着一位刚来的一位佛学院毕业生谈起的。段先生说,我们已经注意到,佛教艺术研究要有佛学的基础,过去认识不够,现在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要吸收一些佛学院的学生充实到敦煌研究院来。听了这一番话,我再次得到深刻的启发,奠定了佛教义理是认识佛教艺术的根本途径和归宿的意识。可以这样说,我苦读佛经、钻研佛理、用佛经理念解读壁画形象,用佛经义理撰写文章,用佛教的真谛识别那些歪曲、亵渎佛教精神的种种谬误,就是从此开始的。也可以这样说,是段先生引导我走上佛教艺术研究的正确道路,并进入了佛教艺术研究更为广阔的“自由王国”。
四、心中始终挂念新疆的黄心川先生
我从事新疆佛教艺术研究工作后,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佛教理论和知识的书籍。为了了解佛教基本概况,我读的是黄心川先生主编的《世界十大宗教》,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印度佛教思想,我读过黄心川先生的《印度哲学史》。当时虽然没有见过黄先生的面,但黄先生的几本著作,给我很深刻的影响。黄先生的学识、威望已在我心中占有崇高的位置。有机会向黄先生当面求教是我企盼多年的愿望。
1990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与新疆佛教协会联合举办的“西域佛教文化讨论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黄心川先生率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多位专家莅临会议。我有机会参加这次会议,也见到了久仰的黄心川先生。会上聆听了黄先生的学术发言和重要的总结报告,收获颇大。会上还结识了许多专家,他(她)们的论文和著作,也都是我后来学术营养的重要来源。这次学术讨论会,使新疆佛教研究学者与以黄先生为旗手的佛教学术界的领军学者建立了联系。此后,黄先生不断对龟兹石窟和新疆佛教研究事业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与支持。黄先生是哲学专家、宗教学专家。尤其在佛教哲学、佛教思想史研究方面造诣颇深,对龟兹出生举世闻名的佛学家、翻译家鸠摩罗什有深入的研究。当向黄先生请教如何推动龟兹佛教、龟兹石窟研究,寻找一个题目,举办一次龟兹佛教研讨会时,鸠摩罗什自然成为首选的研究议题。于是与黄先生商定,借鸠摩罗什诞辰 1650 年的时机,召开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作为推动新疆佛教、龟兹石窟研究发展的契机。
在黄心川先生积极倡议和支持下,经过各方面的努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亚洲太平洋研究所、中国佛教协会和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佛教协会、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联合举办的“鸠摩罗什和中国民族文化——纪念鸠摩罗什诞 165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于 1994 年 9 月在鸠摩罗什故乡,龟兹佛教圣地的新疆拜城县克孜尔石窟召开。在黄心川先生亲临会议指导下,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会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成为新疆佛教文化研究一个新的起点。通过这次学术讨论会,也全面提升了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的学术水平,促进了各项工作的发展,扩大了与国内外学术单位的交流。这是黄先生对龟兹石窟研究事业、对龟兹石窟研究所建设发展的最宝贵的奉献。
黄心川先生一贯关心新疆佛教文化研究的发展,了解新疆学术事业的困难。他与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杨曾文先生,特别关注新疆佛教研究事业的发展和新疆学者的专业提高。每逢在北京召开“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都给新疆龟兹研究所发来请柬,表示出对新疆佛教研究同仁的真诚关怀。黄先生对新疆学术界取得的成绩,始终给予热情的鼓励。2000 年他在《纪念鸠摩罗什诞辰 165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的序言中写道:“龟兹石窟研究所不仅在组织会议上做了大量工作,而且一直为出版这次会议论文集竭尽全力盛春寿和全所同志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出版论文集。我为他们这种敬业的精神所感动。学术事业一直是我国的优良传统,过去龟兹石窟研究所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出版了很多专著,有的专著是我国这方面有前瞻性的研究,代表了较高的水平。”
黄心川先生对我个人,也是满腔热忱地关心和支持,我曾在北京登门拜访黄先生。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与我畅谈新疆佛教研究的一些问题。鼓励我们新疆同志克服困难、努力探索。2001 年,我将 1992 年以来的研究文稿,整理汇编成《考证与辩析——西域佛教文化论稿》,请黄先生作序并题签书名,黄先生欣然应允。在序言中,黄先生对我的文章给予较高评价。对黄先生的鼓励和支持,我一向视为是对我的鞭策和巨大的推动力。2009年 9 月我参加在山东省兖州市召开的“兖州佛教历史文化研讨会”和 10 月在西安召开的“长安佛教学术研讨会”,会上都见到了黄心川先生。先生年事已高,但还是那样精神矍铄,神采奕奕。
虽然这次与黄先生交谈时间不长,但新疆佛教研究、龟兹石窟艺术事业仍是先生关心的主题,黄先生是“中国玄奘研究会”会长,当与先生谈起新疆打算召开学术研讨会时,先生说“玄奘研究会应该在新疆召开了”。在新疆召开玄奘学术研讨会,黄先生很早就有这个想法,曾说过新疆是玄奘西行的首及地区,事迹多而重要,资料也十分丰富,在新疆举办玄奘研究学术会是十分必要的。但因种种原因这个设想没能实现,十分遗憾。几次拜见黄先生,给我最深刻的感怀是:黄先生心中始终挂念着新疆。
五、金维诺先生的学术风范
金维诺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美术史家、美术教育家、国际知名的敦煌学家。新疆从事美术史、佛教艺术研究的人,恐没有不读金维诺先生的论著的。我开始接触新疆石窟艺术时,首选阅读的就是金先生的《中国美术史论集》,其中《新疆的佛教艺术》是我研究龟兹石窟的启蒙、基础性的读物。不久又拜读了先生发表在《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 三》上的《龟兹艺术的风格与成就》。这篇论文将龟兹石窟艺术放在大的文化背景中论述,既着眼于龟兹本土文化的基础,又看到文化交流的外来因素,同时注意论述了佛教义理与艺术的关系。是一篇视野开阔,论述深刻的指导性文章。其中关于大像窟的开凿与鸠摩罗什在龟兹弘扬大乘佛教时代相合的观点,具有启发性。这个论述在先生与罗世平合著的《中国宗教美术史》中得到进一步的强调。这个观点对我以后研究龟兹石窟年代分期和鸠摩罗什事迹有重要的影响。金先生上述论著,是建立在实地考察,掌握了龟兹石窟基本资料的扎实基础上,用深厚的美术史功力、敏锐的艺术观察力而写就的。金先生 1979 年率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到龟兹石窟进行了 45 天的考察与壁画临摹。80 年代结合《中国石窟》的出版,再次赴龟兹、高昌深入考察新疆石窟。上述论著集中了金先生对新疆石窟考察研究的成果。
金维诺先生对新疆石窟研究事业十分关心,他在克孜尔石窟考察时,对坚持在生活、工作条件非常艰苦的一线工作人员,给予真诚的关怀和慰问。记得 80 年代的一天,金先生陪同国外学者来到克孜尔石窟考察。考察之余,先生匆忙来到简陋的食堂,专门看望在克孜尔石窟为《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新疆壁画全集》拍摄图片的我和冯斐先生。金先生是《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的编委,他的关心与慰问,使我们非常感动,增强了我们完成任务的信心。
金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博采众长,不拘旧说。金先生很注意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的研究成果,《中国宗教美术史》在论述龟兹石窟题材内容和年代划分上,采用了龟兹石窟研究所的一些观点。先生指导其学生的博士论文《龟兹石窟壁画的年代研究》中,也体现出这一点。这对学术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的龟兹石窟研究所是一种肯定和鼓励,使我们得到巨大的精神支持。在龟兹石窟研究所初建时,一切都需要创立,学术研究上尤其需要走出步伐,看到敦煌等兄弟单位蒸蒸日上的发展。新疆石窟艺术研究者,深感落后,心急如焚。国内外艺术界的“善知识”们,深知我们的困难、理解我们的心情。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有精神的,有实践的。金维诺先生两者具备,是给予龟兹石窟研究所多方面援助与支持的贤能之一。
1997 年在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所在地——克孜尔石窟召开了“唐代西域文明——安西大都护府国际学术讨论会(佛教美术考察)”,金先生应邀并率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部分学生莅临会议。会上宣读了美术史系几位博士、硕士生的论文。金先生作了会议的总结发言。这次会议在金先生的指导下,取得了重要的收获。会议期间,我向金先生请教了许多问题。其中对我有重要意义的是:关于克孜尔第 38 窟“天宫伎乐”中的有喇叭口的乐器的问题。此前有学者提出此乐器是“唢呐”的观点,我始终怀疑此说。理由是我发现喇叭口是有人后加的。我一直注意调查此问题的来龙去脉。因 1979 年金先生率中央美术学院师生在克孜尔临摹壁画,我就向金先生询问当时临摹的情况。金先生了解的这个问题后,对我的问题非常重视,支持我把这个问题调查清楚。金先生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情况,同时与我一起分析壁画的现状。最后这个问题终于真相大白。当回顾此“公案”的过程时,我永远忘不了金先生的帮助。
9 年后的 2006 年,新疆龟兹学会在库车举办“第二届龟兹学学术研讨会”,已是82岁金维诺先生亲临了这次研讨会。金先生莅临会议本身就是对龟兹石窟研究的极大支持。更令人敬佩的是,在考察库木吐喇石窟时,竟然攀登危崖,进入了第 79 窟考察。当时情景,令众人惊讶不已。金先生自青年时起就为美术事业而不辞艰难,勇于探险。在西藏阿里探索古格王国遗址,就万险不辞,为后学者所乐道与崇仰。这次金先生以身实践,让众人亲睹了一位耄耋之年的贤达的崇高品格和勇敢精神。
这次研讨会金先生奉献了《龟兹艺术的创造性成就》一文。论文突出论述两个问题:一、“龟兹创建了塑绘结合的新型石窟”。先生说:“随着佛教的传播,佛教徒在各地兴建石窟寺,这种渊源深入是由西传到龟兹,但龟兹艺术家却根据当地的具体条件,进行了创造,无论在洞窟形制、洞窟组合、塑绘结合以及表现技艺方面,都显示了当地艺术家的才能。”二、“师徒传承体制的创立与传播”。先生指出:“师徒相承,粉本流布为龟兹艺术的传统,随着佛画东传,这种方法显然对在内地推广也起到了积极作用。”金先生这两个重要论述,是对龟兹石窟艺术研究的新贡献,其理论价值和启示作用都是不言而喻的。
金维诺先生有关新疆佛教艺术的论文还有《中国新疆早期佛教彩塑的形成与发展》《龟兹的寺院壁画》等。此外,金先生大量敦煌佛教艺术的论著,也是研究龟兹佛教艺术有直接关系的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光阴荏苒,诸位先贤已先后驾鹤仙逝。中国评价前贤,常冠以“道德文章”。我想今天缅怀前面诸位先贤,“道德文章”会有更深的含义,他们都是参与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有功之臣。又是新中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开创者、贡献者。也是培养新一代中国社会科学人才的导师。他们功勋卓著,永彪史册。论道德,他们忠于党、忠于祖国,其德崇高无比。论文章,他们的理论建树、学术贡献,堪称时代精华。在当前中国为实现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和世界的大变局的背景下,继承先贤们的精神,沿着他们的足迹,继承他们的遗愿,奋发图强,用出色的成绩,完成未竟事业,以告慰诸位先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