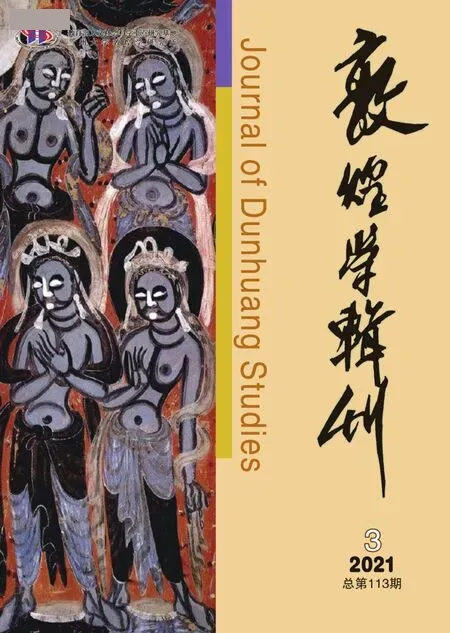民国时期周鳌山收藏敦煌文献史事钩沉
——曾广钧长诗《题周鳌山藏唐人写经卷子》解析
韩春平
(兰州大学 图书馆,甘肃 兰州 730000)
敦煌文献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古籍,是敦煌学的重要研究对象。自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以后,由于遭逢清末乱世,洞中文献未能得到有效保护,大部分惨遭劫掠流落海外,劫馀部分散入甘肃、北京、上海等多地公私藏家。后来经过多年的调查了解,海内外大多数文献的存藏状况已经被摸清,文献概况、内容等多已通过相关目录和图录呈现。当然敦煌文献的流散情况非常复杂,长期以来不断有公私藏品被再度发现,也有部分文献至今下落不明,文献的再发现工作一直都在艰难地开展。曾广钧长诗《题周鳌山藏唐人写经卷子》虽然早在民国时期即已发表,但诗中所述周鳌山收藏敦煌卷子一事沉淹已久,迄未被敦煌学界所关注。
一、作者、藏者与题诗内容
曾广钧(1866-1929),字重伯,号觙庵、伋安,别署中国之旧民,湖南湘乡人,曾国藩之孙。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武鸣知府,后弃职归里。曾氏少有才名,工诗,辞采惊艳,有唐温李之风,与时人李希圣、汪荣宝、孙希孟并称“玉溪体”四大家,著有《环天室诗集》;兼善书法。
周鳌山(1884-1959),湖南岳阳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人士,中国同盟会会员。早年先后就读于湖南陆军速成学校、上海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曾入湖南中学任教,并曾担任长沙《国民日报》主笔,因揭露时弊为北洋军阀所嫉恨。1913-1915年,为逃避北洋军阀通缉,曾赴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其间一度被推举为留日学生会会长,参与并主持留日学生反对“二十一条”斗争。回国之后再次担任《国民日报》主笔,后又迫于军阀压力,退隐乡间,执教于私塾。自1926年夏季起,历任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执法处处长,湖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系首任厅长,该教育厅前身为教育处,周氏曾任处长),以及省政府委员兼湘西善后专使,武汉国民政府革命军事裁判所所长,《国民日报》驻南京特约记者,国民政府南京军事参议院参议,湘西绥靖处长等职。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唐生智所部运输司令。1949年湖南解放前夕,曾参与组织岳阳起义,筹组岳阳和平解放自救会并出任会长。(1)周继健《忆先父周鳌山》,岳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岳阳文史资料》第1辑(内部资料),1983年,第68-72页。新中国成立后移居长沙,先后担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省政府参事室参事。(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岳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刘美炎主编)《岳阳文史》第10辑《岳阳籍原国民党军政人物录》(内部资料),湖南省岳阳晚报出版印刷中心,1999年,第331-332页。
周鳌山擅长书法,热衷文物鉴赏(3)周氏对文物鉴赏的爱好不止于收藏敦煌文献一事,还有其他例证。刘志盛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在湖南省博物馆所藏王夫之手稿《噩梦》书末,有“周鳌山、陈子春、梁基操、黄铁盦、赵曰生、潘雪峰、程潜、陈浴新等人的题识,以及谭戒甫、吕振羽、冯友兰、章士钊等人的题诗。”其中“周鳌山先生题识说:‘右衡阳李君况松所藏船山王先生遗著《噩梦》自书定本,……距今二百六十七年矣。如此巨册,墨渖犹新。予曩在攸县龙氏及南岳图书(馆)所见先生墨稿,皆仅数页,以此视彼,尤可珍已。中华民国三十七年(1948)春周鳌山敬识于金陵。’”(见刘志盛《王船山五篇著作手稿墨迹考述》,《船山学刊》1998年第2期,第28页。)从文中不难看出周氏当时极高的鉴赏水平,以及在业界的不凡影响。,早年曾两度担任长沙《国民日报》主笔,一度担任该报记者,并曾先后为黎元洪、唐生智、孙中山及冯玉祥等多位要人担任秘书,又曾入就谭延闿幕职,文化修养极高。不凡的文化修养,加之屡历要职,使周氏有机会接触并收藏敦煌文献。民国初期,其同乡曾广钧曾创作《题周鳌山藏唐人写经卷子》长篇诗作,揭示了周氏藏品的基本情况。尽管本诗早在作者去世数年后即公开发表,但长期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特别是未被敦煌学界所关注,另外本诗也不见于《环天室诗集》。为便于考察,兹全篇迻录如下:
册府英光抱鹑尾,夏州刺史为天子。
欲铸金枷待洛州,先开石穴藏图史。
敦煌枯碛石如屏,山谷百尺如凿成。
穹窿千年石不堕,纵横数里沙皆鸣。
沙干石槁土复燥,佛作丸泥塞其窍。
藏书不若称瘗书,汲冢包山无此妙。
史牒无征僧不知,漆灯谁问夜何其。
灵踪显晦有期运,一旦雷雨天开之。
州家申明史家怪,犹以媕阿观一概。
拂箖博士叩辕门,请历天梯披倒薤。
从此瑰奇属海人,悬黎结绿几蒲轮。
残丛中驷八千卷,尚入鸿都为国珍。
流落人间凡几起,最大清河一兵子。
若从臣里数倾城,幸有畏公三十纸。
君从何处揄文竿,一钓便得双琅玕。
阙文乘马不足惋,长阵如龙人所难。
自是唐人写经法,沆瀣宗风多宝塔。
妙法莲法惭挺秀,陀罗尊胜同英拔。
甲卷入妙乙卷工,有如宝剑分雌雄。
延津命俦力破水,盘郢啸侣光摇空。
当时抵鹊连城贱,著录宣和无一卷。
直待鸥波识爨桐,始仿兜沙临本愿。
世人购经徒嗜书,惟君赞佛通之儒。
彼以慈悲我仁义,儒墨未用相轩渠。
吾乡唤君作生佛,万家共信心如烛。
问政山高贤首贤,盟心水净谷帘谷。
岂意天花旧讲场,于今遍作逃亡屋。
安得声闻半偈经,却遣苍生罪还福。(4)曾广钧《题周鳌山藏唐人写经卷子》,《国民外交杂志》第2卷第6期,1933年,第105页。
本诗题旨明确,读之一目了然,无烦多述。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诗题并未直接道明周氏藏品为敦煌文献,这也可能是本诗未能引起敦煌学界关注的缘由,不过审读诗作内容可知,所谓唐人写经卷子,其实正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土的遗书文献。从曾广钧生平及诗作内容可以断定,本诗创造于民国初期。(5)曾广钧卒于1929年,本诗又提及张广建所藏敦煌文献一事,按张广建收藏敦煌文献,其事在1914年张氏出任甘肃都督之后,可知本诗写作时间必然在1914-1929年之间。经后文考证,可以将时间范围缩小在1918-1920年之间。全诗篇幅颇长,总共五十六句,含小注计达四百字。从用韵角度来看,通篇共用十二韵,其中前面四十四句每四句一换韵,凡十一韵,换韵首句均押韵;末十二句共用一韵,首句亦押韵。所用多为平韵,间有仄韵。从内容来看,全诗又可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首二十八句为一部分,总括介绍了敦煌文献的情况;后半首二十八句又为一部分,重点述写了周鳌山藏品的基本情况,并以此为基础,结合现实,抒发感想。以下主要就诗作内容作一解析,纰缪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二、前半首:对敦煌文献的整体介绍
本诗虽然名为《题周鳌山藏唐人写经卷子》,但作者一开始并未直接记述周鳌山藏品的具体情况,而是从宏观角度着眼,利用半首诗的大篇幅记述敦煌文献的来龙去脉,为后文书写进行了厚实的铺垫,具体又从文献的形成、保藏及散出等多个方面,分多个段落逐次展开。
“册府英光抱鹑尾”以下四句为一段,概括交代文献的形成原委,但文句颇有不易索解处。“册府英光”,大意指册府之中高文大典所辉焕的奇异光彩。“鹑尾”,系十二星次之一,于分野属南方荆州,于时辰为巳。“册府英光抱鹑尾”一句意思不甚明确。“夏州刺史为天子”,应指西夏李氏建国称帝一事。史载西夏王朝建国称帝之前,宋廷曾历授元昊伯祖继捧、祖继迁及父德明夏州刺史之职。(6)《宋史》卷485《外国一·夏国上》:“继捧立,以太平兴国七年率族人入朝。……初,继捧之入也,弟继迁出奔,及是,数来为边患。……端拱初,改(继捧)感德军节度使。屡发兵讨继迁不克,用宰相赵普计,欲委继捧以边事,令图之。因召赴阙,赐姓赵氏,更名保忠,太宗亲书五色金花笺以赐之,授夏州刺史,充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 咸平春,继迁复表归顺,真宗乃授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景德元年正月二日卒,年四十二,子德明立。……德明连岁表归顺。(景德)三年,复遣牙将刘仁勖奉誓表请藏盟府,且言父有遗命。帝嘉之,乃授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国,充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西平王,……”(见[元]脱脱等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新1版,第13984-13989页。)严格地讲,“夏州刺史为天子”的说法并不成立,原因有二:其一、西夏立国肇始于大中祥符间辽国遣使册封李德明为大夏国王之时,但“天子”名号一般只加于皇帝,并非国王所敢擅用,德明未曾称帝,只做了西夏国王,且并非出于宋廷册封,因此不当称之为“天子”。其二、西夏称帝始于元昊晚期,之前元昊继承父位时朝廷所授官职多同于德明,但已不再授予夏州刺史一职,因此其称帝后固然可以谓之“天子”,但其原职又并非夏州刺史。综上所述,“夏州刺史为天子”的表述似乎过于牵强,与史实不相符合,不过从诗歌创作角度来看,倒也不妨采用笼统的笔法表述相关史事,因此认定本句是指西夏李氏建国称帝并无不妥。“欲铸金枷待洛州”一句意思同样不甚明确。“金枷”,指纹有金饰的刑具,用以械系具有特殊身份的罪犯。“洛州”,本指洛阳,诗中或许另有所指。
本段内容涉及敦煌藏经洞形成的原委。在曾广钧生前,学界已经对藏经洞的形成原委作过初步的探讨。作为最早前往敦煌劫取文献的西方探险家之一,法国人伯希和早在1908年即已提出藏经洞系1035年“西夏侵占西陲时”封闭(7)伯希和曾依据敦煌卷本(即文献)相关内容推断称:“卷本所题年号,其最后者为宋初太平兴国(西历九百七十六年至九百八十三年)及至道(西历九百九十五年至九百九十七年),且全洞卷本,无一作西夏字者,是洞之封闭,必在十一世纪之前半期,盖无可疑。以意度之,殆即千零三十五年西夏侵占西陲时也。”(详伯希和《敦煌石室访书记》,原文载《法国远东学院院刊》第8卷,1908年,第501-529页;引文据陆翔汉译本,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1935年,第7页。)的观点。1909年,伯希和一度游历北京,并向中国学者展示其随身携带的部分敦煌文献,其间包括罗振玉在内的许多中国学者曾与伯希和晤面,罗振玉在获睹伯希和所携文献后还特意为之编目介绍。关于藏经洞的形成,当时罗振玉应该听说并信从了伯希和关于洞窟封闭的观点,因为他在介绍文献时,与伯希和口径完全一致,认为洞中文献“乃西夏兵革时所藏”(8)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东方杂志》第10期,1909年,第42页。。伯希和、罗振玉的观点后来曾长期流行,曾广钧创作本诗之时,显然信从了这一流行观点,认为由于西夏的入侵,造成了敦煌当地“开石穴藏图史”的结果,因此才有了藏经洞文献。
“敦煌枯碛石如屏”以下八句为一段,主要记述敦煌石窟对于保藏文献的有利条件。诗句接续前文“开石穴藏图史”,较为详细地说明了“石穴”(即石窟)的“藏书”情况。“佛作丸泥塞其窍”一句中,“窍”无疑是指藏经洞,而“丸泥”之“佛”应该是指洞中的洪辩塑像。“汲冢”,指《汲冢竹书》,系晋武帝时汲郡(今属河南卫辉市)魏襄王古墓所出土的竹简文献,又称《汲冢书》《汲冢古文》。“包山”,指包山湖所藏金简玉字之书;据明人《古诗纪》“包山谣”条引杨方《吴越春秋》(按应为《吴越春秋削繁》)称:“禹得金简玉字书,藏洞庭包山湖”。(9)[明]冯惟讷《古诗纪》卷3《古逸第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379册,第26页;又见[明]郭子章辑《六语·谣语》卷1,明万历刻本,文字略有出入。本段相关表述符合当时人们对藏经洞的了解。对于相关藏书情况,作者着意加以赞扬,认为敦煌藏书较之汲冢竹书、包山金简两种古代珍笈更为奇妙。
本段及以下三段内容都确然表明,诗中所谓“藏图史”及“藏书”,其图其史其书,不是指任何其他文献,正是后来广为人知的“敦煌文献”,特别是本段已经将“敦煌”“鸣沙”“山谷”和“穹窿”等一一拈出,明白告知所藏文献出自敦煌鸣沙山大泉河岸石窟之中,以下三段所记相关事迹,也均符合敦煌文献散出后的实际情况,诗句文意明白无疑,无烦赘论。
“史牒无征僧不知”以下四句为一段,主要写文献经久埋藏,不为外界所知,但显晦自有期运,后来自然应期面世。“雷雨天开之”,应系作者想象。
“州家申明史家怪”以下四句为一段,主要写文献出土后的流散情况。“媕阿”,又作“媕妸”“媕婀”,意为无主见或犹豫不决,亦指无主见之人。“拂箖”,本指古罗马,这里借以代指欧洲;“拂箖博士”,在此具体是指英国学者斯坦因及法国学者伯希和。“倒薤”,原本是一种篆书书体名称,这里借指含有各种胡语文字的敦煌文献。本段大意是说:文献出土之初,地方官员虽曾向上级呈明了相关情况,只可惜当时国人多昧于辨识宝物,就连史学家也一度认为这些敦煌文献是怪异之物,不了解其真正的价值所在,只会人云亦云;直到欧洲学者前往敦煌,请求架梯入洞披阅文献(国人才发现这些文献竟然价值连城)。
“从此瑰奇属海人”以下八句为一段,主要写文献四处流散的情况。“悬黎”“结绿”,均为美玉名称;“蒲轮”,指用蒲草包裹的车轮,可以减轻震动,这里代指海外探险家运送敦煌文献的车辆(或喻指驼马队)。“中驷”,原指中等马匹,这里比喻劫馀的普通文献。“鸿都”,鸿大的都会,在此指北京。“清河一兵子”,所指不详。按本句之下原有“张广建所得过千卷”八小字注释,依寻常格式,似谓张广建即清河一兵子,但张广建其实未曾有此经历。“臣里”,在此指作者曾广钧故里湖南。“畏公”,指谭延闿。谭延闿(1880-1930),字组庵、祖安,号畏公、切斋,湖南茶陵人,以故曾广钧引为同里。谭氏系民国时期政治家,工于书法。据曾广钧此诗,谭延闿也曾收藏有三十纸的敦煌文献。本段大意是说,欧洲学者发现了文献的巨大价值,但也将大量文献盗运境外,致使瑰宝属之异国他乡。劫掠之馀的普通文献,尚有八千卷之多,后来被运至北京,奉为国宝。其他流落人间的还有几起,其中数量最多者为清河县(当时改称大名道)一个士兵,此外张广建所获也有千馀卷之多。在曾广钧故里,还有谭延闿收藏的三十纸文献,算是湖南本地藏品中的佼佼者了。
谈到张广建所藏敦煌文献的数量,这里需要略作赘述。学界对张广建收藏敦煌文献一事早有关注,但是对张氏藏品的数量向未考定。早年向达先生曾经提到:“民初张广建长甘,以石室写经为买官之券,民间所藏几为一空。”(10)向达《西征小记》,收入氏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367页。虽未明确张氏藏品的数量,但已提示其数必然不少。早年另有一位敦煌文献收藏家周廷元先生,曾依据所知敦煌公私藏卷编写过一篇详细目录,并附《编目赘言》一篇。后来荣新江先生对该《赘言》有过细致考察,但对其中“石室写卷为甘肃大吏所得者,传闻如省长张广建约有六七百卷”的表述未表认同,并在综合《赘言》各处表述的基础上总结道:周氏“所说各家藏卷的数量,动辄数百卷,恐怕是不确切的”。(11)荣新江《甘藏敦煌文献知多少?》,《档案》2000年第3期,第17、19页。张广建藏品后来大都经白坚转手出售日本,部分存留国内。日本藏品一向以保守著名,售予日本的张氏原藏文献除已公布的部分外,还有多少未曾公布无人知晓;至于存留国内的部分究竟又有多少,也至今是个未知数。曾广钧本诗所称张广建所得敦煌文献“过千卷”的说法,尽管目前还无从确认,之前也未见有他人提及,但它无疑为敦煌学界探究张氏藏品的具体数量提供了新的参考,何以会有过千卷的说法,应该不会是曾氏臆测,而是有其一定的根据。
三、后半首:对周氏藏品的述写和感想
自“君从何处揄文竿”以下的后半首诗作中,作者先是扣合主题,述写了周鳌山所藏敦煌文献的数量、书法等多种情况,随后又借题发挥,基于周氏藏品抒发他自己的所感所想。本部分内容又可分为以下几个段落。
“君从何处揄文竿”以下十二句为一段,详述周鳌山收藏敦煌文献的情况。“君”,这里指周鳌山。“揄文竿”,字面意思是举起有纹饰的鱼竿,比喻采用高超的手段。“琅玕”,原意为如珠的美玉,这里喻指精美的敦煌文献。“阙文乘马”,系化用《论语》孔子之语:“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12)[宋]朱熹《论语章句集注》,宋元人注《四书五经》第三种,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第2版,第68页。一般解释为孔子对时俗喜好穿凿的痛恨之语(也有人认为本章属于断简)。孔子的大意是说:古代的优秀史家,对于文献中存在疑义的地方,必然会作存阙处理,以待贤能者为之补救,而不敢妄加穿凿,就像是人们自己有马而不能驯服,不妨先借与他人乘习,使之得以驯顺一般;这种存有阙疑之文的古史文献自己之前还曾见到过,但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不过诗中化用此语,似乎并非指周氏藏品也存在类似的阙疑之文,很可能是指该藏品的卷面存在一定的缺损。“长阵如龙”,用比喻之法说明藏品在形制上属于长卷。“沆瀣”,原指夜间的水汽、露水,在此借指上好的品质;“沆瀣宗风”,意即热衷崇尚。“多宝塔”,在此特指唐颜真卿所书《多宝塔碑》,全称《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为颜体楷书代表作之一。“妙法莲法”(“莲法”应系“莲华”之误),应指《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是古代普遍诵念的佛教经文,敦煌佛教文献中也以本经数量为最多。“陀罗尊胜”,即《尊胜陀罗尼经》,全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又有《尊胜大明王经》等多个异名,简称《尊胜经》,敦煌佛教文献中本经数量亦在不少。“命俦啸侣”,语出曹植《洛神赋》,明人《卓氏藻林》专条注云:“谓朋友会游也,临水登山,命俦啸侣。”(13)[明]卓明卿《卓氏藻林》卷2《交游类》,明万历八年(1580)刻本。“延津”,原指延平津,位于福建延平县(今南平市),这里借指延津剑,实即龙泉、太阿两口宝剑的合称。(14)史载晋代张华因见斗牛之间常有紫气,于是向豫章人雷焕进行咨询,得知原系丰城县所藏宝剑精气所致,于是补授雷焕为丰城县令,秘密寻访宝剑。后来雷焕从地下掘得龙泉、太阿双剑,与张华各取其一。“华诛,失剑所在。焕卒,子华为州从事,持剑行经延平津,剑忽于腰间跃出堕水。使人没水取之,不见剑,但见两龙各长数丈,蟠萦有文章,没者惧而反。须臾光彩照水,波浪惊沸,于是失剑。”(详[唐]房玄龄等《晋书》卷36《张华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75-1076页。)“盘郢”亦系宝剑之名。(15)[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卷60《军器部·剑》引《吴越春秋》称:“越王允常聘欧冶子作名剑五枚:一曰纯钩;二曰湛卢;三曰豪曹,或曰盘郢;四曰鱼肠;五曰巨阙。”(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88册,第372页。)
在前文介绍敦煌文献来历及流散大背景的基础上,从本段转入本诗主题。据本段文意,作者显然不清楚周氏藏品的具体来历,但他一开始便用比喻(双琅玕、长阵如龙)手法告诉读者周氏藏品的数量(两件)和形制(长卷),紧接着采用赋体极力渲染两篇写经在书法方面的不凡之处。诗句中提及藏品具有正宗唐人写经风格,扣合诗题中周氏藏品为唐人写经卷子的表述。值得关注的是,作者还着意点明了所题两种写经的题名。后四句大意是讲:周氏藏品是地道的唐代写经,其书法宗尚颜鲁公多宝塔碑,虽然《法华经》略输于挺秀,但《尊胜经》则无逊于英拔,一者入于神妙,一者尽显工致,正如宝剑有雌雄之分,又恰似延津、盘郢神剑,命俦而啸侣,或力能破水,或光可摇空。毋庸置疑,这样的藏品乃是敦煌文献中的精品,其品相的上乘自不待言,这也应该是作者何以为之题诗的缘由所在,因为凡品显然不值得作者去过多关注,更不值得长诗称颂。
“当时抵鹊连城贱”以下四句为一段,主要评判周鳌山藏品的价值。“抵鹊”一词典出《盐铁论》:“中国所鲜,外国贱之:南越以孔雀珥门户,崐山之旁以玉璞抵乌鹊。”(16)[汉]桓宽《盐铁论》卷7《崇礼第三十七》,《四部丛刊》影明嘉靖本。后世多以“抵鹊”比喻贵物贱用。“宣和”,应指《宣和书谱》,系宋徽宗宣和年间所编法书目录,著录当时御府所藏历代法书墨迹,凡二十卷,以“体例精善,评论精审,资料丰富”(17)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5509页。著称,这里代指正规的文献目录。“鸥波”,原指鸥鸟往还的水面,诗中喻指闲适的退隐生活。“爨桐”,据《后汉书·蔡邕列传》载:“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故时人名曰‘焦尾琴’焉。”(18)[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60下《蔡邕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004页。这里喻指敦煌文献劫馀珍笈。“兜沙”,指《兜沙经》,佛经的一种,这里应指唐钟绍京小楷经典法书《兜沙经》。“本愿”,或指《本愿经》,佛经的一种,诗中可能借以代指各种佛经,因叶韵而用“本愿”一词,同时也有借此佛经之名陈明周鳌山抄经意图这一层含义。
本段字面意思大略可通,作者慨叹当初国人眼力太弱,致使珍贵文献沦为贱品,自然也未被著录于正规目录。诗中“鸥波识爨桐”“仿兜沙临本愿”两句的主语,究竟是指周鳌山还是诗人自己,经考证应该是指周鳌山。曾广钧本人入民国后辞职回到湘乡老家,直至终身。周鳌山虽在民国期间长期仕宦,但也曾有过两次隐退生活:1918年之初,北洋军阀吴佩孚、张敬尧攻入长沙,张氏以湖南督军之命封闭《国民日报》报馆,并通缉时任报馆主笔周鳌山,迫使其“改姓名,逃往宁乡乡下躲避,做私塾教师”,直至1920年出任唐生智秘书;1927年冬季,周鳌山又“迁家南京,闲居无事”,直至次年之夏应聘为《国民日报》驻南京特约记者。(19)周继健《忆先父周鳌山》,第69、72页。结合诗作下文来看,周鳌山可能在当初隐退湖南宁乡期间,一度奉所藏敦煌文献为小楷书法经典,并依仿该文献抄录相关佛经,借以践行其仁义本愿。据此,曾广钧得以鉴赏周鳌山藏品的时间,也应该是在周氏第一次隐退的1918-1920年期间,因为周氏第二次隐退之时,已经移家于南京,其藏品也自应一并携去,退居在家乡湖南的曾广钧显然无从鉴赏。
“世人购经徒嗜书”以下八句为一段,通过赞颂周鳌山的学问修为,阐发了周氏购买和供奉佛经的意义。“轩渠”,本指笑貌、欢悦貌,诗中作“取笑”之意讲。“生佛”,即活佛,通常借指德望崇高的贤达。“问政山”,位于安徽歙县,山下紫阳书院为宋代大儒朱熹讲学之所。“贤首”,佛教用语,意为贤者、尊者,通常用以尊称比丘,或为贤首菩萨简称。“盟心水”一词多见于诗作,但通常并无指实,应系臆想中的盟心、净心之水。“谷帘”,指谷帘泉,位于江西星子县庐山主峰大汉阳峰南康王谷,素有“天下第一泉”之称;谷帘谷,亦即康王谷。本段中作者以赞佛为依托,借以颂扬周氏的仁义秉性及清廉高举之行。
“岂意天花旧讲场”以下四句为一段,意在抒发感想。“天花”,多义词,在此为佛教用语,又作“天华”,意为天界仙花。“讲场”,讲经说法的场所。“天花旧讲场”,旨在说明讲经场的华贵。“逃亡屋”,清戈陆明有《逃亡屋》长诗一首,专记逃亡民众的乱离情状,其中有“荒村寂若行邱墟,寒烟自锁逃亡屋”(20)[清]戈陆明《逃亡屋》,[清]张应昌选辑《国朝诗铎》卷14,清同治八年(1869)秀芷堂刻本。“逃亡屋”一词大约出自唐末聂夷中五言古诗《咏田家》(一作《伤田家》):“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见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卷636,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7347页。)之句。“声闻”,佛教中通常称听闻佛陀言教便能证悟佛理者为声闻,其义颇为繁琐,诗中本词作动词用。“半偈经”,指记载佛陀释迦牟尼半偈舍身的《大般涅槃经》,据本经记载:释迦牟尼曾聆听罗刹讲说佛偈,因对方只讲到半偈为止,为能听取其馀半偈,他不惜答应非分要求,舍身奉施供养罗刹,最终得以如愿。(21)[南北朝]释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卷14《圣行品第七之四》,《乾隆大藏经》,彰化:传正有限公司乾隆版大藏经刊印处,1997年,第245-249页。
本段虽然与之前八句共用一韵,但在书写结构上却与前文不相连属,完全自成段落,实际上是全诗的点睛之笔,也是作者创作的初衷所在。作者此处既基于周氏藏品,同时又超越藏品本身,关照所处的现实生活,借鉴赏周氏藏品抒发了忧时伤世的思想感情,这当然是在借题发挥。本段诗句仍有一些文意不甚明晰,全段大意是说:谁曾料想,当初庄严的天花讲场,如今都不幸沦为逃亡之屋,自己如何才能具有佛陀那种半偈舍身的无畏精神,来替苍生弭罪祈福呢?此处所指现实,应该就是1918-1920年张敬尧统治湖南期间,与其诸弟横行霸道,买田置地,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致使当地民不聊生、逃亡流离的社会惨状。
四、结语
总之,曾广钧《题周鳌山藏唐人写经卷子》以记述周鳌山所藏敦煌文献相关情况为主题,直接或间接揭示了周氏藏品的数量、时代、形制、题名、书法及品相等诸多重要信息。关于周鳌山收藏敦煌文献一事,除曾氏此诗专篇记述外,尚未发现其他文字记录。对于周氏藏品的具体来源,诗中表示并不知情;至于藏品的下落,也无法通过诗作来考知。尽管本诗因文体属性而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无法为敦煌学研治者提供更加充分、准确的文献学信息,且既有记述不无含糊之病,时代等信息也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无论如何,本诗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诗作的解析,可以使久被淹没的周鳌山收藏敦煌文献史事得以钩沉,有望能够引发敦煌学界探访周氏藏品的下落,致力于文献的再发现。当然曾诗的学术价值不止于此,诗中还蕴藏着其他方面的研究旨趣,比如小注“张广建所得过千卷”的表述,可以为考察张氏藏品的实际数量提供有益的参考;再如所谓“畏公三十纸”,又可以为考察谭延闿收藏情况提供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