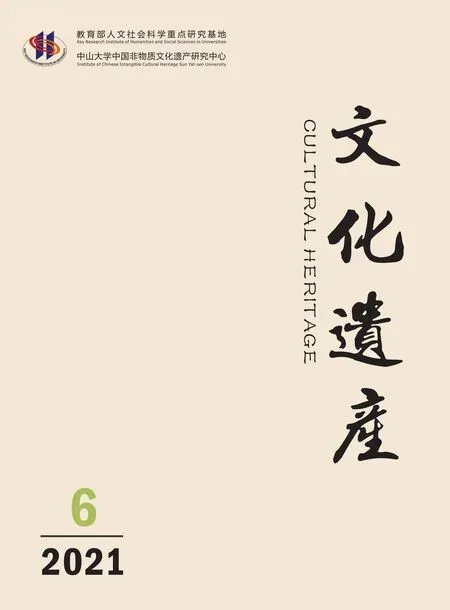活化历史: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学理建设思考*
高小康
一、 非遗研究:发现历史的“缺口”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发生和应用起自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遴选第一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和2003年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非遗保护不同于以往历史遗产考古与保护工作特有的高度专业性。从《公约》的指导和各国的实践来看,具体的保护工作包括建档记录、传承教育、传承人保护、社会传播等多方面公众性的文化活动。因为非遗保护观念的创新性和特殊性,这种文化保护活动不仅仅是具体的工作实践,而且需要在非遗保护的进程中不断进行理论观念和实践方面的科学研究。
我国自加入《公约》以来,在非遗保护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如今教育部把非遗保护增列为本科教育专业就是推进非遗教育与研究的一个重要措施。作为本科教育的非遗保护专业需要有更高层次的学术研究形成专业的学理基础,但由于非遗保护观念自身的创新性和学术内涵的复杂性,这方面的学理研究目前还是个需要开拓的新领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1年颁布《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可以视为非遗保护的前奏。这是20世纪后期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生态危机进行反拨的一种文化政治主张,伦理根据是当代世界不同群体、不同传统文化生存与发展权利的公平性。但随着非遗保护实践的进展,保护文化多样性不再仅仅是政治立场和姿态,实际上正在成为人类克服文化生态危机、寻求健康发展的科学路径探索。因此需要对这种文化实践的价值和目的进行学理探讨,从政治诉求进入到科学研究层次,使非遗保护成为促进人类文化生态健康发展的有效实践。
在教育部本科专业设置中,非遗保护专业是属于艺术学大类的学科范围。这显然是因为非遗项目的文化形态多与艺术相关,在具体项目的保护实践方面需要较多艺术学方面专业知识的原因。作为文化保护专业教育,提供保护知识、专业技能是没有问题的。但高等院校本科教育的目的并不仅仅限于提供现成的知识和技能,更要提供在知识传授背后支撑知识的学理基础教育,帮助学生深化思考、开拓视野,培养创新思维和创造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新的文化研究和保护实践的概念,非遗保护的理论基础、文化价值及其实践的可操作性等方面都是处于探索中的新观念、新实践、新问题,需要在非遗保护进程中不断研究。基于这种状况,应当认识到非遗保护专业不仅限于文化保护实践层面的专业学习,还应当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学理研究作为专业学术基础。
从深层次的学理基础上讲,非遗保护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具体被保护项目的艺术特征和价值的分析判断,而在于非遗保护对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发展关系的重新认识,即从文化传统内在的社会整合性、历史延续性、生态多样性和发展活力的视域,认识非遗对社会发展的普遍价值。从这个学理层面来说,非遗研究是一种历史研究,或者说是文化史学的学理研究。
然而非遗的历史研究又不同于传统史学研究。中国传统史学所追求的研究成果是“实录”,即真实、客观地记录事实。西方的历史研究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就是“叙述已发生的事”。(1)亚里斯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罗念生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9页。总而言之,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历史书写都是记录、叙述发生过的“事实”,即特定的人在特定时空中曾经发生的行为及其结果。历史的记录编纂和佐证历史的史料考证都是以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为前提的。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过去留下的遗产所关涉的历史却与传统史学所研究的历史不同——它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性“事实”,而是影响事实发生的“非物质”因素——规则、技能、习俗、意象、情感、信仰等等。这都是存在于“事实”背后,充满矛盾、缺失、虚构和不确定性的社会记忆内容。从传统史学对历史真实性或客观性的要求来看,这都是不可靠因而不具有历史价值的东西。
然而走向近代的史学研究越来越发现,纯粹客观、真实的记录和史料本身并不一定能够成为对人类对自身的理解和发展有意义的知识。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的那句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就是认为仅凭编年和史料这些客观资料的真实性并不能构成真正有意义的历史。他用笔记本和保存在首饰匣里的干花瓣比喻关于历史事实的编年和史料:
我们每个人在笔记本中记下我们的私事的日期和其他事项(编年史)或把绸带和干花瓣放在首饰匣中……但是我们知道,历史存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它的资料就在我们自己的胸中。因为,只有在我们自己的胸中才能找到那种熔炉,使确凿的东西变为真实的东西……(2)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3-14页。
他所说的“确凿”是指像干花瓣那样客观存在的事实,而“真实”则特指深藏于“自己的胸中”,与干花瓣相联系的蕴涵个人心灵体验的特定瞬间事件记忆。如果说传统史学关注的是事实的“确凿”,那么非遗的史学研究所侧重的就是记忆的“真实”,或者说心灵真实性。从这个意义上讲,非遗史学不同于传统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研究对象的变化,即从确认客观的“事实”转换到唤起内心的记忆。
传统史学历来相信历史记载的可靠性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所谓“信史”“实录”便是对历史著作最高的褒奖。然而如果参照克罗齐的比喻就会发现问题——札记的可靠性(编年)和干花瓣的真实性(史料)都具备了,但如果关于事件当时情境的记忆却淡忘了,那么无论多么可靠的历史叙述和事实证据还有什么意义?
对于传统史学来说有确凿的事实而无真实的记忆似乎是个悖论——有了事实记录当然也就有了记忆,或者反过来说有记忆才会有关于过去的记录。但这种“理所当然”的推论忽略了史学中的空缺问题:有的历史是不被记录的。美国社会学家芮德菲尔德提出了一种“一个文明两种传统”的理论:
在一个文明中存在着具有反思性的少数人的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和不具有反思性的多数人的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大传统通过学校或宗庙培育,小传统则在未受教育的村民社区中自行发展。(3)Redfield,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p.70.
这两个传统同属于一个社会,但却包含着不同的历史记忆。传统的历史书写即“正史”所记录和研究的是“大传统”,而“小传统”是在没受过教育的村民社会中通过口传、习俗等非文字方式传承,因而很少在“正史”中出现,也就是说是不被作为历史记录的。中国正统史学是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如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以及先秦典籍中对“黄帝四面”“夔一足”等传说的理性化阐释等等,都可以看出主流文化对经过官方或文人合理化阐释、整理的正统叙述之外的历史所持的怀疑态度。
然而“一个文明两种传统”显示出了正统历史在小传统记忆方面的缺失。这正是自18世纪维柯、赫尔德以来对民间记忆作为族群传统的历史观在近代历史研究中日益凸显的新史学研究方向。
两种传统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差异非常明显——大传统是书写的,而小传统是口传心授的。在一个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这两个不同的传统可能形成集体记忆的断裂。比利时口述历史学者范西纳在研究“口述传统的动态过程”时注意到记忆的断裂,他称为“浮动缺口”(the floating gap):
起源叙述,集体叙述和个人叙述都是同一过程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当把这些叙述整体组合在一起时,通常整体会出现三个层次。近代时期的信息越往前越逐渐减少,而在较早的时期,由于有些不确定,人们会发现信息要么有中断,要么仅仅剩下一个或几个名字。我把叙述上的断层称之为“浮动缺口”……一些人类学家已经用这些阶段来代表社会中的不同功能。第一个是神话,对应着恒久的过去;第二个是一个重复的(周期性的)中间阶段;第三个是线性时间……历史意识只在两个层次上运作:创世的时间和和最近的时间。由于时间计算的限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Generationenfolge)而变化,我把这个断层称为一个浮动缺口。(4)范西纳:《作为历史的口头传说》,郑晓霞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第17-18页。
范西纳所说的“浮动缺口”出现在口述历史的三阶段演进中——第一个阶段是久远的神话时代,第二阶段是周期性重复的中间阶段,第三阶段是当下的线性连续时间。范西纳认为历史意识只存在于创世时代的神话组织和当下经验的连续性中,而二者之间是会随着代际序列(Generationenfolge)浮动变化的“缺口”。这三个阶段对应的是早期口述历史、中期“周期性重复”的历史再到当代经验这三种历史时期,但在神话时代之后的中间时期是循环重复的“静态模式”,在口述历史中成为断层。
范西纳研究的是非洲土著历史,在神话与当代之间似乎是个空白。而在传统的轴心文明中,这个中间时期正是“大传统”形成的主流历史时期,口述历史因其不雅驯而被主流文化遮蔽,成为集体记忆的“缺口”。如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所说:
历史通常始于传统中止的那一刻——始于社会记忆淡化和分崩离析的那一刻。(5)哈布瓦赫:《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埃尔、冯亚琳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余传玲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7页。
他所说的“历史”就是指正统的或者说作为大传统文化传承内容的历史书写,而“传统中止”的“传统”是指正史之前的集体记忆传统。正统历史书写开始就意味着此前集体记忆传统的“淡化和分崩离析”。一个文明因此而分裂为两个传统——主流历史书写的大传统与“淡化和分崩离析”的集体记忆小传统。
然而反思的、理性的大传统历史知识只是文明的显性表象。隐没在历史表象背后的集体记忆中隐含着文明底层的生命动力。班固曾引孔子“礼失而求诸野”,认为诸子等民间杂说可补正统文化“礼”之遗,说明民间文化对主流文化的传承延续具有互补之用。范西纳所谓“历史意识只在两个层次上运作”,可以理解为在主流文化“大传统”的历史书写中,作为集体记忆的口述历史是缺失的,“小传统”被遮蔽,因此形成了历史意识的“浮动缺口”。非遗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正是从这个“浮动缺口”进入,重新发现被遮蔽的集体记忆,构建大小传统整合的“更大传统”的历史研究。
二、书写的历史与鲜活的记忆
传统意义上的史学所研究的基本内容在于叙述,即历史书写。历史叙述的表层是对事件的叙述,深层是叙述的逻辑——关于事件的因果关系梳理与阐释;使叙述逻辑及其阐释得以成立的根据是关于事件的证据即史料。
然而在德国学者卡西尔看来,历史作为插入人和过去之间的符号系统,不仅仅是证据和叙述;更重要的是这个符号体系背后隐藏的东西:
如果我们知道了编年史顺序上的一切事实,我们可能会对历史有一个一般的框架和轮廓,但我们不会懂得它的真正生命力。而理解人类的生命力乃是历史知识的一般主题和最终目的。(6)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233页。
对于编年史背后生命力的发现,卡西尔强调了赫尔德历史观的意义:
在历史哲学的近代奠基者之中,赫尔德最清晰地洞察到了历史过程的这一面。他的著作不只是对过去的回忆,而是使过去复活起来……正如歌德在一封信中所说的,他在赫尔德的历史叙述中所发现的并不仅仅只是“人类的表皮外壳”。使他极度钦佩的乃是赫尔德的“清扫法——不仅仅只是从垃圾中淘出金子,而是使垃圾本身再生为活的作物。正是这种“再生”,这种过去的新生,标志出伟大的历史学家的特征。(7)卡西尔:《人论》,第225页。
此后,法国史学家米什莱也强调了历史研究要使过去复活的观点:“‘让往昔复活’,这正是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之一。”(8)哈斯克尔:《历史及其图像》,孔令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378页。历史怎样才会“复活”呢?米什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大革命之后很久,有位年轻人向上了年纪的梅兰·德·蒂翁维尔(Merlin de Thionville)请教,如何才能让自己去恨罗伯斯庇尔。这位老先生好像对他的举动很遗憾,但接着猛然一振,“罗伯斯庇尔,”他说,“罗伯斯庇尔,只要你见过他的绿眼睛,你也会像我那样恨他。”(9)哈斯克尔:《历史及其图像》,706页。
在这段叙述中,历史从事件变成了记忆中的现场——大革命时代的创伤通过罗伯斯庇尔的“绿眼睛”所留下的恐怖记忆再度触动心灵而复活了。
稍晚于米什莱的荷兰史学家赫伊津哈接过了米什莱“让往昔复活”的观点,他认为复活历史的要素是“历史思考中的审美元素”,(10)哈斯克尔:《历史及其图像》,第705页。即包含着生动画面和激情的历史情境。在他看来,人们不是从研究文献中而是从图像的感知中了解历史的。他在《中世纪的衰落》一书中对中世纪史研究的创新性在于,把历史研究的重点从证据学转移到图像学,通过对艺术作品的图像学分析、对当时社会公众生活的仪式、风俗和激情的再现来重构历史的生动情境。他在研究公众活动场景时特别指出:
要想完全理解那个时期人们生活的话,就必须牢记这些极富感情色彩的公众活动……现在的读者,在研究那些基于官方资料的中世纪历史时,是永远无法充分认识到那时人们的情绪是多么易于激动。虽然官方的资料可能是最可靠的来源,但这些资料缺少一个内容,那就是无法充分地表达出王侯和老百姓皆有的炽热的激情。(11)赫伊津哈:《中世纪的衰落》,刘军等译,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5-11页。
在这段叙述中,赫伊津哈所关注的那些比官方资料更重要的“极富感情色彩的公众活动”,正是历史书写背后的非物质文化层面。
实际上,早于赫伊津哈的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已体现出从社会生活习俗视野研究历史的特点:“雇佣兵队长和人文主义者的简笔肖像,叙述简练的复仇和恶作剧之类的轶事趣闻,表明诗人和历史学家对待诸如风景、荣誉或者死亡之类各种题材的态度的引文等等。恶行,狂欢,英勇的壮举、对荣誉的渴求,这些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全景中的组成部分。无数来到意大利的旅游者挤满了佛罗伦萨、锡耶纳和威尼斯的大街小巷,充满他们想象的正是这些场景和事件。”(12)贡布里希:《理想与偶像》,范景中等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第50页。
从鲜活的社会生活场景去感受和理解历史,这种“复活”历史的研究意图是近代从事实的研究转向风尚、习俗研究的一种趋势。作为历史内核的集体记忆研究也从客观性延伸到心灵性。哈布瓦赫在研究集体记忆时,特别关注到那些不同于实证史料的非物质性记忆,如梦境,心灵体验等等。他在研究基督教传统时注意到宗教历史的两个传承维度:教义取向(dogmatic)与神秘取向(mystic),“有时是前者占优势,有时是后者占优势,而且最终宗教产生于这两者的妥协。”(13)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0页。他把神秘主义和教义主义之间的关系称作“鲜活的记忆和多少变为成规的传统之间的关系”。(14)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第181页。教义主义以教义经典的保存和阐释为根据,属于基督教社会的“大传统”传承。这种传统多少变为固化成规的传统,逐渐失去了宗教精神在后代社会持续传承的内在活力。神秘主义者则是在心灵中自由地体验宗教以构建自己所感知的直观形象,通过自己的神秘直觉解释经文,以从中发现与当下兴趣相关的新的意义。
在哈布瓦赫看来神秘主义并不比教会传统更精确地接近真实的过去。神秘主义的记忆对经义的解释难以被主流经学所承认,更难以被史料所证明。然而它体现的是当时的人从圣经所获得的心灵体验,那种独特的直觉属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体现了当下的宗教精神需要,因此被称为“鲜活的记忆”。对后代史学来说,这种神秘主义体现了每个时期人们的特定体验。如中世纪的神秘主义所体现的就是中世纪人们对基督教信仰的记忆和心灵体验。由此而形成了关于一代代人的心灵体验历史,这就是“鲜活的记忆”。
作为心灵体验的集体记忆之所以能够被传承认同,就在于它是“鲜活的”,它是被直观地看到、感知到的。被视为虚幻的宗教体验,在建构特定社会的文化共识和情感认同方面却又是实在的。通过“鲜活的记忆”所构建的心灵史是族群认同的历史。这种心灵史的价值不在于考据意义上的客观真实性,而在于它体现了某个文化群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心灵体验和情感认同的凝聚过程。
从非遗保护的视角来看,包括宗教体验在内的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历史性就在于集体记忆活化所形成的文化认同持续建构的过程。形形色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内涵,归根结底都凝聚于集体记忆所蕴涵的情感共鸣和社会共识上,通过这种文化精神的凝聚力在现代世界形成了各种文化传统的社群性、民族性认同。“鲜活的记忆”生产着想象的历史,从而形塑起一个族群、一种文明的精神传统——如美国学者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安德森把现代民族共同体称作“想象的”,是因为在他看来,现代民族共同体“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15)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页。这就是说,作为共同体精神内涵的民族文化传统是一种使群体成员“相互联结的意象”,即通过传播交流而感知到的集体记忆表象。从这个意义上讲,“想象的共同体”就是在社群历史中持续存在和发展的活的历史共同体表象,是社群历史的活力和持续性的证明。
三、非遗保护的生态条件:后全球化文明
非遗学科的学理研究应当与非遗保护和传承的操作相结合,需要把非遗学的学理思维逻辑和研究成果与非遗保护实践打通,通过学理性的研究和深度思维解决真正要保护的文化内涵是什么以及如何才能实现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初衷。
非遗保护不仅仅是从知识与艺术价值角度认知、评价和保护文化遗产的活动,更重要的是与20世纪后期文化政治的全球化趋势相关: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传播与发展造成了全球文化的同质化危机。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提出承认文化多样性,确保属于多元的、不同的和发展的文化特性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和睦关系和共处。在宣言的基础上开始的非遗保护关注的重点是多元文化政策,即为了抵制文化霸权而保护和发展处于弱势的文化,尤其是对处于濒危状态的少数族群文化遗产进行抢救。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描述过一些人类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关于爱斯基摩文化即将消亡的警告:
移民到大陆上的甘贝尔村民“已不再是爱斯基摩人,不再是保有一种他们自己文化传统的民族了。”这是那个时代人类学的一般见识,也同样是预见家乡社区最终要被涵化(acculturation)的补充性看法。(16)萨林斯:《甜蜜的悲哀》,王铭铭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119页。
这种关于土著文化和乡土文化即将消亡的警告正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的认识和观念背景。问题的重点还不是这些传统文明正在消亡中,而是在于挽救这些文化遗产是否可能?在19世纪进化论和历史主义观念影响下,学者们多相信历史进化的必然性和线性。按照线性的历史进化论,传统文明进入现代社会之后面临的是不可避免的被抛弃的命运:“阿基里斯能够同火药和铅弹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17)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页。爱斯基摩人的雪橇、猎鲸生活当然会随着整个族群向南迁移而消失,所以“不再是爱斯基摩人”了。在这个文化背景下对土著和少数族裔文化的保护似乎多在考虑如何建档记录和数字化,如何建立保存乡土文化残余形态的生态博物馆等等,似乎是在对即将消失的文化进行某种临终关怀式的保护、博物馆化的保存和纪念性的追思。
萨林斯却提出了与临终关怀不同的相反观点:“爱斯基摩人还在那里,并且还是爱斯基摩人……爱斯基摩人既变化得多,而同时又变化得非常少。”(18)萨林斯:《甜蜜的悲哀》,第119-120页。他认为,那些原本属于远离现代文明的土著文化在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正在经历着“现代性的本土化”过程:
最近几个世纪以来,与被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所统一的同时,世界也被土著社会对全球化的不可抗拒力量的适应重新分化了。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的同质性与地方的差异性是同步发展的,后者无非是在土著文化的自主性这样的名义下做出的对前者的反应。因此,这种新的星球性组织才被我们描述为:“一个由不同文化组成的文化”(a culture of cultures)这是一种由不同的地方性生活方式组成的世界文化体系……不同的民族要求在世界文化秩序中得到自己的空间……它所代表的方案,就是现代性的本土化。(19)萨林斯:《甜蜜的悲哀》,第123-124页。
萨林斯在20世纪末说当代多元文化的发展是走向“现代性的本土化”,似乎还难以令人信服。但自从非遗保护公约颁布以来,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却在发生着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逐渐从临终关怀转向“由不同的地方性生活方式组成的世界文化体系”建设。
传统文化保护意识的这种变化意味着同质性的全球化正在转向本土化的多样性发展。但真正实现这种文化发展意识的转向,需要非遗保护观念在学理层次上的发展和深化:
首先是对“保护”这个概念的重新解释——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概念是对物质性对象的固化保护,而非遗保护从物质性对象转向非物质文化形态,保护的方式也从固化保护转向活态保护,即通过介入参与使物质性对象成为具有意义的活动。
其次是从“遗产”的遗存观念转向传承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一般意义上的遗产不同:它不是前代遗存之物,而是代代相承的社会生活内涵。
再次是历史观的演变——从线性历史进化论所呈现的“现代性”当下对“本土性”过去的否定转向“现代性的本土化”,即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化的吸收和再生。
总体上说,非遗保护的内容从寻求过去遗存的“本真性”拓展到发现和培育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活力,意味着当代社会文化生态的多样性演化。非遗保护的学理研究中,如何认识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存在、传承与发展状况,重点就在于对当代世界文化环境中各种地方、族群社会的传统文化如何继续传承发展的文化生态根据。
19世纪法国学者丹纳是主张“研究历史就是复活历史”的史学家之一。他“复活”历史的方法就是找到历史生成的基本要素,发现其间的关系。他提出的文化传统生成的基本要素是:种族、环境和时代。(20)泰纳:《英国文学史》序言,杨烈译,《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236页。
丹纳所说的三要素可以抽象为社会、空间和时间,这是文化产生发展最基本的生态要素。可以说他是在20世纪文化生态学创立之前就开始从文化生态视角研究历史的学者。依据对特定种族生活方式、环境影响和历史传承积累的分析,他从物化形态的艺术品和史料中解读出鲜活的生活和生命历程。他这种研究方法受到了赫尔德和温克尔曼关于文化史、民俗史和艺术史研究的影响。对于今天我们解读历史的文本仍然有重要意义。
但在今天的非遗历史研究中,丹纳的文化生态史三要素观念面临着重大挑战,就是文化生态在当代的蜕变问题。
如果把人类征服、改造自然以获取生活资源的能力达到爆炸性水平的工业文明视为人类社会生态的一个顶峰,那么从工业文明到后工业化时代,人类社会的文化生态则发生了颠覆性的演变。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文化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提出了“内爆”(implosion)的概念:从身体在空间的延伸转向中枢神经系统向全球的延伸,(21)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0页。即智能空间的发展在逐步取代地理环境。到21世纪初,美国社会学家卡斯特提出当代城市社会中“流动空间与地方的张力与结合”(22)卡斯特:《21世纪的都市社会学》,刘益诚译,《国外城市规划》(京)2006年第5期。,意味着当代文化生态正在经历着根本性的转换。
新的文化生态正在建构新的历史关系——这正是非遗历史研究所要面对的新问题。简单地说,就是从丹纳的“族群/环境/传承”生态三要素转换为“跨域群体/流动场景/智能传播”这些新生态要素的历史性演化——与特定文化传承相关的群体从传统的社区群体扩展到网络社交群,传统社群所依附的自然环境转换为跨域生活的流动场景,族群共同体的历史传承被智能化分形化传播网络切割和改造。(23)参考高小康《社群,媒介与场景:非遗活化三要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1年第1期。
从丹纳的历史文化三要素到当代新生态要素,这种转换的历史背景是全球化转向后全球化文明的时代文化特征。20世纪后期,以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为代表的文化多元主义强调的是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对抗,或者说是“为承认而斗争”(24)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8页。。但生态多样性存在的基础不是对抗而是多样性的共生。从雅斯贝斯把全球文化发展史区分为三大轴心文明至今,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同文明日益走向全球性联系,走向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但同时全球的文化形态及其生态界限又在不断分化中:从文明类型到民族国家,地域族群,社区,代沟,粉丝圈……一层层分化和裂变。当代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多样性,更重要的是随着信息传播的发展而产生的多维和多质性演化。从芝加哥学派的区位空间生态到移动互联时代的信息生态之间是一个世纪文化生态发展演化的历史——从“全球分裂”到全球分形(fractal),即趋向不规则多维化自组织发展的文化新生态。
这种文化新生态的意义一方面在于对小生态自足性的保护防止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剥夺;另一方面通过大的生态关联来消解断层线对抗的危机——每一个特定的文化生态群落既需要保持自己的群体归属感和内在活力,同时又要构建与整个生态环境的相互性开放关系,即全球冲突下的文化互渗与互享关系。这是非遗保护的总体生态背景——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新生态:在全球冲突背景下通过文化多样性保护与互享重构人类文化共同体发展的理论愿景与实践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