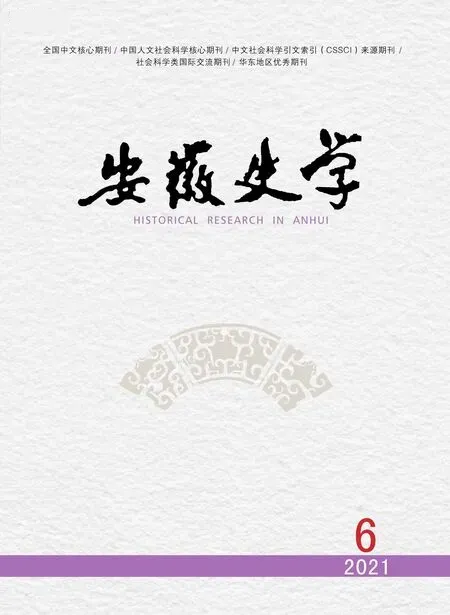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反对依赖国联之政治主张探析
吴元康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安徽 合肥 230051)
关于冯玉祥与九一八事变的关系问题,学术界已有多篇文章予以阐述。(1)如陈兴唐、韩文昌:《“九·一八”前后的冯玉祥将军》,《历史档案》1982年第3期;郭绪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冯玉祥》,《齐鲁学刊》1982年第6期,等。可能囿于视角的不同,这些论文对于冯玉祥对待国联的态度并未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实际上,作为民国要人中严厉抨击国联并强烈反对依赖国联调处中日争端的典型代表,冯玉祥与国联的关系问题当然甚有学术探讨的价值。为弥补上述研究中的缺憾,笔者拟依据冯玉祥的日记、文电等资料,对这一专题进行全面探讨,冀以推进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冯玉祥始终坚决反对蒋介石完全依赖国联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军张学良等人在军事上奉行不抵抗方针,同时采纳顾维钧的提议,立刻电告南京,请求国民政府与国际联盟行政院联络,由其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国民党中央接到张学良的电告后,经开紧急会议,认可顾维钧的建议。19日,外交部将有关指示下达给中国出席国联大会的代表施肇基,21日施肇基致函国联秘书长德鲁蒙,报告日军侵占沈阳及东北各地情形,请国联根据盟约第十一条规定立采步骤,阻止事态扩大。此一举动表明,依赖国联的外交方针正式实施。当晚,自江西赶回南京的蒋介石召集要人开会,再次明确对日问题“诉之国际联盟”。(2)王仰清、许映湖整理:《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76页。22日上午,南京全市国民党员大会,蒋介石发表演说,侈言日本此次举动破坏国际联合会盟约及凯洛格非战公约精神,“余敢信凡国际联合会之参加国及非战公约之签定国,对于日本破坏公约之行为,必有适当之裁判。”(3)《蒋主席演说对日步骤》,《大公报》(天津)1931年9月23日。23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国民书》,声称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院以待合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全体国民应一致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至此,国民政府在军事上不抵抗,在外交上依赖国联作为基本政策得到进一步确定。
面对空前国难的严峻形势,在要不要求助国联的问题上,冯玉祥呈现出与国民党中央截然不同的态度。
1930年中原大战,西北军失利瓦解,冯玉祥被迫隐居在山西汾阳县峪道河乡下。1931年9月21日晨,冯玉祥得知日军侵占沈阳的消息,同日下午,他接到国民党要人孔祥熙从南京拍来的号(20日)电。孔电除报告日军在东北的暴行外,还征询冯玉祥对国事的意见。(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3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88、557、563、603、616页。23日,冯复孔祥熙电,着重谴责蒋介石数年来排斥异己,谋求独裁以致外侮不断的罪行。同日冯在复孔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出致全国同胞电,明确指出蒋介石对日不抵抗,“不以为辱,尤为无气骨无人格之言,曰:听候国联,主张道德,主张公理,试问,中国数十年来积受帝国主义压迫之惨,国际公理究竟安在?”依赖国联主持公道,不过“梦呓”而已。(5)《冯玉祥选集》中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50—651页。另见《冯玉祥表示正式抵抗侵略》,《申报》1931年10月3日。梗(23日)电旗帜鲜明反对国民政府求助国联主持公道的外交方策。从现在寓目的资料看,这也是国内公开反对蒋介石九一八事变后外交政策的第一声。26日,他在复社会名流熊希龄的宥电中,再次强调蒋介石政权不过为帝国主义工具,“既未闻有备战之举,反以镇静为名,以为日帝压服我国民之救国运动,徒曰哀求国联会议”,纯粹为“与虎谋皮,自欺欺人”之举。(6)《冯玉祥选集》中卷,第654、668、686、696—697页。随后,宥电被《申报》等报发表,公诸天下。(7)《冯玉祥近复熊希龄》,《申报》1931年10月12日。但因冯玉祥此时尚为在野的反对派,他的声音被国民党主流派漠视,也就不难理解了。国民政府继续奉行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
从国联方面说,面对该组织成立以来最大的国际事件,为了维护自身威信,国联对中日冲突未尝不重视。自中国代表团将有关报告及诉求提交国联后,国联多次开会,并于9月30日及10月24日两次通过决议,要求日本限期撤兵。日本不惟不接受,相反扩大侵略作为回应,充分显示出国联的懦弱与日本的跋扈。残酷的现实使冯玉祥更加忧心忡忡。11月2日,他在给自己的部下、甘肃地方实力派雷中田的信中,详细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在涉及外患的部分,他特别强调“关于国联者:国际联盟虽对中日问题开会议多次,但欲专恃国联,中国决难取得胜利,必须中国自己努力,方可恢复已失之权利,其他皆不足恃也。”(8)《冯玉祥选集》中卷,第654、668、686、696—697页。12月13日,他在致汪精卫的密电中,再次强烈指责国民党当局依赖国联的政策,“自东省事变发生以来,瞬将三月,南京毫无办法,只知国联是赖,对国人则粉饰敷衍,欺骗压迫,致使外患日趋日烈,存亡之机系于一发。”(9)《冯玉祥选集》中卷,第654、668、686、696—697页。12月25日,他致电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指出“政府盲信国联”的后果,是日本扩大占领的警耗不断传来,必须要改弦易辙,方可挽救危亡。(10)《冯玉祥选集》中卷,第654、668、686、696—697页。
1931年底1932年初,国民党内部广东派在与蒋介石派的争斗中暂时占得上风,蒋介石下野,孙科担任行政院长。粤派得势原使冯玉祥抱有相当大的期许,但在现实中,孙科等人由于多种因素,难以施展手脚,在外交上仍延续依赖国联的政策,使冯玉祥大失所望。这一情绪在冯的日记中时有流露,如1932年1月7日日记,“今日之内政外交,都是违背国民的要求。这样下去,只有失掉国民党的信誉”;(1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3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88、557、563、603、616页。1月20日日记,“痛思国事,万分焦急!前线的恶劣消息不时传来,东北同胞在水深火热之中,政府视若无睹,只说诉诸国联,请求制裁。这有什么用呢?”。(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3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88、557、563、603、616页。
几乎与此同时,国联鉴于日本拒不执行国联的有关决议,使国联自身的威严受到严重影响,为了遮掩弱不中用的形象,决定组织国际调查团赴中日调查九一八事变及后续衍生的系列事件,以为国联最终作出判断提供证据。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团长为英国人李顿爵士,3月中旬抵达中国。
对于国联调查团来华,冯玉祥从一开始就极为反感。1932年3月底,他对该月发生的大事进行总结,即认为调查团来华“有亡国之象征”,因为“帝国主义间合谋宰制东北之机兆矣”。(1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3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88、557、563、603、616页。4月底,他又作总结,认为“国联调查团来中国,这是一个国际阴谋,企图与日寇协调对我实行瓜分共管。他们还欢迎,我真痛恨!”(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3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88、557、563、603、616页。李顿调查团在中国各地受到“皇室般的接待”(15)1932年4月9日李顿致他的妻子的信,见朱利译、金光耀校:《李顿赴华调查中国事件期间致其妻子信件(上)》,《民国档案》2002年第2期。,但在冯玉祥处却吃了闭门羹。原来1932年6月,李顿调查团在赴青岛途中,在泰安停留,欲赴泰山探访正在泰山养病的冯玉祥。冯玉祥认为他们系“一群着洋服的强盗”(16)《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638页。,拒绝见面。
1932年10月2日,李顿报告书在东京、南京、日内瓦三地同时公布。该报告书否认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出于自卫的说法,否定伪满洲国成立的正当性,却又不主张恢复九一八事变前中国东北的原状,剥夺中国军队驻扎东北的权利,企图通过设置顾问会议的办法达到国际共管中国东北的目的。对这份报告书,胡适等人大加褒扬(17)胡适:《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独立评论》第21号,1932年10月9日。,主流社会舆论虽对报告书中损害中国主权的部分严厉批评,但总体上认同,国民党决策层除对若干内容持保留意见外,其余均予以接受。冯玉祥则本其一贯反对求助国联立场,坚决反对该报告书。10月9日,他在张家口联合李烈钧、柏文蔚、熊克武等14位国民党中央委员发出通电,驳斥李顿报告书的种种谬误,尤其反对设置顾问会议的办法,昭告国人:“徒尔求助国联,实为民族自杀”,要求当局“应于政策上有立决之转变,放弃不抵抗主义及依国联之谬想,速解人民束缚,切实与民众合作,全国动员,抗暴日而收复失地”,呼吁民众“不忘主人地位与责任,严密监督政府,坚决为武力抵抗而奋斗,毋使暴日之铁蹄得留于中国,毋使国际不正确之调处得以实现”。(18)《冯玉祥选集》中卷,第766—767、650—651页。该电发至上海后,很快传遍全国,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19)《十五中委指摘报告书》,《大公报》(天津)1932年10月10日。12月,他又撰写出版《反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一书。该书长达260余页,70万字左右,指斥李顿报告书“明明白白地是一部严密而周详的共管中国的计划书!”(20)《冯玉祥选集》上卷,第111页。逐条批驳报告书的内容,彻底否定报告书。1933年2月23日,国联大会通过依据李顿报告书起草的决议草案,日本代表气急败坏,愤而退席,3月27日日本政府正式通知退出国联。中国无法再依赖国联,冯玉祥与国联的关系就此告一段落。
二、冯玉祥缘何反对求助国联
冯玉祥反对求助国联,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一为自始至终,自1931年9月23日发出梗电始,迄1933年初日本退出国联,中国求助国联政策失败止,冯玉祥始终宣示反对立场,一直未改初衷。国民党内胡汉民、李宗仁、孙科等人虽然也认为国联不足恃,但他们基本上在李顿报告书公布后才秉持这一立场,此前并无明显表示。这使他们与冯玉祥略有不同。一为旗帜鲜明,他通过发通电、提议案、出专著等方式,向国人明白昭示自己的立场。他这种毅然决然的态度,是其他任何名人无法比肩的。他堪称反对求助国联政策第一人。
冯玉祥为何大声疾呼不可向国联求助呢?个中原因,可以列为以下三点。
(一)基于冯玉祥对国联的深刻认知
九一八事变前,冯玉祥未曾直接置评国联,但他在特定场合的一些言行间接反映了他对国联的基本倾向。如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英、日屠杀中国同胞及国联的沉寂使冯玉祥清醒地认识到,“现今时代,公理人道,全不可恃”(21)《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80、98、123页。,“现在世界,无公理,无人道”,“如依公理人道,而求民族自决以救国家,实如梦想”。(22)《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80、98、123页。他甚至说“世界之无公理,强凌弱,众暴寡,已成国际定例”。(23)《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80、98、123页。中原大战失败后,他归隐山林,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著作,思想进步相当快,他对帝国主义国家的认识也深深烙上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印记。
九一八事变后,因国民政府将国联视为主持公道的救星,冯玉祥力陈其非计,才得以将自己对国联的具体看法宣示于国人面前,其实这些看法在九一八事变前即已形成。1931年9月23日冯玉祥发出致全国同胞电,明确指出“中国数十年来积受帝国主义压迫之惨,国际公理究竟安在?国人稍有常识者皆知,国联组织不过一列强宰割弱小之屠场耳。”(24)《冯玉祥选集》中卷,第766—767、650—651页。三天后,他在复熊希龄的电文中,又一次重申:“宰割弱小民族之国联,能代中国求独立,能代中国打倒该会常任理事之日本乎?与虎谋皮,自欺欺人。”(25)《冯玉祥选集》中卷,第654、650、696—697、767页。1932年1月20日日记,他再次感慨:“操纵国联的几个列强,都是侵略的帝国主义,谁能替半殖民地的中华民族伸冤呢?事实上恐怕连公道话也不会说一句的。”(26)《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563,595,638、616,674,488,489—490,543页。在冯玉祥看来,日本固然可恶,但操纵国联的英、法等国也非善类,它们在欺压弱小民族问题上是一致的。他后来干脆称国联为“强盗组织”,日本为东方的大强盗,“当然强盗是互相帮助的”,中国求助于国联,就是“找强盗们谈公理”。(27)《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563,595,638、616,674,488,489—490,543页。国联调查团来华,他目之为“一群着洋服的强盗”,来华的目的无非强迫我国接受卖国条约,以便与日本协调,“对我实行瓜分共管”(28)《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563,595,638、616,674,488,489—490,543页。,因为帝国主义的本性“离不了分赃”。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曾多次揭露国联的本性,如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决议就称国联为“强盗机关”,9月30日,中共中央为九一八事件发表第二次宣言,强调“国际联盟,是帝国主义压迫弱小民族的工具,希望国际联盟来帮助中国,无异与虎谋皮”。(2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8、432页。这些措辞与冯玉祥的表述几无二致。从中不难看到,冯玉祥对国联本性的认识极为深刻。在他看来,国联既为帝国主义强国宰割弱小民族的机关,中国向它求助,要么无济于事,要么落得“国际共管”的下场,对中国不惟无益,且贻大患。这是他坚决反对求助国联的出发点之一。
(二)源于冯玉祥坚定的民族气节
1893年,12岁的冯玉祥迫于生计,投身清军,逐渐萌发了朴素的反帝观念。(30)冯玉祥:《我的生活》上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47页。进入民国后,随着军职的不断升迁,冯玉祥的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大,他的反帝观念愈加炽烈。多年来与列强打交道,使冯玉祥认识到“对待帝国主义,非用强硬态度不可,盖我若退一尺,彼便进一丈,只要理由充足,即勿妨以革命精神,与相抗衡也。”(31)《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539页。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在军事上对日本侵略奉行不抵抗政策,对此,冯玉祥从民族气节出发,力陈其非计,主张对日强硬,坚决抵抗。9月2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以为此时应成立雪耻军以对日人”。在9月23日发出的对全国同胞电中,他呼吁“统一革命力量,一致对外,先行对日绝交,准备对日决战”。(32)《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563,595,638、616,674,488,489—490,543页。翌日,他在日记中又提到“国事如此,伤心万分,除与日寇拼命以外,别无善法,如不问人家如何,我总应先去拼拼,为全国倡”,提出处此严重国难局面之下,“须以对日为主,对内为副”(33)《冯玉祥选集》中卷,第654、650、696—697、767页。,后来他甚至说:“国家的事到了如此地步,我要不能抗日,莫如即日死了为好”。(34)《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563,595,638、616,674,488,489—490,543页。1931年12月25日,他于太原致电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向大会提交“实行以武力收复东北失地”案,建议迅即组织国防委员会,挑选劲旅,集中最前方及其它重要地带,实行征兵制及全国总动员,总之,“除以武力与暴日周旋以外,别无保全领土主权之良策”。(35)《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563,595,638、616,674,488,489—490,543页。
正因为冯玉祥甚有民族气节,坚决主张抗击日本侵略,他对蒋介石的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依赖国联的政策当然难以苟同。虽然军事上不抵抗与外交上依赖国联并不具有前后因果的必然联系,但外交上依赖国联确实为国民政府实行军事上不抵抗政策提供了凭借。查1931年9月23日国民政府发表的告国民书,其中提到“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院以待合理之解决,故已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36)《中央、国府告国民书》,《大公报》(天津)1931年9月24日。,这段话表明两者之间的关联已再清楚不过了,难怪冯玉祥在指斥蒋介石的种种行径时,也常常将“不抵抗主义”与“依赖国联”连在一起。(37)《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563,595,638、616,674,488,489—490,543页。冯玉祥既然在抗日问题上态度最为鲜明,主张最为激进,他在挞伐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的同时,当然也要反对依赖国联。
(三)出于他个人企图东山再起的考虑
冯玉祥深知,要想推动国民党决策层走向武力抗日之路,就先要使其丢掉对国联的幻想,故他反对依赖国联政策不遗余力。而唯有在全国实行对日作战后,蒋介石不能腾出手来防范异己势力,他自己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隐居于山西汾阳县乡下。乡居期间,他一边读书,一边密切关注国内局势,图谋重振旗鼓,为此他除与各地旧部暗中往来外,还同各种反蒋势力尤其是两广的实力反蒋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九一八事变后,社会舆论要求停止内争,一致对外。两广派及北方冯玉祥、阎锡山等人深愿团结御侮,但均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12月15日,蒋介石迫于各方面压力,宣布下野,国民党内拥蒋派与反蒋派开始合流。该月底,冯玉祥风尘仆仆,自山西赶往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此前后,他多次表示,此次南来为的是“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并非为了争权夺利。(38)《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560、578、569、603、569页。
事实是否果真如冯玉祥所说再无权利之念呢?答案是否定的。1931年12月底,冯玉祥自宁赴沪慰问汪精卫时,即随身携有武力收复东北失地的详细计划,内容系将冯玉祥、阎锡山在西北各旧部为一种新的编制,分期动员,开赴前方,其兵数约得三十旅。(39)《冯玉祥主张武力收复失地》,《申报》1931年12月31日。因汪精卫正准备拉拢蒋介石重新上台,对冯避而不见,冯的整军计划无从实现。1932年1月28日,汪精卫取代孙科担任行政院院长,成立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翌日,国民党中政会第26次会议,决定设立军事委员会,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人为委员,指定蒋、冯等5人为常务委员。冯玉祥虽然为军事委员会常委,但一点实权也没有,对此他牢骚满腹,威胁如不让他带兵,就辞去一切职务。(40)《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560、578、569、603、569页。对于国民党内的暗斗,旅居上海的张耀曾在1932年1月18日日记中曾提到早至黄炎培家会谈,“闻蒋与粤、冯间仍在预备武力争雄长,心中甚慨,而苦无术回,此亡国心理也”(41)杨琥编:《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13页。,说明时人均观察到冯玉祥有重振军旅的图谋。
对于冯玉祥借国难之机重回部队的心计,国民党内的拥蒋派当然洞若观火。当1931年12月中旬冯玉祥提出全国总动员,武力收复东北失地主张时,蒋作宾认其为“另有作用”。(42)上海市档案馆编:《蒋作宾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94页。1932年1月底,蒋介石重新上台后,对冯玉祥处处设防。3月5日,国民党中央遵照汪精卫的提议,决定由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掌握一切军事大权,其他常委仅为委员长的辅助人员。(43)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早在1月27日蒋介石正式复出前,冯玉祥就认为“国家的外交、财政均为蒋所操纵” ,现军事大权又归于蒋,故“洛会召开而独裁复活”。更让冯玉祥难堪的是,在此前后,1930年一同参与反蒋的阎锡山被委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李宗仁被委为南宁绥靖公署主任,独冯玉祥向隅。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曾提议任命冯玉祥为开封绥靖公署主任,蒋介石不允。冯玉祥恨之刺骨,坚辞内政部长职,不久即称病经徐州赴泰山居住,暗中策划倒蒋。(44)参见杨天石:《冯玉祥与胡汉民》,《团结报》1992年2月29日。
在与蒋介石分分合合的过程中,冯玉祥深知其秉性。在国难局面下,蒋介石“对外不战,对内用武力统一”。(45)《冯玉祥选集》中卷,第654、650、696—697、767页。1932年3月,与冯玉祥走得很近的韩复榘曾切身感受到来自蒋介石方面的威胁。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冯玉祥认识到,只有全国总动员,武力对抗日本,他自己才会有生存壮大的空间。而要推动国民党走向全面抗战,在当时情势下,就需要切断国民党对国联的幻想。冯玉祥之所以坚决反对依赖国联,应该有这些自身利益上的考虑。
三、应该如何评价冯玉祥反对依赖国联的政治主张
国民政府推出依赖国联主持公道政策之初,国内各种政治派别,除中国共产党外,对这一政策或赞成或默认,反对者极为罕见。在此背景下,冯玉祥大声疾呼,力陈求助国联之非计,颇为社会各界侧目。只是形格势禁,冯玉祥的这一政治主张未能对国民党决策层产生丝毫的影响。
那么,应该如何评价冯玉祥反对完全依赖国联的政治主张呢?这个问题要分开来看。总体来说,冯玉祥的这一政治主张建立在深刻把握现实的基础之上,抓住了能否依赖国联这一问题的本质,代表着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因而值得肯定。反过来说,国民政府完全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实为一种误国政策,并不可取。
首先,国联根本没有为中国伸张正义的意愿。国联表面上标榜维持世界和平,实则为强国维系既有世界秩序并宰制弱小民族之工具,大权完全掌握在英、法、德、意、日等五个常任理事国手里,其中主要受英、法二国控制。这些强国的代表往往根据自己国家的利益来行事,追求的是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根本没有公理与正义可言,自然对于涉及强国的争端态度模糊。九一八事变后的中日争端牵涉到国联的常任理事国日本,但因为这一争端系国联成立以来最大的国际争端,各方高度关注,国联如果不出面,很可能意味着它在道义上破产。当中国代表向国联提交中日冲突的照会时,国联的反应并非十分激烈,甚至一度屈从日本的压力,赞成日方由中日直接交涉的主张。只是由于中国代表的据理力争,加上舆论的压力,同时为了表达对日本欲独占中国东北的不满,国联才于1931年9月30日及10月24日分别通过要求日军撤退的决议。日本不惟不履行,反而以不断扩大侵略作为回应。此后国联对于中日争端实行采取拖延与敷衍的态度。国联调查团从1931年12月10日国联通过决议组织遣派到1932年10月2日李顿报告书公布,前后历时竟达十月之久,而报告书既认定日本侵略东北并非自卫,又不允恢复九一八事变前的状态,却提出近似国际共管的建议,实际上变相地承认了日本在东北的优势地位,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与利益。报告书公布后,国联中的许多中小国家认为既然报告书已认定日军行动系侵略行为,那么根据国联盟约的有关条款,力主对日实施经济制裁,对此大国又根本不予理睬。(46)吴秀峰:《国际联盟处理“九一八”事变前后经过》,载《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7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页。国联的种种行径表明,它无意于真正为中国主持公道。它通过要求日军撤退的决议及认定日军进军东北并非自卫等,无非欲借此向日本施压,反对其独霸远东,从根本上说,仍属强国之间利益争夺使然。
其次,国联完全没有替中国主张公道的能力。国联成立之时,本身就是一个极为松散的国际组织,它所依赖的国联盟约并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效力。它之所以还能处理部分较小的国际争端,无非利用大国的影响力来处理事务,一旦遇上中日冲突这样的棘手争端,国联的表现就极为软弱无能。冯玉祥1932年3月10日日记称国联为“纸老虎”(47)《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593页。,所喻至当。1932年,颜惠庆取代施肇基成为中国驻国联首席代表,他在日记中也特别感慨“国联行政院非常软弱”。(48)上海市档案馆译:《颜惠庆日记》第2册,1932年2月9日,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632页。事实正是如此,1931年10月24日,国联通过决议,要求日军在11月16日前撤回9月18日前所驻地点,但主持国联事务的法国外长白里安等人又称根据国联盟约第十一条规定,理事会一切决议应得理事国家包括当事国在内一致通过,才能发生效力。这不过是强国实用主义导致的对国际公法的曲解。日本即借口日方投了反对票,声称理事会决议未得一致同意,不能算通过,日本将不受决议限制,终使撤兵决议成为一纸空文。不久日方为了拖延中日事件的解决,为在中国东北扩大事态,成立伪满洲国,造成既成事实创造条件,忽然一改先前坚决反对国联派遣调查团来华的态度,表示同意国联调查团之行。国联舍此亦无其它办法,不得不借此敷衍世界视听。后来国联报告书公布,日方因其未能完全满足其欲望,强行退出国联,终使英、法等国企图利用国联来约束日本的希望完全落空。其实根据国联盟约第十六条,国联各成员对于被认定为侵略的一方可以对其实施经济制裁,胡适等人曾敦促西方大国“能履行其所应尽之义务,立取有效行动以维世界和平”(49)李学通编:《翁文灏往来函电集》,团结出版社2020年版,第239页。,但英国等国正陷入席卷全球的严重经济危机之中,法国面临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的威胁,自顾不暇,它们不愿冒着直接卷入中日冲突或招致日本报复的风险而对日实施制裁(5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1页。,本质上因为惧怕日本,不敢采取有力行动,终使国联对中国的支持始终是口头式的、会议式的、纸面上的,没有任何实际效果。
由上可见,国联对于为中国主持公道既无心也无力。随着国联对日软弱日渐昭著,国人对国民政府完全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不断发出质疑声音,李顿报告书公布后,质疑声浪达到了高潮,如李宗仁曾在广州发表谈话,指出“中国无论如何都不能依赖国联。事实上,国联对于东省事件,有无解决的诚意,固然成问题,恐怕有无解决的力量也还成问题呢。……事至今日,国人应该彻底觉悟,国联无论如何是依赖不得的!要收复失地,只有靠中国自己的力量。”(51)《附录一:李总司令对国际调查团报告书意见》,载《暴日侵占东北痛史》,中国国民党党务整理委员会1932年印行。李宗仁的这一看法呼应了国内主流民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52)参见胡政之:《盲人瞎马之外交》,《外交月报》第1卷第3期,1932年9月版;《是非明矣,国民更须努力》,《大公报》(天津)1932年10月5日。颜惠庆在晚年曾对此反省,颇有感慨,他指出:中国在九一八事变后对国联寄予重望,最终“陷于一种复杂错综,似有所为,实无作为之机构中,无以自拔。失望愤恼之余,认为已被强国所卖,从而感觉国联也者,无非强国的方便工具,徒供其达到自私自利的企图而已。”(53)《颜惠庆自传》,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77页。颜惠庆作为中国驻国联的首席代表,他的反省应该是极为深刻的。从其回忆中可以看到,他晚年对国联本质的认识与1931年9月冯玉祥两次通电对国联性质的判断几乎完全一致,坐实了冯玉祥的先见之明。
当然,冯玉祥反对依赖国联的主张也存在不足。他既然判定国联系帝国主义列强宰制弱小民族的强盗组织,当然对中国在国联开展活动持否定态度。尽管他也认为“各帝国主义势力在远东之冲突已到了白热的程度”,但最终仍会调和妥协,走上分赃一途。(54)《冯玉祥选集》上卷,第118、106页。他夸大了列强妥协分赃的一面,却忽略了列强之间也有可能因分赃不匀而发生你死我活的争斗的另一面。1932年12月,他在《谈谈中俄复交》一文中甚至提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55)《冯玉祥选集》上卷,第118、106页。这与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形势不相契合。实际上,国联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其内部操纵事务的英、法等强国并不甘心日本独霸远东,与日本矛盾重重,国联中的大部分成员系中小弱国,它们对中国均抱同情态度。中国正可以利用国联这个平台,揭露日本侵华真相,争取更多支持,扩大国际宣传,以便在中日舆论战中争得先机,占据主动。如果将国联这一平台拱手让予日本,日本更加可以混淆视听,肆意妄为,给中国带来更大恶果。国民政府将中日争端诉诸国联,本身并没有错。它错就错在未能谋求自救之道,而将希望完全寄托在国联身上。冯玉祥反对完全依赖国联,当然是正确之举,但他不提倡中国在国联开展活动,似有矫枉过正之嫌。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汲取了九一八事变后的惨痛教训,在向国联申诉的同时奋起抗战,从而迈上了历史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