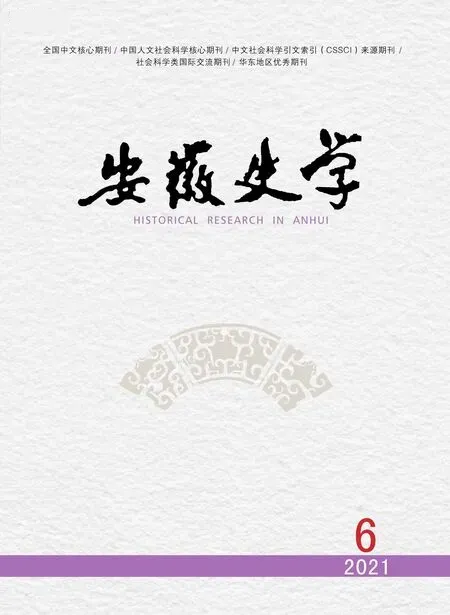清代一个山西商镇的民间灾赈史
——以灵石县静升村为例
白 豆 郝 平
(1.太原师范学院 历史系,山西 晋中 030619;2.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清中期以后,以民间力量为主体的地方赈济日益兴盛,并在地方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学术界对江南社区赈济的研究卓有成效(1)参见吴滔:《清代嘉定宝山地区的乡镇赈济与社区发展模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清代江南社区赈济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清至民初嘉定宝山地区分厂传统之转变——从赈济饥荒到乡镇自治》,《清史研究》2004年第2期;《宗族与义仓:清代宜兴荆溪社区赈济实态》,《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而对华北地区的研究则较为少见。基于小农经济之上的华北农村社会是否有能力施行较大规模的民间地方赈济活动(2)此处探讨的民间地方灾赈不同于近代义赈的“民捐民办”,而主要是指处于清代官府统一领导之下,作为官赈体系附庸的“民捐民办”的赈灾活动。,一直是值得学界关注的问题。因此在探究华北社会应对灾害时,学者们往往将士绅或宗族作为研究重点,却鲜有以村社为单位进行研究的。而将村社赈济与基层社会构成、宗族和地方仓储等之间的诸多联系进行综合考察,将有助于深入了解华北农村社会的诸多复杂关系和多重历史面貌。本文选取山西灵石县静升村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该村自清代乾隆到光绪年间一直存在着较大规模、连续不间断的民间赈济活动,甚至在“丁戊奇荒”期间也没有间断,可以作为深入了解民间赈济与地方社会复杂关系的典型样本。
一、清代静升村的受灾情况与灾赈背景
(一)静升村的基本概况
静升村,古名旌善,位于山西省灵石县东北15公里。清代的灵石县原隶平阳府,乾隆三十六年改属霍州直隶州。“地瘠山多,土田不足养土著之民,不得不仰给邻村,以故逐末者众”(3)《静升村辛酉赈饥碑记》,杨洪主编:《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灵石县卷》,三晋出版社2010年版,第479页。,促进了静升村商业的发展。嘉庆时,新设静升村、苏溪村等五个集场,并重新确定了集期:“城市,期三、六、九;小水镇,期四、五、八;苏溪村,期一、三、五、七、九;静升村,期三、六、七、九”(4)嘉庆《灵石县志》卷2《建置·市集》,清嘉庆二十二年刻本。,可见,静升村的商业经济已达到较大规模。普通集市后来又逐渐发展成为一条横贯东西的五里商业长街(5)商业长街东至杨树沟口,西至富足沟口。,主要经营当铺、京货、饭庄、酒厂、织布、盐店、金银加工和货铺等,鼎盛时期甚至扩展到“九沟八堡十八巷”。
从家族构成来看,该村主要有王氏、祁氏、阎氏(6)根据碑刻记载的情况推测,阎和闫在静升村应是同一姓氏,故而此处阎亦作“闫”。、李氏、孙氏、曹氏、田氏、郑氏和程氏等多个家族,尤以王氏家族的势力最大,在静升村享有极强的话语权。实际上,从处理地方公共事务的经理纠首构成,也可以侧面反映各家族在静升村的社会势力和地位。如清嘉庆十五年《静升村蓄水池碑记》中提到,参与该项事务的经理纠首中,王氏成员所占的比重最多,占总数的一半,祁姓、曹姓、程姓和郑姓家族成员则各占一个。(7)景茂礼、刘秋根编:《灵石碑刻全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11页。
从村社日常管理情况来看,静升村分会而治,以文庙为界,依据地理位置分为东、西两社。两社在文庙办理共同公务,西社事务在后土庙办理,东社事务则在八蜡庙中办理。除东、西社分管各社事务以外,合社处理村内公共事务的情况亦不少见,尤其是在水利建设和灾害赈济等重大事项上。
(二)静升村的受灾情况
将各方志中有关清代灵石县的灾情记录(8)主要包括康熙《灵石县志》、嘉庆《灵石县志》、光绪《续修灵石县志》、民国《灵石县志》以及道光《直隶霍州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平阳府志》、康熙《山西通志》、雍正《山西通志》和光绪《山西通志》中对灵石灾情的记录。进行比对汇总,发现该地发生的灾害主要有顺治四年蝗灾、六年蝗灾,康熙三十年至三十一年旱蝗灾、五十九年至六十年旱灾,道光十二年旱灾、二十七年水灾,咸丰十一年饥荒,同治二年水灾、十年水灾,光绪元年至四年旱荒、五年鼠患和狼灾等。可能囿于地方志的版本及内容选取等方面的限制,雍正、乾隆、嘉庆以及光绪后期的灾害并未在地方志中有所体现。
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清代灵石县的灾况,笔者又查阅了《清实录》《清会典》以及相关碑刻史料中的灾害记录。与方志记录有些许不同的是,《清实录》和《清会典》的灾情记录主要集中在乾隆朝及以后,部分弥补了方志的缺失。除方志中提及的灾害以外,还有乾隆二十四年旱灾,嘉庆九年至十一年旱灾,嘉庆二十二年旱灾,道光十五年灾(9)根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84《户部·蠲恤·缓征三》中的记录:“道光十五年,缓征山西省被灾之右玉、灵邱……灵石二十三厅州县积欠米石。”《续修四库全书》第80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33页。其中并未具体提及具体灾种及灾情,故此处也仅作论灾处理,不另作灾种的区分,以下如是。、十九年灾、二十五年灾,咸丰元年灾,同治六年灾,光绪八年灾、十二年灾和二十六年旱灾等。碑刻资料中的灾害记录也相对集中在乾隆朝及以后(10)除其中一条记录了康熙六十年的饥荒以外,其余都集中在乾隆朝及以后。,灾情记录更加详实,如乾隆二十三年水灾、二十五年饥荒、二十六年水灾、四十三年霜冻、四十四年旱灾、五十七年水灾,嘉庆六年水灾、十年至十一年水灾、二十二年水灾,道光十年旱灾、十二年荒歉、十三年旱灾,咸丰九年岁歉,光绪十六年水灾、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旱灾和三十年旱灾等。
至此,清代灵石县的灾况才大体明晰。经对比分析发现,灵石县连年灾害和数灾并发的现象较为多见。从灾情描述和赈灾情况来看,对灵石县影响较大的灾害主要是旱灾和水灾,其他灾害如蝗灾和霜冻等也偶有发生。具体到静升村来看,旱灾及由此引发的饥荒影响最大,其他灾害如霜冻等也有一定影响。至于灵石县水灾则主要是城市水灾,对静升村的影响并不大。
(三)静升村的灾赈背景
自清中期以来,静升村内长久地维持着民间赈济的传统。从历史背景来看,国家荒政体系的逐渐衰落,客观上促进了民间赈济的兴起和发展。静升村雄厚的经济实力、商业化的公项存储、日臻完备的赈灾机制和强大的宗族实力等都为开展民间赈济奠定了基础。
第一,国家荒政体系逐渐衰落,官赈力量逐渐衰微。对比康熙五十九年至六十年与嘉庆九年至十一年灵石旱灾的官赈情况,前者的赈济方式主要是钱、粮赈济和蠲免等,后者则主要是蠲免和缓征等。从侧面反映了官赈力度在逐渐变小,为民间赈济力量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契机。
第二,静升村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开展民间赈济奠定了物质基础。静升村东、西两社的经济实力都不容小觑,如西社所属赈济堂的经济实力就远超其他各会,晚清时期仍具有较为雄厚的实力。光绪三年,赈济堂曾花费地价银2992两广泛开展置地行动,前后共置水地122余亩。(11)《静升村赈济堂地亩碑记》,景茂礼、刘秋根编:《灵石碑刻全集》,第1419—1422页。六年,赈济堂为文庙捐银500两,占据捐赠总额的1/2。(12)《静升村各会协拨文庙银两碑记》,景茂礼、刘秋根编:《灵石碑刻全集》,第1440页。十八年,赈济堂为重建魁星楼“拨来银,合钱七百三十八千零二十文”。(13)《魁星楼重建碑记》,杨洪主编:《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灵石县卷》,第552—553页。碑文所见,赈济堂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公积银,并将之用于祭祀、修葺神庙以及修建公共设施和赈灾等活动。
第三,借商生息作为累增公项的重要手段之一,客观上加速了赈济资本的扩充。公项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除村社公项以外,各宗族内部和东、西社各分会内部等都各自存有公项。村社公项亦作了进一步细分,如文庙、蓄水池以及义仓等也各自存有公项。这些公项平常自用,如遇村内重大公共事务用项不足的情况,其他公项(14)这其中主要指村社公项和东、西社各分会公项,并不包括各宗祠公项。可作适当调拨挪用,如文庙就曾两次接受其他会的拨银。(15)《静升村各会协拨文庙银两碑记》,景茂礼、刘秋根编:《灵石碑刻全集》,第1440页。关于救灾公积银的最早来源已不可考,官府在灾荒期间发放的赈银以及村内绅商的捐赠应是其资金积累的重要来源。就资金管理而言,主要采取借商生息的方式。当然,利用公项借商生息扩充赈济资金也并非静升村独有,如道光十二年,灵石县重修护城堤以后,县令顾夔对余银的处置办法即是“发典生息,以备岁修之需”。(16)《灵石县重修护城堤碑记》,景茂礼、刘秋根编:《灵石碑刻全集》,第1000—1002页。
第四,静升村在赈灾机制和机构设置等方面日臻完备。村内文庙中设有义仓,留存的赈济碑石详细记录了每次赈济的各项收支及余存,多次提到大宗粮食的粜籴,由此可推断静升村义仓在历次赈济中都发挥了较为积极的作用。(17)主要包括《静升村戊辰年赈饥碑记》《静升村放赈碑记》《静升村辛酉赈饥碑记》和《静升村光绪己卯赈济碑记》等,收入景茂礼、刘秋根编:《灵石碑刻全集》,第1378—1379、1021、1314、1435—1436页。从现有赈济碑的分布地点来看,灾赈事务的办理地点主要设在文庙。赈灾的专项公积银平常应是由义仓经理(18)其他村社公项赈济金多由义仓直接经营,故推测静升村应该也不例外。,到灾时再临时组建救灾机构处理赈务。
二、王氏家族的灾赈实践
王氏家族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均居静升村之首,在宗族建设和参与地方事务上也用力最勤。王氏分为“东王氏”“西王氏”“中王氏”三支,尤以“西王氏”的实力最为雄厚。到清中期时,王家经营规模和实力达到顶峰,经营的商号主要有聚仙楼、天泰号、源盛公、裕源当和延寿堂等。在此期间,王氏家族逐步通过捐纳、荫袭和科举等方式步入官场。具体到灾赈事宜上,除主要的族内赈济以外,王氏家族成员亦热衷于乡邻赈济。
(一)宗族灾赈的资金来源
据统计,从康熙五年到光绪五年,西王氏共积累了族田353余亩,族产有园子地三块,花园一座,铺房、铺院、号子铺等九处。(19)据《西王户建祠堂地基、修坟茔道路并坟茔地亩四至粮石碣》和《西王户房屋地亩并金、木派人丁,五派贴帮户头水旱地四至粮石碣》统计而成,碑刻收入王儒杰、王金钉、王铁喜编著:《王氏族谱乾隆庚戌版续编本》,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610—616页。此外,王氏自六世起分为金木水火土五派,派有支系,各派各支也自有田产。族产主要用于内部的宗族活动,如编纂和修订族谱,祭祖和修建祠堂以及赈济族人等。
作为商业家族,王氏在管理族产上尤为擅长借商生息。早在乾隆十九年,王梦鹏在捐修静升村至马和村两村傍道之后,又“念日久难免损坏,另出银二十两,存放生息,以为每年修补之费”(20)《静升村王公梦鹏捐修两村傍道碑记》,景茂礼、刘秋根编:《灵石碑刻全集》,第418页。,开启了王氏家族借商生息处理公共事务的先例。颇为有趣的是,早期族人捐赠的备赈金成为宗祠内部生息资金的主要来源。乾隆二十二年碑记载:“吾家六翮公为是乡直谅多闻之士,平昔以尊祖合族为己任,弥留之际嘱其子中辉,以三百金贮宗祠。且曰:‘此时,吾族人固无需此,然先时生息,使有余资,倘遇歉岁,以息济之。而毋耗其本,则族人之贫乏者,可以永赖。’”(21)《静升村王氏祠堂捐助义资碑记》,景茂礼、刘秋根编:《灵石碑刻全集》,第438页。六翮公即是王梦鹏,设立的备赈金不久即用于乾隆二十四年大旱的宗族赈济中。
至迟到嘉庆年间,王氏宗族就已经开始有计划地存储公积银了,如《静升村拱极堡积银碑记》就记载:“拱极堡建自乾隆十八年,考之账簿,自嘉庆年间始存公积银钱,后又得树价若干。居是堡者,权其子母环生不已,以为异日修补之资。”(22)《静升村拱极堡积银碑记》,景茂礼、刘秋根编:《灵石碑刻全集》,第1211页。碑记所见,静升村王氏家族宗族公积银的积累主要来源于置产、收息等,其中收“子母生”利息、收房息、收铺息等占很大比例,资金充足时,也会注意购买田产、铺房等,积累产业,增加收入来源,如置村东房一处、置田家沟旧宅、置孙家巷铺房等。(23)《静升村创建兵宪祠堂碑记》,景茂礼、刘秋根编:《灵石碑刻全集》,第1103页。收房息、铺息和子母相生等都是商业投资行为,也为其开展宗族赈济及乡人赈济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至于宗族会将多大比例的族产用于灾时赈济,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定论。不过从《静升镇集广村何户家祠救急碑记》的记载来看,灾荒较为严重时期部分家族将大量族产用于赈灾的情况也是存在的。(24)碑文主要记录了光绪三年何氏宗族将大量族产用于赈济族人的事情。按其中的花费和余银推算,族产大致有880两。如果以最初的大口200、小口77,每日分别给钱12文和6文计算,赈济两月最少应费钱299160文,大约要占到族产总数的1/3以上,可见赈济力度之大。不过碑文记录的最后花费数额低于前期预算,个中原因受限于史料不再深究。《静升镇集广村何户家祠救急碑记》,景茂礼、刘秋根编:《灵石碑刻全集》,第1431页。
(二)王氏家族灾赈的实践路径
根据碑刻记录,自乾隆朝以来,静升村发生的较大灾害几乎每次都伴有民间自救活动,早期救灾的主体主要是王氏宗族,大致到嘉庆年间,逐渐转变为以村社为主。
乾隆二十四年,朝廷下令抚恤山西灵石等56州县本年被旱、被雹、被霜贫民,并缓征新旧额赋。(25)《清高宗实录》卷598,乾隆二十四年十月上,《清实录》第1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79—680页。但从实际效果来看,灵石县的灾情依旧不容乐观,据《赈项存留羡余碑记》:“二十四年己卯大旱,灵邑之人散亡甚伙,族人等计公所捐之资及数年之息,共得三百七十余金,即为买粮分给族之饥馑待毙者,藉是得以安然无恙于大荒之岁者殆三百余人。”(26)《赈项存留羡余碑记》,景茂礼、刘秋根编:《灵石碑刻全集》,第455页。族人王翮公之子王中辉捐资的300两经过经营生息,累计达到370余两,成为此次赈济族人的主要资金。不过,这并不是一次单一的族内赈济活动,王中辉又捐300两用于赈济灾荒中的本镇乡民。(27)《静升村王氏创修守茔房院碑记》,景茂礼、刘秋根编:《灵石碑刻全集》,第580页。王氏宗族成员王如玑也筹款对族外乡人进行赈济:“(乾隆)己卯岁灵邑大旱,公为倡议捐赈数至三千金,乡之饶裕相效为之,所全活者无算,公不自少为功。里人议之,至今多颂公德于不衰。”(28)《静升村王如玑暨陈氏合葬墓志铭》,景茂礼、刘秋根编:《灵石碑刻全集》,第462—463页。
乾隆四十三年八月,静升村“忽降严霜,秋禾尽杀,赤地千里焉。而静升村居民不止千室,乏食者十之七八。”从灾情描述来看,这次霜冻对静升村造成的影响很大。据目前所能搜集到的资料判断,这次灾害涉及的范围不是太大。在缺乏国家赈济的情况下,本村绅士、候选州同王中堂输银千两,并同监生闫纯玺、王荫等悉心筹划,“以赈灾救荒,岁价平粜,邻村之被泽无算,本乡之食德甚多”。(29)《静升村乾隆己亥赈饥碑记》,景茂礼、刘秋根编:《灵石碑刻全集》,第578页。至次年春,赈济活动才基本结束。这次参与赈济的王氏家族成员,除王中堂以外,王中辉亦“慨然出金四百无难色”。(30)《王氏创修守茔房院碑记》,王儒杰、王金钉、王铁喜编著:《王氏族谱乾隆庚戌版续编本》,第588—589页。霜冻之后,旱灾接踵而至,“乾隆己亥(四十四年)大旱,灵石为甚,公(王中辉)复出己资,偕同志者移粟相给,俾不匮乏,计前后不下千余金,慨然倾囊,无一毫顾惜意,远近称巨人长者。”(31)《静升村王公耀环墓志铭》,景茂礼、刘秋根编:《灵石碑刻全集》,第594页。可见,仅王中辉就曾先后两次出巨资对乡人进行赈济。
以上可见,王中辉、王如玑和王中堂等人在乾隆时期静升村的灾赈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三人都是王氏家族成员,其中王中辉,字耀环,十六世,候选州同、乡饮大宾;王中堂,字升庵,十六世,候选州同、乡饮大宾;王如玑,字魁三,十七世,曾历任内府光禄寺掌醢署署正、刑部陕西司郎中等官职。有学者曾指出:“宗族性救济作为一种资源能否成功地发挥作用,取决于其持久性和强度,而后者反过来又建立在地缘和血缘结合的基础之上。聚族而居能够极大地加强宗族内部联系,同时也弥补了其与建立在传统地缘关系基础上的社区赈济之间的裂痕。”(32)吴滔:《清代江南社区赈济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从赈济群体来看,王氏宗族并不排斥赈济宗族以外的乡人,赈济范围则主要以乡里为单位,甚至还有赈济邻村的现象。因此,并不能简单的仅将其定义为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族内救济。实际上,早在乾隆四十年,族人王中堂就已经以监工纠首的身份参与到地方事务中了。(33)《静升村重修马棚碑记》,景茂礼、刘秋根编:《灵石碑刻全集》,第555页。到乾隆五十年,他已经成为地方经理人之一。(34)《静升村下南堡婴冢碑记》,景茂礼、刘秋根编:《灵石碑刻全集》,第619页。这反映了王氏宗族成员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寻求地方社会认同并控制地方社会的诉求。
大约到嘉庆朝以后,我们已经很难再看到王氏宗族成员以个人名义进行较大规模的捐赈了,更多的宗族成员加入到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村社赈济中,并在其中担任重要角色。这既与宗族参与地方事务的诉求有关,也与清代后期王氏家族的逐渐没落有关。动荡的社会局势严重地影响了王氏家族省外的生意,如到太平天国运动时,“设在南方的店铺被砸、被抢,纷纷倒闭……为逃生活命,在外经商者只得弃业返乡”。(35)侯廷亮主编:《王家大院志》,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页。商号运营的艰难在碑刻中也显现出来,“蓄水池拨银捌百两,藉商生息,以给丁祭圣诞之费,历有年矣。迩来商号亏折,前项荡然,费既不支,祀典几至缺如。”(36)《静升村各会协拨文庙银两碑记》,景茂礼、刘秋根编:《灵石碑刻全集》,第1440页。从清后期王氏家族的商业发展形势来看,已然再难独承较大规模的赈济活动。
三、清中后期村社赈济的具体实践
现存记录静升村村社赈济的碑记主要有:道光十三年的《静升村放赈碑记》、咸丰十一年的《静升村辛酉赈饥碑记》、同治七年的《静升村戊辰年赈饥碑记》和光绪五年的《静升村光绪己卯赈济碑记》。但村社统一开展赈济活动的时间远早于道光朝,大致在乾隆时期,静升村就已经开设有专门的灾赈公项了。村社赈济开展的时间,均出现在连年灾荒时期。在救灾事宜上,尚未发现东、西社有较为明显的分赈行为。
(一)嘉道时期的村社赈济
嘉庆九年至十一年,灵石大旱并引发饥荒,粮价一度高至斗米千钱。碑刻资料显示,静升村在嘉庆十一年有放赈行为。(37)《静升村放赈碑记》,杨洪主编:《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灵石县卷》,第372页。但因史料缺乏,我们已经无法得知相关赈济的具体内容。若将其与道光十三年的灾赈联系起来,或许可以有一些新的认识。
道光十二年灵石大旱,秋收更歉,斗米卖钱一千五百文。(38)光绪《续修灵石县志》卷2《杂录·祥异》,清末抄本。次年,仍大旱。除县令顾夔“捐廉平粜赈饥”(39)《灵石知县顾君墓志铭》,景茂礼、刘秋根编:《灵石碑刻全集》,第1232页。以外,并无更多的记录表明官方进行过其他赈济。静升村则开展了较大规模的民间赈济活动,费银2575余两,这是继嘉庆十一年之后的又一次集体赈济。这次放赈设有总理银钱纠首、买粮纠首、收粮纠首、放账纠首等,其中总理纠首3人中王姓占2人,买粮纠首16人中王姓占11人,收粮纠首11人中王姓占7人,比重远超其他姓氏。可见王氏家族在处理地方事务中占有重要地位。
以上资料可见:一是嘉庆十一年的地方灾赈已经初具规模,并具备一定规范。道光十三年赈济活动中,虽然王氏宗族成员占据的比重很大,但有其他家族成员的参与,可看作是以村社为单位的集体赈济。由此推测,嘉庆十一年的赈济也已经是以村社为单位的集体赈济了。此外,嘉庆十一年放赈后,仍能净存银969余两,足见地方灾赈的规模与能力。二是静升村有储存赈银的传统并存在商业投资行为。存储的赈灾银数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嘉庆十一年到道光十三年,本利银已经是最初存银的七倍之多。而且除去买米等所花的费用,剩余的银两仍被存贮并继续投资生息,以便在下次赈灾中发挥作用。
(二)咸丰时期的村社赈济
灵石县:“咸丰十一年饥,居民剥树皮掘草根以食。”(40)光绪《续修灵石县志》卷2《杂录·祥异》。饥荒之下,静升村因商多失业,人乏术以资生,加以乡境欠收,粮价踊贵,贫民力食尤艰,甚者至子散妇离,道馑不免。(41)《静升村辛酉赈饥碑记》,杨洪主编:《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灵石县卷》,第479—480页。在这样的灾情下,静升村再次动用所存公积银进行了赈济活动。
《静升村辛酉赈饥碑记》详细地记录了从道光十三年到咸丰十一年间,公积赈银的所有来源和流向,也证实了村内专门设有赈灾公项。赈济人数多达913户、大小人等2850口,表明静升村对地方赈灾的重视程度,可以判定这是一次遍及村内全体成员的救灾活动。
该赈济活动共有26名总理纠首,仍以王姓居多,共计18人,主要由官员、生员和监生等官绅和士绅群体构成。“宗族内部士绅阶层的存在是国家与宗族并存的机制”(42)吴滔:《宗族与义仓:清代宜兴荆溪社区赈济实态》,《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相较于道光十三年的赈济而言,这是一个较为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静升村内以王氏家族为代表的宗族内部有更多的士绅力量崛起,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在地方赈济事务中拥有重要的管理职能。
(三)同治时期的村社赈济
同治朝被记录的灾害主要有二年水灾、六年灾和十年水灾,并未发现有关同治七年的灾害记载。因此,同治七年立石的《静升村戊辰年赈饥碑记》极有可能是对六年灾荒赈济情况的补录。这次灾害在《灵石县志》中并没有记载,在《清会典》中发现了一条关于同治六年赈济灵石的史料:“同治六年,又豁免山西省被灾之临汾……灵石……二十六厅州县旧欠仓谷。”(43)《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87《户部·蠲恤·缓征六》,《续修四库全书》第802册,第566页。从官方赈济的情况来看,灵石县被灾至少在五分以上,这也在村社赈济的力度上得到了侧面证实。这次赈济共出钱1467271文,米117余石、高粱60石,并净存钱320815文,归入旧账。(44)《静升村戊辰年赈饥碑记》,杨洪主编:《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灵石县卷》,第506—507页。就赈济方式而言,基本还是以实施粮赈为主。从粮食采买的种类来看,之前几次基本都是买米,这次还新加入了采买高粱。
这次赈济活动的管理更为规范和合理,添设了香老、经理出入银钱粮账纠首、经理验票印账收价纠首、经理照票给粮纠首、稽查户口纠首等。从人员构成来看,仍然是王姓成员占较大比重,其中有不少成员如王德生、王臣恭、王丽珍、王思谌、王开棣、王炳辰、王兆丰、张锦华、祁瑨玉、阎叙九、郑容镜、孙道源、祁从智、郑岱云和张慧中等都曾参与过道光十三年的赈济活动。部分成员的社会地位较前也有了更进一步的提升,如王德生的头衔从营千总上升至布政司。值得注意的是,他姓成员数量也在增加,大致以祁姓、郑姓、李姓、闫姓和张姓士绅居多。
(四)光绪时期的村社赈济
光绪朝的村社赈济主要是针对“丁戊奇荒”开展的。据县志载:光绪三年“旱魃为虐……剥树皮而作食,瘦似黑面夜叉,挖坩泥以解饥,肿如大肚弥佛……甚而至于父食其子,夫食其妻,惨矣哉!”(45)民国《灵石县志》卷12《灾异》,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静升村分别于光绪三年、四年开展了多次赈济,说明该村在丁戊奇荒期间的灾况十分严峻。
不过,光绪三年十二月,曾国荃在奏折中将灵石县静升等十八村定为成灾六分(4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3册,光绪朝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75页。,静升村成为灵石县受灾较轻的地区,或许得益于村内自行开展的村社赈济活动。此次赈济中,共费银7877余两、钱6986390文。(47)杨洪主编:《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灵石县卷》,第532—533页。主要花销仍是用于买粮,除大小米和高粱外,还新增了麦子、大麦和黑豆等。赈济方式除赈粮之外,还新增赈钱。
管理机构主要包括二、三、四年香纠、制办买粮人、稽查户口纠首等。办赈人员构成有两个较为明显的变化:一是外姓成员渐次增多,王姓比重有较大幅度下降;二是成员的社会身份有明显降低,具有官员、生员和监生等头衔的成员十分少见。这也间接表明王氏家族在光绪年间已经逐渐没落。
赈灾次数和赈灾费用都说明此次赈灾力度远超之前,不仅是“丁戊奇荒”期间静升村受灾严重的反映,也是其赈灾能力的表现。虽然赈济之后仍净存钱1142902文,但此后因商号不断亏损,导致借商生息的赈银也受到严重影响,村社赈济开始逐渐衰落,并未再开展过较大规模的赈济活动。如光绪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灵石发生严重旱灾,但没有发现静升村再开展如前几次规模的赈济活动。至此,从乾隆年间就开始的大规模赈济活动持续到“丁戊奇荒”以后便基本结束。
余 论
综合来看,旱灾及其引发的饥荒是清代静升村遭遇的主要灾害,相应的赈灾主力自清中期起由国家明显向地方下沉。纵观清代静升村的民间赈灾史,强大的宗族势力及商业化的公项管理是其长久维持赈济传统的重要因素。不同于传统农耕社会的保守,以商业著称的静升村将民间赈济资本与商业经营巧妙地结合起来,从而为村内自乾隆至光绪年间开展较大规模的、连续不间断的民间赈济活动提供了有力支撑。其间,救灾主体由宗族向村社的过渡,充分体现了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相互结合及宗族内部士绅对地方社会的权力渗透。
静升村的个案研究表明,清代华北地方社会具备持续开展较大规模赈济活动的能力。与江南社区赈济研究相比,华北地区村社赈济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从社会史的角度加强民间赈济的在地化研究,应是可行的路径,加强民间文献的发掘和长时段研究视角的应用,将有助于呈现华北村社应对灾害的具体反应及其地方性内在结构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