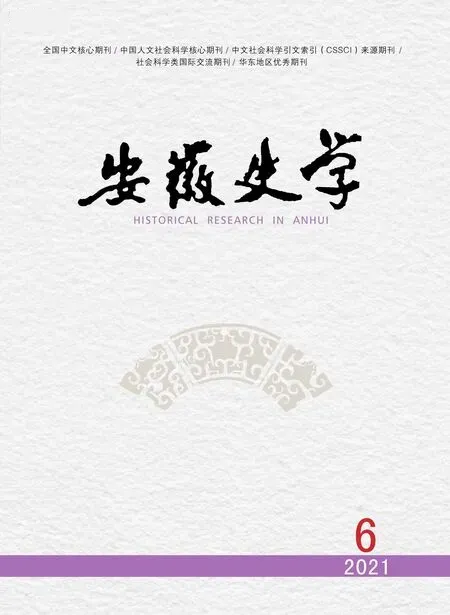租界、治外法权与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国际性
——以《中国论坛》与“伊罗生事件”为中心
谢力哲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引 言
“明目张胆的招摇于国际都市的上海,标明为共党活动者。有之,其伊罗生乎!”(1)扬声:《伊罗生及其中国论坛》,《社会新闻》第6卷第21期,1934年3月3日。这是一份国民党刊物在盘点“中国境内活动的外国共产党徒”时对美国记者伊罗生(Harold R.Isaacs,1910—1986)的耸动性评价,后者是1932年1月创办于上海的英文综合性期刊《中国论坛》(ChinaForum,以下简称《论坛》)的主编。前者还指称这份刊物“可说已成为共党的标准刊物……比诸共党文总下之各种出版物,当然能超出一筹,即与红旗周刊相比较,亦无多让。”其用意虽在于攻击伊罗生及其所从事的共产主义事业,却能从侧面反映出具有鲜明“党刊”色彩的《论坛》在当时文化界的影响力。在沪发行的美刊《大陆报》和《密勒氏评论报》就分别称该刊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当局,以大量篇幅报道中国的学生运动,具有明显的共产主义倾向;(2)“First Edition of China Forum Will Appear Here Today”,The China Press,Jan.13,1932,p.8;“Men and Events”,The China Weekly Review,Feb.18,1933,p.492.英刊《北华捷报与最高法庭与领事公报》亦评此刊旨在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同盟和国民党,且“对学生运动和共产党人表示同情”。(3)“‘China Forum’”,The North -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Jan.19,1932,p.73.足见此刊突出的政治倾向得到了彼时各方的公认。
实际上,早在酝酿创办《论坛》之时,伊罗生就明确希望把它办成中共正式的舆论阵地,公开宣传和报道中国与世界革命。他甚至提出:“与其因需要而受限制,把它搞得平淡无味,结果不值一读,还不如碰运气尽可能地干多久是多久。”(4)陈锦骍:《伊罗生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兼析同盟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虽然基于长远打算,这一过于冒险的主张并未被中共方面接受,但《论坛》仍以其耀眼的左翼面貌赢得了文化界的注目。即使伊氏曾出于自我保护的策略否认该刊的“赤色隶属关系”,声称其不为任何政党组织发声(5)“China Forum Denies Any Red Affiliation”,The China Press,Jul.30,1932,p.3.,但正如研究者指出的:“事实上,《中国论坛》的激进声调足以令新闻界的所有人都相信它是共产党的宣传机构。”(6)Jinxing Chen,“Harold R.Isaacs’ Trotskyist Turn in the China Forum Years”,Twentieth-Century China,Vol.24,No.1,p.36.其主要内容,一是大胆尖锐地揭露国民党政权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白色恐怖”情形;二是宣传和记录中国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三是宣扬中共的政治主张、报道各地革命活动;四是发表了“左联”作家茅盾、鲁迅、丁玲、柔石等人最早的英译小说,推动了中国左翼文化的国际传播。伊罗生还曾与茅盾、鲁迅共同商议编选了一部英译中国左翼短篇小说选集《草鞋脚》(StrawSandals)。
由于《论坛》对执政当局的触犯,国民党书报审查部门曾一度给它安上“侮辱党国,阐扬共党”的罪名(7)姚辛:《左联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218页。,然而这并未令它销声匿迹。尽管因种种制约致使发行周期不稳定,但是就在国统区心脏地带的上海,该刊仍坚持了整整两年(1932年1月至1934年1月,共40期),后期发行量一度达到3500份左右。其所以停刊也并非因为国民党的镇压,而是伊罗生倾向托洛茨基主义后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地下党产生的重大分歧所致。(8)关于《中国论坛》停刊原因的探讨,参见唐宝林:《伊罗生与〈中国论坛〉》,《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6期;Jinxing Chen,“Harold R.Isaacs’ Trotskyist Turn in the China Forum Years”,Twentieth-Century China,pp.31-66;陈锦骍:《伊罗生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兼析同盟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邵雍:《伊罗生、〈中国论坛〉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国近现代史专题》,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0—292页,等。《论坛》的存续无疑与它所处的租界地带和主编者的美国国籍分不开,这便涉及到1930年代租界的自由活动空间、外国公民的治外法权与开展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
学界既有的对于《论坛》和伊罗生的探讨,多聚焦于政治史、新闻史、伊罗生与鲁迅等人的交往、《草鞋脚》的编选等方面,较少将其置于文化史的脉络上进行考察。本文则通过探究《中国论坛》与“伊罗生事件”这样颇具典型意义的案例,以期深入考察租界、治外法权与左翼文化运动之间的实际联系,进而在“历史现场”中阐明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国际性”特质。
一、租界与《中国论坛》的运作
伊罗生1910年出生于纽约曼哈顿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期间曾在《纽约时报》见习,1930年底来沪,先后任《大美晚报》《大陆报》记者。次年夏季与另一位左翼记者格拉斯(Frank Glass,1901—1988,中文名李福仁,南非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后参与中国托派活动)结伴沿长江深入西南腹地游历,又与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50)结识。在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了解中国内陆社会的黑暗现状后,遂对中国革命抱有极大同情,并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深怀憎恶。1931年秋,他在史沫特莱的引荐下认识了宋庆龄等著名左翼人士,并与中共上海党组织和随后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生联系。1932年初,伊氏在格拉斯、史沫特莱与宋庆龄的提议下,与中共地下党合作创办了《中国论坛》——“一份表达接近中共观点的英文周刊”。(9)“Trotsky to Frank Glass”,Jan.29,1934,Trotsky Papers Cataloging Records (MS Russ 13.11),Houghton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Janice R.MacKinnon,Stephen R.MacKinnon,Agnes Smedley:The Life and Times of an American Radical,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p.156.刊物经费的实际资助者是共产国际远东局,伊罗生本人也拿出他担任法国哈瓦斯新闻社(HAVAS)翻译员的部分薪水作为补贴。(10)Peter Rand,China Hands: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5,p.102.
“四一二”政变后,中共的城市组织遭到国民党严酷镇压,尤其在1931年一连串的逮捕和破坏之后,众多领导干部已被转往苏区,至1933年夏,“中共城市工作的基础几乎已不复存在了”。(11)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71—272页。此时滞留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更是时刻处在严密监控之下,对于正艰难求生的地下党而言,亟需觅得一片公开的舆论阵地,《论坛》作为宣传喉舌的珍贵性便不言而喻。这份由美国人操办的英文刊物之所以能在如此危机四伏的环境中突破重围顺利问世,首先就是凭借着租界的有利条件。据茅盾回忆,史沫特莱找伊罗生办刊的目的,“是为的要他出面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取得办《中国论坛》的执照。”(12)茅盾:《关于编选〈草鞋脚〉的一点说明》,《茅盾全集》第2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9页。海外论者亦指出,因为国民党严厉的报刊审查制度,作为外围党刊的《论坛》只能以外国出版物为掩饰在公共租界(原英美租界)注册。伊罗生是该刊唯一登记并负全责的编辑,他还向美国驻沪总领馆申请注册一家名为“探照灯”(Searchlight)的出版公司,试图将出版方变为一家美籍公司,如此无疑又可多一层保护。(13)Jinxing Chen,“Harold R.Isaacs’ Trotskyist Turn in the China Forum Years”,Twentieth-Century China,p.36;Chen,Jinxing,Harold R.Isaacs in the China Scene,1930-1935:A Story of an American Idealist,Ph.D.dissertation,the University of Toledo,1997,pp.95-96.后因“伊罗生事件”的发生,“探照灯出版公司”未能成功注册。
不过,《论坛》初期的筹备与发行工作却是在法租界内进行的。1932年1月初,伊罗生租下了法租界传教士公寓内的一处办公室作为编辑部,租期三个月,并开始在租界各处公共场所张贴海报,宣传“《中国论坛》——报道目前在中国遭受忽视、扭曲和压制的新闻与观点!”(14)Peter Rand,China Hands,p.103.关于法租界的便利优势,如学者指出的:“上海各个区域中,在1916年袁世凯去世以后,又以法租界更为宽松。”较之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工商业不够发达,公董局财税收入较少,行政经费短缺,因而政府治理较差、治安漏洞也较多,“对于那些持不同政见者来说,可以利用的机会也就比较多。”(15)熊月之:《中共“一大”为什么选在上海法租界举行——一个城市社会史的考察》,《学术月刊》2011年第3期。在时人眼里,藏污纳垢的法租界是一个充斥着赌场、妓院、鸦片馆等“社会祸害”(social evil)的地带,而当局之所以放纵这些行业的存在,就是为了从中取利以弥补市政预算的亏空。(16)M.K.Han,“French Colonial Policy in China as Reflected in the Shanghai French Concession”,The China Weekly Review,Jan.23,1932,p.239.在文化监管方面,虽然法租界当局亦实行有报刊审查制度,但并非没有转圜余地。某些在法租界内创办的报刊虽受到华界当局如“攻击本党”“攻击上海市教育局”等指控,但租界方面却认为刊物本身并未威胁到公共秩序,也没有引发道德问题。(17)郑潇:《上海法租界报刊审查制度论述(1919—1943)》,马军、蒋杰主编:《上海法租界史研究》第1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132页。另据时论所称,法租界内的非法籍外国人中,尤以美国人占多数。(18)“French National Policy and the Local Concession”,The China Weekly Review,May.23,1931,p.407.如此看来,对于同样是美国人的伊罗生来说,这也便于他适应法租界的人际环境。万事开头难,法租界的上述因素,无疑都有利于《论坛》的顺利起步。
《论坛》准备工作就绪后不久,日军进攻淞沪的“一·二八”事变发生,租界当局紧急叫停了这份刊物,待到战事结束后的3月又重新面世,共在法租界内印行了三期。当然,租界远非自由天堂,更不意味着左翼活动可以随心所欲地展开。由于《论坛》的激进姿态,特别是它对国民党迫害政治犯和日本侵华等行径的大力揭露,使其在当局眼中颇为刺目,因此恢复发行后,各类现实困难随即纷至沓来:官方与非官方的检查、部分承印者受到恐吓、信件被拦截、多捆刊物被收缴、复印件在邮局不翼而飞,甚至还曾遭遇租界犯罪调查局(C.I.D.)的不速之客的窥探。种种阻扰致使这项工作不得不转入地下状态,直到最后一家愿意与之合作的印刷商也迫于压力而不再承印《论坛》,别无选择的伊罗生只好由中共地下党帮助,在自己的一间临近闸北、位于租界边上的小印刷作坊里亲手印发这份刊物,后来则干脆用起了家里的手动印刷机。1932年6月“伊罗生事件”发生后,传教士公寓方面也以不能继续租给“公开攻击我们所支持的一方的人”为由将他驱逐,他只得将编辑部搬到公共租界的四川路上。虽然频遭打压,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租界的特殊环境令其得以从国民党专制之网的缝隙中突围而出,此乃该刊维持发行的不可或缺的前提,亦正如伊罗生所说:“我在自由与限制以奇特的方式混合在一起的环境里开展活动。”(19)Harold R.Isaacs,Re-Encounters in China:Notes of a Journey in a Time Capsule,New York:M.E.Sharpe,Inc.,1985,pp.15,17,25-26;Peter Rand,China Hands,pp.114,118.
租界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不仅为伊氏本人,也为中共地下党人提供了一定的庇护。《论坛》是伊罗生与地下党密切合作的产物,前者有着美国公民的有利身份,便于公开出面主持刊物,但他毕竟是一位坚持以“报道事实”(Truth-telling)为本位的专业记者,既非正式党员、更非职业革命者。况且操持整个刊物的运作决不可能仅凭单打独斗,有关革命活动的大批秘密消息必须借助地下党方面的传递,同时也需专人协助其搜集和翻译中文资料。这种充满危险性又高度隐蔽的工作,正适合于在各方权力关系混杂的租界中维持。至于那些地下党员都有何人,因相关史料的稀缺尚无从一一考证。除当时任职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中共党员陈翰笙经常以“观察者”(Observer)的化名为《论坛》撰写有关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内幕报道之外(20)Harold R.Isaacs,Re-Encounters in China,p.118,p.26,p.18.,目前已知的大概只有1933年2月《论坛》改版为中英文双语后,由党组织派来的中文编辑袁殊(袁学易)。1935年袁殊被捕后,即有沪上英刊称其因主编《文艺新闻》闻名,随即加入中共,并被指派为《论坛》中文版面的主编。(21)“The Mystery Man’s Associate:Picturesque Career of Red Journalist in Shanghai”,The North -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Jul.10,1935,p.46.
伊罗生与中共之间的联络充满着神秘色彩,一名协助编印刊物的地下党人在他家中住了近一年,却始终未曾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足见彼时那种相互协助又高度戒备的微妙合作关系。(22)Peter Rand,China Hands,p.118.伊罗生与地下党派来的助手们会面时,也几乎从不提及对方姓名:他“从不知道那些不时遇见的如阴影般的共产党人究竟是谁”;“秘密工作的原则就是一个人不知道的,另一人不得说。”他描绘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是:这个外国青年同情者满怀热情从事的事业,就是通过《论坛》报道日本侵华、中国内战、西方列强和国民党政权的恐怖统治,但却从未有机会了解中共党内斗争的实际情况,就是对彼时鲁迅与党内人士的紧张关系也毫不知情。(23)Harold R.Isaacs,Re-Encounters in China,p.118,p.26,p.18.在租界里维系的这种秘密合作,尽管具有很高的政治风险和不确定性,但却切实地保障了《论坛》连续不断的信息来源,使其可以持续刊发有关“左联五烈士”、“牛兰事件”、闽变、华北事变、中央苏区与工农红军、国民党的“剿匪”战争和反共运动等对当局极具“冒犯性”的新闻报道。正如他在其主编的《国民党反动的五年》一书中所鸣谢道的:“没有这些匿名撰稿人与协作者的时间、金钱、精力和他们无私贡献的资料,完成这份历史总结与《中国论坛》特辑是不可能的。”(24)“Acknowledgements”,Harold R.Isaacs,ed.Five Years of Kuomintang Reaction,Shanghai:China Forum Publishing Co.,1932,contents page。
晚年伊罗生在回忆录中十分生动地描述了租界所具备的政治庇护功能:“外国管辖的地区确实为一些可以‘合法’居留的中国人提供了保护性的掩护,有不少人都得以成功地隐蔽下来。中国的文艺刊物只需最低限度地表示自己不涉及政治就可以持续出版,在遭到查禁后又改头换面地再次出现。即便必须在法律限度以内,非共产党的反政府者仍在此开展了大量出版和宣传活动。”(25)Harold R.Isaacs,Re-Encounters in China,p.118,p.26,p.18.一方面,因不平等条约而造就的,由少数领事、大班、金融寡头垄断权力的租界“在文化上则相对自由,并没有为建立西方文化霸权作过太多的努力”;(26)熊月之:《上海租界与文化融合》,《学术月刊》2002年第5期。另一方面,这种文化监管上的相对宽松,又实实在在地为中国的左翼舆论构筑了可资利用的平台。在时人眼中,租界实属一种“畸形之制度”(27)阮笃成:《租界制度与上海公共租界》,法云书店1936年版,第1页。,乃“帝国主义在中国特有之成绩表现”。(28)胡梦华:《帝国主义之研究》,《东方杂志》第22卷第8期,1925年4月25日。租界的长期存在,令无数有识之国人倍感屈辱。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不受本国政府管辖的“国中之国”,它同时也是国民党专制政权中的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空间,为不见容于“华界”的某些敏感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
如伊罗生所说,“在外面可能十分危险的‘非法’行为,在租界之内可能至少还是‘半非法’或者甚至就是‘合法’的。”(29)Harold R.Isaacs,Re-Encounters in China,p.7,pp.15-16.此论可谓“现身说法”之言。对于活跃于沪上的左翼人士而言,可资利用缺口虽然并不大,甚至只能算是一些缝隙,但通过依托租界并以《论坛》为枢纽来连接伊罗生、中共地下党和左翼文化名流这样的隐蔽合作渠道,已经足以维持这一片舆论阵地的生存与延续,由此亦得以窥见租界对于红色刊物的运作所起到的实际作用。
二、治外法权与“伊罗生事件”的解决
与一个政府对它所管辖区域内的无论任何国籍的人民实行独立裁决的司法主权(Territoriality)相对,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指的是一个政府对其在他国境内的本国公民具有独立司法权的法律制度。设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租界的治外法庭,印证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半殖民状态。美国于1844年通过签署《望厦条约》,循英国之路径攫取在华治外法权,并建立领事法庭以践行其特权,后又设立美国驻华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for China),可谓“借西方法治模式、诉讼程式为理念,演绎表达着西方法律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演进进程”。(30)李洋:《美国驻华法院:近代治外法权的另一重实践》,《法学家》2015年第6期。
治外法权的实践目的,就是掠取当地政府之司法权以“保护”本国国民的“合法利益”,洋人遂凭此得以逃脱中国法律的制裁,并易于得到本国领事裁判的轻惩乃至开脱。作为认同中国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进步人士,伊罗生向来对此不平等制度持坚决批判的态度。他在《论坛》上著文抨击道:“治外法权意味着屠杀中国人民的炮舰。它是粉碎中国民族独立的工具。”(31)“State Department Threatens Forum”,China Forum,July.30,1932,p.1.尽管伊罗生反感于这套蛮横的帝国主义霸权行径,但是他也很明白治外法权对自己、尤其是对维系《论坛》运转有着至关重要的保护作用。他坦承:“当然,正是治外法权体制,才使得《中国论坛》的存在成为可能。”当总领馆检察官萨勒特(George Sellett)质问他既然认为洋人在华特权应受谴责,那为何不放弃这些权力时,他的想法是:“我才没那么天真。”(32)Harold R.Isaacs,Re-Encounters in China,p.7,pp.15-16.伊氏自己显然比谁都清楚,正是因为有了治外法权的保障,他才拥有充分的活动空间。尤其是在危急关头,这一特权更是帮助他渡过难关的首要条件。
《论坛》问世后愈发激烈的论调,必然加剧其与当局的对立,而矛盾最终爆发的导火索,是1932年5月以“国民党反动的五年”为题的《论坛》专号。为纪念“四·一二”反共政变五周年而出版这份特辑,从不同角度记录了蒋介石实行白色恐怖政策的恶果,着力报道了各地反共屠杀所造成的人道灾难,揭示出国民党政权在谋取独裁的道路上与英美等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实情。时评家对此的观感是:“这份小册子花费了大量篇幅来论述国民党与国外‘帝国主义者’的勾结,并宣称国民党已经蜕变为一个压迫中国人民的反动政党。它还着力表现国民党反共运动的残酷,并配以大量展现镇压广东与汉口赤色起义的血淋淋的图片。”(33)“The Case of Harold R.Isaacs and George Bronson Rea”,The China Weekly Review,Aug.6,1932,p.343.诚如伊罗生在给妻子的信中所透露的:“它将成为一件滋滋发烫(sizzling)的小玩意。”(34)Peter Rand,China Hands,p.112.
这份专号连带着《论坛》创刊后积累的影响力,终于激起了国民党高层的怒火。6月初,上海市政府向美国驻沪总领事馆发出抗议,要求前者采取行动制止《论坛》,理由是此刊为共产党倾向刊物,并对市府的利益构成了危害。(35)“Municipality Asks American Consul to Clamp Lid on Forum”,The China Press,Jul.8,1932,p.4.南京方面则向美方提交了七项对伊罗生的指控,包括公开支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污蔑中央政府、国民党与中国司法制度等,上述罪名在国民政府制订的法律中最高可判处死刑。(36)“Police Arrest Forum Printer”,The China Press,Aug.13,1932,p.13.被《论坛》指控为与日本当局私下勾结的时任上海市长吴铁城,则向总领事康宁翰(Edwin S.Cunningham)指控伊氏散布谣言,并称国民党上层已下令关闭《论坛》,且声言已掌握了伊氏收受中共资助的证据。(37)Peter Rand,China Hands,pp.113-114.然而碍于其美籍身份,吴铁城也不得不表示这只是针对《论坛》本身,并无针对伊个人的诉求。(38)“Wu Asks Paper,Not Man Gagged”,The China Press,Jul.31,1932,p.1.总领馆遂召询伊罗生,总领事向他宣读了国务院的批复,表示除非他改变原来的办刊路线,否则美国政府将不会干涉中国当局对其采取的任何措施。美方检察官则威胁称:“他的刊物是对治外法权的滥用,他将因此而失去美国的保护。”(39)“American Editor of Communist Paper Defies District Attorney”,The China Weekly Review,Jul.30,1932,p.332.领馆方面摆出伊氏以后倘不变其态度,则美政府将撤销其享受领事裁判权之利益的姿态(40)《英文中国论坛报言论危害民国 市府向美领抗议》,《时报》1932年7月30日,第7版。,显然企图以此逼迫伊罗生软化立场,向中方妥协。
不过伊罗生不仅没有屈服,反而在《论坛》上详细披露事态的进展,并疾呼国民党“已经窒息了那些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人,因为他们威胁到了由中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所创立和扶植的这个极其堕落、野蛮和腐败的制度。现在又来窒息我们了”;(41)“Gag the China Forum”,China Forum,Jul.23,1932,p.6.表示决心“挑战那些说我们躺倒在国民党与帝国主义联盟脚下的所有指控”。(42)“State Department Threatens Forum”,China Forum,Jul.30,1932,p.1.他向外界声明不会扮演“烈士的角色”,而是会“为了一个美国人自由表达他的政治观点”的权利奋斗到底。(43)Chen,Jinxing,Harold R.Isaacs in the China Scene,1930-1935,p.156,p.153.尽管事发后他的父亲和《纽约时报》的驻沪通讯记者都劝其返美,但他回复说自己“并不相信‘容忍退让’或‘示弱敌人’的信条”。(4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 1932, Vol.IV,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8,p.657.
伊罗生还利用自己记者身份的便利,将这一消息传递给在沪英美媒体,后者纷纷跟进关注。《大陆报》声称“伊罗生先生的治外法权特权将被撤除”,此事一旦成真,“将成为首例此类涉及在华美国人的案件”。(45)“U.S.Officials Threaten to Withdraw Extrality From Shanghai Editor”,The China Press,Jul.29,1932,p.1;“American’s Extrality Rights May Go”,The China Press,Jul.31,1932,p.9.《密勒氏评论报》称伊氏以一种蔑视当局的态度坚称自己将继续以原来的路线办刊,无论官方将采取何种行动。(46)“American Editor of Communist Paper Defies District Attorney”,The China Weekly Review,Jul.30,1932,p.332.出于担忧伊案的处理可能会危及外国人在华特权的普遍适用性,一位在华的英籍保守人士则建议将伊氏驱逐出境。(47)H G.W.Woodhead,“The China Forum’ An Abuse of Extraterritoriality”,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Jul.16,1932,p.6.上海左翼文化界的声援活动也迅速展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社会学家联盟联合呼吁“所有革命群众起来为《中国论坛》的继续发行和出版自由而斗争。”(48)China Forum,Aug.13,1932,p.2.宋庆龄亦出面为伊辩护,声明“伊罗生先生通过他的刊物反击国民党与帝国主义,维护了中国人民的实际利益。”(49)“Chinese Hero’s Widow Defends H.R.Isaacs”,New York Times,Jul.28,1932,p.9.
更为有力的舆论支持还是来自美国本土。伊罗生在寻求到宋庆龄和史沫特莱的帮助后,三人分别函电立场偏左的纽约国际政治犯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Political Prisoners),告知国务院企图授权总领馆取消伊氏的治外法权,该会随即将这一消息透露给《纽约时报》。(50)“American Editor of Communist Paper Defies District Attorney”,The China Weekly Review,Jul.30,1932,p.332.《纽约时报》遂于7月28日刊发了这一消息。(51)“Editor’s Charge Is Sifted”,New York Times,Jul.28,1932,p.9.30日又以“美国人被警告将交由中国审判”为题重点报道了该事件,且着力渲染事件的严重性,宣称“在中美关系史上,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威胁要撤销它对美国公民治外法权的保护,任由他去接受中国法庭可能会处以终身监禁或死刑的审判。”(52)“American Warned of Trial by China”,New York Times,Jul.30,1932,p.16.该报突出“可能判处死刑” (Death Penalty Possible)等字样,颇吸引眼球,也有力地促使了事态开始向有利于伊氏的一方倾斜。
通过美驻沪总领馆与美国国务院之间的往来电文,可以更直观地还原“伊罗生事件”的逆转过程。1932年5月底,当伊罗生向总领馆申请注册“探照灯出版公司”时,上海市政府即要求领馆方采取禁止《论坛》出版的相应措施。检察官萨勒特随即就此事与伊罗生沟通,前者的意见是伊的行为虽在美国法律下不构成犯罪,但是因其从事的活动和态度都直接针对中国当局,必然会令美国政府难堪。检察官与总领事都认为应当警告伊罗生:如果中方采取限制他行动的举措,美方将不会予以保护,他们还一度相信“伊罗生一旦接到警告就会终止自己的行为。”国务卿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1867—1950)也指示领事馆应告知伊罗生其抨击与诽谤中国政府的行为可能被视作企图煽动颠覆现政权,这是对在华美国公民之特权恶劣的滥用,中方的抗议和请求是合理的。史汀生措辞严厉地表示,如伊氏一意孤行,则美方不会阻拦中方采取限制措施。(53)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 1932,Vol.IV,pp.654-655,pp.656-658.显然,在前期交涉中,美方基于维护外交关系的考虑而持强硬态度,尤其是明示剥夺伊罗生治外法权的可能,以期迫使其自觉收敛。
《纽约时报》对伊罗生一案的曝光,很快引发了各方的密切关注,媒体将此案的关注点引向美籍公民在华治外法权之存废的方向,更大大激化了事件的严重程度,给美方的处理造成相当的舆论压力,转机遂由此出现。国务卿在给康宁翰的电报中做出详尽指示,且直接引用了7月30日《纽约时报》报道的首段文字,表示目前出现了很多有关伊案的质询,且某些机构还在热衷于炒作“一个美国公民正在因英勇践行言论自由的权利而遭到迫害”的议题。为了化解公众的怀疑情绪、申明治外法权的既定原则,前者要求后者再次向伊氏准确地转达此前的指示,并强调该案“当然不涉及对在华美国公民治外法权地位的否认,也不涉及一旦中方企图以刑事或民事起诉伊罗生时,对他个人及其财产之保护义务的否定。”康宁翰自然意识到威逼手段弄巧成拙,此刻只好尽快补救。他在给国务院的回函中辩称,在沪媒体对总领馆与伊罗生的谈话做了不正确的报道,领馆从未提及会取消他的治外法权。他又在与吴铁城的会面中告知对方,希望更正此前对该案会致使伊罗生失去治外法权的不实报道,且以往的警告仅仅是针对“他的刊物”而言的。(5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 1932,Vol.IV,pp.654-655,pp.656-658.总领馆的检察官也向媒体表示,之前他与伊氏的会面“仅仅只是一次非正式的谈话而已。”(55)“U.S.Officials Hedge on Isaacs ’s Exterality”,The China Press,Jul.30,1932,p.1.到这时,美方应对的重点已经由原来的告诫、威胁转为了强调治外法权的不容动摇性、美国公民人身与财产权的不可侵犯性。国务院和总领馆为避免事态扩大,及时修正了处理此案的态度和口径,以图尽快平息争议。
《纽约时报》8月4日刊登了国务院答复受伊罗生父亲委托质询此事的众议院瓜迪亚(F.H.La Guardia)的信函,公开澄清了“此前报道伊罗生先生被威胁将失去治外法权的新闻是具有误导性的(misleading)。伊罗生先生享有的治外法权的地位与权利在国务院的指示中没有受到一丝损害。”(56)“Status of H.R.Isaacs in China Clarified”,New York Times,Aug.4,1932,p.5.伊氏的人身危机至此彻底解除。《密勒氏评论报》的评论一语中的:“事实是除非伊罗生先生本人自愿放弃他作为美国公民的特权,否则依照法律程序独立运作的政府就没有权力撤销对他公民权的保护义务。”(57)“The Case of Harold R.Isaacs and George Bronson Rea”,The China Weekly Review,Aug.6,1932,p.343.而实际上,伊罗生也很快清楚地意识到了整件事的内情,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就明言:“这不过是又一次虚张声势(bluff)的失败罢了。”(58)Chen Jinxing,Harold R.Isaacs in the China Scene,1930-1935,p.158.他甚至对此感到异常兴奋,因为这反而帮助《论坛》扩大了影响——“南京中央政府的机关喉舌说比起其他中文报刊来,中国人更渴望读到《论坛》”;而《国民党反动的五年》一书在重印后销量颇佳,公众的关注使得《论坛》坚定地成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代言人。(59)Peter Rand,China Hands,p.116.
那层笼罩在伊罗生头上的“死刑”阴影被证明不过只是虚惊一场,说到底,剥夺治外法权只是美方外交官的恫吓伎俩而已。从法理角度而论,无论总领馆还是国务院都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因为如此一来将严重破坏这项特权之于全体美国公民的普适性,且一旦造就援引前例的可能,就会构成对所有在华美籍人士的隐性威胁。国务院决不允许因区区伊罗生一人、区区《论坛》一刊,而去冒这种外交风险。如果说先前总领馆方企图以此来诱逼伊氏屈从的话,那么在事件搅动舆论风波之后,就必须以回归“政治正确”的原则来“以正视听”,才能维护外交部门的形象并给公众一个合理的交代。虽然美方一开始意图积极回应中方诉求,以维护两国友好关系,但在对伊案的不当处理可能造成重大司法危机的情况下,保障伊氏的在华特权就是利弊权衡的必然结果了。
人身安全虽已得到保障,但并不意味着《论坛》从此就一帆风顺。由于美方不反对中方就刊物的发行流通环节采取强制手段,所以《论坛》复刊后仍旧面临重重阻扰。伊罗生就曾公开表示过:“除了使得我们无法长期坚持的财政负担,《论坛》还被禁止通过邮政发行”。(60)“Cunningham to Investigate ‘China Forum’”,The China Press,Feb.18,1933,p.13.与此同时,印刷问题也日益困难。位于公共租界四川路的一位《论坛》的承印商,就在1932年8月遭到上海警方拘捕。(61)“Chinese Printer Arrested”,The North -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Aug.17,1932,p.256.再难找到合作厂商的伊罗生,只好就此转入亲自负责印刷的地下工作状态。(62)Harold R.Isaacs,Re-Encounters in China,pp.15-16.
风波平息后于8月13日出版的《论坛》第24期,再一次让总领馆收到了来自吴铁城的抗议,后者反映新一期的《论坛》不仅没有丝毫改善,反而“造谣和污蔑比以前更为变本加厉”,要求总领馆立刻采取严厉手段抑制这类行为并予以处罚。经过“伊罗生事件”后,总领事谨慎地在给国务卿的汇报中强调,伊的行为并未违反美国法律,“因此总领事馆当然无需遵从市长的要求,尽管这一刊物无疑丝毫没有改善其态度。”总领馆向公共租界的警方表示不会反对后者对“中国论坛出版公司”采取行政手段,但同时也表示“警方不得采取危及伊罗生个人及其财产的任何行动,因为那只能在美国法律程序下适用。”国务院的回复肯定了该意见,即美方不反对压制《论坛》出版的行为,但中方的行动“要严格限定在阻止该刊发行的同时又不牵涉伊罗生人身及其财产问题的范围内。”(63)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 1932,Vol.IV,pp.660-661.
在这之后,由于各种现实障碍一时无法解决,加之伊罗生忙于参与筹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论坛》经历了五个多月的停刊,直到1933年2月11日才又恢复发行。复刊后的《论坛》越挫越勇,不仅扩展为中英双语期刊,在内容上也更加充实,报道了南京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日军侵犯热河、北平的白色恐怖、南京的学生运动、苏联工人庆祝十月革命十五周年、中华苏维埃号召斗争等,“赤色”面貌依然。(64)“‘China Forum’ Resumes After Long ‘Involuntary Suspension’”,The China Press,Feb.12,1933,p.1.时评谓之:“前曾禁止出版,现又复活。并于下半册加辟中文版,大吹大擂。”(65)一棠:《中国论坛又复活》,《人报旬刊》第1卷第5期,1933年4月11日。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随即再次致函康宁翰要求审查并暂停《论坛》。(66)“Yui Asks U.S.Officials to Ban ‘Forum’”,The China Press,Feb.17,1933,p.9;“Cunningham to Investigate ‘China Forum’”,The China Press,Feb.18,1933,p.13.美领馆的发言人则老调重弹,称不会对《论坛》采取任何直接行动,因为该刊迄今尚未触犯美国法律。但如果中方的行动涉及到了伊个人,则美方将介入干预,因为他作为美籍公民是得到治外法权保护的。发言人还再次否认了此前关于褫夺伊氏治外法权的传言。(67)“China Forum Makes Second Bow to Public”,The China Press,Mar.10,1933,p.9.照此后该刊继续发行的情形来看,上海市政府的抗议仍是不了了之。
显然,有“前车之鉴”的总领事馆不愿再度陷入质疑与争议,自然倾向息事宁人。即便伊罗生依然固守原有立场,美方也必需履行其保护外侨之责,中方当局则更是奈何他本人不得。国民党舆论谓其“利用了中美邦交素来敦睦的一点,竟马马虎虎以向中国表示错误了事。”(68)扬声:《伊罗生及其中国论坛》,《社会新闻》第6卷第21期。但其实伊氏连“认错”的表面功夫都没有做过。在保障治外法权及公民言论自由权与国民政府对维持政权稳定的诉求之间,美方在利益衡量之下势必选择前者,这根本上乃是取决于两个整体实力与国际地位悬殊的国家之间不平等的外交关系,强势一方自行其是,弱势一方则不得不忍气吞声——“其洋威风,诚锐不可当也”。(69)甫:《中国论坛休刊》,《社会新闻》第6卷第18期,1934年2月24日。
结 语
伊罗生秉持同情弱小民族的人道主义精神,将治外法权视为帝国主义侵蚀中国主权的产物,然而当危难降临到自己头上时,他还是只有借助这把特权的保护伞方能化险为夷。正如《密勒氏评论报》所论:伊罗生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他在猛烈攻击中国政府的同时,又不得不利用他所憎恶的治外法权体系。(70)“The Case of Harold R.Isaacs and George Bronson Rea”,The China Weekly Review,Aug.6,1932,p.343.而伊氏给出的解释也颇为清醒和务实:“如果中国有一个真正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政府,那么我和其他人都将心甘情愿地交出我们的治外法权”。但是他面对的却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敌人之利益”的国民党政权,在这种情况下要他放弃特权去当“殉道者”,就是“错误且有几分歪曲的说法”了。(71)“U.S.Officials Hedge on Isaacs’s Exterality”,The China Press,Jul.30,1932,p.1.鲁迅曾说:“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说‘不’,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不作声的。”(72)鲁迅:《答中学生杂志社问》,《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3页。伊罗生既然凭借治外法权有了“言论自由”,为何又要主动放弃这个“作声”的权利呢?历史的辩证性就反映在,正是这个从“进步”的观点看来应当被谴责、被废除的治外法权,恰恰又使得伊罗生、史沫特莱、斯特朗等外籍左翼人士能够相对安全地参与到中国革命文化的事业中来,让他们得以利用被“恶法”赋予的特权来揭露统治阶层的专制暴行。
经由伊罗生等人审时度势的充分利用,原为列强诸国及其公民之在华特殊权益服务的租界与治外法权被切实转化成了推动中外合作开展左翼文化运动的助力。朱德盛赞《论坛》“击破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封锁消息的铁壁”,把劳苦大众受压迫的实际情形与“工农红军与苏维埃的伟大胜利,宣布到全世界”。(73)朱德:《朱德同志致中国论坛电》,《红色中华》第156期,1934年3月1日。正是依托租界和治外法权,《论坛》才坚持了长达两年的时间,不仅为中国革命的国际化传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也在中国左翼文化史上占据了的一个特别的位置。
《论坛》的出版发行和“伊罗生事件”的解决,前者依靠租界的活动空间,后者端赖于治外法权的“护身符”。租界和治外法权在损害中国领土与司法主权的同时,又为左翼活动的跨国交流创造了可能,这无疑彰显出民国时期特殊的历史机制。租界提供了容纳编辑人员进行地下工作的空间,惟“洋大人”所独享的治外法权则给予了主编切身的保护,以刊物为阵地、以主编为纽带,美国记者伊罗生、中共地下党人和各界左翼人士三方就这样联结到了一起,实现了有效的国际合作,也造就了一个充分体现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之“国际性”特质的典型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