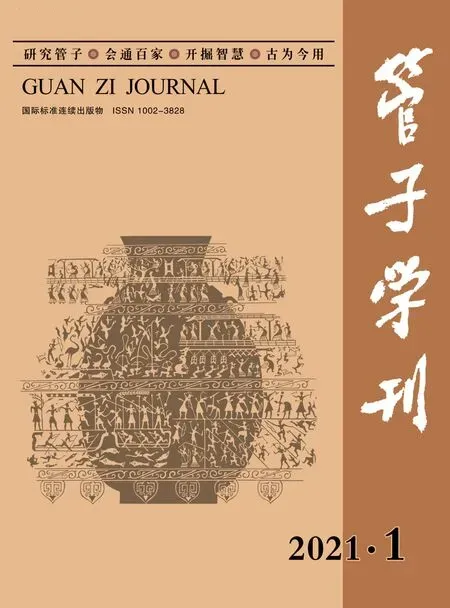黄老思想因素在韩非子政治学说中的作用
徐克谦
(三江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2;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司马迁《史记》将老子与韩非合传,并认为韩非的刑名法术之学“归本于黄老”(1)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612页。。黄老学说是以黄帝、老子为名的一种哲学思潮和政治学说。战国后期,黄老学说已经十分流行,成为显学。按照司马迁的说法,申不害、慎到等法家人物的学说,也都跟黄老有关。生活在战国末年的韩非子受到黄老学说的影响是很自然的。《韩非子》书中有《解老》《喻老》,是最早对《老子》进行注解和阐释的著作。《韩非子》书中也数次提及黄帝,黄帝在他笔下是天下大治的象征。因此,司马迁将老子与韩非合传,并说韩非的思想“归本于黄老”,点明韩非子思想与黄老的重要联系,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从整体上看,《老子》与《韩非子》的学说又明显存在很大差异。《老子》政治上向往小国寡民,无为自化,且认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2)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二版,第275页。,倾向于否定人为建构的法律和制度;黄老学说的核心精神也是强调清静无为,“贵清静而民自定”(3)司马迁:《史记》,第2464页。。这与韩非子主张积极有为地构建严刑峻法,建立中央集权的法治国家体制,似乎是大异其趣、互相矛盾的。以至于前代有不少人对司马迁将老子与韩非同传感到不解,如唐代刘知几就曾批评《史记》老子与韩非并列是“如斯舛谬”(4)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04页。。当代学者对韩非子与黄老思想的关系问题的看法,也颇有分歧(5)参见陈寒非:《归本于黄老:韩非思想的道论渊源》,《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第134-136页。。
笔者认为,韩非子思想受到《老子》及黄老思潮的影响是明显的。从《解老》《喻老》可以看出韩非子对《老子》思想有独到的领悟,他从法家立场和法治学说的需要出发对《老子》思想进行阐发,将《老子》的思想创造性地灵活运用到他的法术理论中,使《老子》的玄妙之“道”和他的法治学说巧妙结合,真正落实为一种“君人南面之术”。韩非子的其他文章,也多有对《老子》思想的借鉴和暗用,甚至《老子》的文风对韩非子也有一定影响,例如《扬权》篇那种押韵的文体跟《老子》就很相似。《韩非子》书中的法术思想与《黄帝四经》等黄老文献中的思想也有不少相通之处。
黄老思想在韩非子政治学说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仍值得加以具体探讨。有些学者认为黄老学说对韩非子的主要影响就在于政治权术,这种权术成为韩非子强化君主专制独裁的利器(6)例如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即认为黄老道家对韩非子的影响,主要就是经过慎到、申不害的学说,最终形成韩非子集权主义、专制主义政治学说中的阴谋权术。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59-409页。,这种观点未免有点偏颇。笔者认为,老子哲学、黄老思想对韩非子的影响,首先在于为其提供了某种哲学基础、思想方法。关于这一点,已有不少学者做了比较充分的论述(7)例如谢祥皓:《韩非的道和法——兼论韩非与老子的关系》,《江淮论坛》1981年第6期,第32-36页。王威威:《韩非的道法思想与黄老之学》,《兰州学刊》2008年第6期,第17-20页。陈寒非:《归本于黄老:韩非思想的道论渊源》,《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第133-150页。,本文不再赘述。除此之外,黄老思想在韩非子政治学说中的一个重要作用,恰恰是在理论上对韩非子法治学说中君主集权专制成分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制约,减轻了韩非子集权政治理论的专制倾向,从而增强了其法治理论的合理性。本文试对这个问题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缘道理”“因人情”而立法
韩非子接受了《老子》的基本哲学观,把“道”视为最高范畴,使“道”成为法家政治法律的终极依据。韩非子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8)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46页。“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9)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26页。“道”既然是最高范畴,当然也是法家的“法”与“术”的源头和依据,其地位远在“法术”之上。《黄帝四经·经法》开篇即说“道生法”(10)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页。。老子所说的“道”非常玄妙,“道”是“空”、是“无”,“玄之又玄”却又是“众妙之门”。《黄帝四经》也同时认为“道”的特点为:“虚无刑(形),其裻冥冥,万物之所从生。”(11)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第5页。“人皆以之,莫知其名。人皆用之,莫见其刑(形)。一者其号也。虚其舍也,无为其素也,和其用也。是故上道高而不可察也,深而不可则(测)也。”(12)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第399-402页。韩非子所说的“道”与此有许多相似之处,“道”不可见,“无常操”,玄妙变化,而其用途却又是无限的。总之,“道”本身虚无,但却生成并控制一切的实有,这正是黄老之“道”的玄妙之处。运用在政治上,就是要用一个至高无上而又玄虚莫测的“道”,来统摄一切的制度安排和政治设施。“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13)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28页。但是,法家大多是实干家,不能只玩弄玄妙,必须落实于事功,见效于具体的法治实践。故韩非子说:“今道虽不可得闻见,圣人执其见功以处见其形。”(14)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148页。
那么,怎样从这个玄妙空虚的“道”推导出实实在在的“法”呢?或者说“道”与“法”之间是怎么衔接的呢?我们在《解老》中发现,韩非子在“道”之下还有一个“理”的范畴。他在《解老》中引述的《老子》还有一句:“道,理之者也。”(15)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147页。这一句在传世本《老子》和新出土的几种简帛本《老子》中都没有。今所见《老子》文本中也没有“理”这个概念,也许韩非子看到的《老子》跟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都不同。而在被认为是黄老学说代表性文本的帛书《黄帝四经》中,“理”却已经是个重要概念。其《经法·论第六》认为, “物各[合于道者],胃(谓)之理。理之所在,胃(谓)之[顺]。物有不合于道者,胃(谓)之失理。失理之所在,胃(谓)之逆”(16)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第130页。。天地有“天地之理”,人事有“人事之理”;凡是“失理”“绝理”的行为,都会招致“天诛”。不论如何,这个“理”字都非常有意义。《经法· 名理第九》也指出,作为“神明之原”的“道”是“处于度之内”的、“不言而信”的,但要落实于现实政治,必须还要成为“见于度之外”“言而不可易”的东西才好操作。
韩非子非常精辟地论述了“道”与“理”的关系以及二者的不同。他指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17)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146-147页。“道”是万事万物之所以存在的根源,而“理”则是“道”在万事万物上的具体呈现。“道”本身不是“理”,但却有赖于具体的、确定的“理”来呈现,“故理定而后物可得道也”(18)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148页。。“道”是玄妙的、不可见的,而“理”则是具体的、客观的、可以度量的,他说:“凡理者,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理定而物易割也。”(19)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148、152页。万事万物都有不同的“理”,“理”不同于玄虚的“道”,是客观的、确定的、可以观察的。也正因为如此,“理”不一定是恒常不变的,“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不可谓常”(20)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148页。。这里包含的哲学意义就是:凡是说得出来的“理”都是具体的、可定义的,因而也是历史的、可变的、有限的。而在这一切之上的那个玄虚的、不可定义的、不变的、普遍的“道”才是永恒的。正因为其永恒、普遍,反而不能定义、不可言说、无定理。故韩非子说:“常者,无攸易,无定理。无定理,非在于常,是以不可道也。”(21)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148页。但恒常不可定义的“道”与具体可考察的“理”又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由此可以看出韩非子的确深谙老子的有无相生之“道”,也非常熟悉黄老关于“审察名理”“正道循理”的一套学说,巧妙地把法家非常实在的一套法术与老子形而上的玄虚之“道”联系在了一起,这就为“法”的制定提供了终极依据和落脚点,使“道生法”的过程具有面向现实的客观性。如《尹文子·大道上》所载:“察其所以然,则刑名之与事物,无所隐其理矣。”(22)高流水、林恒森译注:《慎子、尹文子、公孙龙子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6页。
人们通常认为韩非子法治思想的最大缺陷,在于韩非子所说的“法”完全是君主个人意志的体现,因为“法”是君主制定的,君主的主观意志是“法”的依据。但实际上由于有了黄老思想这个哲学基础,韩非子所谓“法”之上还有更高的原则和依据,这就是“理”和“道”。黄老学说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天下万物,包括人类社会,都有其恒常客观的道理,因此圣人治天下就是让万物按照自身的道理,“物自为名”“物自为正”。所谓“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源于这些恒常的道理。韩非子显然也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认为君主制定“法”必须“缘道理”。韩非子警示世上君主:“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无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势尊,而小易得卿相将军之赏禄。夫弃道理而妄举动者,虽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而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犹失其民人而亡其财资也。”(23)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136页。也就是说,即使是天子,也不能随心所欲,恣意妄为;办事、制定法律,必须“从于道而服于理”。尤其是这个“理”,具有很强的客观性,而“法”必须依据“理”来制定。“理”就是万事万物自身客观存在的“规矩”,“法”是依照这些“规矩”来制定的,“万物莫不有规矩……圣人尽随于万物之规矩”(24)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152页。。这也就是说,“法”并不是君主可以根据个人意志随意制定的东西,它的制定必须符合外在的“规矩”,合乎客观的“道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韩非子法治思想中,“道、理”共同构成客观法则,“法”产自并遵从道理(25)吕廷君:《韩非的“因道全法”思想》,《管子学刊》2020年第3期,第25页。。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也有其客观的“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人情”。《韩非子》书中没有“人性”这个词,但他经常提到“人情”。现代人往往会把先秦文献中的“情”字错误地理解为现代汉语中的“情感”,并且跟“理”相对立。韩非子所说的“人情”并非人的主观情感,而是指人的客观真实情况。“情”指实情,“人情”即人之实际情况,或人类生存的常态、常理。这个“情”跟“理”不仅不是对立的,反而是一致的。《黄帝四经·称》曰:“制人而失其理,反制焉。”(26)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第382页。也是说治理人不能违背人之常情常理。人之常理是什么呢?那就是人都有为自己生存发展谋利的欲望,都是好利恶害、喜贵恶贱的。“法”的制定,就必须符合这种“人情”。韩非子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27)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430-431页。“故安国之法若饥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28)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199页。好的、有效的法律,必定是以“人情”为客观依据,针对“人情”来设计,利用“人情”来发挥作用的。韩非子指出:“是故夫至治之国,善以止奸为务,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29)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476页。既然必须根据“人情”这一客观实际来制定法,那就不能仅凭君主个人的主观意志来制定,否则制定出来的法不符合“人情”,就不能发挥作用。
总之,韩非子认为君主治国,应当“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不逆天理,不伤情性……守成理,因自然”(30)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209-210页;“守自然之道”。这种思想显然与黄老道德学说是一致的。其潜在的逻辑,就是君主必须客观面对人的真实情况,顺应客观现实和事理来制定法律,设计治理方案,而不能主观武断、随心所欲。这种“缘道理”“因人情”而立法的思想,是与黄老道家主张“因顺”“因循”思想密切相关的。如果君主真能做到“缘道理”“因人情”而立法,那么这种法就不可能只是君主个人意志的体现。
二、君权至上与君道无为
战国时期,无论是儒家、黄老道家还是法家,总的来说都认为必须有君臣上下各守其位的国家制度,否则社会秩序就会混乱,无法治理。在这个制度中,君主显然处于核心和顶层的位置。即便是强调民贵君轻的孟子,也没有否认一国之君在行政上处于权力的核心地位。《黄帝四经》反复强调,君有位,臣有处,“君臣易立(位)胃(谓)之逆”(31)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第100页。。“为人主,南面而立。臣肃敬,不敢敝(蔽)其主。下比顺,不敢敝(蔽)其上。万民和辑而乐为其主上用,地广人众兵强,天下无适(敌)。”(32)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第87页。韩非子主张君主要独揽大权,赏罚的权柄要牢牢控制在君主的手中,权势不可以与臣下分享,认为君主要能“独断”。所以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为集权专制的君主服务。在韩非子的法治理论结构中,君主的确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处于中央集权的核心位置。
但是,由于有黄老“无为”思想因素的影响,韩非子法治理论体系中处于中央集权核心的理想的君主,理论上恰恰又不应该是一个随心所欲的专制独裁者。因为正像“道”在老子哲学中处于最高范畴,是宇宙万物的中心,而“道”本身却是“空”和“无”一样,作为“执道者”的君主,虽然身处最高权力中心,他自己也必须效法玄虚的大道,做到无私、无为、虚静,否则就配不上这个位置。这正如《黄帝四经》所载:“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无执也,无处也,无为也,无私也。”(33)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第10页。韩非子也认为,处于政治权力顶点和中心的君主应该效仿“道”的空虚无为,“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保持虚静、谦退、超脱的姿态。也就是说,权力虽然集中在君主手上,但是君主却要尽量少用权力,更不能滥用权力。
在《扬权》《大体》《主道》等文中,韩非子发挥了黄老的这一思想,要求君主“无为”。如《主道》篇载:“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34)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26页。《扬权》篇载:“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将自举之。”(35)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45页。这与《老子》所主张的侯王清净无为而民自化的观点也是相吻合的。韩非子认为君主必须在“道”的高度看问题:“夫能有其国保其身者,必且体道。体道则其智深,其智深则其会远。”(36)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140页。站在“道”的高度,就是要虚静无为,识大体,观全局,“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37)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209页。。君主应该“因道全法”“澹然闲静”。而因顺“道”与依靠“法”,在韩非子思想中已融为一体,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限制君主凭个人智慧和主观意志行使权力的意义,实际上有劝诫君主不要对法治进行主观干预的用意。他在《难三》篇引用老子的话“以智治国,国之贼也”,以此批评子产“不任典成之吏,不察参伍之政,不明度量,恃尽聪明劳智虑,而以知奸,不亦无术乎”(38)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377页。!显然,韩非子认为子产不依据法律,不依靠司法机关,就凭自己个人的小聪明来办案,这是“无术”的表现,是不明智的,也不符合法治精神。韩非子在《解老》篇发挥老子“治人事天莫如啬”的思想,认为“聪明睿智”属于“天”,运用“聪明睿智”于“动静思虑”则属于“人”。人越是“动静思虑”,对“天”的消耗就越大。也就是说,人越是绞尽脑汁来思虑,他的聪明睿智就越是消耗得厉害。就像用眼过度,眼睛就瞎掉了;用耳过度,耳朵就聋掉了。因此,“治人”就是要“适动静之节,省思虑之费”;“事天”就是要“不极聪明之力,不尽智识之任”。这就是“啬”的含义。而要做到“啬”,就必须“服从道理”。圣人在尚未见到祸患之苗头的时候,就老老实实地“服从于道理”,韩非子认为这就叫做“蚤(早)服”。这实际上也就是告诫君主不可自以为是,不可逞能,尽量少用自己个人的小聪明去办事,要尊重客观规律,要依靠法律,“舍己能,而因法数”。又比如在选拔人才时,韩非子强调“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39)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34页。。《老子》说:“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伤其手矣。”(40)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第325页。韩非子也借用老子这一思想,强调君主无为,大臣有为;告诫君主不要代大匠斲,也即不要干预“有司”依法行使职责。
韩非子认为,处于权力中心的君主,实际上就应该像《老子》所说的“三十辐共一毂”的那个轴心一样,以虚无为用。因此,处于最高权力中心的君主之位,并不是一个可以任意耍弄权威的职位。他在《扬权》一文中指出:“权不欲见,素无为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虚而待之,彼自以之。”“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41)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44、48页。《扬权》本是一篇“宣扬君权”,“从哲学高度论证君权至上”(42)《韩非子》校注组:《韩非子校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0页。的文章。但是从文中我们却又可以看出,韩非子理想中的君主,虽然大权在握,却又不应该是一个刚愎自用的独裁者,而应该是一个虚静无为、藏而不露的君主。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老子》哲学在这里所起到的作用。
韩非子曾引用申不害的说法,认为君主应当“独视”“独听”“独断”,这很容易让人把它与“独裁”联系在一起。但其实这里所谓“独视”“独听”“独断”是有特定语境的,实际上是在提醒君主不要向身边小人泄露机密、防止身边亲信和小人干政的语境下说的,意思是说君主应该有自己的独立判断,不能被身边小人蒙蔽,也不能因为身边妻妾、近侍之人的意见而蒙蔽了自己的视听,失去了自己的判断。至于决定朝廷的大事,韩非子倒恰恰是引用《老子》“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主张君主要“议于大庭而后言”。也就是说,君主要避免先发表意见,而应该先听取大臣的意见,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再做出决断。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则可以减少君主个人专断造成的失误。
此外,韩非子还借用《老子》“祸莫大于不知足”的思想来告诫统治者要知足,控制自己的“欲利之心”。一方面韩非子认为人的“欲利之心”是难免的,而且正因为人有“欲利之心”,法家的“赏罚”才有效果。因此对于广大民众来说,有欲利之心很正常,这正是实施法治可以利用的“人情”。因此,没有必要叫民众都学习老聃“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哲学,也不可能让民众都变成老聃。正如他在《六反》篇所说:“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于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为皆如老聃也。”(43)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422页。但是另一方面,他却用老子“知足”思想来告诫君主,“欲利之心”终究是“身之忧”,任其发展,则会导致“计会乱”“邪心胜”“事经绝”“祸难生”的后果。他在《喻老》篇也引用“纣为象箸而箕子怖”“子罕不受玉”等历史故事,告诫统治者欲望膨胀的危害。可见,《老子》哲学在韩非子政治学说中也有劝诫君主收敛欲望的作用。
三、以玄妙莫测之术制约“专制”
当然,总的来说,韩非子的确是主张中央集权的,这一点毋庸讳言。他认为君主必须把关键的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保证君主的绝对权威。他在《喻老》篇发挥老子“鱼不可脱于深渊,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的思想,认为“势重者,人君之渊也。……赏罚者,邦之利器也”(44)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158-159页。。这两者都只能掌握在君主手中。这在韩非子所处的那个正在由氏族封建体制向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转变的历史条件下,显然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迅速地使君主统治的广大地区成为一个真正实行全面有效管理的“国家”,而不再是诸侯纷争不断的封建氏族社会。
然而,从韩非子的角度来说,中央集权并不等于“专制”。不仅不等于“专制”,中央集权还是有效防止各种“专制”的必要条件。“专制”一词在《韩非子》书中出现了若干次。《南面》篇载:“人臣者,非名誉请谒无以进取,非背法专制无以为威,非假于忠信无以不禁,三者,惛主坏法之资也。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踰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此之谓明法。”《难一》篇载:“主有术,两用不为患;无术,两用则争事而外市,一则专制而劫弑。”《亡徵》篇载:“大臣专制,树羁旅以为党,数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出军命将太重,边地任守太尊,专制擅命,径为而无所请者,可亡也。”(45)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118、359、111-112页。可以看出,上面所引韩非子所谓“专制”,都是指朝中“当途者”“贵重之臣”、地方长官、各地驻军将领的“专制”,是与“背法”“擅命”联系在一起的。韩非子正是要提醒君主严防这种“专制”。韩非子认为君主应该掌握的“术”,很多也正是针对臣下各种“背法专制”的奸邪行为和诡计而设计的。可以说,君主如果不掌握“集权”之威,就很难对付重臣、地方长官和军事首领的“专制”。
从中国社会历史现实来看,各级地方官吏以及藩镇、军阀的“背法专制”,对广大百姓危害极大,是人民所遭受的压迫和苦难的直接来源。特别是在中央政府丧失权威,政令出不了皇宫的情况下,地方官员更是胡作非为,无法无天。中国古代所谓“法”,本来就缺乏深厚的宗教资源作为支撑,官民往往易于屈从权威而疏于遵从法律。因此即使有了“法”,若没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为保障,就难免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只有中央“集权”,地方才不敢“专制”。至于处于中央集权核心地位的君主个人,韩非子则借用《老子》思想,劝其清净无为,以静退为宝,不敢为天下先,不要代大匠斲。如果君主真能做到这些,那他也就不能算是个“专制”君主。所以总的来看,韩非子的法治学说至少在理论上并不鼓励“专制”,相反,强化法的地位和维护中央集权,倒是有制约各种个人“专制”的意义。
此外,韩非子认为君主还可以通过各种“术”来控制臣下,使臣下不得肆意“专制”。例如《内储说上》所谓“众端参观”之术,就是要从多渠道获得信息,避免臣下凭借一面之词,欺上瞒下;所谓“疑诏诡使”之术,就是要使臣下相互监督,形成权力制衡。总之,这些“术”大都是用来对付拥有一定权势的官员的,而不是针对普通民众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掌握权力的官吏“知伪诈之不可以得安”“知为奸利之不可以得安”,因而有所顾忌,从而起到防范官员个人胡作非为、专制横行的作用。
那么,有没有制约最高统治者本人专制的“术”呢?显然,韩非子不可能在他那个时代设计出诸如“三权分立”“宪政民主”之类的制度来限制君主本人的专制。但这不等于说韩非子就是拥护君主个人专制的,更不能简单地认定拥护君主专制就是韩非子政治理论的终极目的。实际上韩非子自己曾说:“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故不惮乱主闇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闇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46)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396页。这是韩非子在回应韩国一位名叫堂谿公的老前辈对他的忠告时说的心里话,应该是他真实的想法。据此亦可知,认为韩非思想“只从统治阶级的偏面利益”出发,“仅知有君主,不知有民众”(47)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4册),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版,第75-78页。,是不全面的。韩非子不惮“乱主闇上”,志在为民萌众庶谋利,怎么会一味维护君主独裁专制呢?只不过在战国末年天下苦于长久分裂与战乱的历史现实下,如果能以中央集权为代价平息天下战乱,以君主的威势与法术制约大臣和地方诸侯或军阀官吏的背法专制,也许是两害相较取其轻的选择,也可能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对民萌众庶比较有利的选择。
另外,对于最高统治者本人专制的危害,韩非子也并非没有警惕。韩非子除了以黄老学说中清净无为的思想劝导君主不要依靠个人的聪明、不要凭个人的喜怒治国外,也希望像他自己这样的法术之士能用老子那一套“以柔弱胜刚强”的术来控制和驾驭君主。这种“术”有别于申不害教给君主的潜御群臣的“术”,其实是一种臣下控制君主的“术”,可以称之为“御龙术”。《说难》篇载:“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48)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94-95页。韩非子的《说难》篇,通篇讲的就是法术之士作为臣下,如何在不触怒君主、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对君主进行柔性的劝诱和控制,逐渐使君主被驯化,变得“柔可狎而骑”,以便借助君主之力来推行法治。这其实也是一种以柔克刚、以静胜躁、以雌胜雄的黄老道术。老子主张“知其雄,守其雌”,《黄帝四经》也说要“用雌节”而不要“用雄节”,“守弱节而坚之,胥雄节之穷而因之”(49)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第329页。。可见,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守雌制雄,也正是黄老道术的内容。而法术之士把这种“术”拿来对君主进行驯化,则是韩非子创造性的运用,这也是黄老思想在韩非子学说中发生影响的一个方面。当然,用这种“术”对君主专制权力进行限制和纠正,在实践中的效力是极其有限的。韩非子虽然精通这一整套“术”,最终还是未能使自己免于杀身之祸。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中照录了《说难》全文,并不禁感叹:“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50)司马迁:《史记》,第2622页。
结语
《庄子·天下》篇认为古之道术本来是“皆源于一”的,进入春秋战国以后逐渐“道术将为天下裂”,分化为不同的学术流派。虽然诸子百家不同流派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给各家都贴上固定的学派标签却是到了汉代才逐渐成型的。先秦诸子们自己在当时恐怕未必有明确的学派区分的意识,他们只是就各自关心的问题发表不同的观点进行争辩而已。同时也正如班固在《汉书·艺文志》所说,诸子百家的思想,尽管“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然而“相灭亦相生也”,“相反亦相成也”。正因为如此,诸子的学说中往往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辩驳又互相影响的现象。特别是到了韩非子生活的战国后期,伴随着天下“定于一”的时代呼声与历史趋势,诸子各家学说之间渗透与融合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韩非子》不仅集此前法家思想之大成,同时也吸纳了包括黄老在内的其他流派的思想因素。因此司马迁说韩非学术“其本归于黄老”,“皆原于道德之意”,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不一定因此就要给韩非子也贴上“黄老家”的标签,但必须看到,韩非子深受当时流行的黄老思潮的影响,认真研读过《老子》书并为之解说,而且为己所用,并加以创造性地阐释和发挥。陈鼓应先生曾指出黄老“道”的思想具有“浓厚的古代民主性、自由性的讯息”(51)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第30页。。我们认为正是这种思想因素,在韩非子政治学说中对君主的极权专制提供了某种理论上的制约或减缓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韩非子的政治学说定性为极权主义、专制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