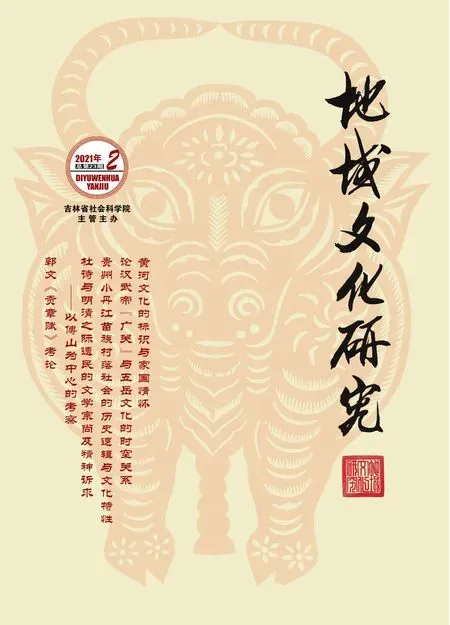郭文《贡章赋》考论
王 准
引 言
诸如西汉司马迁《史记》、东汉班固《汉书》、西晋常璩《华阳国志》、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等众多古代史书均有关于古代缅甸以及中缅关系的记载,展现了两国之间自古以来在地理、民族方面的密切联系。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中缅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往来日益紧密,古代史书对于缅甸乃至中缅关系的记载也与日俱增,两汉、魏晋以后,无论是《新唐书》《宋史》等正史还是《岭外代答》《万历野获编》等游记、野史等均有关于缅甸及中缅关系的内容,反映了中缅两国之间悠久而深厚的交往历史。缅甸特殊的地理特征、地域文化和中缅两国之间悠久的交往历史激发了后世文人的浓厚兴趣。而明代以来,随着中国西南地区的开发力度不断增强,云南等西南地区也逐渐成为文人的关注对象,有学者指出:“‘西南’是明清文学中一个特别且重要的主题,是文化、政治、战争、美学、地理、民族等诸多问题的辐辏交点。”①胡晓真:《明清文学中的西南叙事》,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9年,第4页。郭文《贡章赋》就以精练的内容、生动的笔触,反映了明王朝与麓川政权之间的战争及明代时缅甸宣慰使司等域外土司政权经由云南向明王朝进贡的历史。通过对《贡章赋》相关内容的分析考证可知,该赋体现了明王朝与麓川、缅甸等明代土司政权错综复杂的关系,以赋体文学之铺叙手法联结起了众多历史事件,是历史上中央王朝与地方关系乃至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一个缩影。
一、《贡章赋》的作者与主要内容
在众多明代辞赋中,郭文《贡章赋》有其独特之处,该赋叙写明王朝对麓川政权的军事行动和缅甸军民宣慰使司对明王朝的朝贡活动,是明代辞赋中反映军政大事的作品之一。关于《贡章赋》作者郭文,从各种记载来看,学界普遍认为郭文为明代初年云南昆明隐逸文人,近代方树梅《明清滇人著述书目·集部》:“《舟屋集》,明郭文撰,文字仲炳,昆明人。景泰间布衣,无家室。买舟青草湖,寝处其中,因号舟屋。”①方树梅:《明清滇人著述书目·集部》,昆明: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1944年印行,第2页。清袁嘉谷《滇绎》记明初平、居、陈、郭之事尤详:
杨升庵曰:“滇中诗人,永乐间称平、居、陈、郭。郭名文,号舟屋,诗有唐风,三字(子)远不及也。”按:郭之诗以竹枝一绝最传,其隐居在今草海西隅,盖张志和之流也。顾升庵不言平、居、陈、三人之名,《滇诗略》诸书皆不之及,《明史》亦含混言之。考柯暹《东冈集》附录《滇南别意诗》,则四人之作皆存焉。平名宣,武林人。居名广,海昌人。陈名谦,吴人。东冈跋云:“郭、居皆武进士中贤者。郭善诗文,征南将军都督沐璘继轩师之。居精吏事,总府辟掌薄书数十年,得官。陈官镇抚,有诗名。宣则松雨先生子也,黔府西塾,荐升广南府通判。”是平、居、陈皆流寓于滇者,与郭似不同也。②(清)袁嘉谷:《滇绎》,见秦光玉辑、李春龙点校《续云南备征志》卷30,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09-2310页。
从《滇绎》的记载来看,郭文与平显、居广、陈谦(一名陈廉)不同,前三人属于省外流寓云南的文人,郭文则是云南本土文人。而《滇绎》除了言及郭文为隐逸文人外,还根据明柯暹《东冈集》补充了其为武进士并曾进入明代云南地方统治者沐氏家族幕府参与其事的经历。今人孙秋克也认为郭文为明初云南隐逸文人,指出:郭文,字仲炳、号舟屋,昆明人。大约生活于明洪武至景泰初年。隐居滇池之滨,以诗歌名世,与省外流寓云南之平显、居广、陈廉并称“平居陈郭”,著有《舟屋集》。③孙秋克:《明代云南文学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0页。沐璘为明代黔国公沐英三子沐昂长孙,据《明史·沐英传》载:“璘字廷章,素儒雅,滇人易之。”④《明史》卷126《列传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762页。另据清张履程《明黔宁王沐氏世袭事略》载:“璘,字廷章,僖子。年十三丧父,十五丧祖及母,居丧守礼,读书工诗。”⑤(清)张履程:《明黔宁王沐氏世袭事略》,见(清)王崧辑,李春龙点校:《云南备征志》,卷21,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67-1168页。沐璘“素儒雅”和“读书工诗”的特点说明其热爱文学,俨然有儒将之风,因而像郭文这样的文学之士受到招募也在情理之中。而郭文生活在洪武至景泰年间,这一时期正是明代大规模开发云南和讨伐麓川政权的关键时期,从时间上来说郭文完全有可能参与其中,而郭文入幕于沐璘帐下的经历为其创作《贡章赋》这种反映国家军政大事的赋作提供了素材。
根据方树梅《明清滇人著述书目》所录,郭文《舟屋集》为明万历《云南通志》著录。清代袁文典、袁文揆所编《滇南诗略》著录其诗八首。⑥方树梅:《明清滇人著述书目·集部》,昆明: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1944年印行,第2页。郭文所著《舟屋集》至今未见,只有零星的诗文散见于方志和诗文集中。《贡章赋》收录于明天启年间刘文征所修《滇志·艺文志》,全文如下:
金沙之源发西域,众派合流深莫测。喷烟卷雪走万里,萦蛮络缅南归极。平原靡靡望不尽,海峤遥峰一丝碧。何年贡章城,雄压江之侧。甃砖为门木为栅,二水回环如拱璧。犀贝及鱼盐,杂沓来诸国。异服殊音类非一,市贸纷纷互重译。利之所在势必争,豪酋攻夺岁靡宁。
瘴烟漠漠遮尧日,炎海茫茫隔史星。麓川蕞尔寇,乃敢窥边城。王师振武飞电霆,动摇坤轴掀南溟。裸形髡首总慑服,卉裳椎髻咸来庭。
白㲲紫罽箱篚盈,筒茶树酒陈纵横。有象动千百,骈立驯不惊。朱鞍白盖黄金铃,夷奴驭之如马行,象识夷语随夷情。草树足异色,禽虫多怪声。严冬蛇走喧蚊蝇,夜寒挟纩昼絺绤,瘴毒中人如中酲。吁嗟汉与夷,彼此皆苍生。一为风土移,习俗与性成。我愿天公驱六丁,尽将山岳填谷坑。坐命八荒如砥平,地无南北交化并,同归熙皞为王氓。呜呼!同归熙皞为王氓。①(明)刘文征著,古永继点校:《滇志》卷18,明天启五年(1625)本,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602页。
《贡章赋》篇幅短小,主要包括明王朝征讨麓川政权以及缅甸向明王朝朝贡两大内容。对战争场面的描写与前代一些描写武功的赋作诸如唐赵子卿、赵伯励等的《出师赋》有一致之处。对朝贡场面的描写又与宋司马光《交趾献奇兽赋》等前代朝贡类题材近似。这两者在赋中的结合,体现了郭文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熟悉程度,更凸显了其驾驭语言、运用文字的能力,也使得全赋篇幅紧凑,重点突出而无拖沓冗长之感。而其中所涉地名、创作背景、创作年代和贡物、贡道等问题值得注意,需详加考察。
二、《贡章赋》中的地名、方位等问题
《贡章赋》开篇即言及发源于西域的“金沙”,又言“雄压江之侧”的“贡章城”,还述及“二水回环如拱璧”的特征,对这些地名、江名和地理特征等的梳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与该赋有关的创作年代和历史事件等问题。
根据明彭时等纂《寰宇通志·云南等处布政使司》载:“缅甸军民宣慰使司,在云南布政司西南三十八程,其地通曰缅,旧有江头、太公、马来、安正国、蒲甘缅王五城,元立邦牙等处宣慰使司,国朝洪武二十九年(1396),改置缅甸军民宣慰使司。”②(明)彭时纂修:《寰宇通志》,见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卷7,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0页。明李贤等纂《明一统志·云南布政司》载明代缅甸军民宣慰使司之建置沿革情况曰:“(缅甸军民宣慰使司)古西南夷,不知何种。其地旧有江头、太公、马来、安正国、蒲甘缅王五城。元代至元中屡讨之,后于蒲甘缅王城置邦牙等处宣慰使司。本朝洪武二十九年(1396)始归附,立缅甸军民宣慰使司。”③(明)李贤等撰:《明一统志·云南布政司》,见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卷7,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1页。
就政权性质而言,明王朝所设的缅甸军民宣慰使司是明代时位于中国境外的土司政权。按照龚荫《中国土司制度》一书的研究,土司政权从秦朝创立的“羁縻政策”发展而来,到元代形成土司制度,按照职官不同可分为宣慰、宣抚、安抚、招讨、长官等。任用当地少数民族作为首领,管辖所属领地并向中央王朝纳贡、征兵等是土司政权的主要统治形式和义务。形成于元代的土司制度到明代有了新的发展,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中国以外其他藩属国的民族也纳入到明王朝的土司制度中。①龚荫:《中国土司制度》,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2-168页。以缅甸为例,除了治所位于阿瓦(今缅甸曼德勒)等地、民族属于缅族的缅甸军民宣慰使司之外,明王朝还设立了木邦军民宣慰使司(掸族,今缅甸掸邦一带)、孟养军民宣慰使司(掸族,今缅甸克钦邦、实皆省北部)、大古剌军民宣慰使司(孟族,今缅甸勃固)、底马撒军民宣慰使司(孟族,今缅甸马都八)等以当地民族为土司的地方政权。②参见龚荫《明清云南土司通纂》,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贺圣达《缅甸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5-86页。
上述土司政权的设立,是明王朝国内形势和当时缅甸国内的形势双重影响的结果,就中国而言,明王朝建立后为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对周边国家采取睦邻友好的政策,为自身的长治久安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就缅甸而言,当时的缅甸处于分裂状态,形成了诸多割据政权,他们都想求得明王朝支持以壮大自身。贺圣达《缅甸史》一书指出:“蒲甘王朝(1044—1287)瓦解后,缅甸各地出现了许多并存的地方势力,他们统治的地域不大,力量较为弱小,彼此之间时有战争,而中国的明王朝,是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封建王朝,因此他们纷纷向明王朝纳贡称臣,求得支持,明政府则使其按当地的传统治理本地区。”③贺圣达:《缅甸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6页。这些土司政权的统治区域几乎涵盖了现今缅甸联邦共和国的大部分地区。他们除了接受明王朝册封,按时纳贡并在战争中承担一定的兵役之外,均保持着很大的独立自主性。因此,郭文《贡章赋》可以视为明代辞赋中的涉外题材。
《寰宇通志》和《明一统志》均言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所立之缅甸军民宣慰使司共有江头城、太公城、马来城、安正国城和蒲甘缅王城五座城池。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在古代文献记载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了详细考辨:
按:明张机《南金沙江(伊洛瓦底江)源流考》曰:“又一江源自腾越龙川江,经陇川、猛乃、孟密所部,至江头城,入于金沙江。江头城江中有大山,极秀耸,山有大寺。”按,龙川江即瑞丽江,则江头城在瑞丽江入伊洛瓦底江口,约北纬二十四度处。《马可波罗行记》沙海昂注曰:“据博歪(J.Beauvois)之考订,江头城在大金沙江右岸、龙川江会流处,下流经Katha之下。”所说是也。张洪《使缅录》记永乐五年出使曰:“行次贡章,即缅甸之江头城。”按:贡章即Katha,今亦译格萨。《明史·缅甸土司传》记成化七年事曰:“缅甸宣慰称贡章、孟养旧所辖,欲复得之。帝命往勘,贡章系木邦、陇川分治。孟养系思洪发所掌,非缅境。而缅甸以所求地乃前朝所许,贡章乃朝贡必由之途,乞与之。”《明宪宗实录》卷一九五成化十五年十月乙酉载:“缅甸求孟养、贡掌地,不许”贡掌即贡章。按:贡章(江头城)地当麓川、木邦、缅甸、孟养交接之处,故贸易繁盛,且为争夺之疆场也。④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003页。
通过以上考述可知,郭文《贡章赋》中的贡章城乃明代缅甸宣慰使司所统辖的江头城之别名。陈俊《中南半岛云南籍华人华侨研究》一书指出:“‘江头城’一名始于元代,缅音作kauang—si,古音作kong—cang,明代的‘贡章’系其译音,近音则作‘江新’。”⑤陈俊:《中南半岛云南籍华人华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62页。英人哈威《缅甸史》在记载缅甸蒲甘王朝地名时将“贡章”译为“杰沙(Katha)”,为缅甸蒲甘王朝杰沙县统辖地区之一。①[英]埃·戈·哈威著,姚梓良译:《缅甸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72-73页。按照谭其骧主编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明时期全图》和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热点国家地图·缅甸》所标方位,杰沙(江头城)位于今缅甸实皆省,靠近缅甸克钦邦、掸邦并处于瑞丽江、伊洛瓦底江交汇之处。②参见谭其骧主编《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第61-62页;周敏主编《世界热点国家地图·缅甸》,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14年,不分页。总之,无论是“贡章”“江新”还是“杰沙”都是江头城的不同音译。江头城与太公城(在今缅甸伊洛瓦底江沿岸)、马来城、安正国城、(均位于今缅甸曼德勒)蒲甘,(今缅甸蒲甘)共同构成了明代缅甸宣慰使司的“缅中五城”。
通过上述方国瑜等人的考证亦可获知《贡章赋》中源自西域的“金沙”并非今日人们普遍所熟知的长江上游之金沙江,而是位于今缅甸境内的伊洛瓦底江(Ayeyarwady 又名大金沙江、南金沙江)。按唐樊绰《蛮书》的记载,伊洛瓦底江古名丽水,又名禄卑江,“源自逻些城三危山下”③(唐)樊绰著,向达原校,木芹补注:《蛮书》卷2,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页。(今西藏拉萨),故《贡章赋》言该江“发西域”。而贡章城“雄压江之侧”且“二水回环如拱璧”则印证了该城池位居伊洛瓦底江(大金沙江)和瑞丽江(又名龙川江)两江交汇之处的地理特征。方国瑜指出:“据地图,沿伊洛瓦底江在江头城区为杰沙县,其南自太公城至新姑(阿真谷城)以下为曼德礼县,其对岸为实皆县,又南沿江之东为敏达县,又东为叫栖县(此县北接曼德礼县),又南沿江东为吻外(木魏)县,又东北为密铁拉县,又东为任尾申(元敏申)县,又木谷具县在敏建对岸,敏巫在木魏对岸。盖蒲甘国之疆域,其南以敏巫、木魏、元敏申为界,其北至江头城。”④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006-1007页。江头城位于伊洛瓦底江(大金沙江)和瑞丽江(又名龙川江)交汇之处,在缅甸境内众多城池中又处于北面,地理上距中国云南最近。
如上所述,贡章城联通缅甸境内各地,处于中缅交汇之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了缅甸国内以及中缅、滇缅之间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商贾辐辏。明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载:“江头城外有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而三宣六慰被携者亦数万。”⑤(明)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见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卷5,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91页。与《贡章赋》所言:“犀贝及鱼盐,杂沓来诸国。异服殊音类非一,市贸纷纷互重译。”均是江头城一带贸易繁荣、人们互通有无之情形的反映。而这一交通要道所具有的经济价值使得贡章城成了明代中国与周边国家朝贡贸易的必经之路,亦是兵家必争之地,故而《贡章赋》言“利之所在势必争,豪酋攻夺岁靡宁。”贡章城特殊的地理位置对于明代的民间贸易乃至朝贡外交的顺利开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贡章赋》以“贡章”开篇,继之以明代征讨麓川的军事行动以及彼时缅甸向明王朝朝贡之事,证明了该地作为明代中缅之间政治(朝贡)、经济、军事之要地而备受重视的历史事实。《贡章赋》中的贡章城(江头城)作为缅中五城之一,长期以来处于中缅、滇缅交通要冲之地,在历史上中缅两国的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贡章赋》所涉历史事件及其创作年代、创作动机
《贡章赋》描写了明王朝征讨麓川政权的军事行动,作者用“麓川蕞尔寇,乃敢窥边城。王师振武飞电霆,动摇坤轴掀南溟。裸形髡首总慑服,卉裳锥髻咸来庭。”①(明)刘文征著,古永继点校:《滇志》卷18,明天启五年(1625)本,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602页。寥寥数语以蔽之,虽描写简短但蕴含丰富。
(一)历史事件
《贡章赋》明确提到麓川政权,关于政权性质:据龚荫《明清云南土司通纂》一书的研究,麓川政权的政权性质和缅甸军民宣慰使司的政权性质相同,均为土司政权,但麓川政权属于中国境内的土司政权,其统治者为傣族思氏。②龚荫:《明清云南土司通纂》,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196页。关于该政权的历史沿革,《元史》载:“六年(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六月丁巳,诏以云南贼死可伐(思可法)盗据一方,侵夺路甸,命亦秃浑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讨之。”③《元史》卷41《本纪四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875页。《元史》又载:“十五年(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八月戊寅,云南死可伐(思可法)等降,令其子莽三以方物来贡,乃立平缅宣慰司。”④《元史》卷41《本纪四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875页。《明史·云南土司传》载:“麓川、平缅。元时皆属缅甸。缅甸,古朱波地也。宋宁宗时,缅甸、波斯等国进白象,缅甸之名始此。缅在云南之西南,最穷远。与八百国、占城接境。有城郭室屋,人皆栖居,地产象马,元时最强盛。元尝遣使招之,始入贡。洪武六年(1373)遣使田俨、程斗南、张祎、钱允恭赍诏往谕。至安南,留二年。以道阻不通,有诏召之,惟俨还,余皆道卒。十五年(1382)大兵下云南,进取大理,下金齿。平缅与金齿壤地相接,土蛮思伦发闻之惧,遂降,因置平缅宣慰使司,以思伦发为宣慰使。十七年(1384)八月,伦发遣刀令孟献方物,并上元所授宣慰使司印。诏改平缅宣慰使为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并赐伦发朝服、冠带及织金文绮、钞锭。”⑤《明史》卷314《列传二百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111页。
关于麓川政权统治区域:明钱古训、李思聪《百夷传》载:“百夷在云南西南数千里,其地方万里。景东在其东,西天古剌在其西。八百媳妇在其南,吐蕃在其北。东南则车里,西南则缅国。东北则哀牢,西北则西番,回纥。俗有大百夷、小百夷、漂人、古剌、哈剌、缅人、结些、哈吐、弩人、蒲蛮、阿昌等名,故名百夷。”⑥(明)钱古训:《百夷传》,见秦光玉辑、李春龙点校《续云南备征志》,卷1,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4-75页。
从上述史料来看,《元史》记载的死可伐(思可法)为麓川早期首领,《明史》的记载表明麓川政权兴起于元明之际。《百夷传》由明洪武年间钱古训、李思聪出使麓川所记见闻汇集而成。“百夷”即傣族之别称,其势力范围东至景东(今普洱景东县),西至西天古剌(今印度东部),南至八百媳妇国(今泰国),东北至吐蕃(西藏),东南至车里(今西双版纳),西南临近缅国(缅甸),东北临近哀牢(今保山、腾冲及缅甸北部等地),又与西番(西藏)、回纥(今新疆等地)相临,可谓幅员辽阔。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一书指出:“麓川思氏强盛时,其势力所控制者:麓川、平缅(陇川、勐卯、遮放)之外,在潞江(怒江)以西有干崖(干崖、盏达)、南甸、腾冲、潞江、芒市、户撒、腊撒之地。在潞江以东,澜沧江以西,有孟定(孟定、耿马)、孟琏、大侯、湾甸、镇康之地,在澜沧江以东有威远、镇沅、者乐之地。”①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63-864页。综合《明史》《百夷传》的有关记载和今人方国瑜的考证可知,麓川政权崛起于元末,兴盛于明代。其统治区域以现今云南德宏州陇川、瑞丽为中心,管辖滇西、滇西南广大地区,与缅甸等地相邻。
相关史料记载显示,麓川政权崛起之后,野心膨胀,对云南地区和臣属明王朝的缅甸军民宣慰使司等土司政权时有侵犯之举。关于麓川侵扰云南之事:《明史·云南土司传》载:“十八年(明洪武十八年,1385),伦发(思伦发)反,率众寇景东。都督冯诚率兵击之,值天大雾,猝遇寇,失利,千户王昇战死。”②《明史》卷314《列传二百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111-8112页。“明年(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伦发(思伦发)诱群蛮入寇马龙他郎甸(今墨江)之摩沙勒寨,英(沐英)遣都督宁正击破之,斩首千五百余级。伦发(思伦发)悉举其众,号三十万,象百余,寇定边(今南涧),欲报摩沙勒之役,新附诸蛮皆为尽力。英选师三万,亟趋至,贼列象阵搏战。英列弩注射,突阵大呼,象多伤,其蛮亦多中矢毙,蛮气稍退。”③《明史》卷314《列传二百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112页。
关于麓川政权侵扰缅甸之事:《明史·云南土司传》载:“二十八年(明洪武二十八年,1396)缅国王使来言,百夷(麓川)屡以兵侵夺其境。明年,(明洪武二十九年,1397)缅使复来诉。帝遣行人李思聪等使缅国及百夷(麓川),思伦发闻诏,俯伏谢罪,愿罢兵。”④《明史》卷314《列传二百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113页。从有关记载来看,《贡章赋》中“麓川蕞尔寇,乃敢窥边城。”的描写反映了麓川政权对缅甸宣慰使司的侵犯,赋中所言“边城”即贡章城(江头城)。
虽然还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麓川政权对缅甸宣慰使司所属的贡章城(江头城)采取了实质性的占领行动,但从《明史》等史书对于麓川政权侵扰缅甸的记载来看,作为明代缅甸宣慰使司五座城池之一的贡章城(江头城)很有可能处在麓川政权的侵犯区域之内。而且由于贡章城(江头城)位居缅甸宣慰使司最北之处,与明王朝、麓川政权等明代西南边境诸土司联系紧密,为官方朝贡和民间贸易之要道,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成为麓川政权争夺的焦点也在情理之中。因此《贡章赋》对麓川政权“窥边城”的描写不仅反映了麓川政权与缅甸宣慰使司之间的冲突,而且还透露出该政权对贡章城(江头城)觊觎已久的事实。
麓川政权野心极大且反复无常,持续侵扰云南地区以及缅甸等宣慰司的行径不仅破坏了明王朝与云南周边缅甸等宣慰司的关系,也使得明王朝在中国西南地区的统治受到严重威胁。面对此种情况,明王朝除了运用招谕等和平方式加以安抚之外,也增加了采用军事手段的比重。特别是明正统元年(1436)之后,继任麓川宣慰使思任发更加肆无忌惮,“连年累侵孟定、南甸、干崖、腾冲、潞江、金齿等处,自立头目刀珍罕、土官早亨等相助为暴,叛形已著。”⑤《明史》卷314《列传二百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116页。此番严峻形势使得明王朝坚定了征讨麓川政权的决心,成为之后明王朝“三征麓川”的前奏。
《明史》记载“六年(明正统六年,1441),以定西伯蒋贵为平蛮将军,都督李安、刘聚副之,以兵部尚书王骥总督云南军务,大会诸道兵十五万讨之。”①《明史》卷314《列传二百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117页。为明王朝第一次征讨麓川,此役以明王朝军队获胜告终,前后历时两年。麓川首领思任发失败后逃奔孟养(今缅甸西北部一带地区),明王朝令木邦(今缅甸南北掸邦高原地区)、缅甸(今缅甸曼德勒一带)二宣慰司擒拿思任发,并许以麓川之地。后思任发为缅人所擒,缅人以其为筹码求地。与此同时,思任发之子思机发一方面“乞来朝谢罪,先遣其弟招赛入贡。”②《明史》卷314《列传二百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118页。另一方面“窥大兵归,图恢复,据麓川,出兵侵扰。”③《明史》卷314《列传二百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118页。于是在明正统八年(1443),明王朝“复命王骥、蒋贵等统大军再征麓川。”④《明史》卷314《列传二百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118-8119页。是为第二次征讨,此次战役,王骥“趋者兰(今瑞丽南坎),捣机发巢,破之。机发脱走,俘其妻子部众,立陇川宣慰司而归。”⑤《明史》卷314《列传二百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119页。第二次麓川之役后,思机发“窃据孟养(今缅甸西北部一带地区),负固不服,自如也”⑥《明史》卷314《列传二百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119页。并采取各种手段与明军队相抗衡,以图东山再起。缅甸则于正统十一年(1446)献出思任发妻子等人,千户王政于途斩杀思任发,首级献于北京。为彻底消除祸患,明王朝在多方权衡之后,决定再次展开军事行动。于正统十三年(1448)“复命兵部尚书靖远伯王骥总督军务,都督同知宫聚佩平蛮将军印,率南京、湖广、四川、贵州官军、土军十三万人讨之。”⑦《明史》卷314《列传二百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119页。是为第三次征讨,此次战役仍以明军获胜告终,思机发再次逃遁。
从《明史》中的有关记载来看,正统年间三次征讨麓川的行动虽然都未能直接擒获其首领,但也沉重打击了麓川政权的有生力量。在此之后,明王朝于景泰五年(1454)将原属麓川的银戛(今地名待考)等地划归缅甸,作为回报,缅甸将思机发及其妻子等人献出,思机发后被诛于北京。明王朝又于成化年间将思任法之孙思命发安置于登州(今山东蓬莱),麓川遂亡。⑧《明史》卷314《列传二百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120-8121页。
通过对上述史料记载所提供的线索可知,《贡章赋》所言“王师振武飞电霆,动摇坤轴掀南溟。裸形髡首总慑服,卉裳锥髻咸来庭。”的描写已经概括了明王朝军队大举征讨麓川,取得胜利并对各处土司政权产生威慑作用的事实。达到了消除叛逆、安抚土司政权,稳定边疆地区和宣布明王朝声威的目的,可谓一举多得。因此,《明史》等史料的种种记载足以证明明王朝三征麓川的事件乃《贡章赋》创作的历史背景,该赋也同样成了明代辞赋中反映国家大事、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关系以及中外关系的赋作因而具有较高的文学和史料价值。
(二)创作年代
通过对正统年间三征麓川这一历史事件的考察也可以推知《贡章赋》的大致创作年代。据《明史·沐英传》记载:“子琮(黔国公沐斌子沐琮)幼,景泰初,昂孙璘以都同知代镇。”⑨《明史》卷126《列传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762页。《明史·云南土司传》又载:“景泰元年(1450),云南总兵官沐璘奏:‘缅甸宣慰已擒获思机发,又将思卜发放归孟养。恐缅人复挟为奇货,不若缓之,听其自献便。’从之。”①《明史》卷314《列传二百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120页。沐璘代沐琮镇守之时已是景泰年间,麓川之役虽然基本接近尾声,但余波仍在。综合《明史》中的有关历史事件和沐璘的生平事迹来看,郭文创作《贡章赋》的年代应在明王朝三征麓川之后的景泰年间,也就是1450年—1456年的时间段内。
(三)创作动机
高扬颂美意识,强调中央王朝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并彰显大一统情怀是历代众多辞赋作品的价值取向,《贡章赋》亦然。该赋虽无长篇大论的铺陈渲染,但却通过有关内容彰显了中央王朝的合法性、权威性,也体现出明代时与中国云南相邻的缅甸军民宣慰使司等土司政权对于明王朝的臣服与敬畏。而对割据一方、屡屡挑衅的麓川政权则充满了蔑视。因此,推尊一统,反对割据也同样是《贡章赋》的主要价值取向。
而透过《贡章赋》中表现出的这种尊一统、反割据的大一统意识也可以推知其背后深刻的现实用意。结合史料记载来看,《贡章赋》的有关描写在某种程度上透露出了明王朝与麓川、缅甸等境内外土司政权的微妙关系。对于明王朝而言,麓川政权和缅甸宣慰使司等土司政权的稳定不仅有利于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而且有利于保持各土司政权对于中央王朝的向心力。因而贡章城这一交通便利,经济繁荣之地直接关系到明王朝在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经济利益,有助于密切云南一省与各宣慰司的关系,达到有效管理边陲和维护正统秩序的目的。对于麓川、缅甸等境内外土司政权而言,能对贡章城(江头城)这一交通要道进行有效的控制意味着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并在与明王朝的朝贡活动中争得更多的主动权,从而达到维护自身政权稳固的目的。
而《贡章赋》结尾“吁嗟汉与夷,彼此皆苍生。一为风土移,习俗与性成。我愿天公驱六丁,尽将山岳填谷坑。坐命八荒如砥平,地无南北交化并,同归熙皞为王氓。”②(明)刘文征著,古永继点校:《滇志》卷18,明天启五年(1625)本,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602页。的感叹似乎也是对明王朝长期用兵,劳师袭远以致劳民伤财等种种负面影响流露出的些许不满。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已有人对麓川之役提出异议。比如明正统年间刑部侍郎何文渊上言:“麓川之在南陲,弹丸尔。疆里不过数百,人民不满万余。宜宽其天讨。官军于金齿,且耕且守。舜德格苗,不劳征伐,而稽首来王矣。”③(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0,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55页。更有人指出明王朝之威胁在西北而不在西南,如翰林院侍读刘球上疏言:“麓川荒远偏隅,即叛服不足为中国轻重。而脱欢、也先并吞诸部,侵扰边境,议者释豺狼攻犬豕,舍门庭之近,图边徼之远,非计之得也,请罢麓川兵,专备西北。”④(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0,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56页。从种种记载可证《贡章赋》所言愿“天公”填平山岳,从此四方平坦如砥,地无南北,汉与夷安居乐业,同为朝廷子民的感叹似乎也有对统治者发兵征讨麓川的委婉批评,在颂美之外还隐含有一定的讽谏意图。
四、《贡章赋》中的贡物与贡道
(一)贡物
除了地名之外,《贡章赋》对缅甸向中国所贡之物也做了一番描述,从全赋来看,贡物主要包括“白㲲”“紫罽”“筒茶”“树酒”和“驯象”千百。这些物品均为缅甸特产,常见诸文献记载。比如明天启《滇志·缅甸宣慰使司》载:“其产象、犀、马、椰子、白㲲布、兜罗锦。树类棕,高五六丈,结实如掌,土人以曲纳罐中,以索悬于实下,划实取汁,流于罐以为酒,名曰‘树头酒’。”①(明)刘文征著,古永继点校:《滇志》卷30,明天启五年(1625)本,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988页。《贡章赋》中之㲲,为细棉布之意,即《滇志》所载之“白㲲布”。罽读记,为毛织品,或即《滇志》中之“兜罗锦”一类的织物。《贡章赋》中的“筒茶”虽未见文献记载,但通过云南、缅甸产茶的情况可知其为缅甸所产之茶,贮藏于竹筒之中。与今日云南布朗族、德昂族等民族以竹筒贮茶的做法有类似之处。②施惟达、段炳昌等著:《云南民族文化概说》,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7页。而《贡章赋》中“树酒”(树头酒)的酿造制作方法十分独特,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缅甸物产之丰由此可见一斑。
而《贡章赋》中最能代表贡物原产地特色的当属所贡之象,中国古代贡象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汉代。《汉书·西域传》所载西汉时四方所贡之物有“钜象、狮子、猛犬”③《汉书》卷96《西域传六六》,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928页。等物。随着后世朝贡制度的不断完善,当时东南亚诸国向中国贡象的历史不仅见诸文献记载,还进入文学创作特别是辞赋创作中,比如唐佚名和唐杜洩的《越人献驯象赋》,唐独孤授和独孤良器的《放驯象赋》,宋司马光《交趾献奇兽赋》,明杨士奇《白象赋》、金幼孜《瑞象赋》等。
在明代朝贡活动繁荣发展的局面下,与云南接近的安南(越南)、南掌(老挝)、暹罗(泰国)和缅甸是彼时东南亚地区向中国贡象的重要区域之一。明谢肇淛《滇略》、清檀萃《滇海虞衡志》等书均有关于缅人驯象以供耕战和用作贡物的记载。《贡章赋》中:“有象动千百,骈立驯不惊。朱鞍白盖黄金铃,夷奴驭之如马行,象识夷语随夷情”的描写就是明代缅甸贡象在辞赋中的又一反映,从中可知明代时缅甸向中国进贡之象不仅数量多,而且训练有素、装饰华丽。因此,从《贡章赋》所涉贡物的描写来看,缅甸在与明王朝的朝贡关系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二)贡道
结合上述有关贡章城地理方位等有关内容来看,《贡章赋》中关于大象等贡物描写也隐约展现出一个与朝贡息息相关的交通要道,即所谓“贡象道路”,这一道路按照贡物所经地区的不同又可分为“贡象上路”和“贡象下路”。对于“贡象道路”,万历《云南通志·羁縻志》有着较为清晰的记载:
贡象道路,上路由永昌(保山)过蒲缥,经屋床山,箐险路狭,马不得并行。过山即怒江,过江即僰夷界也,江外高黎贡山,路亦颇险,山巅夷人立栅为寨,此栅,三代谓之徼外也。过腾冲卫西南行至南甸(今德宏州梁河县)、干崖(今德宏州瑞丽市)、陇川(今德宏州陇川县)三宣抚司。陇川有诸葛孔明寄箭山,陇川之外,皆是平地,一望数千里,绝无山溪。陇川十日至于孟密(今缅甸蒙米特),二日至宝井(今缅甸抹谷),又十日至缅甸(明缅甸宣慰使司,今缅甸曼德勒一带),又十日至洞吾(今缅甸东吁),又十日至摆古(今缅甸勃固),现今莽酋居住之地。(贡象上路)
下路由景东(今普洱市景东县)历者乐甸(在景东一带),行一日至镇沅府(今普洱市镇沅县),又行二日始达车里宣慰使司(今西双版纳)之界。行二日至车里之普洱(今普洱市),此处产茶,一山耸秀,名光山。有车里一头目居之,蜀汉孔明营垒在焉。又行二日至一大川原,轮广可千里,其中养象。其山为孔明寄箭处,又有孔明碑,苔泐不辨字矣。又行四日始至车里宣慰使司,在九龙山之下,临大江,一名九龙江(澜沧江),即黑水之末流也。由车里西南行八日至八百媳妇宣慰司(今泰国清迈一带),此地寺塔极多,一村一寺、每寺一塔。村以万计,塔亦以万计,号慈国。其酋恶杀不喜争,敌人侵之,不得已一举兵,得所仇而罢。由此西南行一日至老挝宣慰司(今老挝琅勃拉邦一带),其酋一代只生一子承袭,绝不生女。西行五六十日至西洋海岸,乃摆古莽酋(今缅甸勃固)之地。(贡象下路)①(明)邹应龙修、李元阳纂,刘景毛等点校:《云南通志》,卷16,明万历四年(1576)本,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年,第1485页。
从这一记载来看,“贡象道路”在中国云南境内主要包括滇西、滇西南、滇南三地。而在缅甸境内则主要包括上缅甸地区(包括缅甸北部、中部、东部、西部地区,临近印度、中国西藏。)和下缅甸地区(包括缅甸南部、西南、东南地区,临近老挝、泰国、孟加拉国等地),几乎涵盖缅甸全境。从缅甸对明朝贡的路径来看,两条“贡象道路”的起点从缅甸开始,终点均是北京,是构成彼时中国与东南亚朝贡关系的交通要道之一。《贡章赋》中的有关描写也呈现了有关“贡象道路”的一些情况,从贡章城方位和大金沙江(伊洛瓦底江)流经区域来看,《贡章赋》所涉贡道当为“贡象道路”中临近滇西、滇西南地区和上缅甸的“贡象上路”。赋中“甃砖为门木为栅”的描写吻合了万历《云南通志》之“贡象上路”中“山巅夷人立栅为寨,此栅,三代谓之徼外也。”的记载;赋中“喷烟卷雪走万里,萦蛮络缅南归极。平原靡靡望不尽,海峤山峰一丝碧。”则与万历《云南通志》“贡象上路”中关于滇缅交界处“陇川之外,皆是平地,一望数千里,绝无山溪。”的地理特征较为吻合;而《贡章赋》中“草树足异色,禽虫多怪声。严冬蛇走喧蚊蝇,夜寒挟纩昼絺绤,瘴毒中人如中酲。”的描写也正是“贡象道路”所经地区草木丰茂,动物繁多,气候变幻莫测和瘴疠遍地之情形的反映。因此《贡章赋》也暗示了“贡象道路”的存在和它在明代中国与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朝贡活动和民间贸易中发挥的作用。
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一书指出:“明朝鼓励朝贡贸易,因此,明代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和周边国家的朝贡活动频繁,明廷要求沿途驿站官吏要给予周到的接待,朝廷也给予优厚的待遇……那些与云南驿道相连、方便畅通的对外通道上,贡使相望于道,逐渐发展为固定的贡道,或者‘贡象道路’为明代云南对外交通的一大特点。”②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96-197页。又指出:“除了进贡之外,这两条贡道还是云南出海的重要通道。两条贡道的目的地均在缅甸南部沿海的勃固地区,即摆古或白古,这是从唐代以来,云南利用缅甸沿海港口作海外贸易出海口最长时间的港口……正是这一地区海外贸易的吸引,云南商人把它当作了自己的出海口,因此,明代两条‘贡道’,自然都以摆古为终点,贡道也兼有商道的性质。”③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96-198页。
而明代“贡象道路”与清代时从缅甸进入中国的道路也有交叉,说明“贡象道路”在明代以后的中缅民间往来和朝贡贸易中仍旧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明末至清代滇西和缅甸之间的“腾越八关”所经路线中的“腾越”(腾冲)、“干崖”(瑞丽)、“陇川”(德宏州陇川县)④(清)王崧等纂,杜允中校注:《道光云南志抄》卷1,昆明:云南社会科学文献研究所,1995年,第28页。等地基本上包括了明代“贡象上路”的大致范围。而据《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一书的研究显示,清代南掌(老挝)驯象等物入贡中国,也是从普洱府入境,①李云泉:《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年,第118页。又与明代“贡象下路”所涉地区相一致。而云南境内一些地名、场所等也与“贡象道路”有关。以昆明为例,清檀萃《滇海虞衡志》等书就记载了昆明城东报国寺后园专门用于寄养缅甸等国所贡之象的“象房”②关于缅甸等国所贡之象入云南并寄养昆明等事,详见(清)檀萃《滇海虞衡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秦光玉《续云南备征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57页;罗养儒《云南掌故》,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93页。,昆明城区之“象眼街”等都反映出历史上“贡象道路”的繁荣。因此,《贡章赋》中“犀贝及鱼盐,杂沓来诸国。异服殊音类非一,市贸纷纷互重译。”的繁盛景象再次印证了明代时中国与缅甸等国繁荣的朝贡贸易以及民间贸易,“贡象道路”上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的兴盛对于促进国家统一,繁荣经济,密切外交关系和民间交流等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总之,“贡象道路”的存在和朝贡贸易的繁荣在政治、经济领域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也使得有关地名、贡物和历史事件等进入文人创作视野,产生了《贡章赋》这样反映朝贡等活动的作品。除《贡章赋》之外,明代以后反映与“贡象道路”上缅甸等国朝贡的诗歌、辞赋等作品也时有出现。如清朝吴振棫《贡象行》、沈家霦《缅甸国贡驯象赋》、劳孝兴《暹罗国贡驯象赋》等,虽旨趣各异,但均反映了与明代以来两条“贡象道路”上的朝贡活动有关的内容,它们和明代郭文《贡章赋》一同反映了与中国云南、缅甸、泰国等相邻地区有关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不断丰富着明清文学作品中朝贡题材的表现领域。
结 语
中国云南地区与缅甸自古以来在经济、文化和人员等诸多方面往来密切,特别是明代以来,随着明王朝在中国西南地区的统治不断深入,中国云南地区和以缅甸军民宣慰使司为代表的域外土司政权在各方面的往来也逐渐加深。除朝贡活动外,明清两代的中国与缅甸之间还发生了其他众多历史事件,明正统年间的麓川之战、明万历年间抗击缅甸侵扰滇西地区的战争、明末永历帝逃奔缅甸、清代乾隆年间征缅之役等均是其大者。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不仅影响着古代中国与缅甸之间历史发展的走势,也大大丰富了文学创作。除了郭文《贡章赋》等描写朝贡等活动的作品外,其他关于中国云南和缅甸的文学作品在明清两代还有不少,如明杨慎《宝井谣》和明陈用宾《罢采宝井疏》叙写开采孟密(今缅甸抹谷)宝石劳民伤财之事,尽显忧国之怀;明邓子龙《恤忠祠记》叙抗击缅甸侵略,保卫滇西疆土之事,忠烈之气满纸;明末何慰文之传奇《缅瓦十四片》叙永历帝狩缅之事,可歌可泣;清王昶《南往集》以诗题咏乾隆征缅之事,颇为详尽。这些作品和《贡章赋》一样,在明代云南地方文学乃至明清文学中形成了一个富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创作序列,皆是明清时期中缅、滇缅关系的缩影,具有独特的思想与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