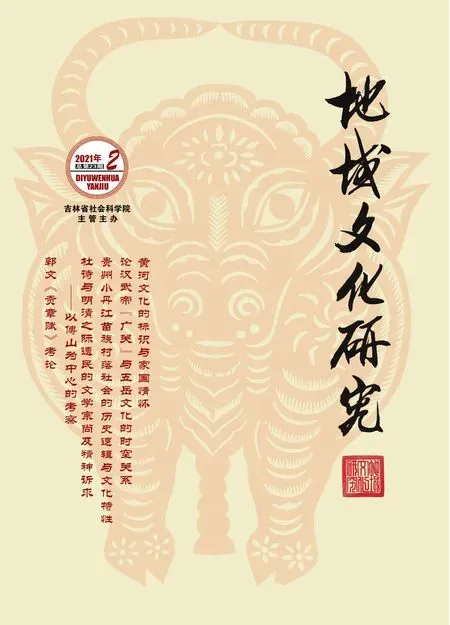陶渊明诗文中的地理空间书写
方立娟
按沈约《宋书》及萧统《陶渊明传》的说法,陶渊明是柴桑人①沈约《宋书》:“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寻阳柴桑人也。”参见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2511页;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认为陶渊明为“浔阳柴桑人也”,参见萧统著,俞绍初校注《昭明太子集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91页。,然而关于古柴桑的地点,目前还有一些争议,渊明故里,也有德安说、九江县说②2017年九江县改为九江市柴桑区。、星子县说③2016年,撤销星子县,设立了县级庐山市。、宜丰县说等说法,关于此,学术界的一些学者已有过不少研究,如夏汉宁的《陶渊明故里之争评述》,欧阳春与李宁宁的《靖节祠、明碑与德安的“陶渊明故里”》,王贤淼、吴国富的《陶潜墓、牛眠地与渊明故里》,钱志熙的著作《陶渊明经纬》等,本文对此不作赘述。不过在陶渊明流传的诗文中,存在着不少值得关注的地理空间,也不乏表示地理距离的文字,另外,其诗文中的地理空间呈现出一定的转移性特征。探究陶渊明诗文中的地理空间书写,便于进一步了解陶渊明的情感。
一、陶诗文中地理空间的现实性、想象性与记忆性
从主体空间的角度而言,在陶渊明诗文的地理空间中,有的是现实存在的并具有“在场”意义的空间,如《时运》中的“东郊”“庐”等,《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之“吾庐”“园中”等空间。还有一类空间具想象性与记忆性,《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言:“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①(晋)陶潜:《陶渊明集》,南宋刻递修本。本文所引陶诗文皆出自南宋刻递修本。“旧居”便是一个承载了诗人记忆的空间,还有诗人未必活动过,但通过阅读或是他人讲述等活动而留下记忆的空间,如《时运》中“延目中流,悠悠清沂”②“悠悠”字下,宋本注:“一作悠想”。的“清沂”,此处中的“悠悠”,又作“悠想”,但这不影响文字理解,从紧随其后的“童冠齐业,闲咏以归”来看,沂水便是一个记忆空间,诗人对沂水的记忆很可能主要来源于阅读。当然,现实空间与想象空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如《停云》中的“八表”,诗人极目望去,望向一个广阔的空间,这个空间从诗人现实所处地出发,向更远处延伸,然目力所限,人未必能看到事实意义上的“八表”,因而这个空间,其实也是现实与想象混合的空间。现实与想象之间、当下与记忆之间其实并没有特别明确的界限,有时在同一篇作品中,亦存在现实性与记忆性的融合。
在《时运》一诗中,诗人则展示了多个地理空间,这些空间有的具备想象性或记忆性,有的具备现实性。东郊和平泽就是现实存在的地理空间,诗人在暮春时着春装游玩东郊,复又望见涨满春水之景象,他在水边洗漱,远望,“挥兹一觞,陶然自乐”③“陶”字下,宋本注:“一作遥”。,继而诗人又言:“延目中流,悠悠清沂。童冠齐业,闲咏以归。我爱其静,寤寐交挥。但恨殊世,邈不可追。”诗人的目光开始从现实河流移向一个想象的且带有记忆性的空间——沂水。沂水虽说是一个客观存在之地,但诗人所望之沂水,是一个属于过去的地理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曾发生过“童冠齐业,闲咏以归”之事,《论语·先进》中曾晳有言:“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④杨伯骏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19页。陶渊明对于沂水的追想很可能出于以前的阅读记忆,也带有想象成分。
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一言:“四首始末回环,首言春,二三漱濯闲咏言游,终言息庐,此小始末也。前二首为欣,后二首为慨,此大始末也。”⑤(明)黄文焕:《陶诗析义》,福建巡抚采进本。然而若从地理空间的角度看,“欣”“慨”这样的心境需要空间承载,不可分开而论。东郊是诗人春游之地,他在游玩后又回归了栖居之地。“花药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横床,浊酒半壶。”不管是东郊或是庐,均为诗人现实活动之地带,“黄唐莫逮,慨独在余。”黄帝与尧的时代才能达到曾晳之志,而这样的时代已经不再,诗人的慨可以理解,可他在对虚拟空间的想象中,很难说没有“欣”的成分,现实空间中的诗人是自乐,过去空间中的人是群乐。这似乎又回应了序言中的“偶景独游,欣慨交心”⑥“景”字下,宋本注:“一作影”;“慨”字下,宋本注:“一作然”,据后文,应为“欣慨交心”。。空间中的现实性、想象性、记忆性相互融合,仿古人之风出游,在游玩中想象古人之风雅志气,这也可令人“欣”,而真实情况是诗人在独游。这种独游不仅仅停留在身体上,也是精神上的独游,这又如何不生“慨”呢?从地理空间角度分析,可以更真切地感受到诗人的欣慨交心。
在陶渊明的行旅诗中,可见现实性、想象性与记忆性的融合,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时来苟冥会,婉娈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渺渺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我行岂不遥,登陟千里余。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①“常”字下,宋本注:“一作恒”;“冥”字下,宋本注:“一作宜又作且”;“婉娈”字下,宋本注:“一作踠辔”;“园田”字下,宋本注:“一作田园”;“陟”字下,宋本注:“一作降”;“川途异”字下,宋本注:“一作修途永”;“初在襟”字下,宋本注:“一作在襟怀”。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诗人路过曲阿,即今天的江苏丹阳,这是一个现实的地理空间,然而诗人对这个现实地理空间描绘并不多,诗人反而提及了几个带有记忆性质的想象空间。“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此处园田也是诗人记忆中的地方,“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看着他乡情景,诗人却怀念过去生活的地方,充满了回忆色彩,“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班生庐”为用典,带有阅读记忆痕迹,又表示了诗人对于隐居的憧憬,园田、山泽居、班生庐与“渺渺孤舟逝”之现实景象相照应,在虚实交替中,诗人的仕隐矛盾也进一步凸显,然而在这首诗中,现实地理空间反而涉及较少,加之诗人自言“绵绵归思纡”,可知在此诗中其归隐之意要盛于出仕之意。
《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的“钱溪”也是一个现实的地理空间,也充满了回忆性。诗人言:“我不践斯境,岁月好已积。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诗人眼中的山川不仅仅是现实存在的,也是能唤起回忆的地方。“微雨洗高林,清颷矫云翮。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②“义风”字下,宋本注:“一作在义”。看似写眼前所见,然而联系起“事事悉如昔”来看,此番画面不仅仅限于诗人眼前所见,又跟诗人的回忆有联系。“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③“梦想”字下,宋本注:“一作想梦”;“析”字下,宋本注:“一作折”;“归”字下,宋本注:“一作壑”;“宜”字下,宋本注:“一作负”。这里的园田是诗人当下心心念念的园田,也可以是诗人记忆中的园田,诗句中充满了对过去的回忆,也有对当下生活的思考以及对未来回归故里的想象。另,《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中,也充满了现实性、记忆性与想象性。不管是现实中的规林,回忆中的旧居,极目望去似乎可以望见的家乡,正说明了诗人归意之深。这些也可知诗人对园田眷恋之深。
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也并非一个纯粹想象的空间。首先,桃花源有现实原型。“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历史上存在过因秦政逃亡之民。《史记》载:“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④(汉)司马迁著,韩兆琦评注:《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793页。又:“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⑤(汉)司马迁著,韩兆琦评注:《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795页。《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曾注:“时苦秦虐政,赋役烦多,故有逃亡辟吏。”⑥(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9页。避世之民的存在有现实原型,因避难而出现的桃花源带着历史记忆性,诗人有可能通过阅读、他人叙述等方式知晓因乱避世之事。当然这个空间也具有现实性,刘子骥为当时现实存在的人,而因乱世避世之现象在诗人生活的年代也较为常见。由此可见其现实性与记忆性的融合。
桃花源形式还比较特别,“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⑦“俨”字下,宋本注:“一作晏一作鱼”。他们村落的布局偏诗意化,也不用交税,是一个世外园林。“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⑧“长”字下,宋本注:“一作良”。可以说,在秦汉时期,要出现这样的农业聚落颇有难度。就算出现了这样的聚落,要想不被发现,也有难度。《奏谳书》载:“令曰:‘诸无名数者,皆令自占书名数,令到县道官,盈卅日,不自占书名数,皆耐为隶臣妾,锢,毋令以爵、赏免,舍匿者与同罪,以此当平。”①张家山二四七号汉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版),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97页。汉初统一后,朝廷又继续盘查人口,完善户籍制度。这样的村庄要延续数个朝代,诚非易事。因而桃花源的存在也具备了一定的想象性质。这又不是普通的想象,若把桃花源正文对桃源的描写跟《桃花源诗》中的“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②“蔽”字下,宋本注:“一作闭”;“尘嚣外”下,一作尘外地。联系起来,会发现桃花源既是人间,也是神界。这是陶渊明对现实的描绘,也是其精神对现实的超越。
现实性、想象性与记忆性的融合,让陶渊明诗文中的地理空间更加丰富,而这种文本性质的丰富,其实更多还是源于作者思想的深度与广度。
二、陶渊明诗文中的地理距离
陶渊明诗文中不乏表示地理距离的文字,如“千里”“万里”“数百步”等。这种跟地理距离有关的文字,可写实,也可表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理空间的范围,同时也连接着作者情感。陶渊明所处的时代,诗文中的“千里”和“万里”等也不怎么受声调约束,因而也更具探究的意义。
很多古人对于地理距离并非笼统概念,也有自己的衡量和认知。《淮南子·地形训》:“阖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水道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陆径三千里。禹乃使太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③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50页。徐凤先《中国文明早期对于大范围地理距离的认知》认为:“《尚书》中这些‘四海’的含义都是指‘由东南西北四个方面的大海围成的大陆的范围’,或者‘所有人民居住的范围’。按照现今的知识,因为今人从小受到的教育,很容易认为‘四海’是一个不具体的表示广大范围的概念,类似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说法。但是在中国文明发展中,‘四海’这个观念最初之所以能够形成,一定是建立在古人真实的知识基础之上的。在中国文明早期向东很容易看到大海,向南看到大海也不太难,但是向西、向北却不容易看到大海。如果不曾向西、向北走到海边,那么他们形成的大地的观念不应该是‘四海’,而是大地向东、向南连接着大海,向西是无边无尽的山脉和荒漠,直至与天相接。其实古文献中有类似的说法,如《淮南子·天文训》说‘天顷西北,地不满东南’。但是更早的文献中却反复提到‘四海’,并将‘四海’认作‘天下’的范围,这暗示着在中国文明早期,我们的祖先曾经真正向四个方向走到了大海的边缘。”④徐凤先:《中国文明早期对于大范围地理距离的认知》,《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第1期。综合一些古文献记载以及今人的一些研究来看,很多古人是有地理距离感的,这种地理距离的表述,也联系着作者的地理认知和文学情感。
陶渊明诗文中有一类词是直接表示地理距离的,如百里、千里、万里、数百步、数十步。这些有的接近实写,有的带有模糊虚化的性质。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他对于距离的感知跟实际情况比较贴近:“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渺渺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我行岂不遥,登陟千里余。”曲阿位于今江苏丹阳,《晋书》曰:“《司马法》广陈三代,曰:‘古者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①(唐)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66页。从江州到丹阳,当时路途崎岖,历经辗转,千里之余的距离应该比较符合实际,这样的距离书写也让作品中的地理空间变得更加直观。《酬丁柴桑》中的“秉直司聪,于惠百里”,这里的百里跟郡县实际管辖的范围比较接近,《晋书》:“县大率方百里,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②(唐)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67页。可知陶渊明对于地理距离是有一定认知的。
接近实写的地理距离可看出陶渊明对于地理距离有一定的认知,然而值得关注的还有虚化性质的距离,如《答庞参军并序》的“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③“通”字下,宋本注:“宋本作怀”。,情感未必可捉摸,而万里也未必是实体的概念,他强调了二人相隔地理距离之远,而心意相通。地理上的距离没有造成心理的距离,这样略带夸张的距离感,反而更加衬托了二人情谊之深。又如《桃花源记》的“夹岸数百步”“复行数十步”,数百和数十其实都是模糊的概念,两百和四百当然很不一样,三十和五十也不一样,在作者的设定中,行走者其实未必知道自己走了多少步,这增加了桃花源的神秘感。《拟古》九首其一“出门万里客,中道逢嘉友”,作客他乡,离家甚远,似万里之遥,而中途结交好友却有意外之感,这当然也超出了地理的界限感。文学中的“万里”“千里”其实模糊了读者对于当时实际地理距离的感知,而作者自身对此是否清楚,也未可知。作者即便清楚这其中的地理差距,却也并没有在作品中进行具体说明,只是以“万里”“千里”等词概述之,而这一类词,恰恰也对应着作者的一种心理上的地理距离感知。这种虚化性质的距离,更多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意识。
陶渊明在诗文中,有时不直接用数量词来表示地理距离,而是用形容词表达。如《己酉岁九月九日》中的“杳然天界高”④“杳”字下,宋本注:“一作遥”。之“杳然”,《拟古》中的“不怨道里长”之“长”等,《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一之的“地为罕人远”⑤“罕”字下,宋本注:“一作幽”。等,这些字词往往有着丰富的内涵。“远”“遥遥”等形容地理距离远近的字或词尤为值得关注。“远”在陶渊明诗文中有着丰富的意味。有的“远”,更多包含了地理距离相隔甚远,如《答庞参军》;四言诗:“依依旧楚,邈邈西云。之子之远,良话曷闻?”也有的远,跟作者内心世界的“远”相关,《酬刘柴桑》有“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⑥“日”字下,宋本注:“一作曰”。句,这里的远游跟行役中的那种“遥遥从羁役”不太一样,这其实可以参考渊明《饮酒》中的“心远地自偏”,这种远更多的是一种内心与世俗世界相距的远,内心世界的认知也可以决定地理距离的远近。《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的“地为罕人远”,这种远也并非行役之远,更多的是地处偏僻,人迹罕至。以陶渊明行役诗为例,“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遥遥”叠字,以示距离之远,这不仅仅是指实际地理之遥,也是诗人与理想家园的距离,“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哪怕换一种审美对象,作者的某种情绪依然无法消解,造成这种地理距离的原因之一便是出仕。“远”的距离较为模糊,而陶渊明诗文中有不少“遥”“遥遥”则表示地理距离之远,也含有一定的情感意蕴。
综上,这些形容地理距离之字词,有一类词是直接表示地理距离的,如百里、千里等,有的接近实写,反映了作者的地理认知,有的含有虚化性质,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意识。也有的不直接用数量词表示地理距离,而是用形容词表达,这些字词往往有着丰富的内涵。这种跟地理距离有关的文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理空间的范围,同时也连接着作者的情感。
三、陶渊明诗文中地理空间的转移
陶渊明诗文中的地理空间呈现出一定的转移性,这种转移性,丰富了陶渊明诗文中的地理距离表达,也影响着其诗文的情感意蕴。
一是陆地与空中之间的转移。如《九日闲居》并序,他在序言中说,“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①“持醪靡由”字后,宋本注:“一作时醪靡至”。此时诗人处于闲居状态,“园”是一个重要的地理空间,这个空间的活动范围似乎很有限。然而诗中却展现了开阔的场景:“露凄暄风息,气澈天象明。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②“澈”字后,宋本注:“一作清又作洁”;“往”字后,宋本注:“一作去”。这些景象从园中即可看见。夏天的风已经过去,秋露凄凉,空中一片澄澈,不见燕子飞过,却能听见大雁的鸣叫声。这样的描绘,不管是于视觉还是于听觉而言,似乎都得到了一种延伸,整个空间瞬间开阔了起来。这说明诗人虽闲居园中,但他对大自然季节性变化的感知非常敏锐,季节变化之快,与诗人闲居的状态形成了一种反差,闲居的人活动范围有限,而外面世界却如这大自然一般变化迅速,年华在不知不觉中流逝。因而诗人发出了“空视时运倾”之叹。恰逢重阳,秋菊开满了园子,诗人因贫穷无酒可饮,连可把握的当下也把握不了,更何谈他事。末尾以“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③“娱”字后,宋本注:“一作虞”。作结,对比“露凄暄风息,气澈天象明。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之情景,可见诗人此时闲居之苦闷。除《九月闲居》并序外,《己酉岁九月九日》《于王抚军座送客》等诗亦涉及地理空间范围从陆地延伸到天空的情况。
二是房屋内外之间的转移。如《归园田居》其二: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④“寡”字后,宋本注:“一作解”;“墟曲中”后,宋本注:“一作墟里人”;“草”后,宋本注:“一作衣”;“土”字后,宋本注:“一作志”。
诗人在此诗中叙述了他归隐后的一些日常生活,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地理空间,一是屋内,一是郊野。这两者之间并非分割开来,反而有着种种联系。“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道出了其房屋的周边环境,这样的环境也影响了其在屋内的感受,“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内外都达到了一种静的状态。享受独处的诗人,有时也会在乡野之地与人交流。“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这样的交谈没有杂言,非常淳朴,与静之境相衬,“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诗人担心自己的农作物遇霜凋零,这其实是一个耕种者的朴素愿望,其中有担忧也有期望,从郊野到屋内再到郊野,诗人的生活在一片静谧中循环,心性也澄静,远离俗世功名。这样两个地理空间之间的交替,底色是一致的,也可看出归隐后的诗人在一些日常生活中可以达到一种身心的静态。除《归园田居》其二外,《时运》《归园田居·怅恨独策还》《杂诗》其二等诗亦涉及地理空间在房屋内外之间转移的情况。
三是从相对范围小的空间转移到大空间等。如《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将圆。果菜始复生,惊鸟尚未还。中宵伫遥念,一盼周九天。总发抱孤念,奄出四十年。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仰想东户时,余粮宿中田。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①“急”字后,宋本注:“一作至”;“菜”字后,宋本注:“一作药”;“抱孤念”字后,宋本注:“一作诸孤念又作介”;“四”字后,宋本注:“一作门”;“有”字后,宋本注:“一作在”;“无所思”后,宋本注:“一作且无虑”。
“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夏日风急,诗人的住所突遭火灾,“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因房屋被毁,诗人只得寄居舟中。他转而却言:“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将圆。”月可照见原居住场所,也可照见舟与菜园,月的出现延伸了地理空间范围。“果菜始复生,惊鸟尚未还”,当果菜获得新生时,逃离的鸟尚未回来,鸟活动的范围也很广阔。“中宵伫遥念,一盼周九天”,诗人夜晚不眠,独立沉思,其思绪所能涉及的地理范围十分广阔,“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诗人在延伸的空间与拉长的时间里,回顾从前,心志仍坚。“仰想东户时,余粮宿中田。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在延伸的空间与时间中,诗人开始追念东户季子时代,那时路不拾遗,粮存田中,这样的时代跟诗人所处的乱世形成了强烈反差。也让他更加坚定了隐居田园的心念。
居住地遇火,生活遇到了一定的困难,诗人的思维却不仅限于眼前困境,他的田园不仅仅是被火烧毁重新恢复生机的田园,他的舟不仅仅是小小的暂时栖身之地,舟与田园有亭亭月照着,焚毁的居住地还在等待鸟的归来,由此可见其内心情感世界之丰富。夜晚沉思,也是“一盼周九天”,在延伸的时空中,他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局限。
陶渊明诗文的地理空间范围的转移,主要包括陆地与空中之间的转移,房屋内外的转移,还有从相对小的范围转移到大空间等情况。此外,还有特殊情况,如有的从当下空间往过去空间转移,如前面《时运》中对于清沂的追想,还有的从田园转移到山中,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禾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②“禾”字后,宋本注:“一作耒”。。通过地理空间的转移,也可看出陶渊明内心世界之广阔。
总之,陶渊明诗文中的地理空间值得关注,这些地理空间有的是现实地理空间,也有的具备想象性和记忆性。陶渊明诗文中一些表示地理距离的字,如“千里”“万里”“数百步”等,跟作者的地理认知和情感有关,丰富了其诗文中的地理空间。诗文中地理空间还具有转移性,通过地理空间的转移,也可以更好地理解陶渊明的内心世界。探索陶渊明诗文中的地理空间书写,便于了解陶渊明的创作情感,对陶渊明作品提供进一步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