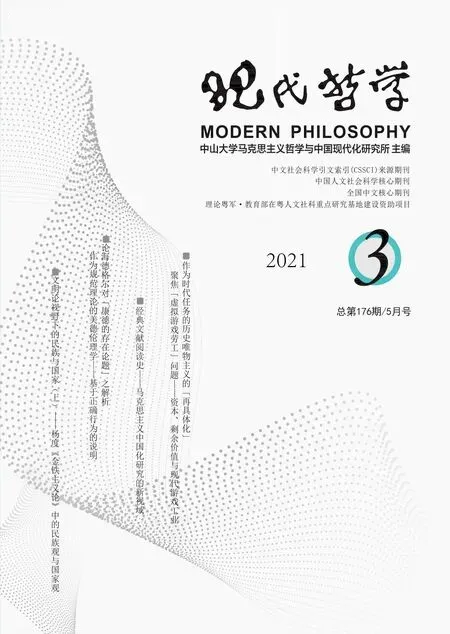二程及其弟子对邵雍先天易学之两极态度辨析
宋锡同
一、二程的学术背景及其易学特质
处于“经学变古时代”的北宋易学,其解经模式一反汉唐以来的训诂、注疏、严守师法、家法等路数,倾向以己意、新意解经,实则是继续沿袭“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易学旨趣来建构其时代之新儒学。其间,由于儒释道三教的合流,更兼道教的大发展,传统道教内部的易学图式越来越多地浮现于世,促使宋代易学在解经方式变化的同时,将汉代以来的象数易学模式转向图书易学模式。宋儒由此以发挥儒门“性与天道”的本体论问题,从而为被撼动的儒家名教重新确立基础。在这一背景下,邵雍的先天易学是以先天图式加元会运世的象数模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即以“先天”为本体,以“观物”为功夫的新儒学理论体系。可以说,邵雍的先天易学是宋代新儒学(即理学)、宋代新易学之典型代表。
与邵雍几乎同时的二程兄弟,其易学思想则不尽相同。二程延续王弼、孔颖达以来的玄学易模式,强调以象解易,阐发其内在义理,构建起以“天理”为本体、以“涵养须用敬”为功夫论,并强调以内圣外王为价值理想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在二程看来,象数、图式并非易学阐释与建构新儒学体系的必需,只要立足易象诠释、发挥义理即可,主张“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1)[宋]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河南程氏遗书》卷20,《二程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71页。以下所引《二程集》上下册均出自该版本,下不赘述。。在二程这里,象和数都不是第一位的,而在数之前的象也是在理之后。由此不难理解,与二程兄弟交往最为密切的邵雍,几欲将其先天象数学传于二程,但二程一边对先天易学大加褒赞,一边却流露诸多微词,明显不认同先天易学。究其原因,一是二程的学术倾向使然,二是二程对先天易学的误解或不解,三是先天易学庞杂的象数模式与不着文字的先天图式,确实使人难以进入其易学思想内核。
与此同时,程门弟子中却不乏对先天易学十分肯定者。事实上,无论二程还是程门弟子中对先天易学肯认者,他们都鲜有传承并发挥邵雍先天易学之人,更乏相关思想成果。可见,先天易学创立之初,似乎就已经预示了其此后流传过程所遭遇的两极态度。因此,正面阐发先天易学,为先天易学正名成为一种必需,而这一工作自然落到邵氏后学百源弟子肩上,其中邵雍之子邵伯温首当其冲。邵雍先天易学的流传,首先得力于邵伯温与百源后学的努力传承,尤其是邵伯温对其遗留的相关文本的整理、刊印。其中,邵伯温、王豫、张岷、牛氏父子以及术士等途径传播远及蜀地,不但在蜀地生根、开花,而且为先天易学后世的传承发展埋下“火种”。
在北宋五子中,与邵雍交游最厚的莫过于二程,《宋元学案·百源学案》也将二程与张载一起列为“百源学侣”,足见邵雍与二程关系非同一般。从双方易学思想渊源来看,似乎确有相关联处。例如,朱震《汉上易传表》曾指出当时象数易学的传承脉络:
陈抟以先天图传仲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是时,张载讲学于二程、邵雍之间,故雍著《皇极经世》之书,牧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敦颐作《通书》,程颐述《易传》,载造《太和》、《三两》等篇。或明其象,或论其数,或传其辞,或兼而明之,更唱迭和,相为表里。(2)[宋]朱震撰:《汉上易传表》,《汉上易传》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分册,经部[五]易类,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页。
这里关于周敦颐将太极图传二程之说,今天在二程的《程氏易传》中几乎看不到相关论述。但如朱震所述,周敦颐传承太极图、邵雍传承先天图、刘牧传承河图洛书之学,均接近于学术事实;而此中所述周敦颐或有传太极图于二程,但二程于太极图并无实质继承与发挥。这说明二程的思想特质与学术重心并不在象数上,而是局限于义理上以象释辞。在二程看来,理才是易之本质,理由象显,而数则不过是象的附随,得象不必细究象数,因此主张“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明理,因象以知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必欲穷象之隐微,尽数之毫忽,乃寻流逐末,术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务也”(3)《二程集》上册,第271页。。二程的《程氏易传》即是通过诠释《周易》经传以阐发其理学主张。无怪乎程门弟子尹焞说:“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传》。求先生之学,观此足矣。”(4)同上,第345页。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二程以象论易,确为宋以来儒家对易学阐释的一大特色,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克服了汉儒以繁杂象数解易且牵强附会的弊端。
二、二程对先天易学不甚看重
在二程之间,邵雍似乎更欣赏程颢,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中载有“康节尤喜明道”“康节所以处明道者盛矣”等句,并有诗《四贤吟》赞程颢为四贤之一。邵雍于临终前特嘱程颢为其作墓志铭,后者在《邵尧夫先生墓志铭》中称赞邵雍:“先生志豪力雄。阔步长趋,凌高历空。探幽索隐,曲畅旁通。在古或难,先生从容。有问有观,以饫以丰。天不慭遗,哲人之凶。”(5)同上,第502页。另一方面,通过程颢《定性书》不难看出,程颢主张“情顺万物而无情”(6)同上,第460页。,这一观点与邵雍先天学中的观物思想非常相近。可惜的是,二者在思想深处的这种一致性,并未在其现实交流中有更多互动,也鲜有更深层次的探讨。《邵氏闻见录》载,二程常从邵雍交游,并说“宗丞(程颢)为人清和,侍讲(程颐)为人严峻,每康节议论,宗丞心相契,若无所问,侍讲则时有往复”(7)[宋]邵伯温撰:《闻见录》卷15,第800页。。种种记载足见在二程中,程颢与邵雍的学术气质更相近。而面对程颐的拘谨和严肃,邵雍则希望他心胸更加开阔、学问更加活泼,并嘱以“面前路径须令宽,路窄则自无容身处”(8)[清]黄宗羲原本、黄百家篡辑、全祖望修定:《百源学案上》,《宋元学案》卷9,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第3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42页。以下所引各册均出自该版本,下不赘述。。
如前文所述,二程对邵雍先天易学不甚看重,并颇有微词。朱熹曾感慨程氏兄弟“甚不把(先天易学)当事”,并说“程先生有一柬说《先天图》甚有理,可试往听他就看。观其意,甚不把当事”(9)[宋]朱熹:《邵子之书》,《朱子语类》卷100,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345页。以下所引各册均出自该版本,下不赘述。。事实也确实如此,程颐以为象邵雍这样穷象数之隐微是在“寻流逐末”“术家之所尚”,如“张闳中以书问《易》之义,本起于数。程子答曰: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必欲穷象之隐微,尽数之毫忽,乃寻流逐末,术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务也。管辂、郭璞之徒是也。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见乎辞矣,则可由辞以 观象。故曰: 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并称“邵尧夫犹空中楼阁”(10)《二程集》上册,第271、97页。。朱熹对诸如此类视易之象数为“寻流逐末”“术家所尚”等评判大为不满,他立足于其“《易》本卜筮之书”的易学诠释立场,说“《易》本是卜筮之书,卦爻辞无所不包,看人如何用。程先生只说得一理”,又说“(伊川)《易传》言理甚备,象数却欠在”(11)《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6册,第2179、2217、2218页。另,朱熹屡屡提及“《易》本卜筮之书”“《易》本是卜筮之书”,仅《朱子语类》就有卷66、68等多处。。朱熹一方面表达程子将易学本身与卜筮割裂态度的不认同,另一方面则是在不满程氏仅就《易》理上理解、诠释易学,却于象数“欠在”。他说:“《易传》明白,无难看,但伊川以天下许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中,若作《易》看,即无意味。唯将来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用处。”(12)同上,第2216页。在朱熹眼里,程氏易学不但象数“欠在”,而且缺乏象数支撑而阐释出来的义理也“无意味”,他作《周易本义》某种程度上也有补《程氏易传》之偏的初衷。
相比程颐,程颢似乎对先天易学中的象数学有所发挥。如《宋元学案》载:“明道闻先生之数既久,甚熟。一日,因监试无事,以其说推算之,皆合。出谓先生曰:‘尧夫之数,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济事。’”(13)《黄宗羲全集》第3册,第570页。二程眼中的邵雍似乎已被披上术士色彩,其先天易学一开始即遇到如此误解。程颢也曾对其弟子说:“昨日从尧夫先生游,听其议论,振古之豪杰;惜其无所用于世。”(14)《二程集》上册,第673页。《宋元学案》又载,邵雍曾经想把易数传给二程,程颐却说:“某与尧夫同里巷居三十余年,世间事无所不问,惟未尝一字及数。”(15)《黄宗羲全集》第3册,第569页。程颢也说:“尧夫欲传数学于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学须是二十年工夫。尧夫初学于李挺之,师礼其严,虽在野店,饭必襕,坐必拜。欲学尧夫,亦必须如此。”(16)同上,第569页。在二程眼里,邵雍之数根本“无所用于世”,并认为秉持这样的象数易学观不过是“侮玩天理”,远离儒家抱持的修齐治平理念。“尧夫之学,先从理上推意,言象数,言天下之理,须出于四者,推到理处,曰‘我得此大者,则万事由我,无有不定。’然未必有术,要之亦难以治天下国家。其为人直是无礼不恭,惟是侮玩,虽天理亦为之侮玩。”(17)《二程集》上册,第45页。足见,在二程看来,邵雍的先天易学与他们自己体贴“天理”,即从传统易学诠释中推阐天理本体,力求明体达用的儒学旨趣迥异。这就不难理解二程为何对邵雍先天易学不感兴趣,其学术思想之旨趣并不在此。二程对先天易学这种不认可的态度也颇遭后人质疑,如清儒王植指出:“至《内外篇》,抉破先天不传之秘,虽伊川亦有所未及。而诸家之随文疏解,言之不得其意者,又何讥焉?”(18)[清]王植撰:《例言》,《皇极经世书解》卷前,《四库术数类丛书(三)》,上海:上海古籍社,1990年,第248页。
另一方面,二程不得不承认邵雍之学博大精深,故有赞邵雍之言:“张子厚、邵尧夫善自开大者也。”“尧夫道虽偏驳,然卷舒极熟,又能谨细心行。”“邵尧夫数法出于李挺之,至尧夫推数方及理。”“尧夫之学,先从理上推意,言象数,言天下之理。”“尧夫之学,大抵似扬雄,然亦不尽如之。”(19)《二程集》上册,第60、97、197、150页。另,《纂图指要》中蔡元定引程颐语:“伊川先生曰:数学至康节方及理,康节之数,先生未之学,至其本原则亦不出乎先生之说矣。”([明]胡广等撰:《皇极经世书二·纂图指要下》,《性理大全书》卷8,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0分册,子部[一六]儒家类,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84页。)难能可贵的是,二程看出先天学与扬雄太玄学多相似之处,这一话题也是后儒在论及邵雍先天易学时而常论及的(20)朱熹也说:“康节之学似扬子云。”张行成说:“先儒谓康节之数即《太元》数也。”李光地说“邵易似从《太玄》悟出”,又引程颢语说“先天生卦造图法全用《玄》”,将《皇极经世书》归源于太玄学,并指出伏羲六十四卦图也脱胎于太玄学。今人金生杨则对邵雍学术源于《太玄》作专门讨论。(《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7册,第3344页;[宋]张行成撰:《易通变》卷2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04分册,子部[一一〇]术数类,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03页;[清]李光地:《宋六子二》,《榕村语录》卷1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5分册,子部[三一]儒家类,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84页;金生杨:《邵雍学术渊源略论》,《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于此,清儒刘师培说:“盖邵子之学,虽由李挺之绍,陈抟之传,然师淑扬雄,则仍汉学之别派也。”(21)[清]刘师培撰、万仕国点校:《汉宋学术异同论》,《仪征刘申叔遗书》第3卷,扬州:广陵书社,2014年,第1597页。这即是认可邵雍先天易学仍不出汉儒之学脉。
对二程对先天易学的两可心态,宋儒毛璞认为他们对邵雍先天易学的赞誉实是出于尊重邵雍人品而“不言其所偏”,但这不代表他们认可先天易学。“尧夫得司马君实以尊其学,得程伯淳以志其墓,相与交推其所长,而不言其所偏,故世莫得而窥之。然伯淳兄弟亦有抑扬。”(22)[宋]冯椅撰:《厚斋易学》卷末《附录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分册,经部[一〇]易类,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42页。在毛璞看来,二程对先天易学的认可,其实是对邵雍人品的肯定,所以对先天易学只能“不言其偏”,言外之意只是“不言”而非“不知”(23)非但如此,毛璞在其所著十一卷《易传》中还认为,尧夫之学是筮法、术数之学,并认为世传先天易学乃后人假托,浅薄荒谬。足可见,对先天易学成见之深、之大。其评论见冯椅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厚斋易学》卷末《附录二》,“尧夫之筮,虞翻、管辂、郭璞之学也;尧夫之数,陆绩、赵实、李淳风之流也,独其人品高耳。若其精于数,则所深讳也,故避其名而自托于《易》,述《先天》之图,推卦变之说,衍《太玄》之象。邵氏既托之《易》,以自神其数。学者每神其数,而并信其《易》。世传邵氏《易》全解,殊浅谬,意后人假托耳。抑观子文所叙尧夫之学,盖自陈希夷。陈授穆、李,此数学也,而尧夫易学大抵专于论象,则托之象以隐其数尔。”这一评论虽然于先天易学有极大偏颇,但不难看出其时代人对先天易学的不同看法与复杂态度。([宋]冯椅撰:《厚斋易学》卷末《附录二》,第842页。)。邵雍试图将其先天易学传于二程(实应为大程),却遭到婉拒,而对那些人品不佳上门来求学者,邵雍却“求而不与”。对此,清儒黄百家评论说:“先生数学不待二程求而欲与之,及章惇、邢恕则求而不与,盖兢兢乎慎重其学,必慎重其人也。上蔡云:‘尧夫之数,邢七要学,尧夫不肯,曰:徒长奸雄,章惇不必言矣。’”(24)《黄宗羲全集》第3册,第570页。需要说明的是,此处黄百家所言的“求而不欲”,与邵伯温《易学辨惑》所述不同,《辨惑》中所言邵雍与章惇、邢和叔交好,但二人因自身原因未能深入从邵雍学习先天易学。相比之下,邵伯温所述更可信。
三、 程门弟子对先天易学的认可
尽管二程对先天易学颇多微词,但其门弟子中却不乏比较认可先天易学者。如程门弟子杨时对邵雍易学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他曾赞邵雍之学曰:“康节先天之学……非妙契天地之心,不足以知此。某盖尝玩之,而浅识陋闻,未足以扣其关键。”(25)[明]徐必达编撰:《邵子全书》卷24,日本内阁文库《浅草文库》所收藏明万历丙午年刊本。“《皇极》之书,解孔子所未言者,然其论古今治乱成败之变,若合节符,故不敢略之,恨未得其门而入耳。”(26)《黄宗羲全集》第3册,第570页。作为程门高足,杨时一边盛赞先天易学,一边感叹自己不得其门而入。同为程门弟子的尹焞也认为,时人视邵雍先天易学为“易数”,实是不知先天易学之“志在经论”本为“经世之学”。他评论说:“康节之学本是经世之学,今人但知其明易数,知未来事,却小了他学问。如陈叔易赞云‘先生之学,志在经论’,最为近之。”(27)[明]胡广等撰:《诸儒一·邵子》,《性理大全书》卷3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0分册,子部[一六]儒家类,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28页。当然,程门弟子对先天易学也有不认可者,如谢良佐坚持认为邵雍之学只是“术数”,“尧夫精易之术数,事物之成败始终,人之祸福修短,算得来无毫发差错……然二程不贵其术”(28)[明]胡广等撰:《诸儒一·邵子》,《性理大全书》卷39,第828页。。这种对先天易学的认知,同样透显了二程及其部分门人视先天易学为术数的观点。尹焞则指出,如果视邵雍之学为术数,实在是“小了他学问”且无见于先天易学的“经世”主旨。
作为程门四传弟子的朱熹,不满于二程易学偏于义理而疏于象数,进而藉由象数易学阐发先天易学。于此,日本学者吾妻重二评议说:“朱熹的先天易学几乎全面继承了邵雍的学说,而程颐却与朱熹相反,尽管他与邵雍关系近,但对邵雍的先天易学却几乎完全未曾予以关注。”(29)[日]吾妻重二:《朱子学的新研究——近世士大夫思想的展开》,傅锡洪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57页。这个评论可谓一语中的。首先,朱熹在易学阐释中兼顾象数与义理,通过融和二者,发挥象数易学来阐释宋儒太极观念下的天理本体,来为他建构理学体系服务。而邵雍的先天易学,正是得益于朱熹及其后学的大力阐发,才得以在南宋之后引起儒家后学的关注和探究。基于此,朱熹清醒地看到二程的洛学与邵雍的先天学之间的学术差异:“伊川之学,于大体上莹澈,于小节目上犹有疏处;康节能尽得物之变,却于大体上有未莹处。”“程、邵之学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节者至矣,盖以其信道不惑,不杂异端,班于温公、横渠之间,则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贬之也。”(30)同上,第574页。朱熹立足其理一分殊的理气观,调和易学象数与义理,自与二程视角不尽相同,但也侧面透出二程对先天易学的理解不尽认同,而后人由此贬斥先天易学更不可取。
而换个角度,恰是二程对以邵雍先天易学为代表的象数易学不甚关注,反而促使朱子对二程易学不满,进而弥补这个缺憾,即发挥象数易学、阐发邵氏先天易学。正如林忠军所论,“朱熹有感于程氏兄弟只言义理,不言象数,即发明图书之学和先天之学,从而图书之学与先天之学得以确认和流传。朱子后学蔡元定父子、胡方平父子、董楷、朱鉴等皆治朱子之学,象数学由此而兴盛发展……元代以俞琰、吴澄等为代表皆阐发朱子象数说,雷思齐、张理在总结了前人之学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见解”(31)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第2卷,济南:齐鲁书社,1998年,第129页。。可见,二程对象数易学的不屑以及对先天易学的不甚看重,促使其后学如朱熹在这一“疏漏”处大加发挥弥补。
综上,尽管二程及其部分弟子对先天易学不甚认同,甚至视之为“术数”之学而轻视之,但程门弟子中不乏有对邵雍先天易学有确实理解并欣赏者如杨时、尹焞等人。但仅就二程与其门弟子所处时代而言,程门部分弟子对先天易学的这种认知仅体现在认可、褒赞程度上,并未予以实际继承或发挥,至于朱熹、蔡元定等程门后学的发挥已经是南宋时代的问题。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先天易学之复杂性让人难得其门而入。这一问题从侧面反映出二程与其门弟子之间对先天易学的看法已趋两极,而难有一致意见。这已经体现出邵雍先天易学流传过程中的两个大问题:一是被误解、误读,甚至被视为“术数”而遭贬斥,而忽略其“经世治乱”之主旨;二是先天之学因其庞大驳杂的形式,更使人难以得其门而入。而让先天易学的真实面目凸显出来、驳正对先天易学的种种误解、为先天易学正名等任务,首先自然落到邵伯温等百源后学的肩上,继而又有张行成以及朱熹、蔡元定等人对先天易学的注解与发挥,使邵雍先天易学再放异彩(32)据实而论,程氏兄弟尽管与邵雍为邻三十载,实并不懂其先天易学之精微。如,邵雍论大衍之数对“不用之一”问题的讨论,实则是指先后天时间之“时差”,是“并其余分”而已。但二程却认为,“‘大衍之数五十’,数起于一,备于五,小衍之而成十,大衍之则为五十。五十,数之成也。成则不动,故损一以为用”。此处“大衍之数五十”中的“不用之一”,被理解为“成则不用,故损一以为用”,这种解释实在太过牵强。一则为什么“成则不用”?二则何故“损一以为用”?这个“损一”究竟该如何用?诸如此类问题,都没做出进一步的解释。而这种理解离邵雍先天易学之易数本义实在太远。此处之“一”,应是先天与后天之间的“时差”之“一”。仅此一点,足见二程对邵雍先天易学尤其象数之学并未透彻理解。当然,学术史上对此一问题的争论与误解历来多有,此一问题有待更深入地展开探讨,此处意在指出二程对邵雍先天易学尤其数论真正的深入理解并不多,至于传承则更无从谈起,尽管二程表面上对邵雍先天易学褒赞有加,实则一无兴趣、二没深解。(《二程集》下册,第10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