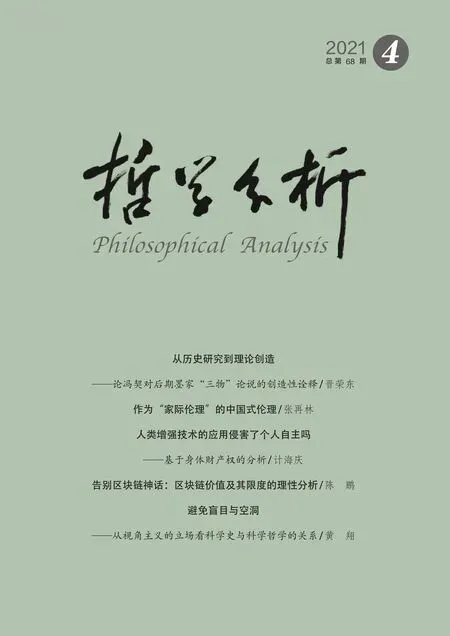拉姆齐、实用主义和维也纳学圈a
[美]谢丽尔·米萨克/文 许振旭/译 张晓川/校
一、拉姆齐的名声
常有人认为,弗兰克·拉姆齐站在维也纳学圈这一边。他在维也纳学圈1929年的“宣言”中被列为“同情”学圈立场的人。bRudolf Carnap,Hans Hahn &Otto Neurath,“The Scientific Conception of the World:The Vienna Circle”,in Marie Neurath &Robert S.Cohen(eds.),Empiricism and Sociology,Dordrecht:D.Reidel,[1973(1929)],p.318.或许可以说,出现在这份“宣言”上并不重要——名单中的不少成员也并不事先知情或同意,而且“宣言”这份材料哪怕在学圈内部也是有争议的。但“拉姆齐同意学圈的立场”这个观点不只是出现于学圈的官方宣告。20 世纪50 年代,卡尔纳普和亨佩尔认为《理论》(Theories)一文——该文发表于拉姆齐去世后的1931 年——对他们从观察和逻辑中建构科学理论的工作极具贡献。当代学者汉斯—约翰·格洛克(Hans-Johann Glock)提出,拉姆齐是剑桥分析派中“杰出的”一员,他抱有与维也纳学圈和维特根斯坦相同的观点:“简单命题只能以这种方式出现在复杂命题中:复杂命题的真值完全取决于简单命题的真值。”格洛克认为,与罗素不成熟的尝试和卡尔纳普在《世界的逻辑构造》中的英勇努力一样,剑桥分析派试图把一切有意义的命题还原为指向感觉材料的基本命题的构造,但此举徒劳无功。aHans-Johann Glock,“The Development of Analytic Philosophy:Wittgenstein and After”,in Dermot Moran(ed.),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wentieth Century Philosophy,London:Routledge,2008,pp.80—81.
造成“拉姆齐与维也纳学圈立场相同”这种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拉姆齐与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关联。维特根斯坦的传记作者雷·蒙克(Ray Monk)说,拉姆齐“无法跟上(维特根斯坦)彻底脱离《逻辑哲学论》中理论的努力”。他还暗示,拉姆齐可能就是维特根斯坦在1929 年的日记中记录的那场梦中的“愚人”b蒙克还认为,维特根斯坦也可能认为他自己才是那个对坏掉的机器修修补补的人。:
今早我梦见:很久之前,我委托某个人为我做一个水轮。现在我不想要了,可那个人还在做。水轮放在那里,做得很糟;它身上遍布槽口,可能是为了把轮页放进去(就像汽轮机的马达那样)。他向我解释这是何等累人的活,而我想,我已经订购了一副桨轮,制作桨轮会比较简单。这个人蠢到我没法跟他解释,也没法让他做出更好的水轮,而我除了让他继续做下去也别无他法。一想到这些我就十分难受。我想,我不得不和那些我没法使之理解我的人一起生活。我确实经常有这种想法。同时还伴有这种感觉——这都是我自己的错。cRay Monk,Ludwig Wittgenstein:The Duty of Genius,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0,p.276.
尽管维特根斯坦从未觉得自己属于维也纳学圈,但他确实从1929 年到20 世纪30 年代中期与他们有过持续的往来。不仅如此,他很快就指控魏斯曼和卡尔纳普抄袭他的思想。维特根斯坦曾经与维也纳学圈一样,试图把一切有意义的语言还原为基本语言,也就是与世界中的简单客体挂钩的那些简单而基本的陈述。维也纳学圈把《逻辑哲学论》当作“新哲学”作品中“最深刻也最正确的”的一部。dMoritz Schlick,“Letter to Albert Einstein”,July 14,1927,Einstein Collection,Hebrew University,EC 21—599,1927.
在维特根斯坦做的梦和维也纳学圈引他为同道的声明不久之后,拉姆齐在1930年1 月去世。他才26 岁,却永远失去了发展和总结他的工作、仔细梳理他与他工作于其中的种种传统之关联的机会。把他的工作拼合、整理起来的任务,只能留给他人来完成了。事实上,拉姆齐的立场与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圈不同,因为他认为:把一切有意义的命题还原为经验和逻辑的初始语言是不可能做到的。他并不支持维也纳学圈的立场;相反,他自称实用主义者。他自始至终都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批评关于意义和真理的“图画论”。这种批评也促使维特根斯坦从他的《逻辑哲学论》转向他的后期立场,也就是把重点转向实践的首要地位以及意义在于用法的观点。a关于拉姆齐对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参见Cheryl Misak,Cambridge Pragmatism:From Peirce and James to Ramsey and Wittgenstei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以 及Cheryl Misak,Frank Ramsey:A Sheer Excess of Powe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0。不仅如此,拉姆齐过世之后,他的批评还使得维也纳学圈的某些成员摆脱他们自己的立场。
拉姆齐当然与维也纳学圈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处,例如他们都对数学的基础、命题和实在的关系感兴趣,也都有逻辑方法上的才能。他有兴趣跟他们讨论哲学,这并不令人意外。b拉姆齐在1928 年春给石里克写信:“我想差不多现在就动身前往维也纳,而且我想问,如果我去了,你或者你的组员有没有空陪我聊聊哲学。如果你有这个时间的话,我会万分感激,因为我在剑桥这里几乎得不到什么刺激,也没取得多少进步。(The Vienna Circle Archive,Noord-Hollands Archief:114-Ram-2.)石里克在拉姆齐提议的那段时间正好不在维也纳,但他邀请拉姆齐在别的时候到访和逗留。他们的问题也是他自己的问题,即便他并不同意他们的解法。而且拉姆齐其实在一开始就参与了维特根斯坦的计划(project),并试图改善其中的某些方面。c例如,他在1925 年写作的《共相》(Universals)一文就是对维特根斯坦关于我们不能先验地确定逻辑形式这个立场的延伸和深化。对此精彩的讨论,参见Fraser MacBride,On the Genealogy of Universals:The Metaphysical Origins of Analytic Philosoph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但即便在他还是个本科生的时候,也就是早在1923 年,他就主张初始语言或基本语言不足以解释种类浩繁的、合法而适真(truth-apt)的信念。我们将会看到,尽管拉姆齐确实影响了维也纳学圈,但他最终会反对而非支持他们的计划。
二、向维也纳学圈介绍《逻辑哲学论》
1921 年,18 岁的拉姆齐受出版家C.K.奥格登之托翻译维特根斯坦在“一战”期间完成的手稿。罗素和凯恩斯想方设法把它带出了饱受战乱之苦的欧洲,并且在桃乐丝·林奇(Dorothy Wrinch)的帮助下将其付印。但这一版本不仅充满错误,而且也没有经过作者的任何修订。它最初发表在《自然哲学年鉴》(Annalen der Naturphilosophie)这个德国期刊上。维特根斯坦很想出一个英文版。拉姆齐精通逻辑学,熟悉罗素的哲学,而且很乐意完成这份工作。1921 年年底,他来到帕特小姐的秘书办事处,直接开始读晦涩难解的年鉴版《逻辑哲学论》打字稿。他向一个速写员念出他的翻译,速写员再把文字整理出来。经过大量通信以及维特根斯坦对自己的想法和翻译的修改,拉姆齐的《逻辑哲学论》译本在1922 年出版了一个德英双语版。奥格登抢走了翻译的功劳,仅仅提了一句“感谢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F.P.拉姆齐先生在本书的翻译和付印准备上的帮助”aLudwig Wittgenstein,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C.K.Ogden(trans.),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22.。然而,当时的人都觉得,完成了这份工作的那个人非拉姆齐莫属。b参见Cheryl Misak,Frank Ramsey:A Sheer Excess of Powe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0。
1923 年9 月,拉姆齐来到维也纳附近的一个小镇,维特根斯坦在那里的小学教书。这两人终于碰面了。他们每天花上五个小时逐字逐句读《逻辑哲学论》,一连读了两个星期。在那时候,拉姆齐是唯一真正读懂《逻辑哲学论》的人(此前维特根斯坦曾宣称,摩尔、罗素和弗雷格都未能理解他的思想)。拉姆齐对此书的评议已准备在《心灵》杂志(Mind)上发表。与维特根斯坦的马拉松式的对话期间,他松了一口气,因为他发现他仍然认为评议中的观点大致是对的。
在1924 年的3 月,拉姆齐前往维也纳停留6 个月,不仅为了得到精神分析治疗,也是为了能有更多时间与维特根斯坦聊天。维特根斯坦的姐姐格雷特尔·斯通伯勒把拉姆齐介绍给了石里克。拉姆齐对石里克的印象终身不变:“我觉得他不大像是个哲学家,而是一个非常友善的人。”cKing’s College Archive FPR 5/5/434.在1927 年的七月,拉姆齐会邀请石里克在道德科学俱乐部宣读一篇论文,即《认知的意义》。石里克的妻子也陪他一起去了剑桥,他们与拉姆齐一家相处非常融洽。剑桥数学家麦克斯·纽曼当时也在维也纳,他把拉姆齐介绍给汉斯·哈恩。哈恩为拉姆齐安排了使用学校图书馆的许可,并且邀请他参加复变函数论的研讨班。拉姆齐未能参加哈恩的研讨会,但他确实感到遗憾——明年他就不在维也纳了,而那时哈恩会开设关于罗素和怀特海的《数学原理》的研讨班。
正是在拉姆齐1924 年的这次访问期间,即将成形的维也纳学圈(以及柏林学圈)正式接触了《逻辑哲学论》。d克里斯托弗·林贝克—利利努提示了我这个故事。1923 年,卡尔纳普在纽约从一些数学家那里得知罗素对新兴的“数理哲学”的影响。卡尔纳普写信给赖欣巴哈,告诉他哪些人与这种新兴哲学有关。这个名单很长。其中包括维特根斯坦、凯恩斯和布罗德,但并未赋予维特根斯坦特别的重要性。赖欣巴哈立即把卡尔纳普的信转交给了石里克,并且让石里克写信给罗素(未提到维特根斯坦),询问他是否有兴趣在他们正在筹划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然后石里克写信给赖欣巴哈,提到那些新数理哲学家之一就在附近:“维特根斯坦住在维也纳附近,他的书是由罗素编辑的。”eArchives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University of Pittsburgh,Han Reichenbach Collection:ASP/ HR-016-42-16.看起来,石里克还没有得到经过修订并且翻译为英文的《逻辑哲学论》副本,因为他不知道罗素其实并不是这本书的编辑,只是给这本书写了导言。他的大学图书馆有一册常见的年鉴版《逻辑哲学论》,但我们并不清楚,1923 年石里克在写这些信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翻看过此书。
1924 年夏天,这一切都会改变,因为石里克遇见了拉姆齐。石里克在8 月5 日写信给赖欣巴哈。他不仅提到了维特根斯坦,而且对他抱有殷切的期盼。那时候他已经读了年鉴版《逻辑哲学 论》:
你听说过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吗?此书发表于《自然哲学年鉴》,并且已经由罗素编辑成德英双语版专著。作者就住在维也纳附近,他的思想富有原创性,为人也特立独行;对他的专著研读越深,越会为之惊叹。英译者是来自剑桥的一位数学家,我在这个夏天刚和他见过面。他有着极为聪明而精密的头脑。aArchives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University of Pittsburgh,Han Reichenbach Collection:ASP/ HR-016-42-16.
石里克在圣诞节的时候写信给维特根斯坦,表达了他对《逻辑哲学论》的崇拜和他面见此书作者的渴望。他还告诉维特根斯坦,数学家库尔特·赖德迈斯特(Kurt Reidemeister)最近在维也纳大学作了一个关于《逻辑哲学论》的讲座,并且提到“去年夏天拉姆齐先生——也就是你的著作的译者——来维也纳小住,我有幸和他见了面。”bWittgenstein Collection,Brenner Archive:M31.石里克问维特根斯坦,他跟赖德迈斯特是否能为自己买到一本《逻辑哲学论》。维特根斯坦回信说,他自己也没有样书,但拉姆齐“肯定会很乐意帮你们弄到几本”cVienna Circle Archives,Noord-Hollands Archief:123/Wittg-1.。1925 年初,维也纳学圈得到了拉姆齐的译本。
维也纳学圈开始仔细阅读《逻辑哲学论》,一直读到1927 年,视之为其哲学运动的奠基性文本。尽管学圈内部观点各异,但至少可以说,他们与维特根斯坦的不同在于:他们明确表示,基本陈述是观察性陈述,而维特根斯坦在这方面含糊其辞。维也纳学圈也忽视了维特根斯坦坚持的一个主张:伦理和宗教没有意义(sense),但要比有意义的命题更为重要。尽管存在这些分歧,维也纳学圈还是合情合理地把维特根斯坦看作他们的同道。维特根斯坦的一个洞见尤其重要——逻辑真理是重言式。它们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为真,也因此免受有意义性的经验标准的检验。1924 年,他们对拉姆齐的兴趣很大程度上与这一点有关。
三、数学和逻辑之为重言式
在维也纳的时候,拉姆齐以《数学的基础》为题完成了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并于1925 年发表在《伦敦数学学会会刊》。他在论文中试图修正《数学原理》的“缺陷”。当时的拉姆齐认同罗素的逻辑主义计划,他的论文大部分篇幅都在试图修补罗素对逻辑主义的致命问题——集合论悖论——的解决方案。他主张对罗素的类型论作一些修正,而修正后的理论将不再需要可归约性公理。
维也纳学圈热衷于接受新思想,尤其是来自剑桥的思想。当时,他们已经读完了《数学原理》和《逻辑哲学论》。《数学的基础》为他们提供了下一个讨论题材。拉姆齐在这篇文章发表后把它寄给了石里克,并且在首页上写了“作者敬赠”。卡尔纳普抄录了其中一部分,石里克则在他的副本上写满了评论。我们能从卡尔纳普的日记中看到,在1927 年1 月维也纳学圈花了两周时间讨论这篇文章,后来的讨论断断续续地持续到1929 年。一月份的记录条目中写道:“魏斯曼跟我们说起拉姆齐的这篇文章。”下一周的条目写道:“我们讨论了维特根斯坦和拉姆齐,非常有趣。”aArchives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University of Pittsburgh:Rudolf Carnap Collection 025-72-06 42-01:68,769.
他们感到特别有趣的是拉姆齐对维特根斯坦的重言式观念的拓展。如同所有的经验主义者一样,维也纳学圈成员很难说明,为什么逻辑和数学的陈述是合法的。毕竟,它们并不满足他们提出的有意义性的可观察性标准。休谟援引了一个太过省事的事实与观念关系的区分:对观念关系的陈述(包括数学和逻辑陈述)可以免受可观察性标准的检验。密尔试图把数学视作可观察的科学,但并不成功。维也纳学圈很高兴能在《逻辑哲学论》中找到他们的问题的部分解答。逻辑真理符合世界的一切状态。因此,它们对世界并不作出任何断言,也因此不必通过世界得到证实。那么数学真理呢?维特根斯坦主张,数学概念由纯粹句法上的或者形式上的等式构成。他认为数学概念没有意义(sense),但这和逻辑没有意义的方式不同。
拉姆齐主张,维特根斯坦的立场“显然是一种狭隘到不可思议的数学观”,因为它只适用于简单的算术。bFrank P.Ramsey,“The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Proceedings of the London Mathematical Society,s2—25/1,1926,pp.338—384.Reprinted in Ramsey,Philosophical Papers,David Hugh Mellor(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164—224,p.180.以下引文简写为 FM。拉姆齐认为,数学真理和逻辑真理一样都是重言式。罗素想要基于一些初始原理(primitive principles)建立整个数学大厦,而拉姆齐认为,罗素完成这个任务的方式应该是把逻辑和数学的初始命题都看作重言式,使得任何建立其上的东西都必然为真。
就维也纳学圈来说,这两步——首先是数学,其次是逻辑,被视为重言式——是哲学上的根本转折点。a参见 Rudolf Carnap,Hans Hahn &Otto Neurath,“The Scientific Conception of the World:The Vienna Circle”,pp.299—318。哈恩的表述尤其清楚,“重言性”这一特征对数学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这个论点能站得住脚的话……那么数学的存在就和经验主义的立场相容了。”bHans Hahn,“Discussion about the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in Brian McGuinness(ed.),Empiricism,Logic and Mathematics,Vienna Circle Collection,Vol.XIII,Dordrecht:Springer,1980(1931),p.34.拉姆齐给维也纳学圈的一个难题指出了一条不错的出路。
四、拉姆齐和维特根斯坦关于同一性的争论
维特根斯坦本人则坚决反对拉姆齐的这个提议。他的抗拒表现在他和拉姆齐关于同一性陈述的本质的争论。这场争论也波及维也纳学圈,这群人至少在这个戏剧性事件中扮演了一些次要角色。1927 年6 月20 日,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和魏斯曼在石里克家中相聚。这也是卡尔纳普第一次见到维特根斯坦。他们讨论了拉姆齐的论文。维特根斯坦对其中的同一性解释提出了一个反驳。卡尔纳普后来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维特根斯坦十分有趣,富有原创性。但他认为,维特根斯坦对拉姆齐的反驳近似于:首先站定一种草率而冲动的立场,然后试图为这种评价寻找论证。一周之后,也就是27 日,他们又聚了一次,这次是在卡尔纳普家。在这场第二次聚会上,维特根斯坦向石里克口述了一封信,让他转交给拉姆齐。(当时维特根斯坦对拉姆齐报以沉默,因为他们在1925 年就弗洛伊德的价值这个问题有过争论。)卡尔纳普打出了这封信,然后维特根斯坦手写了开头和结尾。他这封信写给“尊敬的拉姆齐先生”,信中要求拉姆齐先生回应关于逻辑的这一要点,但不要直接回复给他本人,而是经由石里克转达。c此 信 发 布 在Brian McGuinness(ed.),Wittgenstein in Cambridge:Letters and Documents 1911—1951,Oxford:Blackwell,2012,pp.158—161。
拉姆齐考虑过不答应维特根斯坦只把回信写给石里克的要求。他写了两份给维特根斯坦本人的答复稿本,说石里克“不会明白我的回答到底有何妙处”。他还说,石里克1918 年的《普通知识论》(Allgemeine Erkenntnislehre)里边有一些“可悲的胡说八道”,但他愿意考虑“石里克已经比当时变得聪明一些了”这种可能性。最后,他还是顺从了这位难以相处的朋友,把他的答复寄给了石里克。
维特根斯坦认为,同一性陈述是数学的一部分,所以也是由“等式”(equations)构成的,并且也“因此是伪命题”。拉姆齐认为,同一性陈述是真的,但只是平凡为真——因为它们是重言式。a拉姆齐自己的解释是否令人满意还并不清楚。为了让数学成为一系列重言式,他引入了一系列实体,以保证在这些实体为真的情况下,“a=b”在任何解释中都能为真。但这些实体的引入使得重言式完全不像是那种单纯的、平凡为真的重言式,即维特根斯坦认为构成逻辑的那种重言式。这种辩论总共也就在两封信中完成,并且很快就不了了之。在《数学的基础》发表之后,拉姆齐立即对它表示了怀疑。在1929 年,他将放弃逻辑主义的计划,开始积极探索直觉主义。他在1929 年的8 月写了两条长篇笔记,“有穷主义数学的原则”和“直觉主义数学的形式结构”。他在其中支持了魏尔的引入规则(Weyl’s introduction rules),最终落脚于他自己的替换规则(substitution rules)。b参见Archives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University of Pittsburgh:1983.01:006-06-1;1983.01:006-06-07。维特根斯坦在1929 年1 月回到剑桥,他在当时也对直觉主义感兴趣。两人都对拉姆齐在《数学的基础》中称作“布劳威尔和魏尔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威胁”(FM:219)感兴趣。1931 年,布雷斯韦特出版了拉姆齐的文集,并在导言中警示:拉姆齐已经放弃了逻辑主义,转投直觉主义。这让罗素大为惊讶。cBertrand Russell,“Critical Notice of The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 and Other Logical Essays,Frank Plumpton Ramsey”,Mind,Vol.40,No.160,1931,p.477.
同样在1931 年,卡尔纳普似乎尚未读过布雷斯韦特的导言,但他对拉姆齐的逻辑主义提出了一种担忧。d到底卡尔纳普在什么时候得到布雷斯韦特的编著还不清楚,但有证据表明这不会是在文集出版的很多年之后。上面有卡尔纳普年轻时候大量的评论和注释,另一些注释是在他晚年的时候写的,中间的间隔如此之长,以至于20 世纪50 年代的卡尔纳普已经忘记里边写了什么。参见Cheryl Misak,Frank Ramsey:A Sheer Excess of Powers。他说,拉姆齐在罗素的问题解答过程中作出了英勇的尝试,试图论证集合论悖论中的循环是无害的而非恶性的。卡尔纳普认为拉姆齐的解法“无疑具备吸引力”,但“我们不应该屈服于这种诱惑”。它带有太多这类腔调,似乎存在“一个柏拉图式的观念领域,其中那些观念的存在无关乎有限的人类能否思考它们以及如何思考它们”。卡尔纳普说,既然直觉主义曾被称作“人类学式的数学”,那么拉姆齐的逻辑主义理论大可以被称作“神学式的数学”eRudolf Carnap,“The Logicist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rkenntnis,reprinted in Paul Benacerraf &Hilary Putnam(ed.),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Selected Readings,2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1931),p.39.。拉姆齐关于直觉主义的笔记迟至1991 年才得以出版f参见157 页注b。,维也纳学圈因此从未注意到拉姆齐已经摆脱了作为重言式的数学观,那种对他们来说如此有用的数学观。
五、“事实和命题”
尽管拉姆齐摆脱了逻辑主义这一点在他身后才被注意到,他不认同学圈立场的证据还是可以从一篇学圈在他在世之时读过的论文中找到。这些证据出现在一篇维也纳学圈也读过的文章里。《事实和命题》于1927 年发表在《亚里士多德学会会刊》。维也纳学圈的宣言提到了这篇文章,认为它是拉姆齐同情学圈立场的几篇文章之一。拉姆齐在其中以新的方式使用了维特根斯坦的重言式观念。维特根斯坦曾认为(据拉姆齐说)“逻辑真理不排除可能性,因此不表达信念”(FP:47)。拉姆齐从这个观念出发,得出了他最有成果的洞见。信念排除可能性,并且这是我们得以(1)个体化信念,和(2)度量部分信念(partial belief)的方式。相信一个命题很大程度上在于以某种方式行事,并把种种可能性看作存在或不存在。这种实用主义立场认为,信念本质上对我们的行为具有因果作用。
在这篇文章中,拉姆齐关于真理作了一个被很多人误解为“紧缩”理论或“冗余”理论的评论。根据这些理论,“真理”这个说法是一种多余的附加,可以被直接省去——并没有单独的真理问题,有的只不过是一种语言上的混乱罢了……“凯撒被谋杀了,这是真的”的意思不过是凯撒被谋杀了,“凯撒被谋杀了,这是假的”的意思不过是凯撒没有被谋杀……aFrank P.Ramsey,“Facts and Propositions”,reprinted in Ramsey,Philosophical Papers,p.38.以下因为简写为 FP,并以冒号间隔标出页码。
但拉姆齐认为,一旦你用这种方式表述这个议题,那么有一点就变得清楚无疑——信念、判断或断言的本质才是有趣的问题。他在那句紧缩主义的评论之前说,我们应该首先简短讨论一下真理,“接下来再对判断进行分析”;而在整个讨论的结尾他得出结论说,如果我们已经分析了判断,那么“我们就已经解决了真理问题”(FP:39)。诚然,对命题p 的真值的断言等于对p 的断言。但这种看法丝毫未触及仍然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工作。在紧缩主义的操作之后必须接着展开对信念、判断和断言的考察,而只有这种考察才能为我们带来一种完整的真理理论。
拉姆齐进而展开了他的实用主义式的考察。他认为,信念所关涉的是习惯或行为的倾向。信念不能还原成行为,因为信念还涉及精神因素。除此之外,客观因素也需要被考虑在内。如果一只鸡“相信”某只毛毛虫有毒,那么它就不会吃这种毛毛虫,因为吃了就会带来不舒服的体验:
这样一个信念中的精神因素是鸡的行为的某些部分,这些部分以某种方式关联于客观因素,即毛毛虫的种类及其毒性。对这种关系作出精确的分析会十分困难,但我们可以认为,就这类信念来说,实用主义的观点会是对的。也就是说,鸡的行为和客观因素的关系在于,这些行为具有某种特性,而这种特性使得当且仅当毛毛虫确实有毒时,这些行为才是有用的行为。(FP:40)
在这段文字中,拉姆齐近于接受某种实用主义的真理解释。如果信念导向行为的成功,那么它就是真信念。但对他这种实用主义来说重要的是,行为的成功必须系于信念与相关的客观因素以正确的方式关联起来。a不论他是否进而采纳一种实用主义的真理解释,他确实能采纳一种实用主义的意义或内容的解释。根据这种解释,等价的信念有相同的“因果属性”。(FP:44)《事实和命题》一文因此是拉姆齐对主张符合论的逻辑分析理论的公开拒绝,而这种理论对摩尔、罗素、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圈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在这一阶段,他觉得维特根斯坦可以轻易加入他的阵营。他在文章的结尾处写道:
最后,我必须强调我对维特根斯坦先生的谢意。我对逻辑的观点是从他的观点发展而来的。我所说的一切都归功于他,除了那些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部分。在我看来,他的体系中的空隙需要由这些部分来填补。(FP:51)
维特根斯坦并不认为实用主义的提议是一种友善的修正,而维也纳学圈也对《事实和命题》中的实用主义要旨敷衍了事。如果他们喜欢这篇文章是因为其中的紧缩主义的真理观,那么他们就误读了这篇文章。
六、拉姆齐的《〈逻辑哲学论〉评议》
为什么维也纳学圈对拉姆齐的误读如此严重?部分原因可能在于,没有证据表明他们读过拉姆齐的《〈逻辑哲学论〉评议》(Critical Notice of the Tractatus)。《评议》于1923 年发表在《心灵》杂志。它本可以提醒维也纳学圈去注意拉姆齐对维特根斯坦的计划的担忧,以及相随而来的对他们自己计划的担忧。
拉姆齐在其《评议》中说,罗素的导言可能“不是对维特根斯坦先生的意旨的可靠指引”,因为罗素说,维特根斯坦关注的是一种逻辑完备的语言。但是,拉姆齐写道:
(维特根斯坦)似乎坚持他的学说对日常语言同样适用,尽管表面看来并不如此。……这一点显然很重要,因为像这样扩大论点的适用范围,对于罗素所称的维特根斯坦理论的根本之点(“为了使某个句子得以断言某个事实,……该句子的结构和该事实的结构之间必须有某种共同之处”)以及类似的论点而言,既会大增论点的意趣,又会大减其成真的可能。aFrank P.Ramsey,“Critical Notice,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by Ludwig Wittgenstein”,Mind,32/128,1923,p.465.以下引文简写为 CN,并以冒号间隔标出页码。
拉姆齐同意维特根斯坦的学说应该适用于日常语言,但他之所以能对《逻辑哲学论》提出紧迫而最终致命的难题,其中的关键正在于维特根斯坦的学说并未做到这一点。
拉姆齐指出,《逻辑哲学论》主要由两种要素构成。其一是涵盖大部分篇幅的“非神秘的演绎”——对“图画和世界之间必然存在的某种共性”的仔细论证(CN:468)。其二在于提明或示意所有那些“本质上无法讨论”的东西(CN:468)。他认为这两点都带来困难。也就是说,他向维特根斯坦的精密机器(意义的图画理论)里扔进了一些扳手。维特根斯坦认为此书主要意图是言说和显示的区分,但拉姆齐对此感到担忧。
《逻辑哲学论》中的“表征”(representation)是这样一个观念:图画与实在具有同样的结构,或者同样的逻辑形式。拉姆齐最一般的反驳b他还提出更多的具体问题,比如现在被称为“颜色排斥难题”。参见Cheryl Misak,Frank Ramsey:A Sheer Excess of Powers。,也是对维特根斯坦计划的整体性反驳,在于:
但至少可以说,这种定义显然是十分不完备的;它能适用的地方只有一处,那就是已经得到彻底分析的基本命题。(CN:469)
拉姆齐提到一些不能被还原为对应简单客体的基本语句。例如,既然那些逻辑联结词——如非(~)和或(v)——并不表现客体,包含它们的命题又如何能被还原为基本语句?维特根斯坦把这些联结词当作命题的算子,并且认为,我们能够使用这类符号来表达那些我们不能陈述而只能显示的东西。拉姆齐认为这一点颠覆了维特根斯坦设定的单纯的同型结构。否定算子“~”很能说明这个问题。《逻辑哲学论》对表现、理解和真理的解释本质上是肯定性的(positive)。c参见Steven J.Methven,Frank Ramsey and the Realistic Spirit,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5,p.113。理解一个命题意味着看到,若其为真则事情会是如何。一切基本命题描绘正面事实,而这类命题的一个独一无二的集合能够完全描述这个世界。拉姆齐指出,把~(aRb)表现为反映了一个否定性的事实是“荒谬的”,其荒谬性不会因为维特根斯坦把“~”解释为“它说的是不存在客体或事物的这类组合”而得到缓解。
但不能以基本语言图示的并不是只有逻辑联结关系。拉姆齐宣称:“我们现在必须转向维特根斯坦先生最有趣的一个理论,那就是某些东西不能被说出而只能被显示,而这些东西构成了神秘者(the Mystical)。”(CN:472)他在《评议》中表达了一种不安,这种不安到后来会成为关于言说/显示区分的更为全面的不满。维特根斯坦的表现形式本身就是一个“晦涩难解的实体,本质上无法讨论”。也就是说,维特根斯坦自己对何为表象的讨论就超出基本命题之外。维特根斯坦当然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哲学的讨论必须像梯子一样使用,然后被踢到一边。拉姆齐认为这是一个无法接受的举措。他在《评议》中得出结论是:“我们不能满足于一种只能处理基本命题的理论。”后来他会以更为尖锐的方式表达这个要点。“没法说的东西就是没法说,我们也不能用吹口哨的方式把它吹出来。”aFrank P.Ramsey,(1929b),“General Propositions and Causality”,reprinted in Ramsey,Philosophical Papers,p.146.以下引文简写为 GPC,并以冒号间隔标出页码。
显然,早在1923 年,拉姆齐就已经不再致力于修正逻辑分析派的观点了。很多对语言来说重要的东西不能被还原为初始语言,我们也不能把次级语言扫到毯子下面当作不可说者(如维特根斯坦认为的),或者仅仅是工具性的(如维也纳学圈的某些成员认为 的)。
七、《理论》这篇文章又该如何解读?
布雷斯韦特在1931 年编辑出版的《拉姆齐文集》中收入了拉姆齐1929 年的手稿《理论》。20 世纪50 年代,卡尔纳普和亨佩尔使用了一个知名的提法:拉姆齐语句(Ramsey Sentence)。但重要的是要看到,那个时候的卡尔纳普和亨佩尔已经放松了他们各自的还原论倾向。而在写作《理论》的时候,拉姆齐认为自己是在远离卡尔纳普,而不是接近他。
的确,拉姆齐的《理论》是这样开头的:
让我们尝试这样描述一个理论,把这个理论当作不过是一门语言,以讨论这个理论据说要解释的事实。aFrank P.Ramsey,(1929c),“Theories”,reprinted in Ramsey,Philosophical Papers,p.112.以下引文简写为T,并以冒号间隔标出页码。
也就是说,他的起点是20 世纪20 年代中期的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圈的观点:事实可以用“我们将称作初始体系的一整批话语”或者说初始语言来表达(T:112),而初始语言表达的是简单命题,简单命题要么绝对为真,要么绝对为假。他进而主张,如果我们硬要这么做,我们的确可以使用一套公理和一部词典建构出一种理论,这部词典会把初始语言翻译为次级语言。但他很清楚,这些定义对于“理论的合法使用”(T:129)并非必不可少。表明这类定义如何能够被建构出来,只有“指导性”的意义。这种指导部分在于表明大概要怎样作出定义,因为罗素、卡尔纳普和其他人“似乎认为,我们不仅能够作出这种定义,并且必须作出这种定义”(T:120)。但这种指导部分来说是否定性的。拉姆齐认为,这项计划不会成功。第一个障碍,一个也许可以克服的障碍,是这项计划会变得无比复杂。举例来说,如果初始语言关注的是一系列经验,那么它需要的是“时间次序”和诸如颜色和气味这类东西的结构。
更不容易克服的是第二个障碍,即拉姆齐(在别处)所说的“来自科学哲学的反驳”bFrank P.Ramsey,On Truth,Nicholas Rescher &Ulrich Majer(ed.),Dordrecht:Kluwer,1991(1930),p.35.以下引文简写为 OT。。维也纳学圈的一个难题是,我们对无法观察的实体的信念似乎是无意义的,例如电子或由绿色奶酪构成的月球的背面,因为我们没办法直接观察它们。不仅如此,我们也无法解释例如质量理论是如何改变和改进的。如果以显定义(explicit definitions)的方式解释科学理论,那么理论的每一次改变都意味着旧理论中的术语的意义发生了改变,或者指称新的实体。如拉姆齐所说,“如果我们以显定义的方式建构理论,我们在对理论作补充的时候就不得不改变定义,并且因此不得不改变整体的意义”(T:130)。他认为这一点显而易见:我们必须能够解释,概念如何能够既发生演化而又保留其意义,以及解释理论是如何生长的。因此,“词典本身并不足够”,除非我们满足于一个有限而初始的体系,一个比理论本身要贫乏得多的体系。(T:122ff)任何“有用的理论”必须相比初始体系拥有“更大程度的自由”。如果一种科学理论并不超出当前事实的一份清单,那么拥有这么一种理论就没有意义可言。也就是说,拉姆齐表明卡尔纳普的计划(拉姆齐从《世界的逻辑建构》中理解的那个计划),尽管可以完成,但完成了也无大益处。
拉姆齐进而提示经验主义者,如何以一种不依靠显定义的方式设想科学理论。与他的实用主义一贯的是,他强调信念的后果。理论就是判断或信念的体系,其结果可能成功地应对未来,也可能不成功。我们是以整体的方式使用理论的;我们把理论作为所有那些判断的缩写,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那些不可观察的东西,比如月球的背面:
如果我们的理论允许这种可能性——我们前往那里,或以别的方式查明情况——那么它(指“月球背面有一层绿色奶酪”这一说法)就是有意义的;如果不允许,它就没有意义;也就是说,与此相关的不单是我们关于一般而言的事物的理论,我们关于月球的理论同样关系重大。(T:134)
我们关于月球以及太空中的固态物体的理论,会告诉我们月球的远侧可能是如何构成的——这个理论的整体会让关于月球的不可观察的一面的信念有意义,也会决定它们的真假。
拉姆齐接着采取了一个新的步骤,这个观念后来会让卡尔纳普和亨佩尔感到兴奋。他主张,我们能够解释诸如“电子”这类理论词项的角色,只要我们将其置入一个长而复杂的形式化的语句,这个语句不仅包含理论词项,也包含观察词项。这个语句会是这样开始的:“存在我们称作电子的东西,这些东西……”,然后这个句子会讲一个关于电子的故事。我们为这个故事的需要假设电子的存在,正如我们在聆听一个有这种开头的故事“很久以前,有这样一个女孩,她……”的时候,我们也假设这个女孩的存在。任何对这个理论的补充都是在量词的辖域之内作的补充,而这个量词说:至少有一个电子存在。也就是说,这个理论在演化的时候仍然是关于原来那些实体的。对理论的扩充“严格说来并不本身就是命题,这正像一个以‘很久以前……’开头的故事中的不同句子一样,由于没有完整的意义,因而本身不算是命题”(T:131)。也就是说,它们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初始语言那样的真假可言。我们承诺我们的理论中的这些实体的存在,同时我们知道,如果理论被推翻了,我们对这些实体的存在的承诺也会被推翻。在此之前,我们使用这个理论。
这个创举和拉姆齐在1929 年的实用主义定义观是完全一致的——定义“给出的至少是我们未来的意义,而不只是给出把握某种结构的精妙方式”(P:1)。定义告诉我们,如何通过让词项代表的模糊而复杂的概念变得更精确来继续使用这个词项。尽管关于定义和理论的这个观点并不让1929 年的维也纳学圈十分满意,可是一旦学圈放弃严格的还原主义计划,尤其是因为来自科学哲学的反驳而放弃这种计划,那么拉姆齐的观点就会变得有吸引力。
我们可以从卡尔纳普拥有的那本布雷斯韦特编著的文集中看到,他在1930 年代仔细读过《理论》。亨佩尔听说拉姆齐的思想还要晚一些,迟至布雷斯韦特在1946 年的塔纳讲座。a参见Stathis Psillos,Scientific Realism:How Science Tracks Truth,London:Routledge,1999,p.46。20 世纪50 年代早期,卡尔纳普和亨佩尔开始使用拉姆齐的存在量化语句,显示世界如何能从经验之中被建构出来。b参见Rudolf Carnap,“Beobachtungssprache und Theoretische Sprache”,Dialectica,Vol.12,No.3—4,1958,pp.236—348;Carl G.Hempel,“The Theoretician’s Dilemma:A Study in the Logic of Theory Construction”,Minnesota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2,1958,pp.173—226。这个观念的来源已经在卡尔纳普的头脑中变得模糊,只有在他于1958 年读了亨佩尔的《理论家的两难:理论建构的逻辑》(The Theoretician’s Dilemma:A study in the logic of theory construction)一文的手稿之后才又一次变得清晰。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亨佩尔发明了“拉姆齐语句”这个术语。卡尔纳普写信给亨佩尔,说亨佩尔的论文促使他回头去读布雷斯韦特编著的文集,这才发现自己已经“清楚地划出了”《理论》中的重要段落,信中还表达了对自己得以避免把拉姆齐的观点窃为己有的感谢。c参见 Archives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University of Pittsburgh:RC.1974.01:102-13-53。1966 年,卡尔纳普送给布雷斯韦特他的《物理学的哲学基础》,其中有一章就题作“拉姆齐语句”。
卡尔纳普在1929 年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拉姆齐的创举并不奇怪。如凯恩斯所说,拉姆齐当时就已经“在脱离……形式的和客观性的处理方式。”那种处理方式在卡尔纳普的作品中留下了痕迹。拉姆齐和维特根斯坦起初是想帮助罗素完善《数学原理》的体系。然而,凯恩斯说其结果是:
逐渐抽空其内容,并且将其逐渐约简为干枯的骨架,直至它最终不仅排除了一切经验,也排除了大部分合理思想……原则。维特根斯坦的解法是把此外的一切都当作凭灵感而来的胡言,虽然对个体来说确实深具价值,但无法得到精确的讨论。拉姆齐的反应是转向他自己说的某种形式的实用主义[…]。因此他走向的是一种“人本逻辑”而不是“形式逻辑”。dJohn Maynard Keynes,“Review of the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The New Statesman,October 3,1931.Reprinted in Elizabeth Johnson &Donald E.Moggridge(ed.),Essays in Biography.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Vol.X,London:Macmillan,1972(1931),p.338.
凯恩斯是对的。到1929 年,拉姆齐已经明白,演绎的方法不过是一堆枯骨。《理论》中的核心观点是,用法的问题——在这一事例中就是如何使用科学理论的问题——要比形而上学的问题更为重要。逻辑原子主义的形而上学所能提供的东西并不足以面对现实生活和真实的科学。理论要么真要么假,但并不在严格的、原子主义的意义上,而是在整体论的、实用主义的意义上。拉姆齐处理科学理论(以及其他一切超过初始体系的东西)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与20 世纪20 年代末的维也纳学圈的精神相抵触。拉姆齐的思路是采纳实用主义关于真理和谬误的解释,这种解释追问的是信念的结果是否能够妥善应对未来。
八、拉姆齐在1929 年对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圈的评价
在自我放逐之后,维特根斯坦于1929 年1 月17 日回到了剑桥。拉姆齐死于1930 年1 月19 日。这一年间,两人每天都在密切交谈。他们的交谈堪称关于哲学的正确路线的交锋。如拉姆齐在1929 年的文章《哲学》所说,“维特根斯坦的”方法代表了哲学的一种路线,那就是:
建构一种逻辑,以一种不自觉的方式(unselfconsciously)来从事我们的一切哲学分析,所考虑的始终是事实而不是我们关于事实的思考,确定我们所意谓之事而不必参考意义的本质。(P:5)
与此相反,拉姆齐的实用主义方法把我们带向“人本事实”,而非脱离一切人本理解的事实。他认为我们经常会遭遇那些“我们无法定义,但……[只]能解释它们如何得到使用”的词项。他承认自己一度深受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的影响:
因为过分的经院作风,我过去常常在哲学的本质这个问题上自寻烦恼。我没能看到,我们如何能够理解一个词汇,却不能认清某种给出的定义究竟是对是错。我未能意识到“理解”这整个观念的模糊之处,未能意识到“理解”所牵涉的众多行为,而那些行为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失败并要求得到恢复。(P:1—2)
当然,这一切都预示着晚期维特根斯坦转向“意义之为使用”这个观念。然而在1929 年,维特根斯坦仍然试图建构一种用完美语言作出的理想定义。拉姆齐认为这是经院作风的一种表现,“其本质在于,把含混的当作精确的,并且试图将其塞入一套精确的逻辑范畴”(P:7)。
他在《哲学》一文的一份草稿的开头之处直白地批评维特根斯坦:
哲学必须有点用处,我们也必须严肃看待哲学;它必须澄清我们的思想,进而梳理我们的行为,否则的话,哲学不过是闲谈罢了。否则的话,它就是我们必须克制的倾向……也就是说,哲学的要旨在于:哲学是一种胡言。但这样一来我们必须认真看待哲学之为胡言这件事,不能像维特根斯坦那样假装哲学是意义重大的胡言。aArchives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University of Pittsburgh:1983.01:006-02-03.(文本中有删除线,是拉姆齐本人加的。)
我们必须避免以下对话中的孩子的“荒谬立 场”:
“说‘早饭’。”“说不出来。”“你说不出来什么?”“说不出来‘早饭’。”(P:6)
维特根斯坦坚称哲学是胡言,因此必须抛弃哲学。拉姆齐在《哲学》中的反驳是双重的。首先,维特根斯坦不能去论证(argue for)关于意义本质的这样一种观点——这种观点的结果是,他为这一点给出的论证本身就是无意义的。其实,我们的的确确能理解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论证。这个论证并不是什么一旦爬上去就需要踢到一边去的梯子。这点也针对维也纳学圈对形而上学的否弃。其次,这种哲学是贫乏的。如果真像维特根斯坦设想的那样,哲学的工作是把科学的命题和日常生活的命题“展示于由初始词项和定义构成的逻辑系统”,那么哲学实在并无大用。(P:1)拉姆齐在一条笔记中说:
啤酒颜色的标准化不是哲学,但在某种意义上它是记法的改进,也是思想的澄清。bMaria Carla Galavotti(ed.),Frank Plumpton Ramsey,Notes on Philosophy,Probability and Mathematics,Naples:Bibliopolis,1991,p.55.以下引文简写为 NPPM,并以冒号间隔标出页码。
哲学必须超过记法的改进。
显然,1929 年的拉姆齐路线及其针对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圈的反叛正处在高潮。他在另一条笔记中说:
我们不能作为真正抽离的自我来描绘世界;我们所知的自我是世界之中的自我。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做不到,再怎么尝试也没有益处。哲学肇始于未能理解语言的逻辑;但语言的逻辑并不是维特根斯坦设想的那样。我们为自己制作的图画并不是事实的图画。(NPPM:51)
如果命题是世界的图画并且与任何描绘这种图画的自我无关,那么我们就完全无力抵抗怀疑论或唯我论。那我们如何填补自我和那个世界之间的间隔?我们怎么对那个世界作出断言?维特根斯坦的初级世界“不包含任何思想”。aArchives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University of Pittsburgh:003-30-05.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世界,那么我们切不可忽视“主观的一面”(P:6)。拉姆齐认为,卡尔纳普犯了同样的错误。
平常意义上的唯我论——也就是像卡尔纳普那样认为,初始世界由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经验构成——是不会成功的,因为初始世界是我现在思虑所及的世界……(NPPM:66)
如果我们想要思考这个世界,我们就需要不可还原的次级世界,一个充满假说、规律,以及关于各种客体之存在的主张的世界。卡尔纳普的错误在于,把红色色块还原为点的无限类,以至于摧毁了色块之为我的色块或你的色块的意义。
拉姆齐没有对维也纳学圈作出更多评价。他和卡尔纳普从未碰面。但他在病重期间确实关注卡尔纳普。拉姆齐在去世前一个月,给石里克写了一封关于《世界的逻辑建构》的信,表达了他关于卡尔纳普从初始语言建构世界的这种尝试的怀疑:
我至今还没有对卡尔纳普的书写一篇书评,这让我深感愧疚,因为这实在说不过去。我觉得这本书非常有趣,尽管其中的一些内容我觉得肯定是错的,另一些则非常可疑。
拉姆齐想要首先“澄清关于这些事情的真理”,然后再写卡尔纳普这本书的“优点”和可疑之处。
九、结语
拉姆齐不能被视为同情维也纳学圈的立场。在他身前,维也纳学圈的计划是把一切有意义的语言还原到某种必然为真的经验基础上。他并不知道学圈更为开明也更为实用主义的版本会在他身后出现。20 世纪30 年代早期,维也纳学圈开始明白,符合论的真理观和他们的证实主义相抵触——我们如何能够证明那些完全独立于我们的东西?而“来自科学哲学的问题”,即不可观察的实体和理论的改变,也对他们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菲利普·弗兰克早在1930 年就提议,实用主义才是答案:
除了实用主义的真理观,从事科学活动的物理学家从未使用其他真理观。学院哲学所要求的“思想和对象的相应”不能得到任何具体实验的支持……其实,物理学家只是将一种经验和另一种经验作比较罢了。他们检验理论的真假,靠的是一般所说的“意见一致”。aPhilipp Frank,“Physical Theori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School Philosophy”,in Modern Science and Its Philosoph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9(1930),pp.101—102.
和拉姆齐一样,弗兰克使用“经院哲学”(school philosophy)一词来描述他现在认为需要为实用主义的真理观让步的东西。尽管方式各不相同,随着维也纳学圈分化为各种阵营,很多成员都渐渐趋近拉姆齐的立场。鉴于其复杂度,此处不能详述。如果卡尔纳普在第一次阅读布雷斯韦特的编著时就接受了拉姆齐的实用主义,那么维也纳学圈可能会把拉姆齐的立场当作一个模范,而不是迟至20 世纪50 年代才发现,拉姆齐对一种自由化的经验主义哲学有着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