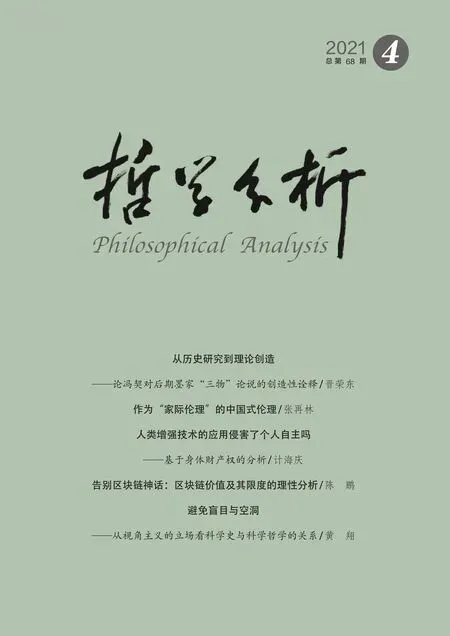作为“家际伦理”的中国式伦理
张再林
家是社会的细胞,又是社会的母体。对于重视“血缘根基”并以“家的精神”为其民族精神的中华民族来说,其对家更是备极顶礼。从中不仅产生了“家国一体”“齐家治国”的政治文化,还为我们推出一种极其独特的中国式“家际伦理”。这种“家际伦理”与其说是一种抽象的“人际”伦理,不如说是一种原始而具体的家人之际的伦理。故这种“家际伦理”实际上是在夫妇之际、父子之际、兄弟之际第次展开的。
一、“人之伦类肇自男女夫妇”的夫妇伦理
《颜氏家训》写道:“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自兹以往,至于九族,皆本于三亲焉,故于人伦为重者也,不可不笃。”(《颜氏家训·兄弟 篇》)
我们之所以对这一论述极其注意,不仅在于它为我们明确指出什么是最重要的家庭之际,而且尤其还在于它一反父权社会以“父子”独尊的家际伦理,而把夫妇之际视为家际伦理真正的造始端倪。其实,这种合乎常理的夫妇优先的观点并非颜氏孤明独发,早在《周易》中它就被古人祭为不易之理。如《周易·序卦传》提出:“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而在与《周易》互为发明的《周礼》中,这种夫妇优先则表现为礼以“婚礼”为根基。故《礼记》提出“夫昏礼,万世之始也”,《礼记·郊特牲》提出“昏礼者,礼之本也”(《礼记·昏义》)。虽然在长期中国历史上,父子之际成功实现了其位序上的“逆袭”,优先的夫妇之际完全让位于其后的父子之际,但伴随着明清之际借古人之酒杯浇今人之块垒的“复古”思潮的兴起,《易》 《礼》的夫妇优先观点又一次重整旗鼓地异军突起。如李贽称“一夫一妇,家家之乾坤”a李贽:《李贽文集》第七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版,第97 页。,“天下之定,观乎家人;家人之正,始于男女”b同上书,第188 页。,唐甄称“盖今学之不讲,人伦不明;人伦不明,莫甚于夫妻矣”c唐甄:《潜书》,北京:中华书局1955 年版,第77 页。,戴震称“人之伦类肇自男女夫妇”d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61 年版,第174 页。,王韬称“欲家之齐,则妇惟一夫,夫惟一妇。所谓夫夫妇妇而家道正矣。天之道一阴一阳,人之道一男一女,故《诗》始《关雎》,《易》首乾坤,皆先于男女夫妇之间再三致意焉”e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原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年版,第3—4 页。。
应该明确指出的,这种为古人强调的家际伦理的“夫妇优先论”,不仅包括发生学意义上的“优先”,而且还包括逻辑学意义上的“优先”,也即“原型说”意义上的“优先”。为了说明为什么夫妇之际是一切家际伦理的“原型”,就必须从古人所理解的夫妇之际的“际”的关系谈起。
首先,正如列维纳斯“他者”伦理学把男女中的女性视为“他异性”来源那样,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夫妇之际亦同样起始于所谓的“男女有别”。这种男女有别可见于“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礼记·坊记》)的周人同姓不婚制,可见于所谓“男女授受不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男女不交爵”,以至于古人认为“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礼记·昏义》)。唯有男女有别,才能使一种情感专一的对偶式夫妇关系得以建立,从而使我们人类自己告别了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群婚制,并从中最终形成了一种本末一贯、枝叶分明的家庭家族的生命共同体。
其次,也正如列维纳斯在强调女性“他异性”的同时并不忽视男女之间的“亲密性”那样,中国古人亦如此。由此就有了《礼记》所谓“为妻何以期也?妻至亲也”(《礼记·丧服传》),所谓“夫妻一体也”(《礼记·丧服传》),就有了《诗经》所谓“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小雅·常棣》)、“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邶风·击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邶风·谷风》)这些无上的美誉,而“比翼鸟”“连理枝”等成语则代表了对这种亲密性无人不知的隐喻。
这样,在男女夫妇之际,我们看到了一种所谓的“亲密的差异”。而这种“亲密的差异”以其不无诡谲的非一非异,恰恰指向古人所谓“不同而一,夫是之谓人伦”(《荀子·荣辱》)这一人伦逻辑。显然,这种逻辑与其说体现了一种美德伦理、规范伦理所遵循的意识之间“同一律”的逻辑,不如说体现了中国家际伦理所恪守的身体之间“模棱两可”的逻辑。这使中国家际伦理一开始就打上了梅洛—庞蒂式“身体间性”的鲜明印记。
既然男女夫妇之际是一种“身体间性”,同时,既然男女夫妇的身体实际上是两性欲望的身体,那么这就决定了,夫妇之际与两性欲望关系,是须臾不可分离的。关于这种两性欲望关系,彭富春先生写道:“在性欲的关系结构中,欲望者是人,所欲物也是人。这使欲望者和欲望物各自都具有两重身份。这就是说,一方面,欲望者既欲望他的所欲物,也被他的所欲物所欲望,因此欲望者同时也是所欲物。另一方面,所欲物既被所欲望者所欲望,也欲望他的欲望者,因此所欲物同时也是欲望者。这意味着,在性欲中的男女关系既不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也不是主动和被动的关系,而是一种不可分离和共同生成的伴侣关系。……他们是具有差异的亲密的一对。虽然你我差异犹在,但亲密导致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a彭富春:《论大道》,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年版,第93—94 页。
这种对男女欲望的“不同而一”的论述与黑格尔所谓的“爱的辩证法”何其相似,因为黑格尔亦指出:“爱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我不欲成为独立的、孤单的人,我如果是这样的人,就会觉得自己残缺不全。至于第二个环节是,我在别一个人身上找到了自己,即获得了他人对自己的承认,而别一个人反过来对我亦同。因此,爱是一种最不可思议的矛盾,决非理智所能解决的……作为矛盾的解决,爱就是伦理性的统一。”a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年版,第175 页。
当黑格尔为解释男女欲望的“不同而一”而求助于一种不无新颖的“爱的辩证法”之际,中国哲学家焦循则从古老的《周易》里发现了揭开这一问题的真正隐秘。对于治易大师焦循来说,以“趋利避害”为宗旨的《周易》实际上是以如何实现我们的身体欲望为目的的。而这种欲望能否实现既不取决我的“己欲”,又不取决于非我的“他欲”,而是取决于“既遂己欲,又遂人欲”这一人我欲望两相孚的“互欲”。凡遂的欲也即《周易》所谓主吉的利,凡不遂的欲也即《周易》所谓主凶的不利。当我们进一步追溯这种“互欲”如何可能时,焦循则告诉我们,正如《周易》一贯主张唯有阴阳相交才能实现遂欲的吉利那样,其答案恰恰就在无师自通、无比自洽的男女夫妇的关系里,因为“夫妇者,一阴一阳之交孚也”b焦循:《易通释》卷五,《易学三书》,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 年版,第121 页。。易言之,正是在男女夫妇两两相交的“互欲”活动里,才能使人我互欲的隐秘真正大白于世。
这样,“孰无施而有报兮,孰不实而有获?”(《九章·抽思》)在男女夫妇之际的“互欲”里,一种爱的自组织型的双向回馈的“无施不报”就应运而生了,成为夫妇际会的至为主要规定。从《礼记》中的必以昏(婚)者,取其“阳往阴来”之义,到《诗经》中的樛木高木能下曲,葛藟攀附而上“犹能庇其本根”(《周南·樛木》);从“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卫风·木瓜》),到“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郑风·女曰鸡鸣》;从爱情中女子虽可“守身如玉”但又可“以身相许”,到《红楼梦》里林黛玉为报雨露之恩倾其一生“还泪”的故事;如此等等,无一不是对这种“无施不报”的如诗如歌的诉说。至于古代稗闻野史中所谓男女夫妇“对食”之说,则以其对“回馈”(“馈”有“食”义)无比生动逼真的表述而使“无施不报”之义得以真正显豁。
人们看到,正是在这种爱的“无施不报”里,从中产生了周礼的“礼尚往来”之说,还有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恕之说。而孟子的“出乎尔反乎尔”理论的推出,更是以“无施不报”为依据的。它不仅告诉我们为什么“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为什么“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孟子·离娄上》),还告诉我们为什么“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它作为“无施不报”原则在君臣之际的一种体现,迥非那些流于“舔痔”之辈的后儒所能梦见。
二、“仁复藏果,果复藏仁”的父子伦理
如前所述,在夫妇之际,从其“亲密的差异”导出“不同而一”。这种“不同而一”实乃“和而不同”的“和”的学说。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则使夫妇伦理与生生之理互为表里,由此就有中国古人的阴阳化生之说。这样,在这种阴阳化生的生命里,诚如王船山所说,“天地率由一阴一阳之道以生物,父母率行于一阴一阳之道以生子”(《尚书引义卷四·泰誓上》)。通过一种黑格尔所谓夫妇关系的“现实化”、列维纳斯所谓夫妇关系的“实体转化”,我们家庭中的“孩子”出现了。进而,随着“孩子”的出现,夫妇之际一变为父子之际。
既然夫妇之际关系是一切家际关系的“原型”,那么,这一“原型”对父子之际同样成立。也就是说,无论是夫妇之际还是父子之际,二者都不谋而合地遵循着一致的逻辑。
因此,正如夫妇之际体现了一种非异非一的“亲密的差异”的关系那样,一种真正的父子之际亦完全如此。故一方面,在父子之际,古人强调子对父的“无违”“色难”“三年无改于父子道”“大孝终身慕父母”,强调“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乃至更有甚者,在一些人眼里,舜对父的逆来顺受、窃负而逃被视为孝道的至极代表。但另一方面,在父子之际,古人又主张“所谓肖子者,安能父步亦步,父趋亦趋,父与子异形离质,而所继者惟志”(《尚书引义·皋陶谟》),主张“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主张“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赵岐注孟子“不孝有三”),主张“父有争子,不行无礼”(《荀子·子道》),“事父母几谏”(《论语·里仁》),其中子对父的他异性的凸显亦成为古人事父之道一大特点。
于是,正如夫妇之际“亲密的差异”导出男女夫妇之间的“互欲”,这种“互欲”又一次出现在父子之际。故父子之际并非单向的父道独尊的领域,而为一种双向的“父慈子爱”的爱的共同体。在这方面,我们看到《诗经》中诗人歌道:“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小雅·蓼莪》);在这方面,我们看到《礼记》释者写道:“以财言之,谓物为本。以终言之,谓初为始,谢其恩谓之报,归其初谓之反,大义同也”(孔颖达释《礼记·郊特牲》)。也正是从这种施、报关系出发,才有了孔子以子女“三年之丧”回报父母“三年之养”的“仁”的思想,才有了《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的“孝”之道,才使“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成为人所皆知的人生警喻,才使“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不失为流淌在中华民族每个儿女心中最美的诗句。
张祥龙先生曾从人类学高度为我们力揭了人之所以要回爱自己父母的真正深意。他指出,也许是由于人类的直立两足行走,它限制了人的骨盆开口处的宽度,宽度限制了产道,使人类的母亲无法像包括黑猩猩在内的其他哺乳动物那样顺利生产,于是,就只能在婴儿还极其不成熟的时候就生下他。结果就是,较之其他灵长类动物,人类抚育子女的时间更漫长,过程也更艰难。反过头来,由于人类特有的深长的时间意识,致使他们能够记得或想到,父母对自己曾有如海深的大恩,自己应该在他们年老时加以回报,此即孝意识的产生。结果就是,那些没有能力觅食的老年人,从年轻的成年子女那里得到食物,正是受到他们子女的供养和保护,才使他们过了生育年龄后还可以继续活着,并由于他们的知识和经验而得到尊重。这一切告诉我们,正如人类学家指出的那样,“人类终身都与儿子们和女儿们保持联系”,并基于此,才使人类以其特有的人性而与其他灵长类动物大异其趣。a张祥龙:《孝道时间性与人类学》,载《中州学刊》2014 年第5 期。
因此,一种发端于夫妇之际的双向回馈的“无施不报”生命运动在父子之际又得以丰富和继续,以至于从张祥龙先生那里我们甚至可以产生这样的结论:这种“无施不报”使我们既可以得出父母生出子女,又可以得出子女生出父母。
这不正是三百多年前明代著名哲学家蕺山先生非凡思想的再次表述吗?因为当时蕺山先生在谈到生命运动时就推出了著名的“果复藏仁,仁复藏果”的命题:
只此一点几微,为生生立命之本。俄而根荄矣,俄而干矣,俄而枝矣,俄而叶矣,俄而花果矣。果复藏仁,仁复藏果。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尾。是故知死生之说,是故知无死无生之说。b刘宗周:《刘宗周全集》第二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年版,第431 页。
在这里,蕺山先生指出,我们人类生命运动如同一棵植物生成那样,看似由因及果地先有“仁”后有“果”,实际上则是互为因果地“仁”与“果”的“互生”过程。这不仅意味着“实体性”模式的终结和“关系性”模式的诞生,而且还意味着正是在这种生命“互生”的过程中,生命开始与生命完成已不再判然有别,而是二者始终首尾相接,从而父代生命的死亡不再使父子生死两隔,而恰恰是这种生死两隔的终结和消解。这样,人“必有一死”、人“向死而在”之说一变为“世代相生”的无死无生之说,也即生命的“生生不息”之说。
在王船山那里,蕺山的父与子“互生”的“世代相生”则是通过一种“父母感生”的“终始之无穷”的方式展开的,它进一步为我们彰显、弘扬了父子际生命的“生生不息”的特征。故船山指出:“人之所自始者,其混沌而开辟也。而其现以为量,体以为性者,则唯阴阳之感。故溯乎父而天下之阳尽此,溯乎母而天下之阴尽此。父母之阴阳有定质,而性情俱不容已于感以生,则天下之大始尽此矣。由身以上,父、祖、高、曾,以及乎绵邈不可知之祖,而皆感之以为始;由身以下,子、孙、曾、玄,以及乎绵邈不可知之裔,而皆感以为始。故感者,终始之无穷,而要居其最始者也。”(《周易外传卷三·咸》)
无独有偶,这种父子之际“互生”所内蕴的“生生不息”之义既为中国古人所开启,同时又在当代西方那些“家哲学”的先知先觉者那里得以揭示,这使它以一种普遍真理的方式贯通中西。关于后者,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列维纳斯的观点尤值得一提。这是因为,列维纳斯不仅提出父子关系“过去每时每刻都从一个新的起点出发得到恢复(se reprend),焕然一新地恢复”a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朱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272 页。,而与蕺山的生死首尾相接的观点如出一理,而且还提出“与孩子的关系——就是说,与他者的关系,这并不是权能,而是生育——建立起与绝对将来或无限时间的关联”b同上书,第260 页。,提出“生育延续历史,却并没有同时产生衰老;无限时间并没有给予老去的主体带来永恒的生命。无限时间穿越世代断裂,它是更好的,它因孩子之不可穷尽的青春而充满节律”c同上书,第261 页。,由于强调父子相传的“生育”,列维纳斯的观点最终与中国古人所发明的世代相生的“生生不息”的精义完全不期而遇了。
“自我的生育,乃自我的超越本身”d同上书,第271 页。,一如列维纳斯所指,一种所谓的“内在超越”由是应运而生。也就是说,当代新儒家所推出的“内在超越”之所以成立,与其说取决于一种其所谓的认识论意义上的“智的直观”的“心体”,不如说最终有赖于一种家世学意义的“以似以续”的“身体”。正是在一种“儿子不是我;然而我是我的儿子”e同上。这一亦离亦即的父子之际,我们才能真正体验到那种既内在又超越的生命的不可思议的神奇。
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兄弟伦理
实际上,父子关系既导致了家的生命在纵向时间上的无限扩充,又使家的生命在横向空间上无限的扩充成为可能。为了说明后者,就不能不谈到兄弟伦理所涉的丰富内容。
也就是说,“父子关系作为一种无数的将来产生出来,被生产出来的自我同时既作为世界上的唯一者又作为众兄弟中的一员而实存”a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第273 页。,诚如列维纳斯所示,父母结合经由“生育”不仅产生了“孩子”,而且这种“孩子”并非单数的,而是复数的,从而就使我们进而又从父子伦理过渡到兄弟伦理。
既然夫妇伦理是一切家际伦理的“原型”,那么,这一“原型”既对父子伦理成立,又对兄弟伦理同样成立。唯其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诗经》还写道“宴尔新婚,如兄如弟”(《邶风·谷风》),而有了新婚夫妇情同兄弟之喻;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诗经》还写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大雅·思齐》),而声称夫妻准则可以直接运用于兄弟之际;以至于由此可见,一代国学大师钱穆所说的古人把全部人生都“阴阳配偶化”这一发现绝非虚语。
于是,一如夫妇之际为我们指向了非异非一的“亲密的差异”,这一点对于兄弟之际亦同样成立。故一方面,在兄弟之际,我们看到了古人有所谓的“骨肉”“手足”之喻,看到了《诗经》中“兄弟既翕,和乐且湛”(《小雅·常棣》)那样的美誉,而《颜氏家训·兄弟篇》所谓“兄弟相顾,当如形之与影,声之与响”更是把兄弟之际这种无比亲密性的描述推向了极致。但另一方面,这种兄弟之际的亲密并不能使我们无视兄弟之际难掩的差异,因为较之于父子之际那种直接而无间的血缘联系,在兄弟之际,其血缘联系由于借助父亲这一“中介”,的确出现了弱化的趋势,并职是之故,才使列维纳斯的家哲学把兄弟关系称作家中“陌生人”的关系。b孙向晨《论家——个体与亲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203 页。
这样,正如夫妇之际“亲密的差异”实与男女夫妇之间的“互欲”互为表里那样,这种“互欲”亦与兄弟交往的原则完全一致。我们看到,正是从这种“互欲”出发,才使古人提出“兄友弟恭”,把双向回馈的“无施不极”视为兄弟之际所遵循的不可让渡的绝对原理。与一种兄长的长我、爱我、佑我、伴我、助我相应的,则是兄弟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知恩之心,进而才有了如同深植于我们生命基因那样的手足之谊、骨肉之情,而这种手足之谊、骨肉之情显然与那种“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情不深”的世俗之情泾渭分明。也正是这种兄弟情深,才使戴震写道“昆弟之情,洽之尽也”(《原善》),才使周公旦有了宁愿自己折寿也祈求兄长武王能够延寿的一片深情,才使孔融、孔褒二人为救朋友竞相赴死的同门争义,才使伯夷、叔齐兄弟在继承君位上相互推让而具名扬千古之举,也才使古人为我们留下“上阵父子兵”的同时亦留下了“打虎亲兄弟”这一著名谚语。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兄弟之情的“互欲”是一种平辈间的“互欲”,故较之上下辈的父子之情的“互欲”而言,这种“互欲”已清除了父子之际“尊尊”的孑遗,而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平等的“朋友”友谊。这使“四海之内皆兄弟”在中国文化中成为可能的同时,也使中国古人从中实现了从“亲亲”的“齐家”到“仁民”的“治国”的成功切换与转型。
中西文化往往是相通的,这一点在兄弟与朋友的内在联系上表现得尤为分明。因为亚里士多德就指出:“兄弟之间的友爱,似乎与伙伴的关系相同,他们是平等的”a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180 页。,进而他还指出,正是基于这种平等,才使兄弟友爱与一种轮流执政、权力平等的城邦体制深深相契、息息相通。殆至列维纳斯哲学的兴起,这种兄弟与朋友的内在联系又被进一步彰显和发明。这表现为,列维纳斯从西方“天父”的宗教学说出发,认为人类就是一个来自“一个父的共同性”,并由“兄弟”构成的大家庭,从而“人人皆兄弟”已不再是道德学家一种一厢情愿的臆想,而是以一种既生物又超生物的家庭生成法则为其坚实支撑的,以至于他提出:“人类自我在兄弟关系中确立,人人皆兄弟这一点并不是像一种道德成就那样被添加到人身上,而是构成人的自我性。……在兄弟关系中,他人复又显现为与所有他者血脉相连;在这样的兄弟关系中,与面容的关系构造起社会秩序,构造起任何对话与第三者的关联;凭借这种关联,我们——或团体——就包含了面对面的对立,就使得爱欲性事物涌向社会生活,那充满表示合乎情理的社会生活,它包含家庭结构本身。”b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第274 页。至此,列维纳斯漫长的家的探索之旅,终于从“亲亲”走向“博爱”,从“爱有差等”走向“社会平等”,并借以向我们表明了人类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与其说是一座血脉的锁链铸就的“围城”,不如说是一种充满无限可能性和通向更为广阔世界的开放系统。
耐人寻思的是,这种对兄弟与朋友内在联系的强调曾是中华文化的一大传统。早在家道最为鼎盛的西周宗法制时期,除了对“兄弟”的大力提撕之外,关于“善兄弟为友”(《尔雅·释训》)的论述可谓比比皆是。如西周铜器铭文中的“孝友惟型”(《厝彝》),“惟辟孝友”(《史墙盘》),如《诗经·皇矣》曰“维此王季,因人则友,则友其兄”,《国语·晋语》称文王“孝友二虢”(二虢为文王弟)。再翻开《尚书》,其中“善兄弟为友”之义更是触目可见。《尚书·君陈篇》写道:“孝乎唯孝,友于兄弟”,《尚书·康诰篇》写道:“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清儒程瑶田由此得出:“宗之道,兄道也。大夫士之家,以兄统弟以弟事兄之道也”a程瑶田:《程瑶田全集》卷一《宗法小记》,合肥:黄山书社2008 年版,第137 页。,查昌国教授亦明确断言:“历代注家都谓西周‘友’为兄弟规范,这一认识得到现代周史研究的进一步证实,是为确论”b查昌国:《友与西周君臣关系的演变》,载《历史研究》1998 年第5 期。。
这种兄弟与朋友之间的不解之缘之所以可能,不仅在于西周的宗法制的核心是大宗统小宗,大小宗实际上是兄弟关系,而且还在于周人所谓的“友”既包括同胞亲兄弟,也包括非同胞的同族兄弟,甚至包括通过联姻的非同姓的兄弟。这也意味着,人们所尊先祖越是久远,兄弟的范围也越是广泛,兄弟的血缘联系也越为递减,兄弟与朋友之间也越失去其界限,乃至四海之内皆可为兄弟,乃至“民吾同胞”“天下犹一家”这些说法绝非虚言。故《礼记·大传》写道:“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在《礼记》中,古人的祖宗崇拜与其说旨在发思古之幽情地怀念其历史上逝去的先祖,不如说旨在活在当下而普爱在先祖庇荫下生活着的芸芸众生、普罗大众。
这不正可视为列维纳斯“天父说”的中国版吗?正如列维纳斯从一种不无神化的父出发,从“亲亲”走向“博爱”、从“爱有差等”走向“众生平等”,中国文化亦从一种“天祖合一”的“祖”出发,其路径与列维纳斯不约而同。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春秋之际,与儒家“亲亲”之说交相呼应,墨家的“兼爱”之说、“尚贤”之说亦在中国大地一呼百应、风起云涌,以至于一度出现了“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上》)这一蔚为壮观的风景。究其原因,这不过是作为“兄友”之道的流风余韵,乃周人文化的历史继承和遗存。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司马迁笔下,在先秦之际有如此多的侠义之士的壮举,如赵氏托孤的故事,“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的豫让的故事,“意气兼将生命酬”“向风引颈送公子”的侯嬴的故事,从中使人感受到的与其说是英雄豪杰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视死如归”,不如说是以其“士为知己者死”的“无施不报”,让人领略到那是西周宗法社会“家”的日薄西山之际,残留在中国文化中的最后一抹壮丽余晖。
同时,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明清之际“以复古为启蒙”的回归家的思潮中,人们除了看到对周人所厚的家的力挺外,还连同看到对周人所厚的朋友之伦异乎寻常之独尊。关于这一点,何心隐指出:“天地交曰泰,交尽于友也。友秉交也,道而学尽于友之交也”a何心隐:《何心隐集》,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版,第28 页。;后来的谭嗣同亦指出,“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惟朋友乎”b谭嗣同:《谭嗣同全集》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350 页。。这种对“家”与“友”不分轩轾的并重,不仅使我们走出“亲亲”与“兼爱”之间二律背反这一中国儒家思想的“阿克琉斯之踵”的阴影,而且一反“三顺说”“三纲说”所带来的积重难返的权力话语的独断,使长期湮没无闻的社会平等思想在中国文化中再次得以彰显。
不无遗憾的是,在长期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虽讲“孝悌为本”,但实际上更多强调的是孝的父子之伦,而顾此失彼于悌的兄弟之伦,更遑论那种“善兄弟为友”的朋友之伦。这不独有悖于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精神,也与人类现代的追求社会平等的精神背道而行。故在中国走向思想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既要认识到中国父子伦理的遗产之不可或缺,又要积极投身于对中国兄弟伦理深刻而丰富内容的深入发掘,唯此才能使我们真正实现中华民族“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这一继往开来的文化伟业。
四、结语
走笔至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结语:
其一,不难看出,这种家际伦理学就其直接置身于、直面于种种原始而具体的家人之际关系而言,是一种类似于列维纳斯现象学的“面对面”的应对型、交往型的伦理学。用王阳明的表述,即它是一种“不虑而知”“不学而能”和“只在感应之几上看”的“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传习录》)的此感彼应的感应伦理学。
其二,在这种家际伦理学里,一种始于男女夫妇间的自组织的爱的双向回馈是其最根本的法则。这种双向回馈不仅以一种“无施不极”的方式,一以贯之于夫妇之际、父子之际、兄弟之际里,而且还以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方式,体现在从夫妇间的非血亲关系,中经父子间的血亲关系,再通过“善兄弟为友”,最后到普天下众生的非血亲关系这一整个家的生命系统生成的“圆圈”之中,从中最终实现了从“亲亲”到“仁民”、从“爱有差等”到“众生平等”这一人际关系的切换和转型。
其三,一方面,这种爱的双向回馈在父子之际沿着纵向时间轴线展开,使我们的生命生生不息通向其固有的无限性,另一方面,这种爱的双向回馈又在兄弟之际沿着横向空间轴线展开,使我们的生命光被四海得以永无止境地普遍扩充。故基于爱的双向回馈的家际伦理以其既内在又超越、既具体又普遍、既生理又伦理,而成为一种真正克服了道德“二律背反”和忠实体现了人类“至善”的伦理。
最后,所有这一切,使得这种家际伦理学既不同于个体主义式的源于同一化、本质化知识话语的“他组织”的西方美德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又不同于时兴的社群主义化的非西方“角色伦理学”,因为后者虽然与家际伦理同样重视人际之间的关系性、对话性,却由于其伦理罔顾对有限生命的超越,并缺失人类德性的普遍性,而与中国传统的家际伦理貌似相同,实则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