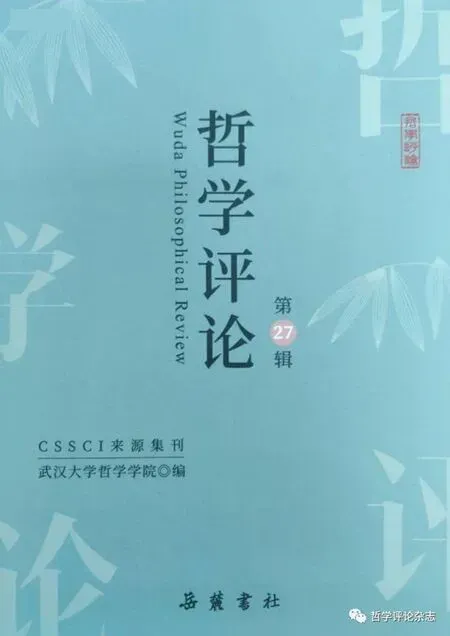论康德本体论证明批判思想的发展
——从《演证上帝存有的惟一可能的证明根据》到《纯粹理性批判》
舒远招 刘丹凤
众所周知,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把有关上帝存有(Dasein)[1]本文把Dasein译为“存有”,把Existenz译为“实存”,把撇开系词含义而专门表示“存在”的Sein译为“存在”,康德实际上交替使用这三个术语。另外,本文把包括系词在内的Sein überhaupt译为“一般的是”。的证明方式分为三种:自然神学的证明从确定的经验开始,并按照因果律而上升到世界之外的最高原因;宇宙论证明从某个“一般存有”的经验推出一个最高存在者的存有;本体论证明则完全先天地(a priori)从单纯概念中推出一个最高原因的存有。康德认为,宇宙论证明实际上以隐蔽的方式把本体论证明当成了自己的推论基础,即肯定了上帝这个最实在的存在者的概念也必然带有这个存在者的绝对必然性,同样,自然神学的证明也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仰仗于本体论证明,因此,撇开其道德神学证明不论,便只有本体论证明所包含的才是“惟一可能的证明根据”(A625/B653)[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3页。本文以下凡引用本书,都只列出皇家科学院版标准页码。A指第一版,B指第二版。了,这种“证明根据”是人类理性所不可忽略的。基于这种理解,康德把对本体论证明的批判置于对宇宙论证明和自然神学证明的批判之前,本体论证明批判思想在康德全部思辨神学批判中也就占有了至关重要的地位。
谈论康德的本体论证明批判思想,自然不能避开其写于前批判时期的《演证上帝存有的惟一可能的证明根据》一文(1763,以下简称为《证明根据》)[2]Immanuel Kant. Der einzig mägliche Beweisgrund zu einer Demonstration des Daseins Gottes. Herausgegeben von Wilhelm Weischedel.In: Immnanuel Kant Werkausgabe II:Vorkritische Schriften bis 1768.Su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2.-9.Aufl.-2003.李秋零教授将康德这部论著译为《证明上帝存在惟一可能的证据》,见其主编的《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本文引自《证明根据》的引文,参考了李秋零教授的译文。。从《证明根据》到《纯粹理性批判》,可以清晰地看出康德本体论证明批判思想由前批判时期到批判时期的发展。正如一些论者所指出的,康德在《证明根据》一文中已经批判了笛卡儿派的本体论证明,这表明康德的思想发展具有一定的连贯性[3]可参见赵林:《康德前批判时期关于上帝存在证明的思想纠结》,《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该文提出,《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神学批判思想在前批判时期的《证明根据》一文中就已经“初具雏形”。该文还指出:在这篇早年撰写的长文中,康德一方面对传统的本体论证明和宇宙论证明进行了深入透彻的批判,另一方面却仍然试图为上帝存在寻找一种新的理性证明。这种矛盾表明,此时的康德正在休谟怀疑论的影响下,艰难而痛苦地挣脱着莱布尼茨-沃尔夫独断论的思想束缚。。但是,《证明根据》一文毕竟还尝试为上帝的存有作出一种“演证”,并且称之为“本体论证明”,这表明前批判时期的思想与《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思想相比还有很大的不同。另外,尽管《证明根据》和《纯粹理性批判》都批判了笛卡儿派的证明,但后者无疑更加全面系统,而且在一些用语上发生了改变。
本文试图表明,从《证明根据》到《纯粹理性批判》,康德的本体论证明批判思想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纯粹理性批判》否定了《证明根据》中康德自己所主张的“本体论证明”,即建立在“惟一可能的证明根据”之上的证明方式;其二,《纯粹理性批判》在吸收和保留《证明根据》中的批判思想的基础上,也推进了《证明根据》对笛卡儿派证明所作的批判,使得批判更富有层次性,更加全面系统。本文在第三部分中还将表明:《证明根据》所说的“Dasein根本不是一个事物的谓词或规定”和Dasein作为“绝对的肯定”有别于“每一个本身在任何时候都仅仅在与另外一个事物的关系中被设定的谓词”,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被说成了“逻辑的谓词”不同于“实在的谓词”。
一、《纯粹理性批判》否定了《证明根据》中康德主张的“本体论证明”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所批判的本体论证明,主要是笛卡儿派的证明,他还明确提到莱布尼茨的名字(A602/B630)。但在《证明根据》中,他其实并没有把笛卡儿派的证明叫作“本体论证明”。在这里,他所谓的“本体论证明”,特指他自己主张的证明方式,即从作为结果的可能事物推出上帝的实存。《纯粹理性批判》放弃或否定了康德自己在《证明根据》中所主张的这个“本体论证明”,这可以视为康德本体论批判思想的一大发展。在批判笛卡儿派本体论证明的同时还主张另外类型的本体论证明,这表明《证明根据》中的本体论证明批判思想还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克服。
在《证明根据》的第三章(Dritte Abteilung)中,康德把关于上帝存有的所有证明根据分为两大类,即要么“从单纯可能事物的知性概念中”(aus den Verstandsbegriffen des bloß Möglichen)得到,要么“从实存事物的经验概念中”(aus dem Erfahrungsbegriffe des Existierenden)得到。第一种情况又分为两个做法:要么是从作为一个根据的可能事物推出作为一个结果的上帝的存有;要么是作为一个结果的可能事物推出作为一个根据的“神的实存”(die göttliche Existenz)。第二种情况同样被分为两种做法:要么是从我们经验到其存有的东西推出一个第一的和独立的原因的实存,并借助于解析该概念而推出该原因的神的属性;要么是从经验教导的东西直接推出第一因的存在及其属性。[1]Immanuel Kant. Der einzig mägliche Beweisgrund zu einer Demonstration des Daseins Gottes. Herausgegeben von Wilhelm Weischedel.In: Immnanuel Kant Werkausgabe II:Vorkritische Schriften bis 1768.Su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2.-9.Aufl.-2003.S.729—730.
于是,康德便把全部证明根据分成了两大类和四小种:第一类的第一种做法是笛卡儿派所为,第二种做法是康德自己的主张,他并且把这种做法叫作“本体论证明”[2]ibid.S.734.;第二类的第一种做法在康德看来很著名,尤其是通过沃尔夫学派的哲学家们而“声名鹊起”,大致对应于《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宇宙论证明,而第二种做法在康德看来很古老,但通过德勒姆(Derham)、纽文迪特(Nieuwentyt)等人的努力而被发扬光大,大致相当于《纯粹理性批判》中的自然神学(目的论)证明,但康德在《证明根据》中把这种做法叫作“宇宙论证明”[3]ibid.。在这四种证明中,康德明确否定了第一种笛卡儿派的做法和第三种沃尔夫学派的做法,即《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说的本体论证明和宇宙论证明。在他看来,说到底只有他自己主张的“本体论证明”和第四种“宇宙论证明”才是可能的。他承认这种“宇宙论证明”(实即目的论证明)具有生动感人的优点,但从逻辑的完备性和精确性的角度来看,他认为只有他自己主张的“本体论证明”才建立在“惟一可能的证明根据”之上,才具有一种演证所要求的“明晰性”。
在《证明根据》第一章(Erste Abteilung)的第二个考察中,康德论述了以一种存有为前提的“内在可能性”。他首先区分了可能性的两种含义:其一,是可能性的“形式的东西”或“逻辑的东西”,这是指凡是可能的东西都不能自相矛盾;其二,是可能性的“质料的东西”或“实在的东西”,这是指可能事物的“材料”或者“质料”[1]后文还将进一步表明:康德对可能性的“逻辑的东西”和“实在的东西”的这一区分,不同于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反驳本体论证明时所提出了“逻辑可能性”与“实在可能性”的区分。因为“实在可能性”是指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事物的可能性,大致对应于“可能性”模态范畴,而这里所谓可能性的“实在的东西”则仅仅是指构成一个可能事物的“材料”或“质料”,是我们所设想的一种东西,如一个可能的三角形必定包含了三个角、三条边等。。例如,一个具有四个角的三角形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在其自身包含了矛盾。但一个三角形和一个具有四个角的东西都是一个可能的事物,它们所包含的“材料”或“质料”都是可能的。因此,不仅在一切自相矛盾的场合没有了内在可能性,而且在没有“材料”或“质料”可以思维的情况下也没有了内在可能性。所有可能的事物不仅具有符合矛盾律的逻辑关系,而且都是某种可以被思维的东西。康德由此提出:如果人们取消了一切存有,则没有质料的东西成为可以思维的东西,而且一切可能性也就被取消了。虽然否定一切实存并不会有什么矛盾,但是,有某种可能性却根本没有任何现实之物,这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如果没有任何东西实存,也就没有任何在此被思维的东西被给予,而且如果人们依然想要某物是可能的,就会陷入自相冲突”[2]Immanuel Kant. Der einzig mägliche Beweisgrund zu einer Demonstration des Daseins Gottes. Herausgegeben von Wilhelm Weischedel.In: Immnanuel Kant Werkausgabe II:Vorkritische Schriften bis 1768.Su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2.-9.Aufl.-2003.S.638.。他的意思是:说没有任何东西实存,就等于说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而在此情况下再说有某物是可能的,这是自相矛盾的。所以,事物的内在可能性要求我们承认某种东西实存,绝对不可能没有任何东西实存。
康德进而提出:一切可能性都是在某种现实之物中被给予的,要么是作为这个现实事物的一种规定,要么是通过该物而作为一个结果。他并且把这个现实之物就归结为上帝,认为上帝的内在可能性就是其规定,而上帝之下的万物的可能性则来源于上帝(上帝是一切可能性的最终实在根据)。由于取消上帝的存在会从根本上取消一切可能性,因此上帝的存在就是必然的。他还把上帝这个必然的存在者从本质上说成是惟一的,是简单而不可分的,是不变的和永恒的,就其本性而言是一种精神。康德还认为,上帝包含了最高的实在性,但并不包含一切实在性,其自身的实在性固然就是其谓词或规定,但其他事物的实在性则是其结果。可见,他把事物的实在性与质料的可能性大致等同了起来。在第四个考察的“结束语”中,他还指出:他所给出的有关上帝存有的证明根据,仅仅建立在“某物是可能的”这一基础上。因此,他的“本体论证明”就是一种“可以完全先天地作出的证明”[1]Immanuel Kant. Der einzig mägliche Beweisgrund zu einer Demonstration des Daseins Gottes. Herausgegeben von Wilhelm Weischedel.In: Immnanuel Kant Werkausgabe II:Vorkritische Schriften bis 1768.Su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2.-9.Aufl.-2003.S.653.。
但是,这一证明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被否定了。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本体论证明”一词仅用于指称笛卡儿派从逻辑上可能的最实在的存在者概念推出该存在者存有的做法。不仅如此,在论述上帝这个“先验理想”时,康德还明确指出:理性把诸物的一切可能性都看作是从一个惟一的、作为基础的、也就是最高实在的可能性派生出来的,并且由此预设了这种可能性是包含在某个特殊的原始存在者即上帝之中的,这是一种“自然的幻觉”(A582/B610)。在他看来,理性固然可以通过最高实在性的单纯概念而将原始存在者规定为惟一的、简单的、完全充足的、永恒的等等,并把上帝理念作为一切实在性的概念而建立为一般事物的通盘规定的基础,但并不要求这一切实在性被客观地给予出来并构成一个事物,这样一个事物是我们的“一个单纯的虚构”(A580/B608),而我们并没有权利作出这类虚构。对康德而言,上帝只是一个调节性的理念,并无客观实在性,因而我们不应将这个“单纯的表象”制作成“客体”,并将其实在化,乃至于人格化。
在这里,康德放弃了《证明根据》中的做法:把一个现实事物的存在当作可能性的前提,而是仅仅把上帝这个可能之物当作一切事物之可能性的先验质料方面的条件。在他看来,每个概念或可能的事物都首先需要从属于“可规定性原理”(A571/B509):在每两个相互矛盾地对立着的谓词中只有一个可以归之于一个概念,这是一条单纯逻辑的原则,大致对应于《证明根据》中所说的可能性的逻辑的或形式的东西。与此同时,每个事物按其可能性而言还需要从属于“通盘规定原理”:在一个事物的一切可能的谓词中,必然有一个谓词是应该归于该物的(A572/B600)。这就超出了矛盾律的要求,而在与可能性总体的关联中来看待每个可能的事物,把每个事物的可能性看作是对可能性总体的一种分有。于是,每个事物在其通盘规定中的可能性,就大致对应于《证明根据》中所说的可能性的质料的或材料上的东西。康德由此提出:对一切可能的谓词,我们都可以超出单纯逻辑方面的考虑而关注到其“先验的肯定”,这就是其“实在性”(事实性),它意味着“一个某物,其概念自在地本身就表达了一个是”(A574/B602)。而每个事物的实在性(可能性)都被理解为要以上帝这个“先验基底”为基础,而这个先验基底似乎包含了全部材料储备,因而一切事物的可能的谓词都可以从这个先验基底中取得。上帝本身也是得到通盘规定的,这就是他所包含的一切可能的先验谓词,如全知、全能、永恒等(A641—642/B669—670)。凭借这些先验肯定或先验实在性而得到通盘规定的上帝理念,构成了其他一切事物的通盘规定的基础,构成了这些事物的可能性的至上的和完备的质料条件。在更精确的规定中,康德还把上帝的最高实在性说成是一切事物的可能性的“根据”而非“总和”(A579/B607),并且把事物的规定或谓词当作了上帝这个根据的“结果”。康德的这些说法与《证明根据》中的说法大同小异,两者之间最有决定意义的区别仅在于: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上帝这个先验理想始终只是一个可能的事物,一个单纯的思想物,而不像在《证明根据》中那样被说成是一个“现实事物”。概言之,康德不再把现实事物当作事物可能性的前提,这就明确否定了《证明根据》所说的“惟一可能的证明根据”或“本体论证明”。
二、《纯粹理性批判》推进了《证明根据》对笛卡儿派本体论证明的批判
我们看到,《证明根据》已经展开了对笛卡儿派证明(当时并未称之为“本体论证明”)的批判,这与《纯粹理性批判》先验辩证论第三章第四节“上帝存有之本体论证明的不可能性”对笛卡儿派本体论证明的批判具有一致性,表明康德在前批判时期就已经否定了笛卡儿派的本体论证明。
1.《证明根据》对笛卡儿派本体论证明的批判
《证明根据》抓住了笛卡儿派证明的主要问题,这就是把上帝的存有混淆为上帝概念所包含的谓词。笛卡儿派试图从作为一个根据的可能事物推出一个作为结果的上帝的存有,也就必须通过分析上帝这个可能事物的概念而在其中发现其存有,如此一来,就必然会把存有与上帝概念所包含的谓词(规定)混淆起来。康德在检查笛卡儿派的证明时提到,人们在作出此类证明时,还首先想象出一个可能事物的概念,并设想所有真正的完善性都统一在它里面,于是认定存有也是一种完善性,于是便由一个最完善的可能事物的可能性推出其实存[1]Immanuel Kant. Der einzig mägliche Beweisgrund zu einer Demonstration des Daseins Gottes. Herausgegeben von Wilhelm Weischedel.In: Immnanuel Kant Werkausgabe II:Vorkritische Schriften bis 1768.Su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2.-9.Aufl.-2003.S.730.。但是,针对笛卡儿派的上述做法,康德指出存有根本就不是一个可能事物的谓词(规定),因而也不是完善性的谓词,由此否决了这一证明的可能性。康德的这一批判确实抓住了笛卡儿派证明的要害:人们在试图从一个单纯可能的概念推出绝对必然的实存时,总是在这样一个仅仅可能的存在物的谓词中去寻找存有,但存有却根本不在其中,因此此类寻找是徒劳的。
康德认为,存有根本不是一个(可能的)事物的谓词或规定,但如果人们正确地理解了它的含义,由此不再像笛卡儿派那样从仅仅可能的概念中推出它,则人们也可以把这个表达当作一个谓词来用。在存有作为一个谓词出现于普通用语的所有场合中,它与其说是“事物本身”(Dinge selbst)的一个谓词,倒不如说是我们关于该事物的思想的一个谓词。例如,说独角海兽具有实存,这无非是说独角海兽的表象是一个经验概念。人们必须亲自看到了独角海兽,或者至少听看到过它的人说起,才能确认它是否真的实存。因此,说“独角海兽是一种实存着的动物”,这并非完全正确的表述,正确的说法毋宁是:“某个实存的海洋动物具有我在独角海兽身上所设想的全部谓词。”[1]Immanuel Kant. Der einzig mägliche Beweisgrund zu einer Demonstration des Daseins Gottes. Herausgegeben von Wilhelm Weischedel.In: Immnanuel Kant Werkausgabe II:Vorkritische Schriften bis 1768.Su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2.-9.Aufl.-2003.S.631.
《证明根据》不仅指出存有根本不是一个事物的谓词或规定,而是我们关于该事物的思想的谓词,表明我们关于某个事物的表象是一个经验概念,而且进一步指出存有是对一个事物的“绝对的肯定”,因而有别于“每一个本身在任何时候都仅仅在与另外一个事物的关系中被设定的谓词”[2]Immanuel Kant. Der einzig mägliche Beweisgrund zu einer Demonstration des Daseins Gottes. Herausgegeben von Wilhelm Weischedel.In: Immnanuel Kant Werkausgabe II:Vorkritische Schriften bis 1768.Su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2.-9.Aufl.-2003.S.632.,即由系词在主谓词之间的逻辑关系中设定的谓词。康德把“肯定”或“设定”与“一般的是”(Sein überhaupt)视为同一的,并认为“一般的是”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系词,它是一个判断中的联结概念,在这里,某种东西可以仅仅在关系中被设定,或者更确切地说,仅仅被设想为作为一种特征的东西同另外一个事物的关系;而在“绝对的肯定”这里,自在自为的事物被看作是被设定的,此时的Sein就等同于存有即Dasein。康德在此不仅把存有这种绝对的肯定同系词在主谓词关系中的设定区别开来,而且把绝对的肯定同系词所设定的谓词区别开来。
康德还举例指出:当我说“上帝是全能的”时,所考虑的仅仅是主词“上帝”与谓词“全能”之间的逻辑关系,把全能仅仅当作上帝的一个“特征”来加以述说,而并未由此包括对上帝存有或实存的肯定。上帝的实存并不像“全能”那样包含在上帝这个主词概念中。即使不认识上帝存有的人,只要他很好地理解我如何使用上帝概念的,也会把“上帝是全能的”判断为一个真实的命题。但上帝的存有却属于他的概念如何被设定的方式,因为存有不属于上帝的谓词。因此,当我说“上帝是一个实存的事物”,这似乎并不正确地在把实存当作包含于上帝主词概念中的一个谓词来加以述说,包含了存有与谓词的一种不经意的混淆。因而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一个实存的事物是上帝,即它具有我们借助于上帝这个表述所表示的全部谓词。”[1]Immanuel Kant. Der einzig mägliche Beweisgrund zu einer Demonstration des Daseins Gottes. Herausgegeben von Wilhelm Weischedel.In: Immnanuel Kant Werkausgabe II:Vorkritische Schriften bis 1768.Su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2.-9.Aufl.-2003.S.633.
《证明根据》批判笛卡儿派本体论证明的这些思想都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得到了保留,并构成了康德进一步批判笛卡儿派证明的要点。著名的“Sein显然不是实在的谓词”(A598/626)命题,就与“存有根本不是一个事物的谓词或规定”具有一致性。另外,《证明根据》中认为存有超出了主词概念,需要通过经验来确证的思想,也与《纯粹理性批判》中对“实存概念的精确规定”相对应,后者也强调一个事物的实存需要被知觉到,由此把实存当作一个经验概念。但是,《纯粹理性批判》不仅在具体表述上与《证明根据》有了变化,例如采用了“Sein显然不是实在的谓词”和“实存概念的精确规定”之类的说法,而且对笛卡儿派本体论证明的论证程序作了更有层析性的叙述,因而其反驳也更加全面系统。
2.《纯粹理性批判》在哪些方面推进了对笛卡儿派本体论证明的批判
《纯粹理性批判》叙述了笛卡儿派两个“版本”的本体论证明,这是《证明根据》所没有作出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批判更富有层次性。在这里,我们依据康德对笛卡儿派的普通版证明和加强版证明的批判,来看看他在保留《证明根据》的批判思想的同时做了哪些推进。
(1)康德对普通版笛卡儿派证明的批判
所谓普通版证明,就是一般的证明,即从一个绝对必然的存在者概念推出其必然存有或实存的证明。康德指出,人们仅仅从名义上解释“绝对必然存在者概念”,把绝对必然存在者说成是“其非存在是不可能的某种东西”(A592/B620),认为一旦否定其存有,就会导致该概念自相矛盾。如笛卡儿还举例表明:上帝的存有就像三角形有三个角一样是绝对必然的。康德在反驳时提出:“判断的无条件的必然性并不是事物的绝对必然性。”(A593/B621)虽然在存有三角形的情况下它必然有三个角(逻辑必然性),但并不意味着有三个角的三角形必然存有(事物必然性)。同样,“上帝是全能的”是一个具有逻辑必然性的命题,但这种必然性并不等同于上帝的必然存有。由于这两种必然性的不同,导致了取消上帝的存有并不会导致矛盾。这就是说,如果我把存有事先设定在一个概念中,则取消其存有会导致该概念自相矛盾,但如果我把主词本身也随同谓词一并取消,那就没有矛盾了。因此结论是:由于在取消上帝主词的同时取消谓词不包含矛盾,因而不能单凭纯粹先天的上帝概念发现其不可能存有的任何标志(A596/B624)。
“判断的无条件的必然性”与“事物的绝对必然性”之间的区分,确乎可以说是对《证明根据》中的类似区分的一种采纳和发挥。在《证明根据》中,康德区分了“逻辑的必然性”与“存有的必然性”,即“绝对的实在的必然性”(die absolute Realnotwendigkeit)[1]Immanuel Kant. Der einzig mägliche Beweisgrund zu einer Demonstration des Daseins Gottes. Herausgegeben von Wilhelm Weischedel.In: Immnanuel Kant Werkausgabe II:Vorkritische Schriften bis 1768.Su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2.-9.Aufl.-2003.S.643.。他也提出,取消了一个可能事物的存在,并未取消该事物与其谓词之间的逻辑关系。这表明,康德把一个可能事物与其包含的谓词之间的逻辑上必然的关系,与包含这些谓词(规定)的这个可能事物的“存有”区分开来,即认定“存有根本不是一个事物的谓词或规定”。但我们也要看到,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是想通过两类必然性区分来否定笛卡儿派的普通版证明,而在《证明根据》中,康德尽管通过这一区分而批判了笛卡儿派证明,但毕竟还试图表明:在他自己的“本体论证明”中,这种区分还具有正面的意义,即肯定了上帝具有绝对的实在必然性。如前所述,康德是想通过把必然要有某种事物的存在当作事物的可能性的最终根据,由此他肯定了有一个绝对必然的存在者即上帝实存。
(2)从康德对加强版笛卡儿派证明的批判
所谓加强版证明,是康德在“上帝存有之本体论证明的不可能性”一节的第七段中叙述的,特指进一步将“绝对必然的存在者”理解为“最最实在的存在者”(das allerrealste Wesen),并且由这个“最最实在的存在者”的概念推出该存在者的必然存有。康德设想,笛卡儿派可能会进一步提出:在最最实在的存在者概念中,其对象的不存在是自相矛盾的。“你们说,这个存在者具有一切实在性,你们也有权假定这样一个存在者是可能的(这一点我暂且承认,尽管这个不自相矛盾的概念还远未证明该对象的可能性)。现在,在一切实在性中也包含了存有,因而存有寓于一个可能事物的概念中。那么,如果该物被取消,则该物的内在可能性也会被取消,而这是矛盾的。”(A596—597/B624—625)这段话的最后一句表明了笛卡儿派会反对把存有从“最最实在的存在者”概念中取消,因为这会导致取消其内在的可能性,因而自相矛盾。但这个最终结论建立在“存有寓于一个可能事物的概念中”这个结论的基础上,而后者是通过一个不太标准的三段论推理得到的。这一推理大致是:A.最最实在的存在者具有一切实在性,而且是可能的(大前提);B.现在,在一切实在性中也包含了存有;C.因而存有寓于一个可能事物的概念中(结论)。
在接下来的八至十三段中,康德对这个加强的证明作出了全面系统的批判。由于加强版证明包含诸多环节,因而康德对之展开的批判就显得比《证明根据》中的批判更加复杂。我们认为,与《证明根据》中的批判相比,康德对这个加强版证明的批判主要在以下几点上有所推进:
首先,康德在总体回应中提出了三个观点,是《证明根据》中所未见的。
总体回应是在本节第八段作出的,康德在这一段中提出了三个观点:其一,当笛卡儿派“不论以何种暗藏的名目把该物实存的概念塞进了一个只能按照其可能性来思考的事物概念中”(A597/B625)时,便陷入了自相矛盾;其二,如果笛卡儿派把实存性命题当作分析命题(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的),则通过该物的存有对该物的思想没有任何增加,但如此一来,就要么把心中的思想当成了事物本身,要么预设了一种存有是属于可能性的,然后以此为借口从内在可能性中推出了这一存有,而这无非是“一种可怜的同义反复”(A597/B625);其三,如果笛卡儿派承认实存性命题是综合的,就像每个有理性者必须明智地承认那样,则取消存有就不会有任何矛盾(A598/B626)。第一个观点是康德对笛卡儿派的一种反击,认为他们把实存塞进一个事物概念中的做法“自相矛盾”;第二个观点指出了笛卡儿派通过把实存性命题当作分析命题的方式而陷入了“同义反复”;第三个观点通过指出实存性命题的综合性而表明了取消实存不会导致矛盾。这些说法都是《证明根据》所没有的。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在指出笛卡儿派在作同义反复时还指出,“实在性”一词——在事物概念中的“实在性”听起来不同于谓词概念中的“实存”这个词——也无助于克服其同义反复。“因为如果你们把所有的设定(不论你们设定什么)都称为实在性,则你们就已经把这个事物连同其一切谓词都设定在主词之中了,并假定它是现实的,而在谓词中你们只是重复这一点。”(A597—598/B625—626)这表明:笛卡儿派把实存混淆为上帝概念所包含的实在性,这并未克服同义反复,因为如此一来,对主词(上帝)连同其一切谓词的设定,也就像系词对谓词的设定那样,仅仅是在上帝主词概念中进行了。
其次,康德针对加强版证明混淆Dasein与上帝的实在性的小前提,而提出的“Sein显然不是实在的谓词”命题,这与《证明根据》中“Dasein根本不是一个事物的谓词或规定”命题在表述上有了区别。
直接可以看出的区别有二:一是主语的区别,《纯粹理性批判》反驳本体论证明一节第十段一开始提出的“Sein显然不是实在的谓词”命题,主语是Sein(相当于《证明根据》中的Sein überhaupt),而《证明根据》中“Dasein根本不是一个事物的谓词或规定”命题中的主语是Dasein,即存有;二是谓语的区别,康德用“实在的谓词”取代了“一个事物的谓词或规定”的说法。
主语外延的扩大,导致了康德在陈述Dasein不是实在的谓词时,不仅像《证明根据》一样论述了Dasein作为绝对的肯定同系词所设定的谓词的区别,而且指出了系词(Sein的逻辑运用)与它所设定的谓词的区别。当然,由于Sein包含了Dasein,所以两个命题并无矛盾,康德依然试图通过“Sein不是实在的谓词”命题来澄清笛卡儿派加强版证明的小前提在Dasein与上帝实在性之间的混淆。Dasein是对一个事物的肯定,当我把上帝连同其全部谓词总括起来说“上帝存在”(Gott ist)或“有一个上帝”(Es ist ein Gott)时,“我并没有为上帝概念增加新的谓词”,而仅仅是把上帝设定在与我的概念的关系中。康德在此强调:一个可能事物所包含的谓词或规定,并不多于一个现实事物所包含的谓词或规定,这与《证明根据》中的思想是一致的。
谓语的改变很可能与加强版证明的推理前提有关:这一证明是从具有一切实在性的最最实在的存在者的概念出发进行推理的。因而当康德把“实在的谓词”界定为“一个事物的规定”(A598/B626)时,就是指上帝这类逻辑上可能的事物的“规定”或“特征”,即如“全能”之类的实在性。不过,在“Sein显然不是实在的谓词”命题后面,康德所说的实在的谓词,是指“上帝是全能的”这个例句中用来指称“全能”的谓词“全能的”,它被说成是“关于可以加给一个事物的概念的某种东西的一个概念”。康德指出,在“上帝是全能的”这个命题中,不仅主词“上帝”拥有自己的客体“上帝”,而且“全能的”这个实在的谓词也拥有自己的客体“全能”,而全能可以加给上帝这个主词概念。从概念的角度看,“上帝是全能的”命题表达了上帝这个主词概念与全能的这个谓词概念的关系,而从概念的客体的角度看,系词“是”所设定的,是“上帝”与“全能”之间的逻辑关系。无论我们从何种角度来理解“实在的谓词”,这总是一个超出了《证明根据》的说法。
再次,康德针对加强版证明“存有寓于一个可能事物的概念中”这一结论,而提出了“实存概念的精确规定”,这也是《证明根据》所未见的一个新提法。
如前所述,康德在《证明根据》中指出,在存有出现于普通用语的所有场合,与其说它是事物本身的一个谓词,还不如说是人们关于该事物的思想的一个谓词。他还以独角海兽为例表明:说一个事物具有实存,这无非是说其表象是一个经验概念。人们必须亲自看到了独角海兽,或者至少听看到过它的人说起,才能确认它是否真的实存,这实际上已经诉诸经验来理解事物的实存了。这些说法,都符合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实存概念的精确规定”的大意,即一个事物的实存需要有对该事物的经验知觉。但是,在《证明根据》中毕竟还未见“实存概念的精确规定”这一用语。而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在精确规定实存概念时引入了“现实性”模态范畴,并且将之同“可能性”模态范畴相对照。在他看来,在感官对象上,我们不可能把该物的实存与该物的单纯对象相混淆。“因为通过概念,对象只是被思考为与一般可能的经验认识的普遍条件相一致,但通过实存,它却被设想为包含在全部经验的连贯关系中的;因为通过与全部经验的内容的联结,关于对象的概念并没有丝毫增加,但我们的思维却通过这个内容而多得了一种可能的知觉。”(A600—601/B628—629)一个感官对象的实存,需要它被知觉到。但由于上帝是一个纯粹思维的客体,我们无法通过诉诸经验知觉来证明其存在,因此康德认为我们虽然不可以把上帝实存说成是绝对不可能的,但它却是一个我们无法为之作出辩护的“预设”。显然,“实存概念的精确规定”这一表述,在《纯粹理性批判》反驳笛卡儿派证明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最后,康德针对加强版证明的大前提,提出了逻辑的可能性不等于实在的可能性,这是《证明根据》所没有的。
逻辑的可能性实际上是概念的不自相矛盾,可以归结为概念的可能性。由于包含一切实在性的最最实在的存在者概念并没有矛盾,因此康德承认它具有逻辑的可能性,如此一来,上帝这个概念的对象也就不是“否定的无”(nihil negativum)。但康德认为,不自相矛盾的概念还远不足以证明该对象就是可能性。如果一个概念借以产生的综合的客观实在性没有特别阐明的话,它就始终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但这种阐明却只能基于经验的原则,而不是基于分析的原理(矛盾律)。所以,康德警告不要从概念的逻辑可能性直接推出事物的实在的可能性。康德还指出,笛卡儿派的“最高存在者”的概念不仅没有扩展我们关于实存的东西的认识,而且也没有给我们提供其实在的可能性。显然,康德在此所说的实在的可能性,就是指一个感官对象的经验可能性,大致对应于“可能性”模态范畴,它并不仅仅基于分析的原理,而是基于经验的综合。所以康德指出:著名的莱布尼茨也未能做到“先天地洞察到一个崇高的理想存在者的可能性”(A602/B630)。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我们需要注意:《纯粹理性批判》中关于逻辑可能性与实在可能性的这一区分,不同于《证明根据》中在可能性的逻辑的、形式的东西与可能性的质料的、实在的东西之间所作的区分,因为可能性的质料的或实在的东西并不是指经验可能性,而仅指一个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其实即一个概念的“内涵”,它恰好相当于《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说的“实在的谓词”,是可以加给某物概念的东西。
总之,由于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所叙述的笛卡儿派的证明包含了两个版本,而且加强版的证明中包含了诸多环节,这就决定了康德在这里所作的批判要远比《证明根据》中的批判全面系统,而且康德在批判中对《证明根据》中的一些表述作出了改变,甚至采用了《证明根据》中没有出现的新提法。
三、《纯粹理性批判》中的“一个逻辑谓词”和“一个实在谓词”指什么
在前文中,我们谈到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把《证明根据》所说的“一个事物的谓词或规定”叫作“实在的谓词”,这是表述上的一个明显的变化,但康德是把“实在的谓词”与“逻辑的谓词”相对的,所以,《纯粹理性批判》对笛卡儿派证明的批判,还包含了“一个逻辑谓词”和“一个实在谓词”的区分,这个“逻辑的谓词”和“实在的谓词”究竟指什么,在国内外康德学界存在广泛的争议,需要专门加以探讨。
康德是在反驳本体论证明一节第九段中提出逻辑谓词和实在谓词这对概念的。他写道:“如果我不是发现混淆一个逻辑谓词和一个实在谓词(一个事物的规定)的幻觉几乎拒绝一切教导的话,我原本希望通过实存概念的一种精确规定来直接了当地瓦解这一挖空心思的论证。人们可以把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用作这个逻辑谓词,甚至主词也可以被自己本身所述说;因为逻辑抽调了一切内容。但规定是一个加在主词概念上、并扩大了主词概念的谓词。因而它必须不是已经包含在主词概念中的。”(A598/B626)这段话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由于这段话前面提到了“混淆一个逻辑谓词和实在谓词的幻觉”,所以人们往往认为,在论述了逻辑谓词之后,“但规定”一句肯定是在论述实在谓词,因而“但规定”中的“规定”也只能对应于前面括号中用来解释实在谓词的“一个事物的规定”,由此认为最后这句话是在说实在谓词是综合命题的谓词,实在谓词必须不是已经包含在主词概念中的。康德《逻辑学讲义》中有关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似乎支持了这一理解:“综合命题在质料上(materialiter)增加认识;分析命题仅仅在形式上(formaliter)增加。前者包含规定(determitationes),后者仅仅包含逻辑的谓词。”[1]Immanuel Kant: Logik. Herausgegeben von Wilhelm Weischede. In: Immanuel Kant Werkausgabe VI,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Erste Auflage 1977, S.542.值得注意:原文中的Bestimmungen和logische Prädikate都是复数。于是,按照许多康德解读者的理解,本体论证明所混淆的逻辑谓词和实在谓词,就是分析命题包含的“逻辑谓词”与综合命题所包含的“规定”。
这是一种流行性的解读。国外学者采纳杰罗姆·舍弗(Jerome Schaffer)[2]Jerome Schaffer:“Existence,Predication,and the Ontological Argument” . Mind,New Series, Vol.71, No.283(Jul.1962), pp.307—325.Oxford Unversity Press on behalf of the Mind Association.、艾伦·伍 德(Allen W.Wood,1978)[3]Allen W.Wood: Kant’s Rational Theolog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and London,1978.、阿利森(Henry E.Allison)[4]Henry E.Allison: 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An Interpretation and Defense. 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 and London,2004.、尼古拉斯·史坦(Nicholas F.Stang)[5]Nicholas F.Stang: Kant’ Argument that Existence is not a Determination. Phis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Vol.XCI No.3, November 2015.等学者意见都把“但规定”当作“实在谓词”,即综合命题所包含的规定。国内学者如赵林[6]赵林:《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看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哲学研究》2006年第4期。、陈艳波[7]陈艳波:《康德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批判中的“存在”论题》,《现代哲学》2009年第4期。、洪楼[8]洪楼:《古典本体论证明及康德的反驳》,《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年第2期。、俞泉林[9]俞泉林:《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对上帝存在本体论证明的批判》,《青年时代》2017年第8期。、杨云飞(2012)[10]杨云飞:《康德对上帝存有本体论证明的批判及其体系意义》,《云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王福玲[11]王福玲:《康德对上帝存有之本体论证明的批判》,《学习月刊》2012年第4期。、胡好[12]胡好:《康德哲学中实在谓词难题的解决》,《现代哲学》2019年第4期。等人也在各自的文章中把“但规定”与“实在谓词”相对应,尽管他们在具体理解上其实也存在诸多分歧。当然,在把实在谓词理解为综合命题所包含的规定时,他们也就康德在此所说的“逻辑谓词”与分析命题所包含的规定对应起来了。[1]参见笔者(舒远招)在其他文章中对这种流行解读模式的批判性分析,如《论康德Sein论题中的逻辑谓词与实在谓词——从二项解读模式到三项解读模式》(《哲学动态》2020年第9期),《实在谓词一定是综合命题的谓词吗?——就Sein论题中实在谓词的理解与胡好商榷》(《现代哲学》2020年第4期)等。这些文章更详细地探讨了“但规定”何以不能与“实在的谓词”,而只能与“实存概念的精确规定”相对应。本文侧重于从《证明根据》关于Dasein的两个命题来论证康德所说的“逻辑谓词”与“实在谓词”,其实就是Dasein(存有)或Existenz(实存)与一个可能事物的谓词或规定。
当学者们作这样一种解读时,自然没有想到把“但规定”中的“规定”与“实存概念的精确规定”对应起来理解,没有意识到康德在此强调“实存概念的精确规定”是综合的实存性命题的谓词,是与第八段强调实存性命题必须是综合命题一致的。同时,人们也没有想到这里所说的一个逻辑谓词和一个实在谓词,就是笛卡儿派加强版证明小前提中的存有(Dasein)和上帝的实在性,也就是《证明根据》中“存有根本不是一个事物的谓词或规定”命题中的“存有”和“一个事物的谓词或规定”。这里的逻辑谓词就是指Dasein或Existenz,只不过笛卡儿派将之当作了同义反复式的实存性命题的谓词,因而需要通过精确规定来真正超出主词概念;就笛卡儿派论证的小前提而言,这里的实在谓词就是上帝概念所包含的实在性(如全能),是上帝这类可能事物的谓词或规定,因而非但不是综合命题的谓词,而且恰好就是分析命题的谓词。[2]在康德反驳笛卡儿派证明的语境中,主要讨论的是上帝的存有与上帝的实在性的关系,故本文在叙述中也聚焦于小前提的这两个方面。诚然,康德在叙述中也提到了一百塔勒,它作为一个可能的事物所具有的规定,也可以算作这里所说的实在谓词。在《证明根据》中康德也谈到了其他可能的事物,甚至谈到了可能的世界。
依据《证明根据》中“存有根本不是一个事物的谓词或规定”来理解这里的逻辑谓词和实在谓词,我们立即可以发现《证明根据》中有别于存有的“一个事物的谓词或规定”,就是这里的实在谓词,等同于这里所说的“一个事物的规定”,两个表达也是相同的。《证明根据》把一个事物的谓词和规定看作可以替换的表达,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像上帝这类可能事物的规定也同时是其谓词,例如全能。而存有,则就是这里所说的逻辑谓词。
如前所述,《证明根据》不仅强调了“存有根本不是一个事物的谓词或规定”,而且在指出存有是一个事物的“绝对的肯定”时,还指出它由此而有别于“每一个本身在任何时候都仅仅在与另外一个事物的关系中被设定的谓词”,这就把存有与系词所设定的谓词区别开来,而后者正好是《纯粹理性批判》反驳本体论一节第十段所说的实在谓词,如“上帝是全能的”这个例句中的谓词“全能的”。康德在提出“Sein显然不是实在的谓词”命题时,指出了Sein要么作为Dasein是对一个事物的肯定,要么作为系词(Sein的逻辑含义)是对一个事物的“某些自在的规定本身”(gewisse Bestimmungen an sich selbst,A598/B626)的肯定。这里所说的一个事物的“自在的规定本身”,正好对应于第九段所说的“一个事物的规定”,而《证明根据》和《纯粹理性批判》同时给出的“上帝是全能的”这个命题中系词所肯定的“全能”即为例子。在《证明根据》中,康德指出全能是上帝的一个特征,与上帝这个主词具有逻辑关系;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指出系词所设定的谓词“全能的”,就是关于全能这个谓词客体的概念,而全能“可以加给上帝概念”,即为上帝概念所包含。
可见,《证明根据》中有别于存有的“一个事物的谓词或规定”对应于《纯粹理性批判》反驳本体论证明一节第九段所说的“实在的谓词”,即“一个事物的规定”(实在谓词客体,如全能);《证明根据》中有别于存有的“每一个本身在任何时候都仅仅在与另外一个事物的关系中被设定的谓词”,则对应于《纯粹理性批判》反驳本体论证明一节第十段所说的“实在的谓词”,即“关于可以加给一个事物的概念的某种东西的一个概念”(实在谓词概念,如全能的)。
在《纯粹理性批判》反驳本体论证明第十段中,康德在说到笛卡儿派对Dasein概念的使用时,还提供了两个例句:(1)Gott ist;(2)Es ist ein Gott。第一个例子是把系词当作肯定上帝存在的逻辑谓词来使用,这就解释了第九段关于逻辑谓词的第一句话“人们可以把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用作这个逻辑谓词”,把系词当作逻辑(实存)谓词来用表明了笛卡儿派在逻辑谓词上的随意性,也表明了它把存在肯定(设定)混淆为系词肯定(设定)的错误。在第二个例子中,主词出现在了谓词的位置上,这就解释了第九段关于逻辑谓词的第二句话“甚至主词也可以被自己本身所述说”。因为康德在此所说的“一个逻辑谓词”特指“实存谓词”,因而当康德说“逻辑抽调了一切内容”时,这首先是指这个实存谓词作为逻辑谓词不是主词概念所包含的一切实在性(实在谓词)。当然,笛卡儿派所肯定的上帝的实存也不具有经验内容,这是通过“实存概念的精确规定”才增加的(增加了一种“可能的知觉”)。
总之,《证明根据》一文在存有(Dasein)与“一个事物的谓词或规定”之间的区分,或者在存有与“每一个本身在任何时候都仅仅在与另外一个事物的关系中被设定的谓词”之间的区分,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被说成是逻辑谓词与实在谓词之分,这是《纯粹理性批判》在术语上的最大创新,也是康德本体论证明批判思想的一个特别的发展。我们不能采用《逻辑学讲义》中关于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谓词的说法来解读《纯粹理性批判》中的逻辑谓词与实在谓词,否则,就不会看到康德对逻辑谓词与实在谓词的区分与《证明根据》批判笛卡儿派的核心思想的关联,也不会看到这一区分是直接针对加强版证明混淆Dasein与上帝的实在性的小前提而提出的。我们的解读也与康德的反驳程序相吻合:康德首先澄清了笛卡儿派在逻辑谓词(Dasein)与实在谓词(上帝实在性或关于上帝实在性的概念)之间的混淆,然后再通过“实存概念的精确规定”来瓦解本体论证明。
——论胡好对逻辑谓词的误读
——笛卡儿自由意志理论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