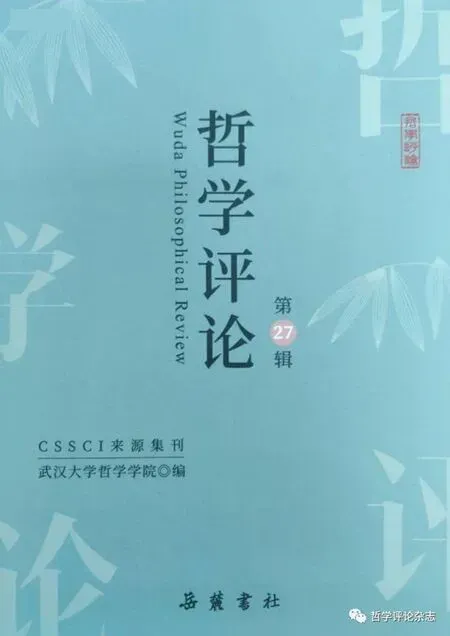原情以见义
——叶梦得的《春秋》诠释
李 颖 张立恩
一、引言
在两宋《春秋》学史上,叶梦得(字少蕴,号石林,1077—1148)有卓著影响。其著有《春秋谳》三十卷、《春秋考》三十卷、《春秋传》二十卷、《石林春秋》八卷、《春秋指要总例》二卷。后二书已佚,《春秋传》尚存,《春秋谳》《春秋考》是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陈振孙认为叶氏《春秋》学著作“辨订考究,无不精详”,[1]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63页。纳兰性德承继此说而予以更高评价,所谓“辩定考究,最称精详”,“其学视诸儒为精”。[2]纳兰性德:《叶石林春秋传序》,《通志堂集》卷12,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242页。真德秀(字景元,后更希元,1178—1235)称其学“辟邪说,黜异端,章明天理,遏止人欲,其有补于世教为不浅”。[1]朱彝尊著,林庆彰等编:《经义考新校》卷183,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3367页。宋人沈作喆(字明远,号寓山,吴兴人)在评价叶氏《春秋谳》时提出,其学对北宋以来的《春秋》学具有某种程度的总结和发展的意味,他说:
国朝六经之学,盖自贾文元倡之,而刘原父兄弟经为最髙,王介甫之说立于学官,举天下之学者,惟已之从,而学者无所自发明,叶石林始复究其渊源,用心精确而不为异论也。[2]沈作喆:《寓简》卷2,《四库全书》本。
所谓“学者无所自发明,叶石林始复究其渊源,用心精确而不为异论”即指明叶氏《春秋》学对北宋以来《春秋》学所具有的总结性地位。元人袁桷(字伯长,1266—1327)在分析汉以后《春秋》学之发展时将叶梦得、刘敞、吕大圭并称,以为“最有功者”,称:“《春秋》家,刘歆尊《左氏》,杜预说行,《公》《穀》废不讲。啖、赵出,圣人之旨微见,刘敞氏、叶梦得氏、吕大圭氏其最有功者也。”[3]袁桷:《龚氏四书朱陆会同序》,《清容居士集》卷21,《四库全书》本。可见,叶氏《春秋》学在两宋乃至整个《春秋》学史上都有重要价值。关于其学,学界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4]可参:潘殊闲:《叶梦得〈春秋〉类著述考论》,《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姜义泰:《叶梦得〈春秋传〉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8年;胡玉芳:《叶梦得的〈春秋〉学》,《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2010年第2辑;许瑜容:《叶梦得〈春秋谳〉研究》,高雄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张悦:《叶梦得〈春秋〉学研究》,扬州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但似不够充分,未能揭明其学所具有的内在义理系统,[5]叶梦得论其《春秋》学三书(《谳》《考》《传》)之关系称:“自其《谳》推之,知吾之所正为不妄也,而后可以观吾《考》。自其《考》推之,知吾之所择为不诬也,而后可以观吾《传》。”(《春秋考原序》,《春秋考》卷首,《四库全书》本)周中孚称,“三书者阙一则无以见石林之用心也”(《郑堂读书记》卷10,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165页)。因此,有学者提出,叶氏《春秋》学“三书具有极强的逻辑关系,前两书为破,后一书为立”(戴维:《春秋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374页),其《春秋》学所走的是一条“批判—考证—立说之路”(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399页)。本文认为这一义理系统可概括为“原情以见义”,即以“原情”为基础,批判三传之学,建立其《春秋》观、凡例与褒贬法度。
二、叶梦得的“原情”说
叶氏对“原情”概念有三种相互关联又有所不同的理解:
(一)原其情感
即对经文事件中人物情感所做的一种“同情的理解”。《左传·隐公十一年》,隐公被桓公与公子翚合谋弑杀,《春秋》于桓元年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叶氏指出,先君卒后,嗣子立于丧次,逾年改元具有合理性:
天子崩,诸侯薨,嗣子立于丧次,礼与?礼也。天子七日而殡,诸侯五日而殡。既殡,大臣以其受命于前王者,即柩前而告之曰顾命,礼与?亦礼也。然则何以逾年始书“即位”、称“元年”?有丧次之位,有南面之位。丧次之位,所以继体也。一年不二君,故虽即位,未成其为君。……旷年不可以无君,故至于明年,天道一变,前王之义终矣,然后始以其正月朔朝庙,见先祖,以所受命者告焉,而称元年,天子称王,诸侯于其封内称爵,自周以来未之有改也。[1]叶梦得:《叶氏春秋传》卷3,《四库全书》本。
其次,他指出,若先君被弑,则《春秋》不书新君“即位”,以此显示继位之君受恩于先君,他说:
然则继故不书即位,岂不即位与?原其情,有所不忍而不书也,……死君而代之位,孰以为忍?而况于继故?继故不书“即位”,所以弭天下之争,而示有恩于先君者,《春秋》之义也。[2]《叶氏春秋传》卷3。
可以看出,其说是对《穀梁传》观点的继承和改造。[3]《穀梁传》说见桓元年传文。其在《穀梁传》的基础上提出“原其情”说,认为《春秋》对于先君被弑,不书新君继位,是出于对继位者不忍继位的内心情感的一种推测和体会。
(二)“揆之以情,所以尽天下之变”
即对经文中人物所处的复杂现实处境(“天下之变”)的一种充分考察(“揆之以情”)。闵元年,“季子来归”,三传都认为经文含有对季子之褒扬,[1]《左传》:“‘季子来归’,嘉之也。”《公羊》:“其称季子何?贤也。其言来归何?喜之也。”《穀梁》:“其曰季子,贵之也。其曰来归,喜之也。”但都未说明为何褒扬季子。何休认为经文褒扬季子是“嫌季子不探诛庆父有甚恶,故复于托君安国贤之。所以轻归狱,显所当任,达其功”。[2]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223页。据《左传》,公子庆父在庄三十二年弑杀继位的公子般,执政的公子季友只诛杀了公子庆父的替罪者而未追究公子庆父,《公羊传》认为季友的做法符合亲亲之道。季友的做法看起来与赵盾不追究弑杀晋灵公的赵穿的做法相同,《春秋》认为赵盾包庇赵穿,从而把弑君之罪归于赵盾。何休之说是说季友的做法与赵盾不同,因此,徐彦认为“嫌季子不探诛庆父有甚恶”是说“嫌有赵盾不诛赵穿而获弑君之恶,故曰甚恶也”。[3]《春秋公羊传注疏》卷9,223页。叶氏对何休、徐彦之说有所继承,同时又从原情角度对《春秋》褒扬季友的合理性进行说明。
依《左传》,庆父弑子般而季友不能讨其罪,乃至于闵公二年庆父又指使鲁大夫弑闵公,可见,似季友对于闵公被杀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受贬责,但《春秋》不但不贬,反而褒之。叶氏认为:“《春秋》之与夺,有正之以法者,有揆之以情者。正之以法,所以立天下之教。揆之以情,所以尽天下之变。”[4]《叶氏春秋传》卷8。就是说,要理解《春秋》之褒季子,就要充分考察其现实处境。他从当时鲁国的具体情势来分析:
使季子始得国而即诛庆父,不幸不能胜,身死而庆父无与制,虽闵公,其可保乎?则鲁固庆父之国矣。二者权其轻重,宁失之缓,不可失之急,故终能图庆父而不丧其宗国,此《春秋》所以原其情而不贬也。[1]《叶氏春秋传》卷8。
在解释庄三十二年“公子庆父如齐”时,叶氏亦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他认为《春秋》对季子所处的复杂处境有充分考量,他说:“季子于此,势不得两全……《春秋》盖察之矣”,[2]《叶氏春秋传》卷7。由此肯定季子行为的合理性,所谓“季子之谋鲁者无遗策,是固君子所以成其意者”。[3]《叶氏春秋传》卷7。可见,其在此所谓“原情”构成正确理解《春秋》褒贬之合理性的基础。
依上理解,叶氏提出,孔子基于对当时复杂现实的充分考察,对那些在周之礼制下看来是僭越的诸侯纳君、救伐等行为给予肯定,他说:
春秋之时,王政不行于天下,诸侯更相侵犯,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讨,其因以灭亡者多矣,则诸侯危亡有能救灾恤患而相与为援者,君子或原情而许之也,故失国而纳,被伐而救,皆得与善辞。[4]《春秋考》卷8。
(三)探明事实原委
僖九年“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文十四年,“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奚齐与舍都是继位且未逾年成君者,但《春秋》书二人被杀却有“杀”与“弑”的区别,叶氏认为这种用词差异正是《春秋》原情观念的体现,他说:“弑君,天下之大恶也,可以未逾年而薄其罪与?曰《春秋》以名定罪,若其义则亦各视其情而已矣。”[5]《叶氏春秋传》卷9。他认为尽管商人与里克都是杀未逾年之君,但“商人之弑以己也取而代之,里克之弑以文公也,盖以纳文公焉”,[6]《叶氏春秋传》卷9。故《春秋》对二者区别对待,他说:
公子商人,齐大夫之三命者也。舍,未逾年之君也,何以称弑其君?恶商人也。成之为君,则可名以弑。不成之为君,则不可名以弑。商人,取舍而代之者也。君子以为异乎里克之杀奚齐,故成舍之为君者,所以正商人之弑也。[1]《叶氏春秋传》卷12。
依此理解,叶氏提出“《春秋》者,原情以定罪”的观点。[2]《叶氏春秋传》卷1。“探明事实原委”是叶氏有关“原情”的主要观点,贯穿于其对所有经文的解释,以上两种对“原情”的理解可以看作是这一观点的合理推衍。在很多经文的解释上叶氏虽未明言“原情”,但实际上其诠释中体现出的正是这种探明事实原委以解经的精神,如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三传都认为此条经文的真相是晋文公召王,《春秋》为天子避讳,故书“天王狩于河阳”。[3]三传说见僖二十八年三传传文。叶氏也承认晋文公召王的事实,但他不认为经文书“狩”是孔子为回护周王权威而进行的避讳,而认为“狩”是周王为本次行为赋予的名称,他说:
狩者何?天子适诸侯曰巡狩,诸侯见天子曰述职。巡狩者,巡所守也。何以书?前以王之自往则不书,今以晋侯召王而往则书,盖王以巡狩为之名也。[4]《叶氏春秋传》卷10。
他认为以往经文不书天王之狩是因为那是天王自己去巡狩,而此次是晋文公召王,所以要记载,但《春秋》不会改变天王赋予巡狩之名的事实,他说:
吾何以知晋侯召王而王以狩为之名与?《春秋》有讳而为之辞者矣,未有讳而变其实者也。……使晋侯实召王而往,《春秋》虚假之狩,是加王以无实之名而免晋以当正之罪,孰有如是而可为《春秋》乎?……不可以晋侯而苟全,此《春秋》垂万世之义也。[5]《叶氏春秋传》卷10。
叶氏认为《春秋》中确实存在避讳,但不会因此改变事实,在此例中,若孔子为避讳晋文公召王而书“天王狩于河阳”,这就不仅虚造周天子巡狩的事实,而且也免去晋文公以下犯上之罪,这不符合《春秋》之义,因此他坚持认为“狩于河阳”是天王本意。
基于对“原情”的理解,叶氏在继承中唐以来学风的基础上提出综合前说、择善而从的解经学立场,所谓“吾以是知学者求之不可不博,而择之不可不审也”。[1]《春秋考原序》。求之、择之须有客观判断标准,他认为这种标准就是既要“当于义”,也要“验于事”。
吾所谓失者,非苟去之也,以其无当于义也,盖有当之者焉。吾所谓非者,非臆排之也,以其无验于事也,盖有验之者焉,则亦在夫择焉而已。[2]《春秋考原序》。
在叶氏《春秋》学中,所谓事与义,即原情与《春秋》义理之间的关系,两者存在着逻辑上的先后关系,这就是以原情为基础诠释经义,其逻辑起点则是由原情而展开的对三传之学的批判。
三、叶梦得对三传之学的批判
叶氏对三传的基本判断是:“《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以不知经故也。《公羊》《穀梁》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以不知史故也。”[3]叶梦得:《叶氏春秋传原序》,《叶氏春秋传》卷首。故其对三传的批判也集中于事与义两方面。
(一)论三传说事之失
叶氏认为《左传》记事存在增衍和虚构。隐十年“秋,宋人、卫人入郑。宋人、蔡人、卫人伐戴。郑伯伐取之”。《左传》曰:
宋人、卫人入郑。蔡人从之,伐戴。八月壬戌,郑伯围戴。癸亥,克之,取三师焉。宋、卫既入郑,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败。
对比可知,经文只书“秋”,而传文书“八月壬戌”,而且经传对此次事件的叙述也存在分歧,传文以宋人、卫人、蔡人三师伐戴,尔后郑伯围戴,克之。依此,传文似是说宋、卫、蔡三师取戴之后,郑伯围戴而克三师,但从经文本身并不能看出这层意思。叶氏由此认定《左传》增衍事实,他说:“经言宋、蔡、卫人伐戴,传言郑伯围戴,是谓三师已得戴,郑伯复从而围之,其言固已衍于经矣。”[1]叶梦得:《春秋左传谳》卷1,《春秋三传谳》,《四库全书》本。
叶氏对《左传》记事亦有所取,但总体来说,其对《左传》更多的是批评,他说:
凡《左氏》载事,与经背者,不可概举。吾初以为理可妄推,事不可妄为,审无是事,《左氏》安敢凿为之说?及反复考之,然后知《左氏》之好诬,真无所忌惮,犹之六国辩士,苟欲借古事以成其说,虽率其意为之不顾也。[2]叶梦得:《统论》,《春秋考》卷3。
叶氏认为《公羊传》说事之失有三:一是“闻之而不审”。隐六年“郑人来输平”,《公羊传》曰:
输平者何?输平犹堕成也。何言乎堕成?败其成也,曰:“吾成败矣”,吾与郑人未有成也。吾与郑人则曷为未有成?狐壤之战,隐公获焉。然则何以不言战?讳获也。
叶氏认为《公羊传》对经文事实理解有误,他说:“输者,归物之名,非堕物之名,则输平不得言堕成。”[3]叶梦得:《春秋公羊传谳》卷1,《春秋三传谳》。《公羊传》之误是其“误以狐壤之战在此时,讳隐公之获,而以输平言之”。但“据《左氏》,狐壤之获,盖公为太子时事,在春秋前,《公羊》不传事,窃闻之而不审,是以并经意失之也”。[4]《春秋公羊传谳》卷1。
二是“不知其事而妄意之”。昭二十三年,“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父。胡子髡、沈子楹灭,获陈夏啮”。《公羊传》曰:“此偏战也,曷为以诈战之辞言之?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叶氏认为,据《左传·昭公二十三年》传文,吴人实以诈战取胜,并非偏战:
据《左氏》,鸡父之战,吴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与陈,三国争之。吴乘其后而击,遂败三国。此正传所谓诈战也,故经书“败”不书“战”,传何以知其为偏战而以诈战言之乎?[1]《春秋公羊传谳》卷6。
他认为《公羊》之误是因其“不知其事而妄意之”。[2]《春秋公羊传谳》卷6。
三是“微闻其事而不闻其实”。庄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陈,葬原仲”。《公羊传》认为《春秋》大夫不书葬,其书葬原仲是为表明公子友如陈看起来是为公事而行,但又不完全是为公事,而是与其私行相通。[3]参黄铭、曾亦:《春秋公羊传(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205页。叶氏驳之:
此何以书?为其将以图国也。庄公在位久,未有嫡子。子般,孟任之子,庶长而得立者也。庆父、叔牙通乎夫人,欲舍般而立庆父,季子惧,不能正,托葬原仲而之陈以为之图。庄公病,召公子友于陈,于是杀叔牙而立子般,君子以是录其行也。[4]《叶氏春秋传》卷7。
他认为经文所书是要表明公子友去陈是为“图国”。可见,《公羊传》之说不确,他认为《公羊传》此失是因其“微闻其事而不闻其实”。[5]《春秋公羊传谳》卷2。
叶氏认为《穀梁传》说事存在“不见事实而妄言经意”[6]叶梦得:《春秋穀梁传谳》卷6,《春秋三传谳》。的问题。《穀梁传·昭公二十一年》经:“蔡侯东出奔楚。”传曰:“东者,东国也。何为谓之东也?……恶之而贬之也。”叶氏驳之,他认为“东”是蔡朱,与东国为两人:
按蔡朱与东国自两人。朱,平公庐之子,而东国,隐太子之子,平公之弟也。……传不知其实,误以“朱”为“东国”,疑“东”与“朱”文相近,故改为东,遂妄为之说,谓经贬东国而去其二名。[7]《春秋公羊传谳》卷6。
他认为《穀梁传》之说正是其“不见事实而妄言经意”的表现。由上其对三传说事之失的批评可见,其说乃奠基于原情观念。
(二)论三传说经之失
隐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左传》曰:“书,时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为霖。平地尺为大雪。”叶氏驳之:
《月令》:始雨水。雷乃发声,始电。仲春之候也。夏之仲春为周之四月,今以三月大雨震电,故书,不在其三日以往也。自癸酉至庚辰,历八日,既已大雨震电,而复大雨雪,故书,不在其平地尺也。此皆记异尔,传不知此而妄为之例。[1]《春秋左传谳》卷1。
而且他认为,下雨超过三天、下雪超过一尺的现象在生活中很常见,如果《春秋》对于这些现象都要记录的话就会不胜其烦:
《左氏》于“大雨,震电”,误以为“大雨霖以震”为例,曰“凡雨,自三日以往为霖”,不惟非经所有,雨三日以上,盖不胜书矣。[2]《春秋考》卷6。
因此,他认为《春秋》记录大雨、震电、大雨雪不是出于这些原因,而是因其要么为灾,要么失时。他认为《春秋》用周正,其解“三月癸酉,大雨,震电”曰:“建寅之月未雨,雨水而大雨,雷未发声而震电”,[3]《叶氏春秋传》卷2。解“庚辰,大雨雪”时称其发生在“建寅之月”。[4]《叶氏春秋传》卷2。建寅之月为夏历正月,周历三月,可见他认为《春秋》用周正,事实上其《春秋考·统论》就明确指出“正朔,王法之所谨,不得不本周正也”。[5]《春秋考》卷2。在他看来,依《月令》所述,大雨震电应发生在夏历二月,而《春秋》所记在三月,周历三月为夏历正月,显然大雨、震电、大雨雪的出现失时。他认为造成《左传》说经之失的原因在于“《左氏》不传经,虽偶闻之而不能必是,以参用所传而幸其或中也”。[1]《春秋左传谳》卷3。
叶氏批评《公》《穀》经说的一个方面表现在对二传日月条例的反驳。隐十年,“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公羊传》曰:“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所谓“取邑不日”是《公羊传》建立的一个关于日的条例,而此条经文书日,《公羊传》认为是《春秋》要表示“甚之”之意,这又是其所建立的有关“取邑不日”例的一个变例。叶氏驳其说,在他看来,经文书内取外邑,详略不同,有只书时者,如僖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娄,取须朐”,也有只记载到月的,如宣四年春“王正月,……公伐莒,取向”,也有记载到日的,如文七年春“三月甲戌,取须朐”,不存在《公羊传》所谓“取邑不日”例,经文不书日是为表明“伐取同时”,[2]《春秋公羊传谳》卷1。此条经文中取郜、取防不同日,只能分别书日,如果非要说成是“甚一月再取”,那么就与文七年春“三月甲戌,取须朐”的书法矛盾,因为,文七年春三月除了记载“取须朐”,并没有其他取邑的记录。[3]参《春秋公羊传谳》卷1。
隐元年,“公子益师卒”,《穀梁传》曰:“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恶也。”叶氏认为《穀梁传》此说是其不知经文之事而又基于其日月条例进行臆想的结果:
益师之恶,于三传皆无见,《穀梁》何由知之?盖见内大夫多日卒,故直推以为例尔,以此见《公羊》《穀梁》以日月为例,皆未尝见事实,特以经文妄意之。[4]《春秋公羊传谳》卷1。
他指出若《穀梁传》之说成立,“则公子牙盖将篡君者,季孙意如亲逐昭公者,而牙书七月癸巳卒,意如书六月丙申卒,谓之无恶,可乎?”[5]《春秋公羊传谳》卷1。可见《穀梁传》日月条例之误。
在叶氏看来,《公》《穀》附会日月条例的根本原因是其不知经文之事,即未能原其情,他说:“《公羊》《穀梁》专以日月为例,……故拘一遍以为例,亦坐不知事之故,使少知之,必能警矣。”[1]《春秋考》卷5。他认为对史书来说,记事必系以日月,《春秋》既是删削鲁史而来,就不可能以日月为例,否则,若史书记事时原本就存在阙日月,那么,日月条例就无法成立,他说:
记史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然与?曰然。《春秋》以日月为例与?曰否。系事以日月,史之常也,有不可以尽得,则有时而阙焉。《春秋》者,约鲁史而为之者也。日月,史不可以尽得,则《春秋》亦安得而尽书哉?必将以为例,有当见而史一失之,则凡为例者,皆废矣。故日月不可以为例,为是说者,《公羊》《穀梁》之过也。[2]《叶氏春秋传》卷1。
由上分析可见,叶氏对三传之学的批判奠基于其原情观念。其对三传说事之失的批评固然如此,此由其訾议《左传》增衍和虚构事实,《公羊传》“不知其事”,《穀梁传》“不见事实”即可看出。其对三传说经之失的批评亦如此,如其批评《公》《穀》二传日月条例时所谓其“未尝见事实,特以经文妄意之”即是。
四、叶梦得的《春秋》观
(一)“ 《春秋》者,史也;所以作《春秋》者,经也”
叶氏认为从材料的来源上说,《春秋》据鲁史而成。《左传·桓公十七年》“辛卯,弑昭公”,此事不见于经,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春秋》有所绝而不书”,叶氏驳之,他认为:“《春秋》据鲁史,郑乱不以告,则鲁不得书于策,鲁史所无有,则《春秋》安得而见哉?”[3]《叶氏春秋传》卷4。依其说,则其对杜预所主张的“经承旧史、史承赴告”[4]皮锡瑞:《春秋》,《经学通论》,华夏出版社,2011年,365页。说有所继承,事实上,其即称:“经但从其告则书之尔”,[1]《春秋公羊传谳》卷6。又称:“经者,约鲁史而为者也。史者,承赴告而书者也。诸国不赴告,则鲁史不得书,鲁史所不书,则《春秋》不得载。”[2]叶梦得:《统论》,《春秋考》卷3。叶氏还提出“《春秋》者,史也,史者各从其先后日月以纪事,而非通一代之事追记而书者也”。[3]《春秋公羊传谳》卷6。他还从《春秋》之名的角度指出“孔子之作《春秋》,亦史而已”,他说:
鲁之有是名久矣,故《公羊》《穀梁》或言以《春秋》为《春秋》,或言“不修《春秋》”之类,则孔子之作《春秋》,亦史而已,故其书之体皆与史同。[4]叶梦得:《统论》,《春秋考》卷6。
依上所述,叶氏似以《春秋》为史书,实则不然,其固然承认“史者,承赴告而书者”,但从其所谓“经者,约鲁史而为者也”来看,又与杜预所主张的“经承旧史”说有所不同,比如他明确提出“赴告未必皆以实”,[5]《春秋考》卷3。因此他认为孔子作《春秋》时对鲁史做了删订:
吾故以为《春秋》从史,史从赴告,赴告之是非,已定于初,其有不实,孔子必有以核之,可正则正,不可正则阙之而已,故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6]《春秋考》卷3。
可见,叶氏反对以《春秋》为史,他说:
《春秋》善善恶恶,以示劝沮于天下后世之书,非徒为史以记事之书也。苟录于经者,其义有取焉,若事有阙,不足见义,则删之而已,焉用不革而必书之哉?[7]《春秋公羊传谳》卷6。
又说:“夫《春秋》者,史也;所以作《春秋》者,经也。故可与通天下曰事,不可与通天下曰义。”[8]《叶氏春秋传原序》。
(二)“ 《春秋》盖天事,非止天子之事”
叶氏认为“所以作《春秋》者,经也”,就是说《春秋》中蕴含着孔子的“一王之法”,涵盖了君臣父子之天理、政教礼治之人事以及日、星、雷、电、螽、螟、蝝、蜚等世间万物,“而吾(孔子)以一王之法笔削于其间,穹然如天之在上,未尝容其心,而可与可夺,可是可非,可生可杀,秋毫莫之逃焉”。[1]《叶氏春秋传原序》。他还提出《春秋》书十二公是“法天之大数”,他说:“其书断取十有二公,以法天之大数,备四时以为年,而正其行事,号之曰‘春秋’,以自比于天。”[2]《叶氏春秋传原序》。
依上理解,他对孟子所云“《春秋》,天子之事”(《孟子·滕文公下》)的观点提出批评: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此得之矣,犹未尽也。夫王政不行,以褒贬代天子赏罚,以为天子之事可也。然诸侯有善恶,固可代天子而行,天子有善恶,则孰当代而行之乎?《春秋》有贬诸侯而去王者矣,诸侯而无王,则王之所绝也,然则《春秋》盖天事,非止天子之事也。[3]叶梦得:《统论》,《春秋考》卷1。
按照《春秋》为天事,他又提出“《春秋》书大事,不书小事,书变事,不书常事”,[4]《叶氏春秋传》卷3。而变事、大事在本质上都属非常之事,如他认为“天子巡守,诸侯来朝于方岳之下”合乎礼制,但僖二十八年经文却书“公朝于王所”,他认为因为这是非常之事,他说:“朝于王所何以书?非常也。晋侯既胜,将合诸侯以尊王室,遂为践土之盟,作王宫于衡雍,王于是往而即焉。”[5]《叶氏春秋传》卷10。
(三)据实书之与《春秋》阙文
不过,叶氏并未就此倒向义理先行而以事为义之附庸,而是主张“《春秋》据其实而书之”。[1]《叶氏春秋传》卷19。襄七年,“郑伯髡顽如会,未见诸侯,丙戌,卒于鄵”,三传都认为郑伯是被弑,叶氏则从“经皆书以实”[2]《春秋左传谳》卷6。的立场上反对此说,他认为若郑伯确为被弑,而《春秋》不书“弑”,这不符合《春秋》之义,他说:
髡顽之卒,三传皆以为弑。《左氏》以为以疟疾赴,固陋矣。《公羊》《穀梁》以为诸大夫因欲从楚而弑,故不书弑,则是纵失弑君之罪,岂《春秋》之义哉?是盖以诸大夫不与髡顽而适卒,故或者疑之以为弑,《春秋》不然之也。[3]《叶氏春秋传》卷15。
可见,叶氏《春秋》观奠立于其原情思想之上。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后世流传的《春秋》中存在阙文,但此阙文非孔子所阙而是“经成而后亡之”,[4]《叶氏春秋传》卷3。如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左传》认为经文中的“甲戌、己丑”是因“陈侯鲍卒,再赴也”。《公》《穀》都认为是“以二日卒之”。叶氏之说与三传都不同,他认为陈侯鲍卒于己丑日,而经文“甲戌”之后无文,是“经成而后亡之”,他说:
《春秋》有阙文与?曰然。仲尼书而阙之与?曰否。经成而后亡之也。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不及见其全文而与之正,犹无马不能借人而与之乘也,是以君子慎乎阙疑。……故《春秋》无阙文,而先儒之说乃以为“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纳北燕伯于阳”谓之公子阳生,曰“我知之而不革”,夫如是,则《春秋》何以定天下善恶而示劝沮与?吾是以知凡《春秋》之阙文,非仲尼之阙疑,皆经成而后亡之者也。[5]《叶氏春秋传》卷3。
他认为《春秋》据实,但“《春秋》则非史也,将别嫌疑以为万世法,则何取于多闻哉?可及者及之,不可及者则去之而已,所以为《春秋》者,不在是也”。[1]《叶氏春秋传》卷3。故孔子之《春秋》无阙文。
五、叶梦得《春秋》学之凡例与褒贬法度
叶氏以其原情思想为基础,建立其《春秋》凡例与褒贬法度。其建立了一系列凡例,兹举二例:
(一)侵、伐例
隐二年,“郑人伐卫”,叶氏云:
声其罪而讨曰“伐”,伐备钟鼓。不声其罪而直讨曰“侵”,侵密声,有钟鼓而不作。罪大则伐,小则侵。侵、伐皆讨罪之辞,服则止矣,故不书胜败。贼贤害民则伐之,负固不服则侵之,大司马之法也。天子在上,诸侯不得擅相讨。天下无道,征伐自诸侯出,凡伐之志,皆恶也。[2]《叶氏春秋传》卷1。
叶氏首先分析了侵、伐的区别,并指出《春秋》记载侵、伐的基本原则。在他看来,侵伐的目的不是为战胜对方,而是要求其服罪,因此“服则止矣,故不书胜败”。但在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征伐出自诸侯,所以他认为凡经书侵伐都是要表达对侵伐者僭越天子权力的贬斥。叶氏此说仍然是建立在原情的基础上,他通过引证《国语》中的材料指出侵伐的区别及《春秋》书侵伐为贬的理由,他说:
吾何以知侵、伐之辨欤?宋人杀昭公,晋赵盾请师以伐宋,发令于大庙,召军吏而戒乐正,曰:“三军之钟鼓必备焉。”赵同有疑,盾曰:“大罪伐之,小罪惮之。袭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备钟鼓,声其罪也。战以于、丁宁,儆其民也。袭侵密声,为暂事也。”乃使旁告于诸侯,治兵振旅,鸣钟鼓,以至于宋。犹行先王之政也。春秋之世,征伐自诸侯出,虽无适而不为僭,然其名则窃取之矣。[1]《叶氏春秋传》卷1。
(二)伯讨、侯执、人执例
叶氏认为侵伐为讨罪,若被声讨者不服,则要入其国,执其君以问罪,就是说经文凡书执都是表示讨其罪,他说:“拘而讨罪曰执。”[2]《叶氏春秋传》卷4。在此基础上,他分别伯讨与非伯讨,僖二十八年,“晋侯入曹,执曹伯,畀宋人”。叶氏曰:“侵而不服,然后入之,数其罪而执其君,伯讨也。”[3]《叶氏春秋传》卷10。他认为经文记载伯讨有一定的条例,就这条经文来说,他提出“侯执之为伯讨”的观点。这一条例的建立是其在三传基础上进行的创新,他说:“《穀梁》固不见其事,《左氏》见之而不能辨,盖不知侯执之为伯讨也。《公羊》虽知之而不悟,其与京师楚同文,亦求之经者不审尔。”[4]《叶氏春秋传》卷10。
不过“侯执”只是判断是否为伯讨的一个因素,如果经文涉及“归”,还要看被执者是否被归于京师,他说:“诸侯有罪,执而归于京师者,伯讨也,故以侯执执而不归京师者,非伯讨也。”[5]《叶氏春秋传》卷9。成十五年,“晋侯执曹伯,归于京师”,叶氏认为经文书“归于京师”则为伯讨:
曹伯庐卒于师,曹人使公子负刍守,公子欣时逆曹伯之丧,未至,负刍杀世子而自立,晋侯为是为戚之会,执负刍以归京师,伯讨也,故以侯执。[6]《叶氏春秋传》卷14。
叶氏认为经文区分伯讨与非伯讨,还可从称君与称人的角度看,他说:“以伯讨者称君,不以伯讨者称人。”[7]《叶氏春秋传》卷4。依此条例,“晋侯入曹,执曹伯”就是伯讨。对《春秋》中有关“人执”的经文,叶氏亦发挥人执非伯讨之说,庄十七年,“齐人执郑詹”,他说:“称‘人’以执,非伯讨也。”[1]《叶氏春秋传》卷6。其对称“人”以执非伯讨之例的分析仍然是建立在原情基础上的,如在此例中,他说:
詹,郑大夫之再命者也。……詹未三命,则非郑之知政者也。郑伯与宋公会于鄄,则同好矣,未几而郑侵宋,故宋复主兵,而齐卫共伐之。至同盟于幽而郑服,故以詹为说而执焉,郑非詹之所得任,则执之非其罪者也。[2]《叶氏春秋传》卷6。
叶氏据庄十五年、十六年经文[3]庄十五年:“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会于鄄”,“郑人侵宋”,十六年“宋人、齐人、卫人伐郑”,“冬十有二月,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分析了郑詹被执的政治历史背景,他认为詹非三命大夫,不是郑国执政者,因此齐人执郑詹只是以之为说辞,非其罪而被执,故经书“人执”表明其非伯讨。
(三)褒贬法度
叶氏建立凡例的目的是要见褒贬法度,比较典型的就是他通过吸收前人观点而建立起来的称名、称字、称人例而表达的褒贬义理。在他看来,依周制,不同官爵的人有不同称呼,若《春秋》在记载某个人物时没有采取与其官职相应的称呼,就说明其中有褒贬,他说:
盖经有书名以见贬者,不应名而名,所以为贬也,宰渠伯纠是已。有去名以为贬者,应名而不得以名见,所以为贬也,齐仲孙湫是已。[4]《春秋左传谳》卷2。
依其说,则《春秋》也应存在以下情况。一是《春秋》虽书其名,但却无褒贬,如僖二十九年,“介葛卢来”。叶氏说:“介,附庸之国也。葛卢,介君之名也。附庸之君以字见,葛卢书名,不满三十里之国也。”[5]《叶氏春秋传》卷10。就是说,《春秋》记载介国之君而称其名,不含褒贬。叶氏将这种观念也贯穿到其对称字的理解上,隐元年,“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公羊传》认为“仪父者何?邾娄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为称字?褒之也”。叶氏反对此说,他认为“仪父”确是称字,但无褒贬:
邾,鲁附庸之国也。五等之国,不能五十里,附于诸侯,以达于天子曰附庸。视王之大夫,四命皆以字见。[1]《叶氏春秋传》卷1。
事实上,针对以上两例,其在《穀梁传谳》中就明确指出:“葛卢称名、仪父称字,法自当书,非进之也。”[2]《春秋穀梁传谳》卷3。
二是《春秋》对于应书名而不书名并采用其他称呼的,存在褒贬。闵二年,“齐高子来盟”。据《左传》,鲁庄公死后,鲁内乱,齐国在闵公二年派大夫高傒再次到鲁慰问。依叶氏,“大国、次国之大夫,小国之卿,亦再命,亦当以名见”,高傒来鲁慰问,《春秋》应书其名,但经文没有记其名,叶氏云:
高子,齐大夫高傒也。子,男子之美称也。何以不言名?褒之也。闵公弑,庆父奔,季子与僖公方适邾,齐侯使高子以南阳之甲至鲁,未知其窥之与?平之与?齐侯之命高子,将曰:可则盟,不可则不卒与。季子立僖公,盟国人而定其位,则高子之为也。《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遂者则遂焉,高子遂之善者也。[3]《叶氏春秋传》卷8。
像以上这种以不同称谓表达的褒贬就是叶氏所理解的《春秋》法度,亦即前述所谓孔子的“一王之法”,他认为“《春秋》因人以立法,不穷法以治其人。因事以见法,不因法以穷其事”。[4]《叶氏春秋传》卷7。从其对经文之诠释来看,其所谓《春秋》法度属于传统儒家所主张的基本伦理原则,如弑君之贼应被诛杀,诸侯有安邻国之义,肯定亲亲之义等。[5]以上诸义分别见其对以下经文之诠释,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闵元年“齐仲孙来”,庄九年“齐人取子纠杀之”,其说见《叶氏春秋传》卷3、8、6。其将此视为孔子的“一王之法”,表明他理解的“一王之法”与《公羊》学不同,[1]在《公羊》学中,“一王之法”往往被理解为作为素王的孔子之法。(参李颖、张立恩:《孔子成〈春秋〉何以乱臣贼子惧?——汉唐〈春秋〉学的视域》,“二、褒贬立法惧贼说之理论困境及汉儒之解决方案”,《哲学评论》第25辑,岳麓书社,2020年,第39—43页)其目的是要维护周代的政治秩序,事实上他说:“ 《春秋》本以周室微弱,诸侯僭乱,正天下之名分。”[2]《春秋公羊传谳》卷1。
六、结语
综上所述,叶梦得基于对“原情”的重视和独特理解,指出三传记事和说经之失,提出《春秋》虽源于鲁史,据实记事,但孔子作《春秋》却并非为著史,而是要法天,以别嫌疑为万世法,由此叶氏建立其凡例与褒贬法度。可见,叶氏基于啖赵以来的新《春秋》学风,扬弃三传之说,试图重构《春秋》诠释之凡例与褒贬法度,就此而言,称其说是对北宋以来的《春秋》学的某种程度的总结和发展,亦不为无据。不过,毋庸讳言,其说也存在误解前人和附会之处,如前文所引隐九年“大雨,震电”之例,叶氏认为《左传》主张《春秋》以“大雨霖以震”为例并因此书之,这是对《左传》的误解,因为《左传》明确说“书,时失也”,这与叶氏的看法是一致的。对此前人已有所见,如《四库总目》就称其《春秋》学“虽辨博自喜,往往有澜翻过甚之病”。[3]《四库全书总目》卷26,“春秋谳二十二卷”条,中华书局,1997年,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