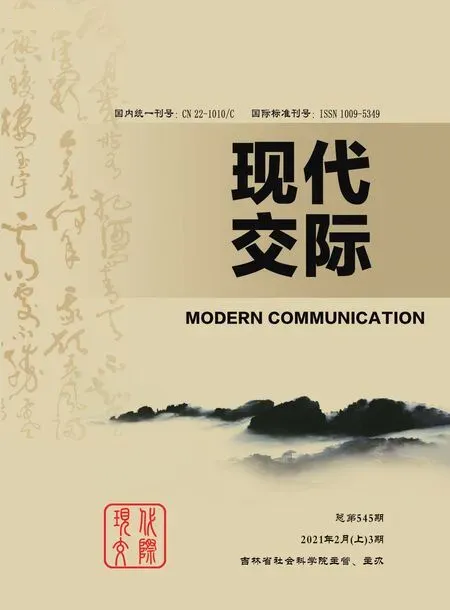吉姆佩尔的伦理困境
——“傻瓜吉姆佩尔”新解
戚宗海
(1.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北京 100089;2.南方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515)
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犹太作家艾萨克·辛格(I.B.Singer)在小说《傻瓜吉姆佩尔》中创造了一个经典“傻瓜”形象:吉姆佩尔。欧美文学批评界多着眼于吉姆佩尔是“圣徒”还是“天真傻子”之辨,典型者如阿尔弗雷德·卡津(A.Kazin)、欧文·豪(I.Howe)等学者[1]20-207。中国学者乔国强认为吉姆佩尔是“真傻”,他的“偏执、离奇、可爱”是犹太人“特有的”性情,是一种“生活智慧”,是“由他们在历史上的尴尬地位和蒙受过多苦难所造成的”[2]。学者刘俐俐认为,吉姆佩尔不傻,他知道“什么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他只是在“魔鬼”的诱惑和“拉比”的教导之间穿梭而已。他的“悲剧”其实反映了辛格对人类在“苦难”与“非正义”处境中的困惑[3]。学者傅晓微认为,国内学界研究者对意第绪语与犹太宗教文明了解不够,对“吉姆佩尔”之“傻”的解读多有偏误[1]210-212。其实,若撇开纯粹的“傻”之真假之辨,反思一下读者(批评者)在“傻”与“不傻”之间的犹豫难断,恰似吉姆佩尔游移于做世俗之“聪明人”还是做上帝之“聪明人”的两难处境。这篇小说因此具有某种普遍的伦理意义:在新旧文明碰撞之际,是如吉姆佩尔一般秉持传统伦理规范,还是如其乡邻一样摒弃故旧道德规范、顺从崇尚欲望的生活呢?辛格将此伦理困境的主题熔铸于小说之中,让读者在嘲笑他人时也揶揄自嘲,更有深思反省。下文将分两部分阐释这一观点:第一部分运用经典叙事学概念剖析读者如何不知不觉卷入这种伦理困境思索的;第二部分深入阐发伦理困境思索的内涵。
一、叙事距离与伦理困境
这部小说中,叙述者讲述了自己受骗、为人所捉弄的一生。开篇处,叙述者就声明:“我是傻瓜吉姆佩尔。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傻瓜。恰恰相反。”此言运用叙事距离这一叙事策略,瞬间形成两种内涵张力,将读者置于智愚之辩的伦理困境之中。
该叙述者是年迈老翁吉姆佩尔,所叙为往昔故事:从孤儿学童生活,到成年成家、立业立家,再到离家游历,最后感知死期将至。这种时空间距所致的叙事距离令其所述可靠程度一时难断。据美国学者艾伯特(H.P.Abbott)的定义,叙事距离即“叙述者在其所述故事中的参与程度”[4]。老吉姆佩尔临终之际追溯往事,每一件往事的叙述都可能要面对两种拷问:一是年龄增长、阅历叠加,往事有几分得以真实反映?当然这个“真实”,也是很值得探究的事。假设叙述者忠于自己内心的判断,则所述内容就可能存在“历史真实”和“叙述真实”的出入,美国学者依金(P.Eakin)指出,叙述者的身份变易不居……须以一种“更宽泛的、经验主义者的方法分析主体性根源与特征”[5]。美国学者兰瑟(S.S.Lancer)指出,“既定文本或声音的权威性是其社会特征和修辞特点的产物”[6]。老吉姆佩尔记忆中的往事,可能因为岁月冲蚀,是以叙述时的人生观与世界观过滤而成的,无论有心为之还是无意压制,对过往故事的叙述难免纹饰,各种情形的区别只在于各方比例和具体细节的出入,相应甄别自然颇费心神。这是就叙述策略而言,阅读伊始就必须面临的意义空间。二是叙述者提出智愚之辨,不禁让人觉得后续阅读是一场历险:一方是“大家”,另一方是独立抗衡的“我”——真相到底是“被众口铄金了”呢,还是“众人皆醉我独醒”?辩解本身就充满了各种叙述陷阱;辩解的话题又是“是智是愚”,此背景下的一面之词,使得所叙故事细节的真假难辨。这是叙述内容给阅读带来的思辨视野。于是,这种叙述策略与叙述内容的巧妙合作,营造出极强的意蕴“张力”。
所谓“张力”,按照卡登(Cuddon)的说法,是“某些批评家所谓心理与情感诸多影响的平衡,它赋予作品以结构和意蕴空间”[7]。《傻瓜吉姆佩尔》开篇数语形成的张力赋予全文类似辩护词的意味,诱导阅读或阐释始终在“智”与“愚”、“真”与“假”之间游移。
在老吉姆佩尔的叙述中,别人说他傻,因其轻信人、易被愚弄,甚至连婚姻生育等大事,亦是如此。但事实上,这都是源于吉姆佩尔不愿意与别人计较。因为“敢说一句不相信”,人们就会“勃然大怒”[8]3-14。选择相信他们,他人得到快乐,吉姆佩尔自己多些安宁,这是吉姆佩尔既往处理方式。他人包括妻子在婚育等问题上欺他、伤他,他以圣书的教导安顿自己的心;就算亲眼见到妻子偷情,也因对孩子——实则为其妻偷情他人所生——的怜爱而不顾亲眼所见,替妻子开脱,“也许我看到的是幻象”;妻子临死吐露生育真相,他依循圣书给她的一生盖棺论定:“我欺骗了吉姆佩尔,这就是我短短一生的意义。”吉姆佩尔靠信仰而活,即便是丧妻后魔鬼来诱惑他报复骗人者,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尔后选择流浪。他发现,“实际上是没有谎言的”。一切迹象表明,吉姆佩尔是因为信仰和善良、因为相信世上有无限的可能,才被利用被欺骗的,这印证了开篇的那句话:“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傻瓜。”
叙述者言辞逻辑清晰,辩解似乎很成功。首先,基本可以肯定其所述属实,至少以他年迈后的心智来看,所述皆事实;若有掩饰杜撰成分,此行为本身就说明他至少不如世人想象那么愚蠢。其次,吉姆佩尔能在谎言欺骗的环境里生活20多年而不怨天尤人、不行报复,因其遵循圣书,以圣书指导生活,内有圣人教诲支持引导;实在迷惑时,还有拉比可以咨询。他相信“肩膀是上帝造的,负担也是上帝给的”“好人靠信念生活”。
然则,此结论值得推敲。设想:若所述为真,则叙述者所说两个细节颇为耐人寻味。其一:初次撞破妻子偷情时,吉姆佩尔的反应是怕惊醒孩子,然后回到面包房,躺在面包袋上一夜哆嗦到天亮。处理方式如此反常,恐怕少有人敢说其正常,只是因为太爱孩子才有如此举措吧?若读者认为吉姆佩尔有近圣者心态,才会如此处事,那么吉姆佩尔自述彼时心绪便值得玩味了:“哎,我讨厌这种鼾声!我讨厌透了。”妻子偷情,他还“讨厌”,可见非圣人;仅“讨厌”,说明他心理确实与众不同——世人眼里此即是“傻”。但是,似乎不能因此断定他之愚蠢,因为他很清楚,“换个人处在我的地位就要叫嚷起来,足够把全镇的人都吵醒”。显然他知道应有的反应是什么。这个细节引得人们思考:“需重新界定‘愚蠢’吗?”但吉姆佩尔随即否定了这个必要:“我蠢驴当够了”“吉姆佩尔不会终生做一个笨蛋的。即使是吉姆佩尔这样的傻瓜,他的愚蠢也有个限度。”多少读者会认为这是个傻瓜呢?但他思考后,又“求教”拉比。聪明人会这么做吗?细节之二:吉姆佩尔老了,“越来越懂得实际上是没有谎言的”,其理由居然是“现实中没有的事情晚上会在梦里遇见……如果来年不遇到,也许过了一世纪会遇到。这有什么区别呢?”正常人大概不会混淆梦境和现实,以幻想为当下处事的圭臬吧?
总之,小说开篇简短数语构建的意蕴张力形成的阐释空间耐人寻味:吉姆佩尔是智还是愚?
二、流浪的吉姆佩尔:伦理困境中的你、我、他
小说结尾处有个细节问题值得深思,即吉姆佩尔为何散尽财产、离家流浪?真如他对乡邻所说“去见见世面”吗?如此含蓄,似乎一反前文直率的风格。若审视其流浪经历,可见其心理世界已变。要明了其因由,则不能不关注一个事实:此时的叙述者和现实作者的精神距离应该是最近的——二者之间还有一个隐含作者。根据中国学者申丹的论断,“‘隐含作者’就是处于某种创造状态、以某种方式写作的作者(即作者的‘第二自我’)……是文本‘隐含’的供读者推导的写作者形象”[9]。换言之,隐含作者身上承载了现实作者对自己文化传统的执着和困惑。此处如何?
吉姆佩尔舍家弃业、流浪远方时,恐怕未曾意识到自身的重大变化:他已从依顺传统转向求证。转捩点出现在妻子葬礼后,吉姆佩尔拒绝了魔鬼的报复乡邻的诱惑。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妻子临终前忏悔:自己有“一大批”情人,“这些孩子都不是你的”。此话“不亚于当头一棒”,可他依然寻得理由安抚自己。他将妻子嘴角残留的“一丝微笑”解读为“我欺骗了吉姆佩尔,这就是我短短一生的意义”。此解读或是误解。其妻嘴角那一丝微笑也许并不存在,因为是“一丝”,微小易误判:听到忏悔后心神震荡,未必能准确捕捉到。或许其妻的“微笑”更像临终忏悔后的一丝解脱与轻松。思及此点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是对他坚信的圣书教诲的验证。但是,当他认为这“一丝微笑”里尚存妻子对后人的警示时,其内心已经失衡或存怨愤:骗人者终得惩罚,其人生唯一的意义只是欺骗了坚信传统的聪明的善良者。这种不平衡迅速化为诱惑他报复乡邻的魔鬼:没有上帝,也没有来生,他们欺骗了你,你也要欺骗他们;把尿倒进面团里,“让弗拉姆波尔的圣人们吃些脏东西。”吉姆佩尔的信仰居然动摇了,一切照做了。然则梦中妻子劝他:“你这傻瓜!因为我弄虚作假,难道所有的东西也都是假的吗?我从来也骗不了什么人,只骗了自己。”此话与其说是其妻显灵梦里,不如说是他心中执着于传统的那面自我在对抗反传统的冲动。执着传统的自我心存理念:做错了事,是不会得到宽恕的,“踏错一步,我就会永远失去永久的生命”。此次他埋掉了所有面包,拒绝了魔鬼的诱惑。可是,四周皆是欺骗谎言,信仰动摇一次便可能有第二次,虽然亦可最终战胜魔鬼,但人生从此再也不同了。因此吉姆佩尔所谓“见见世面”,是为改变环境,坚定信仰。他希望自己没有在这个镇上生活过,“忘记一个叫吉姆佩尔的人曾经存在过”。
若说此细节不足以证明吉姆佩尔的重大变化,那么不妨审视其叙述方式及此后经历的叙述。此前自我辩解、自证非愚是智时,乡邻针对其行为的任一反应,叙述者都给予解释,直接表露内心想法;显然他是存有陈列事实、让读者判断的心思的。而且,至于后来的流浪见闻,他都集中在证明自己离家前的信仰判断准确无误。可见,他所谓“去见见世面”的字面含义只是他彼时心境的冰山一角。他已经到了欲语还休的地步了。这个回复也许是叙述者有意为之、表明不屑于赘言解释?然则叙述者这种傲慢心态如何突然出现?显然它与叙述者自始至终表现出来的谦恭平和不相符。如此,这个回复也是直陈心意,字面含义就是他内心所思所想的了,因为此时的吉姆佩尔确实乱了方寸,需要走出去。
概言之,吉姆佩尔为了信仰选择流浪,因为信仰滋长的土壤已经坏损;他期望从流浪中获取更多的信仰力量。流浪让其释怀往事:他人的谎言其实是异时异地的真事;现实和梦境也只存在时空错位之别。所以,该世界定式距离真实世界“咫尺之遥”的“幻想的世界”。逻辑如此拼凑牵强,如不是其思维不清——傻,便是其自欺建之逻辑,如此方能身心相安——此可谓聪明了,意在回到精神传统。然而,小说结尾处叙述者自述时又现矛盾:“那儿没有任何纠纷,没有嘲弄,没有欺骗……在那儿,连吉姆佩尔都不会受欺骗。”此前认可的无谎言(即无欺骗)此时又变成了有欺骗。这是否意味着,主人公实则非智是愚?
如此,前文的理解和阐释又值得质疑了。
似智似愚,世人冠之以愚;其实智愚间的距离,恰是传统和当下现状之间的抵牾所在。这种人物在辛格笔下并不鲜见。辛格站在世人角度,赋予笔下人物愚人之名,同时寄托作家在无信仰时代拯救文明的执念。正如他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辞中所说,人们对上帝的信仰不再,也“不相信报应和惩罚”,“连人类自己都不信任”。他认为,若此世道与文明还可救药,那必是幻想文学。“人类处于暗无天日之时,被柏拉图逐出文坛的那个诗人也许会起来拯救我们所有的人”[8]317—319。辛格这个“清醒时做的梦”,恰似吉姆佩尔对真实世界的期盼,坚守信仰、忠于传统让他充满希望;别人眼里的人生灰色,在他眼中是上帝的安排,“肩膀是上帝造的,负担也是上帝给的。”
可是,吉姆佩尔需要流浪,在流浪中坚定信仰,透过这世界的“虚幻”,看到彼岸世界的真实;辛格在写作、“神秘主义者和诗人身上”寻求“慰藉”[8]320;辛格是否旁敲侧击他的读者:咱们呢?
总之,辛格运用巧妙的叙事策略铺陈日常琐屑,将读者们引入一个深邃的话题:当传统与现状抵牾之时,如何生活?也许这是人类永恒的伦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