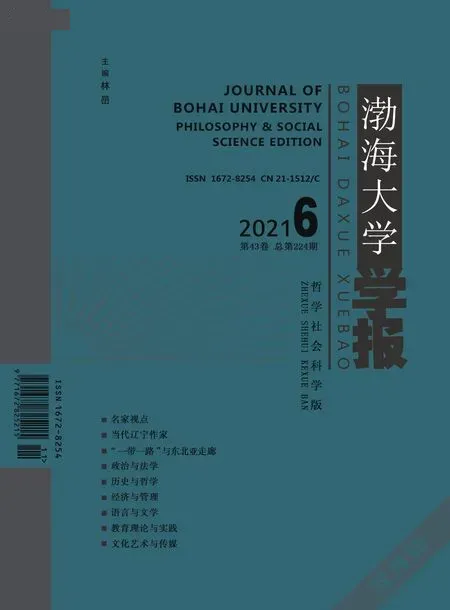“善恶有报”观念与元杂剧复仇精神的伦理正义
李晓一(渤海大学文学院,辽宁锦州121013)
元杂剧作为有元一代文学的代表,反映了广阔驳杂的社会生活,也包蕴着丰富多样的思想观念。其中,“做善事有好报,种恶因得恶果”的观念在元杂剧中得到了大量的表现。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在我国古代出现较早,又与以“劝善化俗”为伦理目的的佛教有着相同的伦理基础。因此在佛教传入后与之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善恶报应”观念,反映出实际社会交往中应当遵循的道德规则。
一、“善恶有报”观念的本土传统
“万事皆有因果”这种观念,在我国古代社会早已有之,这与原始初民尚不成熟的早期思维有关。受“万物有灵”观念的影响,原始社会的人们敬天畏神,对于自然界的种种现象不甚明白,而往往将其与“天”联系在一起,因此这种因果关系带有比较鲜明的神灵色彩。《尚书》[1]《左传》[2]和《韩非子》[3]中都有类似的观点,认为“积善之家”行善事,“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积祸事,“必有余殃”,说明春秋时已产生了与今义基本相同的善恶报应观。墨子也认为天有意志,能“赏善罚暴”,而且善恶报应是具有普适性的,不是只针对平民百姓,即使是天子,也一样要受到上天的监督和赏罚,并分别以“桀纣幽厉”这些不仁之君为例,说明“为不善”必得祸;再以“禹汤文武”这些仁德之君为例,说明“爱人利人”必得福的道理[4],体现出了“善恶报应”观念的平等性,可见在先秦时期这一思想已深入人心。
后世的善恶报应观念也始终不绝如缕,如“积善降福,神明报焉”“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速与来迟”等俗语历代可见,说明人们以这一思想作为对善恶进行选择的依据,依靠这种思想进行道德约束和伦理塑造,已经具有了根深蒂固的传统。
二、“善恶有报”观念的宗教融合
除了我国本土已经具有的“积善余庆”“积恶余殃”等思想外,善恶报应观念与佛教的传入关系密切。有学者指出:“中国佛教要实现劝善化俗的伦理目的,除了教人们明分善恶外,还需以善恶业报轮回的宗教理论与世俗的道德实践相结合,从而使佛教伦理在众生中产生信仰的约束力量。”[5]可见这两种思想有非常接近的伦理基础,因此,善恶果报说自传入我国就与善恶报应思想紧密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善恶报应观念。
在三国东吴时期,康僧会(?—280)曾围绕佛教的善恶果报与孙皓进行辩论,想从我国传统的善恶观角度对佛教的善恶果报理念来理解。东晋时的知名僧人慧远(334—416)认为善恶报应“乃必然之数”,善恶福罪是理所应当、自然而然的事,同时他还强调了在善恶报应问题上,最终应该负起责任的是人,是人自身的与善恶相关的动机和行为,而不是所谓的天神,突出表现出“为仁由己”的观点,反映出他站在佛教立场上,以佛教义理理解和阐述我国本土报应论的思想特色。
慧远的佛教善恶报应论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其与传统的“积善余庆”“积恶余殃”思想可以彼此印证,对儒家伦理的教化功能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南朝梁代萧子显也指出佛教善恶果报论对儒家伦理教化有补充作用:“儒家之教,宪章祖述,引古证今,于学易悟;今树以前因后果,业行交酬,连堞相袭。”[6]北齐的颜之推则确信佛教的善恶报应论:“三世之事,信而有征,家世归心,勿轻慢也。……今人贫贱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业,以此论之,安可不为之作地乎?”[7]可见这一时期的佛教善恶报应论已与当时的社会伦理生活紧密结合,与我国本土的“积善”“积恶”观念也融为一体,使人们意识到个人的行为会带来相应的结果,明白了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的意义和价值。
除佛教外,道教也有自己的善恶报应理论。《太平经》卷三十九载:
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乃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故前为承,后为负也。[8]
道教的这一理论即“承负说”,这一理论强调了“承”与“负”的关系,阐明了前人的行为会对后人产生深远影响,明确了“承前负后”的观点,提醒人们对于善恶行为的选择理应慎重,这与子孙后代的福祸命运联系紧密。可见善恶有报的这种观念一直盛行于我国,并经由儒释道的教义发挥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同,成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伦理观念。
三、元杂剧中的“善恶有报”观念
“善恶有报”这种具有普遍适应性和约束力的观念可以说与我国的戏剧理想不谋而合。“与西方戏剧相比,中国戏剧情节的发展与善恶报应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报应关系总是与道德教化相联系,所以中国人一般都把报应置于教化之中。”[9]在以人情世态为主要描写和表述内容的元杂剧中,出现了大量的善恶有报观念,特别是在讲述复仇故事的元杂剧中,这一观念表现得尤为突出,成了复仇者复仇意志的理论基础和信念支撑。
《窦娥冤》中的窦娥是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她是一个勤劳善良、刚强隐忍的良家女子,她的言行举止、道德品格都完全符合封建社会的道德要求,却因为婆婆引狼入室而身陷牢狱之灾,最后含冤被杀。“窦娥”这个人物形象显然是“善”的,但却遭遇了“恶”的肆意伤害,甚至丢了性命,这看起来并不符合“善恶有报”这一理念,因此剧中的窦娥自己也想不通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遭遇:
【天下乐】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今也波生招祸尤?劝今人早将来世修。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
这一段唱词清楚地表现出窦娥心中的困惑和无奈,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情况下,她把自己的这种人生境遇归结到了善恶报应上,“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今也波生招祸尤?”用这种前世因后世果的理念来自我安慰,以化解心中的委屈,得到心理上的平衡。也正是因为她无法理解自己为善却受恶的命运,才在临死前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呼喊:
【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可见在她看来,天和地是公理正义的评断者,是应该分辨清浊、分辨善恶的,故而,当自己的命运完全与其一贯以来的观念相悖时,她难以遏制心中的愤恨,向天地发出质问:为何“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很显然,这样的结局是窦娥无法接受的,她无奈屈死的结果也与“善恶有报”这一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冲突。但是,故事发展到这里并没有完结,随着她父亲窦天章的出现,窦娥虽已成为鬼魂,还是在父亲的帮助下揭露了张驴儿的种种罪行,使他最终被绳之以法,达到了“善恶有报”的合理结果。如此便使观者明白,好人就算会受到伤害,但坏人也绝不可能逃脱恶报,短暂的取胜并不能改变恶有恶报的命运。
《陈州粜米》中的张撇古也坚信“善恶有报”。朝廷派小衙内和杨金吾来赈灾,两人假公济私、蓄意贪污赈灾钱粮,张撇古揭穿两人阴谋,被恼羞成怒的两人活活打死。张撇古作为“善”的一方,在与“恶”势力的斗争中丢了性命,看起来这场善恶斗争胜败已定,但他却始终认为这些恶人将得到报应:“虽然是输赢输赢无定,也须知报应报应分明。”他对自己弱小受害者的身份有准确的认识,清楚与强大的施恶者之间是无法实现力量等同的,因此对于争斗的结果早有心理预知,但同时,“报应分明”的观念也使他相信,合理的结果可以通过寻找正确途径来实现——他选择的方法便是“拣一个清耿耿明朗朗官人每告整,和那害民的贼徒折证。”并且明确指出,“若要与我陈州百姓除了这害呵,则除是包龙图那个铁面没人情。”可见在张撇古看来,“善恶有报”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真正的实现还是需要有个清官,而包拯就是他在人世间实现“善恶有报”的唯一指望。不过即使包拯也做不到,他还是不会放弃,在死后的幽冥世界中他一样要继续向神灵控诉,要神灵为自己主持公道,“我便死在幽冥,决不忘情,待告神灵,拿到阶庭,取下诏承,偿俺残生,苦恨才平。若不沙则我这双儿鹘鸰也似眼中睛,应不瞑。”他之所以能够如此有勇气去坚持,便是因为坚信“善恶有报”这一传统观念。果然包拯没有让他失望,小衙内和杨金吾两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诸如此类,在许多元杂剧中都可以看到鲜明的“善恶有报”观念。
有的是在故事发展过程中,参与者或故事的讲述者看到事态的变化,不由自主发出的感叹。如《冯玉兰》剧,冯玉兰一家被屠世隆杀害,她一介女流苦痛自怨无力报仇,偏巧遇到个“似青天、如白日、去奸细、理冤枉的大人”,于是大仇得报便是顺理成章之事了,这等巧合连金御史本人也不由感叹“方信道善恶报应,如影随行”。《东窗事犯》剧,秦桧谋害一代忠臣岳飞,地藏王化身呆行者,终将秦桧“剖棺椁剉尸骸”,何宗立不由感慨“恁的呵,恩和仇报的明白”。《蝴蝶梦》剧,王父无端被葛彪打死,王家兄弟又打死了杀害父亲的葛彪,王母慨叹:“似这般逞凶撒泼干行止,无过恃着你有权势、有金资。则道是长街上妆好汉,谁想你血泊内也停尸!正是‘将军着痛箭,还似射人时’。”《救孝子》剧,杨谢祖被诬陷杀害嫂子,王脩然有感于“天地无私,显报如此”,终明察案情,还其清白。《货郎旦》剧,张玉娥、魏邦彦害得李彦和一家妻死子散,最终其子李春郎捉住二人得报大仇,剧本评曰:“又谁知苍天有眼,偏争他来早来迟。到今日冤冤相报,解愁眉顿作欢眉。”《疏者下船》剧,楚昭公逃难汉水之上,先后舍弃妻儿,却始终保全兄弟,后妻儿皆得神明保护平安归来,其弟芈旋由此更加相信“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信不诬也。”
有的是作为受害者坚定心念的思想根基。如《灰阑记》剧,张海棠被大妇诬陷害死丈夫,坚持不认罪,愿与之一同见官,便是因其坚信“可难道天理不昭昭?”再如《荐福碑》剧,张镐无意中得罪龙神,龙神半夜雷轰荐福碑,理由便是“莫瞒天地神只,祸福如同烛影随。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魔合罗》剧,李德昌被兄弟李文道害死,他无力自保,便“托青天暗表,望灵神早报”,只因相信“行善得善,行恶得恶。”《神奴儿》剧,李德云被弟弟、弟媳气死,临死前表示“人间私语,天闻若雷,休言不报也。敢只争来早与来迟”。
有的又成为救助者伸出援手的前提依据。如《还牢末》剧,李荣祖被二妻和奸夫陷害,一家妻死子散,得梁山好汉救出并将害人者“剜心剖腹”后,宋江也表示,正是如此方“显见的天理分明”。《哭存孝》剧,李存孝被李存信和康君立害死,刘夫人明察情由将康、李二人车裂,只为“可与俺李存孝一还一报!”《生金阁》剧,郭成被庞衙内所害,包拯为其申冤,坚信“这场事天教还报你”。《朱砂担》剧王文用被白正谋财害命,东岳太尉立即声明:“便好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若不降严霜,松柏不如蒿草。神灵若不报应,积善不如积恶。”“休将奸狡昧神只,祸福如同烛影随。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果然最后在阴曹地府得到了阎君主持公正,“才见得冤冤相报,方信道天理难容。”再如《赵氏孤儿》剧,韩厥虽“佐于屠岸贾麾下”,却也深知屠岩贾倒行逆施不会有好结果,认为“天也显着个青脸儿不饶人”,“却不道远在儿孙近在身”,由此可见,尽管屠岩贾养了赵氏孤儿二十年,还是免不了被他“身首分张”。
还有的则是在故事的开始就已经明确了这一观念,确定了故事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村乐堂》剧,张本一出场就表示“明有祸福相随,暗有鬼神相报”,为后来理清头绪,明断官司埋下了伏笔。《冤家债主》剧更是完全上演了一场善恶报应、因果轮回的戏剧故事,剧中旁观者崔子玉登场便言:“果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同影响,分毫不错,真可畏也。”张善友一家的祸福转变,离合悲欢,一切都是因果报应的结果。赵廷玉偷了他家的五两银子,转世投胎为他的大儿子,辛苦劳作为他攒下万贯家财;他的老婆赖掉和尚的十两银子,和尚便转世投胎为他的二儿子,吃喝嫖赌把他的财产花光散尽。做善事的结果与做坏事的结果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成了“善恶有报”思想的最佳注解。
由此可见,元杂剧中普遍具有“善恶有报”这一观念,不论是受害者、施救人,还是旁观者,大家都坚信善者终将得到认可,恶人定会遭到报应,这才是公理正义的必然表现。尽管这个过程通常颇多周折,并且体现出多样性,但不论遭遇什么困难,人们还是对这一观念坚信不疑,而戏剧故事的发展也的确还是会在得到各种帮助的情况下,再度回归到正常的伦理规范上来,最终实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结果。因而这个观念也成为受到伤害的复仇者捍卫正义、寻求正义最强有力的思想支撑。
四、善恶有报是实现复仇正义的伦理保障
匈牙利学者赫勒指出:“好人应该幸福,因为他们值得幸福;坏人不应该幸福,因为他们不值得幸福。这种观点是伦理的正义概念的基础。因此,从伦理的正义概念的视角来看,一个好人在其中过得幸福而坏人过得不幸福的世界秩序,就是一个正义的社会秩序。”[10]就表现复仇的元杂剧而言,受害者多为良善守法的无辜之人,或是与世无争的平常百姓,如窦娥(《窦娥冤》)、刘玉娘(《魔合罗》)、王文用(《朱砂担》)等,或是赤胆忠心的忠梗之臣,如岳飞(《东窗事犯》)、杨继业(《昊天塔》)、伍奢(《伍员吹箫》)、赵盾(《赵氏孤儿》)等,他们都安于自己的生活,对于自己的社会身份和角色有准确的认识,是社会秩序的正常维护者,也即赫勒所说的“好人”。但就是这样的一些人,却受到外来势力的强硬摧残,使其本来的平顺生活被恶意打乱,这不仅是对受害人本身的伤害,更是对原来的社会秩序的破坏,因此这些施恶者成为整个社会伦理正义的敌对方。这种破坏造成了社会伦理正义的失衡,必然导致受害人心理的极度不平,需要通过某种方式使其回复平衡,复仇便是受害人为实现心理平衡而做出的选择。复仇的具体方式可能是有所差异的,但其追求复仇成功的目的是一致的,并在实现复仇的过程中使伦理正义也得到了实现。
可以对观者起到惩恶扬善的教化作用,是中国戏曲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功能,与复仇相关的元杂剧中表现出“恩怨分明”“善恶有报”等复仇观念,是对“惩恶扬善”教化思想的鲜明体现。古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强调忠孝节义,强调“善”与“美”,元杂剧中的这些复仇者身上则通常都具有为儒家所赞颂的美德,如岳飞的“忠”、伍子胥的“孝”、窦娥的“节”和程婴的“义”等,这些人就是“美”与“善”的代表,是伦理道德中理应受到保护和尊重的对象;但是,他们所代表的“善”与“美”却遭到了恶势力的毁灭,这必然使观者情绪郁结,充满强烈的悲愤之感。这种心理上的苦闷与压抑在表现复仇的元杂剧中得到了释放。在复仇相关剧目中,我们看到,尽管好人往往会受到恶人的伤害,但这些施恶者最终也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善与恶的伦理评判中,通过受害一方的复仇行为,使善和正义得到了最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