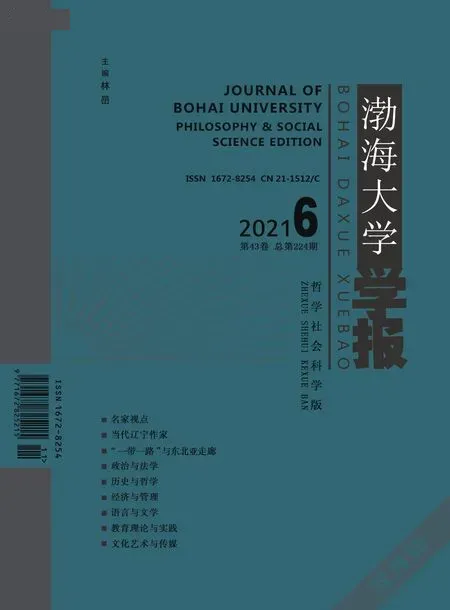个体生命的关注与表达
——马晓丽中短篇小说论
高小弘 李芷一(.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辽宁大连6063;.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608)
提起马晓丽,大部分批评家与读者都会第一时间为她贴上“军旅作家”的标签,的确,凭借着真实而丰富的军队体验与纯熟的小说技巧,马晓丽的许多军旅题材作品倍受欢迎,并多次获得国内的各项文学奖项。然而,如果只用书写题材来框定一个作家及其作品就太简单和笼统了。马晓丽不仅是一位“军旅作家”,她更是一位关注个体生命的作家,人的生存状态永远是马晓丽想要探讨的主题。从某种程度上说,也许军队只是马晓丽熟悉的一个场域,而个体如何存在其实才是马晓丽始终关注的中心。马晓丽始终在追随着个体的生命历程,坚守着个体的理想。她始终在用笔去探测个体生存的冷暖,去捍卫个体的个性与尊严。
一
马晓丽曾经当过炊事员、话务员、通讯员、护理员、护士、干事,女兵可能去的岗位她几乎都去过。作为军队中一名有着丰富经历的个体,马晓丽自然也有了更多关注其他个体的机会与视角。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宏大叙事,透过军队这一复杂而特殊的环境,马晓丽始终在观察形形色色个体在其中不同的生存境遇。
在军队这样一个特殊环境中,死亡如影随形,而面对死亡展现出大无畏精神甚至主动迎上前去的人便成了“英雄”,“几乎所有的经典军旅小说作品都是以培植英雄为其意旨”[1],描写英雄人物可以说是军旅文学的传统。马晓丽的军旅题材的小说中也有英雄,但与传统不同的是,马晓丽并没有将英雄神圣化,而是将其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体去观照。在2000年的短篇小说《舵链》中,马晓丽描写了登陆艇上一个普通的士兵,他身为党员,主动冒着生命危险爬过结满冰的舱盖去抢修舵链,最终拯救了整个登陆艇,无疑是一个英雄。在小说快结尾时,马晓丽揭露了这位英雄内心的真实感受,在九死一生的绝境面前,他也曾想起自己的亲人,也曾害怕。在军队这样一个经常面对死亡的环境中,这是一种真实的心理。但个体之所以能成为英雄,不是因为无所畏惧,正是因为个体为了某种理想和信念能够抛弃心中的畏惧。在“我”问这位士兵为什么害怕还坚持上的时候,他认真地说:“我和班长肯定得上一个,明摆着,我们班就我俩是党员。”在这位普通的士兵决定抛弃心中的恐惧,为了整船人的性命,为了党性去拼命的那一瞬间,他已经成为一名英雄。而马晓丽正是在部队这样一个特殊环境中,重新审视成为英雄的“个体”,她聚焦个体的真实内心,描绘出个体生命历程的一种自我超越。
在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代表作《俄罗斯陆军腰带》中,马晓丽对个体生命的关注表现得更加明显和深刻。这篇小说讲述了秦冲领导的中国军队与鲍里斯领导的俄罗斯军队一起守卫中俄国境线及进行中俄联合军事演习时两个连队之间的交往。在小说中,马晓丽以中国军队中校秦冲的视角叙述了中俄部队的种种不同,跟随秦冲的视角,我们能看到马晓丽聚焦的重点仍然是在中俄军队中士兵个体生存境遇的差异,作家的笔触深入中俄军队双方吃穿住行的各个方面。而小说中中俄双方三次交换腰带则是双方差异碰撞的隐喻。
这三次交换腰带的过程结果各不相同,耐人寻味。发生时间最早的第一次交换腰带出现在秦冲的回忆中,那是一场十分剧烈的冲突。当时两名军官各自对自己手下偷偷交换腰带的士兵发出了怒吼。鲍里斯更是当着秦冲的面用那条俄罗斯陆军腰带暴虐地将自己的兵打到流血,而秦冲因为看不惯鲍里斯的暴虐冲上去与他扭打在一起。之后随着秦冲的回忆中断,此时出现的正是第二次,情景与第一次如出一辙,但是秦冲和鲍里斯却都悄悄地改变了。双方都没有发火,甚至鲍里斯还冲秦冲微微笑了一下,表示支持士兵的交换。但秦冲始终没有说话。而第三次交换腰带出现在小说结尾,并没有发生在双方的士兵之间,就发生在秦冲和鲍里斯之间。这是三次之中唯一一次最终双方真正交换了腰带。秦冲抽下自己的腰带,突然觉出它一直存在而差点被自己忽略的好;而在拿到那条自己一直喜欢的俄罗斯陆军腰带往腰上扎的时候,“秦冲才觉出有些不方便,两个钉眼不是一下就能找准,皮质也显得过于粗硬了些。但这腰带系在身上真的很妥帖,很紧实,很有束缚感”。此时身为军队中的个体,系着俄军腰带的秦冲更深刻地理解了“两个军队就像两个完全不同的家庭,各家有各家的生活方式”,终于可以放平心态从容地对待中俄双方军队的差异。所以,在小说的最后,秦冲的神经性皮炎——小说中由于双方差异造成秦冲心理刺激的一种具象化表现——“竟奇迹般地好了”。可以说,小说题目的那条腰带,串联起的是军队中个体逐渐接纳自身与他者差异的一段心灵史。
在马晓丽笔下,军队中的个体也并非总在炮火连天中面对生与死的考验,在暗流涌动的军队机关部门中的个体生存未必比前者容易多少。《白楼》就讲述了在军队机关“白楼”中的个体生存百态。主人公陆阳是白楼里宣传处的干事,对白楼怀有真正的热爱,曾经怀有这样的理想:如果掌握了这座白楼,哪怕只是一部分,他就会“把白楼竖在战士的心上,而不是立在战士的头上”。但当陆阳身处白楼之中时,他看到一些人逐渐偏离了初心,比如直接被处分离开白楼的曲光、抛弃自己原来价值观委曲求全的冯处长、到处钻营的刘贵田,甚至他自己也曾心灰意冷过。马晓丽在这篇小说中要探讨的是个体应该如何自处。德国哲学家齐美尔认为:“只有超越社会束缚才能得到真正道德的个体”[2],但这种超越“并不意味着一种离群索居式的孤立,而是将道德的基点放在个体生命自身,在个体的一次次自决中活出个人作为应该的生命。”[2](78)主人公陆阳在彷徨后,仍然选择坚守自己的人格,实现了个体的超越,最后他的结局也理所应当地显示出了一些亮色。马晓丽在结尾写道:“白楼仍坚实地伫立着,带着那些高层建筑所无法类比的独特的魅力,带着那种与生俱来的威严。”陆阳这样坚守初心的个体,正是白楼真正的象征。
二
马晓丽曾在访谈中说过:“在我看来,无论生存在哪一种环境中的人,大多数都是有生存困境的……你要用一种什么样的眼光去关照人的生存困境,尤其是精神困境,我觉得这应该是作家应该思考的。”[3]马晓丽不仅关注着外部环境下个体的生存境遇,而且将自己的写作视角深入到人的“内宇宙”,思考着个体精神与心灵的分裂与重构,尤其是《夜》《云端》《杀猪的女兵》这几篇小说,体现了其写作的深度和广度。
《夜》是马晓丽的处女作,描写了护校毕业的女主人公的故事。随着境遇的变化,女主人公做出不同的选择,人生道路也随之辗转于护校、集训基地、战场之间。在夜行火车上,女主人公与一个神秘的小女孩相遇,在小女孩的目光注视下,女主人公“感到如被扒光衣服检查般的窘迫”,而小女孩像知道女主人公的思维活动一样与女主人公进行对话。小说中这位神秘的小女孩是一个符号化的形象,象征着女主人公另一个纯真的、未经世事污染的自我,她对女主人公的注视是一个自我对另一个自我的审视,她与女主人公之间的对话是一个自我对另一个自我的发问,整篇小说则是女主人公的一次精神之旅。马晓丽小说中的两个自我的镜像结构,对自我心灵探寻的主题,在这篇《夜》中都可以找到源头。
《云端》被马晓丽评为“自己写得最好的一篇小说”[4],描写了革命和战争背景下两个同叫“云端”的女性之间的纠葛和命运。小说中的两位女主人公同样呈现出一种镜像对称的结构,无论是她们的名字、所处的立场,以及她们各自男人的性格和相处方式,都是相对的。其实剥开小说中时代、政治等因素,小说所聚焦的仍然是个体的分裂,而云端和洪潮其实都是分裂的碎片,都是不完全的自我主体。云端有着女性天生的柔情,但却依附于男性丧失了独立性;洪潮则锤炼出刚硬、强大的独立性格,却压抑了女性柔软的特质。而小说刚开始时出现的那个“云端”其实才是真正的自我主体,但她只在小说开头的出生与结尾的即将自杀之时出现过,除此之外一直处于“失语”的状态。身为俘虏的云端与革命战士洪潮其实是自我分裂出的两个极端,是自我照镜显现出的两个“镜像”。而这“镜像”并不是真正的自我,是经过他人认知而确立的形象。“镜子是一个绝境,而不是一种反映”[5]。在小说中,云端是由曾子卿塑造的;洪潮是由以主任为代表的革命话语塑造的,那么真正的自我何在呢?正如拉康所说,自我“总是在别处”[6],总是处于与镜像永恒的矛盾中,从而造成了自我的永恒分裂,而这种二律背反式的分裂却是人永远无法逃脱的精神困境。
马晓丽同样探讨个体内在心灵精神困境的作品还有《杀猪的女兵》。如果说《云端》展示的是个体的分裂,那么《杀猪的女兵》强调的则是个体由分裂而导致的异化。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对杀猪从极度恐惧到迷恋,再到掩盖、逃避这段过去,却依然没能逃离,最终因为怀疑丈夫发现了她过去的秘密而在恍惚中用刀捅了丈夫,却被告知丈夫其实并不知道她杀猪的过去。在小说中我们发现,女主人公每一次的转变其实都是由他人决定的:女主人公第一次杀猪是因为班长说了对女性有偏见的话,之后继续迷恋杀猪是因为大家给予的关注和荣誉,没有听班长的劝告而继续杀猪是因为想得到组织干事的爱情;而拒绝杀猪与隐瞒逃避这段过去是因为害怕他人心底的偏见,最终再次举起了刀子也是以为丈夫知道了自己的过去。让女主人公逃离不开的梦魇从表面上看是杀猪的过去,其实本质上是女主人公的自我与他人病态的关系。萨特认为,他人即地狱。自我无法避免成为他人凝视的对象,并在他人的凝视中被对象化、被异化。在小说中,他人围观女主人公杀猪的描写多次出现:
人群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
她知道此刻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她,……
一见她出现了,周围观摩的人群立刻就安静了下来。她知道,此刻所有的眼睛都在注视着自己,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
她听见周围观摩的人群安静下来了,她知道现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自己的身上来了。
在他人的凝视中,女主人公不再有了自我存在的主体性,只是一个“杀猪的女兵”,就如同上文《云端》中“云端”的两个镜像一般。但《杀猪的女兵》中的女主人公显然将他者塑造的镜像当成了真正的自我。组织干事因为偏见的心理原因总觉得女主人公“手上有股子味儿,腥蚝蚝的”,女主人公因此就落下了频繁洗手的强迫症。她过于被这样虚幻的镜像影响而使真正的自我主体异化,从而陷入了真正的“地狱”之中。而实际上,他人是否是“地狱”有很大一部分也取决于自我,“‘他人就是地狱’(即他人使一个人的自由异化)的成分不可能完全消除,但可以尽量减少。这要视一个人自身的努力而定”[7]。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正是自己一步步走向了他人的“地狱”。
三
马晓丽曾在访谈中说过:“作家是要有一种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和一种普遍悲悯的情怀。”[3](151)马晓丽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从未停止,发表于2018年的《陈志国的今生》与发表于2019年的《手臂上的蓝玫瑰》将场景转换到了日常生活中,但不变的是马晓丽对卑微个体的关注。或者不妨说,正是因为对个体生命的关注,马晓丽才没有将自己局限于军旅题材,而是将目光投放到更广阔的日常生活,去关注芸芸众生。正如尼采所说:“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8]而在这样的转向中,马晓丽的写作也在升华。外部环境中艰难的生存境遇与内心分裂异化的精神困境固然是个体卑微的底色,然而在这样的卑微中,马晓丽发掘出了人性的闪光。
《陈志国的今生》讲述了一条名叫陈志国的狗的故事。被“我”领养的陈志国,外表漂亮实际却“满身毛病、一肚子坏心眼儿”,具体表现有不喜欢被无端骚扰、坚决要求在大床睡觉、在家里与人争地位等等。如果得不到满足,陈志国就千方百计地抗争发泄。后来陈志国被“我”送走,在经历了别人的粗暴对待后,再被接回来时陈志国已经变得低眉顺眼、小心翼翼,最终双目失明,逐渐衰老而死。作为一条狗,陈志国的地位是卑微的,实际上,陈志国连抗争的权利都没有。但它却一直努力抗争,执着追求着与人类平等的尊严,即使后来因为抗争它付出了巨大代价,它还是那么“向往外面那个给他带来无可挽回的伤害的世界”。在整篇小说中,马晓丽从未直接点明陈志国是一条狗,而是像称呼人一样称呼名字,因为这样的陈志国其实可以是在生活中挣扎的每一个个体。我们能看到个体的卑微渺小,更能看到个体在与整个世界抗争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与坚韧。就像马晓丽在创作谈《所有的卑微》中所说的:“……对陈志国来说结果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以卑微之躯一直在与这个世界、与自己较劲。重要的是他以一己之力,一直在为改变自己的身份、处境、地位而不懈努力。陈志国让我看到了卑微生命的无奈与无望,不甘和不屈。”[9]这种由无奈无望诞生出的不甘与不屈,正是个体在卑微中闪现的光芒。而这种光芒甚至可以净化和升华另一个个体的心灵。小说中的“我”在经历了陈志国的抗争之后也发生了改变:“我”对生命的感觉变得不一样,开始同情人类以外的其他族群,并为他们的弱小无助流泪。这是作家在小说中流露出的生命意识,这是从马晓丽前期的小说一直贯彻至今的。这种生命意识是对所有卑微的个体,无论自己还是他人,无论人类还是其他物种,都给予平等与尊重、体恤与悲悯。这种境界正如宗白华所说:“……全宇宙就是一个大同情的社会组织,什么星呀、月呀、云呀、水呀、禽兽呀、草木呀,都是一个同情社会中间的眷属。”[10]而在这种境界中,“极高的美感”[10](101)才得以产生,文学才得以产生。
马晓丽的另一日常生活题材作品《手臂上的蓝玫瑰》同样塑造了一个卑微的个体,如果说《陈志国的今生》中的陈志国是一直在与这个世界抗争,那么《手臂上的蓝玫瑰》中的大华则是一直努力去与这个世界和解,去爱这个世界。主人公大华是一个做家政的钟点工,人生充满了阴霾。充满仇恨的母亲、软弱又龌龊的父亲、痴傻的大姐、自私精明的二姐及极度抠门的丈夫构成了她沉重的日常生活。大华将自己的雇主舒姐当作知心朋友,向其倾诉痛苦,不料却发现舒姐表面上善解人意实际却只是将她看作活的写作素材。面对种种不如意,大华虽然抱怨,虽然咒骂,但是她还是尽自己所能真诚地帮助周围的亲人;对于舒姐,她虽然感到无比伤心,却还是没有直接挑明,而是在离开时找了个让双方都体面的借口。总之,就像马晓丽所说,大华是“在无爱的荒蛮之地用力去爱”[11],哪怕“爱得伤痕累累、筋疲力尽”[11](90)。
而自大华内心源源不断产生的爱正是温暖别人,同时也温暖和支撑自己走下去的炬火。如同鲁迅所说:“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12]。在作家笔下,大华的火炬最终也点亮了她周围的世界。虽然人心终究有隔膜,但是在结尾大华陷入迷茫的时候,一向吝啬的丈夫改锥却改变了,同样用爱去陪伴她、鼓励她。马晓丽一直无法理解大华如何能始终保持爱的能力,我们也同样无法理解大华丈夫的改变。但也许我们无须去理解,因为每一个个体都是复杂的、多面的,但无论个体的内心多么幽深莫测,总有闪光。除了互相残杀的兽性之外,还有爱众人的神性,这才是真实的人。由此可以说,马晓丽的这篇作品是由个体出发对人性的赞美,这在当下是很难得的。曹文轩曾经批评“现代形态的文学……将文学带进了冷漠甚至是冷酷……使文学失去了古典的温馨与温暖”[13],而马晓丽的作品,却给予了我们久违的爱与温暖,就像大华手臂上的蓝玫瑰,长在伤疤上,但这些花在阳光下绽放着,闪着耀眼的光,这是人性的闪光,也是蕴含着“真善美”的文学的闪光。
从马晓丽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作家,马晓丽一直在改变,她一直在不断变换角度,转变视角,寻求创新与突破;但始终不变的是她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对现实生活介入的热情。正如秘鲁文学家略萨所说:“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应该坚决、彻底和深入,永远保持这样的行动热情——如同堂吉诃德那样挺起长矛冲向风车,……尽管这样的行动是幻想性质的,是通过主观、想象、非历史的方式进行的,可是最终会在现实世界,即有血有肉的人们的生活里,产生长期的精神效果。”[14]是的,作为读者的我们已经领略到马晓丽带给我们的充满惊喜与感动的风景,而马晓丽的创作之路仍在继续,我们相信,这将会是一趟越来越精彩的文学旅程。